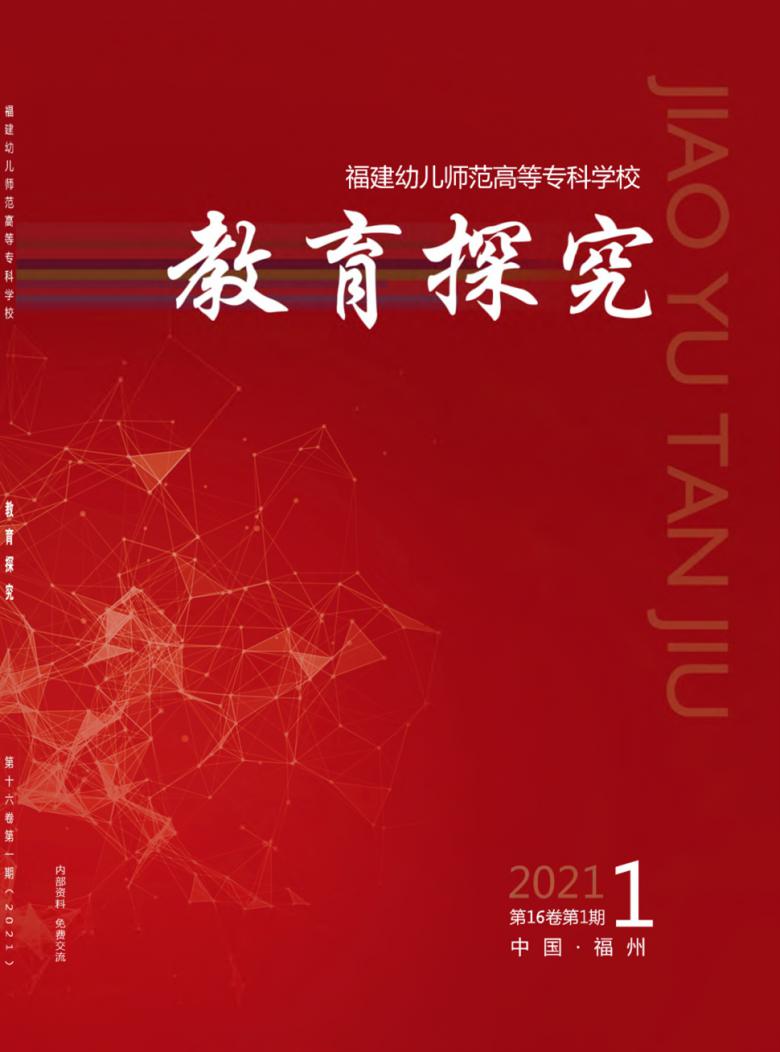試論唐代的州縣關系
佚名
唐代,與州級發生關系的行政單位除了向上的中央朝廷、總管府、都督府、都護府、道之外,還有向下的縣級。唐代在地方行政區劃上,前期實行州縣二級制,后期演變為道州縣三級制,但無論是前期還是后期,以州統縣的地方行政區劃是始終不變的。唐史學界在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甚豐,而對于州縣關系問題的研究卻略顯不足,故本文將對涉及唐代州縣關系的幾個主要問題,略抒己見,以求教于方家。
一、引言
唐代州縣之間最明確的關系是以州統縣,雖然有唐一代,地方行政區劃的級別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無論是前期的州縣二級制,還是后期的道州縣三級制,(注:參見郭鋒《唐代道制改革與三級制地方行政體制的形成》,《歷史研究》2002年第6期。)而且州還曾經在玄宗天寶年間一度改為郡,而以州統縣的這一行政關系卻是始終沒有改變的。
如果從不同的角度分析,這種以州統縣的關系應該包含兩層涵義。其一是從地域的角度講,以一州統屬數縣,由數縣而組成一州;其二是從行政的角度講,即州與縣之間是上級與下級的行政統屬關系。韓愈《送許郢州序》曰:“縣之于州,猶州之于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注:[唐]韓愈撰:《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頁。)韓愈之語,明確地闡明了唐代州與縣之間的行政關系是上下級的行政統屬關系。
唐代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中央政府為了便于對地方進行管理,賦予了州級對縣級的領導權,州級可以秉承中央的旨意對縣級的施政實施領導,而縣級行政機關必須接受它的上級行政機關州級的領導,不僅要對它所轄行政區域負責,同時還必須對它的上級行政機關州級負責。縣級行政機關必須執行上級州級行政機關的決議和命令,辦理州級交辦的相應事宜,并接受州級的監督。
由中央下達到地方的各種詔令,也都要通過州級下達到縣級,再由縣級通過各個下級機構傳達到百姓。唐代公文運作的方式多樣,《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冊、令、教、符。注:天子曰制,曰敕,曰冊。皇太子曰令。親王、公主曰教。尚書省下于州,州下于縣,縣下于鄉,皆曰符。”可知,州下到縣的公文稱“符”,體現了一種自上而下的關系。
關于“符”的格式,《唐開元公式令》保留了尚書省下諸寺的符式,州下到縣的符式亦當按此格式。(注:P.2819,圖版見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365頁。錄文見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21-228頁。仁井田陞:《唐令拾遺·公式令》,東京大學出版會1933年版,第558-559頁。)雖然目前還沒有發現唐代州下縣的符式,但宋人謝深甫等撰的《慶元條法事類》卷一六《文書門一》中卻保留有州下到縣符式的具體格式。
符
某州
某事云云
某處主者云云符到奉行
年月日下
吏人姓名
具官(止書差遣帖式準此)書字
州下屬縣用此式本判官壹員書字(注:[宋]謝深甫等:《慶元條法事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235頁。)
這一符式,當為沿襲唐代符式而來,可以視為唐代州下縣符式的模板。
同時,縣級的各種事務和情報,也都要先上報統轄它的州級,進而再經過其他途徑上達中央。《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凡下之所以達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狀、箋、啟、牒、辭。注: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為狀。箋、啟于皇太子,然于其長亦為之,非公文所施。九品已上公文皆曰牒。庶人言曰辭。”可知,縣上到州的公文稱“狀”或“牒”(注:盧向前先生通過對敦煌文書的考察,認為“上施下”、“下達上”都可以使用“牒”的形式。見盧向前:《牒式及其處理程式的探討——唐公式文研究》,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3輯,中華書局1986年版。),這又體現出一種自下而上的關系。
唐代州縣間就是通過各種自上而下的“符”(注:州下縣“符”的例子,如《朝野僉載》卷四:“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妒。嵩在廳會客飲,召女奴歌。閻被發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為嵩作考詞云:‘婦強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見任。”這段史料的最后一句“省符,解見任”,即為中央(主要是尚書省吏部)根據州級對縣令所做的考狀,做出了對現任縣令免職的決定,并通過這種“符”的形式,將解任令下達到州級,再由州級下達到縣級,從而完成了詔令的下達程序。)和自下而上的“狀”(注:縣上州“狀”的例子,見《全唐文》卷二二二張說《為留守奏瑞禾杏表》:“臣今月三日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國忠狀,言縣界內霸陵鄉新出慶山南之醴泉,北岸有瑞杏三樹,再葉重花;嘉禾三本,同莖合穗。”亦見《全唐文》卷五四五王顏《進黃帝玉佩表》:“去月二十八日,本縣令房朝靜、縣鎮遏將常憲、專知官軍將杜晏等,同于原上,選地對窟,穿深四尺,得玉石□□是一片。穿時為土工所折,今作四段,有懸佩孔子二。其日縣令所由等狀送到州,臣送觀察使,使牒卻令州司自進。”)或“牒”(注:關于縣上州“牒”,在出土的吐魯番文書中,保存了大量西州諸縣上達西州都督府的牒文,李方先生通過對大量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考證,認為:“顯慶三年西州置都督府后,都督府與西州政府也應是一種合署辦公的關系。”(李方:《唐西州行政體制考論》,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既然西州都督府與西州政府具有合署辦公的關系,那么西州諸縣上達西州都督府的牒文,便可以被認為是上達西州政府的牒文,通過這些牒文可以反映縣級與州級的這種自下達上的行政關系。),將州與縣的行政事務聯系起來。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雖然唐代州縣間的行政關系是“以州統縣”,但縣作為地方的一級行政單位,與州一樣都是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的國家行政機關,都要同時服從于中央政府,對中央政府負責,中央政府對州、縣擁有完全絕對的領導關系。而且縣作為地方行政實體,并不是州級的僚屬機構,有縣令、丞、簿、尉及其下的各級官員設置,可獨立地對所轄區域的各種事務進行管理并行使相應的權力。清人王夫之曾曰:“唐、宋以降,雖有府州以統縣,有稟承稽核之任,而誅賞廢置之權不得而專,縣令皆可自行其意以令其民,于是天下之治亂,生民之生死,惟縣令之仁暴貪廉是視,而縣令之重也甚矣。”(注:[清]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二二,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60頁。)明確指出了以州統縣的相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