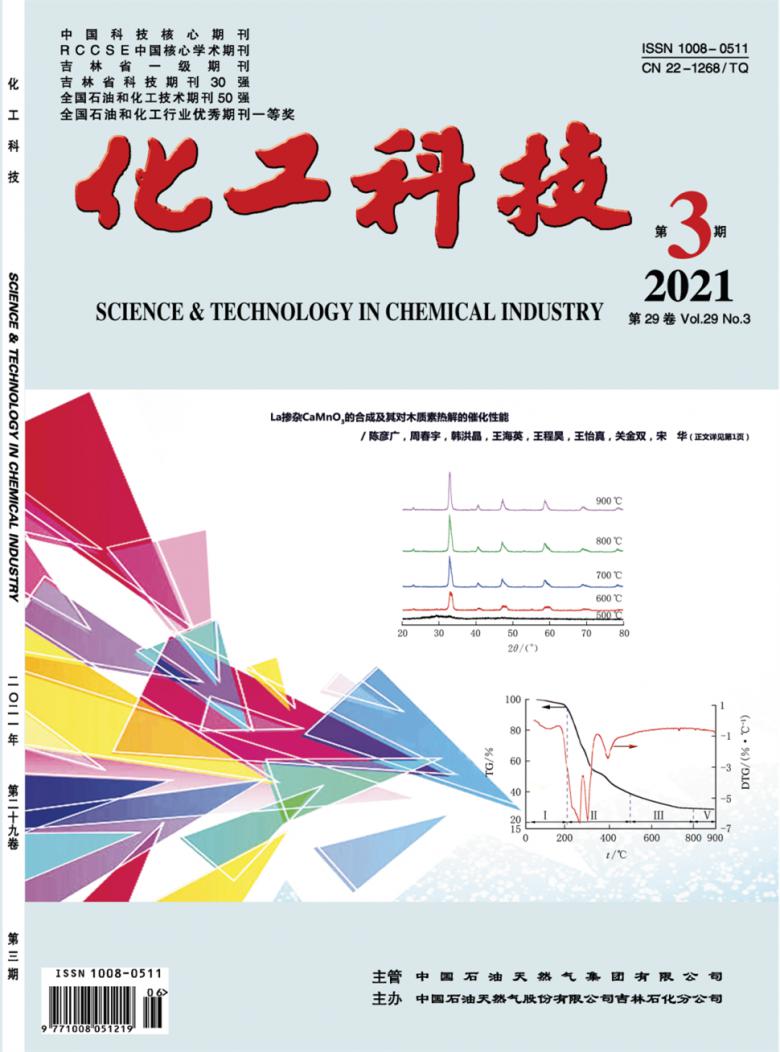唐代“黃坑”辨
佚名
西域胡俗在唐代的傳播,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如胡服、胡食和胡樂、胡舞之類,已有不少論著提及。至于西胡葬俗在當時生活中有何蛛絲馬跡,則缺略,較難探尋。因而,在這方面即使只是提供一些模糊的線索,也有篳路藍縷之功。已故隋唐史專家岑仲勉教授,早在50年代中期,就致力于考察波斯祆教葬俗在唐代的遺存,并舉出如下的例證:
《新唐書》七八《李暠傳》:“太原俗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棄郊飼鳥獸,號其地曰黃坑,有狗數百頭,習食胔,頗為人患,吏不敢禁。暠至,遣捕群狗殺之,申厲禁條,約不再犯,遂革其風。”按此實祆教之習俗,所謂黃坑,西人稱曰無言臺(Silence Tower),至今生息于印度之少數波剌斯(Parsi)人,尚有行之者。唐人目為浮屠法,由于不辨外教之原委也。當日祆教之分布,觀此可得其一臠。[1]
仲勉先生關于唐代太原“黃坑”宗教屬性的判斷,用的是以后證前、以印證中的。由于缺乏共時性的論據,令人看不出在當日河東地區的宗教歷史環境中為何會產生一個祆教殯葬文化的“孤島”。所謂“無言臺”的制度化和定型化,原是中世紀后期的事,很難想象它會在唐代的興生胡或土生胡中超前出現。至于被八世紀的太原人所染習,就更不可思議了。從學術史方面來看,一貫對“塞表殊族之史事”及胡化現象極其敏感的陳寅恪先生,在三次校讀《新唐書》時對卷七十八《李暠傳》的“黃坑”案,并未察覺到有任何祆教背景。[2]這也許可以看作是無言之言,為后人的辨析工作提供了否定性的默證。
讀了岑、陳二師的著作之后,對“黃坑”究屬何物,蓄疑于心,久未能決。直至近年方略有所悟,發表過如下的淺見:
“以尸棄郊飼鳥獸”,當即玄奘所記“棄林飼獸”的印度式“野葬”,它被太原僧徒(《新唐書》卷七八改作“為浮屠法者”)實行,正是恪尊天竺古法。所謂“黃坑”,可能因尸骨“積年”變色而得名。實即佛徒所說得“棄尸處”(古代印度稱為“尸陁林”),其形制與康國之“院”及祆教之“臺”,是不能等同的。從宗教環境看,太原位于佛教昌盛的河東,當地野葬之俗,大可追溯印度淵源,卻不宜與中亞胡俗附會。[3]
以上辨析,簡略粗疏,雖倡異說而鄙意未申。其后續有所得,也未及補入。現草成專文,意在為唐代“黃坑”進新解,并以此權充一份研習唐史的作業,紀念先師岑仲勉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他生前治學從不自矜,對弟子質疑,是不以為忤的。
一、兩唐書“黃坑”紀事的歧異
唐代“黃坑”案發生于玄宗開元初年,約為公元8世紀20年代。主事者為宗室李暠,時任太原尹,并充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有關的紀事,兩唐書詳略不同。為便于比較,先轉錄全文,然后兩個文本的歧異之點。
(一)《舊唐書》卷112云:
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為業,及死不殮,但以尸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為“黃坑”。側有餓狗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禮憲,期不再犯,發兵捕殺群狗,其風遂革。
(二)《新唐書》卷78云:
太原俗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棄郊飼鳥獸,號其地曰“黃坑”。有狗數百頭,習食胔,頗為人患,吏不敢禁。暠至,遣捕群狗殺之,申厲禁條,約不再犯,遂革其風。
在歷代正史中,《新唐書》號稱“良史”,以其“事增于前,文省于舊”見長,往往能刪去《舊唐書》的蕪詞而補其未備,但也難免因筆削而有改變文義的毛病。[4]從上引的“黃坑”紀事看,大同之外的小異是值得注意的。尤其人、坑、狗三項易滋誤會,應予詳辨。
第一,按《舊唐書》記述,“以尸送近郊以飼鳥獸”的“舊俗”實為僧俗,長期被“以習禪為業”的職業佛徒所奉行。《新唐書》改作“為浮屠法者”,把特定的指標一般化,這樣便容易誤導出唐人不辨祆、佛的猜想。 第二,“黃坑”之稱,原是近郊“土人”因僧徒棄尸其地“積年”而起的土名,經《新唐書》縮寫后,文義一變而成太原為浮屠法者對該地的專稱。如果對這個名稱的成因不加明辨,忽視尸體與泥土接觸乃祆教之大忌,反而去聯想華夏“黃泉”之說,就未免失于求之過深,近乎穿鑿了。 第三,覓食于“黃坑”之側的近千頭狗,《舊唐書》明確指出是“餓狗”,除食死人肉外,還侵害幼弱,因此才觸發李暠的厲禁。如果按《新唐書》那樣只說是“有狗數百頭”,則這群烏合之狗與祆教專用之狗,就容易混為一談了。難怪岑仲勉先生會作出“當日祆教之分布,觀此可得其一臠”的推測。
在分辨兩唐書有關“黃坑”紀事的歧異之后,可以說據《新唐書》而斷言其為祆教葬俗,疑點甚多。即使按《舊唐書》立論,理由也不充分。為了進一步探明真相,在文本的對比之后,不妨再作事物的對比,看一看太原僧的“黃坑”與九姓胡的“別院”究竟有什么區別。
二、太原“黃坑”與康國“別院”
唐代九姓胡在大食征服(8世紀中期)前是祆教流行區。據慧超于8世紀初記述,“此六國(安、曹、史、石騾、米、康)總事火祆,不識佛法。”[5]當地的祆教信仰,據《新唐書·波斯傳》,可知其歷史淵源:“西域諸胡受其法以祠祆。”在這個火祆教的故鄉,相應的葬俗獨具一格:“死者多棄尸于山,一月理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為不凈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隨著祆教的傳播,波斯胡的葬俗也被九姓胡所仿行,康國“別院”即其翻版:
國城外別有二百余戶,專知喪事。別筑一院,院內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內,令狗食人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6]
很明顯,康國“別院”與太原“黃坑”是兩種大異其趣的喪葬模式。前者有辦理喪葬之事的專業戶,履行養狗食尸的職能,相當于波斯的“不凈人”,并非太原郊外那種被狗侵害的“土人”。其次,與太原“黃坑”側那群“餓狗”不同,康國“專知喪事”者所養之狗,是拜火教徒的圣物。對此,19世紀德國著名家費爾巴哈已作過精確的闡釋:
狗,在拜火教徒看來,是一種能服務的忠誠動物,所以拿來當作一種行善的(因此是神圣的)東西在禱辭中稱頌;它誠然是一個產物,并不由它自己、憑它自己而成為它之所以為它。可是同時卻只是狗自身,是這個生物,而不是別的,才具有那些值得崇拜的特點。[7]
關于狗的神性,波斯古經《阿維斯塔》的《驅邪典》(音譯《萬迪達德》)第十三章公然宣稱:“世界賴狗的理智而維持存在。”[8]對8世紀的唐人來說,無論是“發兵捕殺群狗”的太原尹,還是為浮屠法者或太原近郊的“土人”,這樣的人狗關系,無異天方夜談,是完全不可思議的。最后,還有一點應該指出,即“黃坑”非“院”,它只是一處郊野,無任何建筑設施可言。其所以被稱為“黃”,或因土色帶黃,或因尸骨“積年”變色,決不會是禮儀性的雅名。因此,也就不必去追溯古典詩歌里“黃壚”和“黃坡”之類的墳墓別稱了。[9] 如前所述,岑仲勉先生還認為:“所謂黃坑,西人稱曰無言臺,至今生息于印度的少數波剌斯人,尚有行之者。”因此,在比較過唐代康國“別院”之后,還應該看看清朝人在孟買所見的“無言臺”,其形制與“黃坑”有無近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