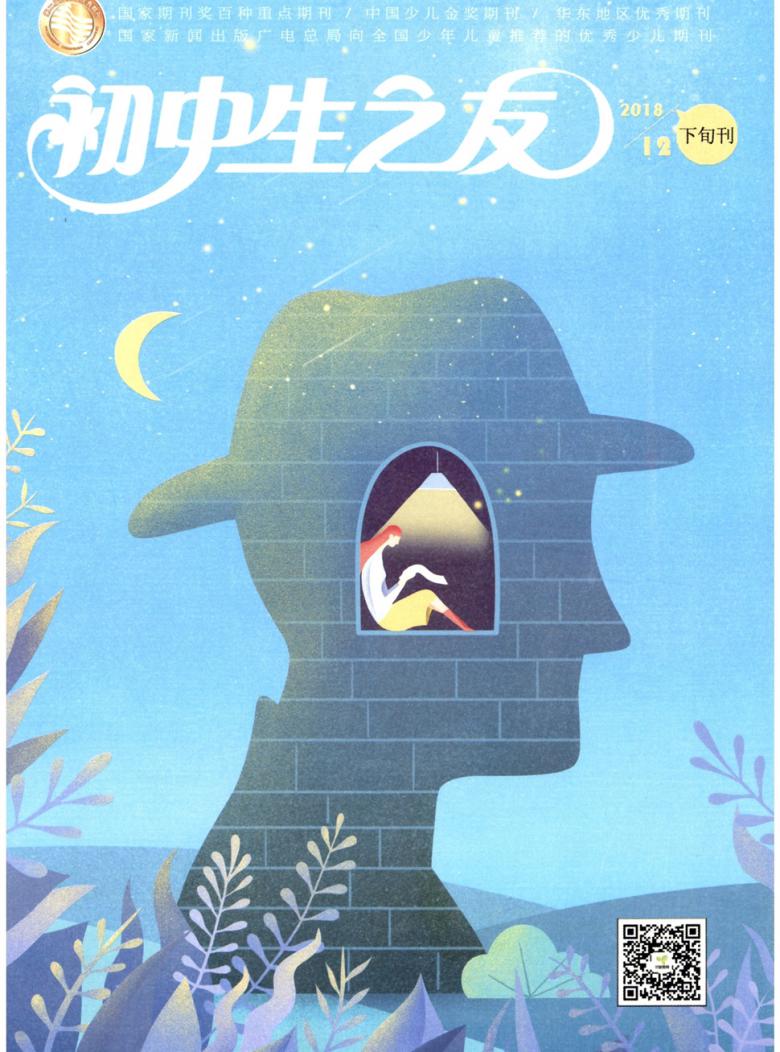毛澤東的歷史觀論綱
易孟醇
毛澤東是嫻熟中國歷史的政治家,他不但自小喜讀史書,至老尤篤,而且多次以領袖的高瞻遠矚,號召大家多讀史書。根據現有資料,至遲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上,他便把學習歷史與學習馬列主義相提并論。他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毛澤東選集》第533頁,以下簡稱《毛選》)。1941年,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號召大家:“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1942年2月1日,他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明確宣布:“現在我們黨的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建國以后,毛澤東又多次重提學習歷史的事。1958年1月21日,在南寧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他面對著幾百名黨的高級干部,倡議“全黨都要學點歷史和法學”,并把學習歷史提到了黨的干部的工作方法的層面上。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的時刻,回顧和學習毛澤東的歷史觀,很有現實意義。
史學目的論
為什么要學習歷史?換句話說,歷史的社會功能是什么?這是每個學習歷史的人必然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也是每個史學工作者必須回答的一個基本問題。
毛澤東的回答,是在1956年8月24日同音樂工作者談話時說的:“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1964年9月27日,他在一份批示中更明確地說:“古為今用。”毛澤東對史學目的的這一高度概括,表達了史學的價值取向。價值的實質是客體功能與主體需要的吻合,吻合的程度愈大,其價值愈大。毛澤東認為,主體(今天的革命者和建設者)對歷史這一客體的需要,是改革現實和創造更美好的將來。換句話說,改革現實,需要了解國情,符合國情,而國情正是歷史的積淀;改革現實,還要從歷史中吸取經驗,增長智慧,接受優秀傳統,發揚歷史積累下來的高尚精神。概括地說,史學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歷史經驗變為現實財富,史學的最大社會價值就體現在這里。因而,毛澤東又說:“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毛選》第533頁)
從史學的這一目的出發,毛澤東提出歷史學習和研究都應貼近現實。毛澤東本人有豐富的歷史知識,而且從來就是把這些歷史知識作為觀察和分析現實的工具,作為改革現實的借鑒。1912年春,毛澤東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學寫的第一篇歷史論文《商鞅徙木立信論》中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是“利國福民”之“大政策”,然而猶欲徙木立信,令人“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千年民智之不開,國幾蹈于淪亡之慘也”。這時他才十九歲,還沒有接觸歷史唯物主義,因而他的分析未必準確,但同時又說明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就養成了把對歷史的分析與對現實的思考緊密聯系起來的思路。踏上革命征途以后,他這種思路更為明晰,更為強烈。他對《甲申三百年祭》的高度評價便是這種思路的反映。郭沫若的這篇文章在1944年3月的重慶《新華日報》連載后,只過了一個多月,毛澤東在黨的高級干部會上就說:“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這年11月21日,毛澤東又致信郭沫若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還說:“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
毛澤東高度重視歷史具有的啟示意義和借鑒意義。這是因為:第一,現實是歷史的延續。毛澤東說:“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毛選》第534頁)人類是帶著歷史的烙印走入現實社會的,又將帶著現實的烙印走向未來。毛澤東在對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內在聯系的把握上,一再強調“不能割斷歷史”。割斷歷史,就不可能了解現實社會的來龍去脈;而只要學習歷史,就可以擴大我們的思維空間,可以對現實社會產生更深刻的認識,從而使我們的行為更符合實際,更有成效。所以,毛澤東說,我們“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毛選》第801頁)。第二,歷史是一座智慧寶庫,它蘊藏著人類幾千年的生產實踐、管理實踐以及政治、軍事實踐積累下來的極豐富的經驗教訓。毛澤東說:“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選》第534頁)毛澤東本人堪稱繼承歷史遺產的典范。在戰爭年代,他經常引用古代的戰例來說明軍事問題,如以“圍魏救趙”的故事說明在抗日游擊戰中在根據地外圍鉗制敵人的必要性,以魯齊長勺之戰說明敵疲我打的方針,以楚漢成皋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等說明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后發制人的意義。第三,歷史是勵己育人的教材。1967年,毛澤東在一封信中,向人推薦《戰國策》中《觸龍說趙太后》這篇文章,并說:“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利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這是從歷史故事中引發出來的驚心動魄的告誡!至于歷史上眾多精英所煥發出來的憂國憂民和愛國愛民的精神、自我犧牲和奉獻的精神、自強不息和艱苦奮斗的精神、清正廉潔和勤政敬業的精神等等,更是世世代代教育和鞭策著后來人。學習和研究歷史,正是為了熟悉這些歷史教材,更好地運用這些歷史教材,以史育人。
毛澤東的史學目的論,深刻地體現了對史學社會功能和社會價值的估量,又具體而微地體現了批判地繼承的史學觀。但在“文革”時期,“四人幫”歪曲史實,隨意比附,搞什么儒法斗爭的討論,并大搞影射史學,葬送史學的科學性和客觀性,把史學推向政治實用主義和庸俗化。這是對毛澤東史學目的論的嚴重歪曲和肆意踐踏。但如果因此而懷疑或否定“古為今用”的原則,則是錯誤的。再說,史學既要考慮它的社會價值,同時也要考慮它的學術價值,即它的真實性、全面性和科學性。毛澤東說:要“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地位。”(《毛選》第208頁)即要“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毛選》第801頁)。史學的學術價值,是史學獲得社會價值的前提。輕率的歷史比附和有意制造的影射史學之類,是偽史學,沒有任何學術價值,因而也就沒有真正的社會價值。
歷史矛盾論和歷史不斷發展論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一部矛盾運動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是社會矛盾運動的結果。他說:“社會的變化,主要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毛選》第302頁)毛澤東的這些論述,科學地揭示了社會發展的內因決定論,從而徹底否定了“民族優劣論”、“地理環境決定論”、“歐洲中心論”以及艾奇遜所說的“人口過剩論”等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外因決定論。毛澤東舉例說:“許多國家在差不多一樣的地理和氣候條件下,它們發展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個國家吧,在地理和氣候并沒有變化的情形下,社會的變化卻是很大的。”他說:“簡單地從事物外部去找發展的原因”的思想,都是歐洲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機械唯物論、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庸俗進化論和中國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觀的反映(《毛選》第301-302頁)。
毛澤東的歷史矛盾論和內因決定論,為史學家提供了一把分析紛紜復雜的歷史現象的鑰匙,而毛澤東本人又是運用這把鑰匙的大手筆。他說:“當馬克思、恩格斯把這事物矛盾的法則應用到社會歷史過程的研究的時候,他們看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看出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以及由于這些矛盾所產生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及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而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會在各種不同的階級社會中,引出各種不同的社會革命。”(《毛選》第317頁)這里,毛澤東最清晰地說明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是社會的最基本矛盾。人與人在生產過程中的關系即生產關系,調整好了,生產力水平就會發展提高,否則就會阻滯生產力的發展。在階級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最集中最突顯的表現是階級關系,因而“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地主階級對于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毛選》第625頁)。
最值得紀念、使后代得益無窮的,是毛澤東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社會的歷史背景和現狀所作的分析。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寫道:經歷了三千年左右的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了手工業,一方面又促進了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但是,帝國主義者的入侵,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使中國逐漸變成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選》第626-631頁)正是在對中國社會的歷史背景和現狀作出上述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毛澤東正確地確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和性質,指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途。回顧黨的歷史,我們不能不承認,從1921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始,我們黨經歷了多少艱難和曲折,才取得這樣的共識啊!這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分析歷史和現狀,解決中國革命中的根本問題的一個光輝范例。1949年8月,當毛澤東再度談論階級斗爭問題時寫道:“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失敗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毛選》第1487頁)階級斗爭史,無疑是幾千年的文明史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但這話說得太絕對了。人類文明史,就大體言之,至少還包括人與自然間關系的科學技術史,和人類的頭腦的活動史,即思想史、文藝史等等。在這種觀點影響下,史學界曾出現以政治史、農民戰爭史代替整個歷史研究的傾向,從而把人類文明史簡單化了。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在“三大改造”以后,毛澤東由于忽視國內階級情況的實際變化,在政治生活中把階級斗爭的弦越拉越緊,以至提出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針,最后導致了“文革”的災難。這是由于他對國內形勢作了錯誤估計,也是由于對階級斗爭學說作了錯誤推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