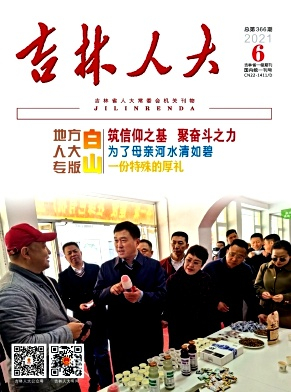從孫中山的“國粹”觀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未知
孫中山晚年多次講到歐美比我們好的是科學,是物質文明,而政治哲學、道德文明是遠不及我們的。因而,他在1924年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演講中,提出要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恢復我一切國粹”,以恢復中華民族“固有的地位”(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41~254頁。)。孫中山的這一表述,頗為中外學者關注,并引發近年來大家對其晚年文化思想的討論(注:有關討論請參閱島田虔次教授《關于孫中山宣揚儒教的動機論》;李侃教授《孫中山與傳統儒學》;張豈之教授《孫中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章開沅教授《從離異到回歸——孫中山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以上四文均見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孫中山和他的時代》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唐文權教授《關于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向傳統政治文化歸攏趨向的若干考查》(《蘇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段云章教授《孫中山晚年識量的幾點探測——以〈建國方略〉、〈三民主義〉為中心》(《中山大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論文集》第10~11集);姜義華教授《論孫中山晚年對西方社會哲學的批判與對儒家政治哲學的褒揚》(《廣東社會科學》1996年第5期);趙春晨教授《從三民主義演講看孫中山晚年的文化取向》(《學術研究》1996年第2期)、《再論孫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廣東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孫占元教授《孫中山與中國傳統文化》(張磊主編《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下冊,人民出版杜1999版)。)。筆者不揣谫陋,擬從孫中山的“國粹”觀入手,就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些探討,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教正。 一 “國粹”是日本明治時代新創的語匯,譯自英語"Nationality",意謂“民族性”、“民族精神”或“民族精華”(注:Martin Bernal著、劉靜貞譯:《劉師培與國粹運動》,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94~95頁。)。黃節在《國粹學社發起辭》中說:“國粹,日本之名辭也。吾國言之,其名辭已非國粹也”(注:黃節:《國粹學社發起辭》,《政藝通報》1904年第1號。)。中國人最早接觸國粹思想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后,1901年9月梁啟超在《中國 ×××是他一再強調的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孫中山認為,“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武力的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要使國家和民族長治久安,就需要有好道德。他以中國歷史為例,總結經驗教訓,說“因為我們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夠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夠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夠同化外來的民族。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頁。)很明顯,他將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作為恢復民族固有地位的前提。 什么是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呢?孫中山認為,首先是忠孝,其次是仁愛,再次是信義,最后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頁。) 孫中山對忠字作了新解釋,剔除傳統的忠君內容,注入新的民主觀念。他說:“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他嚴肅批評那種認為推翻了帝制便可不講忠字的觀點,強調:“在我們民國之內,照道理講,還是要盡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國,要忠于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頁。)。 中國古代以孝行為道德的根源,“百善孝為先”。孝順是儒家倫理中最重要的德性。孔子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注:《孝經·開宗明義章》。)。《孝經》對天子、諸侯、卿大夫、土、庶人的孝行都有規定,孫中山對此特別推崇。他說:“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頁。)。既然忠孝的觀念尚有如此的價值,提倡它也就成為必要。孫中山認為,“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頁。)。 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是以仁為樞紐的德性倫理。孫中山認為,“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說中國“古時在政治一方面所講愛的道理,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于什么事,都是用愛字去包括。”中西交通之后,外國人在中國設立學校,開辦醫院,做了一些慈善工作。孫中山認為這些也是實行仁愛,但他批評那種認為中國人講仁愛不如外國人的觀點,認為“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我們要學外國,只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復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245頁。)。 講信修睦是《禮記·禮運》篇中大同理想的道德境界之一。孫中山指出:“中國古時對于鄰國和對于朋友,都是講信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頁。)。他以商業貿易為例,說中國人談交易,彼此間不需要訂立契約,只要口頭上談妥了,便有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國在中國內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贊美中國人,說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外國人立了合同的,還要守信用得多”(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頁。)。“至于講到義字,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因此,“中國所講的信義,比外國要進步得多”(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246頁。)。 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孫中山說:“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于天性”(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6頁。)。“愛和平就是中國人的一個大道德,中國人才是世界上最愛和平的人”(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頁。)。他在1904年8月31日發表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吁》一文中,對所謂的“黃禍論”作了回擊:“中國人的本性就是一個勤勞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絕不是好侵略的種族,如果他們確曾進行過戰爭,那只是為了自衛”(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11頁、第253頁。)。他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的演講中得出結論說:“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對于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發揚光大,然后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