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美國(guó)歷史評(píng)論》的中國(guó)研究
張 濤
摘 要:作為美國(guó)社會(huì)中一個(gè)較大的學(xué)術(shù)群體,美國(guó)歷史學(xué)家的中國(guó)研究對(duì)于我們了解美國(guó)知識(shí)分子的中國(guó)觀具有很大的參照意義。最權(quán)威的美國(guó)史學(xué)刊物——《美國(guó)歷史評(píng)論》——在20世紀(jì)90年代所發(fā)表的中國(guó)研究文章便從一個(gè)極為重要的角度展示了關(guān)國(guó)史學(xué)界的中國(guó)研究在最近十年的主要線索:中國(guó)的傳統(tǒng)儒家思維方式左右著中國(guó)近現(xiàn)代的社會(huì)發(fā)展和對(duì)外交注。
關(guān)鍵詞:《美國(guó)歷史評(píng)論》;中國(guó)觀;儒家傳統(tǒng)
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中國(guó)社會(huì)發(fā)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綜合國(guó)力的增強(qiáng)、香港、澳門的先后回歸、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與國(guó)際標(biāo)準(zhǔn)的進(jìn)一步接軌,所有這些變革都毫無(wú)疑問地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guān)注。與各國(guó)的政治家、戰(zhàn)略家一樣,歷史學(xué)家也對(duì)中國(guó)問題傾注了極大的熱情。為弄清近十年來美國(guó)歷史學(xué)家的中國(guó)研究所呈現(xiàn)的主要脈絡(luò),本文特別選擇了《美國(guó)歷史評(píng)論》在此期間發(fā)表的中國(guó)研究文章作為考察對(duì)象。筆者做出這一選擇的原因有三。其一,《美國(guó)歷史評(píng)論》是美國(guó)歷史協(xié)會(huì)的“機(jī)關(guān)刊物”,既代表了美國(guó)歷史學(xué)的最高水平,也是美國(guó)史學(xué)界歷史最為悠久的學(xué)術(shù)刊物。其二,與其他歷史時(shí)期相比,20世紀(jì)90年代以后《美國(guó)歷史評(píng)論》對(duì)中國(guó)的關(guān)注程度顯著上升,每年均有一兩篇相關(guān)文章刊載其上,幾乎與該雜志對(duì)歐洲的關(guān)注程度相當(dāng)。第三,歷史學(xué)家是美國(guó)社會(huì)中一個(gè)較大的學(xué)術(shù)群體,他們對(duì)中國(guó)問題的研究至少能從一個(gè)側(cè)面反映出美國(guó)人的中國(guó)觀。筆者考察了1990—2000年間《美國(guó)歷史評(píng)論》所發(fā)表的中國(guó)問題文章。這些文章幾乎一致地認(rèn)為,中國(guó)的傳統(tǒng)思想一一特別是儒家思想一一左右著中國(guó)近現(xiàn)代的社會(huì)發(fā)展和對(duì)外交往。本文擬按照中國(guó)研究文章所涉及的主要問題,從中國(guó)的民族主義問題、中國(guó)的世界地位問題、中國(guó)的社會(huì)問題三個(gè)方面論述美國(guó)歷史學(xué)家是如何從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的角度研究中國(guó)近現(xiàn)代問題的。
中國(guó)的民族主義問題
民族主義的產(chǎn)生可以追溯到18世紀(jì)后半葉的美國(guó)獨(dú)立戰(zhàn)爭(zhēng)和法國(guó)大革命。自此以后,對(duì)民族主義概念的界定就從未停止過。盡管如此,民族主義的基本內(nèi)涵不外乎包括以下幾個(gè)方面:第一,民族主義必須以具體的民族國(guó)家為奮斗目標(biāo)或存在基礎(chǔ);第二,國(guó)家成員擁有共同的文化意識(shí)、歷史傳統(tǒng)、甚至共同的語(yǔ)言是民族主義保持長(zhǎng)久生命力的根本保證;第三,具有獨(dú)立主權(quán)的民族政府是國(guó)家民眾盡忠的對(duì)象。簡(jiǎn)言之,民族主義建立于特定區(qū)域內(nèi)的民眾擁有共同的文化意識(shí)、歷史傳統(tǒng)和民族語(yǔ)言基礎(chǔ)之上,以建立或者捍衛(wèi)主權(quán)國(guó)家為首要目標(biāo)。當(dāng)今世界的所有國(guó)家都應(yīng)當(dāng)是民族主義的產(chǎn)物。中國(guó)當(dāng)然也不例外。
在本文重點(diǎn)研究的12篇文章中,5篇文章明確地以中匡民族主義為主題,另外兩篇間接涉及到了該問題。因此,從1990年到2000年間,《美國(guó)歷史評(píng)論》發(fā)表的中國(guó)研究文章中至少一半以上探究了中國(guó)的民族主義同題。由于特殊的歷史經(jīng)歷和文化傳統(tǒng),中國(guó)民族主義出現(xiàn)的時(shí)間大大晚于大多數(shù)西方國(guó)家。學(xué)術(shù)界普遍認(rèn)為,20世紀(jì)初是中國(guó)民族主義的誕生之時(shí)。美國(guó)歷史學(xué)家考察中國(guó)民族主義運(yùn)動(dòng)的時(shí)間范圍就集中在這一時(shí)期。美國(guó)歷史學(xué)家在考察中國(guó)的民族主義運(yùn)動(dòng)時(shí)傾向于強(qiáng)調(diào)中國(guó)民族主義思想在中國(guó)傳統(tǒng)中的根深蒂固及其潛在的擴(kuò)張性。
對(duì)于任何國(guó)家的民族主義而言,對(duì)國(guó)家主權(quán)的爭(zhēng)取和堅(jiān)持是其核心所在。所謂主權(quán),就是一個(gè)政府自行制定法律并管理所統(tǒng)治國(guó)家的權(quán)力。美國(guó)歷史學(xué)家認(rèn)為,中國(guó)歷史傳統(tǒng)中已經(jīng)包含著較為明確的主權(quán)意識(shí)。天朝觀念則是這種意識(shí)的確切體現(xiàn)。喬安娜·韋利一科恩(Joanna Waley-Cohen)以清朝乾隆皇帝對(duì)待西方技術(shù)的態(tài)度為例,說明中國(guó)的天朝觀念實(shí)際上已經(jīng)包含了較為明確的主權(quán)意識(shí)。乾隆皇帝在1793年接見英國(guó)國(guó)王喬治三世派出的馬戛爾尼伯爵(Lord Macartney)使團(tuán)時(shí)曾經(jīng)告誡來訪者,中國(guó)不需要英國(guó)和整個(gè)歐洲的制造技術(shù)及其產(chǎn)品。韋利—科恩認(rèn)為,乾隆的此番表態(tài)并不代表著中國(guó)從來都對(duì)西方技術(shù)不感興趣。實(shí)際情況恰恰相反。早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就對(duì)西方實(shí)用技術(shù)表現(xiàn)出了濃厚的興趣。及至乾隆年間,耶穌會(huì)傳教士已經(jīng)滲透到了中國(guó)社會(huì)的很多領(lǐng)域,在朝廷的許可下幫助中國(guó)革新技術(shù)。傳教士甚至親臨清朝邊疆平亂前線,輔佐清軍作戰(zhàn)。然而,清廷很快意識(shí)到,傳教士的影響劇增必將危及朝廷對(duì)中國(guó)民眾的統(tǒng)治,加之歐洲教會(huì)內(nèi)訌使對(duì)中國(guó)持友好態(tài)度的耶穌會(huì)遭到打擊。清朝政府便在18世紀(jì)末宣布不再歡迎歐洲傳教士的涌人。乾隆的表態(tài)就是在如此背景下做出的。歐洲人再次成為只能對(duì)中國(guó)天朝制度頂禮膜拜的外夷。韋利一科恩分析道,中國(guó)政府急于修復(fù)天朝體制的行為表明:“中國(guó)人及其統(tǒng)治者一致堅(jiān)決反對(duì)向任何外來者割讓權(quán)利或主權(quán)……這種態(tài)度必須與孤立主義、對(duì)(技術(shù))革新的敵視……以及頑固不化的優(yōu)越感……區(qū)別開來”。[1](P1525-44)清朝政府顯然是因?yàn)楦惺艿搅宋鞣絺鹘淌亢婉R戛爾尼使團(tuán)對(duì)其統(tǒng)治中國(guó)權(quán)力的沖擊才作出上述決定的。
當(dāng)然,我們不可否認(rèn),乾隆皇帝的根本動(dòng)機(jī)在于維護(hù)王朝利益。但中國(guó)王朝維護(hù)自身利益的深層根源卻在于中國(guó)傳統(tǒng)中的天朝秩序思想。這與法國(guó)人佩雷菲特所提及的西方極權(quán)者大多受個(gè)人野心驅(qū)使的情況有著本質(zhì)的差別。[2](P615)我們?cè)诖诉€必須將主權(quán)意識(shí)與民族主義區(qū)別開來,因?yàn)轫f利一科恩顯然僅僅談?wù)摿酥袊?guó)傳統(tǒng)中的主權(quán)意識(shí),而非中國(guó)的民族主義。主權(quán)意識(shí)是相對(duì)靜態(tài)的概念,而民族主義則是捍衛(wèi)或爭(zhēng)取主權(quán)的動(dòng)態(tài)過程。乾隆修復(fù)天朝體制的成功由于暫時(shí)消除了中國(guó)傳統(tǒng)主權(quán)意識(shí)所面臨的挑戰(zhàn)而延緩了中國(guó)民族主義的出現(xiàn)。正因?yàn)槿绱耍袊?guó)的近現(xiàn)代民族主義才出現(xiàn)在西方列強(qiáng)對(duì)中國(guó)天朝觀形成有效沖擊的近代,而中國(guó)近代民族主義者對(duì)傳統(tǒng)主權(quán)意識(shí)的維護(hù)也使中國(guó)民族主義未與歐洲民族主義一樣建立于對(duì)傳統(tǒng)思想的徹底否定基礎(chǔ)之上。這種觀點(diǎn)既為韋利一科恩所堅(jiān)持,也為其他學(xué)者所認(rèn)可。美國(guó)芝加哥大學(xué)的歷史學(xué)家普拉森吉特·杜阿拉(Prasenjit Duara)就是其中之一。杜阿拉在1997年發(fā)表于(美國(guó)歷史評(píng)論)上的一篇文章中認(rèn)為,出現(xiàn)于20世紀(jì)初的中國(guó)近現(xiàn)代民族主義只是中國(guó)人通往普世理想的一個(gè)臺(tái)階。杜阿拉特別指出,20世紀(jì)初期的中國(guó)民族主義乃儒家普救論的延續(xù)。如此產(chǎn)生的所謂“救世”民族主義強(qiáng)調(diào)世界的精神和道德新生。盡管它從表面上看似乎忽視了中國(guó)的自主權(quán)利,但卻以推廣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的方式促進(jìn)了中國(guó)主權(quán)的向外延伸。[3](P1033)
杜阿拉文章的更大意義在于代表了《美國(guó)歷史評(píng)論》近十年來有關(guān)中國(guó)民族主義研究的第二大鮮明特征,即中國(guó)民族主義具有外延性。但我們應(yīng)該明確,歷史學(xué)家不是政治家或者戰(zhàn)略家,其眼中的中國(guó)民族主義外延性不能等同于某些美國(guó)政治家所鼓吹的中國(guó)擴(kuò)張論。杜阿拉相信。中國(guó)民族主義的外延性是一對(duì)矛盾的結(jié)合體。一方面,中國(guó)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在西方列強(qiáng)日益威脅著中國(guó)主權(quán)觀念的傳統(tǒng)根基時(shí)發(fā)生的。中國(guó)民族主義在此時(shí)的出現(xiàn)標(biāo)志著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的本能反應(yīng),因而具有保守性。然而,在另外一方面,由于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的護(hù)衛(wèi)者感覺到了西方威脅的確切存在以及中國(guó)政府在捍衛(wèi)天朝主權(quán)觀問題上的力不從心,他們想到了利用東方世界遭受西方世界威脅的共同經(jīng)歷,借反抗西方世界之名重整中國(guó)的儒家傳統(tǒng)。在這一層面上,20世紀(jì)初期的中國(guó)民族主義又具有向外輸出價(jià)值觀念的“擴(kuò)張”性。例如,康有為于1918年在山東成立的“大同會(huì)”就以“推廣儒家價(jià)值觀”為宗旨。康有為并不反對(duì)建立現(xiàn)代民族國(guó)家,但他認(rèn)為國(guó)家存在的最終目標(biāo)在于實(shí)現(xiàn)“沒有階級(jí)、性別、文化與民族差異”的“大同”世界。這樣一來,康有為的“大同”意識(shí)實(shí)際上削弱了民族國(guó)家的存在意義。據(jù)信,將“大同”理想置于國(guó)家之上的思想,在孫中山那里得到了更大的發(fā)展.據(jù)杜阿拉考證,1924年,孫中山曾在日本的神戶發(fā)表過一次重要演講。孫中山在此次演講中提出了“大亞細(xì)亞主義”概念,號(hào)召亞洲“有色的民族”以共同的文化為紐帶團(tuán)結(jié)起來,用中華帝國(guó)所體現(xiàn)的亞洲“王道”對(duì)抗西方的“霸道”。[3](P1035,1039)另外一位歷史學(xué)家麗貝卡·E·卡爾(Rebecca E.Karl)則從20世紀(jì)初期中匡知識(shí)分子關(guān)于“亞洲”一詞的使用和論述中發(fā)現(xiàn)了中國(guó)民族主義相同的發(fā)展軌跡。[4](P1096—1118)
這些研寒表明,中國(guó)民族主義的外延性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和傳統(tǒng)思想維護(hù)者在西方軍事和文化入侵的過程中所做出的非理性反應(yīng)。正是因?yàn)榉磻?yīng)的非理性,處于初始階段的中國(guó)民族主義實(shí)際上偏離了民族主義的正常發(fā)展途徑,即國(guó)家主權(quán)與民族意識(shí)的齊頭并進(jìn)。然而,《美國(guó)歷史評(píng)論》近十年來所發(fā)表的直接涉及中國(guó)民族主義的文章顯示出,20世紀(jì)初期的中國(guó)民族主義不但未能彰顯中國(guó)的國(guó)家主權(quán).而且在培養(yǎng)中國(guó)民族意識(shí)方面也無(wú)大的作為。就連孫中山這樣一位充滿近代民族國(guó)家意識(shí)的革命先行者也不得不以頌揚(yáng)日本在1905年日俄戰(zhàn)爭(zhēng)中的勝利為條件換取日本人對(duì)“大亞細(xì)亞主義”的認(rèn)同。日俄戰(zhàn)爭(zhēng)是在中國(guó)國(guó)土上蔑視中國(guó)主權(quán)的一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由此可見中國(guó)傳統(tǒng)主權(quán)觀的影響之深和中國(guó)早期民族主義的嚴(yán)重局限性。
盡管如此,上述研究成果仍然具有明顯的片面性。實(shí)際上,單純追求傳統(tǒng)思想的重塑和推廣的所謂“救世”民族主義無(wú)法代表中國(guó)20世紀(jì)民族主義運(yùn)動(dòng)的主流。“救世”民族主義不但具有脫離歷史現(xiàn)實(shí)的缺陷,而且還不時(shí)地遭到以建立主權(quán)民族國(guó)家為目標(biāo)的主流民族主義運(yùn)動(dòng)的打擊。杜阿拉就曾提到“救世”民族主義團(tuán)體被國(guó)民政府禁止一事,禁止源起子與主流民族主義的背道而馳。[3](P1035)但杜阿拉與本文所考察的其他歷史學(xué)家一樣,沒有將主張現(xiàn)代主權(quán)觀的民族主義作為中國(guó)20世紀(jì)民族主義運(yùn)動(dòng)的主導(dǎo)趨勢(shì)。對(duì)儒家思想外延性及其對(duì)亞洲國(guó)家所擁有的潛在感召力的強(qiáng)調(diào)雖然不能說是歷史學(xué)家對(duì)中國(guó)的敵視所致,更不可理解為冷戰(zhàn)思維的遺留產(chǎn)物,但至少反映了歷史學(xué)家以文明類型劃分世界的趨勢(shì)有所加強(qiáng)。
中國(guó)的世界地位問題
美國(guó)歷史學(xué)家將中國(guó)國(guó)家實(shí)體的延續(xù)和維護(hù)植根于以天朝體制為核心的傳統(tǒng)儒家思想之中。這決定了中國(guó)的近代世界地位首先體現(xiàn)在中國(guó)逐漸喪失丁在亞洲以儒家思想為基礎(chǔ)的傳統(tǒng)主導(dǎo)地位。數(shù)位歷史學(xué)家在談?wù)撝袊?guó)民族主義的起源時(shí)就已經(jīng)涉及到了這一問題。杜阿拉筆下康有為的“大同”世界思想以及孫中山的“大亞細(xì)亞主義”都是中國(guó)試圖向外輸出價(jià)值觀以圖重整中國(guó)國(guó)威的具體表現(xiàn)。麗貝卡·E·卡爾以更加詳細(xì)的筆觸分析了20世紀(jì)初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眼中的中國(guó)世界地位。麗貝卡認(rèn)為,中國(guó)人在歷史上第一次認(rèn)真審視自己的世界地位是在清王朝存在的最后十年之內(nèi),即從1895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zhēng)至1911年清廷退位。“亞洲”一詞在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話語(yǔ)中的變化記載了中國(guó)人世界地位意識(shí)的演變軌跡。“亞洲”在漢語(yǔ)里的最初稱謂是“亞細(xì)亞”。據(jù)卡爾考證,“亞細(xì)亞”是在17世紀(jì)時(shí)由歐洲耶穌會(huì)傳教士引人中國(guó)的。但該詞在隨后的幾個(gè)世紀(jì)里都只是一個(gè)含義模糊的音譯詞。即使魏源在1844年出版的《海國(guó)圖志》一書中,人們也無(wú)法找到有關(guān)亞洲的專門章節(jié):魏氏仍然沿用中國(guó)傳統(tǒng)中以“海”劃分世界的方法。19世紀(jì)末出現(xiàn)并被迅速接受的“亞洲”一詞表明,中國(guó)人對(duì)于自己所處的世界以及中國(guó)在其中的地位已經(jīng)有了較為明確的認(rèn)識(shí)。在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視野中,“亞洲”不僅僅是一個(gè)明確的地理概念,而且還包含了濃厚的文化信息。在卡爾看來,對(duì)后來歷史最具影響力的文化信息源于中國(guó)人亞洲種族概念的興起。19世紀(jì)90年代以后,中國(guó)人的亞洲種族意識(shí)經(jīng)歷了從“同文”到“同宗”的演變。所謂“同文”,是指中國(guó)和日本同屆一個(gè)文明。在中國(guó)人眼里,“日本在歷史上對(duì)中國(guó)的文化借鑒顯示并證明了日本相對(duì)于中國(guó)的從屬地位”。日本的逐漸西化以及中國(guó)在甲午戰(zhàn)爭(zhēng)中的失敗使中國(guó)意識(shí)到,中國(guó)的文明體系已經(jīng)無(wú)法束縛日本的離心傾向。以膚色和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經(jīng)歷為基礎(chǔ)的亞洲“同宗”概念隨之出現(xiàn)。“同宗”概念所包含的已經(jīng)不再是中國(guó)的文化主導(dǎo)地位和文化輸出意識(shí)。盡管中國(guó)人的文化優(yōu)越感仍然根深蒂固,但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正在逐漸將重整中國(guó)泱泱大國(guó)地位的希望寄托在“同宗”亞洲國(guó)家的支持和協(xié)同斗爭(zhēng)上。例如,1898年反抗美國(guó)殖民統(tǒng)治的菲律賓人就被包括梁?jiǎn)⒊趦?nèi)的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歡呼為黃種人反抗白種人的先驅(qū)。[4](P1100—1102,1105)
卡爾的分析表明,中國(guó)人的世界意識(shí)起源于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中國(guó)當(dāng)時(shí)所面臨的國(guó)際形勢(shì)決定了國(guó)人對(duì)中國(guó)世界地位的認(rèn)識(shí)是一個(gè)痛苦的過程。一方面,中國(guó)政府和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依然固守天朝觀念下的中國(guó)優(yōu)越情結(jié);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面對(duì)西方列強(qiáng)的步步進(jìn)犯和日本迅速西化的現(xiàn)實(shí)。在此情況下.中國(guó)的知識(shí)精英開始在中國(guó)優(yōu)越性問題上做出妥協(xié),力促國(guó)人向“同宗”的其他亞洲民族學(xué)習(xí),以曲線方式拯救國(guó)家于危亡之際。因此,當(dāng)中國(guó)步人現(xiàn)代世界之初,中國(guó)優(yōu)越情結(jié)遭到削弱,中國(guó)與亞洲其他國(guó)家的主導(dǎo)與從屬關(guān)系也被顛倒過來。為圖中國(guó)自救而采取的向他國(guó)借鑒經(jīng)驗(yàn)并正視現(xiàn)實(shí)的態(tài)度成為中國(guó)在世界意識(shí)覺醒之后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內(nèi)處理對(duì)外關(guān)系的主要方式。
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的束縛不但使剛剛走上世界舞臺(tái)的中國(guó)沉溺于諸如“大同”世界、“大亞細(xì)亞主義”、亞洲“同宗”等幻想之中,而且還使20世紀(jì)前半期的中國(guó)知識(shí)精英以及各屆政府將政策重心放在了國(guó)內(nèi)思想的統(tǒng)一和與擁有相似歷史經(jīng)歷的國(guó)家之間的聯(lián)合上。因此,“重視東方,忽視西方”成為美國(guó)歷史學(xué)家筆下中國(guó)世界地位的另外一大特征。阿瑟·沃爾德倫(Arthur Wal&on)通過考察中國(guó)軍閥制度的演變,既揭示了中國(guó)在20世紀(jì)前幾十年無(wú)暇躋身世界國(guó)家之林的一個(gè)重要原因,也說明了導(dǎo)致中國(guó)敵視西方并最終忽視西方的關(guān)鍵現(xiàn)實(shí)因素。中國(guó)本無(wú)“軍閥”一說,但清朝的瓦解使地方勢(shì)力急劇膨脹,陳獨(dú)秀于是在1918年率先使用該詞以指代擁兵自重的地方勢(shì)力。軍閥混戰(zhàn)不但完全擾亂了中國(guó)的社會(huì)秩序,束縛了中國(guó)處理外部事務(wù)的手腳,而且引發(fā)了一場(chǎng)曠日持久的論戰(zhàn)。陳獨(dú)秀認(rèn)為,中國(guó)唯有打倒軍閥、建立中央集權(quán)政府才能實(shí)現(xiàn)統(tǒng)一。而以胡適為代表的另一方則辯稱,中國(guó)可以依賴軍閥之間的自愿聯(lián)合逐步實(shí)現(xiàn)統(tǒng)一。沃爾德倫認(rèn)為,盡管雙方的觀點(diǎn)相去甚遠(yuǎn).但均未擺脫中國(guó)傳統(tǒng)政治思想的束縛。他們的論戰(zhàn)集中于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的兩大關(guān)鍵要素,即“個(gè)人的道德責(zé)任和中央與地方政府相互關(guān)系的問題”。“陳強(qiáng)調(diào)了個(gè)人作為權(quán)力集中者的作用,他因此實(shí)際上支持采用郡縣體制統(tǒng)治中國(guó);胡則堅(jiān)持封建傳統(tǒng)所代表的分權(quán)思想”。因此,陳、胡二人及其所代表的兩派政治勢(shì)力的爭(zhēng)執(zhí)集中在如何在軍閥混戰(zhàn)的局面中實(shí)現(xiàn)國(guó)內(nèi)思想和政治上的統(tǒng)一。而試圖實(shí)現(xiàn)的統(tǒng)一仍然限于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的范圍之內(nèi)。與此同時(shí),反對(duì)軍閥的陣營(yíng)從一開始便將軍閥與西方帝國(guó)主義聯(lián)系在了一起。反對(duì)陣營(yíng)在民眾中的巨大影響無(wú)疑加劇了中國(guó)社會(huì)對(duì)西方世界的仇視。[5](P1073—1099)
威廉·羅杰·路易斯(Wm.Roger Louis)對(duì)香港問題的研究從另外一個(gè)側(cè)面突出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對(duì)于中國(guó)現(xiàn)代外交的影響力。路易斯以1945—1949年中國(guó)政權(quán)更迭時(shí)期中英兩國(guó)政治家對(duì)香港問題的關(guān)注為切人點(diǎn),探討了英國(guó)能夠在戰(zhàn)后繼續(xù)占領(lǐng)香港的深層原因。當(dāng)然,戰(zhàn)后初期美國(guó)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的態(tài)度經(jīng)歷了從反對(duì)英國(guó)繼續(xù)占領(lǐng)到支持英國(guó)統(tǒng)治的轉(zhuǎn)變。這毫無(wú)疑問為中國(guó)政府收復(fù)香港設(shè)置了幾乎不可逾越的障礙。英國(guó)政府日益強(qiáng)硬的姿態(tài)是不容忽視的另外一大原因。然而,路易斯認(rèn)為,當(dāng)時(shí)主宰中國(guó)命運(yùn)的國(guó)共兩黨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chǎng)堅(jiān)定了英國(guó)政府的強(qiáng)硬。蔣介石政府在抗日戰(zhàn)爭(zhēng)結(jié)束之后樂于利用英國(guó)占領(lǐng)下的香港運(yùn)送大批軍隊(duì)到中國(guó)內(nèi)戰(zhàn)前線,而對(duì)于深處西北、在國(guó)內(nèi)力量對(duì)比中尚處于劣勢(shì)的共產(chǎn)黨而言,香港根本就不是他們需要考慮的迫切問題。路易斯對(duì)于共產(chǎn)黨的立場(chǎng)評(píng)論道:
簡(jiǎn)言之,毛(澤東)從中央帝國(guó)的角度看待世界政治,認(rèn)為中國(guó)本土遠(yuǎn)比邊緣或者邊疆地區(qū)重要。包括英國(guó)、美國(guó)、甚至蘇聯(lián)在內(nèi)的其他國(guó)家似乎相當(dāng)遙遠(yuǎn)。毛和他的接班人滿足于香港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提供技術(shù)、資本投資、及至中國(guó)三分之一的外匯收入和重要的金融服務(wù)。毛的現(xiàn)點(diǎn)在中國(guó)具有代表性,其影響延伸至1997年7月政權(quán)交接之時(shí)。[6](P1056)
我們可以不同意路易斯的分析,但卻可以看出其在中國(guó)的世界地位問題上與其他學(xué)者的根本一致性。此處的一致性是。中國(guó)的政治家更愿意從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的角度出發(fā),以一種既注重實(shí)際又遠(yuǎn)離塵囂的姿態(tài)看待世界態(tài)勢(shì)。也許;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中國(guó)在20世紀(jì)至少一半的時(shí)間里為何總是游離于世界體系之外。
中國(guó)的社會(huì)問題
由于近來《美國(guó)歷史評(píng)論》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的普遍關(guān)注.美國(guó)歷史學(xué)家對(duì)中國(guó)社會(huì)問題的研究同樣被打上了傳統(tǒng)思想的烙印。換言之,中國(guó)的傳統(tǒng)思想不但影響著中國(guó)近現(xiàn)代民族主義運(yùn)動(dòng)和中國(guó)看待世界的角度,而且還是中國(guó)社會(huì)問題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理論基礎(chǔ)。就筆者所考察的歷史學(xué)家而言,對(duì)中國(guó)社會(huì)同題的關(guān)注大致沿著兩大方向進(jìn)行:中國(guó)當(dāng)代社會(huì)問題的歷史根源和中國(guó)社會(huì)的傳統(tǒng)結(jié)構(gòu)。
突出中國(guó)當(dāng)前社會(huì)政策與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的中國(guó)社會(huì)之間的巨大相似之處,是美國(guó)歷史學(xué)家研究中國(guó)當(dāng)代社會(huì)問題歷史根源時(shí)所體現(xiàn)的最大特征。曾與美國(guó)著名漢學(xué)家費(fèi)正清一道撰寫《新編中國(guó)史》(China:A New History)的默爾·戈德曼(Merle Goldman)在2000年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這種關(guān)注模式。戈德曼在文章一開始就表明了他的立場(chǎng):“他們(鄧小平和他的繼任者)實(shí)行的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市場(chǎng)化和中國(guó)社會(huì)向外界開放的政策所造就的中國(guó)與1949年革命之前的中國(guó)而不是毛(澤東)時(shí)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擁有更多的相似之處。”盡管此文嚴(yán)格地講只是一篇回顧與綜述文章,但作者顯然是贊成他所評(píng)述的觀點(diǎn)的。戈德曼從中國(guó)的改革開放政策、民主化進(jìn)程、市民社會(huì)的建立三個(gè)方面闡述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社會(huì)的影響。首先,戈德曼認(rèn)為,鄧小平開始實(shí)施的中國(guó)富強(qiáng)政策可以追溯到19世紀(jì)末的中國(guó)自強(qiáng)運(yùn)動(dòng)。當(dāng)時(shí)的革新派力圖通過發(fā)展經(jīng)濟(jì)與技術(shù)使中國(guó)趕上西方國(guó)家的發(fā)展水平。除此之外,當(dāng)代中國(guó)還借鑒了包括日本、韓國(guó)在內(nèi)的所謂“后儒家思想”鄰國(guó)的發(fā)展經(jīng)驗(yàn),實(shí)行土地改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和出口貿(mào)易等政策。其次,中國(guó)在村民選舉和擴(kuò)大各級(jí)人民代表大會(huì)的立法權(quán)限方面也延續(xù)了19世紀(jì)末的改革運(yùn)動(dòng)。按照戈德曼的解釋,早在1907年。天津就實(shí)行了第一次西方式選舉,而到1909年,這種選舉方式已在中國(guó)全國(guó)推廣。至于立法機(jī)構(gòu)的權(quán)限問題,戈德曼同樣堅(jiān)持,清朝末年的改革者已經(jīng)開創(chuàng)了通過選舉產(chǎn)生國(guó)家議會(huì)并以憲法統(tǒng)治國(guó)家的先例。第三,市民社會(huì)的逐步建立也得益于清末改革者的啟發(fā)。所謂市民社會(huì),即由在政治之外的相對(duì)獨(dú)立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參與政府決策的社會(huì)團(tuán)體所組成的社會(huì)公共區(qū)域。戈德曼認(rèn)為,中國(guó)的市民社會(huì)思想源于梁?jiǎn)⒊拇罅Τ珜?dǎo)。[7](P 153—64)因此,19世紀(jì)末以在變幻的世界格局中維護(hù)傳統(tǒng)封建統(tǒng)治秩序?yàn)橹饕繕?biāo)的維新運(yùn)動(dòng)和洋務(wù)運(yùn)動(dòng)卻為中國(guó)當(dāng)代的社會(huì)政策作了鋪墊。戈德曼不時(shí)地對(duì)中國(guó)缺乏“政治體制的民主化”表示“遺憾”,這進(jìn)一步說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將中國(guó)現(xiàn)行的改革開放視為封建維新運(yùn)動(dòng)的翻版。這種觀點(diǎn)忽視了兩場(chǎng)改革運(yùn)動(dòng)在產(chǎn)生背景、發(fā)起者、社會(huì)環(huán)境和根本動(dòng)機(jī)方面的本質(zhì)區(qū)別,因而是片面而不妥當(dāng)?shù)摹?/p>
從全新的角度分析中國(guó)的傳統(tǒng)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則是美國(guó)歷史學(xué)家近來研究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時(shí)所體現(xiàn)的最大特征。《美國(guó)歷史評(píng)論》2000年12月舉行的“中國(guó)歷史上的性別與男性”論壇集中反映了這種研究趨勢(shì)。在性別問題上,中國(guó)歷史突出了男尊女卑的特點(diǎn)。正因?yàn)槿绱耍蟛糠謿v史學(xué)家將主要精力放在了女性所遭受的歧視及其社會(huì)地位上。論壇則獨(dú)辟蹊徑,從男性社會(huì)角色的角度剖析了中國(guó)的傳統(tǒng)社會(huì)。蘇珊·曼(Susan Mann)從宏觀的角度勾畫出了中國(guó)男性在傳統(tǒng)社會(huì)中的三大角色區(qū)域:家庭、幫會(huì)、友誼。在這三大區(qū)域中,男人的大部分時(shí)間是在與同性的交往中度過的。中國(guó)傳統(tǒng)家庭的家長(zhǎng)以延續(xù)香火為首要任務(wù),男性家庭成員順理成章地成為家庭的決策者.男性的交往范圍也被限定在父親與兒子以及兄弟之間。性別比例的嚴(yán)重失調(diào)使無(wú)數(shù)男性涌人城市謀生。在缺乏家庭保護(hù)而又孤立無(wú)助的情況下,男性往往結(jié)成幫會(huì)。而同鄉(xiāng)、同師門、同年應(yīng)試、同學(xué)等關(guān)系則通常會(huì)為男人之間的友誼奠定基礎(chǔ)。[8]阿德里安·戴維斯(Adrian Davis)的研究探討了男性在家庭兄弟關(guān)系中的角色。戴維斯發(fā)現(xiàn),中國(guó)傳統(tǒng)家庭中不但男女之間存在等級(jí),即使在兄弟之間等級(jí)同樣森嚴(yán)。年長(zhǎng)的兄弟常常被父母賦予更大的家庭決策權(quán)。即使在犯法之后接受法律懲處的問題上,清朝的律法和司法機(jī)構(gòu)也堅(jiān)持長(zhǎng)者從輕的原則。[9]李·麥基薩克(Lee Mclsaac)以中國(guó)抗戰(zhàn)首都重慶為例,分析了中國(guó)幫會(huì)的組織形式和運(yùn)作方式。“袍哥”組織是當(dāng)時(shí)重慶規(guī)模最大且最具影響力的幫會(huì)。盡管.袍哥”組織以《三國(guó)演義》和《水滸傳》中的結(jié)拜兄弟為榜樣替成員伸張正義,但其內(nèi)部的等級(jí)制度仍然十分嚴(yán)格,“大哥”的地位不窖挑戰(zhàn)。[10]諾曼·庫(kù)切(Norman Kutcher)則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中男人之間純粹基于友誼的交往進(jìn)行了研究。庫(kù)切認(rèn)為,在中國(guó)的儒家文化中,以平等自愿、共度難關(guān)為特征的男性友誼關(guān)系之所以長(zhǎng)期受到儒家知識(shí)分子和政府的反對(duì)和排擠,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此類關(guān)系的存在有悖于儒家等級(jí)森嚴(yán)的社會(huì)秩序和國(guó)家體制,并會(huì)對(duì)后者構(gòu)成潛在的巨大威脅。[11]
論壇文章的焦點(diǎn)盡管不一,其結(jié)論卻是一致的。強(qiáng)調(diào)等級(jí)尊卑、中央集權(quán)的儒家思想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具有深刻而徹底的影響。不但男女之間的尊卑界線不可逾越,長(zhǎng)期處于社會(huì)主導(dǎo)地位的男性之間同樣如此。論壇的研究結(jié)果顯示,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中男性的主要活動(dòng)區(qū)域無(wú)不按照君臣、父子、男女、長(zhǎng)幼的等級(jí)秩序組織.只要男性群體不逾越等級(jí)制度的界限,儒家知識(shí)分子和政府不僅會(huì)不加干涉,而且還會(huì)以法律和其他強(qiáng)制手段對(duì)其長(zhǎng)久存在提供庇護(hù)。而基于純粹友誼之上的男人之間的關(guān)系則為儒家思想所反對(duì)和壓制,也不會(huì)得到政府的認(rèn)可。
結(jié)束語(yǔ)
本文所考察的文章涵蓋了20世紀(jì)的最后十年。天朝觀念及其所依據(jù)的儒家思想的無(wú)處不在是貫穿這些文章的主要線索。在我們目前所關(guān)注的歷史學(xué)家的眼中,儒家思維模式左右著中國(guó)近代以來的歷史發(fā)展。它不僅使中國(guó)早期的民族主義運(yùn)動(dòng)和近代外交充滿幻想成分,而且還使中國(guó)社會(huì)一一甚至男性社會(huì)——等級(jí)森嚴(yán)。它雖然阻礙了中國(guó)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但其所引發(fā)的維新運(yùn)動(dòng)卻預(yù)示了中國(guó)以開放心態(tài)爭(zhēng)取新生的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美國(guó)歷史評(píng)論》近十年來所發(fā)表的中國(guó)研究文童還反映出了某些新的動(dòng)向:其一,中國(guó)研究文章的意識(shí)形態(tài)色彩繼續(xù)淡化。在冷戰(zhàn)結(jié)束之前.美國(guó)歷史學(xué)家的中國(guó)研究總是被中美意識(shí)形態(tài)上的差異所困擾。就連費(fèi)正清這樣的資深漢學(xué)家都未能幸免。[12]盡管本文所關(guān)注的歷史學(xué)家也不時(shí)地談及中國(guó)的政治制度,但一般都顯得較為溫和井能從學(xué)術(shù)研究的角度加以對(duì)待。意識(shí)形態(tài)淡化的另一標(biāo)志是對(duì)很多歷史事件的分析比較公正客觀。例如,韋利一科恩在探究18世紀(jì)末中國(guó)再次閉關(guān)鎖國(guó)的根源時(shí).就沒有片面責(zé)備中國(guó)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韋利一科恩認(rèn)為,“18世紀(jì)末期,中國(guó)與西方關(guān)系出現(xiàn)裂痕,責(zé)任并不全在中國(guó)一方”,歐洲教會(huì)的內(nèi)訌導(dǎo)致對(duì)中國(guó)持較為友好態(tài)度的耶穌會(huì)的失利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1](p1528)至于路易斯對(duì)香港問題的研究,雖然我們?cè)谏衔膹?qiáng)調(diào)了他將中國(guó)的立場(chǎng)歸結(jié)為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結(jié)果,但其主要精力還是放在了對(duì)英國(guó)政府和香港歷任總督政策的剖析方面。其次,這些文章體現(xiàn)了美國(guó)的中國(guó)研究中文化研究趨勢(shì)的加強(qiáng)。文化研究以注重考察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的價(jià)值觀念為特征。價(jià)值觀念體現(xiàn)于社會(huì)的意義模式,生活方式和社會(huì)語(yǔ)言都是重要的意義模式。[13](P33)美國(guó)歷史學(xué)家給予極大關(guān)注的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套縝密的價(jià)值體系。杜阿拉、卡爾、沃爾德倫三人的文章則從解讀特定歷史時(shí)期社會(huì)語(yǔ)言中的關(guān)鍵詞所承載的文化信息人手,為我們展示了以前鮮為人知的歷史片斷。杜阿拉和卡爾以“亞細(xì)亞”和“亞洲”兩詞在中國(guó)的接受和使用情形為線索,論證了被傳統(tǒng)思想束縛的近代中國(guó)在面對(duì)西方列強(qiáng)時(shí)的無(wú)奈和無(wú)助心理。沃爾德倫則通過分析“軍閥”一詞的淵源,將讀者引入了中國(guó)20世紀(jì)初的政治爭(zhēng)論之中。至于社會(huì)生活方式,整個(gè)“中國(guó)歷史中的性別與男性”論壇都是圍繞其展開的。然而。“中國(guó)歷史中的性別與男性”論壇更大的意義在于,它將美國(guó)最新的性別理論引入了中國(guó)問題研究。美國(guó)開展女權(quán)主義和婦女史研究已有時(shí)日,對(duì)婦女問題的研究不僅使性別研究成為一個(gè)獨(dú)立的研究領(lǐng)域,而且還激起了人們對(duì)男性研究的巨大興趣。美國(guó)學(xué)者布賴斯.特雷斯特(Bryce Traister)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宣布,現(xiàn)在已經(jīng)到了“將男性重新置于……學(xué)術(shù)文化批評(píng)的中心位置”的時(shí)候了。[14](P276)特雷斯特所表述的并不是一種孤立的觀點(diǎn),而是體現(xiàn)了美國(guó)學(xué)術(shù)界對(duì)過于注重女性問題的性別研究的反思。這種新的性別研究模式顯然也影響了美國(guó)的中國(guó)研究,因?yàn)樘K珊·曼在其文章一開始就說明了組織此次論壇的根本原因:男性史研究盡管已在歐美廣泛流行,但并未引起中國(guó)研究領(lǐng)域的注意。曼因此相信,“本論壇的文章是英語(yǔ)中國(guó)史學(xué)家第一次將性別作為分析范疇以考察男性社會(huì)關(guān)系的合作嘗試”。[8]將男性作為一個(gè)單獨(dú)的研究領(lǐng)域必將給中國(guó)研究提出新的課題和挑戰(zhàn)。
然而,近十年來美國(guó)歷史學(xué)家對(duì)中國(guó)的研究仍然有著明顯的局限性。其中較為突出的缺陷有二。第一,他們的研究視野似有狹窄之嫌。他們不僅將研究的時(shí)間跨度限制在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而且他們對(duì)于中國(guó)歷史問題的解釋也集中在一條線索,即儒家思想。第二,美國(guó)史學(xué)界乃至美國(guó)整個(gè)人文學(xué)術(shù)界近來極其盛行的跨國(guó)比較研究模式并未在中國(guó)研究中體現(xiàn)出來,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新穎的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的涌現(xiàn)。當(dāng)然,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rèn)美國(guó)歷史學(xué)家的中國(guó)研究對(duì)于我們了解美國(guó)人的中國(guó)觀具有參照意義。
[2][法]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guó):兩個(gè)世界的撞擊[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3.
科學(xué).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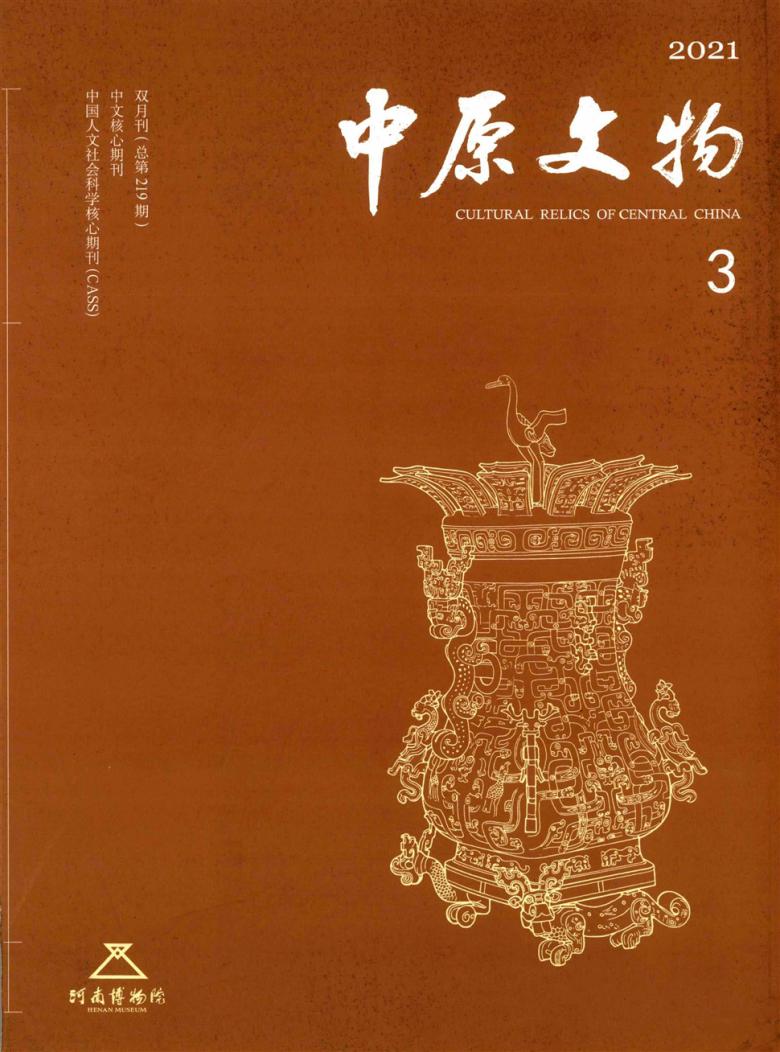
與文化.jpg)
審判.jpg)
學(xué)報(bào).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