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自然區(qū)域、行政區(qū)劃與文化區(qū)域相互關系管窺
周振鶴
對于中國歷史上自然區(qū)域、行政區(qū)劃以及文化區(qū)域三者相互關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見過有專門的討論。本文試圖從宏觀的角度對這一關系進行初步的探討,由于題目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證式的方法予以說明。
在這三種區(qū)域中,行政區(qū)劃是國家行政管理的產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確認,有最明確的邊界與確定的形狀;自然區(qū)域是地理學家對自然環(huán)境進行的科學性的區(qū)劃,不同的科學家與不同的地理觀點,形成互有差異的自然區(qū)劃方案。文化區(qū)域則是相對較不確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綜合來確定,具有感知的性質,主要是人文地理學者研究的對象。
自然區(qū)劃雖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據的是確定的自然環(huán)境,所以各方案之間相去不是很遠。行政區(qū)劃雖由現實的政治需要而確定,但要受制于歷史傳統(tǒng)與自然環(huán)境,從來都是在已有的體系上進行調整與改革,不可能憑空設想一個全新的體系。而歷史傳統(tǒng)中既包含歷史自然環(huán)境變遷的因素,也有歷史文化區(qū)域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文化區(qū)與自然區(qū)也有依存關系,尤其是小文化區(qū)與自然環(huán)境關系更為明顯。要之,行政區(qū)與自然區(qū)和文化區(qū)三方之間有密切不可分的關系。
一、行政區(qū)劃與自然區(qū)域的基本關系
行政區(qū)劃是在自然地理環(huán)境的背景上所劃定的政治空間,因此在人為的政區(qū)與天然的地理環(huán)境之間就存在契合與否的問題。地理環(huán)境是由地貌、氣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動物等因素組成的復雜的物質體系。中國歷史上長期是一個農業(yè)國家,對于地理環(huán)境的地域差異有很深刻的認識,深知行政區(qū)與自然區(qū)的一致對農業(yè)生產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況下,總是盡量保持行政區(qū)劃與自然區(qū)域的一致,以利農業(yè)經濟的發(fā)展,維護封建王朝的穩(wěn)定。但是長治久安又是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標,這個目標是擺在有利社會發(fā)展的目標之上的。而為了達到長治久安,統(tǒng)治者不斷總結歷史經驗,認識到逐步加強中央集權的必要性,在這種政治思想的指導下,行政區(qū)劃與自然區(qū)域的一致性越來越差,尤其是高層政區(qū)在古代中國社會的后期與自然環(huán)境之間已經存在相當大的背離現象。
按照最近的綜合自然地理區(qū)劃方案,中國可以分成三個大自然區(qū),即東部季風區(qū)、西北干旱區(qū)與青藏高寒區(qū)。這三大區(qū)又可進一步分成七個自然地區(qū)和三十三個自然區(qū)。東部季風區(qū)占全國陸地總面積的45%,總人口的95%,過去、現在與將來都是中國最重要的農耕區(qū)。對于作為中國歷史疆域主體部分的東部季風區(qū),古人早就認識到其內部地理環(huán)境的差異性。季風區(qū)內可以劃出三條東西向的分界線,第一條是在東北自然地區(qū)和華北自然地區(qū)之間,正與戰(zhàn)國時期的燕國長城的東段重合。這條界線使得今遼寧省大部地區(qū)在自然區(qū)劃方面屬于華北而不屬于東北。而在《禹貢》所劃分的九州方案中,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同處于青州之中,說明古人對這一界線的認識與今人一致。
第二條界線是分開華北與華中兩個自然地區(qū)的秦嶺-----淮河一線。這是中國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線。此線南北兩側,無論地層、地貌、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顯著不同。比如從氣候上來看,此線是最冷月太陽幅射熱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溫度為攝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與蒸發(fā)相等)的標志線。這個標志作用自古以來就被觀察到,"桔過淮即為枳"可以說是這一觀察的最形象的總結。由于上述原因,秦嶺-----淮河一線歷來被視為中國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線,不但南船北馬、南米北麥由此線而判然,甚至分裂時期南北政權的對峙也常以此線為界。而且在元以前統(tǒng)一王朝之中,行政區(qū)域的劃分基本上不跨越這條界線。
第三條界線是華中地區(qū)與華南地區(qū)的分界,也是熱帶與亞熱帶的分界。這一界線在地理學家當中爭議最大,大致在北緯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間波動。極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歸線以南,其他方案則畫在南嶺與北回歸線之間。在北回歸線以南,夏天時太陽可以從北邊的窗戶射入屋內,古代稱之為"北向戶"或"北戶"。但對于北回歸線古人的認識還不是那么具體,必須以山脈河流為標志才能更直觀地感覺到,所以南嶺常被近似地當成熱帶與亞熱帶的分界線,"嶺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嶺南與嶺北梅花開放先后的差異,標志著嶺南地區(qū)近乎熱帶的風光。這條界線不如第二條界線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區(qū)劃界線也大致遵循此線,除了個別地點,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條界線所劃出的四個自然地區(qū)以下,又可細分為十九個自然區(qū)。而在華北地區(qū)與華中地區(qū)內的自然區(qū)界線也極富標志性。在華北,由于距海的遠近與濕潤程度密切相關,離海越遠,濕潤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區(qū)界線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與西河(即陜西與山西之間的黃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陜西處于不同的自然區(qū)之中。在華中,地勢的抬升與降水量密切相關,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別山、巫山、烏蒙山都成為重要的自然區(qū)分界線。歷代王朝的正式政區(qū)大部分分布在華北與華中地區(qū),這些垂直的自然區(qū)的分界線也都成為政區(qū)之間的界線。
以下我們更具體地來分析一下行政區(qū)劃與自然區(qū)域關系的歷史變遷。
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以后,為了控制邊遠地區(qū),曾對某些政區(qū),實行過犬牙相錯的劃界的措施。這一措施的實質是使政區(qū)的邊界不和重要的山脈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區(qū)負險對抗中央政權。但從大的范圍看來,秦代郡級政區(qū)的幅員與自然地理區(qū)域存在相互對應的關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個獨立的地理單元,或者數郡組成一個完整的地理區(qū)域,少數情況下一郡包含幾種不同的地貌類型。
北方的關中與山東地區(qū)開發(fā)充分,經濟發(fā)達,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員較小,往往是幾郡組成一個地理區(qū)域,如邯鄲、鉅鹿兩郡為黃河與太行山間之三角沖積平原;雁門、代郡、太原、河東與上黨五郡組成山西高原,是黃土高原的一部分。當然這五郡又各自為一個地理單元:雁門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縣、廣靈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黨郡是潞安盆地,河東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東盆地。其他自成一個地理單元的郡還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內史,正占據當時最富庶的關中盆地,或稱渭河沖積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兩種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開發(fā)尚淺,地廣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過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區(qū)域,或包括幾個地理單元。如巴郡是川東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閩中郡是浙閩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與丘陵及鄱陽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劃分重視地理區(qū)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為核心而推廣于四周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證有相當地可耕地,使農業(yè)經濟的發(fā)展有一堅實的基礎。漢興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壞了秦郡分劃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劃小,如內史一分為三,每郡都成支離破碎之區(qū)。其次是削王國之地以充實漢郡,使王國周圍漢郡領域不斷變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黃河兩岸,臨淮郡居淮水東西,與地理區(qū)域脫離了關系。當然南方的漢郡由于地域縮小,也有個別郡反面與地理區(qū)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陽湖盆地的范圍,但這樣的例子不多。因此漢晉南北朝時期,行政區(qū)劃已與自然地理區(qū)劃脫離關系,直到隋代重新統(tǒng)一全國以后才又有了變化。
隋煬帝在大業(yè)三年進行行政改革,將三百余州調整為一百九十個郡,并使絕大部分郡界與山川形勢相符,這不但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劃奠定基礎,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統(tǒng)縣政區(qū)又與秦郡一般,大致與自然地理區(qū)域相適應,但當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圍內。隋郡的幅員遠比漢郡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語了。因此就每一個郡而言,多數只是一個地理單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組郡而言,卻往往與一個自然地理區(qū)域相合。因此秦隋劃郡原則的對比,前者重區(qū)域,后者重分界。
貞觀元年,唐太宗將天下諸州以山川形便分為十道,這十道嚴格地以名山大川及關隘要塞作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組合方面相當完整的地理區(qū)域。這十道是:關內道,潼關以西,隴山以東;隴右道,隴山以西;河北道,黃河以北;河東道,黃河以東,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黃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長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嶺)以南的漢中、川東山地、南陽盆地和江漢平原;劍南道,劍閣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長江以南,南嶺以北;嶺南道,南嶺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東西界外,各道之間都有明確的山川界線。
中國的地貌大勢是西高東低,主要河流山脈都呈東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劃分即以這些山川為骨干,先沿黃河、秦嶺-----淮河、長江及南嶺橫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隴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為標志豎切五刀,就形成了十個地理區(qū)域,十分自然,也相當合理。十道的分劃對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進行監(jiān)察工作,年底回京匯報,這些使節(jié)之間的分區(qū)巡視肯定與十道有關系。所以開元年間將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為固定的監(jiān)察區(qū)。時隔不久,安史之亂爆發(fā),全國范圍內被劃為四十來個方鎮(zhèn)以對付叛亂,這些方鎮(zhèn)在唐后期成為實際上的高層政區(qū),其幅員多與自然地理區(qū)域相對應。如原來的江南西道被調整為宣歙、江西、湖南三個觀察使轄區(qū),江西觀察使與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區(qū)域,湖南觀察使則對應于湘、資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觀察使也與今天的福建省毫無二致,為浙閩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劃小而來,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區(qū)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個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溫、臺、處十州及蘇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則是眾多河流谷地。在這十個半州中,溫州是飛云江流域和甌江的下游,處州則由甌江支流小溪與大溪流域組成,臺州包括整個靈江流域,明州覆蓋了甬江流域,湖州則與苕溪流域相對應。至于錢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條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經得到比較深入的開發(fā),所以州的幅員已經夠小。除了東北一隅以外,十個州的地域和界線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間毫無變化,只有名稱的更改而已。諸州之間由于關山阻隔,形成一個一個的小封閉圈,成為長期保持穩(wěn)定的地理基礎。可見政區(qū)的分劃若與自然地理區(qū)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長期的穩(wěn)定。
唐代無論分道還是劃州,都力圖使之與自然地理區(qū)域相適應,目的不是別的,就是為了尋求同一政區(qū)之內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農業(yè)經濟的發(fā)展。直到二十世紀的今天,綜合自然地理區(qū)劃的工作依然是直接為著農業(yè)生產服務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區(qū)域之間的差異,并使行政區(qū)劃與某一自然地理區(qū)域相對應,顯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農業(yè)生產進行統(tǒng)一指導和規(guī)劃。同樣的氣候,均質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進行同一類型的生產活動,簡化農業(yè)生產管理,便于進行水利建設。所以秦代與隋唐都有意使統(tǒng)縣政區(qū)的分劃與自然區(qū)劃相一致。
漢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專制皇權與地方諸侯王分權的對立,所以西漢盡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東部地區(qū)諸侯王國林立的局面,既奪取王國支郡為漢郡,又以蠶食方式不斷擴大這些漢郡的領域,因此郡域與郡界不斷浮動,在這種情況下,而求其與自然地理區(qū)域相對應,豈不是等于緣木求魚。因此西漢末年的郡大多與自然環(huán)境關系不大。隋唐帝國刻意追求行政區(qū)劃與自然地理區(qū)劃的一致,說明其時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處理,社會主要矛盾已偏向經濟方面。但是隋唐的統(tǒng)縣政區(qū)并非沒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圍劃得過小,在農業(yè)生產方面也產生不良影響,有些建設工程在此州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為水害。但是從總的方面看,可以說,自隋唐時候起,直至清末為止,統(tǒng)縣政區(qū)是與自然區(qū)劃大體一致的。但是高層政區(qū)情況則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經與自然地理區(qū)域發(fā)生偏離。
宋代是中央集權高度發(fā)展的朝代,中央政府顯然有意識地使作為高層政區(qū)的某些路的轄境,偏離山川形便的原則,以利于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該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區(qū)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東北隅饒、信二州(即昌江與信江流域),并在西北邊越過幕阜山而領有興國軍(今湖北東南角)。這樣一來,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區(qū)域了。另外,名為淮南東路,卻地跨淮河南北;稱做河東路,卻領有黃河以西的州軍,同時又不領屬位于河東的河中府與解州。但是宋代的路畢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高層政區(qū),所以這種偏離自然區(qū)劃的路還不普遍,如兩浙路、福建路、廣南東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較完整的地理單元。因此宋代是高層政區(qū)脫離自然地理區(qū)劃的過渡時期。
元代形勢大變。因為行省是集民、財、軍政大權于一體的高層政區(qū),為了防止割據,省界的劃定以犬牙相錯為主導原則,行省的區(qū)劃根本不考慮自然環(huán)境因素,而是根據軍事行動和政治需要來確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動是由北到南進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長的方向。但中國的主要山川是東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黃河、秦嶺、淮河、長江、南嶺等天然界線,因而包容復雜的地貌類型。同時,溫度的變化與緯度的變化成函數關系,南北走向過長的行省也不得不縱貫不同的氣候帶。加之蒙元設置的行省幅員過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濱海地帶到內陸呈逐步遞減狀態(tài),這樣的行省就不免要橫跨濕潤與干旱的不同氣候區(qū)。如元初的陜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蓋了整個陜甘黃土高原和內蒙高原西部,又越過秦嶺包容了漢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貴州高原北部。從綜合自然地理區(qū)劃來看,則是橫跨了西北干旱區(qū)和東部季風區(qū)兩個自然大區(qū)。在季風區(qū)中又跨越了華北溫帶和華中亞熱帶兩個自然地區(qū),并且在華中地區(qū)還跨越了北亞熱帶和中亞熱帶兩個自然區(qū)。
當然這是戰(zhàn)時體制的體現,當時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為了平時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調整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陜西四川行省一分為三,成為甘肅、陜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陜西行省跨越秦嶺的形勢已定,直至今日不變。又在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組建一個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規(guī)模跨越淮河的淮南東路,那么這是淮河南北地區(qū)第一次組合為一個幅員巨大的高層政區(qū)。這兩個行省的建立,意味著秦嶺------淮河這一中國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線在元代完全被棄置不顧,說明自然地理區(qū)域已經不成為劃分政區(qū)的重要基礎,被優(yōu)先考慮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廣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與廣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與廣東,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現。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為兩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稱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縮小和調整。大部分省份都成為比較完整的地理區(qū)域。但秦嶺-----淮河被跨越的狀況依舊,同時還出現新的不合理的區(qū)劃,即將太湖流域一分為二,分屬南京與浙江。清代十八省,進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來。南京被豎切一刀,分為江蘇與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勢,與自然區(qū)劃無關。
統(tǒng)觀歷代行政區(qū)劃的變遷,可以發(fā)現其與自然地理區(qū)劃之間的關系有一個曲折變化的過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漢的脫節(jié),隋唐的契合,宋的漸離,元的背離和明清的漸合。所謂自然地理環(huán)境,以中國的老話說,或可稱之為天時與地利。氣候的兩大因素是氣溫與降水,這可謂天時;地貌、土壤、植被則可比擬為地利。幾千年農耕文化的發(fā)展都離不開天時與地利。行政區(qū)劃是人為劃定的,也許可以說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區(qū)劃與自然環(huán)境相一致,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如何求得天時、地利與人和的配合,以創(chuàng)造農業(yè)發(fā)展的最佳背景。這就是秦代隋唐政區(qū)與自然地理區(qū)域契合的原因。但是當政治需要超過經濟動機的時候,政區(qū)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視了,造成元代行省與自然環(huán)境的背離。然而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也不能長期維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區(qū)劃和自然地理區(qū)域趨向一致。 二、文化區(qū)域與自然地理區(qū)域以及行政區(qū)劃的關系
如果從一般直觀的感覺看來,似乎在不少地區(qū)中,這三種區(qū)域是相當一致的,但仔細分析卻不然。文化區(qū)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區(qū)域,后者雖不如行政區(qū)劃那樣有法定的確切的邊界,但在經過學術論證以后,也有相對明確的范圍。但文化區(qū)域主要是由感知而來的認識,當選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為劃分文化區(qū)域的標準時,其范圍也會有不同的形態(tài)。在各文化因子中,語言(或方言)、風俗、宗教都是比較重要的標準,而其中語言的標準更顯突出。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分析幾個實例來說明文化區(qū)域與自然地理區(qū)域以及行政區(qū)劃之間的關系。我們將會看到既有三個區(qū)域相重的情況,也有兩個地域相重,而另一種區(qū)域與此二地域背離的情況,還有三種區(qū)域互相間都不重合的情況。
以湖南為例。歷史上湖南的的綜合文化地理區(qū)劃可以分成東部的湘、資二水流域與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兩區(qū),兩者的分界以雪峰山為標志。這是與自然地理界線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當時指的僅是湘資流域。沅澧流域則尚未得到深入開發(fā),以五溪蠻為代表的少數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時期,沅澧流域得到開發(fā),成為荊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對沅澧流域的開發(fā)是從湖北方向而來,而且在行政區(qū)劃上與湘資流域分處兩個高層政區(qū),因此通兩宋與元代,沅澧流域與湘資流域分屬不同的文化區(qū)域。方言不同,風俗有別。元代湖廣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廣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對文化區(qū)域的整合作用不明顯,此時沅澧流域屬湖北道,仍與湘資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荊湖南北路合成為湖廣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廣為湖南湖北兩省,這時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資、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漸漸體現出來,經過三百年的整合,湘資流域與沅澧流域不再分屬兩個文化區(qū),而屬于同一個文化區(qū)的兩個亞區(qū)。湖南的類型是文化區(qū)域既與行政區(qū)劃大體一致,也與自然地理區(qū)域一致。
山西則是另一種情況。從表面上看來,山西似乎是三種區(qū)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為行政區(qū)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區(qū),周圍有明確的黃河與太行山為其自然邊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體的感覺,晉中文化與相鄰的河北地區(qū)的燕趙文化與陜西地區(qū)的關中文化似乎有明顯區(qū)別。但仔細加以研究,就會發(fā)現其實不然,就在山西這樣的地區(qū),也存在文化區(qū)與行政區(qū)及自然區(qū)不一致的情況。如從漢語方言來說,晉語有入聲,在北方官話區(qū)里顯得十分特殊。但晉語并不復蓋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運城地區(qū)的方言就不存在入聲,不屬晉語區(qū)的范圍,而與關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與語言的認同,正是劃分文化區(qū)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從歷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發(fā)現,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圍的一體化的山西文化,其中運城地區(qū)與陜西關中文化一體,上黨地區(qū)與河南省的河內地區(qū)文化接近,雁北地區(qū)則與邊塞文化相對一致。這種情況也許會令人感到驚奇。因為在山西這樣一個封閉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體性原本應該是無可懷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福建與江西之間的武夷山是劃分自然區(qū)的標志界線,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對封閉的地形,兩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邊與廣東不存在明顯自然界線。但從文化上看,閩西與贛南及粵東北卻成為一個獨特的客家文化區(qū),既與自然區(qū)不符,也與行政區(qū)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區(qū)的存在,說明文化區(qū)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線(行政區(qū)劃)與天然的界線(自然地理區(qū)域)所限制。當然,除了客家文化區(qū)外,福建其他地區(qū)的文化是存在某種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稱之為閩文化區(qū),但在這一文化區(qū)域中又有明顯的地域差異性,至少可以分為四個亞文化區(qū)。而這些亞文化區(qū)與歷史上的統(tǒng)縣政區(qū)(即唐宋的州與明清的府)的范圍有密切的關系。另外,閩文化區(qū)雖然未覆蓋福建全省,但卻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廣東東南部的潮汕地區(qū),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經看出來的。在王士性的《廣志繹》里就說到:"(潮州)以形勝風俗所宜,則隸閩者為是。"當然,若僅以閩方言為準,則閩文化區(qū)還可以擴大到在地域上并不連屬的廣東雷州半島、海南島與臺灣地區(qū)。
至于陜西省,則是行政區(qū)劃與自然區(qū)劃及文化區(qū)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嶺南北分屬不同的自然區(qū)域,這一點在今天任何自然區(qū)劃方案里都是一樣的,在古代也是這樣認識的。而從文化上看,關中文化與漢中文化也有明顯的不同。關中方言屬于中原官話,而漢中方言卻夾有中原官話與西南官話的成份。而且時至今日,漢中地區(qū)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話演唱的漢劇,而關中地區(qū)卻是秦腔占明顯優(yōu)勢。陜西內部的文化地域差異不但體現在關中與漢中地區(qū)之間,而且還存在于陜北與關中之間。陜北地區(qū)通行的方言是晉語,與關中的中原官話有相當大的區(qū)別,而與山西大部分地區(qū)有共同語言。就自然環(huán)境而言,陜北的黃土高原地貌與關中的渭河沖積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陜西其實是三種不同的文化區(qū)的無機的結合,是自然區(qū)、政區(qū)、文化區(qū)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將秦嶺南北劃在同一行政區(qū)以來,經過七百年時間,在行政管理體制的作用下,關中與漢中地區(qū)的文化卻又有逐漸走向一體化的傾向。這種傾向最明顯表現在中原官話區(qū)的擴大。向北,關中方言侵蝕陜北的晉語,而使之由北而南晉語特征逐漸削弱的現象,亦即入聲字逐漸弱化的趨向。在漢中,中原官話則從東西兩側南下,使得西南官話的范圍收縮到中部一帶。同時,在漢中,在關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過來,漢漢調在關中卻呈逐漸萎縮的弱勢。當然這種文化的整合過程至今尚未完成,因為要將原來自然背景與文化因素差異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區(qū)整合為一,是要經過很長的歷史時期的。
相對陜西地區(qū)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較顯著,盡管湖南的沅澧流域與湘資流域組成一個單一的高層政區(qū)僅有三百年時間,遠比陜西統(tǒng)合秦嶺南北的時間為短。即使加上與湖北共處一個布政使司的時間,也還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開的湖南東西兩部分只是第三級自然區(qū)的差異,而秦嶺所分隔的陜西南北兩部分卻是第二級的自然區(qū)域的差異。相比起來,當然前一差異要比后一差異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亂以后,北來的移民到達荊南與江湘地區(qū),使得沅澧下游與湘資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寖假至于今日,新湘語與西南官話的差異也比關中方言與漢中方言的差異小。
在自然區(qū)域、行政區(qū)劃與文化區(qū)域的關系中,尺度范圍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說的是省區(qū)內以及相當于省區(qū)的大尺度的范圍,已經體現行政區(qū)劃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亞區(qū),行政區(qū)劃的規(guī)范作用就更加明顯,因此文化亞區(qū)往往與歷史上的統(tǒng)縣政區(qū)的范圍相一致。不但如此,在這個尺度范圍里,文化區(qū)與自然區(qū)之間也存在明顯的依存關系。例如在浙江與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個個統(tǒng)縣政區(qū)(即州或府),同時又是一個個小文化區(qū)。尤其在浙江,流域與府與吳語的次方言區(qū)基本重疊。在山西與湖南,也有同樣的現象。這一現象的產生決非偶然,是與經濟開發(fā)過程相聯系的。一個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個縣先行開發(fā),其他縣再由這一二個縣分置而來。因此一府之內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對于其他府則有相異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該府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因此對該府起著一種文化垂范的作用,從而使該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強。這從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該府的權威土語這一現象可以看出。 三、簡短的結語
對于文化區(qū)域與行政區(qū)劃以及自然地理區(qū)域的關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確的認識。東漢時期,巴郡太守但望給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將巴郡一分為二,其分割方案與依據是:"江州(今重慶)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精敏輕疾。墊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態(tài)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為兩郡:一治臨江(今忠縣),一治安漢(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魚池,鹽鐵足相供給,兩近京師。"從自然地理背景看,兩漢的巴郡東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濱江山險"。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東西兩部分自成地理單元。從人文地理基礎看,東西部有風俗的差異。東部"其人半楚,精敏輕疾",西部卻"姿態(tài)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東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為據,巴郡可以分為巴東與巴西兩郡。風俗的差異就是文化差異的表現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據之一。在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區(qū)域、文化區(qū)域與行政區(qū)劃相一致的典型。雖然當時朝廷未接受這一意見,但我們卻由此可以看出,關于上述三種區(qū)域的統(tǒng)一性問題,已經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區(qū)域是社會的力量,劃定行政區(qū)劃的是國家的行政權力,而自然地理區(qū)域的劃分則是受自然規(guī)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區(qū)域與行政區(qū)劃以及自然地理區(qū)域的關系事實上體現了社會、國家與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
由于中國疆域遼闊,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這三者有不同的關系,而且從歷史上看來,這一關系又是逐漸在變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隨著時代的前進而發(fā)生變化,行政區(qū)不斷發(fā)生變遷。在今天,如何調整行政區(qū)以促進現代化建設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同時在學術上,這項研究也可視為是聯系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兩大分支的橋梁,尤其因為行政區(qū)劃是政治地理研究對象,文化區(qū)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內容,因此這一研究等于是將自然地理與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機關系進行深入探討。對于如何更深刻地認識人地關系,使地理學成為研究人地關系而不單純只是研究自然環(huán)境的科學,有重要的學術參考意義。而且研究三者的關系對于文化區(qū)的重新塑造,深化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認識,也有一定作用。
國外這方面的探索尚未見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國,其行政區(qū)劃大多與自然區(qū)劃沒有關系,許多州與縣的形狀只是簡單的幾何圖形,談不上三者之間的關系。歐洲各國雖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圍,較少涉及行政區(qū)劃與文化區(qū)關系的問題。我國與歐美國家不同,在文化區(qū),尤其是行政區(qū)的變遷方面積累了豐富的歷史資源,應當在學術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對地理學理論的發(fā)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貢獻。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標是要探討行政區(qū)與自然區(qū)及文化區(qū)三者之間最一般的關系,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作用。弄清楚行政區(qū)劃對文化區(qū)的整合作用,自然區(qū)對文化區(qū)的制約作用以及如何調整改革行政區(qū)劃以適應經濟與文化的發(fā)展,并與自然區(qū)保持某種程度的協調。但茲事體大,以上所說只是一個提綱,詳細研究,還待將來。
學.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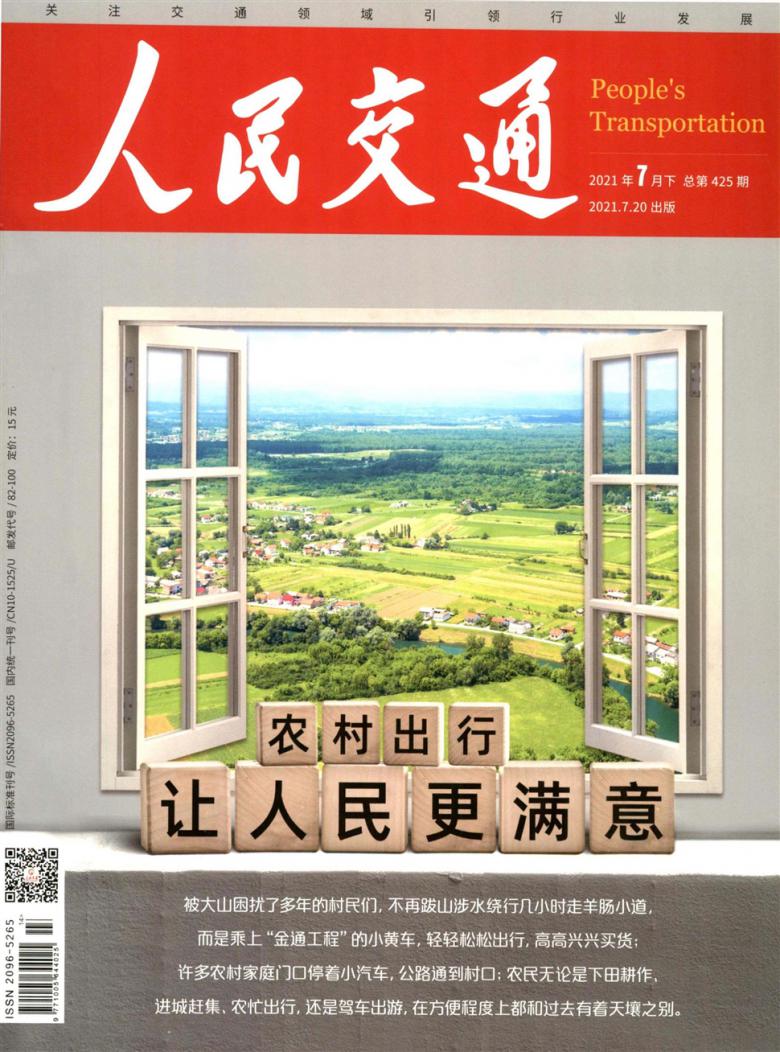


境影響評價.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