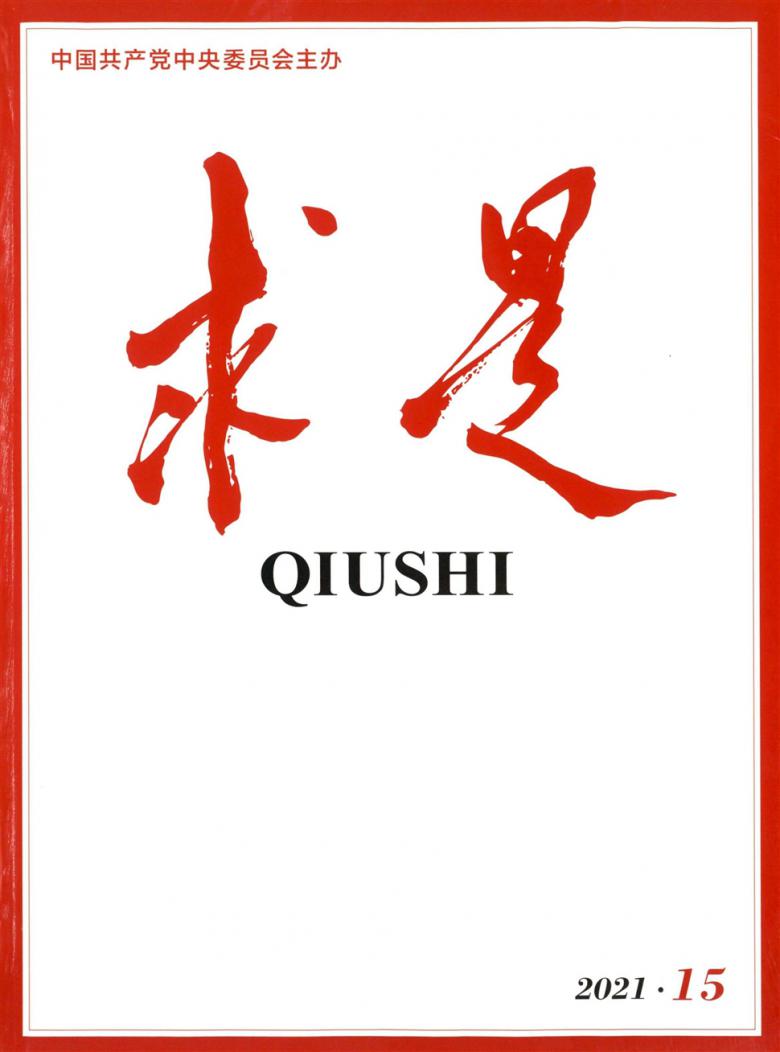內生與延續:近代中國鄉村高利貸習俗的重新解讀(上)
未知
【內容提要】高利貸習俗的生命力非常頑強,能夠超越不同社會形態而存在。它是長期相沿、為廣大民眾反復使用的高利貸習慣,本文特指私人、店鋪借貸中超出社會認可、對債戶非常苛刻的借貸利率習俗。從20世紀上半期華北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資料來看,此習俗花樣繁多,大致可劃分為加大利、先扣利、多算日期、糧錢互折、糧食與糧食及其他實物的互折等六類,由此可見高利貸習俗類型與模式的共性和表現形式的差異性。其所以能夠長期延續,主要是因為除了高利貸,農民沒有其他更多的融資辦法,而高利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調劑生活中所遇到的資金或實物的不足。如果不考慮這一社會經濟基礎,只用政治干預的辦法予以取締,則會導致民間社會秩序的紊亂。
【摘 要 題】現代史專論
【關 鍵 詞】高利貸習俗/20世紀上半期/華北/長江中下游
【正 文】 一
在人們的社會經濟活動中,借貸是一種歷史悠久、不可或缺的融資行為。民俗起源于生活,與其他社會生活領域一樣,借貸活動也折射著濃厚的民俗氣息。所謂高利貸習俗,籠統說來,就是長期相沿、為廣大民眾反復使用的高利貸習慣。民俗學家烏丙安依照同類題材和內容的密切相關性,將民俗分為12個系統、48個系列,(注:烏丙安:《民俗學原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頁。)但我們從中看不出借貸或金融習俗的歸屬,究竟劃為何類,尚須研究。就其運作的具體過程而言,高利貸包括借貸關系的主體即借貸當事雙方、借貸的信用方式、借貸期限、借貸利率、借貸的償還等環節,由此構成高利貸習俗的鏈條。這種借貸之所以成為高利貸,最能體現本質的內容是其高昂的利率,所以本文闡述的核心是高利貸利率問題。
何謂高利貸?迄今為止,這仍是一個沒有解決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關鍵是很難做出一個科學的量的規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給出的定義為“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資本叫做高利貸資本”。(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5、671頁。)這一定義顯然過泛,與西歐中世紀的高利貸概念沒什么區別,即只要是有償借貸,不管量的大小,都屬高利貸。不過,從馬克思的具體論述來看,高利貸資本的本質特征是重利剝削,它不僅占據了債務人的全部剩余勞動,甚至還占有一部分必要勞動,使其精疲力竭,每況愈下。
20世紀80年代末,有的中國學者仍然只是依據馬克思的定義,而不是具體論述,認為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傳統借貸都屬于高利貸。(注:劉秋根:《試論宋代官營高利貸資本》,載《河北學刊》1989年第2期。)這一對傳統借貸形式不加任何區分的觀點,當然更有泛化高利貸之嫌。按此界定,民間私人借貸、店鋪借貸、典當業借貸、錢會借貸等傳統借貸形式都可以歸屬高利貸范疇,實際上不同類型的借貸,運作方式及其性質并不相同,必須根據具體問題而有所區別。例如,典當業是一種以動產抵押為主的傳統金融機構,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高利貸行業,但近年有的學者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將典當業劃為高利貸非常片面。(注:馬俊亞:《典當業與江南近代農村社會經濟關系辨析》,載《中國農史》2002年第4期。)筆者認為,完全否認典當業的高利貸現象也不客觀,但由于經營成本較高,確非以往人們想象的那樣嚴重,總體說來利大于弊;至于錢會,完全是一種多人集資和借貸的互助組織,根本不能算高利貸;而私人借貸和店鋪借貸的情況較為復雜,其中親友之間的無息借貸和低利借貸不能說是高利貸,民間所謂高利貸是超出社會廣泛認可的利率。
前幾年,筆者在博士論文中,鑒于高利貸利率的概念難以界定的情況,“姑且參考國民政府的提法,以超過年利20%或月利1.67%就算高利貸,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注:李金錚:《借貸關系與鄉村變動——民國時期華北鄉村借貸之研究》,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頁。)現在看來有取巧之嫌。其實,不僅南京國民政府對此有過規定,革命時期的中共政權也頒布和執行過有關規定,如抗戰時期規定借貸年利率不得超過10%或15%。同樣是權力規定,為什么僅以國民政府的規定為標準?顯然并未表明充分的理由。無論如何,兩個政權的規定都大大低于社會認可的利率,而是否高出這一規定就算是高利貸,則不能輕下斷語,因為政府規定與社會經濟基礎的距離經常很大。
基于以上理由,本文所述高利貸習俗,并非泛指所有傳統的民間借貸,也不是社會認可的借貸利率,譬如舊中國物價平穩時期,通常借錢月利為3分,糧食借貸年利率為7分,而是特指私人、店鋪借貸中超出社會認可、對債戶非常苛刻的借貸,此屬社會陋俗。我認為,這或許是一個能夠反映民間真實生活世界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以前,對民間借貸有泛化高利貸的傾向,而今卻又有淡化乃至否定高利貸的論調。此一判斷也屬極端,均不足取。 在近代鄉村,盡管民初以降有農業銀行、信用合作社等現代金融機構的出現和發展,但傳統高利貸仍是十分重要的融資現象,所以對此問題的研究有著相當的歷史價值。而從另一角度而言,由于以往民俗學界對此探討尚屬空缺,所以又有重要的民俗學價值。近些年來,筆者主要研究20世紀上半期華北和長江中下游鄉村的信貸問題,茲即以這些地區的調查資料為中心,對高利貸習俗作簡要討論。
二
與“現在的”民俗不同,“歷史的”民俗資料很少記載民俗生活的全部動態過程,它保留的主要是民俗事象、民俗文化和民俗符號,民俗主體基本被懸置起來。(注:高丙中:《民俗文化與民俗生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53頁。)高利貸習俗也是如此,資料文本極少記錄借貸雙方討價還價的具體細節,而是主要表現或抽象為借貸習俗的類型。在此限制下,要復原民俗生活的整體是不可能的。一如法國歷史學家勒華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所用宗教裁判所審判資料可謂豐富至極,但他仍然表示“在民俗這個領域里,‘復原’只是一種幻想。”(注:[法]勒華拉杜里:《蒙塔尤》,許明龍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94頁。)所以,本文所介紹的主要是高利貸習俗的事象、模式,通常為民間俗稱的種種名目。此習俗花樣繁多,不勝枚舉。據統計,江西鄉村的高利貸習俗有23種名目。(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等編:《1949-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農村經濟體制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頁。)由于同名不同義、同義不同名者較多,要想準確地分類是很難的。這里僅就借貸方式及其利率的不同特點,粗略劃分為以下六類:
第一類:加大利 這種高利貸直接表現為借貸利率的高昂,在借貸關系中頗為常見。 錢債有“大加”利之說,如山西黃土坡村稱“大加一”,即月利10分。(注:宏流:《地主剝削式樣》,載《晉綏日報》1947年3月30日。)太行山區鄉村又稱“老一分”、“十利”,即借1元,月利1角,10個月本對利。甚至有“加十五”、“大加二”的,即10個月期限,利錢高至150-200%。(注:魏宏運主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2輯,中國財經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1326、1361、1326、1361、1360、542頁。)江蘇嘉定縣有“日拆利”,每元每日加利1.2或1.5角。(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江蘇省農村調查》,1952年印,第83頁。)糧債也有加大利的各種名目。如山西興縣有“冬五升夏三升”之說,即春借冬還,每斗以5升行息。如冬季不能償還,至來年夏季再還,每斗又加3升利。(注:司法行政部編:《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1930年印,第834、857、824頁。)芮城縣稱“放伙帳”,借麥1石,加利4-8斗不等。(注:司法行政部編:《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1930年印,第834、857、824頁。)河南開封、偃師等縣稱“揭麥帳”,如年底借麥1斗,麥后還麥一斗二三升。(注: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547頁。)河北贊皇縣稱“加五利”,亦名谷利,即借糧1斗還1斗半,且須“尖還”,即平斗借尖斗還。(注:魏宏運主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2輯,中國財經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1326、1361、1326、1361、1360、542頁。)江蘇常熟縣有“粒半”、“粒六”、“粒七”乃至“粒八”,即指5分利、6分利、7分利和8分利。(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江蘇省農村調查》,第217、20、61、439、47、61、140、216、439頁。)浙江麗水縣有“對合利”,7月借9月還,利為本的一倍。(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浙江省農村調查》,1952年印,第30頁。)安徽滁縣有“四撞十”,春借4石稻,秋收時連本還10石。(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安徽省農村調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頁。) 再就是利滾利、驢打滾與印子錢,它們成了一些地區高利貸的代名詞。 “利滾利”,即屆期不還,以利作本,重計利息,逐期滾算,利息學稱作“復利”,是債主規避風險的一種有效方式。在河北稱為“臭蟲利”,形容其繁殖過速。(注:田文彬:《崩潰中的河北小農》,引自天津《益世報》1935年4月27日。)山西稱“駒子生息”、“羊羔生利”、“黑驢打滾”(注:劉大鈞:《我國佃農經濟狀況》,上海太平洋書店1929年版,第55頁;崔哲:《“相財主”殺刮農民的“奧妙”》,引自《晉綏日報》1946年7月26日;宏流:《地主剝削式樣》,引自《晉綏日報》1947年3月30日。)等,與臭蟲利的意思是一樣的。在江蘇青浦縣稱“母子債”,到秋收不能償還利息,就重寫借據,將利作本,利上滾利,如借對本利1石,次年不還,第3年就還4石。(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江蘇省農村調查》,第217、20、61、439、47、61、140、216、439頁。)安徽宣城縣稱“放月利”,一般月利3分,每月利上滾利,一年后可滾至5倍。(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安徽省農村調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頁。)湖南臨湘縣,每元每日利息1角,滿10天即算復利,如此計算,借洋1元,1個月須還本利8元。(注:馮和法:《中國農村經濟資料》,黎明書局1933年版,第1125、1124、1125頁。) “驢打滾”,在有的地區,意指利息為本金的1倍,如太行山鄉村就有這樣的借貸習慣,借1元還2元,又稱“轱轆利”、“梯梯利”。(注:魏宏運主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2輯,中國財經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1326、1361、1326、1361、1360、542頁。)但通常含義是,屆期不還,利息加倍,是一種比利滾利更為苛刻的復利借貸。在河北豐南縣,這種借貸以一年為期,利息為50%,如到期不還,就利息加倍。(注:豐南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豐南縣金融志》初稿,1989年印,第5頁。)在河南新鄭縣,則以一月為期,利率4-5分,“如過期不還,則利率即按數學級數以增加,成為最厲害的復利!”(注:盧錫川:《新鄭縣唐河農村的調查》,載《河南大學農學院委刊》第1卷第3期,1930年。)在河北贊皇縣,將“到期不付利,利加一倍”的情況,又稱“大加一”。(注:魏宏運主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2輯,中國財經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1326、1361、1326、1361、1360、542頁。)天津郊區,稱“倍倍錢”。(注:實業部中國經濟年鑒編纂委員會:《中國經濟年鑒》上,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E198。)在湖南桃源縣,稱“孤老錢”,每月一對本,即借洋1元,過1個月還2元,過2個月還4元。(注:馮和法:《中國農村經濟資料》,黎明書局1933年版,第1125、1124、1125頁。)安徽滁縣關山鄉稱“老驢滾”,春季借稻1石,秋收還2石,到期不還,加倍計息,至翌年還4石。(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安徽省農村調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頁。)湖北隨縣稱“老呱呱”,借10元,1個月還本利12元,超過1天另收2元,超過2天收4元。(注:湖北隨州志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隨州志》,中國城市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頁。) “印子錢”,亦稱折子錢,規定債務人分期償還本息,債主將還款日期及每次應還本利數額寫在折子上,每還一次就在折子上加蓋印記,其主要特點是數額特小、期限特短、利息特高。在河北,此種借貸期限一般為2個月,短至1個月,鮮有過百日者。款額多為一二元,10元以上者極少。普通月利20分,如借銅元500枚,每日還本利20枚,一月共還本利600枚。(注: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中國農業金融概要》,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93頁。)天津郊區,農民需款少,就向印子房借,最多借5元,每日還5分,120天還完,本利共6元,月利達60分。(注:《中國經濟年鑒》上,E198。)在江蘇漣水縣,借錢10千,按10日攤還,每日繳還本利1200文,合月利60%。(注:陸國香:《蘇北五縣之高利貸》,載《農行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5月。)安徽安慶縣,借錢300銅元,每日還款15枚,1個月本利總數450枚,合月利50%。(注:汪洪法:《我國農民負債之特質》,載《文化建設》第2卷第6期,1936年。)
第三類:借多付少 借多付少與先扣利有形似之處,即債主付給債戶的數額都比約定本金減少,實際卻有質的區別。先扣利,是債主扣除部分或全部利息后再付給債戶少于本金的數額,債戶償還的是剩余利息和全部本金。借多付少,則不是因為扣除利息后付給債戶的金額減少,而是一種本金的部分扣除,債戶償還的仍是全部本金和全部利息。顯然,這是一種比先扣利更為苛刻的借貸習慣。 此類借貸在河北鹽山縣有的稱“回頭扣”,也是借8元按10元還本付息;有的稱“九出十歸外加三”,即借9元作10元,月息3元,每月還本利13元。(注:張愛國主編:《鹽山縣志》,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68—469頁。)在獻縣,債戶借10元,只能得到8元,至期仍還本金10元和全部利息。(注:1998年3月22日訪河北獻縣小流屯村朱玉庭等人資料。)在山西聞喜縣,向商號借貸百元,只給九十四五元,按百元還本付息。有的付給九十四五元后,還預先扣除百元的全部利息。這樣借者所得減至八九十元,本金百元仍要全部償還。(注:《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第811、776頁。)河南開封縣,有“大加一”之法,即借1000文,先扣除100文,得900文,仍按1000文行息。(注:《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第811、776頁。)在江蘇鹽城縣,稱“過頭錢”,債主將本以七、八折放出,約定兩三天或十天、八天償還,另加20-30%利息。(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江蘇省農村調查》,第217、20、61、439、47、61、140、216、439頁。)浙江吳興縣南潯區,則是蠶農冬季借糧,每石先交保證金2-4元,不予發還,還時仍照市價計算,并付月利2-3分。(注: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吳興農村經濟》,該所刊1939年版,第51頁。)安徽來安縣安樂鄉,稱為“八撞十”,借8元作10元算,外加利息。(注:安徽省財政廳等:《安徽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第1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291、299、299、320頁。)湖南耒陽縣、湖北部分地區稱“九出十歸外加三”,借9元作10元,月利3元,1個月還13元。(注:馮和法:《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第1124頁;南經庸:《湖北農村金融之建設與統治》,載《經濟評論》第1卷第2期,1934年3月。)
第四類:多算日期 從借貸日期上做文章,是債戶提高利率、剝削債戶的又一手段。 這種借貸在太行山區有出門2分利(算一月)、過6天算一月、兩月一季利,甚至出門半季利等名目。(注:魏宏運主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2輯,中國財經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1326、1361、1326、1361、1360、542頁。)山西有一種“臭蟲利”,又稱“日夜忙”,即一天一夜算兩天。(注: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山西金融志》初稿,1984年印,第136頁。)興縣高家村,有一種“捆月子”的辦法,即約定借期半年,4個月頭上提前還也得出半年的利;如至期還帳,則“過三不過五”,6個月零5天就算7個月的利。(注:胡正:《斗垮地主白老婆——高家村訴苦清算大會速寫》,引自《晉綏日報》1947年4月16日。)山東臨沂、郯城二縣“行利帳”的規定更為苛刻,過期一日,增息半月,過期半月以上,增息一月。(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編:《山東省華東各大中城市郊區農村調查》,1952年印,第70頁。)在江蘇上海縣馬橋區,借糧不論是前一年11月、12月,還是當年1月、2月,到7月收稻時,都要繳納同樣的利息。(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安徽省農村調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頁。)江西興國縣也是如此,借谷不管是去年11月、12月借的,還是今年1月、2月、3月借的,到7月割禾還債時,都要交50%的年利。(注:《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頁。)無錫梅村鎮,則是借款過月一日作一月計,如上月29日借,至下月1日還,利息須以2個月計,如本月5日借,6日償還,亦須支付1個月利息。(注:倪養如:《無錫梅村鎮及其附近的農村》,載《東方雜志》第32卷第2號,1935年1月。)浙江義烏縣也是如此,債主用兩頭月計算利率,如2月28日借的錢,即便在3月1日清償,也要算二個月。(注:吳辰仲:《浙江義烏縣農村概況》,引自天津《益世報》1935年3月9日。)
第五類:糧錢互折 農民在借糧、借錢時,債主根據市場物價的季節變動,對糧食與貨幣做有利于己的相互折算,核心是“聽漲不聽落”,以提高借貸利率。 最常見的是農民借糧食以后的糧錢折轉。在山西五寨縣,地主就有“籽折錢,錢折籽”的放貸辦法。沙灣村農民保后子1926年向地主借債40元,當年糧賤,地主就將錢折成40石莜麥。第二年,莜麥漲價,地主又將40石莜麥折錢280元。(注:宏流:《地主剝削式樣》,載《晉綏日報》1947年3月30日。)經過糧錢互折,二年間合年利300%。方山縣“放土債”的辦法則是,春夏之際借莜麥1斗,時價1000文,加5行息,至秋后償還時,如莜麥價格漲至1000文以上,就以1斗加息半斗歸還莜麥;如莜麥價格降至1000文以下,就按借麥時1000文的價格加息還錢。如債戶愿還莜麥,就按借時的高價折合成低價時的莜麥數額,另加息歸還。(注:司法行政部編:《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1930年印,第834、857、824頁。)在河南魯山縣,有“雙保險”、“兩頭利”之說,即借糧還錢者,糧價“聽漲不聽跌”,還債時按借用期間的最高糧價計算金額;借錢還糧者,糧價就低不就高,歸還時按借用期間的最低糧價折算糧數。(注:程岷源:《高利貸形式何其多》,載《魯山文史資料》第4輯,1988年。)在江蘇蕭縣長安村,貧民借糧時按當年最高市價折成銀元,到收獲時再按較低的市價折成糧食歸還,譬如借麥1石,按該年最高麥價每石10元計算,到收獲時,麥價跌至每石5元,就按此將10元折成2石小麥清償債務,利息達100%。(注:江蘇省立徐州民眾教育館:《長安村農村經濟調查報告》,載《教育新路》第12期,1932年12月。)在漣水縣,農民于春寒時借糧,收獲后以錢償還,糧價以春價計算,隨漲不隨落,故貸谷1斗,非2斗莫償。(注:陸國香:《蘇北五縣之高利貸》,載《農行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5月。)安徽來安縣安樂鄉也是如此,春天借糧1石,到清明時作價,聽漲不聽跌,待糧食下場時再依當地市價折成糧食付還,通常借糧1石,須償還2石左右。(注:安徽省財政廳等:《安徽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第1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291、299、299、320頁。)在湖北,農民春耕時借谷1石,以同樣的方式于秋收時還谷達3石。(注:程理锠:《湖北之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系》,蕭錚主編:《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臺北成文出版社、美國中文資料中心1977年版,第45599頁。)在湖南衡陽縣,稱這種借貸為“標谷利”,四、五月間借谷1石,以最高價折為現錢,第二年七、八月間又以最低價折谷償還。與上述蕭縣長安村不同的是,還要加月利6-7%,總共利息竟達原本的3倍以上。(注:馮和法:《中國農村經濟資料》,黎明書局1933年版,第1125、1124、1125頁。) 也有借錢還糧的折轉情況。如浙江南田縣的“放谷債”,借銀10元,至夏秋早稻或晚稻收獲時,以較低的市價折合還谷。(注:施沛生主編:《中國民事習慣大全》,上海廣益書局1924年版,第9頁。)安徽滁縣大王營鄉,債主先估計秋收新糧上市的價格,再按此對半付錢折成糧食放予債戶,群眾稱為“隨市作價,聽漲不聽跌”,如稻谷上市估計每石8元,僅借4元或4.5元,秋收時債戶還1石。(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安徽省農村調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頁。)歙縣巖寺區一地主借給農民30石糧的錢,按4千元1石折成糧,而當時糧價2萬元1石,等于借1石還5石,借30石糧的錢要還150石糧。(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安徽省農村調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