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住宅不可侵犯權(quán)
未知
【正文】
一、近代憲法對住宅不可侵犯原則的確認(rèn)
一般都認(rèn)為,作為憲法權(quán)利的住宅不可侵犯權(quán)是普通法“每個人的住宅是自己的城堡”(Everyone’s home is his own castle.)傳統(tǒng)的延續(xù),主要針對的是公權(quán)力的侵犯。從清末立憲開始,歷部憲法草案以及正式頒布的憲法都確認(rèn)了住宅不可侵犯的原則,不過具體行文上有所差異,也有一些很重要的爭論。
筆者見到的最早介紹上述原則的是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印行的一本憲法著作《中外憲法比較》。作者首先介紹了“家宅自主”的歷史起源:
“英人有言曰:各人之家,各人之城郭也。意蓋謂家者,無城壁以圍之,無城塹以界之。既不莊嚴(yán),復(fù)不壯大,渺然小也。然而人居于是,雖帝王不敢濫入焉。故謂之城郭。一私人之家,其尊而不可犯如此也。故今之立憲國,皆以此權(quán)載之于憲法,不許濫入家內(nèi)之門戶,不許妄拘家內(nèi)之眷屬,不許強取家內(nèi)之財物。”
然后作者列舉了世界各國憲法的有關(guān)規(guī)定。最后作者又回到中國歷史。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引用最為常見的《周禮》和漢律、唐律上“夜無故入人家”的資料外,作者特別指出,“人民各私其家”、“保家宅自主”觀念的出現(xiàn),是因為“民當(dāng)亂世,失家宅自主之權(quán),故各思自保。”作者感嘆說:“國之不存,家將焉附?知家宅失其主權(quán)為可痛,盍先群力以保此國家之主權(quán)哉!” 這不免夾雜了一些作者個人的不正確認(rèn)識,但也可以看出當(dāng)時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岌岌可危所給予知識分子個人的沉痛刺激。
宣統(tǒng)年間一份私人起草的《中國憲法草案》規(guī)定:“中國人民除法律限制外,若不受許諾,其家宅有拒絕他人侵入及搜索之權(quán)。”起草者解釋說:
“無故不得侵入搜索等事,中國法律固無不然,所痛者一般貪污州縣或巡視鄉(xiāng)里,或勘驗案件,縱差殃民,不一而足。除原告與被告應(yīng)遭災(zāi)禍外,凡附近民家,亦無不煨自侵入,借端訛索。窮愚拒之不敢,聽之不甘。故凡地方聞有是事,輒先期相戒,率家人避,偶有避之不及,則如遭劫然,粒粟寸草,為之一空。吁!我人民果無權(quán)乎哉?抑州縣官有以蹂躪而剝奪之也?”
在另外一份清末憲法稿本上也有類似的條文:“大清帝國臣民居處住所不得侵入。凡強入人家宅居,搜索人家中,又驗看人秘密文書信函等事,皆有法律定之,不得出法律范圍之外,不得違法律所定之格式與時效。”起草者解釋說:
“人為權(quán)利之主體,個人對國家所有之權(quán)利,曰法律上權(quán)利。法律必保護個人之利益。如有侵犯之者,必加以制裁。然有不法行為生法律上之結(jié)果時,則不能不服從法律,受國家權(quán)力之干涉。案:訴訟法上,人民居處住所家屋為私權(quán)上之特有權(quán),他人不得侵犯之。書信秘密權(quán)亦為憲法上所保護,他人不得儕押之。雖然,預(yù)審判事如因事實有必要時,不能不侵其所有權(quán)與秘密權(quán),以達(dá)檢證搜查之目的。”
清廷最后公布的《欽定憲法大綱(1908 )》也做了類似的規(guī)定,但要簡略許多:“臣民之財產(chǎn)及居住,無故不加侵?jǐn)_。”“無故”這一用語過于模糊,不符合法律明確性的要求。此后的憲法包括草案中都沒有再用這個詞。
辛亥革命之后,這一原則繼續(xù)得到堅持。《大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草案》(1912年1月25日)規(guī)定:“大中華民國國民,非依法律,不得侵入其住所及家宅。”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12年3月11日)規(guī)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袁世凱時期的《中華民國約法》也規(guī)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進步黨憲法討論會會員擬憲法草案》(1913年5月)規(guī)定:“中華人民居住之安全,非依法律所定無論何人不得侵之。”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憲法委員會決議,1919年8月12日)規(guī)定:“中華民國人民之住居,非依法不受侵入或搜索。” 曹錕時期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1923年)第七條也規(guī)定:“中華民國人民之住居,非依法律,不受侵入或搜索。”據(jù)當(dāng)時的制憲會議記錄,這一條文照原案通過,沒有爭議。 但在會議討論中李國珍曾就此條發(fā)表如下意見,對我們了解其立法意圖有所幫助:“第六條注意在住居安寧,故條文規(guī)定中華民國人民之住居非依法律不受侵入或搜索,至不加自由二字者,以居住自由另有第八條之規(guī)定。”
20世紀(jì)20年代也是省憲運動的時代。許多省的憲法也確認(rèn)了這一原則,并首次做出了針對軍隊侵占民房的規(guī)定。如湖南省憲法:“人民有保護其居宅之權(quán)。人民居宅不得駐屯軍隊,但戰(zhàn)時依法之程序得駐屯之。人民之居宅除經(jīng)本人允許偶或依合法之程序外,不受搜查檢查。”浙江省憲法也規(guī)定:“省民有住居不可侵權(quán)。省民住宅無論平和戰(zhàn)士,非經(jīng)所有人及住居人承諾或依合法程序不得借作公用。”也有一些維持了原來的規(guī)定。如《湖北省自治法草案》規(guī)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一份由自治同志會撰寫的憲法大綱草案也規(guī)定:“人民的住宅非依法律不受侵入或搜索。”
20世紀(jì)30年代,國民黨政權(quán)穩(wěn)定之后,又出現(xiàn)了一個起草憲法的高潮。閻錫山主持制定的《中華民國約法草案(1930年10月29日擴大會議在太原公布)》第三十三條規(guī)定:“人民之居住非有犯罪嫌疑或證據(jù),經(jīng)有該管官署負(fù)責(zé)之聲明,不得侵入或搜查。” 但《訓(xùn)政時期約法》(1931年6月1日公布)第十條堅持了以前比較簡單的規(guī)定:“人民之住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錮。”
到五五憲草時,對上述規(guī)定產(chǎn)生了較多的爭論,特別是對是否將“但書”條款具體化的問題。討論的基礎(chǔ)是最先公布的兩份私人草案——吳經(jīng)熊草案和張知本草案。吳案規(guī)定:“人民有居住之自由,其居住處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錮。” 張案規(guī)定:“人民有居住之自由,非因犯罪或其它緊急危難,不得侵入或搜索。軍隊除戰(zhàn)事區(qū)域或租賃外,不得屯駐于人民之住宅。人民有遷徙之自由,非妨害公共秩序及善良風(fēng)俗,不得停止或限制。”
許多人都對后一種規(guī)定的具體化風(fēng)格持肯定態(tài)度。如中華民國律師協(xié)會常務(wù)委員會變相贊成后一種意見,建議規(guī)定為:“人民有居住之自由,其居住所在,非有法律規(guī)定之原因,及有法院之命令,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閉。違反上述規(guī)定這,應(yīng)負(fù)刑法與民法上之責(zé)任。” 湖北憲草研究會則沿襲了太原約法的規(guī)定:“人民之住所非有犯罪嫌疑或發(fā)見犯罪證據(jù),不得侵入或搜索。” 還有人建議:“搜查人民住宅以日間為限,并須依照法令及合法手續(xù),而經(jīng)憲法明文規(guī)定者行之。”
著名法學(xué)家章友江的評論最為詳細(xì),有許多可以和張知本的意見互為發(fā)明之處。他對吳、張草案以及此前的太原約法都提出批評:
“居住為人民養(yǎng)護之地,當(dāng)有完備的安全保障。人身自由為自由的基本,而居住自由則為其靜止的方面,故非常重要。吳氏草案對于本條之規(guī)定過于簡單…和張氏的草案比較,只見其含混不周而已。”
對太原約法:
“這一條文的特點在注明搜索等須有該官署負(fù)責(zé)之聲明,否則即不能任意搜索。但仍有流弊。因為他沒有沒有規(guī)定侵入或搜查的聲明應(yīng)由司法機關(guān)頒發(fā),如波憲一00條,希臘憲法第十五條規(guī)定,非有法定原因及法定方式,不得侵入及搜查住所。這就是太原約法及張氏草案的概括,但過于簡單。”
章還詳細(xì)討論了軍隊侵占民房的問題說:
“軍隊占民房,在中國已變?yōu)槌@袝r且將民房任意拆毀損害,民不堪苦者久矣。張氏草案能顧及之,可謂良藥對癥也。張氏草案條文注明搜索或封錮的理由,以確定居住自由的范圍,使人民容易領(lǐng)會而做保障此項自由的標(biāo)準(zhǔn),此亦其優(yōu)點也。”
章提出了自己的具體修改意見:
“中國人民的住宅任意受軍警的侵入搜查,應(yīng)當(dāng)在憲法中更具體的規(guī)定其手續(xù)。參考猶哥憲法十一條,我以為吳氏憲法草案二十六條應(yīng)修改之如左:人民之居住,非有犯罪嫌疑,緊急危難,或公益之故,不得侵入搜索封錮或扣押文書器物。當(dāng)未搜索之前,官廳須示法院所頒發(fā)而列具搜索理由之令狀。被搜查者見此令狀后,得向就近法院申訴,但此項申訴不能阻止搜查之進行,搜查須立即執(zhí)行,并須有公民兩人臨場,搜查既畢,官廳應(yīng)立即告被搜索人以搜索之結(jié)果,并關(guān)于一切攜去被查之物件,開給正式簽字之單據(jù)。夜班巡警,除遇倉促事變,例如聞屋內(nèi)呼救之聲外,不能擅入住宅,若于夜間有入住宅之必要時,須有當(dāng)?shù)厝嗣翊砘蚬忻袢嗽趫霰O(jiān)視。”
他還認(rèn)為,僅有“這種規(guī)定還是不夠的,因為對于違反這項條文的人,沒有規(guī)定相當(dāng)?shù)奶幜P,所以在實際上,上文等于虛設(shè)。吳氏張氏及太原約法草案,均無此項規(guī)定,故是缺點。猶哥憲法第十一條規(guī)定,官吏違反上述各條規(guī)定者,以非法侵入住宅論罪。但希臘憲法十五條的規(guī)定更為完美。”他建議增加一條:“凡違犯是項規(guī)定者,以非法侵?jǐn)_住宅論罪處罰,并應(yīng)賠償一切損失,給付賠償金,此項賠償金額,由法院定之,但決不能少于二十元。”
但也有一些人傾向于吳經(jīng)熊的草案。如陳肇英草案規(guī)定:“人民有居住之自由,其居住處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錮。” 第一次公布的憲法草案初稿規(guī)定:“人民居住處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錮。”當(dāng)時有人提出意見說:“應(yīng)改為人民有居住之自由,其居住處所,除遇室內(nèi)呼助,或不可抗力之情形,與現(xiàn)行犯發(fā)生室內(nèi)等事,得由警察逕自侵入外,非依法庭之命令,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錮。”理由是“以防止政府之恣肆行為而保障人民之自由福利。” 但最后通過的五五憲草采納了吳的意見:“人民有居住之自由,其居住處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錮。” 據(jù)會議記錄,在具體討論的時候,原稿無“居住自由”四字,經(jīng)黃右昌提議、吳經(jīng)熊附議而添加。
抗戰(zhàn)后期開始了新一輪制憲運動。當(dāng)時國統(tǒng)區(qū)的意見大略不外上述。這里要介紹的是共產(chǎn)黨提出的草案。1946年延安向政協(xié)提出了兩份草案,一份是在五五憲草基礎(chǔ)上修改的。該案規(guī)定:“人民有
教學(xué)參考.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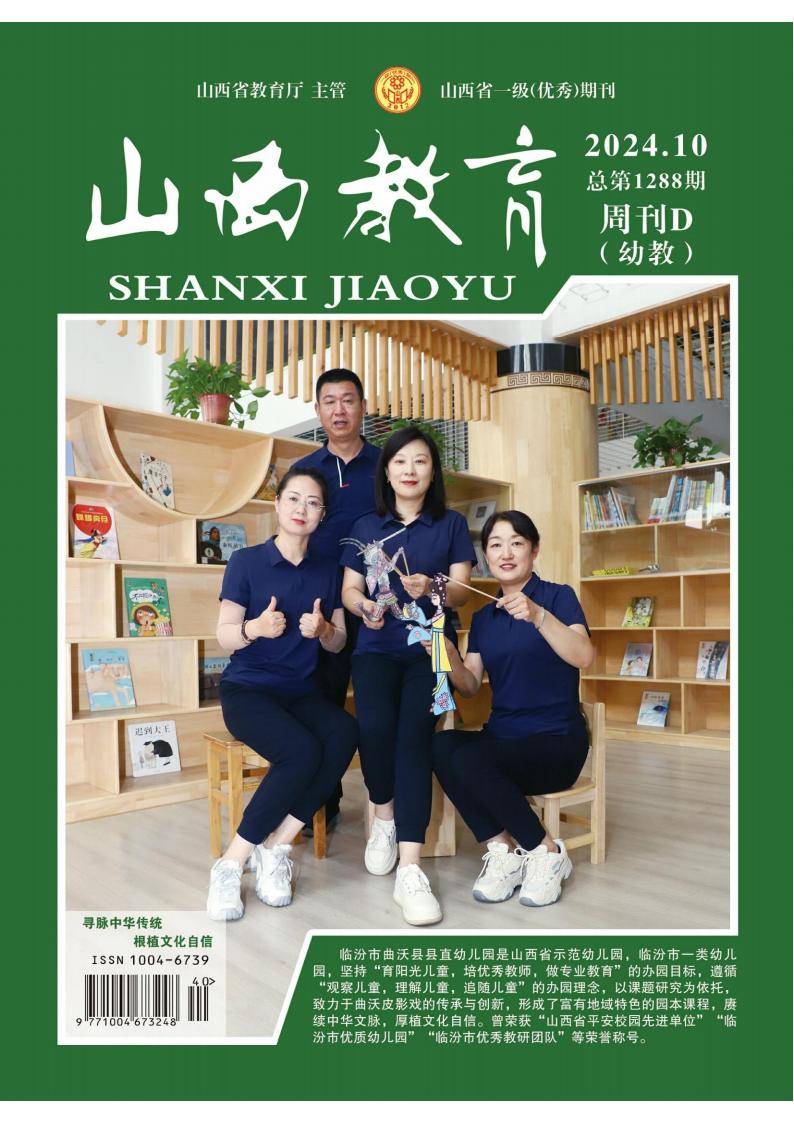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