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主義形態(tài)轉(zhuǎn)變之嚆矢:近代中國海防愛國主義
邵先軍 崔家生
摘要:愛國主義由古典到近代的形態(tài)轉(zhuǎn)變是時代的要求。近代中國海防危機(jī)牽引下的愛國主義噴涌澎湃。既有古典愛國主義傳統(tǒng)中御敵獻(xiàn)身精神的延續(xù)傳承、發(fā)揚光大,又有學(xué)習(xí)西方這一愛國主義近代要素在反侵略中孕育萌芽。鴉片戰(zhàn)爭前后海防前線的愛國實踐,開啟了愛國主義的形態(tài)轉(zhuǎn)變,“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近代愛國主義萌芽是在海防反侵略實踐中孕育、在總結(jié)反思海防戰(zhàn)爭失敗中被明確提出來的。
關(guān)鍵詞:愛國主義;形態(tài);轉(zhuǎn)變;海防愛國主義
近代百余年,中國處于劇烈的變革轉(zhuǎn)型時期,既有的愛國主義傳統(tǒng)頑強地發(fā)揮了其特定的歷史作用并逐漸得到更新,新的愛國主義內(nèi)涵艱難孕育并日漸形成。愛國主義從古典到近代形態(tài)的發(fā)展轉(zhuǎn)變,濫觴于海防領(lǐng)域。海防是維護(hù)國家主權(quán)、領(lǐng)土完整和安全,國家海洋權(quán)益,防備外來侵略而進(jìn)行的軍事、政治、外交、經(jīng)濟(jì)、科技和教育方面的建設(shè)和斗爭。海防事務(wù)主要是指防御外敵從海上入侵的事務(wù)。可見,海防和愛國主義緊密相連,從一定意義上講,愛國是海防事務(wù)的必然主題,熱愛海防、關(guān)心海防、建設(shè)海防是愛國的必然要求,海防事務(wù)是愛國主義的重要表現(xiàn)途徑。因此,凡是本著熱愛祖國的海防、維護(hù)祖國海防利益而進(jìn)行的建設(shè)海防、保衛(wèi)海防的思想和實踐,都可稱為海防愛國主義。海防愛國主義既是愛國主義在海防領(lǐng)域的一種特殊形態(tài),又包含著愛國主義的一般。我們把近代史上國人保衛(wèi)海防、建設(shè)海防過程中體現(xiàn)出來的愛國情懷稱為近代中國海防愛國主義。
一、中國社會從古代到近代的性質(zhì)轉(zhuǎn)變,對愛國主義從古典到近代的形態(tài)轉(zhuǎn)變提出了必然要求
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決不是一次普通的海防反侵略戰(zhàn)爭,它的爆發(fā)是一個標(biāo)志。在此之前,中國是一個與外部世界來往不多、獨立發(fā)展的封建社會;自此之后,中國由獨立的封建社會逐漸演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文化的發(fā)展,往往要打上帝國主義侵略壓迫的烙印,表面看起來中國似乎是獨立的,實質(zhì)上國家主權(quán)已受到帝國主義的嚴(yán)重侵害。這樣的社會性質(zhì),從晚清到民國,一直也沒有改變。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止,近代這110年的社會性質(zhì),前不同于秦漢以來任何一個歷史朝代,后不同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特殊的社會歷史形態(tài),即在封建社會崩潰中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近代中國政治黑暗,經(jīng)濟(jì)凋敝,社會殘破,民不聊生,國家瀕臨滅亡的邊緣。巨大的屈辱和災(zāi)難,給中華民族提出了新的歷史任務(wù),正如十五大報告指出的:“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華民族面對著兩大歷史任務(wù):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xiàn)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務(wù)是為后一任務(wù)掃清障礙,創(chuàng)造必要的前提。”在強烈的愛國精神的鼓舞下,中國人民開始了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艱難而執(zhí)著的探索。一個又一個救國方案被提了出來,又在社會實踐中逐個失敗,經(jīng)過了一系列這樣不可缺少的發(fā)展環(huán)節(jié)之后,直到中國共產(chǎn)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dǎo),領(lǐng)導(dǎo)全國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才完成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第一個任務(wù),也為第二個任務(wù)即實現(xiàn)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
在這一時期里,中華民族能夠歷盡千難萬險,百轉(zhuǎn)千回,卻矢志不渝,不屈不撓,終于迎來了最后的輝煌,離不開愛國主義提供的強大精神動力。在異常強大的敵人面前,我們的民族沒有屈服,在極端深重的危機(jī)面前,我們的國家沒有滅亡,如果沒有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強大支撐,這是不可想象的;在這一時期里,偉大的中國人民在百般屈辱中卻能夠漸漸覺醒,我們的社會在千災(zāi)萬難中卻能夠始終保有進(jìn)步的動力,我們的民族獨立逐漸淪喪最后卻能夠失而復(fù)得,如果愛國主義一直停留在與封建社會農(nóng)耕經(jīng)濟(jì)條件相適應(yīng)的古典形態(tài),同樣也是不可想象的。每一次反對外敵入侵的抗?fàn)帲瑹o不凝結(jié)著愛國主義的熾烈激情;每一個救國方案的提出,無不閃耀著愛國主義的理性光芒;每一個救國方案的實踐,都向愛國主義本身提出了順應(yīng)時代潮流而發(fā)展升華的必然要求;而每一次救國實踐的失敗,又都激起了愛國救亡的更大浪潮。同一段歷史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解讀,近代百年既是中華民族在愛國主義旗幟下救亡圖存的歷史,是中國社會近代化的歷史;同時也是愛國主義自身在仁人志士的探索奮斗中蛻變轉(zhuǎn)化的歷史,是中國近代愛國主義孕育、生成、發(fā)展、成熟的歷史。
愛國主義作為一種觀念形態(tài)的社會意識和社會心理,屬于社會政治文化范疇,是一定政治和經(jīng)濟(jì)的反映。在人類社會發(fā)展歷史過程中,由于國家在不同時代所面臨的矛盾、困難、任務(wù)和目標(biāo)的不同,反映在愛國主義上會使其呈現(xiàn)出一定的時代性特征,因而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范疇,“愛國主義的具體內(nèi)容,看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之下來決定。”愛國主義的不同歷史內(nèi)容,反映了不同時代或同一時代不同發(fā)展階段中,國家民族最高利益所面臨的挑戰(zhàn)和矛盾的不同。中國古代社會長期的封建農(nóng)耕經(jīng)濟(jì)文化條件,形成了以“華夏中心主義”為基調(diào)、以“忠君”為表現(xiàn)形式的古典愛國主義傳統(tǒng)。中國社會從古代到近代的轉(zhuǎn)型,必然要求發(fā)展出與近代社會經(jīng)濟(jì)文化條件相適應(yīng),滿足近代中國需要,符合近代中國特點的愛國主義形態(tài)。
二、近代中國海防愛國實踐的噴涌澎湃,為愛國主義從古典到近代的形態(tài)轉(zhuǎn)變提供了現(xiàn)實可能
令中國“處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數(shù)千年未有之強敵”主要來自海洋方向。“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fā)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帝國主義侵略是近代中外民族矛盾的直接起因,并且加劇了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在近代歷史上,“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們,都打過我們”,百余年間,帝國主義先后發(fā)動了數(shù)百次侵華戰(zhàn)爭和事變,這些侵略,絕大多數(shù)來自海洋方向,或是與海軍有很大的關(guān)系。“在一百余年的中國近代史中,真是有海無防,僅來自海上的外國入侵竟達(dá)四百七十余次。”甚至有人認(rèn)為“從一定意義上說,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列強侵略中國的歷史,更是一部列強從海上侵略中國并頻頻得手的歷史。如果說侵略與反侵略戰(zhàn)爭是構(gòu)成中國近代歷史發(fā)展演變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那么,在海洋方向入侵與反入侵的軍事斗爭,則關(guān)系著侵略與反侵略戰(zhàn)爭的勝負(fù)成敗,從而也就決定了近代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命運。”
我們經(jīng)常說,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了近代中國的大門,其實,這不僅僅是對鴉片戰(zhàn)爭一例個案的生動描述,也是對以其為代表的整個近代期間帝國主義侵略特點的準(zhǔn)確概括。首先,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基本上都是海上強國,其侵略行為帶有濃厚的海洋背景——通過海上霸權(quán)對外侵略擴(kuò)張是當(dāng)時資本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共同特征。其次,對中國的歷次侵略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依賴海軍,列強的海軍在戰(zhàn)爭中或為主力或為先導(dǎo),平時也動則以武力相威脅。嚴(yán) 復(fù)曾感嘆:“自道咸以來,沿海諸邊,往往多事”。“邇者江淮之間,英日最盛,而德亦狡焉思逞矣。俄涉東省,法人滇粵……凡其淺水軍艦,隨時皆有直達(dá)腹地之憂,而地方官吏始棘手矣。或交涉稍有枝節(jié),或萑苻稍見鴟張,動且鼓輪而來,裝炮懸旗,肆行恫喝。”即使是與中國陸地接壤的俄羅斯,海軍力量在侵略中國時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璦琿條約》的簽訂,奕山就受到了俄國兵船鳴槍放炮的武力威脅。在后來的北京談判過程中,俄國故伎重施,派兵船集結(jié)在天津附近海面。
列強侵略接踵而至,萬里海疆頻頻告急,觸發(fā)了海防抗?fàn)幍娘L(fēng)起云涌,隨著民族戰(zhàn)爭依次爆發(fā),海防愛國主義在近代反侵略抗?fàn)幹惺桩?dāng)其沖,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高潮。近代中國在列強堅船利炮的沖擊下海禁大開,海防形勢異常嚴(yán)峻,面對“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海防建設(shè)一方面任務(wù)異常復(fù)雜艱巨,另方面卻要面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意無意制造的重重阻礙與困難。此雖非中國之福,而中國必自此而自強。正是這緊張嚴(yán)峻海防形勢、脆弱如卵的海防安全和一再失敗的海防斗爭,給國人上了最生動直觀的海防教育課,極大激發(fā)了愛國主義熱情,加速了民族覺醒,令“自應(yīng)建數(shù)千年未有之奇業(yè)”成為時代的呼聲。
為建設(shè)海防、保衛(wèi)海防,中國人民外與侵略者、內(nèi)與賣國勢力進(jìn)行了尖銳的斗爭,表現(xiàn)出熾熱的愛國情感、深沉的理性探索、堅韌的愛國意志和無私的效國實踐。尤其是“在民族戰(zhàn)爭期間,愛國主義為社會接受的程度最廣泛,其傳播的范圍和速度急劇擴(kuò)大和加快。”在列強堅船利炮的沖擊下,愛國主義凸顯為一切要求進(jìn)步的中國人反抗侵略的共同思想基礎(chǔ),“救亡圖存”的口號將各個階級和階層的志士仁人都召集到愛國主義這面旗幟之下,匯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一方面,代表先進(jìn)生產(chǎn)力的資本主義海上強國對中國進(jìn)行非正義的侵略,占據(jù)反侵略正義地位的中國封建主義在生產(chǎn)力上卻落后于敵,而且始終以維護(hù)自身狹隘統(tǒng)治利益為最高目的,往往置民族大義于不顧投降賣國,使得以忠君為表現(xiàn)形式的古典愛國主義在海防斗爭實踐中雖發(fā)揮了巨大作用但卻最終被證否;另一方面,海防愛國主義應(yīng)時代召喚而噴涌澎湃,海防慘敗的苦果一再激起新的探索,列強侵略造成的一切負(fù)擔(dān),最終都轉(zhuǎn)嫁到勞動人民的頭上,使得廣大民眾具有最頑強的反抗精神,形成了近代愛國力量的堅定主體。由海防形勢演變引起的如此種種情形慢慢匯集成某種客觀條件,使古典愛國主義的經(jīng)濟(jì)、政治和社會心理基礎(chǔ)發(fā)生了動搖,為愛國主義內(nèi)容實現(xiàn)蛻變超越,孕育出符合時代要求的近代形態(tài)提供了現(xiàn)實可能。 三、海防愛國主義孕育了近代愛國主義的萌芽,開啟了愛國主義從古典到近代形態(tài)的蛻變超越
反抗侵略,鞏固海防,是近代中國海防愛國主義的中心主題。在這一主題之下,中國古典愛國主義傳統(tǒng)中的御敵獻(xiàn)身精神在海防領(lǐng)域延續(xù)傳承、發(fā)揚光大,“華夏中心主義”等陳腐思想在嚴(yán)峻的海防危機(jī)中得到批判擯棄蛻變超越,“師夷長技以制夷”等近代愛國主義要素在海防需要中得以孕育萌芽傳播擴(kuò)散。
抵御外侮、反抗侵略,是愛國主義的永恒主題,既是中國古典愛國主義與近代愛國主義的相同主題,也是近代中國不同形態(tài)愛國主義共同的基本主題。在中國古代史上,凡是外患襲邊、民族危難之際,就是愛國主義噴涌高漲之時,就會有民族英雄挺身而出,英勇抗敵。霍去病、岳飛、文天祥、戚繼光、史可法……抵御外侮、反抗侵略,作為中華民族精神一種的象征,是千百年來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華,光輝閃耀,世代流傳。
帝國主義頻繁的海上入侵,決定了民族戰(zhàn)爭是近代中國歷史舞臺上最為直接、最為激烈、最為悲壯、也是最為人們所熟悉的愛國主義表現(xiàn)形式。歷次海防戰(zhàn)爭本身就體現(xiàn)著中國愛國主義的光輝,戰(zhàn)爭的根源是“西人東來”的侵略意圖與國人保衛(wèi)家園的愛國精神之間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古典愛國主義在近代海防戰(zhàn)爭中的自然延續(xù),一方面使御敵獻(xiàn)身精神發(fā)揚光大,如眾多將領(lǐng)的以身殉職、無數(shù)無名戰(zhàn)士和百姓的血灑海疆,另方面也逐漸產(chǎn)生出愛國主義的近代因素。
近代愛國主義有三個基本要素:一,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是近代愛國主義的基本主題;二,向西方學(xué)習(xí),是反帝愛國的合理手段和核心要素;三,反對封建專制制度,是反帝的邏輯要求和學(xué)習(xí)西方的歷史流向。
如前所述,反抗外敵侵略也是古典愛國主義的基本主題之一,所以反抗帝國主義侵略這一要素的近代特性只能是“帝國主義”。很明顯,這只能是中國愛國主義近代化的一個外部動因和邏輯前提。歷史表明,近代早期,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最初所表現(xiàn)出來的恰恰也只能是古典愛國主義的自然延續(xù),而它又無技以制夷”從少數(shù)先進(jìn)分子的個別思想,發(fā)展為影響廣泛的社會思潮,進(jìn)而形成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最終趨向反封建的歷史道路,代表了近代愛國主義層層遞進(jìn)的展開過程。這一過程的核心要素是向西方學(xué)習(xí),這一要素的最早萌芽,是在海防實踐中孕育并被明確提出來的。
鴉片戰(zhàn)爭期間,購置和仿造西式武器裝備的師夷制夷活動已經(jīng)在海防前線出現(xiàn),開啟了近代中國學(xué)習(xí)西方的最早實踐。林則徐認(rèn)識到“彼之大炮,遠(yuǎn)及十里內(nèi)外,若我炮不能及,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提出引進(jìn)西方“良器”,學(xué)習(xí)西方“熟技”。他曾組織編譯有關(guān)西式大炮瞄準(zhǔn)發(fā)射技術(shù)的書籍,還委派龔振麟等人對西式武器加以研究和仿造。佛山的軍工廠采用了許多西方造炮技術(shù),在加工工藝、瞄準(zhǔn)儀器、炮彈種類、發(fā)火裝置、炮座、火藥配比等技術(shù)上進(jìn)行了模仿和改進(jìn)。林則徐到粵后“購西洋各國洋炮二百余位,增排兩岸……并購舊洋船為式,使兵士演習(xí)攻首尾、躍中艙之法”,又曾“捐資仿造兩船,底用銅包,篷如洋式”。廣州知府易長華和士紳潘仕成模仿夷船式樣制造了戰(zhàn)船。潘仕成和大城知縣高邦哲還分別制成水雷并進(jìn)行了實驗。在浙江戰(zhàn)事吃緊之時,嘉興縣丞龔振麟首創(chuàng)鐵模鑄炮法,大大加快了鑄炮速度。魏源稱贊該法“一工收數(shù)百功之利,一炮省數(shù)十倍之貲,且旋鑄旋出,不延時日,無瑕無疵,自然光滑,事半功倍”。1842年,龔振麟著成世界上最早全面論述金屬型鑄造的科學(xué)著作《鑄炮鐵模圖說》,并印發(fā)沿海各省參用。
即使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認(rèn)中國人學(xué)習(xí)西方的成果,1842年6月攻陷吳淞后,英軍在當(dāng)?shù)剀姽S中發(fā)現(xiàn)了中國仿制的西式大炮和滑臺。因此。在近代反帝愛國運動中先后登上歷史舞臺的兩種潮流,向西方學(xué)習(xí)和反對封建制度,才是近代愛國主義的關(guān)鍵因素。近代愛國主義在反侵略中孕育,在學(xué)習(xí)西方中萌發(fā),在反封建中確立。可見,“師夷長技”:“這并非第一次看到中國人的才智和善于模仿,我感到這次戰(zhàn)爭在某些方面,將使他們得到的好處比壞處要多。戰(zhàn)爭將啟發(fā)他們的智能,將來任何時候如果和中國人再發(fā)生戰(zhàn)爭,我們將比這次遭到更多的困難。”如果說戰(zhàn)爭真能啟發(fā)智能,那么也只能是外因,它的啟發(fā)離不開內(nèi)因的作用,鴉片戰(zhàn)爭在中國首先啟發(fā)的是那些戰(zhàn)時堅決抵抗侵略和戰(zhàn)后繼續(xù)關(guān)心海防、建沒海防的有愛國心、報國志、效國行的人的智能。
理論來源于實踐。鴉片戰(zhàn)爭期間及戰(zhàn)后,嶺南地區(qū)和江浙、福建等東南沿海抗英前線曾經(jīng)一度出現(xiàn)購置、仿制西洋武器的浪潮,雖然由于技術(shù)障礙及戰(zhàn)后清廷上下茍安思想抬頭和對海防建設(shè)的忽視,它并未帶來近代軍事工業(yè)在中國的勃興和西洋軍事技術(shù)的大規(guī)模引進(jìn),說明此時尚未形成向西方學(xué)習(xí)的普遍自覺。但它畢竟是近代中國引進(jìn)西方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shù)的初次嘗試,是中國早期近代化的第一次啟動,是國人御侮抗敵激情和理性的結(jié)晶,展現(xiàn)了近代中國海防愛國主義的一個方面,為海防愛國主義的后續(xù)發(fā)展提供了一個起點,開啟了一條道路,為心憂海防的人們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jīng)驗和思想營養(yǎng),對戰(zhàn)后一些目光敏銳的思想家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先進(jìn)主張?zhí)峁┝藛⑹竞徒梃b的材料。曾參加過鴉片戰(zhàn)爭浙東抗英的魏源,戰(zhàn)后把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如何抵御和戰(zhàn)勝列強侵略上面。他與林則徐交游甚密,承其志,繼其業(yè),在林所輯《四洲志》的基礎(chǔ)上,歷經(jīng)十余年之艱苦努力,幾經(jīng)擴(kuò)版,增補編撰成長達(dá)百卷的《海國圖志》。在序言中他明確指出:此書是“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并稱“攘剔”外敵,“奮武”海防,“此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畫也”,愛國激情躍然紙面。他在書中飽含激情而又不失理性地總結(jié)反思了鴉片戰(zhàn)爭失敗的經(jīng)驗教訓(xùn),勇于承認(rèn)先進(jìn)技術(shù)在戰(zhàn)爭中的重要作用,認(rèn)為“力不均、技不等而相攻,則力強技巧者勝”,明確提出向西方學(xué)習(xí),“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以期達(dá)到“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制之”的目的。可見,“師夷”只是其海防思想之手段,而目的則是“攻夷”、“款夷”、“制夷”。
四、結(jié)語
中國古典愛國主義與近代愛國主義區(qū)別的關(guān)鍵在于反侵略的途徑不同,不同的反帝途徑又形成不同的歷史流向,嚴(yán)守“夷夏大防”與師夷制夷革新變法是二者區(qū)別的重心所在。愛國主義在近代中國正是以其古典形態(tài)作為出發(fā)點。在反抗帝國主義海上入侵的偉大斗爭中,應(yīng)海防需要而逐漸孕育出學(xué)習(xí)西方這一近代因素的最早萌芽。“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萌芽誕生得異常艱難,它沖破了“華夏中心主義”的思想樊籬,驚醒了“天朝上國”無所不有的迷夢,顛覆了“用夏變夷”的單向文化傳播思維定式,給近代中國帶來了思想解放的第一縷曙光。雖然其成長壯大仍然阻力重重甚至因而一度停滯不前,但是巨大的軍事功利價值賦予其頑強的生命力,它一旦產(chǎn)生就會沿著自己的邏輯向前發(fā)展了。近代中國學(xué)習(xí)西方經(jīng)歷了一個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上升過程,愛國主義從古典到近代形態(tài)的蛻變超越,歸根結(jié)蒂是從海防愛國主義肇始的。

線.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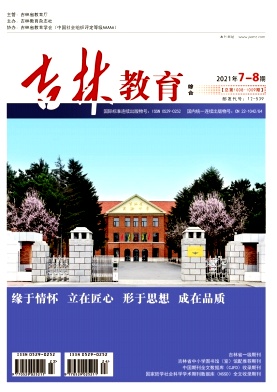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