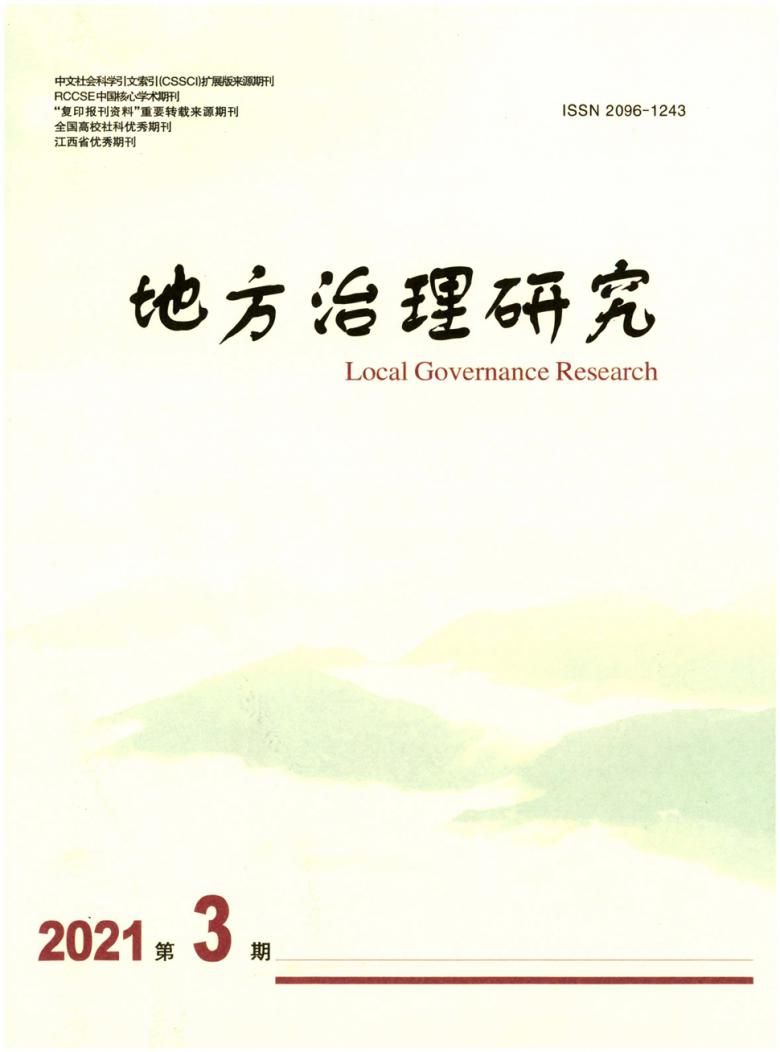中國外出農民工及其匯款之研究
佚名
一、外出農民工匯款研究的理論背景
在城市農民工、流動人口問題研究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研究農民工外出對于流出地的農村發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在此問題上,一直有兩派針鋒相對的理論觀點。一派是所謂“現代化理論”,強調農民工、流動人口的積極意義,認為,農民工的流出是城市化、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環節,可以帶來農村地區的發展,可以使外部世界的資金、技術、信息、新觀念傳到農村,可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Ahlburg ,1996:391-400;Solinger,1999:184;Parish,1973:591-609)。另一派是所謂“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 ),它認為,作為核心地帶的大都市的發展,是建立在農村地區的不發展基礎之上的,換言之,都市地區的發展是以對作為邊緣地帶的農村地區的剝奪和剝削為前提的(Frank ,1985:160;Santos:1985:171-172)。“依附論”提出了大都市與邊緣衛星地帶(metropolis-satellite)的觀點,認為,目前發達與不發達地區之間的關系是,發達的大都市地區剝奪了不發達的邊緣衛星地帶的剩余價值或經濟剩余。所謂“發達的大都市地區與不發達的邊緣衛星地帶”的關系是層層推進的,比如,相對于歐美發達國家而言,不發達國家就成了邊緣衛星地帶;而在不發達國家內部,相對于該國的中心大都市地區而言,該國的農村地區則成了邊緣衛星地帶。弗蘭克說,審視這種“大都市—衛星”的結構,我們可以發現,每個衛星都扮演著一種吸收其本身的衛星的資本和經濟剩余,并將部分的剩余輸送至都市中心的角色(Frank ,1985:160)。依附論所涉及的不僅是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而且,該理論也在探討一國之內不同區域發展的關系、富裕地區與貧窮地區的關系。
筆者以為,上述兩派觀點在經濟學理論上也表現為,均衡論與非均衡論之爭。所謂“均衡論”認為,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一個國家的生產要素與商品是可以在各地區之間自由流動的,這種自由流動的結果是,該國家各地區的工資水平和利潤率是會逐漸趨于平衡和均等的,這種演變的結果會促使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十分均衡地上升。也就是說,否認在市場條件下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性。所謂非均衡論則認為,市場的發展,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最終帶來的是“不均衡”。資本和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是“極化效應”,從城市流往農村是“涓流效應”。美國經濟學家赫什曼認為,受到提高收益力量的驅動,勞動力與資本總是從邊緣地區(農村)迅速地流入核心地區(城市),結果是強化了極化效應,進一步促進了核心區的發展(周起業等,1989:6-7)。所以,非均衡論認為,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極化效應總是處于支配地位。要改變這種狀況,要縮小地區差距,切實可行的辦法只有加強政府的干預。通過這種干預,使地區發展的步伐得到調節。
那么,中國農民工流動的結果究竟如何呢?農民工進城打工、匯款回家,究竟是縮小了城鄉的差距,推進了農村的經濟發展呢?還是造成了更大的不均衡呢?中國農村工在城市里打工、匯款回家鄉的模式究竟與其他國家的模式相同?還是不同呢?中國外出農民工給家庭匯款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呢?針對上面所陳述的焦點問題,中國案例所證明的,究竟是更傾向于現代化理論呢?還是依附理論呢?本文試拋磚引玉,闡述一孔之見。
本文提出的一些假設和驗證都建立在幾次實證調查的基礎之上。最主要的調查有兩次。一次為農村調查,是1999年8月,筆者組織對四川15個區縣農村地區移民和外出農民工的家庭進行調查,采用入戶調查方式,共完成農民家庭戶有效問卷451份。下文中,凡標注1999年數據的,即指此次調查。另一次為城市調查,是筆者于2000年11月組織中國人民大學和清華大學師生,在北京市豐臺區的右安門、西羅園、東鐵匠營、豐臺鎮、花鄉,以及在此區域內的建筑工地、服裝城、農民工集中居住點等地區做的問卷調查。豐臺是北京地區外來民工最為集中的地區,外來流動人口大約有32萬人。該調查采用配額抽樣和問卷面訪方式進行,共完成有效問卷493份。下文中凡標注2000年數據的,即指此次調查。本文以下的分析,主要是依據這兩次調查的數據。此外,人民大學的王鼎同志也于2000年7月在北京市做了一次流動人口問卷調查,本文有一處使用了該數據,并在使用之處作了特別說明。在此,謹對參加上述調研的全體師生致以謝意。再者,本文少數地方還使用了筆者過去的“個案”研究材料。
在開始正文之前,還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匯款”一詞,是泛指農民工寄回和帶回家鄉的錢,由于“寄回和帶回”說起來比較羅嗦,所以,就簡稱“匯款”。另外使用“匯款”說法,與國際學界在此問題研究上的"remittance"一詞也可以對應。總之,請不要誤解為僅僅是從郵局寄的錢。
自農民工外出打工以來,匯款就成為改變農民家庭生活,甚至是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資金來源。關于該項資金的影響作用,歷來為社會學家們所關注。
二、中國外出農民工匯款比例高于其他國家
外出農民工給農村的家庭匯款的現象,在對其他國家農民工的研究中也常見到(Ahlburg,1996:391-400),此種現象本身不足為奇。然而,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外出農民工匯款的比例最高。
在國際上,以往的研究證明,外出農民工向家鄉匯款的比例一般是很低的。例如,印度西北部的12個村莊,外出農民工匯款占農民家庭總收入的比例為0.1%至39%不等,平均為6.5%,印度東部農村為0%至8.4%不等,平均為1.3%,其他的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以及新幾內亞、利比亞等非洲國家的情況也均如此(周紅云,1996:37;康內爾,1976:96)。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國外出農民工往家鄉匯款或帶款的比例通常較高。比起上述國家來,比例顯然是高多了。根據以上所述及的筆者組織的兩次調查的數據,均可以證明中國城市農民工高比例匯款的現象。
首先,我們看看農民工往家鄉匯款的情況(見表1)。
表1農民工給家庭匯款分組(1999年)
在表1中,70.3%的農民工都給家里匯款,比例是不低的。有29.7%的外出民工沒有匯款,表面看起來也占相當的比例,但是,筆者以為還應考慮到如下的情況:即,此次是在三峽庫區所做的調查,被訪者不少是庫區移民。調查時,我們能從舉止言談中感到,出于想得到更多移民補助款的考慮,被訪者往往傾向于將得到匯款數說小。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匯款的數目也是不低的。其中,匯款在2500元以上的,占到匯款總人數的36.5%,而平均每個農民工寄回帶回的錢數是2576元。下面表2是在城市調查的,匯款比例和匯款占收入的比例均要高一些。
表2寄回帶回老家的錢,占城市農民工全部收入的多大比例(2000年)
表2顯示,只有24.7%的農民工沒有往家里匯款,而75.3%的城市農民工都往家中匯了錢。從匯款的比例看,將自己收入的40%以上匯給家鄉的人占城市農民工總數的50%.那么,匯款寄回家鄉以后,在農村家庭的生活中占有何種地位呢?本次調查也顯示,我國城市農民工匯款占農村居民家庭收入的比例,也是比較高的,參見下面表3.
表3城市農民工匯款占農村家庭總收入的百分比分組(2000年)
表3顯示,得到的匯款占總收入50%以上的農民家庭,比例達46.3%,匯款占總收入80%以上的農民家庭比例仍達22.3%.而且,這種匯款是持續性的,成為農村居民穩定的生活來源。匯款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平均值約為40%.根據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的研究,寄回、帶回的收入占農民家庭總收入的比例,四川為43.3%,安徽為38.6%(農業部農研中心課題組,1996:45)。所以,筆者的調研結果,與農業部的數據是極為接近的。
此外,通過回歸分析發現,匯款對于農村生活的影響頗大。在表4的回歸系數分析中可以看到,外出農民工給農村家人的匯款,對于提高農村家庭收入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他們在外打工時間越長,則對于提高農村家庭收入越是起到促進作用;在外打工的家庭成員越多,則農村家庭收入越高;農村家庭收到的匯款越多,則對于自己生活地位的評價越高。再者,隨著外出農民工年齡的增大,他們匯款的熱情不是減少而是增大,表4第五條顯示,農民工年齡與農民工匯款多少的關系,回歸系數竟高達0.608.如此等等,都證明,外出農民工的匯款在農村生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匯款支持著和支撐著農民家庭和農村經濟,匯款也是農民工和家庭聯系的最重要的經濟活動之一。從生活方式的角度看,匯款和接受匯款,已成為外出農民工和農村家庭互動的重要內容。
表4關于匯款對于農民工和農村生活影響的回歸分析(1999年)
既然中國農民工的匯款高于世界上其他國家,那么匯款所起的作用就不一定與其他國家相同。前述的經濟學理論認為,從城市流往農村的資金是“涓流效應”,而在中國的場景下,此種流通的路徑就要比其他國家的寬廣得多,或許可稱之為“水渠效應”吧!
三、對于農民工高比例匯款現象之分析
中國農民工高比例匯款,既有中國農民工自身的主觀原因,也有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環境發揮作用的客觀原因。
曾有過一些理論從農民工自身角度解釋匯款原因,美國哈佛大學的斯達克(Oded Stark)和盧卡斯(Robert Lucas)提出了“契約安排”(contractual arrangement )理論解釋匯款現象。他們認為:“匯款行為是遷移農民與其家庭之間的自我約束的、合作的、契約性安排的一部分或一項條款。”“在不發達國家,從農村移往城市的農民與其家庭其他成員間的關系,是通過一種協商的契約性安排而加以模式化的。遷移的農民和其家庭通過這種契約,保障其各自的利益以及家庭整體的安全。契約雙方彼此充當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的角色。”(Stark &Lucas ,1988:465-481;洪大用,1996:10)
斯達克和盧卡斯還提出外出農民工與家庭互補的觀點。他們認為,遷移農民與其家庭“在某一時點,一方的凈收益可能為零,甚至是負值;但在接下來的某一時點,他可能是完完全全的受益者,對方則可能是凈收益為零,甚至是負值。換句話說,由于這種契約關系天然地具有長期性,契約的每一方都面臨著一個時間收益的問題”(洪大用,1996:12;Poirine,1997:589-611)。當然,此種觀點在中國的場景下也是不難證明的,中國農民工常常把孩子放在老家,由老人照看;而農忙時,他們也常常回到家鄉去,幫助家里干農活,顯然,雙方是互補的。另外,家鄉、家庭,也確實為農民工提供了保障,一旦發生經濟上的危急,農民工可以回家鄉去。
但是,在中國的場景下,如果將匯款僅僅解釋為:雙方平等交換的、信守合同的“契約安排”,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狀況的。中國家庭歷來重視內部關系,即使沒有外出和匯款,家庭成員之間也保持著高度的目標一致性和密切的互動關系。高比例匯款是中國農民特殊的家庭關系,以及他們對于家庭關系認識的必然反映。總的來說,中國人更注重家庭的整體利益而不是家庭某一個成員的個體利益。個人節衣縮食,為家庭積累財富,這在多數中國家庭中是很平常的事。在農村,全家攢錢為一個孩子進城讀書的事情比比皆是,而孩子讀書以后,收入并不高,并不一定能償還當初的錢款,如果說有返還也多是感情上的,這很難用契約關系中的交換的平等性來衡量。所以,中國農民家庭成員之間是一種天然的“利他主義”(altruism),當然,此種利他主義僅限于家庭內部。對于農民工消費的多次調查均證明,農民工在城市里的消費是非常節儉的。92.6%的城市農民工,在消費上主張“生活上越儉越好,能剩就剩,多存少花”(馮桂林、李淋,1996:13)。所以,農民工將打工節省出來的錢寄回家是很自然的事情,原因是,家庭本來就是一個整體,并不是因為有什么契約安排或核算。農民工的家庭也常常將匯款存起來,以備在外打工的孩子將來成家結婚時使用。所以,這種匯款近似于一種存款。這一點是中國家庭與西方家庭的重要差別,西方家庭重視個體的獨立性、尊重個體的權益,中國家庭則更為強調整體事業,個人利益受點損失沒關系,家庭整體事業得到推進才是目的所在。中國家庭更注重的是縱向關系而不是橫向關系,費孝通先生說:中國家庭關系的主軸是父母子女的縱向關系,而不是夫妻之間的橫向關系(費孝通,1998:41)。這樣,子女匯款給父母和父母為子女出錢辦喜事都是天經地義的。因此,高比例的匯款是中國農民家庭倫理關系的正常體現。
從客觀方面看,匯款已成為今日中國農村家庭資金積累的主要渠道。首先,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中國農民是如何進行資金、資本積累的。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之所以落后,就是因為中國的普通農民沒有資本積累的源泉。全國解放以后,在受到多數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政治和經濟封鎖的情況下,50年代中期以后又與蘇聯的關系逐漸惡化,這樣,中國的工業發展幾乎完全沒有國際資本的投入。在此情況下,國家只好靠建立城鄉分割的體制,形成工業產品和農業產品的巨大“剪刀差”,換言之,靠從巨大農業人口獲得的剩余來投入工業,以期完成城市中的工業化。但是,這樣的政策,顯然,不僅談不上對于農業的投入,反而造成農村發展上的嚴重滯后。梁漱溟先生與毛澤東主席曾經有過一次關于農民問題的激烈爭論,爭論的焦點就是農民生活和農村的發展問題。梁漱溟說:工人生活是九天、農民生活是九地,意謂應改善農民生活。60年代以后,推行“農業學大寨”政策,這也是在嚴重缺乏資金的情況下,提倡“先治坡,后治窩”,靠老百姓勒緊褲腰帶,從苦日子里省出一點一滴的錢,來建立一些不規范的、技術嚴重落后的農村小型工業,當時稱為“社隊企業”。當然,1979年以后,隨著人民公社的解體,隨著農村產權體制和管理體制的重大變遷,農村的產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單一糧食生產的局面被打破,多種經營、副業和農村小工業蓬勃發展;這種因資源重組帶來活力所創造的比較大的財富,奠定了從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依靠農村自身的投入而實現的鄉鎮企業發展的新局面。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的市場化體制迅速建立起來,資金大量流入資本利率較高的城市地區,從全國看,農村發展的資金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特別是如果與城市的發展相比較,農村的資金投入就顯得極為匱乏。在這種總體資金投入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外出農民工的匯款就成為發展中的至關重要的機會。
當然,在一部分農村地區,國家投資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比如扶貧資金、國家投資的與農業有關的建設項目等。90年代以來,其他一些資金投入的可能性增加了:比如市郊開發與農村土地出售的資金,當然,這只是涉及到臨近大城市的地區;又如一些村辦企業的資金積累;再如依靠特殊關系獲得的銀行貸款等。然而,對于絕大多數的農民家庭來說,所有上述資源都難以企及。普通農民要想獲得起始資金,要么靠累積資金速度甚慢的種植業、養殖業,要么靠銷路不保的多種經營,要么靠外出打工,相比之下,最簡捷的道路,還是到城里去打工掙錢。特別是對于不甘心與父輩茍同的年輕人來說,外出打工,幾乎是他們的惟一出路。
那么,農民外出打工收入狀況如何呢?此次調查顯示,外出農民工的收入,確實大大高于他們在農村的收入。根據人民大學王鼎同志2000年7月的調查數據計算,農民工在北京的月收入是他們在家鄉時月收入的4.32倍(平均值)。
根據筆者組織的北京豐臺調查,外出農民工個人在城市里一年的收入比在農村時的收入平均高出8252.88元。各分組高出的情況,請參見表5.
在表中,收入比在家鄉時高出3000元至25000元以上的農民工占到城市農民工總體的71.8%,可見,農民工進城打工的收益是相當可觀的。正是因為城鄉之間有著勞動力價格的巨大差異,在北京調查中,當詢問農民工外出流動的原因時,在眾多選項中,農民工選擇最多的是:“在老家收入水平太低,沒有機會掙錢”。
總之,匯款是收入轉移的一種形式,它可以導致收入分配機制發生某些變化。農民工的匯款本質上是資本在地區間的流動。上文已經證明,中國農民工的匯款比例是很高的,大批資金匯往家鄉,使農村急需的資金得到了補償,其結果當然是有利于縮小城鄉差距的。不少調研都做出了正向的評價。例如,江蘇的調查證明:“據統計,蘇北不少市、縣民工返鄉已超過外出打工總數的25%左右。勞務輸出大戶建湖縣,目前以返鄉民工為主體或骨干創辦的鄉鎮企業已達241個,村辦企業530個,職工人數80553人,鄉村辦企業產值達33億元,利稅2.7億元。另一勞務輸出大戶響水縣,近年來發展起以打工返鄉農民為主體的鄉村股份合作制企業2500多個,聚斂股資數億元……”(陳德美,1997:56)。
表5農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比在家鄉時個人的收入高出多少比例(2000年)
那么,匯款對于貧窮與富裕地區之間相互關系的影響如何呢?這一點是“現代化理論”與“依附理論”爭論的焦點。下面,筆者特提出外出農民工匯款的“邊際效益心理”的觀點,希得相與析。
四、農民工匯款的“邊際效益心理”
按照“依附理論”的假設,外出農民工匯款的結果并不會改變貧困與富裕地區之間關系的“馬太效應”(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效應)。“核心與邊緣區理論”的假設是,外出農民工的匯款,只會是“涓流效應”,它并不會縮小區域差距。例如,里查德·H.亞當斯對于外出農民工比例甚高的埃及開羅農村地區的研究證明,外出打工農民工的匯款對于農村收入差距的影響是負面效應的,因為,外出農民工多是已經富裕的農民,所以匯款的結果反而是拉大了差距(Adams ,1989:45-71)。
那么,中國的情況如何呢?匯款是更多地流向富裕地區還是貧窮地區呢?匯款是更多流向富裕家庭還是流向貧困家庭呢?北京的浙江農民工是比較多的,80年代就已經有了號稱“浙江村”的浙江農民工聚集地。早期浙江農民工向家鄉的匯款也是比較多的。但是,此次調查的數據卻證明,與其他地區相比,浙江農民工向家鄉匯款的比例反而是比較低的了。倒是那些貧困地區新出來的農民工匯款比例較高。因此,隨著中國外出的農民工逐漸向中西部推進,新出來的較貧困農民工匯款積極性和匯款比例均高于已經富裕起來的農民工。所以,此種心理和態度上的變化會對于縮小地區差異起到一些積極作用。
對于上述假設,筆者特根據在北京豐臺的調查數據,用回歸方法作出四方面驗證。
第一,數據顯示,近來,在北京,浙江等富裕地區的農民工匯款比例低于中西部農民工匯款的比例。換句話說,已經富裕地區的農民工,往家中匯款的積極性,遠不如那些尚未富裕地區農民工的高(見表6)。
在表6中,雖然回歸系數不是很高,但是,生活水平比浙江低的那些省份,匯款的比例和匯款在農村家庭收入中的比例卻都高于浙江。
第二,筆者比較了農村的不同產業結構與匯款之間的關系。筆者所提出的問題是,農民工家鄉的地方財政最主要來源于什么產業,這一點,對于農民工匯款是否有影響?筆者的假設是:如果以農業為主的鄉村得到的匯款多一些,這就好比是“雪中送炭”,顯然是有利于縮小農業為主的鄉村與非農業鄉村的差距;反之,如果匯款更多地流入了工商業為主的鄉村,那么,對于收入較低的農業村來說,就好比是“雪上加霜”,其結果就會擴大農業村與工商業村之間的差距。結果,數據證明,以農業為主的鄉村得到匯款的比例,高于以工商、服務業為主的鄉村。所以,我們可以判斷,高比例的匯款,起到了輔助貧困村莊的作用。參見下面表7:
表6與浙江農民工相比較的其他省份農民工匯款比例
表7農民工家鄉產業結構對于農民工匯款的影響(2000年)
上表中,農業為主鄉村的農民工比之其他類型產業鄉村的農民工,將較高比例的收入寄回家鄉,說明農業產業收入低,農民工更傾向于將較多的收入寄回家鄉。農業與服務業對比,對于農民工匯款影響高達0.45.欄中個別項目之所以不具顯著性,是因為樣本量較少。由于外出農民工有這樣一種心理傾向,如果家鄉收入比較高,則他們傾向于將比較少的錢寄回家,如果家鄉的收入比較低,則傾向于將較多的錢寄回家。農民工心理上的這樣一種調節,實際上影響著農村的經濟關系。因此,總的看來,農民工的匯款,對于經濟比較落后的農村地區,還是起到了促進的作用。
第三,農民工家庭不同層次的居住地點,對于他們匯款行為的影響。我們知道,雖然城市外來工多數是來自農村,但也有相當比例來自城鎮,這樣我們就可以驗證一下,是家在農村的匯款多還是家在城鎮的匯款多。一般說來,在中國,經濟條件從“核心地帶”到“邊緣地帶”的排列順序是:地級城市、縣城、鄉鎮、村莊。如果按照“依附理論”的假設,匯款將較多地流入“核心地帶”,而較少地流入“邊緣地帶”,然而,回歸分析卻證明了相反的結論,匯款與“邊緣地帶”是正向的回歸關系,與“核心地帶”是反向回歸關系(見表8)。
表8民工家庭居住地位置對于農民工匯款的影響(2000年)
表8顯示,與老家在鄉鎮、縣城或在地級城市的人相比,家住村莊的民工,更多地將自己的收入寄回家鄉,與此相對應,農村家庭的人得到的匯款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也就更高。這一點證明,匯款確實可以起到將核心地帶的收入轉移到邊緣地帶去的功能,換言之,可以起到縮小城鄉差距的功能。
第四,從個人家庭層次上看,農民工在農村家庭收入的高低對于農民工匯款比例的影響是負向的,即農村家庭收入高的農民工,向家鄉匯款的比例要低一些,反之,農村家庭收入低的農民工,向家鄉匯款的比例要高一些,參見表9.
表9農民工在農村家庭的收入對于農民工匯款行為的影響(2000年數據)
所以,外出民工在農村的家庭,越是收入高的接到匯款越少,越是收入低的,則接到匯款越多。
總之,從以上的四個層次都可以看到,匯款是傾向于流向那些收入比較低的農民工家庭,流向那些產業是以農業為主的農民工家庭,傾向于流入經濟還比較落后的、居于內陸的而不是東南沿海的農民工家庭,更傾向于從“核心地帶”流入“邊緣地帶”的村莊而不是流向地級市、縣城或鄉鎮。
那么,這里面有兩個問題,第一,為什么越是貧困地區的農民工、越是貧苦的農民工向家鄉匯款的比例越高呢?第二,為什么越是貧困地區的農民工家庭越能獲得較高比例的匯款呢?
對于第二個問題比較容易做出回答,即,貧困地區的農民家庭收入低,所以,同樣數目的匯款,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會高一些。對于這一點,也可以理解為“邊際效益”在發揮作用,即,在收到同樣數目的匯款后,在越是貧窮的農民家庭中,它發揮的效用會更高一些。
對于第一個問題,筆者試提出農民工匯款的“邊際效益心理”的假設。即,外來民工在匯款時,是要比較這樣一筆錢的功效的。如果老家的家庭里已經比較富有了,寄回家去,發揮的效益也是有限的,那么,農民工匯款的動力就會受到阻礙,熱情就有所降低。反之,如果家里一貧如洗,正在等著這筆錢糊口,弟弟妹妹還在等著這筆錢交學費,那么,農民工顯然就會動力十足、熱情高漲、竭盡全力、節衣縮食,省下錢來寄回家。試看筆者過去所組織完成的個案,它反映了兩類城市農民工心態上的差異。
富裕地區的農民工
個案114.被訪者G ,男22歲,廚師。他來自江蘇L 地區,那里經濟發達,村子里人均年收入可達14000元左右。他家收入在村子里中等偏下,父母兩人年收入在20000元左右。因此,G 不往家里寄錢。在北京消費較高。他做廚師,每月至少有800元收入,吃飯不花錢,與別人合住,每月房租130元。剩下的錢主要是用來買衣服、抽煙。買衣服花的錢比較多,從他的穿戴可以看出,他外面雖然罩著白色的工作服,領口上露著真維斯的襯衫。買過一架600多元的相機,再就是買過一輛變速自行車。平時的業余生活是聽音樂臺或是去電影院看電影,有時去附近的大學打籃球,偶爾也去跳舞。
貧困地區的農民工
個案102.被訪者W ,女,24歲,初中二年級,肄業。四川D 縣農民,父母在老家種地,W 自已現在北京一家裁縫店工作。W 說:“我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都在家鄉上學。弟弟學習不怎么樣,估計以后也要出來打工。妹妹學習特別好,總拿獎狀回來。我出來打工也是為了給她賺學費,只要她爭氣,我一定要供她上大學。”“我賺錢是為了給弟弟妹妹上學用的,還要為弟弟娶媳婦攢錢,掙的錢當然要往家寄錢了。”
個案55.被訪者C ,女,20歲,家在廣西B 縣農村,現一個人在深圳一家旅館做臨時工。她說:“在旅館,每月的收入不固定,旺季的時候多些,淡季少些,但每月除掉伙食費,都不低于400塊錢。我家里父母年紀都大了,還有兩個未成年的妹妹,生活很困難。到深圳后,我基本上每月都能往家里寄300塊錢,在家里已經能解決很多問題了。”*
當然,農民工匯款的邊際效益心理,其文化前提是,形成了“家庭共同體”的基本認識,如前所述,這一點是其他國家的文化中所沒有的。
五、外出農民工及其匯款的負面影響
按照上述農民工的邊際效益心理,匯款的結果似乎是農村地區的貧富差距會由于此種心理作用而趨于縮小。同樣,按照“新古典主義平衡假設”(equilibrating hypothesis),在發展中國家,由于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從而使農村窮人獲得更多的新機會,這有利于降低農村內部或農村與城市之間的不平衡性“(周紅云,1996:33)。然而,當我們考察農村的貧富差距時,發現的卻是差異比較大的情況。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研究:”1987年以來,農村的基尼系數是在提高。其中提高最快的是西部地區,由1987年的0.1660增加到1994年的0.3162.“(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課題組,1996:12-13)
筆者此次調查也證明,四川農村地區的貧富差距是比較大的。
表10四川被調查農戶家庭各收入組占總收入的比例(1999年)
上表顯示,占人口20%的最低收入組,在全部收入中只占有2.22%的份額,而另一端的20%最高收入組,占有的份額達到57.24%.用基尼系數方法測量,達到了0.5293598的水平,貧富差異是相當大的。當然,此次調查缺少歷史比較的數據,即,僅根據現有的數據還難以判斷在歷史上,特別是自改革以來,歷年的收入差距演變情況。然而,根據筆者多年來研究的經驗,近年來,中國農村中的貧富差距一直處于擴大的趨勢。
這樣就產生一個問題,根據本文第三部分的研究,農民工表現出匯款的“邊際效益心理”,而此種心理的效應是會縮小富裕家庭與貧窮家庭差距的,然而,為什么最終結果貧富差距還是在擴大呢?
筆者以為,“邊際效益心理”雖然可以調節外出農民工的匯款行為,但是卻不能調節“外出戶”與“非外出戶”之間的經濟鴻溝。農村貧富差距的擴大,比較突出的體現為“有外出農民工家庭”與“無外出農民工家庭”之間的差距。對于外出戶與非外出戶的差異,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曾做過研究,證明:“外出就業使外出戶的收入水平明顯提高,外出收入已成為外出戶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外出戶的總收入水平明顯高于非外出戶,而且在經濟相對更不發達地區,這種差距更為顯著”(農業部農研中心課題組,1996:44)。
本次調研證明,外出戶與非外出戶農民家庭經濟的差距是很明顯的。從表中,我們看到,外出戶與非外出戶的收入水平有很大差距。有外出農民工家庭總收入均值為11474.58元,而無外出農民工家庭總收入均值為7475.47元;有外出農民工家庭人均收入2316.53元,而無外出農民工家庭人均收入是1704.36元,兩者的收入差距是明顯的。
表11有外出農民工的農戶家庭(1999年)
上述對于外出戶與非外出戶的分析還涉及到了一個頗為引人關注的問題,即農民工的大量外出是否會導致農業產量和生產力的下降?其實,這是一個很難測量的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利普頓(Michael Lipton)“曾以非洲社會為例證明,人口外流確實導致了農業產量的下降,但這個結論并未被廣泛接受,亦有人以印尼西爪洼為例,證明了相反的觀點”(馮仕政,1996:24)。以往的研究還證明:“在農業資源條件較差的地方,不斷增加的人口,可能導致農業生產潛力較為薄弱的邊遠山區的開發,或者對現有耕地的過度利用——或是休耕時間不夠,或是過度施用化肥——而導致土地肥力下降,人均產量亦隨之下降。人們必須尋找非農業資源來保證基本的生活需要。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產量本身就是人口流動的原因而不是人口流動的結果。因此,至少在農業條件較差的地區,人口流動和農業生產之間存在著雙向因果關系。而在農業條件較好和有途徑進入城鎮市場的地區,一些農民利用本地的區位優勢發展新產業或改造現有農業生產,成為當地的富裕階層,進入城里專事非農業活動,他們留下的勞動力空缺一方面通過當地勞動力在空間上的重新分布,另一方面則通過農業條件相對較差的地區的剩余勞動力的流入得到彌補。也就是說,在農業條件較好的地區,短缺的勞動力通過一種梯級流動模式得到了補充。一個比較著名的例子是,50年代香港新界手工業興起,大部分本地人都移居城鎮或海外,這導致了大批廣東人的涌入,以從事當地急需的蔬菜種植。這種情況下,人口流動顯然未導致農業產量和生產力的下降,只不過使農產品種類及各自的產量有所變化”(馮仕政,1996:24)。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研究證明,“在那些現金很緊缺的地方,追加現金投入給農業生產帶來的邊際收益高于追加勞動的邊際收益,外出就業帶回的現金收入對農業生產的正面影響高于勞動力減少對于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農業部農研中心課題組,1996:59)。反之,在現金不緊缺的地區,負面影響就會較大。該研究還指出:“本研究實施過大量的現場訪談。訪談得到的有些印象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在有的村,許多外出戶都贊成外出,認為外出是好事,不會影響農業生產,外出戶的地甚至比非外出戶種得好;在另一些村,也有不少外出戶承認外出戶外出勞動力緊張,比非外出戶的地多少總會差一些。”(農業部農研中心課題組,1996;44)
本研究的數據證明,農民工外出對于農業生產還是有明顯的負面影響的。上面表中的數據顯示,有外出農民家庭平均所擁有的田地畝數17.98畝,比無外出農民家庭田地畝數16.4畝還要略高一些,然而,其生產的糧食1749.74斤,卻明顯低于無外出農民家庭的2715.52斤。
六、結語
讓我們回到本文一開始提出的“現代化理論”還是“依附理論”的問題上來。在城市農民工問題上,中國的實例所驗證的結果,究竟是“現代化理論”占上風呢?還是“依附理論”占上風呢?本文的結論,似乎對于兩個流派都有印證。對于中國農民工匯款特點的分析證明,中國農民工匯款比例高于其他國家,所以,其效果顯然是更有利于農村的發展。對于匯款原因的分析證明,中國農民的特殊家庭關系,使得外出打工的農民與家鄉的資金流通渠道可以長期保持高流量。對于影響匯款因素的回歸分析、對于農民工的心理效應與匯款的變化的分析,印證了:由于“邊際效益心理”發生作用,外出農民工向家鄉的匯款是有利于縮小區域之間、貧富地區之間和貧富農戶之間的差距的;然而,在負面影響一節,又證明:由于有外出農民工戶與無外出農民工戶之間差距的擴大,又使得區域之間的差距、群體之間的差距拉大,以及外出對于原有農業生產的損傷,似乎“依附理論”又是占上風的。
所以,筆者以為,中國農村發展的復雜性在于,有利于現代化的因素與不利于現代化的因素同時存在。如果有利于現代化的因素占上風,那么,農民工進城打工、匯款回家就會有利于農村的發展;反之,如果不利于現代化的因素占上風,那么,農民工進城、勞力流失就不利于農村發展。在這里政策的調節就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的個案也證明了,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并不是哪一個單獨的理論流派可以涵蓋得了的。每一個理論流派只是對于社會現象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做出解釋,換一種角度則常常會發現相反的狀況。任何一種社會理論都只是部分地合理,因此,對于社會現象、社會問題的分析常常需要同時應用不同的理論模型。對于社會現象的總體認識需要多種理論視角的綜合(Crenshaw &Ameen,1994:1-22)。
當然,本文僅僅是從外出農民工給家庭的匯款一個角度,來分析它對于民工流動、對于農村的影響,而實際發揮作用的還有其他許多因素,比如:技術、信息、文化、生活方式、新觀念等等。所以,要想判斷現代化理論還是依附論何者占上風,還需要綜合考慮這眾多的因素。
「
1陳德美,1997,《潮起潮落:看民工返鄉創業》,《中國農民》第3期。
2費孝通,1998,《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
3馮桂林、李淋,1996年6月,《我國當代農民工的消費行為研究》,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國際研討會論文,北京。
4馮仕政,1996,《城鄉人口流動對其農村來源地的影響》,《國外社會學》第3期。
5洪大用,1996,《關于家庭與農民遷移進城之關系的研究》,《國外社會學》第3期。
6康內爾,T.1976,《來自農村地區的流民:村莊研究之證據》,倫敦:牛津出版社。
7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1996年6月,《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研究:外出者與輸出地》,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國際研討會論文,北京。
8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課題組,1996年6月,《轉軌變型期的中國勞動力流動與勞動者收入》,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國際研討會論文,北京。
9周紅云,1996,《貧窮國家人口遷移對農村來源地的影響》,《國外社會學》第3期。
10周起業等,1989,《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1Adams,Richard H.1989,"Worker Remittances andInequality in Rural Egypt."EconomicDevelopment and CulturalChange 38.12Ahlburg ,Dennis A.1996,"Remittances andthe IncomeDistribution in Tong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15.13Crenshaw,Edward &Ameen,Ansari 1994,"The Distributionof Income across National Populations:Testing MultipleParadigms."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3.14Frank ,A.G.1985,《低度發展的發展:依賴理論的基本假設》,載于蕭新煌編:《低度發展與發展》,臺北: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15Kandi,M.&Metwally,M.F.1990,"The Impact ofMigrants'Remittances on theEgyptian Economy,"InternationalMigration 28.16Parish ,William-L 1973,"InternalMigration andModernization:The European Case."Economic-Development andCulturalChange 21.17Poirine ,Bernard 1997,"A Theory of Remittances as anlmplicit FamilyLoan Arrangement."World Development 25.18Santos ,T.Dos 1985,《依賴結構的分析》,載于蕭新煌編:《低度發展與發展》,臺北: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19Solinger ,Dorothy J.1999,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Urba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Stark,Oded &Lucas,Robert E.B.1988,"Migration,Remittances ,and the Famil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Cultural Change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