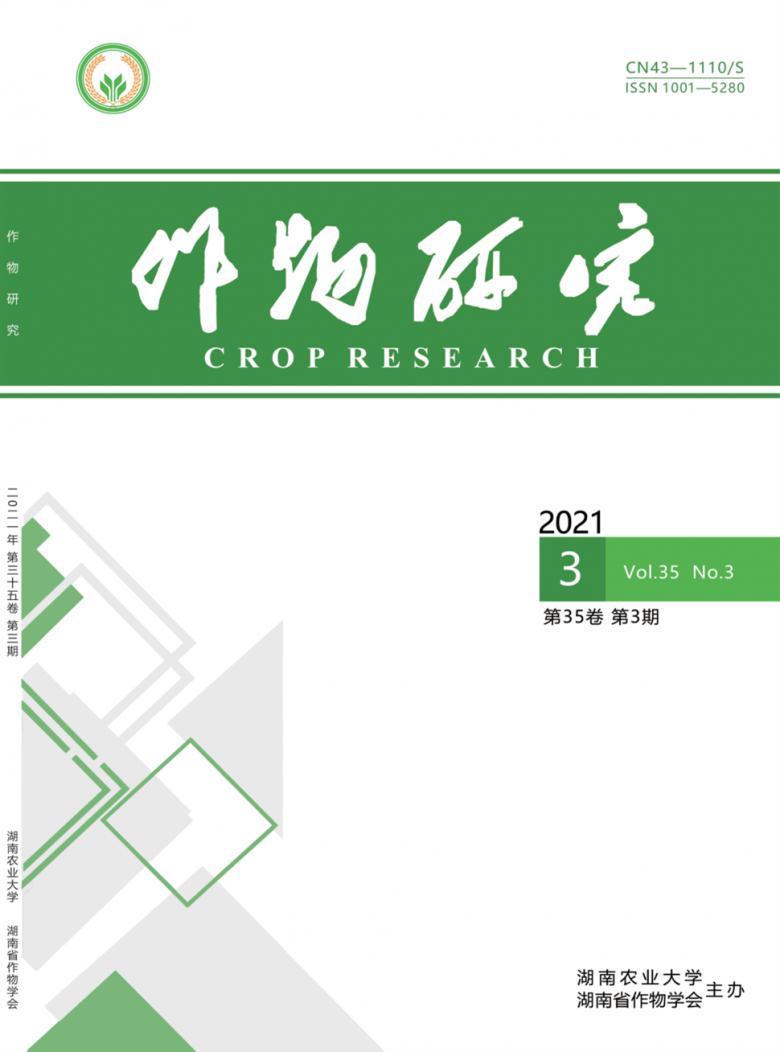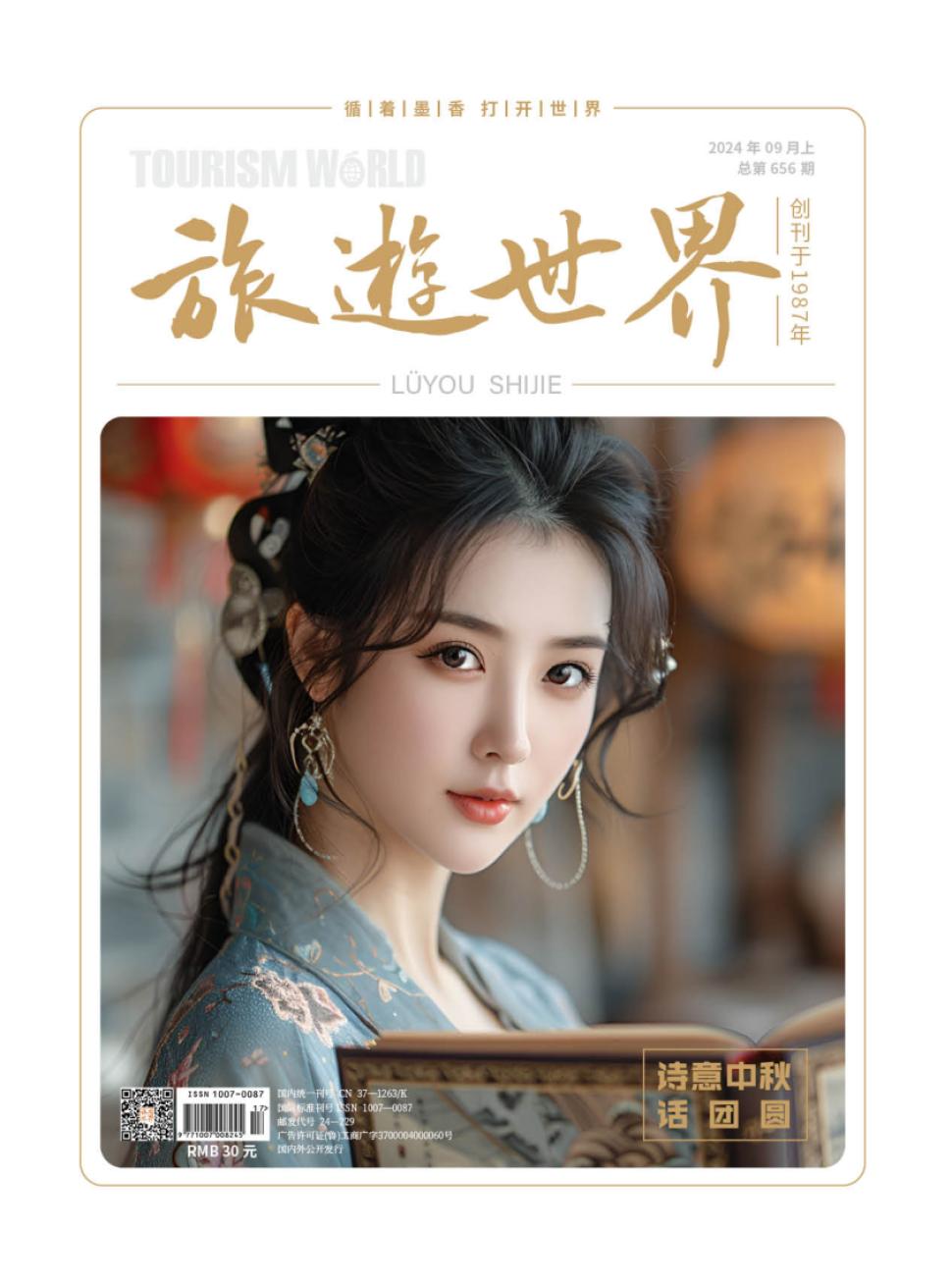矯正和提升農民工群體地位的理性思考
孫玉娟
關鍵詞:農民工群體,地位,失調,矯正
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出現的農民工發展到今天,越來越以一種群體的、整體的方式生存與發展。從理論上的理想狀態講,他們是實現工業化、城市化和完善我國社會結構的依賴力量。但是,由于多種因素的相加作用,該群體不但沒有受到足夠關注和政策保護,還處于地位失調狀態,從而引發其角色緊張并形成群體效應,對我國社會結構和經濟發展極為不利。因此,矯正和提升農民工群體地位,對完善我國社會結構,實現城鄉融合目標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農民工群體現實地位的解讀和描述
農民工群體地位失調指其地位中介化功能向度與曖昧的法律性向度及邊緣化社會性向度不一致。從功能(職業)角度來講,農民工群體為我國現階段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卓越的、不可或缺的貢獻;從法律角度來講,該群體沒有獲得合理、合法的地位;從社會資源分配角度來講,該群體力圖擺脫農村體制卻又力不從心,始終在城市與農村的夾縫中生存。遵循上述三個向度的地位概念,從以下三個角度來描述和解讀農民工的現實地位情況。
(一)曖昧的法律性位置
“法律性位置”含義與“政策性位置”相似,指政府及社會對農民工群體的定位和定性。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農民工數量激增,該群體被稱為“盲流”。由于作為“集體排他性屏蔽”的戶籍制度的存在,農民工群體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名分,從中央到地方還存在限制性政策限定農民工的進入范圍。農民工群體地位處于“曖昧”狀態,或受歧視或被忽視。
(二)邊緣化的社會性位置
“邊緣化”概念一般等同于“城市體制之外”或“城市底部化”,也指農民工群體徘徊于農村體制之外的情形,或超越城市和農村兩個體制,處在兩個體制邊緣或處在兩個體制之間即中介化狀態。如在資源分配方面,將城市與農村相比較,農村并沒有處于被優先考慮的位置。當農民工還是完全意義的農村農民時,已經處于資源分配的邊緣。農民工進城是農業“過密化”或“內卷化”的結果。但是,進城并沒有改變邊緣化的資源分配狀況。由于地方經濟快速發展,而農民工群體的工資收入(貨幣分配)卻沒有增加,相對于城市居民來講,處于資源(貨幣)分配的劣勢狀態,沒有享受到與城市體制內部成員一致的資源分配份額,沒有被納入城市居民享受的社會保障體制之內。在人事分配方面,農民工群體處于雙重邊緣化位置。一方面,農民工整體教育水平和技術技能水平與城市居民相比有較大差距,即使按照正常的勞務市場或人才市場規則進行競爭,也處于機會的邊緣化位置。另一方面,政府出于社會穩定等原因考慮,對農民工進入市場進行規定,如必須辦理各種繁雜的證件,否則就不能務工,對一些工種明確規定不準農民工進入。在競爭能力處于劣勢情況下,又遭遇了不平等的競爭規則,只能夠留在“次屬勞動力市場”,干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最苦、最臟、最累的活兒。在獎賞分配方面,從符號分配來講,“農民工”三個字本身就是尷尬組合,“所指”模糊。英文中根本找不到合適對等詞,通常譯成“migrant worker”(遷移的工人)或“farmer worker”(農夫工人),無法表達農民工處于“農民”之邊與“工人”之邊的狀況,還暗含著歧視成分和權力運作。從聲望分配角度來說,存在城鄉反差問題。在農村,農民工是精英,處于“聲望之巔”,在城市,是“打工仔”、“民工”、“外來務工人員”。雖然200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中明確提出: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現實生活中農民工群體很難真正享受到官方賦予的符號。
(三)潛在的中介化功能位置
由農民工群體職業與身份分離性特點所決定的中介化功能位置是潛在的,多數人沒有意識到,甚至忽視。從功能主義角度來講,社會分工是一種功能安排,農民工群體的職業性向度等同于功能向度。沃勒斯坦將現代世界體系劃分為三個類型:核心國家、邊緣地區以及準(或半)邊緣地區,認為準邊緣地區的位置的存在本身遏制了核心與邊緣之間的兩極分化和沖突。農民工群體的位置恰如“半邊緣地區”的位置,其功能也如“半邊緣地區”所發揮的功能。因此,我們將農民工群體的地位向度稱作“中介化功能位置”。農民工作為跨越農業、工業的群體,是產業分化的促進者,作為跨越城、鄉的群體,是城鄉經濟差距和文化差別的縮小者,作為跨越東、中、西部地區的群體,是我國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平衡者,作為跨越農民、工人階級、城市居民的群體,是階級、群體矛盾的調和者。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主要表現為利益差別上的矛盾、非對抗性的矛盾,主要是“利益集團”之間的經濟利益沖突。解決矛盾的辦法有兩種:一是借助外部力量來壓制,二是通過內生力量來消減或化解。農民工群體的出現和存在正是社會有機體內部形成的化解矛盾的內生力量,是平衡我國現階段現實的“工人/城市居民利益集團”和潛在的“農民利益集團”之間利益沖突的重要力量。
農民工群體地位失調的負面影響
農民工群體地位失調是多種因素合力造成的。由于政治邏輯的權力與資本邏輯的權力的較量和妥協,農民工群體地位失調成為事實。失調事實的刺激與沉淀,一方面轉化為一種心理傾向,農民工群體自身的混沌心理定位與城里人的心理排外傾向共同建構了農民工群體的地位失調;另一方面演化為一種話語表達,“農民工”一詞高頻率和長時間使用,實質是“溫和暴力”不斷演練,不但強化了農民工群體本身的邊緣化位置感,還強化了城里人(包括居住在城里的決策者)和村里人把農民工視作邊緣群體的觀念,從而進一步影響針對該群體的意義分配、機會分配和資源分配,加重弱勢群體的弱勢化,加劇農民工群體地位失調的現實。這種心理傾向和話語表達又轉過來進一步建構失調,在無意識中表現出與權力共謀或服務于權力運作,結果造成農民工群體角色緊張并形成群體效應。
緊張表達的規模效應。緊張指尚未表現為公開沖突的不滿。緊張表達指各種社會不滿的釋放。對具有近1.3億成員的農民工群體來說,如果地位失調情形未得到及時矯正,社會安全閥制度不健全,群體心理調試不積極,社會控制又欠力度,緊張表達的方式可能是非和平的、抗議式的,緊張表達的后果可能波及全國范圍和各個行業。因此,農民工群體角色緊張可能誘發嚴重的社會影響。
緊張表達的示范效應。示范效應既指群體內的示范效應,也指相似群體間的示范效應。在農民工群體內部,某一個地方的子群體或某一個行業的子群體的緊張表達可能會誘發其他子群體的緊張表達,甚至在緊張表達的時間、方式上可能會趨同。農民工群體的緊張表達還可能會誘發其他相似(弱勢)群體的緊張表達。
緊張表達的網絡效應。農民工群體是建立在業緣、地緣、血緣基礎之上的網絡化群體,緊張表達會通過業緣、地緣和血緣傳遞并得到進一步強化和擴大。每年年底在全國各地發生的“討還欠發工資”的集合事件,網絡性作用不可小覷。
矯正和提升農民工群體地位的思路
近年來,我國政府為矯正農民工群體地位出臺了系列政策法規,農民工群體地位在法律性向度和社會性向度方面有所改善。但是,理論機遇能否轉化為現實圖景,不但取決于黨和政府相關政策能否得到制定和落實,還取決于農民工群體本身是否具有把握和運用機遇的素質,也取決于其他社會成員和群體能否配合協作。因此,要解決該群體地位失調問題必須合力推動,政策層面要改革,大眾心理要調整,話語系統也應有所動作。這樣才能改變農民工群體曖昧的法律性位置和邊緣化的社會性位置,使其地位的合法性明朗化,獲得與其重要的中介功能相符的資源分配,有機地融入城市。
(一)作為決策者必須進行理性革命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出現了封閉的社會關系與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并存的局面,隱含一種結構的斷裂,即理論與現實之間的脫節和禮俗文化滯后于政策文化時產生的“墮距”。農民工群體的出現和存在表明了這種結構斷裂,要彌合或者超越這種斷裂需要有開放的社會關系與開放的經濟關系相呼應,不要過多設定針對“非主流”群體(包括農民工群體在內)的參與限制。因此,應校正決策者決策思路,充分張揚價值理性和目的理性,站在重建社會結構的角度,拋開既得利益的羈絆,消除傳統和情感的束縛,改革思維模式,把農民工群體地位建設納入開放的社會關系的建設范疇。
(二)作為農民工群體必須進行自身革命
農民工群體地位建設面臨三方面挑戰:文化、技能方面的挑戰。農民工群體本身應有良好的文化積累和技能儲備,政府層面和農民工群體本身要有充分和清醒的認識,注重下一代的教育和培養,防止匱乏的文化資本再造邊緣化的群體,防止地位失調的代際再生產;心理方面的挑戰。逐步消除戶籍制度炮制的“二元”心理烙印,改變我是“鄉里人”的心理定勢,驅散邊緣化的心理陰霾,樹立“我也可以和城里人一樣”的心理和“人人都是自由人”(強調自由遷徙)的觀念;必須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境界和法制觀念。隨著社會發展和改革深化,農民工群體將實現從農民到工人的轉變。但是,傳統的農村生活所折射出的思想道德觀念,在其身上表現得還比較明顯。作為工人階級大軍的新成員或準成員,加強對農民工的組織紀律性和社會公德教育,增強其組織觀念,使其能在生活中遵紀守法,文明行事,禮貌待人,愛護公共設施,主動參加各種公益活動,自覺遵照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的要求,樹立一代新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