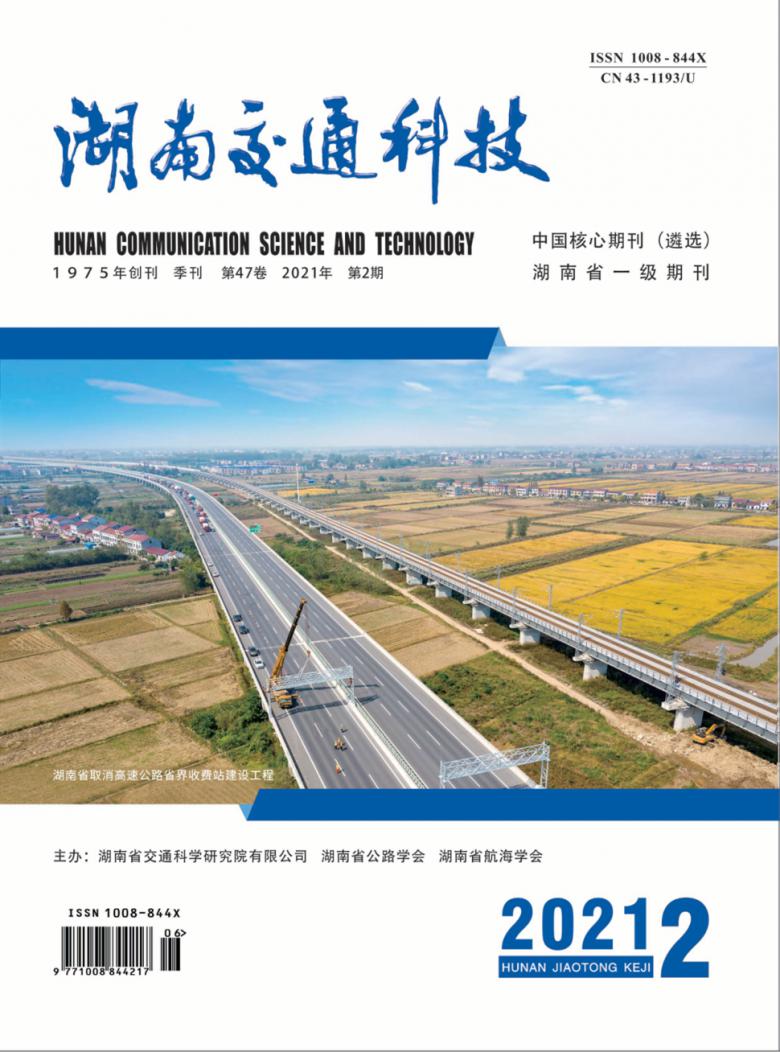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互動關系分析
張冬冬
摘 要:非正規金融是廣大農村經濟主體為滿足其融資需求,繞開官方正規金融自發開展和形成,游離于政府監管之外的非官方資金融通活動和組織,它的出現打破了正規金融的壟斷地位,對于農村經濟增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優勢,本文從實證的角度分析了非正規金融對山東省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非正規金融 農村經濟增長 互動關系 沿用亞當斯和費奇特的界定方法,可以把受到中央貨幣當局或者金融市場當局監管的那部分金融組織或者活動稱為正規金融組織或活動,主要是指四大國有銀行、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等。把所有處于中央貨幣當局或者金融市場當局監管職務之外發生的金融交易、貸款和存款稱為非正規金融組織或活動,主要以金融服務社、基金會、私人錢莊和各種合會、親友借貸等民間金融機構形式存在。 在我國正統的經濟與金融理論框架范圍內,長期以來是沒有非正規金融體系的地位的。我們不僅沒有正視其存在,更沒有深入探究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背景之下生存、繁衍及其與經濟發展的耦合規律。只是簡單地認為:非正規金融擾亂了金融秩序,分流了社會資金,助長了社會丑惡現象,容易形成不穩定的社會因素,因此在我國數十年來的金融實踐工作當中(包括改革開放之前與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段時間內)對非正規金融一直是采取打壓、限制甚至取締的態度。從新中國建立之初取締“金融黑市”到改革開放中期以來數次整頓金融秩序,非正規金融每每都是“出頭之鳥”,被首先予以治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開始陸續有學者利用實證的方法將非正規金融納入研究視野,分析非正規金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取得了一些成就。 國內較早的有徐笑波、鄧英陶(1994)等利用金融相關率對農村金融狀況進行描述;后來,宋宏謀、陳鴻泉和劉勇(2003)等利用金融發展指標對農村金融狀況進行討論;張兵、朱建華等(2002)對農村金融深化的績效做了實證檢驗;胡金焱、朱明星(2005)對山東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做了實證研究;王鳳霞,歐真真(2010)對江蘇省的非正規金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做了相應的實證研究。 本文通過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從實證的角度有針對性地對山東省農村經濟增長以及當前農村非正規金融發展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進行研究,分析了非正規金融的自身優勢,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指標選取 本文數據來源于《山東省統計年鑒》,數據樣本區間為2000--2009年的數據,利用eviews 6.0統計軟件進行實證分析。 金融發展指標主要包括農村正規金融指標和非正規金融指標。由于山東省的金融結構是銀行主導型的,廣大農村地區最基本的金融工具是存款和貸款,所以本文采取農業貸款(ND)作為正規金融指標來衡量,而由于非正規金融的隱蔽性非正規金融指標只能采用非正規金融的估算值(FG)來衡量非正規金融發展,估算方法采用郭沛(2004)對中國農村非正規金融規模估算的方法,并且采用窄口徑數據。考慮到財政對農村經濟增長的作用,我們應該考慮到金融發展的財政因素,財政指標采用財政支農(CZ)金額。在本文中我們采用第一產業的生產總值(GDP)作為經濟增長指標。 二、實證分析 (一) 模型建立 此處采用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f(K,L,F)進行實證分析,其中K代表勞動力投入,L代表資本投入,F代表金融發展。假設勞動力投入量達到一定數量時,經濟面臨的是規模收益不變,于是得出總產出只取決于資本投入和金融發展水平,即: Y=f(K,F)min(L,L)?茲 ?茲>0 又由于金融包括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兩部分,即:Y=F(Fi,UFi) 把下式代入上式得出:Y=mf(K,Fi,UFi) 也就是說,在上述假設條件下,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f(K,L,F)就演變為, Y=mf(K,Fi,UFi),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f(K,L,F)的實證分析也就演化為Y=mf(K,Fi,UFi)的實證分析。 (二) 單位根檢驗 為了防止非平穩時間序列造成虛假回歸,在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前我們要對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時間序列是否平穩。為防止異方差性我們先把序列取對數然后再進行單位根檢驗。 表中單位根檢驗的結果表明,各指標變量都不是平穩序列,而非平穩序列會造成虛假回歸,所以需要進行平穩性轉換。 由計量經濟學原理可知,通過差分的方法可以消除單位根的非平穩性從而得到平穩序列,因此我們通過差分來進行平穩性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