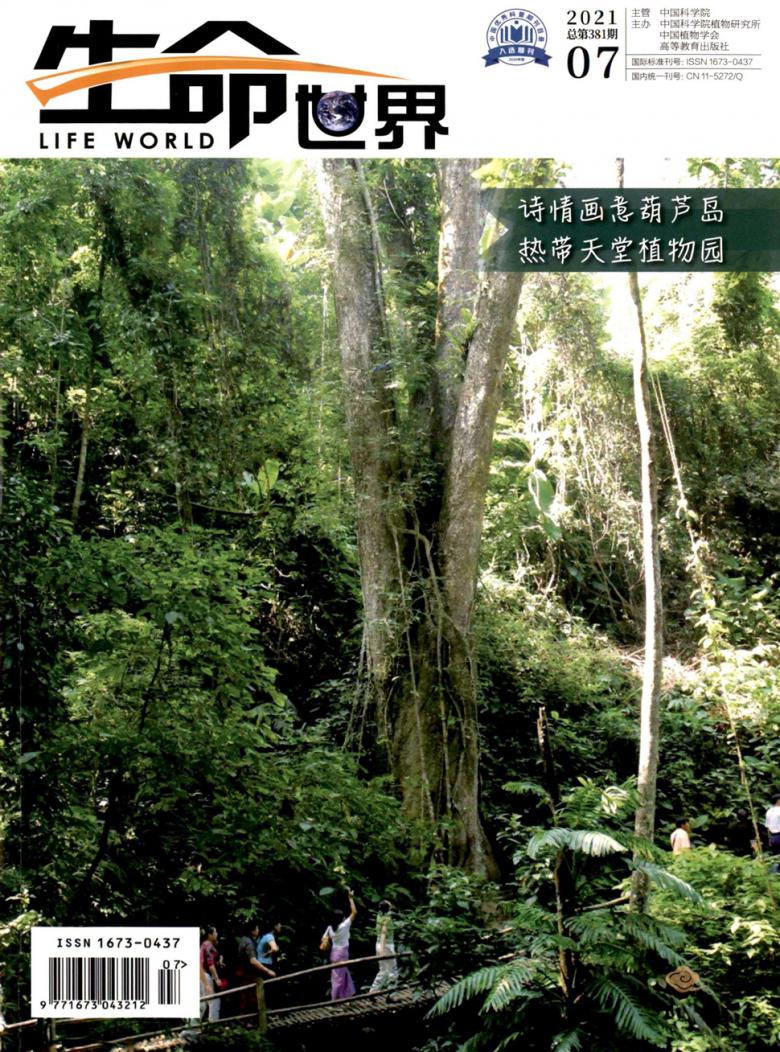淺談《老子》的百年散文藝術
未知
摘要:20世紀以來,諸子學勃興,“以子證經”的學術傳統被打破,《老子》及先秦道家學統得到重新審視。百年間圍繞老子其人其書和“五千言”真諦展開了廣泛的討論,《老子》文學研究雖寂寞卻也成績斐然。就散文藝術而言,研究者對《老子》的文體形式、情感內涵、藝術特色與文章風格等進行探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本文就以上幾個方面對20世紀的《老子》散文藝術研究狀況作了簡要回顧,并對其得失和未來的研究趨向作了評說和瞻望。 關鍵詞:《老子》;百年散文;散文藝術 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pre-Qin thinkers study vigorous growth, “has passed through by the sub-card” the academic tradition is broken,Laozi and pre-Qin Taoism studies the series to obtain carefully examines. During hundred years and “5000 words” the true meaning have launched the widespread discussion regarding father its person of its book, althoughLaozi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lonely actually also makes brilliant achievements. Speaking of the prose art, researcher toLaozi the literary style form, the emotion connotation, the artistic feature and the article style and so on carried on discuss and have achieved certain achievement. This articleLaozi the prose art research condition has made the brief review on the above several aspects to the 20th century, and will do to its success and failure and future research trend commented on and peeks.
key word: Laozi; Hundred year prose; Prose art
前言 20世紀初,諸子學興盛,“以子證經”的學術傳統被打破,《老子》及先秦道家學統得到重新審視。本世紀的《老子》研究大致上圍繞兩大問題展開了幾次熱烈的討論:一是關于老子其人其書的生平里籍考證、篇章辨偽及校注,二是《老子》哲學思想的探究。老子的哲學思想充滿著辯證法的智慧,深不可測,因而,“五千言”的真諦,至今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雖然老子其人其書撲朔迷離,紛紜之議兩千年,迄今也很難說已真正解決,但是《老子》成書當晚于《論語》,定稿約在戰國初期;全書思想理論一貫,文體文風一致,大體出于一人手筆,則取得了大致一致的意見。較之于哲學思想研究的繁盛,《老子》文學研究尤其是散文藝術研究要寂寞得多。80年代以前除了魯迅《漢文學史綱要》單列“老莊”一章略加論列外①,大多只是只言片語的涉及,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80年代以后隨著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拓展,《老子》文學研究引起了學界的注意,出現了一批比較系統的研究成果。縱觀20世紀的《老子》散文藝術研究,主要集中在文體形式、藝術特色和文章風格等幾個方面。本文從以上幾個方面對百年的《老子》散文藝術研究狀況進行簡要回顧,并對其得失和未來的研究趨向作一個粗淺的評說與瞻望,以期對未來的《老子》以及先秦諸子散文藝術研究提供一些借鑒與啟示。
一、文體特性研究
《老子》雖為語錄體卻無對話與場面描寫,也無設教授學的痕跡,是更為純粹的“立意”、“見志”之作。今本《老子》八十一章,結構完整,文辭精練,大體有韻,體近詩歌,加之“玄之又玄”的哲學思想,使“五千言”蒙上了一層朦朧的詩意。對《老子》詩性特征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模糊到清晰的過程。魯迅指出《老子》“時亦對字協韻,以便記誦”[1](第三篇《老莊》),認為其之所以講究用韻,是為了供人誦讀傳記。張振鏞認為:“其文理精而詞簡,整齊而有韻,蓋沖口而出,自有聲律”,認為《老子》用韻并非有意為之,而是“發之于天籟,本之于自然”的結果 [2](P32)。柳存仁認為“其書為有韻口訣體”[3](P64)。雖然沒有明確指出《老子》的詩體特征,然而聲韻律調卻是詩歌的基本特性之一。惟錢基博謂《老子》“辭以簡雋稱美”,“意以微妙見深”,“其文緩而旨遠,余味曲包”[4](P30),似含有詩意品味的意味。朱謙之對《老子》用韻研究用力甚勤,在所撰《老子校釋》中專列《老子韻例》作專題研究,并獨有心得:“余以為《道德》五千言,古之哲學詩也。既曰詩,即必可以歌,可以誦;其疾徐之節,清濁之和,雖不必盡同于三百篇,而或韻或否,則固有合于詩之例焉無疑。”[5](P313)至此對《老子》詩性特征的認識已趨明朗。任繼愈稱之為“哲理的詩篇”[6]。陳鼓應亦認為:“《老子》五千言,確是一部辭意錘煉的‘哲學詩’。”[7](P7) 對《老子》詩性特征的系統深入研究當在80年代以后。湯漳平《論〈老子〉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一文[8]認為,《老子》是一部“具有完整哲學體系的哲理詩”,不但是“繼《詩經》之后,《楚辭》之前的一部重要詩作”,而且是“我國詩歌史上的鴻篇巨制”。湯氏并從詩歌藝術的角度對《老子》作了評說:“作者采用詩的形式,以簡潔的文字,流暢而富于音樂美的語言,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思想。”章滄授認為《老子》散文的“顯著特征是詩歌化”,表現為“押韻獨密,音韻悠揚”,“長短變化,錯落有致”,“詞約義豐,生動形象”,“多用復疊,盡理窮義”[9]。陸永品雖然認為“不如說它是哲理散文詩更為確切”,但作者的論述仍然是從詩歌藝術的角度展開的:“運用音樂的旋律,輕松的筆調,來闡釋枯燥乏味、窈冥深邃的哲理”,“言辭簡要,旨意深遠”,“能夠引起人們的興味”,“既是詩,又是歌,讀之能給人以輕松愉快之感” [10]。一些研究者還從創作和接受的角度探討了《老子》所具有的詩的“意境”。朱俊芳認為《老子》是“以純熟的詩體寫作的”,它“將哲理與詩,精妙地熔為一爐,鑄成一種亙古不衰的藝術魅力”,既具有“朦朧的詩意”,又具有“深厚幽遠的意境”,因而“它不僅具有思辨的說服力,更有美的感染力”[11]。李嚴認為“不妨把它視為中國文人哲理詩的開端”,“老子創造性地運用了意象化和形象化的創作手法”,“是創造朦朧美的能手” [12]。許結認為老子“是以詩人的情感與形象去表現哲思”,“在創作上,老子對‘天道’或‘人道’的探究首先充滿著詩人的情感,而表現出強烈的抒情性”,“老子運用比興手法將宏深的哲理轉化為形象,以表達精微玄妙的內心世界”[13]。許結另撰有《〈老子〉與中國古代哲理詩》一文[14],探討了《老子》五千言作為哲理詩的特色及其影響,認為構成《老子》作為哲理詩的主要審美特征,是“處處表現出形象化的情節、抒情性的描寫和深婉的理趣美”,以及“《老子》帶著詩意的微笑融自然、人生、藝術于一體的審美意境”,并指出,以詩寓理,于自然中悟道豁情、探索人生哲理,在情景意興中蘊藏機鋒理趣,這些《老子》哲理詩的特點,決定了中國古代哲理詩的基本精神,對后世的哲理詩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老子》獨具特色,雖是文的形式,卻有“詩”的風致,然而是否即可逕稱之為“詩”?有的研究者發表了不同的看法。陳柱認為:“老子多對句矣,多韻語矣,然仍不可便謂之韻文,便謂之駢文也,謂之駢文之祖可耳。”[15](P32)詹安泰認為應稱之為“詩文騷賦的混合體”[16]。譚家健稱之為“散韻結合的格言體散文”。[17](P89)張松如也指出:“老子是在做詩嗎?以其用韻語,也可以作如是觀吧。……但一不入樂,二少抒情,吾人只得于驚嘆其超凡的智慧中,領悟出豐富的詩的樂趣,難以風雅、騷賦相比附也。”[18]蔡靖泉《〈老子〉的藝術成就和文學地位》一文[19]認為:“就整體言,《老子》應歸于散文類,故不妨稱之為‘詩化散文’”,“《老子》有著較高的藝術性,的確可以稱之為精妙的美文。”“《老子》有機地糅合中原和楚地的語言藝術形式而成的詩化散文,一方面將春秋以前韻散結合的語言藝術形式發展到極致,另一方面也宣告了從口頭文學向書面文學轉化的完成。”[19]我們認為,先秦尤其是春秋諸子大多具有良好的“詩學”修養,為文多用韻語與偶句,然而說其具有“詩味”尚可,直接稱之為“詩”則難免削足適履。實際上,稱《老子》為“詩”的研究者,在闡釋其藝術特性時,又往往自相矛盾,多是從散文藝術的角度立論。憑心而論,《老子》在哲學概念與語言選擇的困難中與“文學”不期而遇,詩情、哲理、文思、玄言,熔鑄為一,從而把它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的大道之精微,用“可道”的方式會意于它的“不可道”,《老子》貢獻于后世“文學”者,正在于哲理與文思的會通處,可謂先秦文章中的別一體,很難于“散文”或“詩”的發展線索上為其找到準確的位置,因此,對于《老子》做出符合實際的文體定位,需要謹慎從事。
二、現實關懷與情感內涵研究 老子以清虛自守,卑弱自持為其哲學根基,以“無為”、“不爭”為處世準則,然而老子并未忘懷世事。魯迅獨具慧眼,認為:“老子之言亦不純一,戒多言而時有憤辭,尚無為而欲治天下。”[1]《老子》文多“憤辭”的憂世之言和“欲治天下”的救世之心為當代學者所認識,研究者大多是從現實關懷與情感投入兩方面進行探討。 湯漳平認為:“《老子》最富于現實主義精神,最少宗教迷信色彩”,是“對《詩經》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8]。陸永品亦發表了相同的意見:“我國古代文學,從《詩經》開始,就深深地扎根于現實主義的土壤上,具有反映社會生活和批判不合理的黑暗社會的優良傳統。老子的散文也繼承的這個特點。”[10]朱俊芳認為,形成《老子》藝術魅力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深沉的批判現實的精神,指出:“《老子》的許多言詞詩章都是關注社會人生的,對現實社會中許多至關重大的大小問題發表深刻見解,抒發憤激之情”,“《老子》所表現出的批判現實的精神對后世的叛逆文學有著深遠的影響。”[11]蔡靖泉對《老子》文章中所體現的現實意義作了具體分析,認為老聃疾偽求真,所著《老子》充分反映出他對真實的執著追求,真實地描寫生活,如實地批判現實,“既是他求真精神的具體表現,又是他作品的藝術特色的鮮明體現。”[19]顯然,研究者對《老子》現實品格的挖掘,不過是傳統“君人南面術”之說在現代文化語境下的另種說法。《老子》以五千言之精妙,表現了囊括天人、包孕萬象的心胸,眼冷心熱,于表面的“虛靜”中蘊含對現世的執著關懷,僅以“現實主義”一語論之,終顯流于皮相,因此,如何認識老子的憂世之言與救世之心,尚須深入地體察與感悟。
《老子》所重在天道自然,有情之“我”于“五千言”中似乎是不存在的,然而老子以虛靜自然的人生理想與現實社會碰撞,因理想人格被否定而激發起憤世之情,“五千言”乃以天地之“無情”看待人間之“有情”,發而為文,又時時于精微中吐“憤辭”,于玄妙中露真情。80年代以來的研究者對此也作了一些探討。蔡靖泉認為:“老聃之所以作《老子》,正是其憤世嫉俗的豐富而強烈的感情所激動而不得不發”,“老子在抒情之時,往往因感情強烈而不由自主地將自我融入作品中直抒其情,從而鮮明地展現出自我形象”,甚至從中可以看到“老聃那忿懣之極的音容和表情”[19]。朱俊芳認為:“《老子》以敘事、抒情、議論多種方法,刻畫了老聃復雜而鮮明的形象”,他堅執理想而遺世高蹈,既是一個“古之博大真人”,又是一個充滿憤世之情的“憂世疾俗的士者”。[19]李嚴則對此作了更帶學理性的闡述:“《老子》寓情于理,情、理交融,在對哲理的闡發中滲透著抒情性”,“哲理為感情所浸透,與感情相融合。作者以其蘊含哲理的感情感染讀者,使讀者在體驗其感情的同時,接受其哲理。”[12]《老子》以五千言精妙,將自然與人生囊括其中,包含著對宇宙本體、天人關系、社會現象的深沉思考與熱切關注,研究者論述的范圍僅局囿于社會現象這一層面,而《老子》于宇宙人生的永恒性的關照中所融含的“太上忘情”之“情”,將是一個常說常新的話題。
[1]魯迅.漢文學史綱要[A].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張振鏞.中國文學史分論[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3]柳存仁.上古秦漢文學史[M].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 [4]錢基博.中國文學史[M].前國立師范學院鉛印本,1939,北京:中華書局,1994. [5]朱謙之.老子校釋[M[.龍門聯合書局,1958;北京:中華書局,1984. [6]任繼愈.老子今譯[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7]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及評價[M].臺北:商務印書館,1970,北京:中華書局,1984. [8] 湯漳平.論<老子>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地位[J].中州學刊,1981(2):115-120. [9] 章滄授.論〈老子〉散文的藝術特色[J].安慶師院學報,1985(1):61-67. [10] 陸永品.老子的散文[J].齊魯學刊,1982(2):68-72. [11] 朱俊芳.論〈老子〉的藝術魅力[J].沈陽師范學院學報[J].1987(4):62-67. [12] 李嚴.老子的文學特質述論[J].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哲社版),1998(1):86-91. [13] 許結.從創作看老子的文藝思想[J].中州學刊,1992(3):81-91. [14] 許結.〈老子〉與中國古代哲理詩[J].學術月刊,1990(2):58-64. [15] 陳柱.中國散文史[M].商務印書館,1937. [16] 詹安泰等.中國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17] 譚家健、鄭君華.先秦散文綱要[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18] 張松如.〈老子校詁〉商兌[J].社會科學戰線,1992(4). [19]蔡靖泉.<老子>的藝術成就和文學地位[J].荊州師專學報(哲社版),1995(3):4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