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顆明珠 同放異彩――讀俞平伯、朱自清兩篇同名散文想到的
鄭喜林
【論文關(guān)鍵詞】俞平伯 朱自清 同題同名散文 槳聲 燈影 河水 月光 瑰寶 珍珠
【文論文摘要】1923年8月的一個晚上,俞平伯與朱自清同乘一船,暢游秦淮河,事后兩人同題作文,記述此行此情此景。兩篇同名散文都是境界極佳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瑰寶,中國散文藝術(shù)中的珍珠。兩篇《槳》,從題材上講完全是一樣的,思想傾向也基本相同,但其風(fēng)格不同,情致互映,藝術(shù)筆法也各有千秋。同一景物、同一秦淮河上的夜景,在兩個人筆下卻有不同的意境和感知,可以說他們列出的意境是獨特的,有各自的體驗,體現(xiàn)著個性發(fā)展,情感表現(xiàn)和審美感受力之不同。兩篇《槳》的主導(dǎo)傾向是對現(xiàn)實意識局限性的超越,是全面自由的審美意識的體現(xiàn),這就是該文的美學(xué)魅力之所在。
1923年8月的一個晚上,俞平伯與朱自清同乘一船,暢游秦淮河,事后兩人同題作文,記述此行此情此景。俞先生先寫成,由于“候他文脫稿”,至到朱先生以同名《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以下簡稱《槳》)寫成后,兩篇散文同時發(fā)表在《東方雜志》第2l卷第2號上。這成為現(xiàn)代散文史上一段佳話。至于俞朱二人的關(guān)系,他們不僅同是文學(xué)研究會的成員,同創(chuàng)辦過《詩》的月刊,而“在小品文(即散文,筆者注)的領(lǐng)域中,也常常是俞朱兩家并存的”,“他們的發(fā)展,在最初是完全相同的,就是在寫《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的時代”。(阿英《朱自清小品序》)
兩篇《槳》,從題材上講完全是一樣的,思想傾向也基本相同,都表現(xiàn)“五·四”退潮以后知識分子在黑暗現(xiàn)實面前、在歷史文化心理重負下的一次想尋覓又盡閑適,又無法輕松自懷的,不無迷惘、彷徨的復(fù)雜情緒、心理。但其風(fēng)格不同,情致互映,藝術(shù)筆法也各有千秋。正如文學(xué)評論家李素伯在《小品文研究》中所評說的那樣:“我們覺得同是細膩的描寫,俞先生是細膩而委婉,朱先生是細膩而深秀;同是纏綿的情致,俞先生是纏綿里滿蘊著溫熙濃郁的氛圍,朱先生是纏綿里多含有眷戀悱惻的氣息。如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俞先生是‘朦朧之中似乎胎孕著一個如花的笑’,而朱先生的則是‘仿佛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正因為它們各顯其不同的風(fēng)采,所以才都留在了現(xiàn)代散文里。作家創(chuàng)作,往往是在尋找,創(chuàng)造某種風(fēng)格,有了這種“調(diào)子”,那主題也就具體確定下來,藝術(shù)形象也就萌發(fā)了。我們欣賞時,一旦感受到了作品的風(fēng)格,就等于進入了某種藝術(shù)意境,那具體的個性化的審美方法也就形成,也就找到了理解作品的途徑。
同一對象(秦淮河上的夜景),為什么會有不同的再現(xiàn)、表現(xiàn)?就是因為文學(xué)作品不僅是自我以外的客觀世界的再現(xiàn),而且是自我本身的表現(xiàn)。正因如此,所以對同一客觀世界的再現(xiàn),由于審美理想,即主體因素的不同,在藝術(shù)形象中就會產(chǎn)生不同的特點。如同是寫燈光,朱先生是“大小船上都點起燈火。從兩重玻璃里映出那輻射著黃黃的散光,反暈出一片朦朧的煙靄”。“透過這煙靄,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縷縷的明漪。在這薄靄和明漪里,聽著那悠然的間歇的槳聲,誰能不被引入他的美夢去呢?”注意,黯淡的燈暈水波,逗起游人的美夢,使情與景相互交融、同步展開。俞先生寫燈光正好與朱先生相反,“看!初上的燈兒們的一點點掠剪柔膩的波心,梭織地往來,把河水卻皴得微明了。紙薄的心旌,我的,盡無休息地跟著它們飄蕩,以致于怦怦而內(nèi)熱,這還好說什么的!如此說,誘惑是誠然有的,且于我已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顯然這里的寫景是直接在道情,他把朱先生那化在暈黃燈影中的細膩、婉轉(zhuǎn)、深秀、含蓄的心境直接道了出來。以“微漾著、輕暈著夜的風(fēng)華,不是什么欣悅,不是什么慰藉,只感到一種怪陌生,怪異樣的朦朧。朦朧之中似乎胎孕著一個如花的笑——這么淡,那么淡的倩笑。”我們看,俞先生對著景色,馬上就要進行生澀的心理剖析,批評思想傾向。在歌女表情“如花的笑”——“色”之后,馬上發(fā)了一段“色”即“空”的議論,似有似無,以此來遏制“欲”的沖動。他這綿密柔膩的筆墨與朱先生畫的“輕輕的影和曲曲的波”相照,顯然朱先生的清秀散淡。
他們都寫了“燈月交輝、笙歌徹夜”的秦淮河上的綺麗夜景,寫出了槳聲、燈影、河水、月光之間的關(guān)系及變化,水中燈影、燈下水光、悠揚笛聲與纏綿月色相互交融的一幅幅和諧而多種色調(diào)、多種情味的畫面美景。但同中又有異,其藝術(shù)手法、文筆情韻和整體意境效應(yīng)是不同的。朱先生是精鏤細刻的描繪,細筆畫景,淡墨寄情。其細膩深秀是“一言一動之微,一沙一石之細”都不輕輕放過。他將秦淮河上的夜景拆開來看,拆穿來看,把景分成若干段。如寫槳聲,是幽涼沉重的汨汩之聲;寫燈影,是昏黃的光暈漾成了朦朧的夢;寫河水,是靜靜的,冷冷的綠著的,凝著六朝脂粉滲著歌妓的淚,又載著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和道德反省的。還寫了天未斷黑時與燈火通明時的河水變化,由“陰陰的變?yōu)槌脸亮恕薄憻艄鈮旱乖律约盁襞c月并存、交融的變化。總之,是緊緊扣住燈影水波這些典型材料,從各個角度進行細針密線的描繪和渲染,表現(xiàn)出一種影影綽綽、淡淡的喜悅和淡淡的哀愁的情緒變化,可以說是采用全景式的直接描繪,逼真地表現(xiàn)出當(dāng)時當(dāng)?shù)亍靶庐惖淖涛丁薄赖木辰纾瑥亩〉锚毺氐拿孛堋保纬勺约旱乃囆g(shù)風(fēng)格。
俞先生采用的手法似乎正相反,濃寫情,淡繪景,情景晦澀,委婉曲折,濃得化不開。寫華燈映水,畫肪凌波的景致則線條粗疏,筆墨簡潔,有時索性跳躍著留下空白。寫秦淮夜景,則用間接含蓄的手法,給一種縹縹緲緲,如墮云霧的空靈、朦朧之美。
在歌肪藝妓到來之前,兩篇文章都用了伏筆,為后來的窘迫及夢的幻滅作了鋪墊。但二者是有別的。俞先生的伏筆是情理分析型的。他寫道:“當(dāng)時淺淺的醉,今朝空空的惆悵;老實說咱們萍泛的綺思不過如此而已,至多也不過如此而已。你且別講,你且別想!這無非是夢中的電光,這無非是無明的幻想,這無非是以零星的火種微炎在大欲的根苗上”。這段實際是對當(dāng)時“頗朦朧,怪羞澀”的迷醉感的理性分析,而且是很真誠的。它既承認(rèn)了弗洛伊德所謂的性本能、潛意識的“本我”的喧動存在——“欲的胎動”,又顯示了一種超脫、超越與超度的“超我”的意向,可以說是性本能的騷動,理性、感性的超脫。本能與超越兩種成分在朱先生的筆下也能存在,但它幾乎都化成了景物風(fēng)光;他不是直抒胸臆,更多的是寄情于景。在那黃已經(jīng)不能暈的燈光水影前,“這真夠人想呢”,其實這正是俞先生所說的“夢中的電光”、“欲的微炎”。與此同時,士大夫的潔身自好的風(fēng)度,對社會苦難的感嘆以及更重要的“五·四”人道主義觀念的力量,也時刻制約著作家。它使俞先生坦誠反思,使朱先生深情望月:“但燈光究竟奪不了那邊的月色;燈光是渾的,月色是清的。在混沌的燈光里,滲入一派清輝,卻真是奇跡!那晚月已瘦削了兩三分。她晚妝才罷,盈盈的上了柳梢頭。天是藍得可愛,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兒便更出落得精神了。”“燈與月競能并存著,交融著,使月成了纏綿的月,燈射著渺渺的靈輝。”恐伯這里有更多士大夫的風(fēng)度和美學(xué)存在。渾的燈光與清輝的月爭相對照,很能表達朱先生文章的題旨,足以涵蓋后面一大段令人困惑的道德述論。俞先生也寫月輝,但他是力求在感官享受中去領(lǐng)悟哲理。“燈光所以映她的儂姿,月華所以洗她的秀骨,以蓬騰的心焰跳舞著她的盛年,以飭澀的眼波供養(yǎng)她的遲暮。必如此,才會有園足的醉,園足的戀,園足的頹弛,成熟了我們的心田。”是清輝的月華給了人們一切美好的東西,給了他幽甜。朱先生筆下的月輝,是寄希望于靈肉矛盾之間,正視情的漾動,珍視情的價值。“岸上原有三株兩株的垂楊柳,淡談的影子,在水里搖曳著。它們那柔細的枝條浴著月光,就象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纏著、換著,又象月兒披著的發(fā)。而月兒偶然也從它們的交叉處偷偷窺著我們,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樣子。岸上另有幾株不知名的老樹,光光的立著;在月光里照起來,卻又儼然是精神矍鑠的老人。”當(dāng)我們讀這段出現(xiàn)在迷亂以后的燈光夜景,我們能想的是什么?能想到郁達夫的某種美學(xué)與人的追求,還是想到人文主義的某種姿態(tài),還是一種對美的、對大自然的珍重?這里恐怕有更多的民族文化的沉淀。筆者覺得,還是不要用某種理性去框范那景朦朧、情朦朧的意境吧!至于“燈與月竟能并存著,交融著”一段,文筆則含蓄而清韻。這段月輝詠嘆,筆致可謂情濃似酒,意酣如飴的清醇。從縱向看,雖然后來他在諸如《荷塘月色》、《背影》、《春》、《綠》等篇里,文筆越來越趨于散談樸素,但清俊醇厚卻是貫穿散文創(chuàng)作之始終的;橫向看,在二、三十年代散文作家中,文筆清新者實在不少,如俞平伯的清新夾帶著晦澀,冰心的清新熔著綺麗,郁達夫的清新顯得自然灑脫,巴金的清新尤為明快。而朱先生的清新,則更含蓄,更見功力,更帶酒味。所以說它是和醇厚連在一起的清新。
我們這樣比較,其目的不僅是為了發(fā)現(xiàn)同和異,而且要進一步找到這些同異的背后有什么涵義,從而加深我們對文學(xué)現(xiàn)象和它的本質(zhì)、它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和外部關(guān)系的認(rèn)識,幫助我們揭示文學(xué)的某些規(guī)律,從而得出較為深刻的結(jié)論。
我們看同一景物、同一秦淮河上的夜景,在兩個人筆下卻有不同的意境和感知,可以說他們列出的意境是獨特的,有各自的體驗,體現(xiàn)著個性發(fā)展,情感表現(xiàn)和審美感受力之不同。俞先生是意朦朧、情朦朧,在朦朧中透出空靈、才華,格調(diào)晦澀;朱先生是水朦朧,景朦朧,在朦朧中透出真切,在淡談的語言中埋藏著跌宕起伏的情感,格調(diào)明晰。在主客體的結(jié)合上,俞先生是直接寫感官效應(yīng),寫主觀心理印象中的景;朱先生則更側(cè)重于視覺畫面,在細描風(fēng)景中悄悄滲入情。他寫景朦朧,所以能容納憧憬,“這真夠人想呢。”寫情朦朧,所以能迷醉舒展,“瘋狂似的不能自主。”他們通過創(chuàng)造一種審美意識的對象,符號系統(tǒng)——意境,一種鮮明而又朦朧的境界,把情境、體驗創(chuàng)造出來,使情感具體對象化,使其有所表現(xiàn)、依托、歸宿,使其能看得見,摸得著,這就把只能意會不能言傳,難以把握的東西把握住了,不好言說的東西說出來了。在對象的創(chuàng)造中,實現(xiàn)了自己的本質(zhì),所以它是美的。意境究意美在哪里?因為意境體現(xiàn)著充分發(fā)展的個性和個體意識,它是對現(xiàn)實境界之超越的根本特性,它能把內(nèi)心世界和對象世界的最細微、最獨特的東西傳達出來。王國維的“境界說”稱“境界非獨為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人間詞話》)我們說兩篇同名散文都是境界極佳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瑰寶,中國散文藝術(shù)中的珍珠;它們在審美境界中達到了主客同一,物我兩忘,情景交融。
這情與景同步展開,又呈逆態(tài)反差。
從景物色調(diào)變化看,大致經(jīng)歷了一條由期待的朦朧,逐漸走向耀眼眩目,最后落入昏暗的三段發(fā)展軌跡;而文中的情緒色調(diào)變化,也大致經(jīng)歷了由對閑適、對夢幻的憧憬,逐漸走向沉醉迷亂,最后融入寂寞惆悵的三個發(fā)展軌跡。對照一下兩條基本軌跡,不難發(fā)現(xiàn)起始是同步的,展開部分是對應(yīng)的,但在逼近高潮出現(xiàn)轉(zhuǎn)折時(即歌妓來相擾),景與情呈現(xiàn)反差,正是這種“六朝金粉”的遺留“艷跡”——歌妓賣唱,與作者恪守的道德律的矛盾——逆態(tài)反差,不僅造成記游情節(jié)的高潮,同時也導(dǎo)致了結(jié)尾、余音又重新同步吻合、和諧起來。景就是“黑暗重得落在我們面前”;情就是“我們的心里充滿了幻滅的情思”。從結(jié)構(gòu)構(gòu)思來講,與敘事線索(外在線索)相對應(yīng)的情緒、心理波瀾(內(nèi)在線索)是順著這條觀賞路線而發(fā)展、而變化,并緊緊地纏繞在這“觀景”敘事線上,基本是景至情至,景移情移。
但俞朱二人的造境方法是不同的,俞先生是以意造境,以審美意識創(chuàng)造審美境界,通過感情的渲染把人引入審美境界,不大重視具體視覺形象的再現(xiàn)。如文章開頭一句“我們消瘦得秦淮河上的燈影,當(dāng)圓月猶皎的當(dāng)夏之夜”。就是從對情緒心境的分析來融化景物風(fēng)光的。與朱先生那開篇用語言丹青點染的水景畫相比,顯然線條比較粗疏。朱先生是以境寫境,以審美對象——物象創(chuàng)造審美境界,通過白描景物,將情感滲于其中,以情心、情眼、情手來再造自然環(huán)境,千萬情景交融的“有我之境”。 獨特的意境就存在于獨特的的風(fēng)格之中,而風(fēng)格的獨特性,就是個性化的審美方法(創(chuàng)造方法),它與每個人的氣質(zhì)、思想感情、藝術(shù)修養(yǎng)相聯(lián)系。楊振聲在《朱自清先生與現(xiàn)代散文》中指出:“他文如其人,風(fēng)華是從樸素出來,幽默是從忠厚出來,腴厚是從平淡出來。”此說不謬,但不能令人滿意。用“文如其人”作解釋,從“世界觀與創(chuàng)作方法的矛盾”,“形象大于思想的角度”來論證,是不全面的。用藝術(shù)個性產(chǎn)生于現(xiàn)實個性又高于現(xiàn)實個性的理論予以根本性的說明會更全面些。藝術(shù)高于現(xiàn)實生活,也高于現(xiàn)實思想感情,只能用現(xiàn)實個性與審美個性的辯證關(guān)系來作解釋。藝術(shù)風(fēng)格是藝術(shù)個性的體現(xiàn),而作家的個性、品格、作風(fēng)是現(xiàn)實個性的體現(xiàn),是屬于現(xiàn)實個性范疇的,是現(xiàn)實人的特點。當(dāng)進入審美關(guān)系后,現(xiàn)實個性將上升為審美個性、藝術(shù)個性,是高度個性化了的“我”,正如歌德所說:“是歌曲創(chuàng)造了我,而不是我創(chuàng)造了歌曲,在它的力量中才有我。”在現(xiàn)實生活中,俞朱“兩個人都希望‘現(xiàn)代’能加上‘光明’,然都缺乏著自己創(chuàng)造的力。這是他們非常共同的地方。這情形,在他們的思想根底上可說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俞平伯,一般地說,是比較樂觀,但也畢竟跳不出‘往昔的追懷’的圈”,“他和朱自清一樣地知道必須執(zhí)著‘現(xiàn)在’,但他卻不自主的,想把自己帶到過去以至往昔,這傾向一天比一天來得強”。他是“眼睛雖依舊向著‘現(xiàn)代’,而他的雙雙腳印,卻想向回兜轉(zhuǎn)。”(阿英《朱自清小品序》)如歌妓來相擾時,俞先生對歌妓們“欲的胎動”,寫得含而不露,雖只顯示人性的一面,但很真實,給人的感覺仍是若隱若現(xiàn),朦朦朧朧;他對妓船的態(tài)度比較恬淡、超脫,所以能“簡單、松弱”,怡然自若。朱先生在歌舫前則是發(fā)窘、猶豫、乃至惶恐不安,歌舫三次相擾,他“受了三次窘”。歌舫越是干擾,或越是強烈,而主人公的樂觀憧憬就越是破滅,也就越是受促;這種逆態(tài)反差還表現(xiàn)在歌舫離開以后,誘惑消除后,他又怕又窘,歌舫真地離開了又有盼望、憧憬的不滿足感,重新導(dǎo)致那種悵惘、寂寞。整個看理想追求是朦朧不確知的。
可以說朱自清是一個“帶著傷感的眼看著‘現(xiàn)在’的剎那主義者。”(同上)他有缺乏投身革命的勇氣,找不出產(chǎn)生的根源,想不出療救的方法的一面,也有積極肯定的一面,愛憎分明,具有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和不沾于污泥的人格。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在舊時代正在崩潰,新局面尚未到來的時候,衰頹與騷動式的大家惶惶然,只有參加革命或反革命,解決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參加這種實際行動時,只有暫時逃避的一法,當(dāng)然這是痛苦不安的逃避,象一葉扁舟在無邊的大海上,象一個獵人在無際的森林里,似乎在掙扎著。”可以說他這是獨善其身的掙扎,在掙扎中有逃遁,在逃遁中也有掙扎。這種現(xiàn)實處境是由他的整個政治態(tài)度所決定了的。除此而外,還不應(yīng)忘記朱自清是一位正直的知識分子,是能遵循“為人生”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主張的文研會成員,他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是嚴(yán)肅的,對掙扎在秦淮河上的歌妓也是懷有同情之感的。我們說在《槳》中的“我”,已不再是現(xiàn)實中的俞平伯、朱自清了,而是理想中的自我,非現(xiàn)實中的我。在現(xiàn)實中的個性可能是受壓抑的,而藝術(shù)個性卻能充分發(fā)展,不受束縛,因作品中的自我是審美創(chuàng)造的產(chǎn)物,它既有審美主體特點,也有審美對象的特點,已具有了不同于現(xiàn)實對象的審美意義。
他們對人生意義有了新的理性思考,特別是道德反省(即特定時代的社會條件下的人性思考),一方面他們以人道主義觀念為依據(jù),對人的七情六欲的大膽認(rèn)同和肯定,應(yīng)當(dāng)說俞先生在這方面更豁達些,他把秦淮河上的“一抹胭脂的薄媚”說成是“姐妹們”“臉上的殘脂”,其內(nèi)涵就更深邃些,不難發(fā)現(xiàn)作者對被蹂躪與被損害的歌妓們的同情之感;而擺脫糾纏后的他,也顯得更加開朗大度,因而得到“園足的醉、園足的戀,園足的頹弛,成熟了我們的心田”。像俞、朱二位這種從解剖書生的迷醉入筆的寫法,則更具有對傳統(tǒng)禮教的挑戰(zhàn)性。這是非常可貴的。另一方面又對這種在水波燈影挑逗誘惑下的迷亂的憧憬,給予了明晰透辟的觀照和超脫力量,提供了三個極為復(fù)雜而糾纏的依據(jù)。(一)是人道主義博愛精神,俞先生就引用周作人的詩句,以表白他拒絕歌妓的理由,“因為我有妻子,所以我愛一切的女人;因為我有子女,所以我愛一切的孩子”。兩個人在這里顯示的主要是博愛精神。(二)是對社會苦難,對民眾不幸,感時憂國的憂患意識,朱先生表現(xiàn)的更為強烈些。(三)是傳統(tǒng)文人潔身自好,同時又不無矜持的心理習(xí)慣,還有士大夫以求人格完善的精神傳統(tǒng)。朱先生對暈黃的燈光,清朗的月輝的描寫,以及他在后來道德禮遇、情感、價值的惶惑心境,則更多地體現(xiàn)了這后兩種制約。《槳》之耐人咀嚼、耐人尋味的意趣,正是在這三種“解脫力量”之微妙關(guān)系中。朱先生是靠情的漾動,俞先生是靠理的平衡來支撐全文的。
審美主體要對現(xiàn)實超越。當(dāng)作者將自己思想感情融注于自己筆下的形象時,由于他們既飽含著生活氣息,又高于生活,給人的啟示、聯(lián)想,往往會大大超越作者原來的思想,而具有更廣、更深、更為普遍、更為豐富的意義。他們在時代允許的限度內(nèi),超越了階級意識的局限,追求人生自由幸福,反映著人類的價值追求。理想追求雖說是朦朧,不明確的,帶有一定的感傷主義,但都證明了近代的人道主義最終壓過了士大夫的情趣,所以當(dāng)秦淮夜泛將要結(jié)束時,讀者一方面為月的清輝終于不為黃暈的燈火所淹沒而感到道德意義上的凈化;另一方面也因后來的寂寞惆悵、夜幕降臨,又為情的價值而“悄然”輕嘆。但該文最終給予我們的是人生的最高價值,最深的底蘊。所有這些社會、政治、歷史、文化意蘊的感傷,又都如此自然地化為情與景的同步、反差交融之中,都化為光和影的朦朧曲線,“微波的殘影”“靜靜的,冷冷的綠著”的秦淮河水。兩篇《槳》的主導(dǎo)傾向是對現(xiàn)實意識局限性的超越,是全面自由的審美意識的體現(xiàn),這就是該文的美學(xué)魅力之所在。我們欣賞時完全可以根據(jù)這些不同形象的啟示,聯(lián)系自己的人生道路、生活經(jīng)驗與藝術(shù)修養(yǎng)去聯(lián)想、去發(fā)揮、去補充、去創(chuàng)造,而大可不必拘泥于某個一人一事。
“俞朱雖然并稱并存,在成果上是俞高于朱的,無論在內(nèi)容上,抑是文字上,抑是對讀者的影響上。要說朱自清優(yōu)于俞平伯的所在,那我想只有把理由放在情緒的更豐富、奔拼,以及文字的更樸素、通俗上。”(同上)關(guān)于這方面的評價我們從《槳》這篇文章里可得到印證。但更應(yīng)提及的是朱自清的確是一位有杰出建樹、有獨特風(fēng)格的散文家。他那精鏤細刻的描繪手法,姿情橫溢的情趣,別具一格的風(fēng)味,以及三者的和諧同一,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散文創(chuàng)作對于創(chuàng)建白話散文做出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對于五四以后以及當(dāng)代散文創(chuàng)作有著深刻的影響。
阿英《朱自清小品序》
楊振聲《朱自清先生與現(xiàn)代散文》
吳周文《論朱自清的散文藝術(shù)》
葉圣陶《朱佩弦先生》
《朱自清研究資料》,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81年版
王國維《人間詞話》
李素文《小品文研究》
雜志.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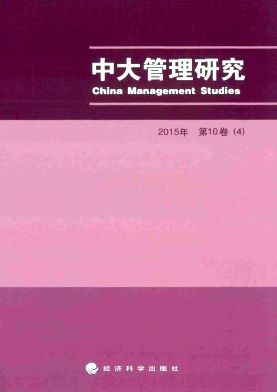
學(xué)報.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