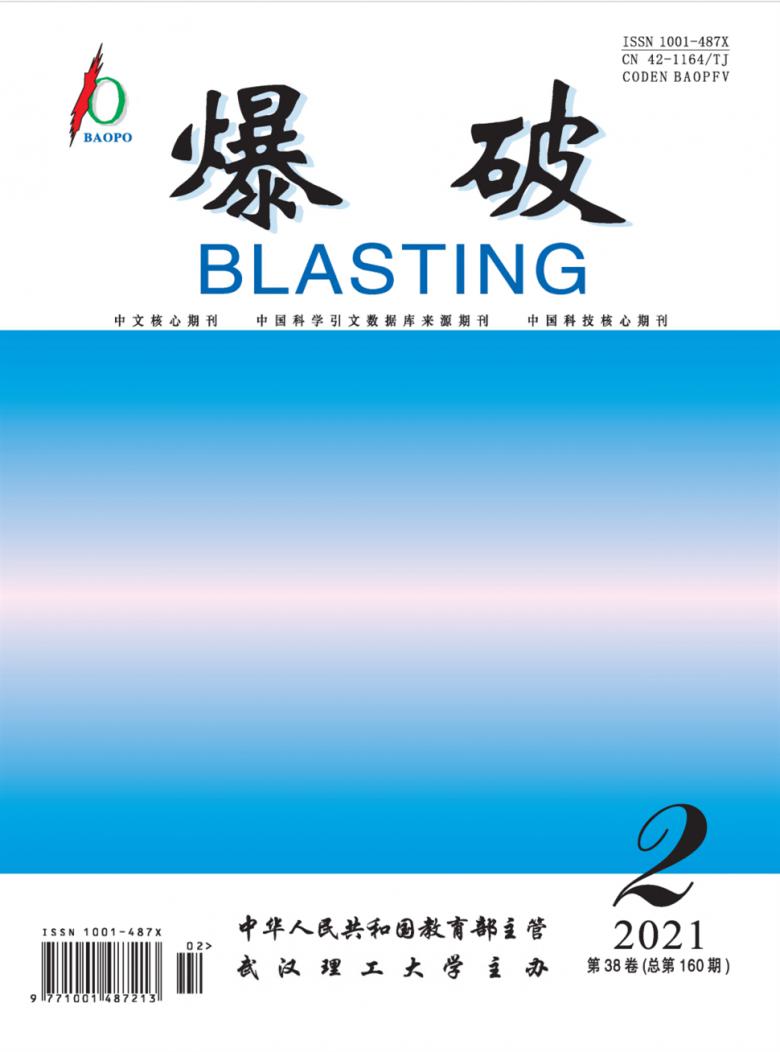淺談審美的兩難困境——汪曾祺散文新論
劉琴
論文關鍵詞:傳統現代性審美困境
論文摘要:汪曾祺散文承襲了明清文人的“閑適”語言風格,并進而形成了個體化的語言風格。因為現實社會語境中諸多因素的限制,他的“閑適”言說實質上是對自己精神內在家園的遮蔽,具體體現在他的言說與生命存在的沖突以及他對傳統和現代的復雜體認.這些復雜的審美感受在審美上所形成的兩難困境源于汪曾祺對生命的曲折表達。
汪曾祺小說寫得好已是不爭的事實,自第一本散文集《蒲橋集》出版以來,他的散文也成功地進入了我們的視界。1997年汪曾祺謝世之后,學界對他的研究更為深入。可是,這種深入多聚焦在小說上,對他的華彩散章卻用力不多。誠然,釋讀小說是于“解蔽”中找出埋藏,而散文的喜悅和悲傷因真實變得透明,失卻深度解讀的快樂。但是,我們對汪曾祺世界的探詢。不能只限于其文本世界,其文本表述方式與個體精神世界的深在勾連同樣吁求我們矚目。散文因靈魂的自由能漫溢出作家精神世界的各種真實信息,于是,解讀汪曾祺散文所呈現的種種精神沖突,成為我們探詢汪曾祺世界的另一條路徑。
一歷史的懸置
汪曾祺散文雖多,卻不外乎記人事與風物小品兩類。《蒲橋集》在封面總述其散文“記人事,寫風景,說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這段汪曾祺自撰的廣告語鮮活地道出其散文的個性風范。據汪曾祺自述,他的散文風韻源于傳統文化語境,這里的傳統主要指稱明清文人與五四散文傳統,至于西方現代主義,他年輕時也曾受過影響,“也可以說是摹仿。后來不再摹仿了,因為摹仿不了。”(雌明清文人中是歸有光、桐城派、李卓吾等人對他影響最深。說到五四散文傳統,汪曾祺從其師沈從文和廢名那兒承傳過來的是對“五四”進行反思的寫作傳統,這個寫作傳統實質上在汪曾祺心中“與他向往的明清筆記的文人語言傳統是一回事情”。換句話說。汪曾祺散文靈魂的源頭是與明清文人語言傳統密切勾連。
考察明清文人語言傳統還須回溯明清文人身處的文化語境,他們的語言姿態建立在時代景深之上。如所周知,文字獄的興盛致使明清兩代的優秀文人退居社會的邊緣,沉浸在國家話語中的他們遭際著痛不欲生的靈魂斷裂,一方面是國家及告密者的暴力脅迫,一方面是千百年來“士”人所賴以存活的明亮而煊赫的治國理想的崩毀。日日茍全于冰與火的邊緣,他們只能擔荷起歷史的密集苦難痛楚地活著,這種痛苦被他們以各種生存方式消解著。于是,明清文人們寄興山水,縱情園林,賞玩花草,品味飲食,在對生命細枝末節的體味中走進了一個文學藝術自我愉悅的心靈“唯美化”時代。“也許在這個肆意暴虐并且瀕于覆亡的時代,由‘唯美化’所體現的精神現象,就適宜用‘閑適’二字來概括了。”(撈這種“閑適”的生存圖景正包容著我們所欲破解的隱秘信息。我們發現,明清文人的生命中充斥著難抑的痛楚:永遠不能高踞廟堂之上為自己的國家幻想作出告慰,還要為肉體的茍活膽戰心驚著,但他們的言說卻是如此的閑適優雅。在他們身上,言說與生命本質出現了分離,而且是永遠沒有彌合的分離。這場遙遙無期的分離為我們留下了大量充溢著個人生命情趣的精雅文字,也在歷史上懸置下一種別樣的生存圖景,那就是他們那“閑適”的生存言說實質上是人的另一種實存:人可以在其生命本質之外自在地生存。
明清文人的“閑適”生存言說源頭可追溯到莊子。這位先秦時代的逍遙客以“自然之情”體驗“天地之美”,并超越一己生命而“與天地精神往來”。他告訴我們,純真之氣和精微之美能使人逾越生命本質的逼迫和追問,成為一個真的人,而真的人,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盡管莊子對“真的人”的闡述對解釋明清文人生命本質和言說的分離問題頗有啟示。但它并不能支撐起人在現實生活里的生命失重。要確定分離問題的要旨所在.我們不得不超越“真的人”的烏托邦神話。明清文人于最無助的時候在生存方式上承襲了莊子的“逍遙游”,然而,這種逾越生命本質的另一種實存并不能成為一種常態,為言說與生命的分離負責,它多半在歷史上成為一種懸置,人們會體味,卻很難去尾隨。
二言說與生命存在的沖突
在部分研究者看來,這一歷史的懸置似乎在汪曾祺身上得到較為理想的回應。他的文字也雍容自若,他的語言也張弛著閑適情懷。可是,這一比較雖然有著表面的合理性,危險卻不容冰釋。繼續回到文化語境上來。
我們知道,汪曾祺所處的文化語境雖也命途多舛(1920年出生的汪曾祺經歷了20余年的戰亂和10余年“人心惟危,道心惟危”的文化浩劫),卻最終走向了一種多元化態勢.這一態勢能夠為文化人發揮其表達功能提供著長足動力。雖然語言姿態可以承傳,從明清文人與汪曾祺各自所處的文化語境的不同,我們依然可以對那些專屬于明清文人的精神元素能否被后人完成同等復制產生懷疑。更進一步說,我們還忽略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根本上說,文學就是個體化生存的事業。汪曾祺對明清文人的語言姿態的承傳,經過個體化的衍變,就很難把時間所清洗的東西如數還給我們,最終會成型為汪曾祺個人的語言范式。如果說汪曾祺呈現出與明清文人相近的“閑適”的生存姿態,它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意義對接,刻上了他個人生命印痕的那一部分就難以完成歷史重疊。發現歷史的某些相近可能對我們認識一個作家有幫助,然而,就目前來看,在重疊歷史論的陰翳下明亮作家的個體化印痕,對這個作家的認知會更具客觀性。
汪曾祺的散文幾乎寫的都是經年舊事。像“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湯”、“昆明城外。遍地皆植馬尾松,松毛易得”、“徐志摩上課時帶了一個很大的煙臺蘋果,一邊吃,一邊講”等等,是一些很溫暖的人事。汪曾祺在《文集自序》中認為不是什么樣的內容都可以寫進散文。那么,為什么他的散文世界充斥的基本是經年往事?汪曾祺以為“必須把熱騰騰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樣,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經過反復沉淀,除凈火氣,特別是除凈感傷主義。”以我的理解,是“沉淀”使他對他經歷過的時代變得諒解了,也愿意回過頭去看一看。這和對傳統文化的懷戀不全是一回事。王安憶在《長恨歌》里塑造出一個舊日的上海,讓我們記住的是王琦瑤所生活的陰暗的上海弄堂。這部小說你可以說王安憶在懷舊,也可以說她在反思那個逼仄的年代,當然也可以說什么都不是,王安憶只是寫出了一個她想象中的上海。這些不同角度的解讀無礙根本,因為好的小說就是復義多解的,問題的關鍵是在于汪曾祺和王安憶為什么都固執地沉迷于敘寫往事,尤其是汪曾祺,他的作品收編的都是自己的陳年記憶。我以為,這關涉到一個時間視角問題,人一旦攫取了某種時間維度去觀照人間世,諸如前塵、現世和未來的時間分類的問題雖然層出不窮.但是終結式的解決辦法還得在現世中尋找回答。
汪曾祺就愛隔一段距離往回看.他的回望并不是印證往昔與現在的新與舊、好與壞.而是讓它們在時光行程中互為辯證。美才是往昔與現在的最后依歸。正是對“美”的呼吁和訴求構成了汪曾祺的本文,成其心中最神圣的內在家園。以我的理解,“美”在汪曾祺眼中意味著人的自我實現。意味著生命的本真存在.這同樣也是許多走個體化之路的知識分子的生命旨歸。但是,人的言說并不見然與生命本質獲取同一。人是不斷個體化的人卻被拋在社會化的命途上,“社會生活的組織化與整一化,要求個體必須與他人趨同,差異被認為是危險的,整一的組織化和社會生活對個人有一種強迫就范的壓力。”這種壓力使人的生命趨向孤獨與焦慮,為了緩解社會化的壓抑,他以融人外部世界的言說實現了社會期待式的正常生存,卻又導致了言說與生命的偏離,成為對生命的一種整容。這種偏離在某些時候會呈示出一種尖銳的對立。譬如魏晉時期“竹林七賢”的放任輕狂、孤傲不羈和阮籍的窮途迷哭,還有稽康的死亡琴聲,讓《廣陵散》的悲音如風一般敲打著往者與來者的心魂。譬如明代的徐渭在斷裂的生命里對自己肉體的一次次戕殺,一次次痛不欲生換來的只是無情的挫敗,他在放誕的言說中最終成為一個茍且者。我們發現,汪曾祺散文里的言說雖淡美如菊,卻不能清洗掉生命世界中真實的痛感。他的現代體驗的獨特蓋由于這個層面的存在,這就是淡美如菊的言說和生命的真實痛感之間所構成的存在沖突和矛盾。我們知道,淡美如菊的言說產生于一個封閉的時空,即現代之外.若人能永在現代之外,淡美如菊可能是美妙的,但事實上,世界已將中國納入現代之中,淡美如菊自然就無法恒久維持。汪曾祺感受到的精神的沖突乃至存在的沖突就在于他已經知道了現代,進而知道了淡美如菊的虛幻,他是如此沉湎于淡美如菊的現代之外.他又是如此擅長淡美如菊的言說,他更是如此清楚淡美如菊的虛幻,因之,這種存在沖突所產生的現代體驗才是如此深刻而獨特。于是,本是巨大的人生悲楚化為平常話語,本是無法屈抑的苦痛咽進了靈魂深淵處,種種精神苦難轉化為情趣盎然的精神自娛。 事實上。向回看就是時間的回流,是寫過去的生存現實,更進一步說是在沉積中敘述出一個屬于自己審美視野的過去,自然就會對過去的時間和空間進行審視和反思,這種回溯能讓我們體悟到時間的悲劇感。線性向前的時間一旦往回看,望著時間不可逆轉地遠逝,而它帶給我們的東西無論美丑好壞都要失去.這種生命一無所獲的結局就成為我們最難以言及的哀傷。汪曾祺以他那平淡潔凈的言說慢慢地為我們揭開了人的生命淵藪中最悲涼的一層,于是,過程中的溫馨成為蒼涼,自娛變作哀戚,譏諷化為悲楚。生命因這真實的痛感而令我們久久咀嚼,長長回味。
三傳統與現代的復雜體認
在時間回流中,汪曾祺的散文于回瀾拍岸中讓我們重溫過去的風韻和余傷。像《下水道和孩子》是對孩子夢幻想的書寫,《懷念德熙》是為“藹然仁者”立言,《隨遇而安》的悠然自述中涵容了對民族精神人格的反省。就是《紫薇》、《蘿卜》、《天山行色》這類純風物小品,也飽含著傳統的風韻,譬如龔定庵的《說居庸關》的第一句便促生出《天山行色》的起首句:“所謂南山者,是一片塔松林”,“這樣的開頭,就決定這篇長達一萬七千字的散文。處處有點龔定庵的影子。”引)通過回望傳統,我們重新認知了傳統的力量。傳統是一種濃烈的精神濡染,汪曾祺除了對傳統的正面力量給予了肯定,他的傳統回溯還隱藏著另一種視角,隱藏著對傳統的負面規約的冷眼。隱藏著歷史清理中產生的必然歧義,后者在汪曾祺后期散文如《可有可無的人》、《吃飯》等文中尤其凸顯。到汪曾祺生命的最后階段,他的文字越來越樸素凝重,無聲的悲鳴寒風一般陣陣吹進我們的肺腑。
汪曾祺的現代性思索也存有另一種視角。在《香港的高樓和北京的大樹》、《香港的鳥》等散文中,汪曾祺提到“樹被人忽略了”、“對于某些香港人來說,鳥是可吃的,不是看的,聽的”。淡淡道來,卻使人對現代性單向度地大量繁殖和擴張產生一種憂慮,一種警醒。在文化的意義上,汪曾祺的這一憂慮和警醒易被認為是對傳統的懷戀,很容易被判釋為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如今,在現代化研究大家艾森斯塔特的理論修正下,我們明白了“實際上現代性有多種面相、多元的模式”,“批判現代性也不等于反現代性.而完全可能是用一種現代性來反對另一種現代性。”就此而言。作為對現代性理解模式專制的險情警告,汪曾祺那既渴求現代性又質疑現代性的復雜文化心態也是一種現代性,一種意義和反義在自身內部同時生長與繁殖的復雜現代性。
事實上,現代性所蘊涵的內容,在不同的人那里。會有著不同的角度和尺度。我們能夠接收現代性中那些咄咄進擊的元素.也應該允許對人生踐行路線作出不同的理解和交叉。不同的交叉點隱伏在密集的語詞里,不時給一往無前的人們添加一些猶疑。
憑借上述體驗,我們能夠發現汪曾祺散文里存在著許多矛盾的、悖論式的圖景。有淡美如菊的言說和生命的真實痛感之間所構成的存在沖突和矛盾,還有現代性渴望和現代性焦慮的錯綜互文。這些圖景雜陳在一起。無論現象上的還是文化上的,都會將其繁復而蕪雜的生命感受作用到汪曾祺的審美感知領域。從而令他步人一個審美的兩難困境。這種不能定論的審美兩難困境也因四處旁顧,不能專營,伸展著審美意蘊在萬端紛紜的因果網絡中的可能性和豐富性,它不是審美范式專制下的一點意外,而是對復雜的審美景觀的一種挽留。
巴烏斯托夫斯基在《金薔薇》中寫海涅到盧浮宮,總是久坐在密羅斯的維納斯雕像前哭著。“哭的什么呢?哭的是一個人被侮辱了的完美。哭的是那走向完善之路既艱難且遙遠。”罔我以為,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人人都是那久坐長哭的海涅,巨大而無所不在的文化和歷史阻力對于有限存在的我們而言,是無法徹底擺脫的,在有限存在與無限期許的磨礪中,生存之痛綿綿而生。而人類的偉大就在于他有能力在沉淪中自我超升.雖然他們由于自身的有限性永遠不能走到終級的完善天國,但他們在承認有限性的同時始終在尋找新的可能性與開放性。汪曾祺散文所呈現的復雜審美景觀就是一種關于有限和無限的尋找,那里洋溢著即興的、跳躍而靈動的生命內力,有真實而鮮活的迷惘,有孤獨而自由的突奔,還有辛酸的收益。這些浸淫著蒼涼的尋找讓我們對生命深懷感激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