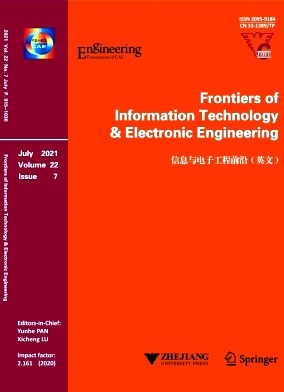關于散文觀念的突破與當代散文的前途
陳劍軍
中國散文從先秦時期就有“文”與“野”之爭,比如在《論語?雍也》里,就有“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的品文評人的標準。到了魏晉南北朝,又有“文”與“筆”之辯:“文”指詩賦等有韻的文學,“筆”指章奏、論議等無韻文章。后來,“文筆”又有所泛化,“文”指文辭優美的文學作品,自然也包括散文。也就是說,散文不僅要有“性靈搖蕩”、“流連哀思”的內在感情美,還要有悅耳動聽的音律,要有形、音、義俱佳的文字美,正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這是中國散文的一筆豐厚財富,也是西方散文所欠缺的。中國散文能披荊斬棘艱難前行,并在上世紀90年代之后大放光彩,與這一偉大傳統的“支援”密不可分。那么在今天,我們有什么理由為了散文的“野”而丟掉“文”的傳統呢?我認為這是每一個熱愛散文的讀者和作家、散文研究者必須面對和認真思考的問題。
四 “真實”與“虛構” 散文的“真實與虛構”是與“真情實感”同一級別的散文核心觀念,也是關系到當代散文前途的關鍵性問題。 散文的真實性問題,一向被視為散文的基石。這種對真實性的嚴格要求有著深遠的文化傳統背景:中國的散文最早是應用文,后來又與史傳結合。應用文與史傳對題材的要求十分嚴格,不但作品中的人物、大的歷史事件要符合歷史真實,即便一個細節也不能杜撰。所以左思說:“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B12 這種對“本”和“實”的嚴格要求,對現代散文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以至于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人們都篤信散文必須描寫真人、真事、真景物,并將其視為散文最基本的要求和不容偏離的創作原則。比如周立波在其主編的《散文特寫選》(1962年)的序言中,就寫下一段頗具權威的話:“描寫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散文特寫絕對不能仰仗虛構。它和小說、戲劇的主要區別就在這里。”甚至到了90年代中期,在一篇標榜“散文新觀念”的文章中,還有論者堅守真實性這片散文的最后“疆界”:“從接受美學的角度,散文如果描寫的不是關于實際發生的事情,而是關于可能發生的事情,讀者就會出現閱讀障礙……如果越來越多的人在散文中像寫小說一樣虛構事實情節,那無疑是‘自毀長城’,失去疆界的散文也就失去了散文自身。”B13 可見,“真實性”觀念的確立不僅源遠流長、根深蒂固,而且是一種較為普遍的散文觀念。那么,應如何理解散文中的真實與虛構的問題?或者說,我們應怎樣去把握散文中真實的“度”呢? 首先應看到,傳統散文觀念所強調的是一種“再現”式的“絕對真實”,即與作者有著直接關聯的、來源于作者個人的生活經歷。但從散文的創作規律和散文的發展趨勢來看,要使散文所描寫的內容與作者的“個人經歷”完全吻合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由于:第一,散文中所表達的“個體經驗”并不完全等同于“個人經歷”。“個人經歷”是個人歷史的真實記錄,它是一種“實在”,是難以更改的,而“個體經驗”是對以往“個人經歷”的一種整合。它一方面已不具備“個人經歷”的即時性和臨場感,另一方面又加進了不少作者主觀想象的成分。比如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巴金的《海上日出》,都是以“個人經歷”為素材,然而他們的描述又不完全拘泥于個人的經歷,而是一種綜合了各種個體經驗的藝術化表達,我們能說這種表達違背了散文的“真實性”原則嗎?第二,由于散文創作往往屬于“過去時態式”,而按照一般的心理表征,時間越長,空間越大,越容易造成錯位和誤置。這樣,從親身經歷到記憶中的真實,再到筆下的物象情景,其生活的原生狀態實際上已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變形。換言之,由于時空的錯位、記憶的缺失、主觀意識的介入,作家已不可能在作品中再現原來的真實環境了。第三,也是更為主要的一點,我們發現,進入90年代后,隨著文學環境的寬松、作家心態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改變,散文也變得越來越自由開放了,于是出現了大量“法無定法”、敢于“破體”的作品。比如賈平凹的游記,就有大量虛構性的成分。余秋雨的《道士塔》、《這里真安靜》等作品,更是將小說的場面描寫、戲劇的情節沖突移植到散文中。至于“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其虛構和想象的成分則更多。事實上,散文這種偏離“真實”法則的創作傾向不獨發生于90年代的中國大陸,早在80年代,臺灣地區一批有志于變革散文的作家便在這方面做出了努力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比如簡貞的《女兒紅》、《秋夜敘述》,林耀德的《房間》,林幸謙的《生命的風格》等作品,均是以虛構、想象和意象的密集奇詭著稱。甚至余光中、楊牧等老一輩散文家,也不甘落后寫出了像《蒲公英的歲月》、《年輪》這種在真實與虛構、想象與寓言間恣意穿梭交織的作品。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散文的“真實性”雖然是一個誘人的話題,或者說是一個美好的愿望和期待,但對于實際的散文寫作來說,它也僅僅是一個愿望和期待而已。誠如上述,對于發展和變化了的當代散文而言,“虛構”和“想象”對于散文事實上已是不可避免的。何況,一切文本都有虛構性的特征,散文怎么能夠無視文學的鐵律而獨擁“真實”呢?既然散文無法回避虛構和想象,我們又有什么理由將散文的“真實”原則推向極端,硬要作者按真人真實真景去創作呢?須知:如果作者筆下的一事一物甚至一個細節都必須與現實生活“逼肖”、“吻合”,達到“真實無偽”的地步,那么,散文作家也就變成了高爾基比喻的那條蜈蚣一樣根本就無法動彈、無從下筆了。所以,在清理散文的地基和建構新的散文觀念的今天,我們應拋棄封閉保守的散文觀念,旗幟鮮明地提出“有限制虛構”的觀點。所謂“有限制”,即允許作者在尊重“真實”和散文文體特征的基礎上,對真人真事或“基本的事件”進行經驗性的整合和合理的藝術想象,同時又要盡量避免小說化的“無限虛構”或“自由虛構”。在我看來,只要我們把握好“真實與虛構”的“度”,既不要太“實”又不要過“虛”,散文的“真實性”這一古老的命題便有可能在新世紀再現原有的活力。 五 “在場”與“出場” 這一組矛盾主要是針對當代散文的現實性而言,長期以來,中國散文的一大癥結就是現實性的缺失。進入新世紀以來,這個問題有了一定的改觀,但當代散文在反映現實生活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在價值取向和審美趣味上出現了偏差。這種偏差具體表現在: 其一,過度美化現實。進入90年代以來,楊朔式的一味歌頌“詩化”現實在理論層面似乎被唾棄了,但在實際創作中,仍有不少散文作者“無意識”地迷醉于“楊朔模式”的醇美酒漿中。甚至像劉亮程這樣的“新鄉土散文家”,在他的“鄉村哲學”的抒寫中,雖然一方面有批判,有黑暗和苦難的展示,但他唱得更多的仍然是鄉村的牧歌。從他作品的深處,有時我們還可依稀聽到楊朔“詩化”生活的余音。再如任林舉的長篇散文《玉米大地》,它的描述很抒情,文字也相當優美,尤其是它所體現出來的大地意識、民間情懷和審美品格,在近年的散文中并不多見。然而,在一篇七萬多字的長篇散文中,作者只是確立了“玉米”這一中心意象,將所有的人事、現實、歷史、生命和回憶統統與玉米掛上鉤,“在紙上把玉米再耕種一篇”。這樣不但過度美化了玉米,讓玉米承擔了太重的思想和情感負荷,而且也顯得有些牽強附會、矯情做作。像這樣過度美化現實和大地 的散文,在近年出現的“新鄉土散文”中可以說是屢見不鮮。
其二,將現實等同于“一地雞毛”、雞零狗碎的日常生活的純搬照錄,或枯燥乏味地記流水賬。這種創作狀況在“原生態散文”、“在場主義散文”中較為常見。在這一些散文中,作者為了使作品具有所謂的“強烈的現場感和生活質感”B14,或為了“介入”、“去蔽、敞亮和本真”B15 ,恨不得把自己身邊的瑣事,把親歷過的“現實生活”都搬到作品中。比如在周聞道主編的《從靈魂的方向看》這本2008年在場主義散文年度選集中,便有不少這樣的例子。如有一篇題為《雙河場》(作者袁瑛)的作品,寫一個叫“雙河場”的小鎮,先寫這個小鎮名字的由來,接著寫一條叫“觀音閣”的小巷子。從巷子里的補鍋匠鋪子、賣壇罐鋪子,寫到雜貨鋪、裁縫店,再寫到裁縫店的女主人、裁縫店對面的軍屬寡婦,還有老住戶辛老師。寫了“觀音閣”后再寫出另一條街“橫街子”,采用的也基本上是甲、乙、丙、丁,記流水賬的寫法。《雙河場》寫的的確是生活的“原生態”,但這樣一地雞毛、散亂拖沓,看到什么寫什么,只在現實生活的表面上滑行,而且行文又是如此簡陋的“原生態”展示又有什么意義呢?因為這樣的“原生態”展示并不具備文學的意義和審美價值,它不但割裂了現實的內在聯系,也缺乏藝術的轉化和創造,因而只能是一盤散沙,一堆原材料的堆積。實事求是地說,在“在場主義”和“原生態寫作”的旗號下的不少作品,大多還處于這種原材料堆積的“半成品”狀態,它們展示的往往是現實的局部,而不是整體。之所以有上述的缺憾,是由于作家只注意到了“在場”,而忽略了“出場”。
我這里所謂的“出場”,并非要散文家淡化、退出、回避現實生活的“現場”,而是要有一種在具象中進行抽象和思考的能力。即是說,散文作家在面對現實時,首先要做到既貼近現實又要與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和必要的張力,要身在其中,又能出乎其外。即一方面要用感性經驗和細節來表現現實,臨摹現實,解析現實,思考和批判現實,另一方面又要通過夢想、心靈的滲透、審美的燭照和詩性的文字,使現實騰飛起來。其次,真正具有“現實性”的散文雖然貼近和直面現實,卻始終對現實擁有一種大愛,并滲透進心靈的呵護、理想和希望。這正如王兆勝所說:“每個人都有一顆心,問題的關鍵在于:他的‘心燈’能否清澈明亮,能否有古道熱腸,有沒有大的光輝。如果不能,他的人生恐怕就是冰冷和黑暗一片;反之,他就有‘一孤燈而照千年暗’的溫馨與輝煌。”B16 我覺得王兆勝這段話是我們認識和理解散文寫作中的“現實性”的關鍵。也就是說,首先我們要擁有一顆清澈明亮的“心燈”,這樣就不會被無邊的黑暗和冰冷淹沒,反而會在黑暗和冰冷中感受到溫馨甚至輝煌。第三,“現實性”的寫作還要求對現實要有所發現。米蘭?昆德拉說:“發現唯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乃是小說唯一存在的理由。一部小說,若不發現一點在它當時還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說。”B17 我們說,“發現”并不是小說的專利,散文同樣要“發現”,甚至可以說,有沒有發現,是衡量一篇(一部)具有“現實性”的散文是否優秀的一個重要標尺。這種發現在我看來主要有兩個關節點:一是發現被現實掩蓋或被人們忽視了的瑣事、瑣物和生活細節;二是發現現實生活的可能性,即描述出現實后面的可能性以及它的走向,這就是余華所說的“我覺得文學就是現實產生以后,后面又發生什么,這就是文學要表達的現實”B18 。是的,散文作家惟有善于發現,善于寫出“文學要表達的現實”,散文才有可能真正解釋出被日常生活所掩蔽的生活中的真相,揭示出人的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和精神狀態,從而經由審美之途抵達一種大的境界和情懷。也惟其如此,散文才真正擁有了我們所需要的“現實性”。比如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就是一部既“在場”又“出場”的經典性散文。作品真實而細致地寫了園子中各種人和他們卑微的生活及抗爭,寫了園子中各種景物和生活細節,甚至于園子石階上一張坐皺了的報紙、石階下的果皮作者也沒放過,這些都造成了十足的“在場”感。但《我與地壇》的可貴處在于它既是“在場”又是“出場”的:一方面作者認為人類的困境是一種宿命的存在,個體無法知道也沒法反抗這種“宿命”,另一方面又堅信人類靠母愛,靠愛情,靠對生命過程的追求和智慧的感悟,可以“識破”命運的機心,并使人類從困境中解脫出來。史鐵生以對人性的洞察和至囿至慈的寬容,對苦難的現實做出了一種迥異于世俗的理解:他發現了苦難也是財富,虛空即是實在,而生存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選擇,需要承擔責任與義務。他由個人的嚴酷命運上升到對整個人類的生存困境的思考,于是,他的散文便超越了一己的悲歡,具有一種闊大的精神境界和人性內涵。 韓少功的長篇散文《山南水北》寫鄉村的底層生活,也是既“在場”又“出場”、既具體又抽象的杰作。在作品中,韓少功寫了大量的苦難,寫了農民在全球化大潮沖擊下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韓少功的高明之處在于,他不是為了寫苦難而寫苦難,為寫困境而寫困境。韓少功既沒有把鄉村看做天堂,也沒有將鄉村寫成地獄。韓少功熟悉、理解和包容鄉村的一切,因此他筆下的鄉村,既有蟲鳥的鳴叫、跳躍的月光、驚飛的夜鳥,也有大糞的味道、滿身的臭汗、喧囂的人生;既有黑暗中的沉淪與掙扎,又有沉靜的純美;既有狡黠與欺詐,又有同情與溫暖;既有血淋淋的殺戮,又有苦難中簇擁出來的大同情和大憐憫。這些是韓少功筆下真實的鄉村,而他散文中的現實整體性也由此而生。韓少功重返生活的現場,將他的思想探索與他的感官,與大量的生活細節以及充滿聲色、味道、光影的大自然連接起來,于是,他的《山南水北》便由第一現實進入第二現實,直達精神和人心的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