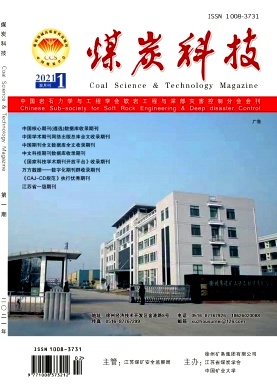自貶與低俗化:魯迅雜文諷刺修辭的詩學分析
佚名
[摘要] 在出于對虛偽的憎恨與輕蔑,魯迅常常表現出對于“美名”的排斥與逆反心理,因而時常有意地向凡俗化的價值取向偏斜,在文章對自我形象進行貶低化與低俗化的處理,并在此基礎上,以反詩意、低俗化的方式對偽道德、偽審美進行嘲弄與破解。
[關鍵詞] 自貶、低俗化、反詩意
虛偽或虛假是魯迅雜文諷刺筆鋒所向的一個主要目標。 他在“女師大風潮”與“三一八”慘案之中的體驗,使他對某些知識界人士的虛偽與惡性形成了深切的感受與情緒性記憶,以至于用雜文與他所說的“正人君子”之流的對抗與纏斗幾乎成為他一生的近乎偏執的行為與思維方式。他說過:“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
一、拒絕“美名”
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對于各種“美名”有著一種近乎過敏的逆反式反應。早在《新的薔薇》一文中他就說過:“有些講‘公理’的,說我的雜感沒有一看的價值。那是一定的。其實,他來看我的雜感,先就自己失了魂了,——假如也有魂。我的話倘會合于講‘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維持會’會員了么?我不也成了他,和其余的一切會員了么?我的話不就等于他們的話了么?許多人和許多話不就等于一個人和一番話了么?”顯然,魯迅已經對這些虛偽的對手不抱任何幻想,他決然地在自己與對方之間劃下了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正是因此,他以一種反諷式的態度寫道:“公理是只有一個的。然而聽說這早被他們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 看上去,這似乎是一種情緒化的應激反應,然而,事實證明,從這以后,對“公理”、“正義”等等各種“美名”的逆反心理幾乎構成了魯迅的一種固定的體驗與思維模式。
甚至到一九二七年,當他看到新月書店為《閑話》一書所做的廣告中有“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的語句,就寫了《辭大義》一文說:“這回所覺得新鮮而惶恐的,是忽而將寶貴的‘大義’硬塞在我手里,給我豎起大旗來,叫我和‘派’的‘主將’去對壘。我早已說過:公理和正義,都被正人君子奪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大義么,我連它是圓柱形的呢還是橢圓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仗’?” 不但如此,他似乎對于所有的好名稱都有一種近乎本能的警惕與不信任。例如“從去年以來一年半之間,凡有對于我們的所謂批評文字中,最使我覺得氣悶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種月刊叫作《長夜》的上面,擺出公正臉孔,說我的作品至少還有十年生命的話。記得前幾年,《狂飆》停刊時,同時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發表,大意說《狂飆》攻擊魯迅,現在書店不愿出版了,安知(!)不是魯迅運動了書店老板,加以迫害?于是接著大大地頌揚北洋軍閥度量之寬宏。我還有些記性,所以在這回的公正臉孔上,仍然隱隱看見刺著那一篇鍛煉文字;一面又想起陳源教授的批評法:先舉一些美點,以顯示其公平,然而接著是許多大罪狀——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狀。將功折罪,歸根結蒂,終于是“學匪”,理應梟首掛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眾。所以我的經驗是:毀或無妨,譽倒可怕,有時候是極其“汲汲乎殆哉”的。更何況這位常燕生先生滿身五色旗氣味,即令真心許我以作品的不滅,在我也好像宣統皇帝忽然龍心大悅,欽許我死后謚為“文忠”一般。于滿肚氣悶中的滑稽之余,仍只好誠惶誠恐,特別脫帽鞠躬,敬謝不敏之至了。
他甚至出這樣的經驗:“如果開首稱我為什么‘學者’‘文學家’的,則下面一定是謾罵。我才明白這等稱號,乃是他們所公設的巧計,是精神的枷鎖,故意將你定為‘與眾不同’,又借此來束縛你的言動,使你于他們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險性的。”
他甚至在給李小峰的信中表露出這樣的心理:“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原不過是教書。然而有些青年大開其歡迎會。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什么‘戰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應該在北京,廈門奮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廣州來了,這就是并非‘戰士’的證據。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時是委員——接著演說,說這是我太謙虛,就我過去的事實看來,確是一個戰斗者,革命者。于是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我的‘戰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誰去推辭?我只好咬著牙關,背了‘戰士’的招牌走進房里去,想到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么?”
二、“俗人”魯迅
正是由于不屑與那些他心目中的虛偽之徒為伍,也由于時常有人對他進行“捧殺”,他便幾乎對所有的好名稱都產生了某種逆反心理。作為對這些偽善與偽崇高的一種反彈與對抗,他時常選擇一種自貶式的態度,對自己、對自己的動機與行為進行一種自我貶低與消解,否認自己行為與動機中具有什么崇高的因素,便成為他的一種常見表現。例如他時常將自己與與“正人君子”們之間的纏斗說成是“開玩笑” 、“尋些小玩意來開開笑口”:
俗語說:“好死不如惡活”,這當然不過是俗人的俗見罷了,可是文人學者之流也何嘗不這樣。所不同的,只是他總有一面辭嚴義正的軍旗,還有一條尤其義正辭嚴的逃路。
的生活的枯燥是最可怕的,于是便不免于有時得罪人,有時則尋些小玩意兒來開開笑口,但這也就是得罪人。得罪人當然要受報,那也只好準備著,因為尋些小玩意兒來開開笑口的是更不能豎起辭嚴義正的軍旗來的。
不僅如此,與各種“美名”相比,魯迅顯得似乎更“樂于”“接受”別人加在他頭上的惡名。人家稱他是“有閑”,“南腔北調”,他就把自己的集子命名為《三閑集》、《南腔北調》。人家說他是“買辦”,他就取“康白度”為筆名。至于以“學匪”自況,稱自己的書房為“綠林書屋”一類則更是常事。這種近乎任性的表現,實際上是對對手的一種絕不妥協的對抗與示威。正是通過這種對“美名”的拒斥與對“惡謚”的收納,魯迅固執而孤傲地表現著對于虛偽的話語霸權的掌握者的不馴服的對壘姿態與蔑視,不僅如此,這種收納與使用是一種主動的帶有優勢心理的玩笑式行為,正是這種玩笑化這使得對方強加的各種罪名與“惡謚”的嚴肅性與攻擊性被瓦解,成為一種笑料。
有意地自我凡俗化與自我貶低是魯迅對抗與消解偽崇高的一種常用方式。例如,魯迅經常強調自己寫作狀況與動機的凡俗性,尤其是著意強調其中的利益因素。
我何嘗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還是釘住書桌,非寫不可的“創作沖動”;雖然明知道這種沖動是純潔,高尚,可貴的,然而其如沒有何。前幾天早晨,被一個朋友怒視了兩眼,倒覺得臉有點熱,心有點酸,頗近乎有什么沖動了,但后來被深秋的寒風一吹拂,臉上的溫度便復原,——沒有創作。至于已經印過的那些,那是被擠出來的。這“擠”字是擠牛乳之“擠”;這“擠牛乳”是專來說明“擠”字的,并非故意將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裝在玻璃瓶里,送進什么“之宮”。倘用現在突然流行起來了的論調,將青年的急于發表未熟的作品稱為“流產”,則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簡直不是胎,是貍貓充太子。所以一寫完,便完事,管他媽的,書賈怎么偷,文士怎么說,都不再來提心吊膽。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愿意看,稱贊好,我終于是歡喜的。后來也集印了,為的是還想賣幾文錢,老實說。
在此,魯迅對自己的寫作著力貶低化,與此相對的,他先將當時某些人所崇奉的崇高價值進行極化處理——“白刃在前,烈火在后,還是釘住書桌,非寫不可”、“藝術之宮”等等,在這個參照系之下,他對自己進行貶低化處理。我們看到,這種貶低首先表現為一種低俗化、瑣碎化與非詩意化描述:“被一個朋友怒視了兩眼”、“臉上的溫度”、“裝在玻璃瓶里”,甚而將自己的寫作貶稱為“打胎”、“貍貓充太子”等等,并且,刻意強調自己對微小的經濟利益的在意與追求——“賣幾文錢”。
可以說,對寫作與文化行為的經濟目標的強調與大肆“鼓吹”是魯迅文章中常見的論調,他正是用這種充分現實與凡俗化的有意的價值偏斜去瓦解知識界中某些人的偽崇高論說。他在《為半農題記《何典》后,作》中,替劉半農為《何典》做的廣告辨護說:“大學教授做一個滑稽的,或者甚而至于夸張的廣告何足為奇?就是做一個滿嘴‘他媽的’的廣告也何足為奇?”因為即使按照某些人的清高論調,“有時也覺得教授最相宜的也還是上講臺。……然而必須有夠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并尖銳地指出“這主張在界大概現在已經有一致贊成之望,去年在什么公理會上一致攻擊兼差的公理維持家,今年也頗有一聲不響地去兼差的了,不過‘大報’上決不會登出來,自己更未必做廣告。”而對于劉半農而言,雖然正業是講授音韻學,“可是北京大學快要關門大吉了;他兼差又沒有。那么,即使我是怎樣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對他印賣書。既要印賣,自然想多銷,既想多銷,自然要做廣告,既做廣告,自然要說好。難道有自己印了書,卻發廣告說這書很無聊,請列位不必看的么?說我的雜感無一讀之價值的廣告,那是西瀅(即陳源)做的。”隨后,魯迅以一種近乎巴赫金所謂的廣場狂歡的叫賣語調戲謔地寫道:“順便在此給自己登一個廣告罷:陳源何以給我登這樣的反廣告的呢,只要一看我的《華蓋集》就明白。主顧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書局發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