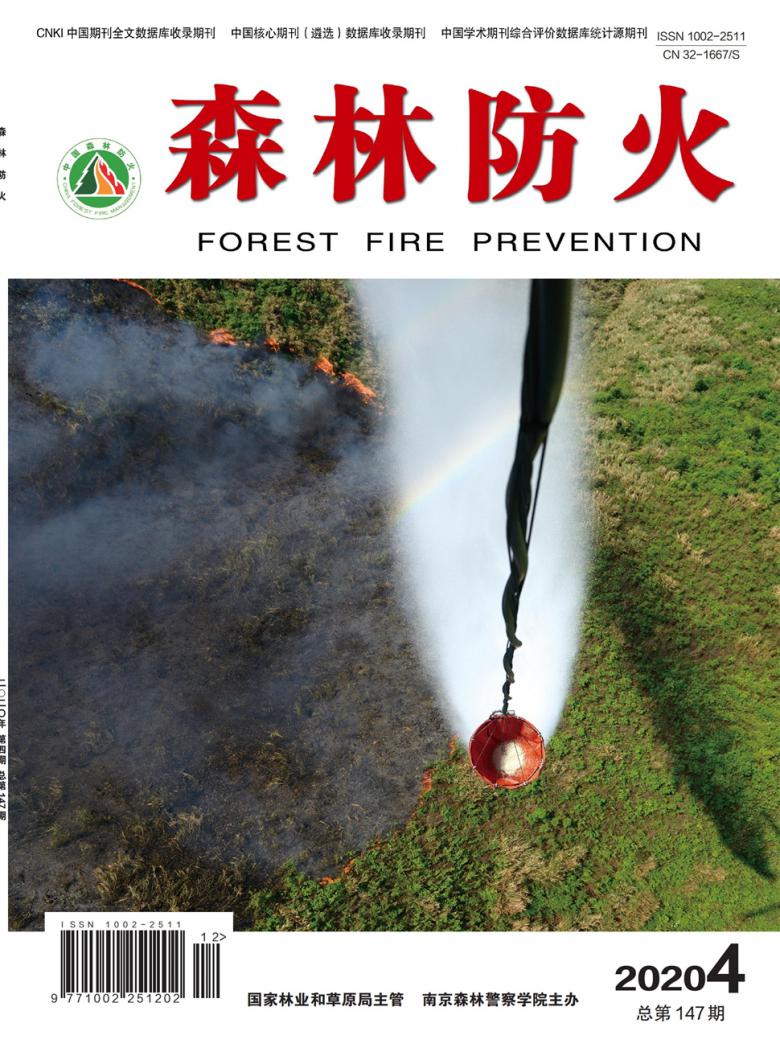中國的職業階層與高等教育機會——關于一種稀缺資源分配狀況的研究
佚名
提要:作為一種稀缺的資源,的高等機會在社會各階層的分布嚴重不均。本報告對90年代以來的多次調查資料的深入表明:高等教育的階層差距在許多方面超過了城鄉差距。在被調查的37所本科院校中,農民與非農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整體差距是5.6倍,其中與黨政干部子女的差距接近18倍;而在全國重點院校中,兩者更分別高達9.2倍和31.7倍。更進一步的在于,導致這一結果的制度性原因并沒有隨著高等教育的爆炸性擴張而消除,相反,大幅度增加的高校收費卻使低收入弱勢階層的子女在面對高等教育時遭遇更大的障礙。
在中國,高等教育機會歷來是一種非常稀缺的資源。獲得這種資源的年輕人將登上一個社會性的“臺階”,進入社會的主流階層或集團。1)正因如此,圍繞這種獨特資源的分配或獲得的狀況,將成為衡量中國高等教育的平等性乃至社會公平問題的重要標準。
本文將從社會階層和流動的角度來考察20世紀8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機會在不同職業階層子女間的分布狀況。之所以選取職業作為衡量標準,主要是考慮到在中國特殊的二元經濟和社會結構、官本位、部門和行業壟斷等制度環境中,不同的職業實際上涵蓋了并外顯為不同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它基本上是政治權力、經濟收入和教育背景(及相應的社會聲望)的聚合點,成為劃分社會階層的重要標尺。就一般情況而言,在迄今為止的當代中國的語境中,提起“干部”、“知識分子”以及“”工人“和”農民“這些主要的職業身份,我們一般總是能夠想到其中的群體或個人所可能擁有或不擁有的一切。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這方面已積累了為數不少的調查資料,問題在于對這些相互隔離和缺少呼應的資料未能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本文將充分利用這些資料,在進行系統解讀的基礎上,綜合出較為明晰的現狀認識文本,并盡可能地展開歸因分析。考慮到操作的簡便以及現有資料的可利用程度,本文所說的職業階層以高等教育機會獲得者的父親的職業為依據。
父親職業與高等教育機會
早在高考制度恢復不久的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即有學者指出,父親職業對子女考入高等學校有相當,干部和職員以及專業技術人員的子女,較工人、農民子女有更多的機會。能夠證明這一結論的早期資料是對在京8所高校1980年入學新生家庭背景的一項抽樣調查結果,其中父親系農民的占20.2%,系工人的占25.0%,系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的分別為15.5%和39.3%.2)另外,胡建華等人1982年6月對南京大學和南京師范學院在校生的調查表明,父親為農民的占在校生總數的22.7%,包括工人在內的“體力勞動者”的子女占40%,而當年江蘇全省農業勞動力(農民)和體力勞動者分別占勞動力總數的80.3%和90%.3)由此可以算出,一個農民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只有非農階層子女的1/14,而腦力勞動者子女的同類機會則是體力勞動者子女的13.6倍。
進入90年代以后,有多位研究者對不同高校學生的家庭背景進行了調查,表1匯集了其中的一些結果。從對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武漢大學,以及廈門大學和鄭州大學的調查中可以發現,農民的子女接近或略微超過25%,而“干部”子女則均超過30%(為30.4%,32.1%和32.4%),顯示出高度的一致性。與此相對,工人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以及軍人和個體私營業主的分布情況在三次調查中顯示出較大差異,其中專業技術人員最高達25.5%,最低為15.6%,相差近10個百分點,而個體私營業主的相差最高達5倍。對于這種差異,由于不了解每項調查的具體條件設定,筆者無法解釋。但總起來看,作為體力勞動者的農民和工人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遠較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為低。
與上述三項調查相比,孟東方和李志對重慶地區8所高校的調查結果則顯示階層差距有所縮小:工人和農民子女的比例都有上升,其中農民子女達39.2%,較前三項調查結果高出14-16個百分點,而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子女的比例則有較大幅度下降。
考慮到重慶高校的層次普遍較低(在現有高校中僅有兩所大學為“重點大學”,但不知是否列入了調查范圍),而前三項調查學校除鄭州大學外都是全國重點院校,可以推斷,在層次較高的“重點大學”,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的子女占更大優勢,工人、農民子女的合計份額不到一半;而在一般的地方性高校中,差距有所縮小,工農子女的比例也超過了50%.
如果引入由筆者委托調查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資料,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中國高校階層差距所呈現的金字塔狀格局。表2列出了這兩所頂端高校90年代本科生的來源,雖然其中反映的只是城鄉差距,但可以進行簡單的置換,即假定學生的父親都是“農民”(實際情形并非如此,因此有高估農民子女比例的傾向),那么其比例在兩校中都很少超過20%,在最低的年份則只有16%左右。這不僅遠遠低于重慶市8所高校的39.2%,也明顯低于武漢大學和廈門大學等的23%-25%.
這一推論為1998年4月實施的一項大規模調查結果所證實。該項受到世界銀行和中國教育部資助的調查涉及不同層次的高校(大專除外)37所、1994和1997級學生近7萬人。從表3所示的結果可知,農民子女的比例隨著院校層次的升高而降低(在第一類院校中的比例低于總體比例近10個百分點);干部、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的子女則逐步升高。調查分析還表明,與1994年級學生相比,在1997級學生中,這種下降和上升的趨勢更加明顯。
接下來讓我們對上述調查數據進行還原,給出階層差距的量化結果。要說明的是,由于缺少與學生“父親”的年齡段(推定為40—60歲)和調查設定的各種職業完全對應的人口基數統計資料,難以對階層差距給出精確的。不過,在對相近的資料加以甄別后進行嘗試還是必要的,盡管由此得出的結論可能與實際情形稍有出入,但有助于對看似漠然的數據賦予為較確定的社會內涵。
在此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從業人員”資料來取代學生父親的職業分布狀況。1980年全國從業人員為42361萬人,其中鄉村31836萬人,城鎮10525萬人。在前者中,除去640萬黨政干部和科教文衛人員,假定余者皆為職業身份上的“農民”。后者包括科教文衛部門1649萬人,假定為“專業技術人員”;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部門527萬人,假定為“黨政干部”。這里不清楚“企事業單位干部”的數量,假定其與黨政機關干部相當,那么廣義的“干部”數量將達到1054萬人。扣除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的人數視為“工人”,總數為7822萬人。這樣,四個主要的職業階層在總從業人員中的比例分別是75.2%、18.5%、2.5%和3.9%.由此可以得出其子女獲得高等教育機會的可能性之比是:1:5:25.1:37.5.也就是說,在1980年,工人、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子女升入前述北京8所高校的機會將分別是農民子女的5倍、25倍和37倍以上。
按照同樣的可以推算出,1990年,農民與另外三個主要職業階層子女進入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的可能性之比分別是1:3:26.8:22.5;1995年進入武漢大學的比例分別是1:3.7:32.7:21.1;進入廈門大學和鄭州大學的比例是:1:2.9:30.3:14.4;1995年進入重慶8所高校的比例則是1:2.3:13.9:6.4.4)
而根據前述對37所高校的系統調查資料推算(結果見表4),在90年代中期(以1995年為基準年度),在除卻了“大專”的高校中,農民子女與工人、干部、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子女進入高等學校的可能性之比為1:2.5:17.8:12.8:9.4,其中在第一層次高校中是1:4:31.7:22.6:17.4.而農民階層與非農階層的整體差距是5.6倍,在第一層次高校中則是9.2倍,其中與黨政干部子女的差距竟分別達到17.9倍和31.7倍。“農”與“非農”之間高等機會的差距要大于城鄉之間上的差距。進而,我們還可以算出,作為體力勞動者的工人和農民子女,與作為腦力勞動者的黨政干部、企業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的子女的機會之差也非常之大:在高校總體中為9.6倍,在全國重點院校中接近15倍。
要交待的是,由于表1所列的各項調查中個體工商業者、私營企業主的子女所占比例相差太大而不具有可比性,因此筆者省略了與其它階層的比較。但對前述37所高校的大規模調查結果應該具有可信性,它顯示,這一新興階層(在總就業人口中的比例1995年為3.4%)的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優勢雖然不如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子女那么明顯,但高于農民和工人的子女,分別為其3.4倍和1.4倍。關于軍人子女的情況,由于不了解軍人(軍官)的具體數量,無法給出較確定的指標,但肯定遠遠高于工農子女,可能接近另外三個主要階層中的一個。
父親職業與學生所在專業
已有的調查表明,父親的職業不僅著子女獲得不同層次的高等教育機會的大小,而且還進一步與其所能夠進入的學科密切相關。考慮到不同專業的學生畢業后有不同的職業選擇、面臨不同的就業難易度(在國家不“包分配”而較多受“市場”調節的條件下尤其如此),并形成經濟和地位的若干差異,這種調查結果所蘊含的意義值得深思。
表5所列劉宏元對武漢大學的調查顯示,在該校的“熱線學科”專業中,農民和工人子女的比例進一步低于其在總體中的比例,而在“基礎學科”專業中情況則相反。與此相對,黨政干部、企事業單位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的子女則更多地進入了“熱線學科”,三者相加在“機”中達59.4%,在容易與“國際接軌”的“國際貿易”和“國際”專業中更高達80%左右,幾乎形成壟斷地位。
這一特點在孟東方和李志對重慶8所高校的調查結論中也較為明顯。二人了父親職業對子女進入“熱門專業”和“冷門專業”5)機會的影響。在被調查的785名“熱門專業”的學生中,黨政干部、企事業單位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的子女合計占47.1%,高出總體比例(33.9%)13.2個百分點;農民子女則只有24.8%,低于總體比例14.4個百分點。而對449名“冷門專業”學生的則發現,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的子女較少,農民子女則占54.8%,高出總體15.6個百分點,其中在農學、農業化學、鑄造三個專業中,竟分別占到72%、73.1%和80%.關于工人子女的情況,盡管在熱門專業中并無明顯優勢,但就讀冷門專業的比例也較低,比總體低9.5個百分點。
父親職業與學生的錄取分數
眾所周知,1978年以后中國的高考制度遵循的是一種看似“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普遍性原則。這似乎讓人們有理由相信:它能夠確保一種形式上的平等,也即取得了相同考分的年輕人進入高等學校的機會均等。但余小波的調查結果則證明了這一推論難以成立。
余對某電力學院2000級學生入學時填寫的“學生情況登記卡”中的錄取分數進行了統計分析,其結果見于表6.它顯示,學生父親的職業不同,其錄取分數也存在著較大差異,農民子女的平均分數要高出干部子女22分,高出工人子女18分。其中工科類高出干部子女26分,財經類高出30分。而在表6-2所列的16個專業中,就農民子女與干部子女相比,只有兩個專業低于后者,其他皆以農民子女為高,其中財務管理高50分,電算高60分。再將其與工人子女相比,4大類專業也全都高于后者,16個專業中只有3個略低于工人子女,而其他皆高于后者,其中有7個專業相差20分以上,2個專業相差40分以上。
工人子女與干部子女分數的差距不像農民子女與其相比那樣明顯,但平均分也高出后者4分,在4大類專業中只有文科類低于干部子女,理科類與之相等,而其他兩大類都高于干部子女。在進一步細化的16個專業中,有11個專業高出干部子女,其中有6個專業高出10分以上,兩個專業高出40—50分以上。
那些經歷過中國的高考制度洗禮的讀者能夠領悟,22分之差意味著不同層次大學之間“門檻”的高低之別,可能是“一流與二流”或者“重點與非重點”的分界線。也就是說,這種差距意味著農民子女本來可能進入比調查學校更高層次的學校。但是他們不僅未能如此,反而在已錄取學校的專業分布中處于劣勢。
通過余小波提供的學生父親職業與入選專業關系的分析可以看出,干部子女入選專業排在前5位的是:經濟學、電氣工程和自動化、計算機科學與技術、信息與通信技術、會計學(表5第三列),均為該校熱門或強勢專業;工人子女入讀專業排在前5位的是:數學與數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熱能動力工程、電氣工程及自動化、自動化,多數為一般專業;而農民子女入選專業排在前5位的是:供用電技術、物、熱能動力工程、建筑環境與設備工程、化學,基本上為冷門專業,特別是面向服務的供用電技術所占比例高達61%.
值得玩味的是,在干部子女排在前五位的專業中,其平均分都低于農民和工人子女,其中“電子信息與通訊技術”專業低于農民子女32分,“計算機科學與技術”低41分。而從其他11個專業中農民子女的平均分來看,都高于熱門專業中干部子女的最低分和次低分,有7個專業高于最高分,其中“財務管理”專業竟高出44分。這表明,從分數上看,農民子女完全有足夠的優勢更多地進入這些“強勢專業”,而干部子女更多的進入熱門專業并不是出于高考成績競爭的結果。它甚至還會讓我們生發出一種必然要生發的聯想:那些考分比已錄取的農家子女低、但卻高于干部子女的農民出身的考生,是否被更多地淘汰了呢?
關于高等階層差距的歸因
關于導致高等教育階層差距的原因,可以從家庭背景和制度因素兩方面加以探討。6)家庭背景的“天然”是直接而深刻的,那些擁有較強勢的職業以及與之相應的較高文化程度和收入的成員,在引導子女朝向“精英”化努力方面無疑更具優勢。但是,家庭背景并非孤立地發揮作用,它必然在特定的教育和社會制度環境中被有意無意地放大或縮小。進而,就的情況而言,高等教育始終是計劃體制的一部分。雖然20世紀90年代之后各高校逐漸擁有了一定的“自主權”,民辦高等教育也在興起,但“計劃”的色彩依然濃厚,政府特別是中央和省級政府在招生計劃的制定和分配上具有初始的或最終決定權。因此,我們的分析就不能不集中于制度的因素,圍繞制度與“家庭職業背景”的互動如何影響著高等教育機會的分配而展開。
1,它是基礎教育階段機會不平等累積的結果
在中國龐大的金字塔型教育體系中,高等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并不是一種自生的孤立現象。它是整個教育體系結構性不平等的一部分,在相當程度上是基礎教育階段機會不平等累積的結果。
眾所周知,城鄉分割的義務教育辦學制度,使的少年兒童——95%以上為“農民”子女——在通向學業成功的競爭中從一開始就處于劣勢。在公共教育經費不足、靠農民自身的力量又無法承受義務教育之重的情況下,農家子女往往在初中甚至小學階段就被淘汰出局,從而無緣參加高等教育機會的競爭。根據筆者的,自1986年頒布《義務教育法》到2000年的15年間,中國大約有1.5億少年兒童沒能完成初中教育,其中的絕大部分為農民子女。而義務教育階段城鄉機會的差距,到了高中階段又進一步擴大。從初中畢業生升入高中(普通高中)的比例來看,城市的升學率從1985年的40%提高到了1999年的55.4%,而同期農村則從22.3%下降到18.6%,兩者間的倍數差從1.8倍擴大到3倍,絕對差則從17.7個百分點擴大到36.8個百分點。7)這就使得80%左右的農村初中畢業生無緣參加高考。一連串的淘汰機制,決定了農民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大大降低。而高中階段城鄉教育質量的差距,又進一步導致農村的學生處于不利地位。
而在城市內部,重點小學、中學與普通小學、中學的劃分和相應的資源分配,也使不同學校的學生所接受的教育在質量上有著很大差別。近十多年來愈演愈烈的“擇校風”實質上表現為各社會階層圍繞著不公正分配后的教育資源的爭奪。但經驗事實告訴我們,真正有實力“擇校”的,可能主要是政府官員、高中級專業技術人員以及界的中上層,就一般職工和市民而言,除非有相當的“關系”背景和經濟實力,否則在麻煩的戶口遷移手續和高額的“贊助費”面前,可能也難以如愿。從結果來看,在那些獲得了更多資源的重點學校就讀的學生,多數是強勢階層或上層、上中層階層人員的子女。方長春近年對馬鞍山市的抽樣調查顯示,在該市的初中畢業生中,出身于上層家庭者有69.1%進入了該市“最好的高中”,而在中上層、中層和中下層分別為20.2%、12.0%和14.7%,下層則只有5.1%.方的還證實,學生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其所就讀的小學和初中學校也越好。8)這無疑為這些階層的子女在高等教育機會的競爭中占居優勢打下了基礎。
2,傾斜的招生名額與錄取分數線:高等教育機會初次分配的不平等
教育資源分配的制度性不平等不僅表現在大學之前的基礎教育階段,在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分配中也非常突出。概而言之,由教育主管部門掌控的全國高校在各地區招生名額的分配,以及與之相關的錄取分數線的劃分,打破了高考制度實行“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神話,導致了農民子女在“被選拔”的過程中處于劣勢,而客觀上有利于居于城市的各社會階層的子女。
作為計劃經濟的產物和密切涉及政策制定者的直接利益的結果,我們知道,教育主管部門在以地區為單位的招生名額分配上,一貫采取傾斜的政策,最突出的表現是在全國范圍內向北京和上海傾斜,在省區范圍內則向省會城市傾斜。出自2000年2月14日《中國青年報》的一篇報道指責說,(1999年?)“河南、山東人口均接近1億,但招生總量僅有8萬人左右。而北京人口僅1000多萬,招生總量卻達2.5萬之多。”這種傾斜導致各地不同的“錄取比例”,也即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不同。以1998年的情況為例,當年全國普通高校的平均錄取率為36.3%,最高的上海市為60.3%,而低于30%的有河南、安徽等8個省區,最低的甘肅省只有21.9%,最高和最低之差是3∶1.9)1999年北京市的錄取比例高達72.6%,其中理科考生更達78.9%,與此同時,仍有多個省區不到30%.當年北京市理科最低錄取分數線僅為327分,它意味著,在這座擁有數不清的特權的城市,考生只要獲得平均相當于百分制的43.6分就可以上大學,各門功課平均不及格也可以上本科。10)
招生名額分配的傾斜在那些居于金字塔頂端的高校中更加顯著。表7列出了1993年之前清華大學在部分省市的招生人數,它顯示,蘇、皖、鄂、川4省合計得到的名額始終低于首都北京,在高考制度恢復之初的幾年間甚至不足其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由此可以推算,在1990年,主要由強勢階層子女構成的北京市的考生考取這所精英學校的概率,要比主要由農民子女構成的4省考生高出14.5倍。11)
名額分配的嚴重失衡自然導致實際錄取分數存在著令人驚詫的差異。“同一張試卷,同一次高考,不同省市的錄取線動輒相差100余分。”“在同一所高校,各地同
學的高考分數差可超過200分“,”在北京能上清華的分數,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點大學;在北京能上重點的,在一些省則無學可上。“北京、上海比一般省區低,省會城市比當地落后地區低。(表8)無怪乎有人公開指斥:”這是社會主流階層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其子女搞普遍特權。“12)
要指出的是,錄取分數線的傾斜雖然主要表現在省、市、自治區之間,乃至一省內部的地區之間,但就全國來看,由于處于不利地位的省區往往是農業人口占絕對多數,因此最終也就意味著這種分數線更多地對農民子女不利,他(她)們將在無形中被更多地淘汰,而機會更多地流向了其他社會階層的子女。
3,“保送生”與“機動指標”:“腐敗”參與的再分配
如果說招生名額的初次分配已經明顯地有利于居住在首都、省會等大中城市——高層的權力、文化和經濟精英的居住地——的社會成員的子女,那么錄取過程中的再分配,則進一步偏向于能夠對錄取過程直接或間接施加影響的權勢階層的子女,而背離包括無關系背景的工人在內的低社會階層子女。干擾再分配之公正性的主要有以下兩種形式。
第一為錄取過程中的“靈活性”。眾所周知,雖然各高校都會根據志愿填報情況劃分明確的錄取線,但“線上生”的人數與最終錄取數總是保持一定的差距,通常為1:1.2左右,也即大約有20%的“線上生”會被淘汰。一般說來,各高校會遵循按分數“從高到低”錄取的原則,但權力和接近權力的“關系”總是有施加影響的空間。對于有特殊背景的考生,超過當該學校的錄取線,甚至只要達到所在省、市、區的“控制線”即會被保證錄取。這種優惠措施的集中性獲益者有兩類,一是各高校教職工的子女,他(她)們報考父母所在的學校總是會得到這種“職業特權”或“行業性福利”;二是那些掌握各種資源分配的權力、對高校乃至高校負責人個人的有重要影響的個人,以及一些“協作單位”的負責人。對后一類社會成員的關照近年來已經演化成制度性保障,名為“機動指標”。頗負名望的上海大學2001年夏天不慎泄漏的這方面的“招生黑幕”不過是冰山之一角。有報道指出,“機動指標”的數量在有些高校可能在三位數,占招生總數的比例最高時曾達到8%.13)而各種力量角逐的結果,被擋在高校大門之外的20%的考生,自然主要是那些遠離權力的社會成員的子女,甚至會包括一些高分考生。
第二種表現形式是已經受到社會輿論廣泛指斥的“保送生”和“特招生”。自1984年開始實行的“保送生制度”,據說在初期較為規范,后來則“變味了”:被保送的“三好學生”、“優秀學生干部”大多是干部和教師子弟。2000年夏天由多家媒體披露的湖南省隆回一中的“保送生舞弊”案證明了這種指斥的正確。在該校送出的14名“保送生”中,13名系作假,其中兩人分別是該校正副校長的兒子,另外11名均為縣及縣屬單位的干部子弟。“14)而關于因為某方面的”專長“可以降分錄取的特招生中的腐敗,也早已是一種公開的秘密,最近則由于西安市圍繞”特長生“的大面積舞弊事件的敗露而成為輿論的焦點。所有這些公開的和沒有公開的舞弊,無疑使強勢社會階層的子女更多地獲得了高等教育機會,拉大了高等教育的階層差距。
結語
居于較高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階層成員的子女具有更多的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這幾乎是世界各國的普遍現象,在有些國家則形成幾近壟斷的現象。15)由于缺少連貫的和高度整合的調查統計資料,我們難以將中國的狀況與一些具有可比性的國家進行具體比較,以衡量其高等教育機會不平等程度的國際水平。但本文的考察已充分說明,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會分配和獲得確實存在著系統的和結構性的嚴重不平等狀況,各主要社會階層對這種稀缺資源占有的不平等程度,在許多層面可能高于經濟收入的差距。
造成這種不平等的原因固然有來自家庭的理應被接受的“天然”影響,但是與政策制定者有著切身利害關系的制度性安排,以及在制度的執行過程中各種強勢社會成員所施加的干擾顯然也非常重要。盡管這種制度性安排和腐敗現象近年來被不斷地批判著,并且嚴重損害了教育當局和高等學校的信譽,但是由于它涉及了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們的直接利益,尚沒有被更加平等和公正的制度所取代的跡象。這樣,盡管中國的高等教育基于“產業化”或延緩“就業壓力”的現實需求而大大增加了絕對的機會數量,并接近了“大眾化”的門檻,但這可能只是一種假象:大眾化的高等教育所接納的真正的“大眾”(工農子女)多數仍然處于邊緣,而位于金字塔頂端的“一流”或“重點”大學——這才真正是孵化新“精英”的巢穴——中的“大眾”依然主要限定于強勢階層。如此,我們就難以斷言中國的高等教育在完成了它的爆炸性數量擴張的同時已經實現了質的結構性轉變,因為它并沒有實質性地增加“平等”和“公正”的內涵。
注釋
(1)北京清華大學畢業生的去向突出地說明了這一點:在該校1982-1986年畢業的4615名學生中,分配到中央國家機關和中央屬企事業單位的為2675人,高達58%.見清華大學志編輯委員會編《清華大學志/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227頁。
(2)見施云華、諸子平:《我國“機會均等”建設芻議》,《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科版)》1993年第1期,原資料出處不明。
(3)轉引自魯潔:《教育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474頁。
(4)要說明的是,由于每項調查涉及的學校不同,我們難以拿1990年代的調查結果同1980年的情況進行比較,并由此斷定階層差距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
(5)劃分標準是:根據各校負責人對本校專業“冷熱”狀況的評估,將師范院校的心、機,醫學院校的臨床醫學,農業院校的園林、機制,外語院校的、日語,以及其它院校的外貿、電腦軟件、外貿英語、管理、視為“熱門專業”,農業院校的農學、農業化學,師范院校的生物、中文,理工科院校的鋼鐵冶金、鑄造以及其它院校的文秘、數學、物理視為“冷門專業”。見孟東方、李志論文:《學生父親職業與高等學校專業選擇關系的》,《青年研究》1996年第11期。
(6)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個人努力的重要性。但是從社會階層的角度而言,難以證明哪一個階層的子女更具有努力的意愿并最終獲得成功,也即無法檢驗“自致性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著一個人獲得高等教育機會。
(7)關于密切關聯到農民—非農民階層教育差距的城鄉教育差距的考察,見張玉林《城鄉教育差距》,《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6期。
(8)方長春:《階層差異與教育獲得——一項關于教育分流的研究》,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4,16-23頁。當然,類似現象并非20世紀末的新鮮事物,在1960年代初期的廣州市,能夠有70-90%的學生升入大學的當地重點中學中,只有11%是工農子弟,48%為1949年前入黨的干部子弟,余者則為原居住區居民(1949年之前的富裕階層)的子女。見劉精明《教育制度與教育獲得的代際影響》,載李強等著:《生命歷程——重大社會事件與中國人的生命軌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56頁,原資料出處不明。
(9)《中國教育報》2001.12.5.
(10)《中國青年報》2000.2.14.
(11)當年4省高中畢業生(視為參加高考人數)為51萬人,而北京市為4萬人,相關數據出自《中國統計年鑒1991》,716頁。
(12)《中國青年報》2000.2.24.
(13)2001年8月17日《南方周末》2001.8.17;《中國青年報》。2000.6.14.
(14)關于保送生制度的,見《中國青年報》2000年8月17日、8月21、22日的連續報道。
(15)參照鐘宇平、陸根書:《西方學者論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對公平的影響》,《西安大學學報》(社科版)第21卷第1期,200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