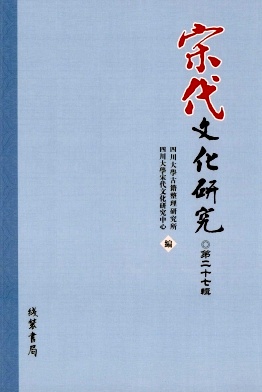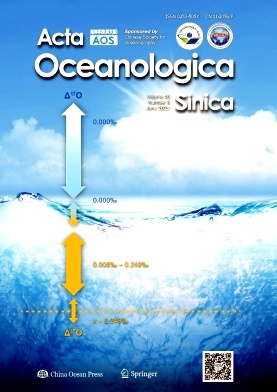譚其驤的歷史地理學研究
陳其泰
歷史地理學作為一門科學,是20世紀以來,特《20世紀中國歷史考證學研究》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逐步創立和完善的。20世紀30年代由顧頡剛、譚其驤等發起成立“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英文名為:了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為日后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礎。歷史地理學的對象、任務、方法、范圍漸趨明朗,與歷史學、地理學的區別與聯系也基本達成共識,并出版了一些高質量的論著,完成了由傳統輿地學(沿革地理)向現代科學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的轉變,并且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等研究歷史地理的中心。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譚其驤、史念海、侯仁之、陳橋驛等著名學者起了關鍵作用。譚其驤不僅在歷史地理考證方面有重要的建樹,而且培養了大批人才,被公認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的主要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
譚其驤(1911—1992)字季龍,浙江嘉興人。1930年畢業于上海暨南大學,1932年在燕京大學研究生院畢業后,任北平圖書館館員,兼輔仁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教師。后任浙江大學教授,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他主編有《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等,論文輯有《長水集》(上下冊)及《長水集續編》等。楊向奎先生這樣概括譚其驤的學術成就:“譚先生自三十年代開始即從事歷史地理學的教學與研究,對歷代疆域和政區變遷有深刻研究,并自有一套理論體系,他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即為其多年研究的結晶。五十年代開始又從事歷代水系變遷的研究,對黃河、運河、海河以及云夢、鄱陽的研究成果,均超越前人。他應當是繼承乾嘉以來沿革地理學的大宗,并將其現代化的人。”①
(一)秦漢疆域行政區研究
譚其驤早年從事典型的沿革地理考證研究。1931年,他選了顧頡剛先生講授的“尚書研究”一課。顧頡剛在講義中認為《尚書·堯典》的寫作年代在西漢武帝以后,證據是《堯典》里說虞舜時“肇十有二州”,而先秦著作稱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州,沒有十二分制的。到漢武帝時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所以《堯典》的十二州應是襲自漢武帝時的制度。譚其驤不同意這一看法,認為十二州為東漢之制而非西漢之制。顧頡剛便鼓勵他寫出來,譚其驤又查了《漢書》、《后漢書》、《晉書》等有關篇章,于是就有了師生間往來書信,結果如顧頡剛所說:“現在經過這樣的辯論之后,不僅漢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連帶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對于這些時期中的分州制度,二千年來的學者再沒有像我們這樣的清楚的了!”②在這次討論的基礎上,顧頡剛寫成了著名的《兩漢州制考》,而譚其驤則激發了研究沿革地理的興趣和信心。
譚其驤發表于1933年的《漢百三郡國建置之始考》就是考證秦漢郡縣國建置的。郡縣制形成于戰國時代,秦統一六國后,采納丞相李斯的建議,廢除分封制,在全國推行郡縣制。《史記·秦本紀》和《秦始皇本紀》都提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分天下為36郡,卻沒有列舉36郡的具體名稱。長期以來史學界存在多種不同的說法: (1) 《漢書·地理志》在各郡國下注稱“秦置”、“秦郡”或“故秦某郡”,共有36郡,包括秦始皇三十三年所置的南海、桂林、象三郡,也就是說36郡是秦一代總郡數,漢興以后才有所增益。(2)《晉書·地理志》則說秦始皇平南越,增置了閩中、南海、桂林、象四郡,合計40郡。(3)清代考據學興起后,對秦郡問題作過考證的學者不下數十家,其中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等贊同《漢志》之說,楊守敬《嬴秦郡縣圖》則信從《晉志》的說法。大多數人認為《漢志》、《晉志》均有脫漏,36郡是秦初并天下時的郡數,后來陸續又增加了一些,但對于增加的數目及具體郡名,各家說法不一。姚鼐《復談孝廉書》認為,除了《漢志》中提到的36郡外,南海等三郡不屬于秦郡,而補充了河內、濟北、鄣三郡,且河內、濟北是項羽時設立的,不是秦郡。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認為,南海、桂林、象、九原四郡不應在初并天下時的36郡之內,而以黔中、廣陽、東海、楚郡補足,加上九原等四郡,共計有41郡。王國維《秦郡考》則以黔中、閩中、陶、河間補足36郡,再加上廣陽、膠東、膠西、濟北、博陽、城陽、南海、桂林、象、九原、陳、東海12郡,共計48郡。他按照五行相勝說的理論,說秦以水德取天下,數以六為紀。因而秦始皇二十六年設置36郡,后來陸續擴大到42郡、48郡,均為六的倍數,都是秦制規定的結果。
-------------------------
① 楊向奎:《河山集·序》,見《河山集》(三),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② 譚其驤:《討論兩漢州制致顧頡剛先生書》,見《長水集》,38~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譚其驤的《漢百三郡國建置之始考》,同意全祖望之說,只是加了閩中郡,為42郡。后來他又重新思考,于1948年又寫了《秦郡新考》,從《史記》、《漢書》、《華陽國志》、《水經注》、《晉書》等可信史料中發掘論據,核實除內史外,秦郡數目為46,加上另外可能存在的二郡,總數有48。除了《漢志》中所言32郡外,補黔中、廣陽、閩中、陳郡為36郡,這就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時設立的。秦始皇三十三年南平百越,北伐匈奴,又設立了南海、桂林、象和九原四郡,東海、常山、濟北、膠東、河內、衡山六郡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后析內郡所置。王國維說有陶、河間、膠西、博陽、城陽,而譚其驤說有常山、河內、衡山、鄣、廬江,兩說不同。譚其驤最后寫道:“夫考古之事,竭其能事耳。生千百年之后,上究千百年前之典章經制,史文闕略,焉得必無遺漏?多聞闕疑,庶幾其可;若必欲斷言為三十六或四十八,徒見其牴牾鑿枘,是亦不可以已乎?”①1944年,他還寫了《秦郡界址考》,對長期被人們忽略的秦郡界址作了詳密的考證,糾正了許多源于《通典》,且為楊守敬《歷代輿地圖》所沿襲的錯誤,并將46郡的轄境、治所列了表,甚便讀者。
----------------------------
① 譚其驤:《秦郡新考》,見《長水集》,10~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但最新考古發現對秦郡數目的確定有補充作用,2002年湖南省龍山縣里耶戰國古城一號井出土了大批文物,其中有36 000余枚簡牘,時間在秦始皇二十五年至秦二世二年之間。簡文出現了“洞庭郡”、“蒼梧郡”,這兩郡史籍未載。秦郡設置多以區域命名.較少有以城邑名者,“洞庭郡”合起成例,說明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郡的設置較歷史記載要廣泛得多.
在此前后,譚其驤寫于1934年的《新莽職方考》,以《漢書》、《后漢書》紀傳及《水經注》為主,旁及漢魏雜著,博稽先儒考證,加上自己的見解而寫成的一篇文章,將西漢末年王莽時期郡縣易名情況一一考證清楚,并附考了王莽時期的郡縣官制、王莽制采偽古書,又總結了王莽改漢郡縣名稱的通例。“譚其驤此文,填補了這一時期政區地理的空白,不僅比較完整地復原出新莽政權的政區建置,還總結出王莽設置政區和命名地名的規律。”①當時王伯祥讀后,盛贊此文“例嚴體精,深造自得”,“附考三則,尤征覃思”,立即補人他主編的《廿五史補編》第二冊中。
————————
①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傳》,載《史學理論研究》,1996(1)。
(二)黃河變遷史研究
在我國諸多河流中,黃河是僅次于長江的第二大河,也是歷史上變遷最頻繁、水患最嚴重的一條河流。司馬遷《史記·河渠書》后,歷代正史河渠志均以記述黃河變遷為主。治理黃河成了歷代王朝的頭等大事,自從《漢書·溝洫志》載賈讓“治河三策”以來,東漢的王景、明代的潘季馴、清代的靳輔等,都是治理黃河的著名人物,但河患不僅沒有減輕,反而愈演愈烈。原因何在?清代學者胡渭的《禹貢錐指》,對歷代黃河變遷作了總結性的研究。20世紀50年代岑仲勉先生著有《黃河變遷史》,所收資料十分豐富,詳細論述了歷代黃河經流的大勢、河患和治河方略,糾正了前人有關黃河研究中的一些錯誤,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很有參考價值,但在關鍵問題上依然沒有突破。
關于譚其驤黃河變遷史研究的緣起,他在《長水集自序》中做過這樣的敘述:“五十年代以前我講中國歷史地理這門課時,每次講到歷代黃河的變遷,除要講到歷史上歷次重要決溢改道外,一般還要把歷史時期分成幾個段落,指出各個段落的不同情況,哪幾個段決溢頻仍,不斷改道,哪幾段相對地平靜無事。但我一直講不清楚何以不同時期會出現迥不相同的情況。過去治黃河史的學者,慣于把各個時期黃河災害輕重的原因,歸之于時世的治亂和防洪工程的成敗。我覺得歸之于時世治亂則與史實不符;實際上亂世黃河不見得多災,治世往往反而多徙;歸之于工程成敗則于事理不可通,總不能說數千年來的治河技術一直在退步,賈魯、潘季馴、靳輔等人主持的河工反而不及大禹和王景的工程有效。直到六十年代初我認識到黃河的決徙雖在下游,病原則在于中游黃土高原的嚴重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輕重與植被的好壞密切相關,而當地人民的土地利用方式則是植被好壞的決定因素。我抓住這一關鍵因素的歷史演變認真做了一番探索,這才基本上找出了各個歷史時期河患輕重不同的根本原因,寫成了《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長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我自以為這才是一篇夠得上稱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論文,文章的結論對當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有一定參考價值。”①.
歷來的研究者,都把東漢以后黃河的長期安流局面歸功于王景治河有方。譚其驤的《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從歷史上論證黃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決定性因素》,則否定了這一傳統說法。他精辟地論證了黃河中游地區農牧業的交替發展、植被狀況與下游河道變遷的密切關系。文章用具體的歷史事實,闡明了黃河變為害河是近一千年來的事。他把唐以前即前期黃河決溢改道的具體情況分作三期:第一期,從有歷史記載的殷商時代起,到秦以前,在這一千幾百年的長時期內,黃河決溢改道的記載很少,主要是因那時森林、草原、支津、湖泊還很多,特別是戰國以前,山陜峽谷流域和涇渭北洛上游,基本上都是農牧區,農業經濟比重較小,因此黃河下游決徙少。他說:“那時山陜峽谷流域和涇渭北洛上游二區還處于以畜牧射獵為主要生產活動方式的時代,所以原始植被還未經大量破壞,水土流失還很輕微。”第二期,秦漢時期,這二區的土地利用情況發生了變化,封建政權不斷移民實邊,進行墾荒,黃河中游從畜牧射獵為主變成以農耕為主,戶口數字大大增加,盲目亂墾濫伐,沒有采取任何水土保持措施,結果必然給下游帶來無窮的禍患。“西漢一代,尤其是武帝以后,黃河下游的決徙之患越鬧越兇,正好與這一帶的墾田迅速開辟,人口迅速增加相對應;也就是說,這一帶的變牧為農,其代價是下游數以千萬計的人民,遭受了百數十年之久的嚴重的水災。”王莽時邊釁重開,內地也爆發了農民起義,所以東漢建立后內徙邊郡,漢族人口減少,少數民族大批遷入,兩者的比例發生了變化,“以農為本的漢族人口的急劇衰退和以畜牧為生的羌胡人口的迅速滋長,反映在土地利用上,當然是耕地的相應減縮,牧場的相應擴展。黃河中游土地利用情況的這一改變,結果就使下游的洪水量和泥沙量也相應地大為減少,我以為這就是東漢一代黃河之所以能夠安流無事的真正原因所在”。
-------------------------------------
① 譚其驤:《長水集·自序》,9~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第三期,東漢王景治理以后,黃河出現了長期安流的局面,與黃河中游邊區和河套地區變農為牧密切相關。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政治混亂,戰爭頻繁的階段,但卻是黃河最平靜的時代,原因就在于東漢以后,本區農業人口大量內徙,而以畜牧為主的少數民族大批遷入,加之戰亂,人口驟減,原已開墾的農田被廢棄,牧場擴大,水土流失減少。直到中唐以后,黃河中游的川原荒坡又被墾辟殆盡,水土流失愈來愈嚴重,這也就是使得近一千年來黃河下游河床越填越高,決徙之禍越鬧越兇的癥結所在。最后,譚其驤對治理黃河提出了具體措施:“1.山區園林化。封山育林,同時利用荒坡、荒溝、荒地,大量植樹種草。這樣做不僅增加了林、牧業收入,并且對蓄水保土,調節氣候,改良土壤都發生良好作用。2.溝壑川臺化。在溝壑中打壩淤地,制止溝蝕,變荒溝為良田。這樣做既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又為逐步停耕坡地,把耕地從山坡上轉移到溝川準備了條件。3.坡地梯田化。用培地埂的辦法,起高墊低,把坡地修成一臺臺的梯田。4.耕地水利化。打井,挖泉,開渠,修水庫,天上水、地面水、地下水一齊抓,節節蓄水,層層灌溉。”一句話,就是改進農業生產結構,從單純的農業經濟逐步向農、林、牧綜合經營發展。①驗之于今日,這些建議也是切實可行的。他說:“解放以來黃河中游盲目開發的嚴重后果已從實際上證明了這一論點的正確性,我在這篇文章中所揭示的事實,正被人們作為歷史的經驗在吸取,相信搞好中游的水土保持,終于將成為公認的消弭黃河水害的根本措施。”②現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提倡退耕還林,植樹種草,積極調整產業結構,目的就是為了防止水土流失,切實加強和改善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充分驗證了他的預見性。
-------------------------
① 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見《長水集》,1~3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② 譚其驤:《譚其驤自述》,見高增德、丁東:《世紀學人自述》,111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
此后,譚其驤又主編了《黃河史論叢》,收輯了一些論述歷史時期黃河變遷、若干重大洪水、黃河改道及歷代治河的重要文章,為現代的黃河研究與整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對黃河的認識也在不斷提高,主張全面規劃治理黃河時,既要抓水土保持這個根本,又要重視工程防治,兩者不可偏廢,要真正摸清歷史時期黃河變遷的原因及其規律,總結人們在治理黃河過程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他列舉了需要注意的二個問題:“第一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第二是全面地看問題,要用辯證研究方法,而不是片面地、形而上學地看問題。”①對于漢代以前黃河下游的變遷,他也作了詳細的考證,寫有《〈山經〉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和《西漢以前的黃河下游河道》兩文,從《山海經》人手,根據《北山經.北次三經》所載人河諸水,用《漢書·地理志》、《水經》及《水經注》所載材料加以印證,從而鉤稽出一條從未被人所知的上古黃河故道,有力地證明西漢以前黃河故道決非“禹河”一條,進而又論證西漢以前黃河下游故道既非清人焦循所說的沒有改道,也不像東漢班固、北魏酈道元、清人閻若璩、胡渭及近人岑仲勉所說的只有周定王五年這一次改道。他認為,在春秋戰國時代,黃河下游以走《漢志》所載河道為常,也曾不止一次走《禹貢》、《山經》所述河道。約在戰國中期,齊、趙、魏各在當時的河道,即《漢志》河的東西兩岸修筑了綿延數百里的堤防,此后《禹貢》、《山經》河即斷流,專走《漢志》河,一直沿襲到漢代。在論述漢以前黃河下游河道情況時,他發現一引人注意的現象,即“從新石器時代經歷商周直到春秋戰國時代,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著一片極為寬廣的空白地區。在這一大片土地上,沒有發現過這些時期的文化遺址,也沒有任何見于可信的歷史記載的城邑聚落”。原因何在?譚其驤經過考察后認為,春秋以前黃河經常泛濫改道,人們只能在高地居住,平原任其荒蕪,當然就不可能出現聚落,更不會形成城邑。戰國以后,黃河下游開始構筑堤防,這“是河北平原古代勞動人民在黃河兩岸修筑堤防的結果”。而黃河在這里決溢改道,對人民生活影響很小,因此為一般古代文獻記載所不及。②譚其驤對這篇文章非常滿意,說:“古今學者講到漢以前古黃河全都知道有一條見于《禹貢》的河道,誰也不知道還有其它記載。如今被我從《山經》中找出這么一條經流鑿鑿可考,遠比《禹貢》河水詳確得多的大河道來,怎不令人得意!”③
--------------------------
① 譚其驤:《黃河史論叢·前言》,1~2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
② 譚其驤:《〈山經〉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見《長水集》,39~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③ 譚其驤:《長水集·自序》,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三)移民史研究
譚其驤在暨南大學求學時曾師從潘光旦,對移民問題、血統與人口素質的關系、漢族與少數民族的交流與同化、江南的宗族、一些民族和地方人口的來源等問題有濃厚的興趣,畢業論文即以《中國移民史要》為題,略述自上古到清代國境內各族的遷移大勢,并得到老師潘光旦的激賞。1930年,他進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后,仍然對移民史有興趣,不過“覺得要研究移民史,應該一個地區一個地區逐步搞,或一個時代一個時代逐步搞,而不急于搞全面的史略、史要或簡史,搞清楚當前各地區人民的來歷,才是研究移民史的首要課題”。于是,譚其驤決定主要根據地方志中的材料,按今省區一省一省地搞,他先從材料比較好找的湖南做起,完成了《中國內地移民史——湖南篇》,后又以《湖南人由來考》為題發表。這篇文章分上篇:歷史上之陳跡——當時記載之一鱗半爪,敘述了從上古秦漢、六朝時期湖南境內民族的由來,下篇“今日湖南人之由來——后世追述之整理與統計”,以湖南諸府、州、縣方志中的五種,即道光《寶慶府志》、光緒《邵陽縣鄉土志》、光緒《武岡州鄉土志》、光緒《湘陰縣圖志》和光緒《靖州鄉土志》為根據,說明了出于漢族血統的湖南人的由來,最后總結論是:“一曰:湖南人來自天下,江、浙、皖、閩、贛東方之人居其什九;江西一省又居東方之什九;而廬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什九。二曰:江西人之來移湖南也,大都以稼穡耕墾;江蘇、安徽、河南、山東人之來湖南也,大都以為官作宦,以經商服賈。而長沙都會之地,五方雜處,尤多江、浙、皖長江下流之人。三曰: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湖南北部,而湖南南北部之分,以湘陰、平江作之界。四曰:湖南人來自歷古,五代、兩宋、元、明居其什九;元、明又居此諸代之什九;而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間,又居元、明之什九。五曰:五代以前,湖南人多來自北方;五代以后,湖南人多來自東方。南宋以前,移民之祖籍單純,幾盡是江西人;南宋以后,移民之祖籍漸臻繁雜,始多蘇、豫、閩、皖之人。清代以前,江西移民與其他外省相較,其他外省相差懸如;至清代而湖北、福建之人,有崛起而與江西并駕齊驅之勢。清代以前,本省移民與外省移民相較,本省移民地位甚低;至清代而本省移民之地位,有崛起而超越于外省移民之上之勢。”①在撰寫此文搜集材料的過程中,譚其驤發現近代的湖南“漢人”中又有相當一部分出于少數民族血統,如向氏、舒氏、田氏、彭氏、覃氏、符氏、扶氏、蘇氏、楊氏等大姓,實際上都是出自漢代之后的當地少數民族,而不是他們精心編撰的漢族世系。因此他寫了《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一文,認為“今日湖南全省人口之中,其可確保為純粹漢族者,恐絕無僅有矣。世有感于優勝劣敗之說,以為蠻族日就于消滅,今日南方人為純粹漢族者,讀此文其可以知其謬乎!且清季以來,湖南人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竊以為蠻族血統之活力之加入,實有以致之;然則蠻漢之不同,不過因其開化有先后之別耳,在種族本質上固無優劣之可言也”②。這篇論文充分肯定少數民族血統與漢族人口的結合對漢族人才輩出的作用,很明顯受到了潘光旦優生理論的影響。
其后譚其驤的主要研究方向雖然轉向了沿革地理,但對一地區人口的來歷仍然很感興趣,所以1936年到廣州,即有《粵東初民考》之作。他經過考證后,認為“有史以來最先定居于粵東境內者,實為今日僻處于海南島之黎族,漢唐時稱為‘里’或‘俚’者是也”。在研究過程中,他首次注意到南朝高涼馮寶之妻、黎族的冼夫人的巨大貢獻,認為“冼氏為俚族第一偉人,佐其夫及子若孫三代,歷事梁、陳、隋三朝,先后討平李遷仕、歐陽紇、王仲宣諸亂,梁、陳易代之際,皆能保境安民,一方為之宴然”③。以后他一直想著文表彰這位杰出的黎族婦女,但都未能如愿,直到1988年才寫成《自漢至唐海南島歷史政治地理——附論梁隋間高涼冼夫人功業及隋唐高涼馮氏地方勢力》一文,詳細闡述了漢唐之際海南島的歷史。
----------------------------
① 譚其驤:《湖南人由來考》,見《長水集》,349~35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② 譚其驤:《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見《長水集》,3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③ 譚其驤:《粵東初民考》,見《長水集》,258、2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940年,譚其驤到遵義,發現從唐末至明代聚居在遵義一帶達800多年的楊保民族已經湮沒無聞,連當地耆宿也不知楊保為何物。他從地方史志、雜書中鉤稽史料,證以當地見聞,寫了《播州楊保考》,對楊保的族源、遷徙、占據播州的經過、與其他民族的關系、消亡過程、后裔分布等都作了考證。主要論證了兩點:(1)宋濂的《楊氏家傳》以播州楊氏族譜為本,說楊保首領楊氏的始祖楊端“其先太原人”,唐末人播據有其地,五傳至北宋時楊昭,無子,以同族宋初名將楊業曾孫持節廣西,與昭通譜的楊文廣之子貴遷為嗣,“自是守播者皆業之子孫也”,這是楊保漢化后的依附虛構之辭,不可據為信史。(2)播州土司楊保實是唐末從瀘(治今瀘州市)、敘(治今宜賓市)二州的邊徼羈縻州地區遷來播州的少數民族中的酋豪,即為羅族(今稱彝族)的一支,后裔漸次漢化,遂依托為中原名門之后,著于譜牒。驗之于出土文物,也是相合的。70年代出土的《楊文神道碑》記載楊氏先世“漢以來,聚族會稽,至鼻祖端,始入□□□□……”①楊文是楊端的十五世孫,卒于南宋末咸淳元年(1265年),早于宋濂《楊氏家傳》百有余年。從碑文中可知宋時楊氏家族還只說先世出自會稽,沒有會稽之前籍隸太原之說,由此可見,《家傳》中“其先太原人”以及楊貴遷系楊業之后的說法,顯然是宋末明初之間編造出來的,與史乘記載背謬之處甚多,不能因出于名家之手而遽爾置信。
1934年,譚其驤寫了《晉永嘉喪亂后之民族遷徙》,以東晉、南朝僑州郡縣建置的記載為基礎,用地名學的研究方法,對西晉末年至南朝宋中期150余年間的人口南遷作了定量分析,并論述了移民的遷出地、遷入地的分布對南方的影響。葛劍雄說:“此文在紛紜的史料中找到了僑州郡縣設置過程這把‘鑰匙’,解開了永嘉南渡后移民遷徙、定居與土著化的一系列關鍵問題,對中國移民史研究、地名學研究和定量分析都具有開創意義。”②
-----------------------
① 貴州博物館:《遵義高坪播州土司楊文第四座墓葬發掘記》,載《文物》,1974(1)。
②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傳》,載《史學理論研究》,1996(1)。
(四)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
從50年代起,譚其驤就把全部精力放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工作上。他非常重視地圖的作用,說:“地理之學,非圖不明。地圖對表達地理情況所起的作用,往往比地理著作更大。”①《中國歷史地圖集》分8冊,上起原始社會,下迄清代,共有20個圖組,304幅地圖,工程之浩大、圖幅之繁多、繪制之精良、考訂之詳盡,都是過去所沒有的。圖集所反映的內容,不僅限于中原王朝的管轄范圍,還包括各少數民族政權和邊疆政權的管轄區域。在政區處理上,不僅有一、二級政區,而且還包括了所有的縣和縣以下的重要城鎮和聚落。除政區外,還收錄了主要的山嶺、關津、長城、考古遺址等,更注意自然地理的變遷,如河流、湖泊、海岸線等。圖中對所有的點、線和其他符號所代表的內容,都進行了詳盡的考訂,吸取了前人研究的重要成果和文物考古資料,具有很大的權威性。
————————
① 譚其驤:《中國古代地圖集·序》,見《鄧之誠學術紀念文集》,41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譚其驤以歷史文獻資料為主要依據,吸取了考古學、地理學、民族學等相關學科的最新成果,如古城、居民點、宮殿、寺廟、倉庫、墓葬、長城、運河、道路、堤壩、烽燧等遺址的發掘和整理,找到了一大批可靠的地理坐標,有的證實了文獻記載的正確性,有的糾正了記載的錯誤,有的改變了后人的誤解。另外,考古所發現的珍貴文字和符號的資料,如簡牘、文書、碑刻、銘文、書籍、地圖等,也成為編繪歷史地圖的重要參考。由于《中國歷史地圖集》體例謹嚴,考證精良,內容完備,考訂精審,繪制準確,因此受到了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高度評價,迄今仍是最權威的中國歷史地圖集。著名學者侯仁之贊揚道:“這是我國歷史地理發展史上的一項重大成就,是對于歷史悠久的傳統特色的一個巨大發展。”并說這部地圖集的出版,“還將為我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帶來一定的推動作用。一方面它為我國各地區歷史地圖集中政區部分的編繪,樹立了典范;另一方面它又為其它重要的歷史地理研究的成果,在繪圖表示時,提供了可靠的依據”①。
在繪制過程中,譚其驤抱著尊重歷史事實,恢復歷史真相的態度,為了充分體現各民族共同創造歷史的精神,對歷史上的少數民族政權疆域給予同樣的顯示,如增加了一幅公元920年的吐蕃圖。《中國歷史地圖集》自1982年起分冊出版,至1988年出齊。這是我國歷史地理學最重大的一項成果,也是譚其驤最杰出的貢獻。
但譚其驤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歷史地圖集》只是一部以疆域政區為主的歷史地圖集,還不足于全面顯示中國歷史人文地理和歷史自然地理各分支的要素,未能充分反映我國歷史地理研究的成果。從1982年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主持下,他又主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可惜由于去世而未能完成。但在譚其驤的籌劃下,這一重要研究課題沒有停頓下來,這部三卷本的《國家歷史地圖集》將陸續出版,包括疆域、政區、民族、人口、文化、宗教、農業、手工業、城市、交通、戰爭、地貌、氣候、災害、植被等圖組一千多幅地圖,將成為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歷史地圖學的一個嶄新里程碑。
---------------------------
① 侯仁之:《近年來我國歷史地理學發展的主要趨勢》,見華林甫:《中國歷史地理學五十年》,59頁,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
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繪在帛上的兩幅地圖,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歷史地圖。譚其驤對其進行了研究,指出它的時代是那么早,比以前傳世的我國最早的《華夷圖》、《禹跡圖》早了1300多年,為地圖學史提供了最早的實物資料。它的準確性是那么高,從而為我國地圖學史增添了極為光輝的一頁。《西漢初期長沙國深平防區圖》所顯示的漢初長沙國的南界既不是以五嶺為界,也不同于《漢書·地理志》中的桂陽、零陵二郡南界。也就是說,五嶺以南的部分土地歸長沙國管轄。這幅圖在其主區及近鄰區范圍內畫著八個縣治:營浦、春陵、泠道、南平、齙道、桃陽、觀陽、桂陽;其中春陵、觀陽、蛇道三縣,不見于《漢書·地理志》,這是當時長沙西南邊界的一部分。從這一地區設縣之多,證明秦漢時代當地經濟文化已發展到相當高的程度。另外,該圖所記注的水道往往于后代記載的水名不同,可據以推究其演變過程,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①
--------------------------
① 譚其驤:《二千一百年前的一幅地圖——馬王堆漢墓出土地圖所說明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見《長水集》,160~18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譚其驤之所以能夠在歷史地理學領域取得如此大的成績,關鍵在于他對歷史文獻資料有一種正確的態度,在講到如何搜集、整理、鑒別、分析文獻資料時,他提出值得重視的三點:“第一點,搜集資料要做到基本上齊備”;“第二點,不要把傳說當作真實史料”;“第三點,不要輕信前人對古代文獻資料所作的解釋”。一句話,既要利用史料,又不要過分相信史料,要經過分析、鑒別,才能得出符合事實的結論。如關于洞庭湖的演變,長期以來地理學界、水利學界根據近百數十年來湖面日趨填淤,普遍認為整個歷史時期湖面都是在不斷地縮小,不同的只是快慢而已。譚其驤從先秦史料出發,結合當地的地貌條件,指出古籍中的云夢泛指楚王游獵區,包括山、水、湖、平原多種地形,范圍也極為廣闊。云夢澤只是它的一小部分,在長江北岸,江漢之間。進而他推斷先秦兩漢的洞庭湖不可能像見于南北朝著作《荊州記》、《水經注》里所記載的那么大,更不可能有唐宋記載里所謂“八百里洞庭”那么大。其實,洞庭湖在歷史時期不是一直由大變小,而是經歷了一個由小變大,由大變小的演變過程。①近年湖北省的地質工作者,通過鉆探和實地考察,也認為歷史上不存在跨大江南北的云夢大澤,結論與譚其驤的考證不謀而合。又如在宋元史籍中,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稱為長沙或石礁,但近代有些中外學者均誤認史籍中的七洲洋即今西沙群島。譚其驤經過考證后指出,明以前文獻記載中的七洲洋,指的都是僅限于今海南島東側七洲列島附近的洋面。清代圖籍中的七洲洋,有廣狹二義:狹義沿襲明以前舊義;廣義則范圍極廣,包括西沙群島海面在內,但也不專指西沙群島海面,更不等于就是西沙群島。②
譚其驤不僅重視文獻資料,也十分留意野外考察,曾去冀、豫交界的黃河故道進行實地調查,因而在歷史地理學研究方面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他晚年又倡導歷史文化地理研究,重點研究歷史時期文化區的界定和演變過程,并希望對中國歷史上文化區的形成和演變做深入的考察,寫有《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和地區差異》。他指出任何時代,都不存在一種全國共同的文化,而且各個地區的風土習尚也不盡相同,并不是有些學者所認為的中國文化是亙古不變且被于全國的以儒學為核心的文化,雖然儒家學說一直是兩千年來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卻從沒有建立起它的一統天下,猶如基督教之于歐洲諸國,伊斯蘭教之于穆斯林國家那樣,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點。③近年來區域文化研究方興未艾,呈現勃勃發展之態勢,如吳越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等專門課題相繼展開,并取得了極為可喜的成績,這一學術發展趨勢,與譚其驤晚年的研究志向是完全一致的。
1934年,顧頡剛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對譚其驤評價說:“譚君實在是將來極有希望的人,他對于地理的熟悉,真可使人咋舌。任何一省,問他有幾縣,縣名什么,位置怎樣,都能不假思索地背出。對于地理沿革史,夙有研究興趣,且眼光亦甚銳利,看《禹貢》半月刊、《史學年報》、《燕京學報》諸刊物所載可知。他在燕大研究院畢業生中,應列第一。”④譚其驤在歷史地理學領域探索耕耘了半個多世紀,他的主要貢獻可以簡要歸結為:“繼承和發展了傳統的文獻研究方法,結合現代科學理論,開辟了歷史地理研究的新途徑,解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和實際課題。”⑤
--------------------------------
① 譚其驤:《云夢與云夢澤》,見《長水集》,105~12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② 譚其驤:《七洲洋考》,見《長水集續編》,156~16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③ 譚其驤:《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和地區差異》,見《長水集續編》,171~18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④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胡適往來書信選》(中),258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⑤ 葛劍雄:《長水粹編·前言》,5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