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社會之間:現(xiàn)階段村委會的定位
瞿華
關(guān)鍵詞:國家 社會 村委會
作為一種有中國特色的草根民主,村民自治制度一直吸引著眾多學(xué)者的關(guān)注,甚至有人把它作為第三次“農(nóng)村包圍城市”的力量積蓄(前兩次指中國的解放戰(zhàn)爭和1978年農(nóng)村改革政策的推行)。從總體研究取向上來看,主要存在著三種不同的觀點,一,推進(jìn)論,認(rèn)為中國現(xiàn)階段的村民自治將促進(jìn)整個中國民主制度的前進(jìn)(徐勇,1997)。二,懷疑論,認(rèn)為村民自治作為一種基層民主,究竟能對中國的大社會發(fā)生多大的影響值得懷疑(黨國印,1999)。三,否定論,認(rèn)為所謂的村民自治。只不過是一種形式化的程序,并沒有多大的實質(zhì)性發(fā)展(沉延生,1998)。
上述三者觀點雖然不同,但同樣都涉及到一個組織——村民委員會(以下簡稱村委會)。從形式上看,村委會既是村民自治的前提(需要村委會的安排組織),又是村民自治的結(jié)果(村委會直接作為村民自治的象征而選舉產(chǎn)生)。因而如何看待村委會這個組織,就成了村民自治的根結(jié)。村委會是作為農(nóng)村改革的產(chǎn)物而誕生的。顯然,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國家性建構(gòu),同時,它又不屬于國家的正式行政組織之中。根據(jù)1982年憲法第111條的規(guī)定,村委會是基層群眾性組織,是農(nóng)村自治的基礎(chǔ)和象征。《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條也明確規(guī)定,村委會是對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wù)的基層群眾性組織,辦理本村的公共事物和公益事業(yè),調(diào)解民間糾紛,協(xié)助維護(hù)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建議。那幺作為這幺一種國家性的建構(gòu)的自治組織,或者說一種新的社區(qū)發(fā)展資源配置模式,村委會在當(dāng)代農(nóng)村究竟處于一個什幺位置?只有搞清楚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進(jìn)一步地對村民自治作出回答:現(xiàn)階段村民自治的合理性及其發(fā)展的可能性。
本文嘗試著用國家與社會這一解釋框架來對村委會這一村落社區(qū)組織給予一個定性的分析。只所以采取這一框架,是基于以下幾個方面。一,從眾多的研究來看,“國家與社會”的模式可以很好的解釋當(dāng)前中國農(nóng)村的眾多問題(孫立平,1994;張靜,2000)。二,本文對村委會的探討,目的就是為了解釋村民自治這一制度,如上所述,村民自治制度作為一種國家性的建構(gòu)與社區(qū)組織相結(jié)合,所針對的就是國家政權(quán)建設(shè)的另一階段:國家對社會的讓權(quán)。因而用國家與社會的解釋框架,可以和我們所要達(dá)到的目的對應(yīng)起來。三,對于村委會這種“半法人行動者”(朱又紅、南欲子,1996),國家與社會的框架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更清晰的解讀。當(dāng)然,用這一框架來分析也會遭到一些根本性的質(zhì)疑:中國是否存在西方式的“國家——社會”。因而筆者在此贊同一種理想型的建構(gòu)來提供一種新的視角以理解農(nóng)村社區(qū)的結(jié)構(gòu),把國家—社會當(dāng)作是一種分析工具,而不是抽象的概念。
我們的實地調(diào)查資料來自江蘇淮陰漣水的H村。該村位于江蘇的中部,經(jīng)濟(jì)狀況在江蘇屬于落后地區(qū),基本沒有集體企業(yè),私人的非農(nóng)經(jīng)濟(jì)也不多,村委會的權(quán)威在該地區(qū)還是非常大,這給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方面。
一 國家與社會:作為一種解釋框架
國家與社會是西方政治社會學(xué)的核心問題之一。它關(guān)注建立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相互對應(yīng)的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探討權(quán)利的界定、分化。平衡和規(guī)范秩序的社會法則的變化。關(guān)于國家與社會的關(guān)系,西方學(xué)者基本上是以一種二元論的觀點來看待。無論是洛克,霍布斯等人社會先于國家的觀點,還是黑格爾的國家擁有絕對高于社會的權(quán)力(在他看來,社會是處于家庭與國家之間的中間地帶),都把國家—社會看成是一種緊張的關(guān)系,并且存在著一種博弈的過程。同時,在這些觀點中,社會又成了國家力量的蓄水源(豬口孝,1991)。因而有學(xué)者將國家與社會的關(guān)系定義為:一,國家是緩沖世界經(jīng)濟(jì)影響的裝備,社會則是吸收世界經(jīng)濟(jì)影響。二,國家是管理國際關(guān)系影響的裝備,社會則是忍受國際關(guān)系的影響。三,國家為統(tǒng)治結(jié)構(gòu),社會為統(tǒng)治對象。四,國家是統(tǒng)治精英分子活動的舞臺,而社會則是補(bǔ)充精英分子的蓄水池。五,國家是參與的市民調(diào)整利害的場所,社會則是表示利益集合的場合(豬口孝,1991)。
與此相反,存在著另一種對于國家與社會的理解。在這種觀點中,闡述了國家與社會的高度融合。造成這種國家與社會高度融合的動因,包括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變遷,同時也包括其它三種力量的發(fā)展,以信息儲存和行政網(wǎng)絡(luò)為手段的人身監(jiān)視力,軍事暴力手段的國家化已及人類行為的工業(yè)主義。這種論點的代表就是吉登斯(吉登斯,1998)。在他看來,所謂的國家,即民族—國家,是指對其對其統(tǒng)轄的社會體系的再生產(chǎn)的各方面實施反思性的監(jiān)控。而社會是指任何擁有主權(quán),有地域邊界的空間,并且這一概念只不過是歐洲國家發(fā)展史的一個片段——作為權(quán)力集裝器的民族—國家的產(chǎn)物,而并非自古有之。因而在他的論述中,國家,社會都是一種暴力與疆界相結(jié)合的空間,更著重于一種與前現(xiàn)代國家形態(tài)的比較,而不是西方傳統(tǒng)意義上的行政與政治意義(孫立平,1994)。
當(dāng)然,也有一些學(xué)者(張靜,2000)反對西方這種對立的觀點。她認(rèn)為,近來許多關(guān)于中國國家政權(quán)建設(shè)和自治的研究中,一直把國家—社會處于一種對立的狀態(tài),而看不到他們之間的聯(lián)系。社會并不是一個獨立的概念,它實際上更是在與國家的相對關(guān)系中獲得了其自身的規(guī)定性的,在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和緊張中尋求平衡。(鄧正來,1997)。即國家—社會是一種互相建構(gòu)的框架。延伸至中國,張靜認(rèn)為,中國傳統(tǒng)的秩序論證從“合”的立場出發(fā),主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體統(tǒng)一,并以為這是達(dá)成秩序的要件。權(quán)利分立在這里不僅不是討論秩序的前提,而且有可能被視為有悖于秩序建設(shè)的東西,國家與社會是型構(gòu)上的同一性,而非社會獨立的組織化(張靜,1997)。
但是從中國的實際狀況來看,西方純粹的兩元對立的觀點和中國傳統(tǒng)的兩者合一的論點,在分析當(dāng)代中國社會時似乎都有其不足之處。一方面,中國社會在許多方面確實存在著國家—社會型構(gòu)上的同一。另一方面,從意義和效果來看,國家與社會又存在著分立點,可以說是一種結(jié)構(gòu)與功能的分離。實際上,國家—社會這一框架是作為一種現(xiàn)代性而被建構(gòu)的,那幺在傳統(tǒng)的西方式的理解和中國的解釋框架之外,是不是還存在著另一種形態(tài)?當(dāng)代中國農(nóng)村的改革正好為這一研究展現(xiàn)了一個舞臺。現(xiàn)階段村民自治的實行,無非就是要造就一個大社會,以保障個人的權(quán)利。從農(nóng)村的村級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來看,作為自治主體的村落社區(qū)(其象征主體是村委會),是作為“社會”層面的代理人,相對的鄉(xiāng)鎮(zhèn)政權(quán)則是作為“國家”的代理人。因而在下文我們將分析鄉(xiāng)鎮(zhèn)政權(quán)—村落社區(qū)(村委會)的互動關(guān)系,以此來給村委會一個明確的定位。我們會看到,國家—社會的對立緊張關(guān)系只具有哲學(xué)層面上的意義。事實上,當(dāng)代中國農(nóng)村的秩序是一種國家—社會相互交融的形式,而村委會也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治組織,而是介于國家與社會之間,這對于國家—社會的二元形態(tài)產(chǎn)生了另一種理解。
二 鄉(xiāng)鎮(zhèn)政權(quán)—村落社區(qū)的互動
人民公社的解散,是國家另一種意義上的對農(nóng)民的讓權(quán)。因此其主旨就是要把權(quán)力下放給農(nóng)民而使其有更大的發(fā)展空間。承擔(dān)這一重任的就是村民自治的產(chǎn)物——村委會。根據(jù)《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guī)定,村委會是群眾性的自治性組織,因而無論從人員的編制,待遇,戶口等方面來看,它都同它的上級組織——鄉(xiāng)鎮(zhèn)政權(quán)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從文本解讀的意義上來看,這二者代表著國家—社會兩個層面。但在實際層面上,我們往往會看到村委會并不是作為村民的保護(hù)人,相反卻承擔(dān)著國家經(jīng)濟(jì)人的角色,對于這種困惑,通過實地調(diào)查我們可以有更好的了解。
村委會作為村落社區(qū)的組織,承擔(dān)著維護(hù)村落秩序和個體權(quán)利的任務(wù)。這種要求是全方面的。在此,我們將從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三個主要維度來闡述村委會在社會再生產(chǎn)過程中所確立的自身定位。
一, 經(jīng)濟(jì)層面。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以后,象H村這樣以農(nóng)業(yè)為主的村莊,基本就沒有集體生產(chǎn)活動,處于各干各的狀況。也想辦一些村辦企業(yè),但由于缺資金,技術(shù)等而一直沒有搞起來。外出打工是H村一個很大的收入來源。該村幾乎所有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在外打工。但與以往單個外出打工不同的是,現(xiàn)在的H村外出打工基本上是一種集體的形式。據(jù)村委會W主任介紹,該村目前外出打工基本上先由縣里面的勞務(wù)輸出部門和外地協(xié)商好,再把具體的人員要求,技術(shù)要求等傳達(dá)到村。村委會根據(jù)實際情況在村里挑選人員,同時在外出打工的時候,一般也有村委會的某一負(fù)責(zé)人隨隊具體管理。對于這種外出打工的“行政化”,W主任認(rèn)為,主要是目前單個的外出打工不好找,而且對于輸入勞務(wù)的地方也不好管理。而目前這種方式便于各部門的統(tǒng)籌管理。但是對于一些具體的管理方式,據(jù)一些曾帶隊外出打工的村委會的干部介紹,在外打工時,往往并不是以這種村委員的干部身份帶來的權(quán)威,而是自身在村里的一些資源,如親戚關(guān)系,這種社會資本往往比所謂的干部身份更好使。
為了發(fā)展經(jīng)濟(jì),H村除了外出打工還大力調(diào)整農(nóng)產(chǎn)品結(jié)構(gòu),挖掘潛在的資源。淺水藕就是一個。淺水藕作為H村的一個特色而被鎮(zhèn)政府安排到發(fā)展計劃上。面對鎮(zhèn)政府的安排,村委會感到很為難。淺水藕本來是作為一種副產(chǎn)品在H村種植的,幾乎家家都種一點,但主要用于自己消費。現(xiàn)在要把這作為一主業(yè)來發(fā)展,村民的風(fēng)險問題需要有人來承擔(dān)(要不農(nóng)民不可能進(jìn)行轉(zhuǎn)向)。這使得村委會處于了兩難之中。一方面,鎮(zhèn)政府把這當(dāng)作一項行政任務(wù)下發(fā)給了村委會,同時,村民又對村委會不能提供有效的風(fēng)險保護(hù)而抗議。結(jié)果,村委會只能選擇了個折衷的處理辦法。首先村委會的各個干部家率先種植了淺水藕,作為示范的榜樣。并且通過三番五次到鎮(zhèn)政府抱怨種植的困難而謀求到了一些補(bǔ)貼給予村民作為風(fēng)險補(bǔ)助。同時在村里進(jìn)行廣泛的宣傳,認(rèn)為這是“國家的政策”,不完成就要收回土地,并且要罰款。最后,村委會干部通過各自在村里的社會資源,動員親戚朋友,直至終于使每家都種上淺水藕。
外出打工,種植淺水藕本來應(yīng)該是個人的事情,村委會在這種事情里面本來可以起個輔導(dǎo)作用,如收集信息,提供一種建議等。但當(dāng)村委會面對鎮(zhèn)政府這樣的國家機(jī)構(gòu)時,問題就發(fā)生了。村委會要接受鎮(zhèn)政府的“指導(dǎo)”,但作為民選的組織,又要顧全地方的利益,就只有在兩者之間謀求一種平衡。
二, 政治層面。從村委會的干部編制來看,主要有主任,副主任,會計,這些是以村務(wù)為主。另一方面是有關(guān)政務(wù)的——村支書。不同于民選的主任,村支書是直接由上一級組織提名的。眾多的實證材料表明,村支書在村委會中占有絕對的領(lǐng)導(dǎo)地位。如果主任和村支書關(guān)系不好,一般主任是很難真正辦好事的,所以“一肩挑”是眾多村委會的做法,H村也不例外。W主任還兼任了村支書。這種設(shè)置本身就存在一個矛盾。村支書作為黨的上級組織的任命,是要服從于上級組織,村主任作為民選的利益代表,應(yīng)該站在村民一邊。當(dāng)這兩者發(fā)生矛盾時,個人該如何選擇?但從實際的情況看,這種“一肩挑”的措施在目前來講還是非常有效的。W主任認(rèn)為,一般情況下這種“一肩挑”不太會發(fā)生大的矛盾,如果真有發(fā)生,那幺個人的能力在這時就非常重要了,權(quán)衡利弊而取舍。
對于村委會來說,5年一次的村委會選舉是一件大事。和開始舉行村民選舉時鎮(zhèn)政府提供候選人不一樣,現(xiàn)在鎮(zhèn)政府在選舉時一般很難讓自己滿意的人入選,這也帶來了一個后果——很可能雙方在以后的工作中不合作。H村就發(fā)生了這樣的事,前任M主任并不是鎮(zhèn)政府所滿意的對象,因而在M當(dāng)選后,鎮(zhèn)政府在各項工作中都不予以支持,終于使其提前推出。現(xiàn)任的H主任是去年剛當(dāng)選的。當(dāng)選前他就是村支書,鎮(zhèn)政府對他一直比較滿意。同時他自己開著一個農(nóng)具點,賣一些化肥,農(nóng)藥,種子等。并且利用一套土壤測試儀經(jīng)常給村民測量土壤的肥量狀況。在當(dāng)?shù)厝丝磥硭且粋€能人,對于這樣一個雙方都比較滿意的對象,H當(dāng)選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許多學(xué)者在研究村落社區(qū)的權(quán)力構(gòu)成時,都提到了有關(guān)精英轉(zhuǎn)換的問題(董磊明,2002)。目前的村委會由于是一個自治性組織,過去那種純粹的官制系統(tǒng)的人員已不是各方所關(guān)注的對象,這時的精英是一種“能人統(tǒng)治”,他們與上級組織關(guān)系不錯,在村落社區(qū)也有一定的威信和聲望,有利于村務(wù),政務(wù)的開展。
三, 文化層面。有學(xué)者在研究中國轉(zhuǎn)型期以來的文化時指出,現(xiàn)階段中國文化是典型的官方文化(國家層面)和市民文化(社會層面)相混合,并且通過對比文革時期的文藝作品和現(xiàn)階段的電影電視來舉證(陳東風(fēng),1995)。這一結(jié)論同時也很適合目前的農(nóng)村社區(qū)。從村委會的工作出發(fā)來看,主旋律的宣傳還是占主導(dǎo)地位。在H村目前最主要的就是關(guān)于“三個代表”思想在基層的宣傳工作。在上級領(lǐng)導(dǎo)的安排下,H村印刷了多份“三個代表”的宣傳刊物,分發(fā)給農(nóng)戶,并且通過廣播宣傳“三個代表”的重要性。在進(jìn)村的兩旁道路上,掛滿了各式橫幅。除了這些,W主任介紹,每當(dāng)上面發(fā)下有關(guān)農(nóng)民的一些政策時,村委會都會即使的給農(nóng)民介紹。如前一階段的一事一議,農(nóng)民的減負(fù)卡等。在很多時候,村委會都是直接作為下屬機(jī)構(gòu)而面對村民宣傳工作國家政策。但另一面,村委會作為村民的利益化組織,也負(fù)責(zé)農(nóng)民的文化娛樂活動。雖然現(xiàn)在差不多家家都有了電視,但由于H村地出偏僻,能收到的頻道并不多,所以一些鄉(xiāng)村傳統(tǒng)的娛樂一直保留著。如逢年過節(jié)都會請一些劇團(tuán)來唱戲。當(dāng)然不是以前的革命樣板戲,一些傳統(tǒng)的經(jīng)典節(jié)目又成了大家關(guān)注的焦點。同時,一些被禁止了多年的傳統(tǒng)儀式也重新出現(xiàn)了,如一些舊式的結(jié)婚禮儀,祭祖等,很多時候村委會是以一種默認(rèn)或支持的方式出現(xiàn)的。
村委會作為村落社區(qū)的文化傳承者,顯示著在新時期國家文化和村落文化的一種互動新形態(tài)。一方面村委會還作為國家在村落社區(qū)中的“代理人”而表現(xiàn)著國家性,同時,作為社區(qū)的利益化組織,又是村落自身活動的核心組織者。
三 結(jié)語
在上面的闡述中,我們看到了另一種不同于國家—社會的框架。村委會作為國家性建構(gòu)的自治組織,在經(jīng)濟(jì)層面上,他要服從國家的指導(dǎo)性建議,同時他有要考慮到地方的利益。政治層面上,從管理者的組成到整個體系的運(yùn)行,都在兩方權(quán)衡,文化層面,一邊要無條件的進(jìn)行國家官方主流文化的宣傳,同時又帶有“小市民”特色的文化也風(fēng)風(fēng)火火。黃宗智在研究中華帝國晚期的社會—政治體系時,設(shè)想由大小不同的三塊構(gòu)成。頂部是國家的正式機(jī)構(gòu),底部是社會,兩者之間的是大小居中的第三塊,這就是清代司法領(lǐng)域的運(yùn)作之處,便是諸如鄉(xiāng)鎮(zhèn)的鄉(xiāng)保與村里正等縣以下行政職位的立足之處,便是國家官吏與士紳領(lǐng)袖由合作進(jìn)行公益活動的地方(黃宗智,2002)。在這一討論中,黃設(shè)置了第三領(lǐng)域——即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鄉(xiāng)保,里正等。經(jīng)過20世紀(jì)初以來的國家政權(quán)建設(shè)至如今,村民自治過程中的村委會也具有了上述第三領(lǐng)域的特征。上面是以國家政權(quán)形式出現(xiàn)的鄉(xiāng)鎮(zhèn)政權(quán),下面是村落社區(qū),這也使得村委會既有自治因素,又有行政因素。從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層面來看,村委會一方面要接受國家的“指導(dǎo)”,同時又有著自身變通的方式,并且這種變通已經(jīng)制度化了。
理解了這一點,對于中國農(nóng)村現(xiàn)階段的村民自治就會有一個更清晰的了解。農(nóng)民所要的并不是絕對的自治,他們并不拒絕官方的介入,相反,他們一直反對的則是村落里的“偽國家權(quán)力”(實際上是地方的惡勢力),相對于此,他們當(dāng)然要尋求“自治”(張靜,2002)。村委會的這一獨特性,正好滿足了農(nóng)村的需求,在官方與社會的相互權(quán)衡中取得個人最大利益,這或許也是農(nóng)民理性的表現(xiàn)。因而我們在理解村民自治和村委會的時候,也不能再把他看作是一種純粹的自上而下的外在建構(gòu)。鄉(xiāng)村社會政治權(quán)力的雙軌制在上下之間的權(quán)衡,造就了這一歷史的結(jié)合體。
參考書目:張靜:《國家與社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孫立平:《改革前后中國大陸國家,民間統(tǒng)治精英及民眾間互動關(guān)系的演變》,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季刊》1994(3)張靜:《基層政權(quán)》,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鄧正來:《國家與社會》,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 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三聯(lián)書店,1998 朱又紅、南裕子:《村民委員會與中國農(nóng)村社會結(jié)構(gòu)變遷》,載《社會學(xué)研究》1996(4)豬口孝:《國家與社會》,時報文化出版企業(yè)有限公司,1991 黃宗智:《中國的“公共領(lǐng)域”與“市民社會”—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第三領(lǐng)域》,載亞歷山大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陳東風(fēng):《官方文化與市民文化的妥協(xié)與互滲》,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季刊》1995
鎮(zhèn)企業(yè)會計.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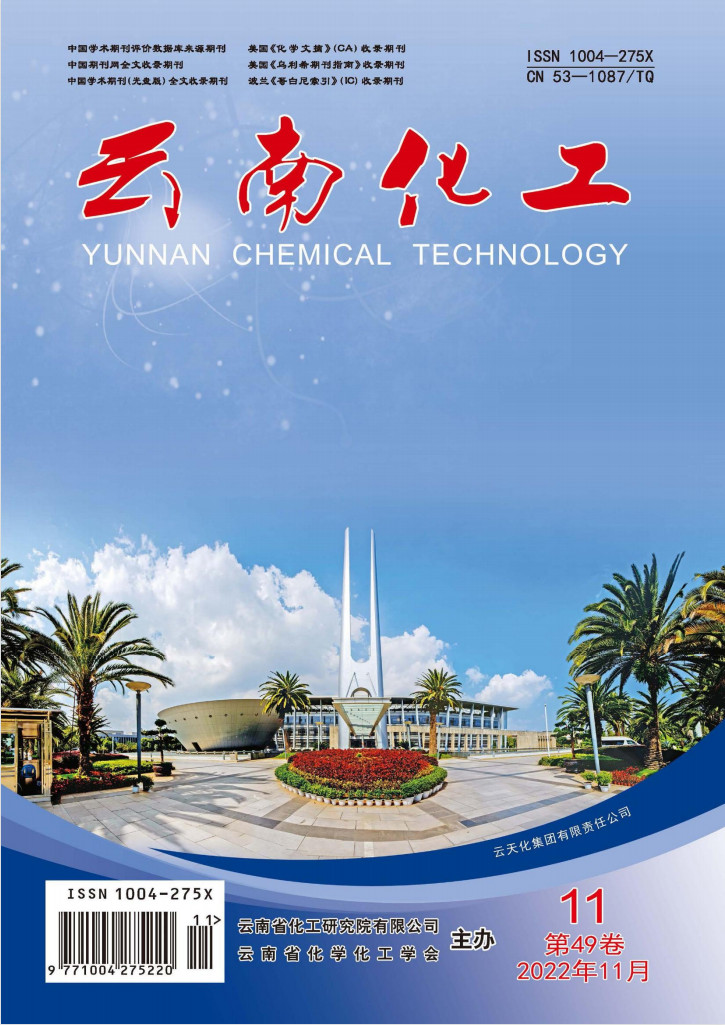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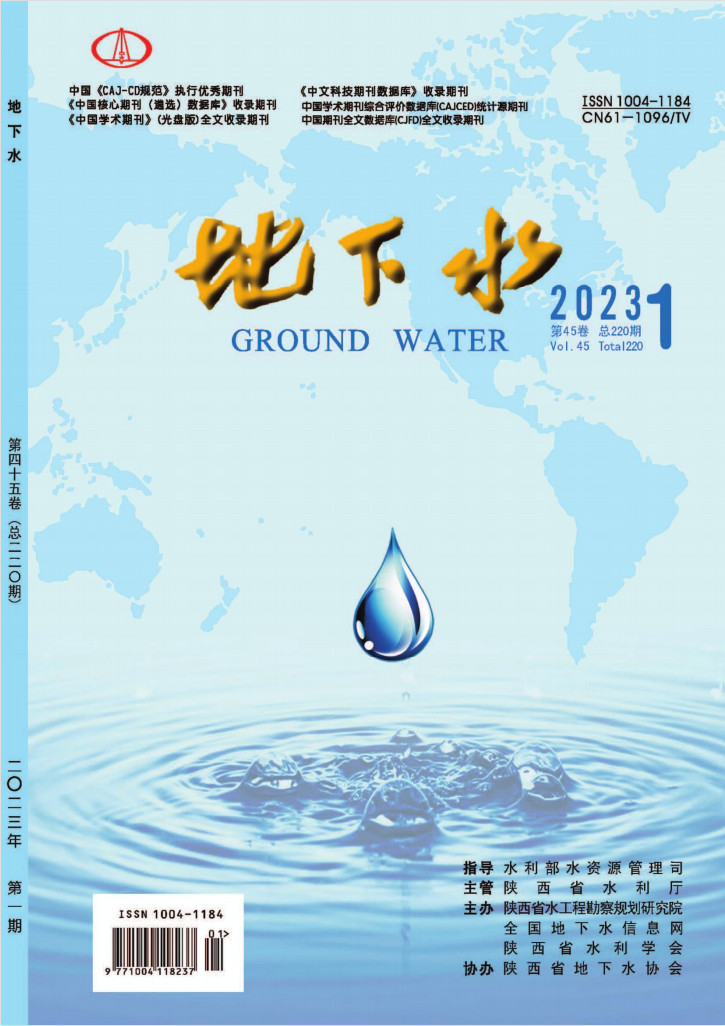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