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會選舉:農民工的參與現狀與原因分析以武漢市調查為例
黃輝祥
Through analysing the investigation outcome o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in Wuhan City,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the peasant workers participating into the village elections is lower. The causes
are institution restriction, information obstructed, low benefit connection, weak
sense of the political effectiveness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rivacy of
the election cost and the common of the elected object, etc..In the village
election, the lower participation proportion of the peasant workers shows that
the peasant work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lacks institutional channels. The
cardinal measure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lies in institution innovation and
brings the peasant workers into the orbit of democrat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political life.
Key Words:
Village elections; Peasant work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內容提要:筆者通過對武漢市農民工政治參與狀況調查結果的分析,認為農民工參與村委會選舉的比例較低。其原因主要有制度性限制,信息溝通不暢,利益關聯(lián)淡薄,政治效能感弱和選舉成本的私人性與選舉對象的公共性之間的矛盾等。村委會選舉中農民工的參與缺失表明,農民工的政治參與缺乏有效的制度性渠道;改變這種情況的根本措施在于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將農民工納入到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會化的軌道中來。
關鍵詞: 村委會選舉 農民工 政治參與
村民自治的實行,使農民獲得了參與社區(qū)管理的制度性渠道。特別是199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修訂頒布后,各地按照法律規(guī)定實行村委會直接選舉,極大的調動了億萬農民參與國家和社會管理的積極性。廣大農民紛紛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投票選舉自己的當家人,表現出極大的參政熱情。一些地方村民參選率達到90%以上。但是,在廣大村民積極行使民主權利的背后,卻掩蓋了不同階層農民參與的差異性。事實上,公民政治參與的狀況受其社會經濟地位、自身政治素質和政治文化等的影響。不同的社會階層或團體,其政治參與狀況也各不相同。因此,在農民日益分化的背景下,對農民政治參與進行階層化研究對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就有著重要的意義。
本文所要考察的是村委會選舉中農民工這一特殊階層的參與狀況。改革開放后,隨著國家城鄉(xiāng)治理體制的松動,農民開始到城市務工經商。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目前中國有8800萬流動人口(實際人數可能更多),其中大部分是農民工(陸學藝,2002)。農民工雖然仍與農村保留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是他們畢竟離開了農村,多數實現了職業(yè)上的轉換。這種改變使其與傳統(tǒng)農民在社會經濟地位、自身政治素質等方面多有不同,因此在村委會選舉中其參與狀況也會與一般村民有著明顯的不同。為了考察村委會選舉中的農民工參與狀況,2001年春夏之際,筆者等人在武漢市就農民工的政治參與狀況進行了問卷調查,一共獲取有效問卷753份。本文的分析將以此為基礎。
一、 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
(一)人口特征
在753名調查對象中,男性有420人,占55.8%,女性333人,占44.2%。調查對象中絕大多數是年輕人,18-35歲的年青人占了總數的69.7%(詳見表1)。從文化程度上看,被調查的農民工中文盲、半文盲有51人,占6.8%;小學有117人,占15.5%;初中有377人,占50.1%;高中或中專的有169人,占22.4%;大專以上有34人,占4.5%(有5人未回答)。總的來看,有77%的被調查農民工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其文化程度較一般村民高。調查對象中的文盲數只占6.8%,顯著低于全國農村勞動力中文盲半文盲占15.3%的比例;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者分別占到50.1%和22.4%,大專文化者占4.5%,顯著高于全國農村勞動力37.4%、8.2%和0.2%的水平。 從年齡和文化程度來看,這些被調查的農民工絕大多數應算農村精英。
表1:農民工的年齡狀況
年齡 18歲以下 18—25歲 26—35歲 36—45歲 45歲以上 未回答
人數 76 335 189 104 46 3
比例(%) 10 44.5 25.2 13.8 6.1 0.4
(二)經濟狀況
農民工走出鄉(xiāng)村涌入城市的動因是多方面的,卻以打工掙錢為最主要的外出動機。從我們的調查來看,有548人選擇“掙錢”作為外出的動機,占被調查者的72.8%。他們中在外打工2年及以上的占66.5%,還有12人的外出年限在8年以上。也如他們所愿,他們中的許多人的收入狀況是不錯的(見表2)。他們中月平均收入在200元以上,即年收入在2400元以上的占88.3%,而2001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則為2366元,也就是說,絕大多數農民工的收入水平高于農村居民收入的平均數。月收入在600元以上的占35.2%,明顯高于2001年全國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60元(國民經濟與社會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2001年)。可見農民工中有相當一部分已經達到了甚至超過了一般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換句話說,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在城市生活有較為充分的收入保障,也具有了一定的經濟地位。
表2:農民工的月平均收入
月收入(元) ≤200 201—400 401—600 601-800 801-1000 ≥1001 未回答
人數 80 198 202 133 72 60 8
比例(%) 10.6 26.3 26.8 17.7 9.5 8 1.1
二、村委會選舉:農民工的參與
從調查情況來看,農民工參與村委會選舉的情況并不令人樂觀。這主要表現在:
(1)農民工參與村委會選舉的比例比較低。村委會選舉是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礎,是農民政治參與的重要形式。但是對被調查的農民工而言,只有145人參加過家鄉(xiāng)的最近一次村委會選舉,僅占有調查對象總數的19.3%,而沒有參加過選舉的則有599人,占79.5%。(詳見表3)
表3:您出來后,有沒有參加過家鄉(xiāng)最近一次村委會選舉嗎?
人數 比例(%)
有 145 19.3
沒有 599 79.5
未回答 9 1.2
(2)從參選的方式上看,不利于農民工真實意愿的表達。在參加選舉的145人中,有占52.4%的人是親自回村參加選舉的;請別人代投的有23人,占15.9%;函投的有21人,占14.5%;通過其它方式投票的有17人,占11.7%。(詳見表4)盡管村委會選舉允許委托投票,但是親自參加選舉比其它方式能夠更為真實的表達農民工的選舉意愿。比如,委托投票往往將選擇權交給了被委托人,委托人的選舉意愿是否得到尊重和表達則完全取決于被委托人。
表4:請問您是怎樣參加投票的?
人數 比例(%)
親自回家投票 76 52.4
請別人代投 23 15.9
村里寄來選票,我填好后再寄去 21 14.5
其它 17 11.7
未回答 8 5.5
(3)服從性參與的特點比較明顯。服從性參與是一種被動型參與,主要是由于受到他人命令、動員或暗示等而形成的。在回答“為什幺要參加選舉”時,62.8%的人認為“這是公民的義務”;28.3%人選擇了“村里要我參加”;有7.6%的是出于怕得罪人參與選舉。而出于利益動機主動參加選舉的只有24人,僅占16.6%。(詳見表5)
表5:請問您為什幺要參加選舉?(可多選)
人數 比例(%)
村里要我參加 41 28.3
大家都選,所以我也選 25 17.2
這是公民的義務 91 62.8
選舉對自己有好處 24 16.6
不選會得罪人 11 7.6
其它 33 22.8
未回答 8 5.5
三、原因分析
作為中國鄉(xiāng)村社會政治參與的一種重要形式,村委會選舉投票行為既有政治參與行為的一般特征,又有中國國情所決定的特殊性。因此,影響村民投票的因素既要從政治參與的共性中去找,也要從中國特有的鄉(xiāng)情國情中去找(肖立輝,1999)。由于農民工群體的特殊性,影響其參與行為的因素似乎要比一般的村民更為復雜。
(一)制度性限制。按照現有的制度安排,村民只能在自已戶口所在地的村進行村委會選舉,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而農民大多屬于“離土離鄉(xiāng),但沒有脫籍”的農民,他們長年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已不在原籍,而戶籍仍在原地。如果按照戶籍標準,他們只能在戶籍村參加選舉。這就給這部分人參加選舉帶來了很大的困難。雖然我們在媒體上不時看到有外出村民包車、甚至包機回村參加選舉的情況,但是這樣的情況畢竟是非常少見的。
(二)信息不暢的影響。農民工很難與家鄉(xiāng)保持比較通暢的聯(lián)系,對家鄉(xiāng)村里的公共生活信息所知非常有限,一方面,由于時空阻隔,農民工很難獲取村委會選舉的詳細信息。另一方面,農民工流動的不確定性使家鄉(xiāng)的村級組織也很難將有關信息傳遞給他們。因此當家鄉(xiāng)村里舉行村委會換屆選舉時,他們很可能因為不知道情況而不能行使“自己選擇當家人”的權利,即使有些外出村民知道舉行選舉,也由于信息不充分(對選舉的細節(jié)所知有限)而放棄選舉。如有40.1%的調查對象以“選舉時我不知道”來解釋自己沒有參加選舉的原因。有24.7%的調查對象不參加選舉的原因是“對候選人不了解”。
(三)利益關聯(lián)度的降低。馬克思主義政治參與觀認為,人們之所以參與政治,是建立在切實的物質利益基礎之上的,而不是出自“本能”、“理性”、“理智”這些虛無縹眇的精神原因。“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82頁),“政治權力不過是用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拉斯韋爾也曾指出:“各種政治運動的生命來自傾注在公眾目的上的私人感情。”這種利益與人們越貼近,人們對它的追求就越迫切,由它所引起的參與動機就越強烈,反之也是如此(陶東明、陳明明,1998)。
顯然,農民工與家鄉(xiāng)農村的利益關聯(lián)在日益淡薄。從農民工流動的動機來看,選擇“掙錢”的人最多,占調查對象的72.8%。這說明農民外出本身就是利益比較的結果,即在城市可能獲得更多的收益。而在城市的工作也確實滿足了農民工的逐利動機,如前所述,他們的收入普遍比在農村要高。這就進一步疏離了農民工與家鄉(xiāng)的利益關聯(lián)。調查表明,農民工對家鄉(xiāng)關注的總趨勢是日益下降或減少。對家鄉(xiāng)的事情持“很關心”態(tài)度的人,只有211人,占28%;“比較關心”的有225人,占29.9%;“關心一點”的有239人,占29.9%人;當然完全不關心的人所占的比例也不高,只占8.6%(還有1.8%的人未回答)。不僅如此,城市生活、工作的經歷也在改變著農民工的思想觀念,他們對家鄉(xiāng)的社會認同程度也在下降。比如,在問到“您現在對家鄉(xiāng)的風俗人情、觀念、行為等還看得慣嗎?”時,只有1/3多一點的人認為“基本都看得慣”;有47.6%的人回答“有些看得慣,有些看不慣”;有10%的人則回答“基本都看不慣”。(詳見表6)
表6:農民工對家鄉(xiāng)的風俗人情、觀念、行為等的認同
人數 比例(%)
基本都看得慣 267 35.5
有些看得慣,有些看不慣 359 47.6
基本都看不慣 75 10
不清楚 33 4.4
未回答 19 2.5
與對家鄉(xiāng)的關注和社會認同下降相反,農民工對城市的喜愛程度較高,盡管他們還沒有進入到城市原生社會體制中去,市民和農民工之間的隔閡依然較深。有27.8%的調查對象認為自己“很喜歡”城市的生活,有36.1%的人認為“有點喜歡”城市的生活;而表示“不喜歡”的只有6.2%。(詳見表7)因此,有近半數(45.7%)的調查對象表示希望把戶口遷到城市來。不希望的有16.1%。(詳見表8)值得注意的是,有相當一部分調查對象對這兩個問題持“無所謂”的態(tài)度,分別占19.4%和37%。這可能和農民工在城市中的邊緣處境有關。
表7: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評價
人數 比例(%)
很喜歡 209 27.8
有點喜歡 272 36.1
不喜歡 47 6.2
無所謂 146 19.4
說不清 74 9.8
未回答 5 0.7
表8:農民工是否希望把戶口遷到城市:
人數 比例(%)
希望 344 45.7
不希望 121 16.1
無所謂 279 37
未回答 9 1.2
農民工與家鄉(xiāng)利益關聯(lián)程度的日益減弱,對家鄉(xiāng)的關注和社會認同的下降,都使他們對家鄉(xiāng)有一種疏離感,他們不僅是城市里的“邊緣人”,也慢慢在鄉(xiāng)村被“邊緣化”。這深刻地影響到他們的政治參與行為。他們既難積極爭取當干部,也不會認真參加投票甚至不參加投票。如在回答“對當村干部的態(tài)度”時,有40.5%的人選擇“無所謂”,28.6%的人選擇“不想當”,只有17.8%的選擇“想當,并會積極爭取”。此外,調查對象中599人沒有參加選舉的農民工中,有16%的人因為“選舉對我來說不重要”、10%的人認為“選舉太麻煩”、8%的人認為“選了對我也沒有什幺好處”,而沒有參加選舉。
(四)政治效能感弱。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對自己政治參與行為影響力的主觀評價。政治參與的主動性與人們對參與的功效感有關(亨廷頓等,中譯本,1987)。一般來講,政治效能感與公民參與行為呈正相關關系。對選民而言,政治效能感是指選民對自己參與投票能否關系到選舉結果的主觀推測,即選民對投票功效的評價。如果選民“所面臨的選擇沒有什幺重大差異”以及“所作所為無足輕重,不能有效改變結果” (達爾,中譯本,1987),選民是很容易放棄選舉的。在村委會選舉中,當村民意識到自己一票重要時,他往往會積極去投票,甚至不計較投票成本;相反,如果他發(fā)現自己的一票無足輕重時,他就會不太在意自己的一票,甚至根本不去投票。此次調查對象的參選率不高與他們的政治效能感不強有關。在沒有參加選舉的調查對象中,有32.7%的人認為“上面都定好了,選也白選”,17.2%的人認為“我的一票起不到什幺作用”。
(五)選舉成本的私人性與選舉對象的公共性之間的矛盾。村委會是村民民主選舉出來的群眾自治組織,執(zhí)掌村莊公共權力機構。其公共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村委會不是為村莊內特定對象,而是為全體村民服務的公共組織;二是村委會的職責是在村莊范圍內為全體村民提供公共產品,而不是私人產品。村委會的公共性使選民選舉村民委員會的收益很難量化,但是村民為選舉支付的成本卻是私人性的,其對選舉付出的感受是實實在在的。就農民工而言,其親自回家鄉(xiāng)參選的主要成本有:往返的交通費用,因誤工而導致的收入損失,回到家鄉(xiāng)的額外支出,如走親訪友需支付的費用,等等。與選舉支出的私人人性相比,農民工參加選舉所能帶來的收益卻是模糊的和未知的。因此,農民工往往是理性地放棄了參加村委會選舉,即使參加,也多是盡量避免親自回家鄉(xiāng)參選,而是采取委托投票或函投的方式參選。
村委會選舉是億萬農民行使社會主義民主的廣泛實踐,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生動體現。但是我們的調查表明,農民工參與村委會選舉的情況并不樂觀,絕大多數農民工處于參與缺失狀態(tài)。其原因非常復雜,既有宏觀環(huán)境的影響,也有農民工自身的因素,還有參與對象的原因。但是作為理性的經濟人,村委會選舉中農民工的參與缺失是在約束條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
村委會選舉中的參與不足,表明現有的制度安排不能滿足農民工的政治參與要求。一方面,他們由于種種因素的制約而無法有效地參與農村的民主選舉;另一方面,由于現有體制的束縛,他們又不能在居住地和工作地的城市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農民工是當代中國一個龐大的弱勢群體,其是否穩(wěn)定關系到整個國家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農民工的政治參與如果得不到充分尊重和有效滿足,將有可能引發(fā)這部分人的不滿情緒,從而影響政治穩(wěn)定和社會發(fā)展。 盡管我們可以通過一些技術創(chuàng)新手段,如,合理安排選舉時間,建立更為合理科學的農民工投票機制等來暫時提高村委會選舉中的農民工的參選率,但是更為根本的解決辦法是改變制度約束,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來解決農民工政治參與渠道不暢的問題。具體地說,就是通過以居住地而不是戶口所在地為選民登記條件,進而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使農民工參與居住地的政治生活,從而使受過城市文明熏陶、初步具有了現代意識的億萬農民工成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生力軍,而不是被排斥在政治社會化和民主化進程之外。
1.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180頁。
2.肖立輝:《影響村民投票的因素分析》,載《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9年第3期。
3.陶東明、陳明明:《當代中國政治參與》,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頁。
4.亨廷頓等:《難以抉擇――發(fā)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華夏出版社,第87頁。
5.羅伯特•A•達爾:《現代政治分析》,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13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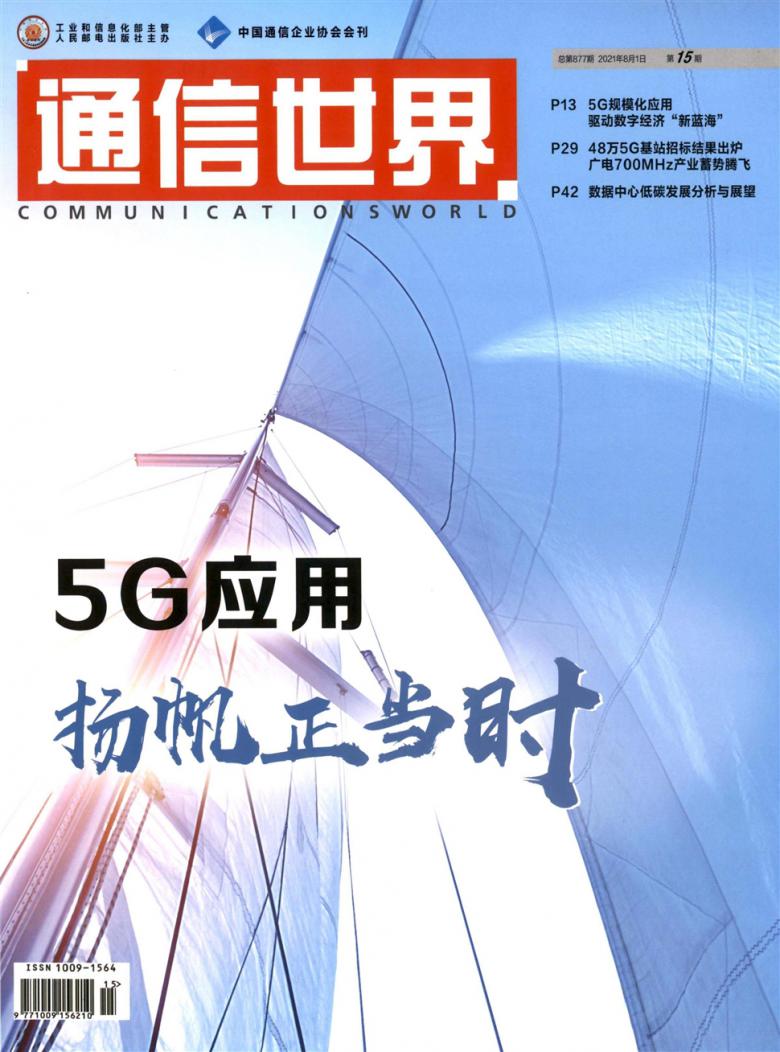
生產業(yè).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