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論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幾個重要問題——對《刑法修正案(八)》的解讀
黃繼坤
【摘要】“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并非單純處罰“賴賬不還”,其背后蘊涵著處罰詐騙勞務(wù)的法理,據(jù)此,可以對可罰性條件“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作出合理解釋,即一方面它是提高“賴賬不還”的違法性程度、作為刑罰擴張事由的“客觀的超過要素”,另一方面是限制詐騙勞務(wù)行為成立本罪的范圍、作為刑罰限制事由的“客觀的處罰條件”。另外,搶劫罪中的“暴力、脅迫”、敲詐勒索罪中的“威脅”與詐騙罪中的“詐騙”不是本罪“其它逃避支付勞動者勞動報酬的方法。 【關(guān)鍵詞】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勞動報酬;惡意欠薪;詐騙勞務(wù);逃避支付
《刑法修正案(八)》新規(guī)定的“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從罪狀表述來看,似乎均在表明本罪的規(guī)范目的在于處罰拖欠勞動者勞動報酬這種“賴賬不還”的行為,現(xiàn)在本罪被俗稱為“惡意欠薪罪”就反應(yīng)了這種普遍性認識。但是,如果國家動用刑罰處罰單純的“賴賬不還”行為,顯然把刑罰權(quán)過分?jǐn)U張到了民事領(lǐng)域,有違刑法謙抑性原理。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本罪。
一、保護法益與行為對象
(一)保護法益:勞動者的財產(chǎn)權(quán)
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被規(guī)定在刑法第276條“破壞生產(chǎn)經(jīng)營罪”之后,作為第二百七十六條之一。因為刑法第276條是刑法分則第五章“侵犯財產(chǎn)罪”的最后一個罪名,所以從“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所屬的類罪名來看,其法益可以確定為“財產(chǎn)權(quán)”。同時,犯罪是侵犯法益的行為,因此,可以通過行為特征確定法益內(nèi)容。法條明確規(guī)定本罪的行為是“以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因此,本罪的法益是勞動者的財產(chǎn)權(quán),其具體內(nèi)容通過行為對象“勞動報酬”體現(xiàn)出來。
(二)行為對象:勞動報酬
勞動報酬是勞動者付出體力或腦力勞動所得的對價。很顯然,按照《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規(guī)定,勞動者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的報酬,是“勞動報酬”。具體包括兩部分:一是工資。是指用人單位依據(jù)國家有關(guān)規(guī)定或勞動合同的約定,以貨幣形式直接支付給本單位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但是不排除約定支付實物報酬),一般包括計時工資、計件工資、獎金、津貼和補貼、延長工作時間的工資報酬以及特殊情況下支付的工資等。二是各種依法應(yīng)由用人單位繳納的社會保險。根據(jù)我國《勞動法》與《社會保險法》有關(guān)規(guī)定,國家建立基本養(yǎng)老保險、基本醫(y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yè)保險、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險制度,基本養(yǎng)老保險、基本醫(yī)療保險、失業(yè)保險由用人單位與職工即勞動者按照國家規(guī)定共同繳納,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由用人單位繳納、職工即勞動者不繳納。繳納社會保險是用人單位的法定義務(wù),以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傷、失業(yè)、生育等情況下依法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zhì)幫助的權(quán)利,依法由用人單位繳納的社會保險理應(yīng)屬于“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所規(guī)定的“勞動報酬”的范疇。
然而,是否可以反過來說:“‘勞動報酬’,是指勞動者按照《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規(guī)定,通過自己的勞動而獲得的報酬”[1]呢?對此,需要判斷的是:能否將本罪中的勞動報酬限制在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依《勞動法》與《勞動合同法》而形成的勞動關(guān)系之中,而把勞動者與用人單位或雇主之間依照民事法律而形成的勞務(wù)關(guān)系或雇傭關(guān)系排除在本條適用之外?
本文認為,勞務(wù)關(guān)系同樣為本條所規(guī)制,其中,勞動報酬為勞務(wù)合同所直接約定的金額。首先,只要勞動力成為商品,就會在勞動者與用工單位或雇主之間形成勞動關(guān)系或勞務(wù)關(guān)系;對于勞動者而言,勞動關(guān)系與勞務(wù)關(guān)系的區(qū)別沒有實質(zhì)性的意義,無論怎樣,勞動者都有獲得對價性的勞動報酬的權(quán)利。只要勞動者履行了約定了的勞動義務(wù)卻沒有獲得勞動報酬的,那么就是對勞動者權(quán)利的侵犯。從實質(zhì)違法性的角度上看,勞動關(guān)系與勞務(wù)關(guān)系的區(qū)別并不影響違法性。其次,從語義上講,無論是勞動關(guān)系中的勞動者,還是勞務(wù)關(guān)系中的勞動者,都為本條所使用的“勞動者”這一法定概念所涵攝,沒有足夠的理由不得進行縮小解釋。最后,在實務(wù)中,在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發(fā)生糾紛的情況下,究竟是勞動糾紛還是勞務(wù)糾紛,區(qū)別起來具有相對性與隨意性。對于相同的案件,在不同地區(qū)、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手中,得出的結(jié)論也不盡相同,因此,若對“勞動者”進行縮小解釋,不僅不利于保護法益,而且不利于本罪的司法適用。例如,若采取縮小解釋,則在某拖欠工資的案件中,如果勞動行政部門認為是勞動糾紛的,行為人就可能成立本罪;如果勞動行政部門不認為是勞動糾紛而是勞務(wù)糾紛的,行為人就不可能成立本罪。很顯然,將行為的違法性取決于第三方的主觀認識的做法絕非妥當(dāng)。可見,對本罪中的“勞動者”不能進行縮小解釋,而只能是將勞務(wù)關(guān)系中的勞動者涵攝于其中。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勞動力成為商品,才會發(fā)生勞動報酬。勞動報酬乃基于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的合意以及法律強制性的規(guī)定而最終形成的具有對價性的財產(chǎn)性利益。發(fā)生在勞動過程中的應(yīng)由用人單位支付給勞動者的各種經(jīng)濟補償金、賠償金,不屬于“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中的勞動報酬。
二、實行行為
從文義上看,本罪的實行行為包括兩種,一是“以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數(shù)額較大的行為”,二是“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數(shù)額較大的行為”,二者的共同點在于“不支付勞動報酬”。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之外的方法是指與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性質(zhì)相同的方法,如無償將財產(chǎn)贈與他人、以明顯的低價轉(zhuǎn)讓財產(chǎn)等。“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中的“支付能力”應(yīng)該以公安機關(guān)立案時為準(zhǔn),如果立案時行為人有支付能力而不支付的,以第二種實行行為定罪處罰;如果在立案時行為人沒有支付能力的,則需要調(diào)查其沒有支付能力的原因,如果行為人實施了“以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勞動報酬的行為,則以第一種實行行為定罪處罰。反之,不是犯罪。
學(xué)界有力觀點認為,兩種行為類型中,“后者可以包含前者”;行為的內(nèi)容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由于本罪行為的實質(zhì)是不履行支付勞動報酬的義務(wù),屬于不作為犯,所以,上述兩種行為類型,都以行為人有支付能力為前提。轉(zhuǎn)移財產(chǎn)時,已經(jīng)表明行為人具有支付能力;行為人沒有支付能力而逃匿的,不可能成立本罪。”[2]
但是,如果后者可以包含前者,前者的言下之意也是“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者勞動報酬”的話,那么刑法規(guī)定“以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就沒有實際意義了。刑法將二者并列規(guī)定,說明二者并非處于包含關(guān)系,至少是應(yīng)該有所區(qū)別的。如果說本罪行為的實質(zhì)是不履行支付勞動報酬的義務(wù),屬于不作為犯,那么刑法只是單純處罰“欠薪不支付”行為。可是,為什么不用刑法規(guī)制其他民事領(lǐng)域中的“欠賬不還”呢?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是:行為人“拒不支付勞動者勞動報酬”的行為包括詐騙勞務(wù)的情況嗎?本文認為,不支付勞動者勞動報酬僅僅是法益受到侵犯的直接表現(xiàn),并非行為的實質(zhì);本罪的行為實質(zhì)包括兩方面的內(nèi)容,一方面是詐騙勞務(wù),另一方面是單純的欠薪不支付。具體理由如下:
從結(jié)果無價值論的立場來看,本罪的處罰根據(jù)在于“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未能得到支付”;從“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未能得到支付”這一結(jié)果出發(fā),追溯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幾種情形:1、在簽訂、履行勞動合同(或勞務(wù)合同)過程中,行為人隱瞞沒有支付勞動報酬能力的事實或掩飾內(nèi)心不支付勞動報酬的真實想法,在應(yīng)該支付勞動報酬時不支付的;2、雖然在簽訂、履行勞動合同(或勞務(wù)合同)過程中,有支付勞動報酬能力或者支付勞動報酬的意思,但是在應(yīng)該支付勞動報酬時,行為人產(chǎn)生不支付勞動報酬的意思而不支付的;3、雖然在簽訂、履行勞動合同(或勞務(wù)合同)過程中,有支付勞動報酬能力或者支付勞動報酬的意思,但是在應(yīng)該支付勞動報酬時,因為意外事件、經(jīng)營原因等,行為人雖有支付意思但因失去支付能力而不能支付的。
第3種情形中的行為,顯然不能作為犯罪;第1種情形中的行為其實就是詐騙行為,依法完全可以按照詐騙罪、合同詐騙罪的有關(guān)規(guī)定進行處理;第2種情形中的行為,雖然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是從刑法的謙抑性來看,很難說具有使用刑法規(guī)制的必要性。
(一)立法之所以將詐騙勞務(wù)行為納入本罪規(guī)制,是因為在證據(jù)上難以認定成立(合同)詐騙罪。
從證據(jù)的角度看,行為人是否實施了“隱瞞沒有支付勞動報酬能力的事實”容易查證,但是行為人是否實施了“隱瞞或者掩飾不支付勞動報酬的真實想法”則不然,因為“不支付勞動報酬的真實想法”藏于行為人的內(nèi)心,如何收集證據(jù)材料證明勞動者因為被騙而付出勞動,委實困難。而且,實務(wù)中發(fā)生的詐騙勞務(wù)行為,更多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因此,很難收集到足夠充分的證據(jù)將詐騙勞務(wù)行為以詐騙罪定罪處罰。如果說勞動合同、勞務(wù)合同也屬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那么發(fā)生在簽訂、履行勞動合同、勞務(wù)合同過程中的,以特定方法實施的詐騙勞務(wù)行為完全可以按照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理,如行為人接受勞動者的勞動后,不按照約定支付勞動報酬,反而逃匿的,就成立合同詐騙罪。成立詐騙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由于我國司法實踐通常將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為目的”理解為“不歸還”的意思,而實施詐騙勞務(wù)的行為人通常只有“拖欠勞動報酬的意思”,即使主觀上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意思”的,也會在外觀上表現(xiàn)為“拖欠勞動報酬的意思”,從而否定成立詐騙罪必須具備的“非法占有為目的”的主觀要件。因此,雖然在《修正案(八)》規(guī)定“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之前,理論界一再呼吁以“詐騙罪、合同詐騙罪”規(guī)制“惡意欠薪”行為,但是司法實踐基本上沒有采納這種主張,而是求助于立法。
(二)立法之所以將拖欠勞動報酬的行為納入刑法規(guī)制,是因為“拖欠勞動報酬”很難與“詐騙勞務(wù)”相區(qū)別。
就第2種情形而言,從外國立法例來看,只有極少數(shù)國家或地區(qū)處罰單純拖欠工資的行為,比如韓國、俄羅斯等。這是因為單純的拖欠工資的行為的違法性相對較低,難以達到值得科處刑罰的程度。
但是,很難從證據(jù)上把第2種行為與成立詐騙罪或合同詐騙罪的第1種行為加以區(qū)別。將第1種情形中的詐騙行為與第2種情形中的單純拖欠工資行為加以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二者最關(guān)鍵的區(qū)別其實在于“不支付勞動報酬的意思”的產(chǎn)生時間。在接受勞動者勞務(wù)后或支付勞動報酬時才產(chǎn)生“不支付勞動報酬的意思”的是單純拖欠勞動報酬;其余的,只要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勞動合同(或勞務(wù)合同)過程中,產(chǎn)生“不支付勞動報酬意思”,并對此加以隱瞞的,就可以評價為“隱瞞或者掩飾不支付勞動報酬的真實想法”的詐騙行為。然而,現(xiàn)實中大量的“拖欠勞動者勞動報酬拒不支付”的行為,又有幾個是在支付勞動報酬時才產(chǎn)生“不支付勞動報酬的意思”、才產(chǎn)生“非法占有為目的”的呢?況且,無論是詐騙勞務(wù),還是惡意拖欠勞動報酬,所發(fā)生的法益侵害結(jié)果都是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沒有被支付。因此,第二種情形中的行為不是不可罰,而是如何處罰的問題。
但是,若將二者同等對待,則又打擊面過寬,違背刑法謙抑性原理,不利于保護人權(quán)。為此,《修正案(八)》除了在罪狀的設(shè)置上,將上述兩種情形均納入刑法規(guī)制范圍之外,還通過規(guī)定“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這一可罰性條件以限制處罰范圍,下面將就此作進一步分析。
三、“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的性質(zhì)與內(nèi)容
(一)“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的性質(zhì):作為罪責(zé)擴張事由的“客觀超過要素”與作為刑罰限制事由的“客觀處罰條件”。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規(guī)定,“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或者以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情節(jié)惡劣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嚴(yán)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我們發(fā)現(xiàn),在罪狀的表述上,正式通過的法條作了三處修改,一是把“以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調(diào)整到“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之前;二是將草案中的“情節(jié)惡劣”修改為“數(shù)額較大”;三是增加了“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這一規(guī)定。修改一只是形式上的表述有別,沒有實質(zhì)上的意義;修改二充分考慮到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是侵犯財產(chǎn)罪,其法益是“財產(chǎn)性利益”的本質(zhì)特征,這樣規(guī)定有助于正確地認定犯罪;如何理解修改三即所增加的“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的性質(zhì)及其內(nèi)容,可能存在爭議。
最有可能的見解是將其視為成立犯罪的最后一個客觀要件,而且是認定犯罪既遂的標(biāo)準(zhǔn)。但是,這種理解存在問題。一方面,從法益保護的角度看,本罪的行為對象是“勞動者應(yīng)該獲得的勞動報酬”,從法理上看,只要行為人在依照約定應(yīng)該支付勞動報酬而不支付的,就已經(jīng)發(fā)生了法益侵害結(jié)果,行為就已經(jīng)既遂,因此,將其視為犯罪既遂的標(biāo)準(zhǔn),延遲了既遂的成立時間。在行為人詐騙勞動者勞動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在前面分析本罪實行行為的過程中,已經(jīng)論證了本罪的實行行為的本體是發(fā)生在簽訂、履行勞動合同(或勞務(wù)合同)過程中的詐騙勞務(wù)行為。根據(jù)認定詐騙罪的有關(guān)法理,只要勞動者因為被騙而付出具有對價性財產(chǎn)利益為內(nèi)容的勞動時,行為人的行為就已經(jīng)成立犯罪,因此,將其視為成立犯罪的客觀要件,并不妥當(dāng)。
本文認為,根據(jù)前述本罪的實行行為所包含的兩種具體情形,作如下理解更為妥當(dāng):
第一,行為人雖然在簽訂勞動合同(或勞務(wù)合同)、接受勞動者勞動時,有支付勞動報酬能力或者支付勞動報酬的意思,但是在應(yīng)該支付勞動報酬時,才產(chǎn)生不支付勞動報酬的意思的,“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是“客觀的超過要素”,在犯罪構(gòu)成中起的作用是“使違法性的程度達到值得科處刑罰的程度。”[3]換言之,在這種場合下,行為人單純的逃避支付勞動報酬或有能力而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雖然數(shù)額較大,但是并沒有達到值得科處刑罰的程度。為此,刑法規(guī)定這一“客觀的超過要素”,目的在于提高行為的違法性程度,從而賦予這種行為的刑事可罰性。
在這種場合下,承認“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是“客觀的超過要素”的意義在于:將其視為提高違法性程度的罪責(zé)擴張事由,不僅可以削減人們提出的“刑法過分?jǐn)U張到民事領(lǐng)域”的質(zhì)疑,而且通過增設(shè)提高違法性程度的“客觀的超過要素”,立法在實質(zhì)上將沒有達到科處刑罰程度的“惡意拖欠勞動報酬”行為予以刑法規(guī)制,擴大了刑罰適用的范圍,但在實際效果上起到了限制處罰范圍的作用。
第二,在行為人簽訂勞動合同(或勞務(wù)合同)、接受勞動者勞動時,隱瞞沒有支付勞動報酬能力或掩飾不支付勞動報酬意思的情況,行為人“以轉(zhuǎn)移財產(chǎn)或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報酬”,數(shù)額較大的,行為本來成立詐騙罪或合同詐騙罪,此時,“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是客觀處罰條件。[4]
“客觀處罰條件”這一提法源自大陸刑法理論。日本刑法學(xué)說認為,如果有犯罪,原則上對犯罪人產(chǎn)生了刑罰權(quán),但有時候,在犯罪事實之外,發(fā)動刑罰權(quán)例外地以存在其他它外部事實為條件。這種事實就是客觀處罰條件。[5]德國刑法理論有著與其相同的表述,“應(yīng)受處罰性的客觀條件,是指這樣一些情況,它們與行為直接相關(guān),但既不屬于不法構(gòu)成要件也不屬于責(zé)任構(gòu)成要件。”[6]可見,在三階層犯罪論體系下,客觀處罰條件只有行為已經(jīng)具備了構(gòu)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有責(zé)性,即已經(jīng)成立犯罪的前提下才有存在的余地。[7]因此,客觀處罰條件不是構(gòu)成要件的要素,其是否存在既不影響違法性,也不影響有責(zé)性。
在這種場合下,將“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視為客觀處罰條件的意義在于:
對已經(jīng)成立詐騙罪或合同詐騙罪既遂的行為給予的刑事政策上的寬恕,只有具備“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這一客觀處罰條件的,才發(fā)動刑罰權(quán);如果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分責(zé)令支付之后支付了的,則不發(fā)動刑罰權(quán),從這一點上講,與作為“罪責(zé)擴張事由”的“客觀的超過要素”不同,客觀處罰條件是“刑罰限制事由”;對于犯罪人而言,這一處罰條件不是“惡”的條件,而是為其架上的一座改過的“金橋”。
然而,無論“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是作為“刑罰擴張事由”的“客觀的超過要素”,還是作為“刑罰限制事由”的“客觀處罰條件”,最終都在事實上限制了本罪的處罰范圍,“這有助于保護勞動者權(quán)益,又縮小了打擊面,平衡了兩方的利益。”[8]不僅如此,由于設(shè)置了這一可罰性條件,使本罪比依照詐騙罪或合同詐騙罪規(guī)制詐騙勞務(wù)行為更具有可操作性,充分發(fā)揮了立法智慧。
(二)“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具體內(nèi)容
1.政府有關(guān)部門的外延
在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形成勞動關(guān)系的情況下,根據(jù)《勞動法》第91條規(guī)定,用人單位“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工資的;拒不支付勞動者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報酬的;低于當(dāng)?shù)刈畹凸べY標(biāo)準(zhǔn)支付勞動者工資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zé)令支付勞動者的工資報酬、經(jīng)濟補償,并可以責(zé)令支付賠償金。根據(jù)《社會保險法》的有關(guān)規(guī)定,社會保險由社會保險經(jīng)辦機構(gòu)征收。用人單位不辦理社會保險登記的,由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責(zé)令限期改正;用人單位未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由社會保險費征收機構(gòu)責(zé)令其限期繳納或者補足。因此,“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中的“政府有關(guān)部門”是指勞動行政部門、社會保險行政部門以及社會保險費征收機構(gòu)。
在雇主(包括用人單位與自然人)與勞動者形成勞務(wù)關(guān)系的情況下,雙方之間形成民事法律關(guān)系而非勞動法律關(guān)系,受民事法律而非勞動法律調(diào)整。若雇主以轉(zhuǎn)移財產(chǎn)或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報酬,或者有支付能力而不支付勞動報酬的,沒有“責(zé)令支付勞動報酬”的法定專門機構(gòu)。由于勞動關(guān)系與勞務(wù)關(guān)系很難區(qū)別,即使是勞動行政部門越權(quán)對本屬于勞務(wù)關(guān)系中的雇主作出“責(zé)令支付勞動報酬”的決定,雇主仍不支付的,也可依法立案追訴。勞動者也可能訴求政府,若政府作出責(zé)令支付決定,而不支付的,也有成立本罪的余地。
2.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含義
責(zé)令支付應(yīng)該由政府有關(guān)部門調(diào)查事實之后,以書面的形式作出,是其依法行政的重要內(nèi)容。“仍不支付”意味著行為人在收到責(zé)令其支付勞動報酬的決定后,不按照決定的期限、條件、標(biāo)準(zhǔn),履行支付勞動報酬的義務(wù)。“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原則上要求行為人收到了支付令。只要在規(guī)定的期限內(nèi),行為人沒有足額支付的,公安機關(guān)就應(yīng)該依法立案追究其刑事責(zé)任。
需要思考的,如果行為人逃匿,導(dǎo)致事實上政府有關(guān)部門的支付令無法送達行為人的,‘是否屬于“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呢?本文對此持肯定態(tài)度。因為“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作為“客觀的超過要素”或“客觀的處罰條件”不要求行為人在實施本罪的實行行為時,對其有故意或者過失,但是行為人是知道或者應(yīng)該知道政府有關(guān)部門對“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具有重大監(jiān)管職責(zé)的,若其逃匿支付勞動報酬,政府有關(guān)部門一定會調(diào)查事實,作出責(zé)令其支付勞動報酬的決定,因此,因為行為人逃匿,而事實上導(dǎo)致責(zé)令支付勞動報酬的決定無法送達的,也是“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仍不支付”。
四、本罪與他罪的關(guān)系
(一)本罪與搶劫罪不存在法條競合關(guān)系
搶劫罪中的“暴力、脅迫”方法是否本罪中“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之外的其它“逃避支付勞動報酬”的方法呢?如果勞動報酬作為財產(chǎn)性利益是搶劫罪的行為對象,而且搶劫罪中的“暴力、脅迫”方法是本罪中“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之外的“逃避支付勞動報酬”的方法,那么本罪與搶劫罪之間存在法條競合關(guān)系。
現(xiàn)代刑法無論是立法、理論還是實踐均承認財產(chǎn)性利益是侵犯財產(chǎn)罪所保護的對象,如日本刑法第236條第二項規(guī)定,以暴行或者脅迫方法取得財產(chǎn)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的,成立搶劫財產(chǎn)性利益罪。所謂財產(chǎn)性利益,大體是指普遍(狹義)財物以外的財產(chǎn)上的利益,包括積極財產(chǎn)的增加與消極財產(chǎn)的減少。[9]取得財產(chǎn)性利益的方法,主要存在三種情況,一是使對方負擔(dān)債務(wù);二是使自己免除債務(wù)(包括延期履行債務(wù));三是接受別人提供的勞務(wù)。[10]雖然后一種情形即勞務(wù)是否屬于財產(chǎn)性利益,存在爭議,[11]但在“約定了對價的勞務(wù)是財產(chǎn)性利益”這一點上并無爭議。勞動報酬體現(xiàn)的不僅僅是具有對價的勞務(wù),而且是用人單位或雇主與勞動者之間,基于勞動合同或者勞務(wù)合同而發(fā)生的債,對于用人單位而言,應(yīng)該支付的勞動報酬是債務(wù),對于勞動者而言,應(yīng)該獲得的勞動報酬是債權(quán),因此,勞動報酬是財產(chǎn)性利益。既然財產(chǎn)性利益是侵犯財產(chǎn)罪的行為對象,那么勞動報酬也是侵犯財產(chǎn)罪的行為對象。而搶劫罪是侵犯財產(chǎn)罪中最嚴(yán)重的犯罪,因此,勞動報酬也是搶劫罪的行為對象。
既然勞動報酬是搶劫罪的行為對象,那么在以下情形中:①勞動者因為受到暴力或者脅迫,當(dāng)場免除了行為人支付勞動報酬的義務(wù)或者事實上因之而不再繼續(xù)行使索要權(quán),政府有關(guān)部門沒有作出責(zé)令支付的決定的;②勞動者因為受到暴力或者脅迫,當(dāng)場免除了行為人支付勞動報酬的義務(wù)或者事實上因之而不再繼續(xù)行使索要權(quán),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作出責(zé)令支付的決定后,行為人仍不支付的;③勞動者因為受到暴力或者脅迫,當(dāng)場免除了行為人支付勞動報酬的義務(wù)或者事實上不再繼續(xù)行使索要權(quán),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作出責(zé)令支付的決定后,行為人支付了的;④勞動者雖然受到暴力或者脅迫,但是并沒有免除行為人的支付義務(wù),而是繼續(xù)索要,并由政府有關(guān)部門作出了責(zé)令支付的決定,行為人仍不支付的;⑤勞動者雖然受到暴力或者脅迫,但是并沒有免除行為人的支付義務(wù),而是繼續(xù)索要,并由政府有關(guān)部門作出了責(zé)令支付的決定,行為人支付了的。在上述情形中,假設(shè)行為人使用暴力,但沒有造成勞動者輕傷及以上后果,則①②成立搶劫罪既遂,依法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③成立搶劫罪既遂,行為人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后支付的,可以視為“退贓”,作為酌定量刑情節(jié)加以考慮,但仍然判處年3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④搶劫罪未遂;⑤成立搶劫罪未遂,行為人經(jīng)責(zé)令支付后支付的,可以作為酌定量刑情節(jié)予以考慮。
假如搶劫罪中的“暴力、脅迫”方法是本罪中“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之外的“逃避支付勞動報酬”的方法,則只有②④成立本罪,其它三種情形均不成立犯罪,若比較法益侵犯的程度,第①與第②完全相同,不同之處僅在于后者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之后仍不支付。將是否作為犯罪處理、是否發(fā)動刑罰權(quán),完全決定于非實行行為的可罰性條件是否具備,顯然不妥當(dāng)。然而,若僅僅因為我國刑法規(guī)定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①③就由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重罪成為了無罪;④中的搶劫未遂成立了犯罪,而①中的搶劫既遂反而成為了無罪。這種解釋結(jié)論實在無法使人信服、讓人接受。更何況,搶劫罪中的“暴力”方法,包括殺人、傷害的方法,在造成勞動者輕傷及以上后果的情況下,上述情形均成立搶劫罪既遂,尤其是在殺人、重傷的場合下,絕非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所能評價的了的。[12]
因此,從罪刑均衡的角度看,搶劫罪中的“暴力、脅迫”方法不是本罪中“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之外的“逃避支付勞動報酬”的方法。即使單純從語義上分析,也能得出同樣的結(jié)論。
刑法明確規(guī)定了“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兩種“逃避”支付勞動報酬的方法,這兩種方法之外的方法只能是與之類似的方法。[13]這種類似性或相同性體現(xiàn)在何處呢?“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將“逃避支付”與“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并列規(guī)定,說明二者存在根本性的區(qū)別,這種區(qū)別只能是后者是有支付能力的,而前者未必有支付能力,而如何查證行為人是否有支付能力,顯然是存在難度的。對于前者,需要追究其沒有支付能力的原因,如果是因為經(jīng)營本身的原因如經(jīng)營不善導(dǎo)致破產(chǎn)而失去支付能力的,顯然不能作為犯罪處理,為此,刑法只處罰那些逃避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轉(zhuǎn)移財產(chǎn)”是使自身減少或失去支付能力的逃避行為,與之具有相同性質(zhì)的行為應(yīng)該在“減少或失去支付能力”上尋找,如無償將財產(chǎn)贈與他人、以明顯的低價轉(zhuǎn)讓財產(chǎn)、編造虛假的債務(wù)就屬此類。“逃匿”是使勞動者無法行使索要權(quán)的行為,但是“逃匿”行為不針對其它任何對象,更不侵害勞動報酬之外的其他任何法益,從這一點上看,與“逃匿”性質(zhì)相同的其他行為如變換辦公場所、使用保安不讓勞動者進入等屬于其他逃避支付勞動報酬的方法。無論是“轉(zhuǎn)移財產(chǎn)”,還是“逃匿”,作為“逃避支付勞動報酬”的方法行為,都沒有使勞動者對勞動報酬本身作出處分。
而搶劫罪中的“暴力、脅迫”達到了“足以抑制勞動者反抗的程度”,在使用暴力、造成勞動者輕傷以上后果的情況下,行為的嚴(yán)重性質(zhì)遠非“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所能比較,也是“逃避支付”所不能評價的;無論是勞動者因為遭受“暴力、脅迫”而免除行為人支付勞動報酬義務(wù),還是不索要勞動報酬,都使勞動者對勞動報酬作出了處分。既然如此,搶劫罪中的暴力、脅迫,又怎么能評價為“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之外的“逃避支付勞動報酬”的方法呢?
同樣的道理,因為“利益詐騙罪、敲詐勒索利益罪中,被害人如果沒有處分財產(chǎn)性利益的行為,如只要不作出免除債務(wù)的意思表示,就不成立既遂”,[14]所以敲詐勒索罪中的“威脅方法”,[15]詐騙罪中的“詐術(shù)”,都不是本罪中的“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之外的“逃避支付勞動報酬”的方法。
總之,搶劫罪中的“暴力、脅迫”方法不屬于本罪中“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之外的“逃避支付勞動報酬”的方法,本罪與搶劫罪之間不存在法條競合關(guān)系。上述5種情形中,如果行為人使用暴力,造成被害人輕傷以上后果的,都成立搶劫罪既遂;若沒有造成輕傷后果的,則①②③成立搶劫罪既遂,第④⑤成立搶劫罪的未遂。
(二)本罪與詐騙罪或合同詐騙罪的競合之處理
本罪與詐騙罪或合同詐騙罪的法條競合關(guān)系可能存在兩種情形,一是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勞動合同或者勞務(wù)合同過程中,隱瞞沒有支付勞動報酬能力的事實或者掩飾不支付勞動報酬的意思即實施詐騙行為,使勞動者陷入錯誤,履行勞動義務(wù),沒有獲得勞動報酬的;二是行為人在應(yīng)該支付勞動報酬時,使用詐騙方法,使勞動者免除其支付勞動報酬義務(wù)的。
就第一種情形而言,根據(jù)前文中的有關(guān)分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已經(jīng)包含了第一種情形,即本罪與詐騙罪、合同詐騙罪之間存在法條競合關(guān)系,在這種情況下,應(yīng)適用特殊法條優(yōu)于普通法條的原則,將所有詐騙勞務(wù)的行為均按“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定罪處罰。第二種情形涉及到問題是,“使用詐騙方法使勞動者免除其支付勞動報酬義務(wù)”是否屬于本罪中的“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之外的其他“逃避支付勞動者勞動報酬”的行為。換言之,“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等方法”是否包含了“詐騙方法”,以及“使勞動者免除支付勞動報酬”是否可以評價為“逃避支付勞動者勞動報酬”。前文已經(jīng)從語義上論及“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之外的逃避支付勞動報酬方法”不包含“詐騙方法”,在此不再贅述。因此,“使用詐騙方法使勞動者免除其支付勞動報酬義務(wù)的”,即使經(jīng)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責(zé)令支付后又支付了的,也成立詐騙罪。
【注釋】 [1]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guān)規(guī)定》,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頁。 [2]張明楷:《刑法學(xué)》(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12頁。 [3]“客觀的超過要素”的理論為張明楷教授所首倡。參見張明楷:《犯罪構(gòu)成體系與構(gòu)成要件要素》,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第227頁。 [4]在德國,則有純正(真正)的客觀處罰條件與不純正的客觀處罰條件二分說的提法。(參見[德]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總論),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667 - 669頁。)周光權(quán)教授認為“客觀的超過要素”的實質(zhì)是“內(nèi)在的客觀處罰條件(不純正的客觀處罰條件)”。(參見周光權(quán):《論內(nèi)在的客觀處罰條件》,載《法學(xué)研究》2010年第6期,第125頁。)本文同意周光權(quán)教授的這一見解,但是采取二分說恐怕會引起概念上的混淆,不如直接將刑法中的可罰性條件劃分為“客觀的超過要素”與“客觀的處罰條件”。 [5]大谷實:《刑法講義総論(新版第三版)》,成文堂2009年版,第510頁。 [6]前引[4],耶賽克,魏根特書,第667頁。 [7]前引[4],耶賽克,魏根特書,第667頁。 [8]周光權(quán):《刑法修正案(八)的深度解讀》,《中國司法》2011年第5期,第44頁。 [9]張明楷:《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研究》,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頁。 [10][日]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第4版),束京大學(xué)出版會2007年版,第182頁。 [11]詳見劉明祥:《財產(chǎn)罪比較研究》,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頁。 [12]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方面認為搶劫罪中的“暴力、脅迫”方法屬于本罪中“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匿”之外的其它“逃避支付勞動報酬”的方法,另一方面又依想象競合的理論,以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則只能證明搶劫罪中的“暴力、脅迫”方法不是本罪中的其它“逃避支付勞動報酬”的方法。 [13]]此處,刑法采取“例示法”把概括條款與個案列舉相結(jié)合,“只針對犯罪的‘特殊重大情形’舉出一些例子,并且賦予法官對此類的或類似的案件同樣課以刑罰之任務(wù)。”而對于罪狀含義,則需借助類比解釋的方法加以揭示。(參見[德]亞圖·考夫曼:《類推與“事物本質(zhì)”:兼論類型理論》,吳從周譯,臺北學(xué)林文化事業(yè)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63頁。) [14][日]大谷實:《刑法講義各論》(新版第2版),黎宏譯,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頁。 [15]如果行為人敲詐勒索勞動者勞動報酬,使行為人陷入恐懼,免除或者事實上不索要勞動報酬的,成立敲詐勒索罪。未得逞的,成立敲詐勒索罪的未遂。

.jpg)
劃研究.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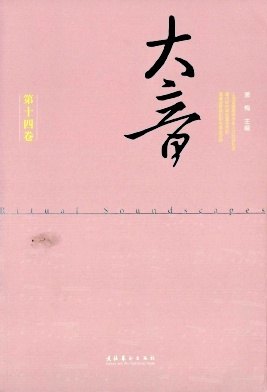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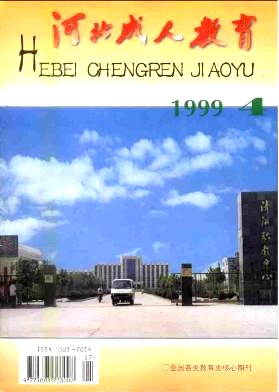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