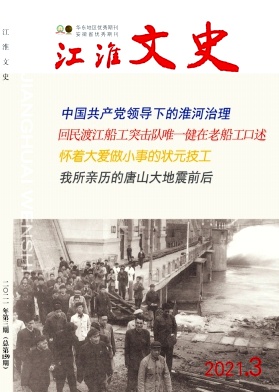外燥與氣象醫學研究探析
佚名
作者:丁建中, 張六通, 邱幸凡
【關鍵詞】 外燥
摘要:六淫燥邪及外燥的文獻零散且研究進展甚微。從外燥與季節、氣候并結合現代氣象醫學研究進展,提出對外燥的研究應包括:重視對外燥與氣象醫學理論文獻的收集整理,探索建立外燥病邪的季節、“溫度濕度”量化指標的動物模型,以闡析外燥致病機理。
關鍵詞:外燥; 氣象醫學
Theoretical Studies for the Outerdry in Weather Medicine
Abstract:The documents and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about the dry and the outerdry were rare.The outerdry of the season and weather and geography were reviwed primarily in the article.The suggestion for the dry(outerdry)should consist to arrange and collect of the documents,establish the animal quantitative model about the season,temperature and moisture,and study the mechanisms of the model.
Key words:Outerdry; Weather medicine
近年來從氣象因素、生物致病因子和機體反應性等綜合研究六淫風、寒、濕、火(熱)等病邪,結果顯示確有其物質基礎并取得一定進展,有的已達分子水平[1]。燥邪致病,《內經》罕有記載,但自喻嘉言著《醫門法津?秋燥論》后,秋傷于燥才漸被公認。燥邪分內燥、外燥,內燥不為六淫之燥氣所感。本文對外燥與季節氣候、并結合現代氣象醫學研究等提出燥邪現代研究之寓意。
1 外燥與季節、氣候
《素問?天元紀大論》《素問?五運行大論》《素問?六微旨大論》《素問?氣交變大論》《素問?五常政大論》《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素問?至真要大論》等七篇論及自然界氣候變化可作為致病因素,甲子說、子午流注說、五運推導說、六氣演變論等,意在探討氣象氣候以及時間變化與醫學科學的關系。“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憂思恐”,實際上把天地之間的四時六氣,與人體內部的五臟活動聯成一體,外則四時六氣之變化,內則陰陽氣血運行于五臟六腑之間,動中變化以致產生四時六氣以養萬物;內在的陰陽營衛氣血運行,五十度而復大會,動之不己。“成敗倚伏生于動,動而不己則變作矣”。(《素問?六微旨大論》)運氣學說強調四時六氣的恒動性,如太過或與之不及乃疾生之根[2]。中國古代的氣候學知識曾領先世界,《呂氏春秋?十二紀》之時的《孟秋紀》中寫道:“行之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谷,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所復還,五谷不實。行夏令,則多水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這一段首先記載了這個月(即秋季第一月)的主要氣候特點是“涼風至”,如行夏令,即維持夏季炎熱多雨的氣候,就會蚊蠅孳生,瘧疾蔓延……。古有風、熱、暑、濕、燥、寒“六氣分治”之說[3]。以五運而言,四運金“在天為燥”,《素問?天元紀大論》為年中白露至立冬;以六氣而言,“陽明司天,其化以燥”,(《素問?至真要大論》)是從秋分至小雪,主氣為陽明燥金,客氣為厥陰風木。“一交秋分,燥金司令,所起之風,全是一團燥烈之氣,干而不潤。是以無草不黃,無木不凋,人身應之,燥病生焉。凡有身熱咳嗽、內煩口干一切百病,無不起于干燥”。(《醫學傳燈?卷上》)“霧露數起,殺氣時來,草木不生蒼干,金乃有聲”。(《素問?六元正紀大論》)“金氣治之,燥之分也,燥熱在上……萬物窮燥”。(新刊《圖解素問要旨論》卷之三)漢、唐時代,困于《內經》病機十九條中未提及燥氣為病,直至金元,劉河間在《素問玄機原病式》中補充一條“諸澀枯涸,干勁皴揭,皆屬于燥”;明?李杲指出,燥有內、外之分而逐引重視。清?喻嘉言著《醫門法津》“秋燥”專論,更直言相諫”:“春月地氣動而濕勝,斯草木暢茂。秋月天氣肅而燥勝,斯草木黃落。故春分以后之濕,秋分以后之燥,各司其政。今指秋月之燥為溫,是必指夏月之熱為寒然后可,奈何《內經》病機一十九條,獨遺燥氣。他凡秋傷于燥,皆謂秋傷于濕,歷代諸賢,隨文作解,弗察其訛,昌特正之”(《醫門法津?秋燥論》)。以此確立秋燥病名。一般而言,若燥氣肅殺過盛,其表現以寒涼為主;燥氣不及,則從火化,即常令雖已進秋涼季節但仍炎熱不退,常喻此為“秋陽以曝”。“秋深初涼,西風肅殺,感之者,多病風燥,此屬燥涼,較嚴冬風寒為輕。若久晴無雨,秋陽以曝,感之者多病溫燥,此屬燥熱,較暮春風溫為重”(《重訂通俗傷寒論?第八章》)。在喻氏影響下,吳鞠通則明列秋燥為九種溫病之一。然四方四隅均可生燥氣,深秋氣溫驟降之涼未必就較初冬氣溫上升之風寒為暖,北方深秋之燥也遠較南方初冬之寒涼;西北燥證遍見于四時,非獨秋有,且多以涼燥為主,此情尤與東南方有異,“干旱則燥氣勝,干熱、干冷則燥氣亦勝”。《醫原》均指出燥邪的特點和形成與歲運及時令有關。
2 現代氣象醫學研究
地面接受太陽輻射能也隨著季節發生顯著的變化,是形成寒來暑往、春夏秋冬四季交替的根本原因。氣候學中把太陽輻射、下墊面和大氣環流作為氣候形成和變化的三個重要因子。太陽輻射是大氣的主要能源,下墊面則是能量接收、貯藏、轉化的主要場所。大氣環流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它顯著地影響到各地的氣候,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是一種氣候現象。人類活動對自然植被和大氣成分的影響日益加大而成為第四個重要因子,又是社會經濟系統之氣候系統的一個聯絡點。按熱量和水分狀況的綜合反應將中國氣候類型分為9個氣候帶。中國秋溫與春溫的差別大致以秦嶺淮河一線為界,此線以北(除沿海外)及西北地區一般春溫高于秋溫,原因是在秋季由于北方的冷空氣南下代替了濕潤溫暖的夏季風,因為空氣干燥、地面散熱較強,故氣溫迅速降低。以華北地區為例,9、10月夏季風急劇南撤和冬季風的迅速到來,許多情況下,秋季出現時間的遲早與強冷空氣向南爆發的遲早有關,正所謂“一陣秋風一陣寒”。干燥空氣造成毛發干燥和黏膜彈性降低、干裂,纖毛運動減少,黏膜分泌減少,血流減慢,吸進的空氣變熱,涼肅空氣則使毛細血管收縮,革蘭氏陽性細菌和流感病毒隨濕度與風速的減低而數量增加;空氣中陽離子過多時,特別是CO2分子(濃度達104~105個離子/cm3?s)可降低纖毛運動,減少黏液的轉運而致,咽干、頭痛;皮膚pH通常是4~6,若氣象因素改變皮膚pH值,常利于傳染病病原通過皮膚對人體的感染;空氣溫度、濕度影響黏膜的干燥程度(特別是鼻黏膜),其黏膜分泌減少,抗體含量降低,易于傳播疾病。高令山等報道127例外感者中燥咳15例,常見于9月下旬至11月中旬,特別是晚秋之時,成人和兒童哮喘發作厲害,似乎對風冷敏感。更見“老慢支”和秋燥皮膚瘙癢,提示秋季咳喘常伴感染和過敏之雙重病因。值得注意的是,肺并非單純的呼吸器官,還具有調節血液循環(朝百脈)、協助水液代謝(通調水道)及一套復雜的免疫防御功能(衛外)。正常成人每天約吸入空氣2 000 L,因此最容易遭遇到環境空氣中有害因子如微生物、塵埃、毒性氣體之侵襲。氣溶膠顆粒是環境空氣中有害物質,包括微生物的存在形式與載體,小于5 μm的顆粒可進入周圍氣道,由于氣流減慢并形成層流,顆粒因重力沉降作用而沉積于氣道黏膜表面的顆粒,可借助黏膜纖毛系統排出。支氣管黏膜中的黏液纖毛機械防御、細胞免疫、體液免疫功能是人體抵抗致病因素(因子)侵襲的主要屏障。實驗證實肺氣虛患者或動物鼻分泌物、唾液、氣管灌洗中細胞免疫及體液免疫功能下降,局部屏障功能受損,是衛外不固、反復上感的主要原因。采用五季平均水汽壓、平均相對濕度與月平均降水量三項指標對1986~1991年呼和浩特四季氣候的研究結果顯示,長夏主濕之論點符合當地情況,但卻冬季最“燥”,春季次之,秋季更次之[4]。有學者調查227名進入新疆沙漠腹地(彩南油田和火燒山油田)工作的石油工人的健康狀況。據火燒山氣象站資料,上述地區7月份平均氣溫25.7℃,最高氣溫36.9℃,月最小相對濕度11%,月定時最大風速10 m/s;該地域年干燥日數(相對濕度30%者)60~100 d,年干熱日(日最高氣溫35℃,對應日平均濕度30%者)10~27 d。采用臨床癥狀、生理機能、生化代謝、心理行為、精神情緒和作業能力等綜合指標,觀測在酷熱、干燥、風沙、以及空曠與寂寞等環境下作業的石油工人所出現的不適癥狀,并將31個燥癥狀按部位及臟腑屬性分為口、鼻、目、膚、二陰、肺等12類,再依其特性分為脾胃類、胸腎類、五官類和膚陰類。結果顯示,沙漠燥證不僅是人體對熱環境的病理反應,還涉及到多系統多臟器生理和病理變化,并與心理、精神障礙有關[5]。陰津是維持人體生命活動的重要物質。陰津的耗傷必然會導致組織細胞的功能受損,甚至形態結構的改變,之所謂“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機”。有學者提出急性傷陰過程可分為早期肺胃津傷和晚期肝腎陰傷,結合臨床上急性傷陰之證多伴有血清離子紊亂,設想肺胃津傷階段可能主要是以細胞外液損傷為主,肝腎陰傷階段主要是以細胞內外液共同損傷為特征[6]。
3 外燥與氣象醫學研究展望
后世論燥,或述其象,或述其性,其文又散在于少數名家精選病案之中,相比風、寒、濕等病證的研究深度而言更顯不足。至今未見對外燥致病機理的實驗研究及溫燥與涼燥的“溫度濕度空間”量化研究報道。建議對外燥的研究應包括:3.1 重視對外燥(邪)與氣象醫學理論文獻的收集與整理。應組織一定規模的協作力量,系統收集歷代名家對燥邪的論述并進行理論研究,這項基礎性工作將豐富六淫燥邪的學術內內涵。3.2 深入開展對外燥與氣象醫學在病機病證中的研究。臨床溫燥、涼燥之證尚不少見,但由于病例各異且醫家對此感悟不均,尤其是近年來缺乏有組織的對燥邪的較大規模的學術研討與臨床經驗之交流,使散在的研究或經驗難以形成系統的理論闡析和規范的治則。應積極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探索建立外燥病邪的季節、溫度、濕度等量化研究的動物模型,在此基礎上開展從細胞、分子甚至基因水平對燥邪之病理生理等方面的實驗研究,為釋析其病因病機提供科學的、客觀的依據。
[1] 張六通,梅家俊,黃志紅,等.外濕致病機理的實驗研究[J].中醫雜志,1999,40(8):496.
[2] 夏桂成.略論運氣學說基本精神及與婦產科學的關系[J].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3,19(1):5.
[3] 張啟明.五臟應四時四方的氣候變化證據[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04,10(2):67.
[4] 王 鼎,劉忠庶,王玉亭,等.從呼和浩特氣候變化論“四時五行”[J].內蒙古中醫藥,1994,13(2):34.
[5] 周銘心,陶培永.沙漠燥證初探[J].中醫雜志,1997,38(8):493.
[6] 仝小林,王 君,李 寧,等.增液湯對急性傷陰動物模型的細胞保護作用及其機理研究[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03,9(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