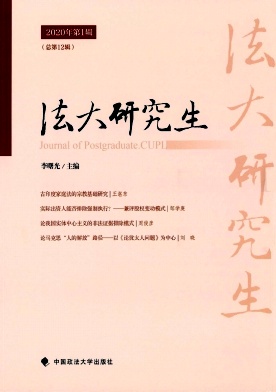無政府狀態下國際制度的效用
胡慧敏
[摘要]本文從無政府狀態兩種含義切入,分析在缺乏中央政府而導致強制力匱乏、國家迫于生存僅關注自身實力和相對獲益情況下,國際制度何以仍能得到遵守。國際體系并不缺少秩序,國際制度通過從意識形態上使秩序合法化、規范行為主體行為、促進行為主體間合作、提供解決爭端程序來塑造和維持國際秩序。
[關鍵詞]無政府狀態;國際制度;遵守;秩序
幾乎所有的國際政治理論都視無政府狀態為國際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無政府狀態的具體含義至少有兩種。一種含義是缺少政府,也就是缺乏有政治權威的中央政府,即華爾茲所說的國際政治中“缺乏全體系范疇的權威機構”和基歐漢認為的“世界政治中缺乏一個共同的政府”。〔1〕另一種含義是缺少秩序。秩序的匱乏意味著混亂與無序。本文認為,在因缺乏中央政府而導致強制力匱乏、國家迫于生存僅關注自身實力和相對獲益情況下,背叛、欺詐并未泛濫成災,國際制度〔2〕仍能得到遵守。國際體系并不缺少秩序,國際制度通過從意識形態上使秩序合法化、規范行為主體行為、促進行為主體間合作、提供解決爭端程序來塑造和維持國際秩序。
政府缺席背景下國際制度的遵守
就無政府狀態指缺少政府,即缺乏有政治權威的中央政府這一含義而言,無政府狀態并不具有積極或者消極的內涵,它未必暗指現在的世界秩序以普遍的混亂、動蕩為標志。主流國際關系理論都接受無政府狀態的預設,并將無政府狀態理解為缺少有政治權威的中央政府。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阿克塞爾羅德(RobertAxelrod)和基歐漢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個人或國家相信沒有機構可以實施規則,或制定和強制實施行為規則,或強制相互合作。〔3〕無政府狀態意味著世界政治中缺少中央機構來強制承諾實施。因而國際制度很難得到遵守。新現實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一樣,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意味著缺少共同的中央政府。然而,根據新現實主義的觀點,各個國家并不相信缺少共同的中央政府僅僅意味著沒有機構可以確保承諾的實施。新現實主義者強調,國家認識到,在無政府狀態下,沒有超級權威阻止其他國家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來破壞或奴役本國(著重號為作者所加)。〔4〕因而國家的核心利益是生存。阻止其他國家實現有利于它們的相對實力以及在合作中關注自身的相對獲益才是國家的真正目標。對于相對獲益的關注將減少國家合作的動機,背叛和欺詐行為屢見不鮮。
而事實上,國際制度在缺乏強制時仍然可以得到遵守。下面兩點則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一事實。
(一)缺少強制并非國際制度的致命傷
威克斯曼(JacobWerksman)有一句經典評論,“如果國際制度不能通過強制解決國家間爭端來履行國際義務,那么它將成為國際法律體系的惟一致命弱點(Achilles heel)”。〔5〕這些觀點有著共同的預設,沒有履行的契約是無效的契約,而履約依賴于強制,強制則依托政府。這一假設簡明直接,它暗示在世界政治中,因為強制的不存在,國際制度將因缺乏履行而歸于無效。但這一邏輯在世界政治中并不完全適用。現實世界中,制度的有效性可以不依賴于遵守,強制未必是遵守的必要條件,沒有世界政府也能產生強制力。
第一,并非所有制度的有效性都依賴于遵守。奧蘭·楊以執行的任務和發揮的功能為標準對國際制度進行分類,以此闡明制度形成過程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和制度形成后的有效性問題。他將國際制度分為四種:規則型制度(regulatoryregimes)、程序型制度(pro ceduralregimes)、項目型制度(programmaticregimes)、創生型制度(generativeregimes)。遵守只有在規則型制度中才成為中心議題,并非其它類型制度的主要關注點。例如,程序型制度重視國際制度產生集體選擇的能力,對項目型制度的挑戰則在于建立組織機構實現共同目標和創造所需資源。即便是以遵守為中心的規則型制度,也存在違反容忍度,并非所有的規則型制度一遭違反立刻失效。規則型制度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違反和欺詐(不同制度在這一程度上存在差別),而不會危及制度社會功效的發揮和有效性的維持。國際社會中許多例子都清楚地表明,在很多情況下,對國際制度低限度違反是常事且并不會引起很大關注。遵守協議是一個復雜的現象,并非僅由強制力就可以完全解釋。一些規則安排較之其它幾乎不會讓單個行為者產生欺詐的動機,它們幾乎不需要強制,很容易得到遵守。博弈理論中由共同利益困境所產生的合作(collaboration)問題與共同背離困境所產生的協調(coordination)問題之間的區別,要求建立兩種不同的制度。在共同背離困境下,制度一旦建立,將導致行為者的希望趨同,并使行為者強迫自己進行合作。因為偏離合作將損害自己的利益。因此,在這種制度下,就不存在管理和監督方面的問題。〔6〕這些規則安排已經成為社會慣例(socialconvention),慣例的遵循無須強制。
第二,并非所有的遵守都依賴于強制。在說服主體依循規則這一問題上,各種制度之間并不相同。〔7〕一些制度以可能的懲罰(contingentPunishments)為特點,另一些則以可能的報償(contingentrewards)為特點。這兩類制度在遵守問題上存在根本區別。前者提出了強制的問題,后者則可以拒付渴望的報償為威脅來獲得遵守。
制度自身的一些特點也構成決定制度能否得到自覺遵守的因素。參與者數目的多少是因素之一。參與者數目少則便于檢查各方是否遵守安排和懲罰欺詐者。〔8〕透明度高的制度也容易得到遵守。如果違規行為易被發現,那么行為者出于對其他行為者針鋒相對(tit for tat)的報復的恐懼,將趨于遵守制度。而且,出于聲譽考慮,只要那些意欲違規者預料到其行為將被發現,那么他們就會控制自己不去破壞規則,即使他們知道其違規行為遭到制裁的可能性很小。〔9〕
制度參與者常常采取步驟使國際制度國內化,從而給予國際制度與國內制度同等的法律地位。不僅如此,一些國家還將履行制度職責的任務分派給具體機構,并明確一套程序指導其工作。〔10〕在遵守問題上,一旦國際規則國內化,國際制度與國內或地方性制度在這一方面的區別就將消失。
第三,并非所有的強制都依賴于政府。沒有強制可以帶來制度的遵守,但因此認為國際制度的遵守永遠不需要強制的觀點也是幼稚的。在一些情況下,強制是制度發揮效用的關鍵因素。但這并不是說必定需要一個中央政府來強制執行國際制度的規定。其它行為體也可以成為制裁主體。對國際組織、國家、非政府組織這三者的考察將有益于解決國際社會分權制裁(decentralizedsanctions)問題。眾所周知,通過制裁促進國際制度的遵守并非國際組織所擅長。但一些以實施國際制度為宗旨的國際組織,比如WTO、IMF,它們能夠在促進規則遵守上采取行動,而這是制度參與者決策時無法忽視的。
當然,相對于政府行動而言其力量有限,但絕非微不足道。有些情況下,國際制度的成員國會自己設法對違規者采取制裁行動來促進制度遵守。非政府組織在對國際制度違反者的制裁上也已有所行動,包括物理行動,如沉沒冰島捕鯨船只;經濟行動,如組織對違反國貨物的聯合抵制,等等。當然,這些分析決不旨在提出制度的有效性與強制無關,而只想表明相對于其它類型的制度而言,遵守問題主要與規則型制度相關。而即便在規則型制度中,轉化為社會慣例的制度也不會讓行為者產生欺詐的動機,許多規則型制度對違規行為還有一定容忍度。另外,制度本身的一些特點,以及國際制度的國內化也將影響制度的遵守。一言以蔽之,遵守制度是一種日益復雜的社會現象,不能專橫地強調沒有強制就沒有遵守。
(二)對相對獲益的關注只是對國際制度的限制而非否定。
新現實主義者雖然與新自由主義者一樣,將無政府狀態理解為缺少有政治權威的中央政府。但對于無政府狀態的后果,兩派有明顯分歧。新現實主義者不同意僅僅將缺少有政治權威的中央政府理解為缺少中央政府強制承諾實施。他們強調,無政府狀態意味著沒有超級權威阻止其他國家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來破壞或奴役本國,因而國家的核心利益是生存。國家的主要目標不是追求最大的獲益(gain)或報償(payoff)。在任何時候,國家的基本目標是阻止其他國家實現有利于它們的相對實力,在合作中關注自身的相對獲益。新現實主義認為,如果一國相信它的伙伴國會實現、或者可能實現相對多的獲益,那么該國就將拒絕參加,或背離、或限制它對合作安排的承諾。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參與的安排正提供、或已經提供較大的絕對獲益,國家也會背離合作。而且,即使該國相信它的伙伴國會遵守共同安排的承諾,它也會因為關注相對獲益而拒絕合作。〔11〕總之,無政府狀態下由于對相對獲益的關注,國家違背協定欺詐背叛的情況將增加,遵守制度互信合作的興趣將減小。
一旦國家產生對相對獲益的興趣,合作確實會變得困難。但這并不是說制度將歸于無效。相對獲益的關注只是對國際制度的限制而非否定。
第一,對相對獲益的關注是有條件的。相對獲益可以是重要的驅動力量,但其前提條件在于,只有在一段時期內的獲益改變了另一段時期的權力關系,以及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即隨后變化的權力優勢被用來反對其本身。〔12〕這一條件凸顯了意圖的重要性。斯坦恩認為,只有當實力影響國家的偏好和意圖時,它才算是實力,才能真正起作用。國家對他國意圖的重視并不亞于對他國實力的評估。由于受不同的價值偏好和利益趨向等的影響,一國可能更為擔心敵對國而非盟國的相對獲益。也就是說,如果別國不會利用增長的實力來反對本國,那么相對獲益在此就沒有太大的重要性。而一些國家對別國追求利益行為的敏感,從根本上說是受了那些國家意圖的影響和驅動。
第二,國家受相對獲益驅動的行為影響有限。當肯·斯奈德(DuncanSnidal)對關注相對獲益時國際合作的情況進行考察,認為現實主義有關相對獲益阻礙合作的觀點是片面的。他通過嚴密論證指出,只有兩個行為者時,或者在緊張沖突的囚徒困境中,對相對獲益的關注才會使行為者選擇背叛。在真實而復雜的世界政治中,這兩種情況體現得很微弱。而許多現實主義者可能不加鑒別地就把兩個行為者世界中的相對獲益,轉換成更為普遍的國際政治。現實主義追求相對獲益大大減少了國際合作可能性的觀點,并不是一個普遍有效的觀點。這種觀點僅僅適用于特殊的國家關注相對獲益的嚴密的兩極體系。一旦出現下面三種情況:即如果不是完全地關注相對獲益,如果最初國家之間的絕對獲益不是囚徒困境或國家的數目增加到三個甚至更多,那么這種觀點的真理性就很快下降。〔13〕
國際制度塑造、維持世界秩序
關于無政府狀態的另一種含義是缺少秩序。秩序的匱乏必然意味著混亂與無序。現實主義基于人性惡的假設,認為國際關系的本質是霍布斯《利維坦》中所描繪的,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沖突是國際政治的規則,而非例外。國際社會是一個人人為戰的斗爭舞臺,是一個零和博弈的競技場。
然而國際社會果真如此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雖然無政府狀態具有缺乏秩序的意義,但是現在很少有人認為無政府狀態是無秩序狀態。布爾(HedleyBull)認為,國家之間存在引導國際實踐的共同規則和制度框架。〔14〕他對國際體系存在秩序的事實進行了詳盡的敘述后,稱之為“無政府社會”。他認為,在國際社會中,政府制定規范、“游戲規則”、制度和產生某些集體結果,特別是秩序、穩定和維護國家體系的程序。在國際社會中,成員國“自認受相互關系中的一套規則所約束,并在共同制度中發揮作用。”〔15〕雖然國際社會處于一種碎化狀態,但既然存在國際社會,就有一定的社會組織形式,社會成員也有一定的行為規范。
無政府狀態的世界政治并不意味著它完全缺少組織。在一些事務領域,確實存在對各個行為者之間關系較為細致的安排。〔16〕因此,國際體系并不缺少秩序,國際社會可以是一個無政府的有序社會。
事實上,國際社會一直處在有序化的進程中。民族國家誕生以來,國際社會就從未停止過沖突與紛爭,但結果并非國際社會的崩潰瓦解。弱國并未被大量吞并以至消失,國家具有良好的生存和持久性記錄。〔17〕也就是說,國際社會并非一個純粹自助的體系。國際社會通過國際法、外交慣例、各種國際協議、國際組織來規范和限制民族國家的行為。弱國能夠依賴大量國際規范、制度和慣例來加強自身安全。國際社會有序化的努力在當前終于取得重大進展。這種有序不以世界政府為目標,不以犧牲國家主權為代價,僅是一種無政府狀態下有序的質與量的強化。它的目的只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全球、區域或次區域提供安全、穩定、秩序、發展環境等極其重要而急迫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物品。在這樣的國際社會中,通過各種各樣的國際規則、機制和制度安排,不斷規范、約束行為體的行為方式和關系模式,維持一種規范有限卻不斷擴大的國際秩序。它雖然未使國際社會處于全面的秩序狀態,但是,就整體而言,放任自流和混亂的狀態開始改觀。〔18〕
布爾將“秩序”定義為“(秩序的組成部分)依照某種模式而相互關聯;它們之間的關系并非純粹偶然的,而是具有某種可以辨識的規則”。“世界秩序是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為維持社會生活的基本或首要目標而采取的人類行為的模式或傾向”是“對人類活動、國家行為所作的旨在維護人類社會合作、穩定與和平的一種合理安排”。〔19〕1978年美國哈佛大學斯坦利·霍夫曼教授在《支配地位,還是世界秩序?》一書中提出,世界秩序主要由三個不可分割的定義要素構成:(1)世界秩序是國家間建立和睦關系的一種理想化的模式;(2)世界秩序是國家間友好共處的重要條件和規范行為的規章準則;(3)世界秩序是合理解決爭端沖突,開展國際合作以求共同發展的有效手段和有序狀態。因此,世界秩序“不過是使合乎倫理的對外政策行動作為可能的一系列的過程、程序與全球體制”,是“用以延續整個人類社會生活的主要目的的人類活動的樣式或安排”。通過這些定義,可以概括出世界秩序的三個基本層次:①觀念層次。它包括信仰體系、共同價值以及對世界政治事件的態度和認知模式。②行為層次。它指人類行為模式及傾向,行為者用行為來表達對觀念的理解。行為者威懾、談判、武裝、協調、合作、妥協等行為,都形成和強化他們對全球秩序的觀念。③制度層次。它指行為體創立的體現觀念、行為,并規范觀念、行為的各種制度安排。制度層次的內容涉及世界秩序中更為正式和規范化的內容。
國際社會有序化的努力根源于國際行為主體對秩序的迫切需求。這種迫切的需求將不可避免導致國際制度通過配置各國間的權力和利益,管制和調整國際行為體在相互關系中的行為,促進以主權國家為主的相互間合作與協調,有助于保證國際社會有限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從而塑造和維持秩序。
第一,國際制度從意識形態上使秩序合法化。秩序可以說是對人類活動、國家行為所作的旨在維護人類社會合作、穩定與和平的一種安排,但誰來安排、體現誰的意愿是問題的關鍵。國際制度基本都是在各個國家相互博弈和理性選擇基礎上產生的,是合意的結果。即便那些由權蓋四方的霸主強制訂立、推行的制度,如果要想發揮正常的作用,一般也必須以其他個體的接受為前提。并且制度作為公共物品,往往在一定范圍內具有合法性而被其它主體接受。當前的國際制度是國際關系轉型期重建和維護秩序的現實選擇,它基本得到了國際行為主體的認同,由國際制度所塑造的秩序也因體現了國際社會和平與發展的普遍要求而具有合法性。
第二,國際制度規范行為主體的行為。克拉斯納(Stephen.D.Krasner)將國際制度定義為,“在國際關系的議題領域所形成的一系列隱含的或明確的原則、規范、規則以及決策程序”。〔20〕羅伯特·基歐漢(Robert.O.Keohane)和約瑟夫·奈(JosephenNye)認為國際制度是“一套指導性安排”,包括“調整行為及控制其結果的規章、準則和程序的網絡”。〔21〕盡管定義各有側重不同,但學者們對國際制度對行為進行規范化這一核心內涵并無歧見。國際關系中的國家面臨著一個社會化的問題。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社會化,主要是指國家學習、接受、融入國際制度的過程。任何一個國家,如果要在國際體系中得到承認和接受,就必須遵守基本的國際準則和規則。國際制度一方面為國際行為者達成可行的一致模式提供指南,另一方面通過禁止確定的行動來約束國家的行為。〔22〕
第三,國際制度促進行為主體間的協調與合作。國際制度本身就是國際行為主體協調、合作的產物。制度一經產生,又具有自身的邏輯圖式而獨立于行為體。制度為國際行為主體提供了合作的框架和規范,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國家利益形成和國家行為。世界政治如同不完善的市場,存在許多缺陷,從而阻礙互利合作的出現。國際制度有助于在信息不完全、不對稱的局面下減少不確定性,使行為者在追求信息方面的交易成本大幅下降,從而推進政府間談判,達成相互有益的協議。針對國際交往過程中的機會主義風險,國際制度通過原則、規范的道德約束作用改變行為者的效用曲線,通過規則和決策程序的有形激勵促成行為者的履約行為,從而減少沖突紛爭、增進協調合作,國際政治經濟交往活動得以正常、順利展開。
第四,國際制度提供解決爭端的程序。國家在相互交往中建立起國際制度,并通過制度來促進合作,但這并不是說有了制度安排、有了合作行為的國際社會將充滿和諧。基歐漢在《霸權之后》一書中早就表明,合作不是和諧,也不意味著沒有沖突。相反,合作只會在行為者認為它們的政策處于實際或潛在沖突的情況下而不是和諧的情況下才會發生。即便行為者相互協調、進行合作,因為權利、利益分歧仍會產生種種紛爭。爭議大多不會導致國家間交易的終止和協議的廢棄,各國也往往不會選擇單邊自助、簡單訴諸武力來解決爭端。國際制度提供了解決爭端的程序,各國能夠從和平解決爭端中獲益。比如在國際貿易爭端中,各國就很少訴諸單邊的貿易報復,關貿總協定(GATT)的報復條款僅僅運用了一次,而且這次行動還是無效的,〔23〕而是依據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來解決它們的貿易爭端。
結束語
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一個基本事實,對國際制度的遵守及作用的發揮施加了諸多限制。國際制度本身也并非萬應良藥,發揮的工具作用也有限。但國際制度仍然蓬勃生長并顯示了其旺盛生命力。缺乏中央政府、缺乏和諧秩序并不否定國際制度存在的價值。國際制度在沒有權威時仍能得到遵守,甚至還塑造和維持世界秩序。當然,國際制度自身也有缺陷,現存國際秩序也并不完美,因而,消除現存制度的霸權因素,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新秩序仍是我們的訴求。
[注釋] 〔1〕KennethN.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MA:Addison_Wesley,1979,p.88;RobertKeohane,Internation al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EssaysinInternationalThe ory,Boulder,Colo.:Westview,1989,p.1. 〔2〕本文所論述的國際制度,涵蓋了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insti tution)和國際規制(internationalregimes)的基本含義。為論述方便,本文在行文中不再對這兩個概念進行區分。 〔3〕RobertAxelrodandRobertO.Keohane,“AchievingCoopera tionUnderAnarchy:StrategiesandInstitutions”,WorldPol itics38(October,1986),p.226. 〔4〕約瑟夫·M.格里科:《無政府狀態和合作的限度:對最近自由制度主義的現實主義評論》,大衛·鮑德溫主編:《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頁。 〔5〕JacobWerksman,ed.,Greening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London:EarthscanPublications,1996),xvi. 〔6〕阿瑟·斯坦:《協調與合作:無政府世界中的制度》,大衛·鮑德溫主編:《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第42頁。 〔7〕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對禁止、要求、允許三者的區別作了有益的區分。見ElinorOstrom,GoverningtheCommons:TheEvolutionofInstitutionsforCollectiveAc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8〕同注〔4〕,第133頁。 〔9〕奧蘭·R·楊:《國際制度的有效性:棘手案例與關鍵因素》,詹姆斯N·羅西瑙:《沒有政府的治理》〔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頁。 〔10〕KalRaustiala,“TheDomesticationofInternationalCommit ments,”WorkingPaperWp95 115,InternationalInstitutionforAppliedSystemsAnalysis,1995. 〔11〕同注〔4〕,第129頁。 〔12〕羅伯特·基歐漢:《制度理論和冷戰后時代現實主義的挑戰》,大衛·鮑德溫主編:《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第275頁。 〔13〕當肯·斯奈德:《相對獲益和國際合作的模式》,大衛·鮑德溫主編:《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第202頁。 〔14〕HedleyBull,TheAnarchicalSocie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7,p.15 16. 〔15〕Ibid.,p.13. 〔16〕KennethOye,CooperationUnderAnarch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 〔17〕K·J霍爾斯蒂,在《沒有政府的治理:19世紀歐洲國際政治中的多頭政治》(詹姆斯N·羅西瑙:《沒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指出,在過去的185年中,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屈服于永久的征服,而在此期間卻誕生了大約150個新國家。在持久性方面,國家遠比典型的公司安全。國家社會的規范以及用來維護國家地位、減少戰爭幾率的治理制度可以部分解釋國家生存的原因。 〔18〕俞正梁:《國際無政府狀態辨析》〔J〕,《外交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 〔19〕Stephen.D.Krasner,ed,InternationalRegimes,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1. 〔20〕Ibid. 〔21〕RobertO.KeohaneandJosephS.Nye:PowerandInterde pendence,Boston,1977,p.19. 〔22〕RobertO.KeohaneandJosephS.Nye,JR:“PowerandIn terdependenceRevisited”,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Au tumn1987,p.734.) 〔23〕轉引自羅伯特·基歐漢:《霸權之后》〔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1年版,第1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