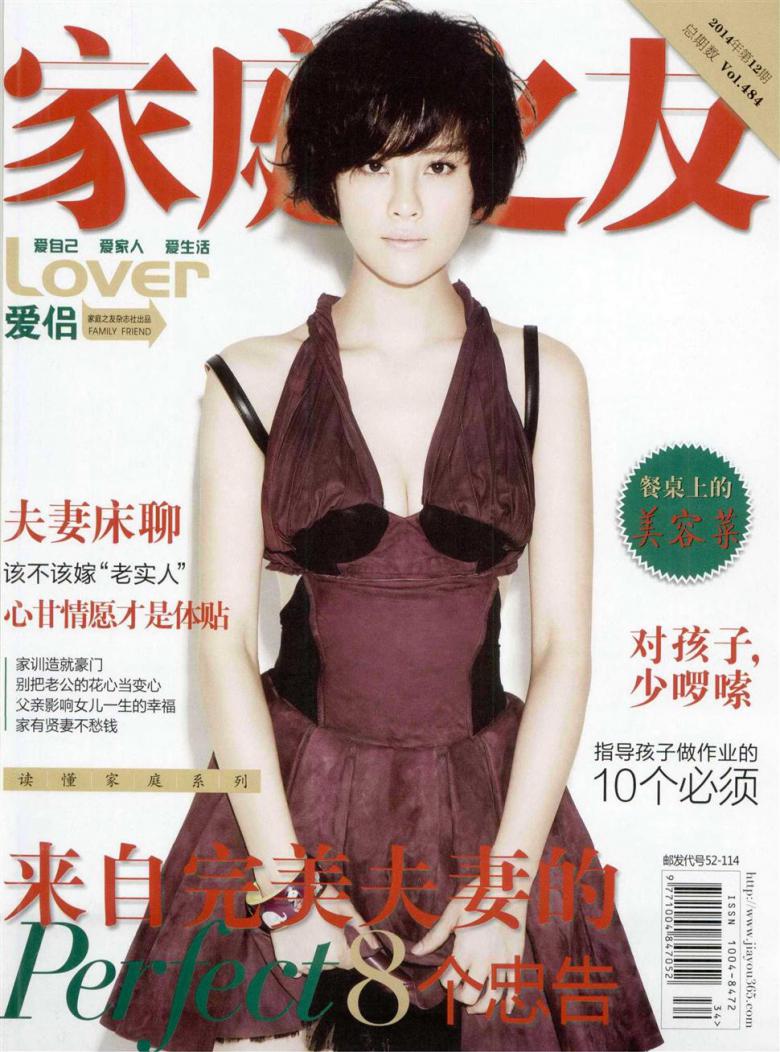言論自由與政府機構的“名譽權”
佚名
注釋:
[1] 輿論監督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匯,英文對應詞也許可以是surveillance by public opinion 或 public scrutiny。 [2] 例如在英國普通法歷史上,批評政府曾被稱為煽動性誹謗(seditious libel),構成一種犯罪,言論屬實不是抗辯事由,參見 William T. Mayton, Seditious Libel and The Lost Guarantee of A Freedom of Expression, 84 Columbia Law Review97-102(1984)。 [3] 我國《憲法》第四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4] 例如齊齊哈爾市第二輕工業局訴《南方周末》報社等案,北海市交警支隊訴《南方周末》報社案,岳陽監獄訴高子川和《黃金時代》案,包頭市郵電局訴鄧成和案,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訴《民主與法制》雜志社案,山東管縣人民法院訴《法制與新聞》雜志社等案,等。 [5] 《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一條:“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 [6] 例如著名的福田區人民法院訴《民主與法制》雜志社名譽侵權案。1995年3月,《民主與法制》雜志社刊載了一篇題為《一場耐人尋味的官司——<工人日報>被訴名譽侵權案》的文章。隨后,審理文中所指《工人日報》案的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以原告身份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訴稱《民主與法制》雜志社在文章中對案件的“審理活動和判決結果肆意歪曲、詆毀,嚴重侵害了本院名譽”。深圳市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于1995年7月作出判決,責令《民主與法制》雜志社向原告賠禮道歉,為其消除影響、恢復名譽,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5000元”。 [7] 一些政府機構在受到正確批評的時候依然能夠我行我素,從反面說明了這一點。 [8] 參見具體涉及到法人名譽權問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十項,實踐中發生的法人名譽權糾紛案也說明了這一點。 [9] 賀衛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的發言,肖英:《名譽權要有界限》,載《中國青年報》1999年9月15日第5版。 [10] 冷靜:《從法院狀告新聞媒體談起——一起名譽侵權官司所引發的思考》,載《北大法律評論》第2卷第1輯,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頁。 [11]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的規定,可以提出精神損害賠償要求的,限于公民。上述《解答》第十條規定:“公民、法人因名譽權受到侵害要求賠償的,侵權人應賠償侵權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公民并提出精神損害賠償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據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給受害人造成精神損害的后果等情況酌定。”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也規定:“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人格權利遭受侵害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12] 一些日本學者持如是觀,參見王利明、楊立新主編:《人格權與新聞侵權》,中國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頁。 [13] 這一觀念在社會契約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洛克曾言,對于國家是否違背原始契約而侵害公民權利的判斷,應當由人民做出,“人民應該是裁判者,”因為受托人或代表的行為是否適當和是否符合對他的委托,除委托人之外,別無他人可做裁判者。[英]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49-150頁。麥迪遜也認為,政府官員是否及在何種程度上違背公眾的信托,“這一問題只有人民才有資格通過自由的檢察和自由的討論加以決定。”Gaillard Hunt ed., The Writings of James Madison, New York: Patman’ s Sons, 1904,p.338。另外,羅伯斯庇爾也說:“但是,法官本身究竟由誰來裁判呢?因為,歸根結底,必須使法官的職務上的犯罪行為或錯誤行為,也像其他文官的職務上的犯罪行為和錯誤行為一樣,受到社會檢查法庭的制裁。由誰作出終審判決,由誰解決這些糾紛呢?因為必須要有一個人在這里成為最后的裁判者,也應當給他以發表意見的自由。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必須永遠記住這一原則,即公民應該有權對于社會活動家的行為發表意見和寫出文章,而不受任何法律的裁判。”[法]羅伯斯庇爾:《革命審判和法制》,趙涵輿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61頁。 [14] 《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條中的誣告陷害罪所針對的是誣告陷害自然人的行為,《刑法》并沒有規定誣告陷害“國家機關”的犯罪。 [15] 筆者所接觸的比較法資料表明,在受誹謗的政府機構是否可以提起民事訴訟這個問題上,只發現加拿大法律給予政府機構民事訴權;英國、印度、澳大利亞的法律曾經給予政府機構民事訴權,但是現在已經放棄了這種做法。作為加拿大這項法律之基礎的英國Bognor Regis U.D.C. v. Campion案判例已被貴族院推翻,所以這項法律的合理性也遭到質疑。主要參見 Nick Braithwaite ed., The International Libel Handbook, Butterworth-Heinemann, 1995; Coliver, Sandra, ed. , Press law and practice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ess freedom in European and other democracies, International Centre Against Censorship, 1993; Pnina Labav ed., Press Law in Modern Democracies , Longman Inc. ,1985。 [16] 許多人可能認為,對于獨立性較強的司法機構的行為的評論,應當受到限制,例如不能評論司法決定等,以免影響司法決定的權威和執行。本文認為,司法決定的權威源于它的合法性,但是在最終意義上源于多數公民對司法決定的認同,不能僅僅因為維護司法決定的權威而限制公民的言論自由。應當區分開這兩種問題:對司法行為的評論,對審理中案件的評論。限于主題,本文從輿論監督政府行為的角度所討論的是前一個問題。不妨多說幾句的是,這兩個問題是密切相聯的,本文對它們的觀點也是一致的,那就是無論對于何種問題的評論,只有當這種評論嚴重影響了司法運作和審判秩序時,才是司法機構主動予以限制的對象。至于后一種情況下的評論被訴侵犯私人的隱私權和名譽權的問題,是另當別論的。 [17] 可以考慮適用以下規定實施行政或刑事處罰:《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九條第(一)、(七)項,《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刑法》第二百七十八條。 [18] 《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九條第(五)項規定了這種行政法律責任。 [19] 《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的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20] 例如《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款、第四十一條,《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六條、第三十一條。 [21] 對于這一問題,一位法官坦言,不僅原被告之間存在爭論,而且“在法院內部,合議庭成員之間,甚至在審判委員會委員之間也有分歧。”康長慶:《試論報紙侵害名譽權問題》,載《新聞傳播與研究》1998年第1期(作者當時為北京市朝陽區法院民事審判庭法官)。 [22] 我們僅從被告的角度來進行成本分析。就被告而言,整個成本核算至少包括以下這些費用:調查費用,包括訴前調查費用和訴后調查費用;律師費用;時間損失;訴訟費和損害賠償等費用;其他損失例如因為發表批評性言論而遭到打擊報復,等。這些成本綜合在一起,可能是相當巨大的。它們很可能高于發表一道關于政府機構的信息所帶來的預期收益。而自由論壇一般不存在這之中的大部分預期成本。 [23] 冷靜:《從法院狀告新聞媒體談起——一起名譽侵權官司所引發的思考》,載《北大法律評論》第2卷第1輯,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75頁。 [24] 參見劉運龍:《論地方立法中“部門利益”傾向及防范對策》,載《人大研究》1997年第6期。 [25] 參見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析審判活動中的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載《人民司法》1997年第12期;侯銳鋒、何向南:《關于檢察環節執法中地方(部門)保護主義的調查分析》,載《學術交流》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