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實踐中的國際正義原則
佚名
我們已經(jīng)愈來愈相信,外交是服從并且服務(wù)于"國家利益"的。但是到底有沒有一個客觀存在的"國家利益"標(biāo)準(zhǔn),我個人覺得還大可懷疑。閻學(xué)通教授是洋洋灑灑的寫出一本《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但以我的駑鈍,不能明了書中高妙。比方說,掉在陵水機(jī)場的那個飛機(jī),還是不還?沖到領(lǐng)事館里去的朝鮮難民,是給小金還是放生?無論當(dāng)局如何決策,都可以解釋成為了"國家利益"而做出的"苦心孤詣"。所以單單拿"國家利益"來解釋外交實踐,有時竟是可疑的。
我們也看到,無論大家多么崇拜"國家利益",但是起碼在口頭上還必須經(jīng)常拿"國際正義"來說事兒。比諸"國家利益","正義"就更加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所以我試圖總結(jié)出一些原則,作為一種判斷的標(biāo)準(zhǔn),也寄托我的理想。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出了兩條著名的正義原則:
第一,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權(quán)利,他們可以擁有與別人的類似的自由相容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權(quán)。
第二,社會和經(jīng)濟(jì)的不平等應(yīng)該如此解決:(1)使條件最不利者也能得到最大的利益;(2)一切的公職和職位在機(jī)會完全平等的條件下對所有人開放。[1]
那么在國際社會中,我們可以對上述原則做出以下的推演:
第一,國家不分大小強(qiáng)弱,都享有平等的主權(quán)以及由此衍生的一切權(quán)利,而所有這些權(quán)利以不妨礙它國的同等權(quán)利及人類的共同利益為界限;
第二,國家在享有權(quán)利的同時也對國際社會中的其他成員負(fù)有義務(wù),比如;相互承認(rèn)和尊重主權(quán)、償還國際債務(wù)、信守出于自愿而簽訂的國際協(xié)定等等;
第三、國與國之間巨大的貧富差距[2]應(yīng)該消除,起碼降到比較低的限度內(nèi);應(yīng)該建立起這樣一種經(jīng)濟(jì)秩序,使處于"赤貧狀態(tài)"的國家起碼不至于在國際貿(mào)易繼續(xù)受到盤剝;世界市場的自發(fā)作用應(yīng)該被限制和調(diào)控,財富的分配不再僅僅遵循資本的法則,而應(yīng)該按照"條件最不利者也能得到最大的利益"的原則實現(xiàn)再分配。
第四,國家平等,或者說,在國際政治事務(wù)中每個國家都享有同等的決定權(quán)是實現(xiàn)公正分配的先決條件。
由此還可以再引申出下面的結(jié)論:
第一,國際正義實際上是與國內(nèi)正義相對應(yīng)的。假使一個國家在國際上要求實現(xiàn)平等公正的原則,那么在國內(nèi)它就不能無視和踐踏這些正義,如果不能保障對于公民的正義,那么對國際正義的要求就沒有立足之地;同樣,在國內(nèi)實行正義的國家卻在國際上追求霸權(quán)和暴利,那么它也應(yīng)該受到譴責(zé),甚至從歷史經(jīng)驗看,這樣的國家將損害其賴以立國的道德基礎(chǔ),最終"自己打敗自己"。[3]
第二,國際事務(wù)不應(yīng)該聽任大國、強(qiáng)國主宰,應(yīng)該模仿國內(nèi)民主建立起國際民主秩序,在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時(即國際社會的"公共領(lǐng)域"),任何國家都擁有同等的發(fā)言權(quán)--需要注意的是,此處強(qiáng)調(diào)的是"公共領(lǐng)域"的問題,而毫無疑問,在國際社會也存在著類似國內(nèi)社會的"私人領(lǐng)域",也就是說,個別國家內(nèi)部的事務(wù)并不需要全體國際社會成員的投票表決。
第三,權(quán)力與義務(wù)是對等的,當(dāng)一個國家的行為損害它國的主權(quán)或者人類的共同利益時--比如執(zhí)行侵略和種族滅絕的政策,它必須受到與其罪責(zé)相當(dāng)?shù)膽土P,也就是說,在此意義上的國際干涉是不違背國際正義原則的。
同時,我們所設(shè)計的國際正義不僅包含國家間的正義,還理所當(dāng)然的包含針對個人的正義。基本人權(quán)(也就是我們前邊所列舉的"全球底線倫理")約束所有的國家,侵犯這些權(quán)利的國家(即羅爾斯在《萬民法》中所稱的"法外國家"outlaw states)將受到譴責(zé)以至強(qiáng)行制裁與干涉。
當(dāng)然,承認(rèn)國際干涉的合法性很可能導(dǎo)致對主權(quán)原則的惡意破壞,所以我們必須對此做出相關(guān)的幾點限制:1)反對直接以道德觀念來判斷和打擊反人權(quán)的行為,而應(yīng)該模仿國內(nèi)法治社會的司法程序,對任何涉嫌反人權(quán)的行徑進(jìn)行審判,避免先入為主的對某一國家進(jìn)行道德歧視;2)以人權(quán)為理由進(jìn)行國際干涉必須取得國際社會的合法授權(quán);3)不能在此問題上存在任何雙重標(biāo)準(zhǔn),應(yīng)該絕對無條件的一以貫之;4)對人權(quán)存在著不同的理解和解釋,這種差異的存在本身就是基本人權(quán)之一--思想自由的體現(xiàn),因此必須反對將一國對人權(quán)的理解強(qiáng)加給別國,但是,并不因此意味著普遍意義的基本人權(quán)不存在,各個國家都必須遵循"底線倫理";5)應(yīng)該盡可能的避免以戰(zhàn)爭作為干涉手段[4]。
第四,由西方主導(dǎo)的現(xiàn)行國際經(jīng)濟(jì)秩序,一方面利用國家壁壘來限制勞動力等生產(chǎn)要素的自由流動(發(fā)展中國家向發(fā)達(dá)國家的人口流動從來沒有象現(xiàn)在一樣受到如此苛刻的限制),一方面它們又要借自己的強(qiáng)勢地位來打破窮國的一切"萬里長城",追求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即所謂的"經(jīng)濟(jì)全球化")。這種雙重標(biāo)準(zhǔn)不符合平等的原則,實際上也造成了不平等現(xiàn)象越來越嚴(yán)重的后果,因此是實現(xiàn)國際正義的巨大障礙。應(yīng)該首先消除對生產(chǎn)要素流動的雙重標(biāo)準(zhǔn),實現(xiàn)勞動力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有序的但是自由的流動,另外模仿國內(nèi)的福利體系,建立國際福利體系。
對于牽涉到國際財富分配的第四點,還需要再做一些說明。我們套用羅爾斯的原則得出此結(jié)論,但是對于不存在"無知之幕"的國際社會而言,到底"憑什么"富國必須援助窮國呢?我們知道,今日西方福利國家的形成,都是經(jīng)歷了漫長的發(fā)展過程,最關(guān)鍵的原因有兩點,第一是社會觀念的進(jìn)步,過于懸殊的貧富差距不再被認(rèn)為是"天經(jīng)地義",而原始積累時期罪惡被認(rèn)為必須"補(bǔ)償",第二是社會安定和發(fā)展的需要,一個良序社會不可能容忍長期存在的巨大的不平等。那么在國際社會道理也是相同的,西方的殖民掠奪和不合理的經(jīng)濟(jì)秩序雖然不一定是造成今日南北差距的決定性因素,但肯定是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最起碼的,西方工業(yè)國有義務(wù)以援助的形式來給予補(bǔ)償;同時,國際社會要保持安寧,各個國家要和平共存,也需要立即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否則只能是不斷的制造出絕望與仇恨[5]。 "9·11"之后似乎有更多的有識之士意識到了這一點。而鄧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如果發(fā)達(dá)國家不拿出錢來幫助發(fā)展中國家發(fā)展,發(fā)達(dá)國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場也就沒有了。"[6]
所以說,實現(xiàn)國際社會范圍內(nèi)的分配正義,從長遠(yuǎn)而言,對于發(fā)達(dá)國家也是有利的。
至于更為具體的制度設(shè)計,已經(jīng)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之內(nèi),本文沒有能夠完全解決國際正義的動力、動因和物質(zhì)支撐(裁判權(quán)加執(zhí)行權(quán))諸問題--但在此可以做一點簡單的補(bǔ)充:我認(rèn)為,在政治領(lǐng)域,聯(lián)合國體制是實踐國際正義原則的最大的一筆現(xiàn)有資源,它囊括了絕大多數(shù)的主權(quán)國家,并且初步完成了一個框架,起碼在理論上保證了各個國家對某些問題享有平等權(quán)利,同時它也提供了國際干預(yù)的一種合法授權(quán)機(jī)制,所以我們可以在聯(lián)合國的現(xiàn)有框架內(nèi)進(jìn)行改革,未來的國際社會契約也可以通過聯(lián)合國來實現(xiàn),而那些肆意破壞聯(lián)合國權(quán)威,以地區(qū)性的政治軍事集團(tuán)來取代聯(lián)合國的企圖,無疑是和建立國際正的努力背道而馳的;在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我們遇到的困難則大得多,現(xiàn)有的國際經(jīng)濟(jì)規(guī)則由西方國家制定,并且它們主宰著各種各樣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國際經(jīng)濟(jì)組織,這樣一種局面如果不能改變,那么得不到發(fā)言權(quán)的窮國就無法爭取到真正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因此國際分配正義的實現(xiàn),還要首先取決于平等正義的落實。
盡管"知易行難",但我們?nèi)匀辉敢饪隙ǎ喝祟惖纳羁谭词『屠硇詻Q斷,"國際社會"的健康發(fā)育以及正義原則被普遍接受,使得我們有理由對未來國際關(guān)系領(lǐng)域的更大變化保持樂觀的期待。也正如羅爾斯所深信的一樣,他的正義理論是一個"能夠?qū)嵺`的烏托邦(realistic utopia)",透過人類不斷的努力,一個更加正義的社會終將實現(xiàn)。
注釋:
[1] 對這兩條原則的中文表述有數(shù)種不同版本,此處據(jù)戴維·米勒等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xué)百科全書》,鄧正來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2年版,第632頁。
[2] 有關(guān)國際貧富差距的情況可以參見附錄。
[3]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雅典,修昔底德就認(rèn)為雅典人的帝國主義政策導(dǎo)致了其內(nèi)部的爭斗。參見《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上卷),謝德風(fēng)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60年版,第141頁。
[4] 這五點內(nèi)容部分的吸取了張汝倫和哈貝馬斯的觀點。參見張汝倫:《哈貝馬斯和帝國主義》,哈貝馬斯:《獸性與人性--一場法律遇到的邊界上的戰(zhàn)爭》,《讀書》(北京)1999年第9期。
[5]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jī)之后,許多人已經(jīng)開始對金融市場的自我運轉(zhuǎn)產(chǎn)生的懷疑,認(rèn)為應(yīng)該對資金流動進(jìn)行限制,而這種限制要由某種形式的制度安排或者"世界政府"來承擔(dān)。被認(rèn)為是頭號金融投機(jī)者的索羅斯甚至也宣稱:"如果集體利益無法在市場中實現(xiàn),你身為公民,就必須關(guān)切集體利益。如果你不關(guān)切,就得為社會的動蕩和不公正而自責(zé)。位于金融中心的國家,發(fā)展這種全球責(zé)任感十分重要。"參見張帆:《對全球金融危機(jī)的反思》,《讀書》(北京)1999年第9期。
[6] 鄧小平:《增進(jìn)中印友誼,加強(qiáng)南南合作》,《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頁。
村金融.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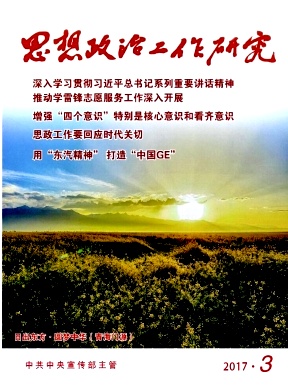
理與康復(fù).jpg)

.jpg)
與財富.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