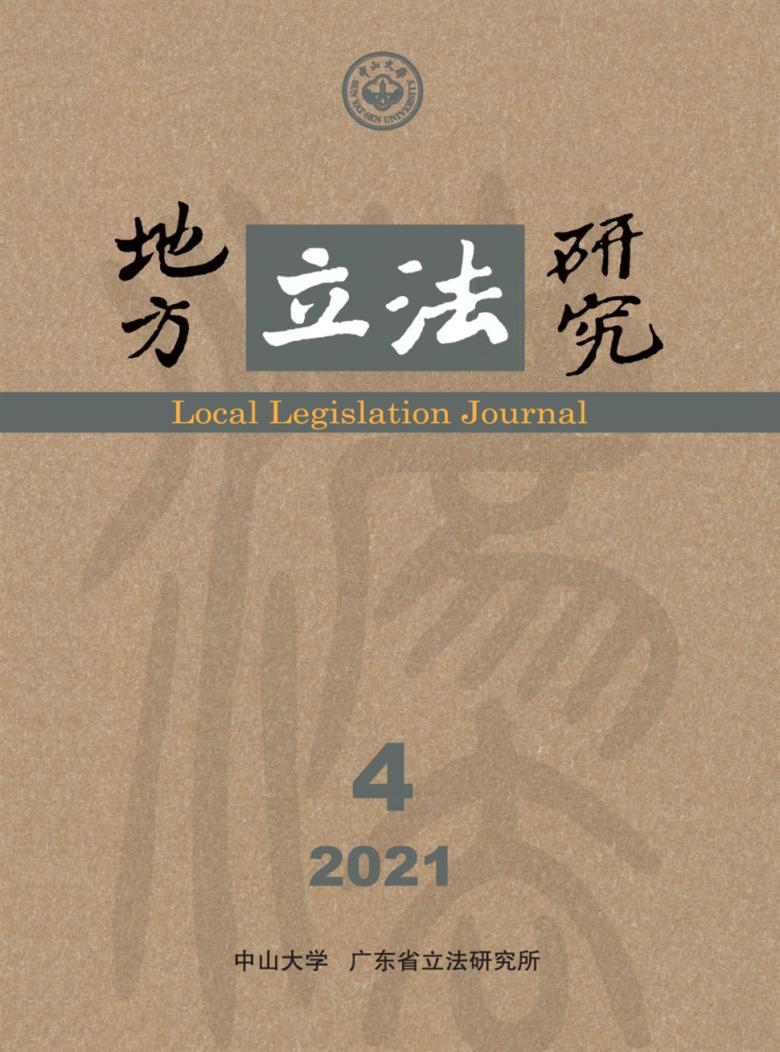略論因應人大代表與選民關系變化的制度途徑
郭劍鳴
一、人大代表與選民關系出現的新挑戰
1.選民結構的復雜化,對人大代表聯結選民帶來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的跳躍式發展引發了我國社會結構的分化重組。從橫向層面說,社會分工日益深化,新興產業不斷涌現,選民的從業行業、工種不斷被細分;這些行業的性質、特點、前景各異,給選民帶來的利益預期也不同,處于不同行業的選民自然會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和政策需求。開放前,選民結構只是簡單的板塊狀,現在有不斷被行業分割為線狀和點狀的趨勢,當然給人大代表溝通聯結選民帶來困難。從縱向層面說,在社會經濟變遷中,雖然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但國民財富增長并不均衡,收入差距不是縮小而是越拉越大,財富的“馬太效應”日益顯現。改革前,我國城鎮的基尼系數(反映收入差距)為0.16,農村的基尼系數為0.22,最近二十年,除個別年份,這一系數持續平緩上升,2000年已達到0.4的警戒線水平[2]。出現一方面我國20%左右的人口擁有6萬多億元儲蓄存款中的80%,而另一方面我國農村的貧困發生率高達28.6%,城鎮的貧困發生率也有8%。說明我國國民基于收入差距的分層逐漸形成,處于不同收入層次的選民自然也會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和政策需求。而且,選民的行業分化和層次分化是交織一起加深選民結構的復雜化的,選民成分的復雜化使選民難以形成相對清晰一致的利益主張,不利于人大代表收集歸納選民的要求。
2.選民的地方利益情節膨脹,使人大代表在整體利益與地方利益間的選擇及不同區域利益間的選擇中陷于兩難。在社會變革中,由于政策性、區位性、資源性及歷史性等原因,我國的區域發展極不平衡,出現較為明顯的東、中、西部發展階梯,同一區域的不同地方之間也存在類似的發展差異,而且有拉大之勢。統計數字表明,2000年滬、京、深等高收入發達地區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PPP值,購買力平價指數,下同),高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8320美元),而云、陜、甘、寧人均GDP在2000美元左右,緊貼著世界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1800美元),其中,貴州只有1247美元,而上海高達15516美元,上海為貴州的12倍,有人形容這種現象為“一個國家四個世界”[3]。在廣東省,2000年,廣州、深圳、中山、東莞等8個城市一般預算收入增加額占了全省的市縣級增收額的85%,而另外卻有10個縣的收入出現負增長,26個縣欠發工資[4]。處于不同發展層次的地區的選民最關心、最希望解決的問題存在較大差異。例如,東部發達地區資源短缺、人口稠密,西部落后地區則資源豐富、地廣人稀,東西部在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人口控制政策上會有不同的價值趨向。1998年長江水災,中、東部廣大地區損失慘重,指責西部有關省份亂砍濫伐森林資源;而西部居民則把盡快開發當地資源作為脫貧致富的主要途經,以資源優勢換區位優勢、技術優勢無可厚非。尤其在財政金融政策方面,東部發達地區主要持效率優先觀念,希望國家把有限的財力投向有發展基礎的地區,以獲取更好的經濟效益;而中西部不發達地區更強調公平,希望國家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以扶持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縮小區域間發展的差距。國家層面同樣也面臨均衡發展的難題,可是國家提取的財力資源主要來自東部地區,在這里作出效率與公平的政策選擇,集中地折射出國家利益與東部地區利益、國家利益與中西部地區利益、東部地區利益與中西部地區利益間的三角關系。人大代表由選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人大代表聽取、反映選民的意見,代表選民的利益是其根本職責。在社會變革中,不同發展區域的選民對同一政策問題會有利益分野。人大代表如果一味地堅持區域利益,大會的議事效率將大打折扣,國家利益也會受損;如果簡單地服從國家利益,地方的特殊性表達不了,大會開不出特色,也會辜負選區選民的期望。目前,人大代表的這種兩難境地還不明顯,但隨著社會變革的深入,將是不容回避的.
3.選民的業界利益情節膨脹,以行業為基礎的利益團體逐漸生成,提升了選民對人大代表影響和監督能力;同時,也對人大會議中的業界代表分配及議事的行業內容提出了新要求。改革前,在計劃經濟平均分配利益的制度安排下,選民的業界利益相對模糊,行業歸屬和認同意識不強,我國的利益團體始終未能發育.改革后,市場體制取代計劃體制,利益均分的格局被迅速打破.尤其是近十年,行業差距、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越拉越大.以行業差距為例,1995年我國16個大行業之間職工人均貨幣工資的基尼系數為0.101,1999年這一數字上升為0.121,五年間提高了20%[5]。其中,電訊行業與機械制造行業職工人均工資比達到了2.5/1以上。行業發展靠基礎靠技術,也靠政策扶持;在產業政策的調整中,各行各業都希望得到更多的政策扶持,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為此我國各大行業均成立了行業協會或公會,他們除了加強行業內部的自律外,更主要的是為提升行業的影響和地位,加強與公共機構的溝通,并適時進行游說,具備利益團體的主要特性。例如,1998年起,我國放寬了對房地產開發業的管制政策,終于迎來了2000年房地產景氣指數的穩步攀升,這與房地產業協會努力密切相關。其它類似的情況,如《憲法》修正案中提升民營經濟的地位、《婚姻法》的修改等均與民營企業協會、婦女聯合會的極力主張分不開,近年來,各級人大收到的涉及行業發展的議案逐年增多,說明各行各業已開始有意識地介入到人大的議程中來。
4.選民的城鄉利益分野加大,農村選民增長了對人大代表中農村代表比例偏低及農情民意得不到充分表達的不滿情緒。歷史上,我國就是典型的二元結構社會的國家。建國后,由于特定的背景,我國選擇了優先發展工業、優先發展城市的道路,城鄉差別依舊。改革開放后,雖然農村面貌煥然一新,但與城鎮發展相比還是不夠,城鄉差別有擴大的趨勢。城鄉差別主要體現在:戶籍和身份、社會保障和醫療福利、收入、勞動條件等方面。以人均收入為例,1978年城鄉差距為2.36/1,1999年擴大到3.26/1,如果加上各種福利,城鄉差距高達5/1的程度[6]。1990-1999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為6.9%,而農村居民只有4.8%[7]。尤其是1997年來,農民收入增幅連年下滑,農民一方面增收困難,另一方面又負擔沉重,“三農”問題日益嚴峻。農民迫切希望有更多的渠道表達農情民意,有更多的農民代表維護其合法權益。但我國選舉法規定,縣、省、全國三級人民代表大會每一農村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分別為城市代表所代表人口數的四、五、八倍[8]。根據最新的人口普查數字,農村人口不及城鎮人口的2.5倍,因此,無論從絕對值還是相對值來說,農村代表的名額都明顯低于城鎮代表的名額。由于制度安排上,不足以充分有效地表達農民的意愿,農民集體上訪的情況較為嚴重。二元結構的延展,使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在政治、經濟和重大社會問題上逐步有了不同的見解,農民對城鎮居民的優遇也由羨慕而轉向不滿和抗爭,尤其對國家不斷加大對城鎮的投入而對農村農業的投入卻一直處于欠賬狀態表示不解。這種態勢的發展必然對農村代表和城鎮代表的議事心態產生不同的影響。
5.選民的社會動員程度不斷提高,選民的權利意識和發展欲望被迅猛激活,對人大代表和政府工作的質量提出了挑戰。選民已不再滿足人大代表只在人大會議上發揮表決功能,更要求代表們能善解民意、勇于表達民意直至為選民利益而抗爭。有調查表明,選民逐漸把人大代表從“榮譽性”職位定位轉化為“功能性”職位定位,認為人大代表不應只是“勞模型”、“好人型”,更應是“能人型”、“活動家型”[9]。這意味著,人大代表如果不具備相應的能力和勇氣,將不再受到選民的擁戴。
二、因應挑戰的制度途經分析
1.在代表構成制度上,嘗試地區代表制和行業代表制相結合,以地區代表制為主導的制度。即各級人大代表的名額先按該區域各組成部分的人口比例進行分配,各組成部分僅將所分配到的代表名額中的一部分按同樣的方式分配給次級地方,選舉出地區代表,另一部分名額則在該區域各行業中組織選舉,產生行業代表。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廣東省的人口數量分配給廣東代表團120位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廣東省再將其中的80位確定為地區代表,分配給深圳、廣州、中山等次級地方選出;另外40位確定為行業代表,在全省各行業選舉產生。這樣,一個代表團內有地區代表和行業代表的明確分工,地區代表主要關注縱向各級區域的社會整體發展需要,行業代表側重反映橫向各業界發展的需要,職責分明,有利于各類代表收集民意、提升民意,人大會議的議程也會更有效率、更有質量。
2.提高代表制的民主程度,將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提高到更高的層級。提高代表制的民主程度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擴大代表的規模,降低每一代表所代表的選民數額,從而減少代表制的層級;一是擴大選民直接選舉代表的范圍,使選民盡可能地貼近政治過程,最大限度地滿足選民直接參政議政的要求。兩者相較,前者無論怎幺增加代表數額,總會有幅度的極限;這樣做,既增加了民主的成本,又降低了民主的效率,在我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社會里是不適宜的。后者在我國尚有推廣提升的空間。我國目前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最高只到縣區級,直接民主制的程度不能滿足在社會變革中選民民主意識迅速增長的要求。但根據我國的國情,直接民主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以先在設區的市人大代表選舉中實行直接選舉制的改革。這類市的轄區幅員適中,人口相對集中,市民素質較高,通訊傳媒條件先進,可以支持選民直接與候選人溝通以及選民對當選代表的監督。在取得經驗的基礎上,省級人大代表的選舉可以嘗試間接選舉和直接選舉相結合的制度,即一部分代表通過間接選舉的方式選舉產生,一部分通過直接選舉的方式選舉產生。這方面的改革不強求全國統一步伐,各地的條件不同,可以先在直轄市、發達地區的省份試行。
3.設立人大代表的工作假日制度,支持代表全面深入地調查分析社情民意,提高代表履行職責的質量。隨著社會變革的深入,社會問題日益復雜化,選民的觀念、見解和利益要求也趨向多元,要準確把握民意并非易事。我國各級人大代表(除人大常委會委員)均為兼職,其中多數還是業務骨干,平時都有繁重的工作,沒有多少空閑深入體察民意、系統思考社會問題,不利于代表保質保量地履行職責。建議根據不同情況,分別給予全國、省級、市縣級人大代表20天、10天、5天左右的工作假日,以便人大代表認為必要時,可以集中一段時間聯絡選民、開展調研、編寫提案。代表在工作假日展開調研時,所在單位和有關部門要給予盡可能的便利和協助;對沒有工資收入的代表,國家要給以相應的補貼。目前,在人大會議召開時才著手思考問題的代表不在少數,有的代表由于準備不足,在會期討論中只能“空對空”談不出實際問題。設立人大代表工作假日制度,有利于改變這種代而不表的現象。
4.調整人大代表中農村代表與城市代表的比例結構,適當增加農村代表的數額。現行關于農村代表與城市代表的分配比例是1979年選舉法規定的,時隔20多年,農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農民的整體素質有了一定的提高,繼續這樣執行已不適宜。加之近年來,我國的“三農”問題日益突出,農民增收緩慢、農業的基礎削弱、農村社會出現諸多不穩定因素,深入了解和研究農村的實情,加大解決“三農”問題的力度,是我國長期而緊迫的任務。我國農村面廣、人多、差異大,更需要在各級人大中有更多的農村代表將各地的農情民意帶到各級決策層,使決策層能更全面地傾聽到農民的真實呼聲,制定切實可行的農村政策,加快縮短城鄉差別的步伐。
5.在全國和省級人大常委會中設立地區事務委員會,加大協調地方利益矛盾的力度。如前所述,改革后,我國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性加大了,各地的地方利益觀念提升了,地方保護主義色彩濃厚了,一些地方出臺“土”政策來對抗國家、省的法規政策的現象已不鮮見。如果代表中也彌漫這樣的觀念,將妨礙參政議政的客觀公正,既有損國家整體利益的實現,又無助于形成真正發揮地方優勢的政策。設立地方事務委員會就是要加強對體現各地方特色的提案的審議及對各地優勢的考查研究,對確有助于發揮地方優勢,又不違背國家整體利益的提案和要求,要給予充分的支持,并推動類似法規政策的出臺;加強對各地方性法規和政策的審查監督,對地方保護主義的政策法規要堅決予以撤銷和封殺;加強對各地區代表團的溝通和聯絡,促進各地人大間及代表間的交流與合作。
注釋: [1][美]科恩:《論民主》,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80頁。 [2]香伶、李實:《收入分配格局的新變化》,載《2001年:中國社會經濟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1月,139-141頁。 [3]參見胡鞍鋼、鄒平:《社會與發展-中國社會發展地區差距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4]仲大軍:《二元結構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載《2001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200頁。 [5]同[2],第142頁。 [6]《從基尼系數看貧富差距》,載《中國國情國力》2001年第一期。 [7]《中國統計年鑒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年1月,第29頁。 [8]蔣碧昆:《憲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5月,第134頁。 [9]廣東省教育廳青年社科基金項目:“潮汕文化與粵東現代化”系列調查報告(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