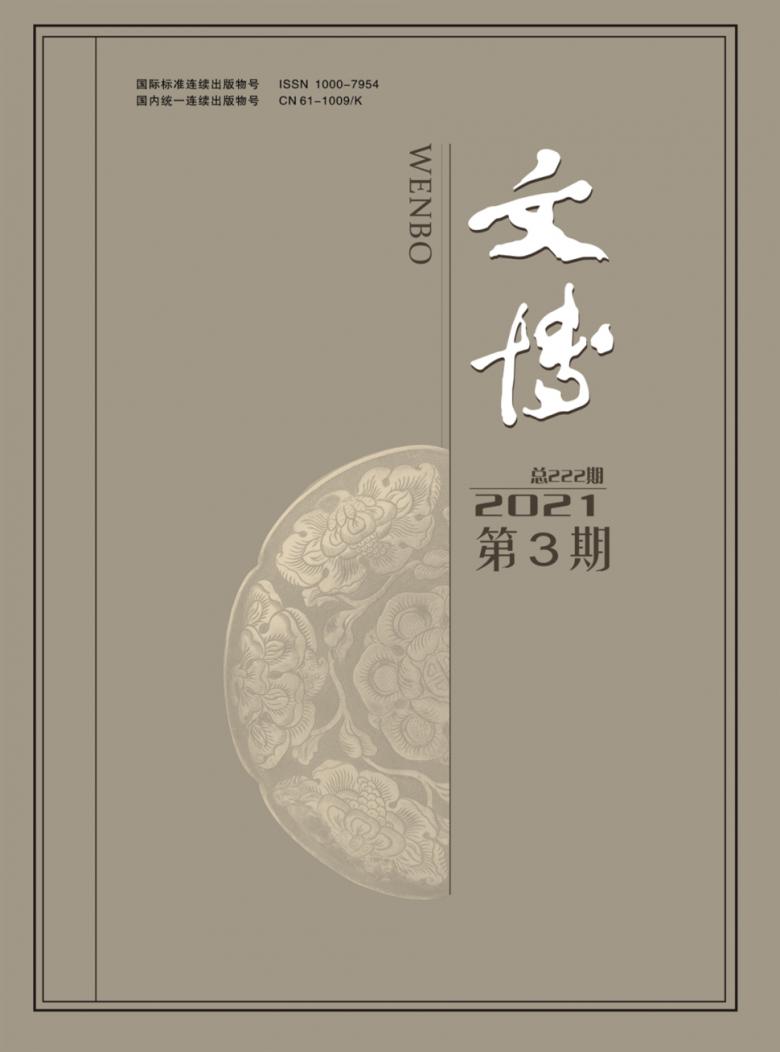對“曾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員禁止在娛樂場所從業”規定的若干質疑
佚名
提要: 《娛樂場所管理條例》第5條第2項的合法性可以從兩種路徑出發進行。無論是作為《刑法》第54條第4項的具體化規定而存在,或者是作為罪犯被適用剝奪政治權利刑罰之后產生的附隨后果而存在,《娛樂場所管理條例》第5條第2項都存在違法因素。這項規定導致多方面的實質危害,應當予以修改。
一、的提出
《娛樂場所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5條第2項規定:因犯罪曾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不得開辦娛樂場所或者在娛樂場所內從業(以下簡稱“不得在娛樂場所內從業”)。該規定禁止正在或曾經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從事某種社會活動,屬于對公民的“職業限制”,實質上是對公民經濟自由的限制。對《條例》第5條第2項合法性的討論,有兩種路徑,一種路徑是將《條例》的規定看作是對于《刑法》第54條第4項規定的具體化,是下位法對上位法的進一步細化和落實。那么所要分析的是,“在娛樂場所內從業”是否屬于“擔任國有公司、領導職務”的具體類型;一種路徑是認為《條例》的規定與《刑法》第54條第4項之間并非原則規定與具體落實的關系,而是應該將“不得在娛樂場所內從業”看作是罪犯被適用剝奪政治權利刑罰之后產生的一種附隨后果,該種附隨后果并非剝奪政治權利本身所具有的內容。那么所要分析的是,作為附隨后果,“不得在娛樂場所內從業”是否與剝奪政治權利刑罰之間具備足夠的關聯程度。本文將從兩種路徑出發分析《條例》規定的違法性,進而指出其實質危害,最后提出修改建議。
二、“在娛樂場所內從業”不屬于“擔任國有公司、企業領導職務”的具體類型
通過將《條例》第5條第2項與《刑法》第54條第4項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在權利限制范圍、主體范圍方面,還是在權利內容限制方面,《條例》第5條第2項均屬于違反上位法規定的違法規定。
1、權利限制范圍方面,《條例》第5條第2項超越了《刑法》規定的范圍。《刑法》第54條第4項規定的是“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國有”一詞作為定語是僅限定國有公司,還是既限定國有公司,又包括國有企業,是判斷《條例》是否符合上位法的關鍵。如果刑法規定的內容是,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不能擔任國有公司和任何企業(不僅包含國有企業,也包含非國有企業,當然也包括娛樂場所)的領導職務,那么,《條例》的規定在適用范圍這一點上還是符合刑法的規定的;但如果刑法規定的是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不能擔任國有公司和國有企業的領導職務,那么條例對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的娛樂場所從業資格進行如此限制,則屬于擴大權利限制范圍,過多地限制權利主體的經濟自由,因為從我國實際情況看,90%以上的娛樂場所在經濟形式上都屬于非國有企業,基本上屬于私人投資、私人經營的私營企業,不屬于刑法規定的國有企業。從這個角度看,《條例》的規定屬于超越《刑法》的立法原意,存在著違反上位法的嫌疑,應當通過《立法法》規定的行政法規監督程序進行監督,如有必要,有關機關可以予以撤銷或者改變。
我們認為,從立法原意以及前后邏輯順序看,《刑法》第54條第4項規定的范圍還是國有公司和國有企業,而并非對擔任所有企業領導職務的限制。理由如下:第一,從設立剝奪政治權利刑罰的目的看,是通過該種刑罰的設立達到剝奪罪犯參加國家政治活動的權利,是一種接近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例如選舉代表、擔任公務員等;按照國家政治生活與社會經濟生活分離的原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無論如何不會成為政治權利的一部分內容,只有在泛政治化時期,才會將從事經濟生活的權利看作是一種政治權利。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情況下,擔任國有公司和國有企業的領導職務與擔任私營企業的領導職務存在著根本上的差異,前者是代表國家對國有公司和國有企業進行管理,實質上是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一種形式,因而可以被納入剝奪政治權利的范圍;而后者純粹是私人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參與,與國家政治生活無關,應當被排除在剝奪政治權利的范圍之外;第二,從《刑法》第54條第4項規定的前后邏輯順序以及語義關聯程度看,無論是在“企業”之前的國有公司,還是“企業”之后的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都是一種國家政治生活的形態體現,均是作為國家權力行使的特殊類型而存在,而在這些特殊類型之中的“企業”一詞應該是國有企業的一種簡略表述;或者是說,國有公司的“國有”一詞的界定效果能夠及于“企業”。
2、在主體范圍方面,《條例》的規定超出《刑法》規定的范圍。《刑法》第54條第4項是指在剝奪政治權利期間,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不得擔任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的領導職務。在被剝奪政治權利刑罰執行完畢之后,無論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處于何種類型,該類人的政治權利即完全恢復,在政治權利的享有上等同于普通人,該種應有之意在選舉法的選民登記制度當中有充分的體現。而《條例》第5條第2項規定的是“因犯罪曾被剝奪政治權利的”,需要引起我們重點關注的是“曾”字,一個“曾”字即代表了過去和現在兩種類型,包含了兩類主體范圍,即正在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當然不能在娛樂場所內從業或者開辦娛樂場所;以及曾經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也不能在娛樂場所內從業或者開辦娛樂場所,而這一點已經超出《刑法》第54條第4項所限制的主體范圍。
3、在權利內容限制方面,《條例》的規定也明顯超出了《刑法》的規定內容,存在違反上位法的嫌疑。《刑法》第54條第4項規定的是“領導職務”;而《條例》第5條第2項規定的是“開辦”或者“從業”。對此,需要區分投資者和從業人員兩種不同的類型。而對于投資者又存在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開辦者是投資者,但僅僅是股東而不擔任娛樂場所的領導職務,對于該種情形的限制屬于擴大限制范圍;另一種情形是開辦者既是投資者也是管理者,對于該種情形的限制還可以說是符合上位法的規定。對于從業人員來說,也存在擴大解釋范圍和限制解釋范圍。前一種情形是包括娛樂場所領導人員在內的所有娛樂場所的從業人員;另一種情形則是僅指娛樂場所領導人員之外的其他娛樂場所的普通從業人員。對于前一種情形還可以說僅在限制范圍上對上位法有些許擴大,但對于后一種情形則屬于明顯超越上位法規定的違法規定,因為無論在何種情形下,普通員工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在普通商業場所就業不是一種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體現。
三、作為附隨后果,“不得在娛樂場所內從業”與剝奪政治權利刑罰之間缺乏足夠的關聯程度
如果《條例》第5條第2項為“因犯罪曾被剝奪政治權利”設定了“不得在娛樂場所內從業”的附隨后果,那么這種附隨后果通過剝奪政治權利的連接適用于應當或可以剝奪政治權利的四類犯罪[①].因此,要判斷《條例》第5條第2項的規定是否合法,必須分析作為附隨后果的“不得在娛樂場所內從業”與剝奪政治權利刑罰之間是否具有足夠的關聯程度。這個問題又可以分解為以下兩個問題:第一,政治權利與經濟自由之間是否具有足夠的關聯,以至于在剝奪政治權利的基礎上,需要附帶地限制作為經濟自由的娛樂場所從業;第二,“不得在娛樂場所從業”與應當或可以剝奪政治權利的四類犯罪是否具有合理的對應,以至于“不得在娛樂場所從業”可以有效地適用于這些犯罪。
(一)政治權利與經濟自由缺乏合理的關聯
我國憲法對“政治權利”未作出明確界定,憲法學界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政治權利和自由,是指憲法和規定公民有權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權利,以及政治上享有表達個人見解和意愿的自由。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1]政治權利是實現人民主權原理及各種具體的民主制度的前提條件和必然要求,具有能動的性質,屬于一種積極的權利或曰“接近國家的自由”。[2]所謂“經濟自由”,其實就是各種“經濟活動的自由”,具體包括選擇職業的自由(擇業自由)、營業的自由(營利自由)、合同的自由(契約自由)、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以及財產權等有關自由權利。經濟自由的特質在于排除國家或公共權力的干涉,即要求國家或公共權力保持一種相對的消極不作為的態勢,為此乃屬于一種“防御國家的自由”。[3]經濟自由與人身自由、精神自由,號稱“三大自由”,這些自由構成了“私自治”原則的法基礎。[4]從政治權利與經濟自由的屬性與功能差異可以看出,兩者是各自獨立的權利體系,在實踐中是可以適當分離的。經濟自由作為“私自治”原則的法基礎之一,其功能在于為公民提供一個可以脫離國家控制的自主空間。這種自由是先于政治權利而存在的,政治權利雖然對經濟自由的實現有保障作用,但經濟自由并不以政治權利為基礎或支撐。在被剝奪政治權利的情況下,公民雖然無法接近國家,但是他仍然可以退居于經濟自由所提供的自主空間,在其中追求個性和幸福生活,國家的介入仍然是被拒絕的。這就是說,經濟自由的行使并不以享有政治權利為前提。剝奪政治權利只是表明該公民的素質不符合參與政治的要求,因而有必要在特定時期內禁止其參與政治,以維護政治的純潔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公民行使經濟自由就會危害到正常的經濟秩序,從而必須限制其經濟自由。由此可以得出,政治權利與經濟自由之間缺乏足夠的關聯,以至于剝奪政治權利可以導致附帶地限制經濟自由。
(二)“不得在娛樂場所從業”與應當或可以剝奪政治權利的四類犯罪缺乏合理的對應《條例》第5條第2項為“因犯罪曾被剝奪政治權利”設定“不得在娛樂場所從業”的附隨后果,這種附隨后果通過剝奪政治權利的聯結適用于應當或可以剝奪政治權利的四類犯罪。盡管這種附隨后果并非刑罰,但在性質上它與作為刑罰的“禁止從事特定職業”具有相似性,即都是因犯罪人的特定行為而禁止其從事某種活動。“禁止從事特定職業” 這種刑罰具有特定目的,主要在于剝奪或限制罪犯利用某種職業進行再次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