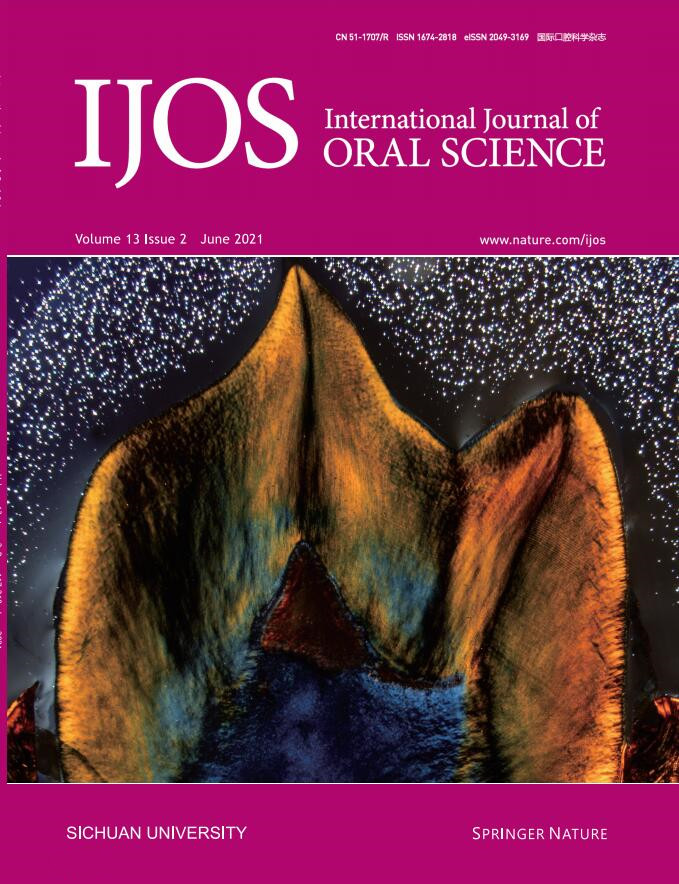后WTO時代我國媒介產業重組及其資本化結果——對我國媒介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胡正榮
關鍵詞: WTO 媒介產業重組 資本化 重新制度化 政治經濟學
一、認識我國媒介產業重組的政治經濟學框架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被學者和業者設置成為一個普遍適用的、解決眾多問題的議程。這種議程設置的背后有著非常復雜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動因,學界和業界的種種觀點都貫穿著長期意識形態化后強烈的反作用傾向,希望借助外部力量,特別是外部經濟力量解決內部媒介的意識形態問題。其實,這是一種典型的、簡單化的線性政治經濟觀,即自由市場必然可以帶來民主政治、市民社會等結果 [1] 。在當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以及與之相關的政府、各種跨國公司的互動使我國媒介與 WTO 的關系變得相當復雜而非線性。我國國內業界和學界是希望意識形態問題經濟化,而美國國內有相當的勢力是希望將經濟問題逐漸政治化 [2] 。
我們可以借鑒政治經濟學等研究框架,認識后 WTO 時代我國媒介產業發展的基本方向。首先,在我國日益與外部世界進行政治、經濟和文化互動的背景中研究我國媒介。這是一個內部與外部互動的視角。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冷戰時代經濟自給自足、政府相互對抗的世界格局逐漸被后冷戰時代的資本全球流動、市場開放、跨國公司日益突顯在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全球化所取代 [3] 。然而,現實主義者則認為即使全球化時代仍然強調國家( State )的作用,重視利用權力進行干預和保護 [4] 。其實,就我國這樣一個后發現代化和被動全球化國家而言,兩種理論均有自己的市場,而且在政策和實踐層面均可見到其應用。其次,在我國制度變遷和社會結構進化的動態過程中研究我國媒介。這是一個歷史、現實和未來動態關系的視角,即歷史結構主義的視角。所謂制度,就是各種社會利益的博弈達到均衡時所表現出來的結果,即社會博弈的均衡 [5] 。我國正處在各種社會利益博弈、社會資源重新分配的過程中。制度本身是變動中的變量,而不是常量。另外,在制度變遷的同時,我國的社會結構,特別是社會分層結構也處在劇烈的變動中。這種重新分配狀態和分配過程必然產生剝奪與被剝奪的關系 [6] 。西方社會討論社會結構變化都是建立在法理統治、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三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基礎上的,對他們而言,這三個條件是常量。而對我國而言,恰恰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經濟制度以及社會結構都是在變動之中的,都是變量 [7] 。因此,就必然需要關注這些變量對我國媒介業的影響。再次,研究我國媒介產業重組,需要特別關注政府與產業( government-business )這對政治與經濟范疇 , 而不是國家與社會( state-society )和公共與私人( public-private )這些范疇。在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政府扮演著最為重要的角色,特別是政府的變動、決策直接制約各種產業行為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8] 。而在我國私人財產權的確認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之前,公共與私人尚不可能成為問題。
二、前 WTO 時代我國媒介產業重組過程:市場化與集團化
如果以 2001 年 12 月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為分界線,那么,我國媒介產業重組可以分為兩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為前 WTO 時代,時間是從 1978 年我國媒介業開始改革到 2001 年,該年 8 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新聞出版總署下發了《關于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干意見》(“ 17 號文件”),這個文件標志著面對內外挑戰我國媒介業深化改革的全面啟動,此階段的特點是以市場化為主,繼而開始集團化;第二階段為后 WTO 時代,時間從 2001 年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到未來的若干年,特點是以集團化為主,繼而實現資本化。
(一)我國媒介業市場化的近 20 年( 1978-1996 )
20 世紀 80 年代,我國媒介業就開始了市場化的改革。首先,政策上許可媒介部分內容非意識形態化、娛樂化和平民化;其次,經濟上,政府向媒介撥款減少,媒介的收入從這樣依靠政府資助徹底轉向了依靠市場經營獲得,如廣告等。這就形成了我國獨特的 “一元制度,二元運行”( One System, Two Operation (OSTO) )的媒介體制,一元制度就是指媒介為國家所有制,二元運行就是既要完成現行政治結構所要求完成的意識形態宣傳任務,又要通過廣告等市場經營收入支撐媒介的經濟再生產。簡言之,用市場上賺取的經濟收入完成意識形態領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務。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我國有關媒介的政策環境進一步放開,各種媒介的數量增長迅速、產業規模擴大、廣告營業額上漲明顯、媒介市場競爭日益加劇 [9] 。 1996 年 1 月我國第一個報業集團,也是第一個媒介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成立,標志著我國媒介在個體實現市場化的基礎上終于又開始進入規模經濟的時代。
可以說,連續 20 年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為我國媒介的市場化和集團化創造了良好的經濟條件,但是,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后期以來,我國經濟的增長開始減速,進入一個結構轉型和制度創新,特別是需要以產業政策促進發展的新階段 [10] 。我國媒介業也從近 20 年來的媒介內容、形式,強化市場經營,增加廣告收入等微觀改革中開始走入了一個瓶頸,即缺乏合理的產業結構和高效的媒介制度。
通過考察近 20 年我國媒介市場化帶來的問題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瓶頸。首先,媒介總量相當大,但是,媒介資源分散,難以形成規模經濟( economy of scale ),也不可能形成范圍經濟 (economy of scope) 。同時,為了爭奪市場份額,媒介之間常有惡性競爭。其次,當日益市場驅動的媒介開始出現程度不同的多元化傾向,資本權力開始或多或少地對媒介產生影響的時候,政府便通過政策等手段開始控制媒介業的“散、濫”,以保證媒介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根本定位。因此,在政府政治權力的調控下,加上 90 年代后期我國經濟增長放緩,從 1999 年開始,媒介市場業出現了緊縮,媒介的廣告收入增速放緩,乃至部分媒介出現收入下降的現象。
的確,市場化實現了我國媒介業超常規增長,但也帶來了媒介部分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 、經濟與社會資源浪費、政治控制減弱的問題。
(二)集團化的提出及實踐( 1996 年 -2001 年)
媒介集團化是國內外和媒介業內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就內部動因而言,主要有面對媒介日益市場化后的形勢,強化而不是削弱政治控制的考慮,這是政治利益集團最為重視的根本因素;面對我國國內媒介業規模大但實力弱的狀況,整合媒介資源,逐步強化核心媒介,調整和合并弱勢媒介,這是政治利益集團推進集團化的直接因素;國內其他產業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開始的成立企業集團,組建國有企業的“國家隊”,形成產業的“航空母艦”,參加國內和迎接跨國公司競爭,也影響了媒介業的決策者,這是政治利益集團推進媒介集團化的時代背景 [11] 。就外部動因而言,全球化是我國不得不接受的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結構和新的世界秩序, 20 世紀 90 年代歐美國家媒介產業風行的購并、重組、整合、集中浪潮,給我國分散而弱小的媒介產業以極大的震動。為了保證政治集團在媒介產業中的長久利益,該利益集團就只有不斷調整自己以應對全球化的進攻,不論這種調整是在表層的政策、管理手段和控制方式,還是深層的制度安排。
自1996 年開始,我國政府不斷調整規制體系,連續發布有關媒介業的法令和政策多種,涉及媒介業產權所有、結構調整、組建集團、內容版權、媒介進入資本市場、向跨國媒介集團及國際資本開放的領域及程度等 [12] 。這是我國 50 多年來最為集中的時期,這些政策更加突出了政府對媒介產業的調控權和壓力程度。
在代表市場力量和資本力量的媒介業多年說服( lobbying )之后,我國媒介決策者終于在 1996 年開始了集團化的進程。 1996 年,我國第一家報業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成立。從此,在市場驅動和競爭需要下,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各種媒介集團。截止 2001 年 12 月我國正式加入 WTO 時,我國已經有報業集團 26 家、廣播電影電視集團 8 家、出版集團 6 家、發行集團 4 家 [13] 。
我國媒介集團化與歐美國家媒介集團化有著媒介整合和集中的外在相似形。但是,在其他方面有著相當大的差異。首先,在集團化的政策和規制方式上,歐美是放松管制( deregulation ) , 而我國是強化政治管制,有限度開放經濟管制;歐美國家越來越從對媒介所有制、集中的問題的結構規制( regulation of structure )轉向了行為規制 (regulation of behavior) [14] ,而我國是還處在結構規制的起步階段;其次,在集團化的手段上,北美是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進行,而我國是通過政府力量強行重組而成( bureaucratic-led ),其中,組織結構設置、人力資源調配、媒介資源配置等均在行政命令中完成,而且仍然保持了政治階層組織的根本特征;再次,在集團化的路徑上,歐美可以通過購并、整合、細分、戰略聯盟、跨國化 (acquisition, merger, persific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trans-nationalization) 等渠道實現集團化,而我國則是主要通過合并渠道完成,在現行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中,不可能真正戰略聯盟等渠道建構跨地域、跨媒介的媒介集團。總之,我國的媒介集團化并未打破原有政治經濟權力結構,而只是通過政府行為實現的產業重組。在我國加入 WTO 后的幾年中,日益顯現出一定的發展困境。
三、后 WTO 時代我國媒介產業重組的繼續:集團化的困境
全球化時代國際政治經濟力量變化給我國媒介集團化提供了一個全新參照系和外部格局。
一是政府干預與發展的關系。冷戰結束后,自由主義政治和經濟思潮得到復興。一方面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歐洲國有企業紛紛私有化。 80 年代以后,跨國公司日益成為政治經濟的主導力量之一,公司經濟成為當代產業經濟的標志。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從拉丁美洲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逐步轉向東亞國家出口引導增長,期望都能夠出現東亞經濟奇跡 [15] 。但是,從拉美和東亞先后出現的金融危機看,學者們已經開始懷疑這種建立在政府干預基礎上的密友型資本主義( crony capitalism )的有效性,指出了它巨大的局限性 [16] ;經濟學家研究認為韓國政府用了不到 20 年的時間通過政府行為打造了世界級的韓國企業,而 20 多年來我國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改革,組建國家隊始終有相當難度,由此,對我國政府打造“國家隊”的發展戰略,學習其他東亞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也提出了質疑 [17] 。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正是由于政府作用過大,而市場力量不夠,同時,沒有良好的金融體制,才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的問題 [18] 。
二是發展模式和路徑問題。上述發展中國家在資本力量成為主導之前的前全球化時代,即冷戰時期發展的,當時它們依靠國內政府支持、國外美國保護等發展內向和外向經濟。而我國則面對的是公司經濟已經成為經濟主導,市場自由開放和資本自由流動的全球化時代,我國沒有了外部的保護力量,面對著市場和資源很大程度上已經被重新劃分后的格局 [19] 。在這種不同政治和經濟時空下,不同政府和產業占有的資源有很大的不同,這也就決定了發展戰略會以資源為基礎而出現不同的路徑方向 (path dependence) [20] 。因此,我國媒介重組與歐美媒介重組會有著不同的路徑和結果,雖然,形式相似,甚至我國媒介重組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和學習西方和其他國家。
除了上述的外部環境和時機的變化,我國媒介產業重組還面臨著國內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特殊情境。首先,經過 20 多年經濟高速發展,我國積累了大量的資金,特別是民間資本充裕,它們急迫地希望進入媒介產業的重組過程中。同時,媒介產業本身也已經具有了相當的經濟規模。其次,近年來,我國的政治權力結構變革使得政府規模縮小,政府職能開始發生變化,即政府的政策性職能與監管職能相互分離 [21] 。政府職能調整使得剛剛運行不久的媒介集團的產權歸屬和管理歸屬等成為現實的問題。
自 2001 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以來,我國媒介產業重組的速度加快,截止 2002 年底,我國共有報業集團 38 家,比上一年增加 12 家;廣播影視集團 20 家,比上一年增加 12 家,出版發行集團 15 家,比上一年增加 5 家。速度之快反映了急迫的政治和經濟需要。可是,卻越來越陷入一種難以突破的困境。這種困境正好呼應著國際上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媒介整合和集中所產生的問題,即席卷主要歐美國家的媒介整合和集中造成了媒介所有制的高度集中,資本操縱公共利益日益突出,媒介生產過剩,導致資源巨大浪費等。類似的問題在我國媒介集團化過程中也已經開始出現。
首先,制度困境,即媒介產業重組政策與現行我國政府制度結構的矛盾日益突出。 2001 年 8 月政府下發的“ 17 號文件”明確提出以資本和業務為紐帶組建跨地區、跨媒介的媒介集團,集中全國媒介資源優勢,打造我國媒介的“航空母艦”。但是,這種政策要求與我國現有的政府結構不相匹配。一方面,縱向上,我國媒介是隸屬于各級政府的,就廣播電視業而言,中央 “ 82 號文件”等相關文件,要求減少廣播電視機構,撤消地區(市)和縣級廣播電視機構等。這就是我國廣播電視體制改革中的“四級變兩級”。但是,自文件發布以來,執行過程并不順暢。地區(市)和縣政府,特別是我國經濟發達地區的地、市、縣政府拖延執行政策,其實,根本原因是經濟上的考慮,因為如果撤消這些機構,就意味著這些政府原來的投資和未來的收益都拱手相讓給了上級政府。另一方面,橫向上,現行我國媒介均為一級地方政府所有,跨地區意味著一個地方政府對媒介的投資、所有權和未來的預期收益都將重新歸屬為跨地區媒介集團所在地的那個政府所有。這對地方政治和經濟利益是巨大的沖擊。還有一方面,各級政府中有多個部門管理媒介事務,黨的宣傳部整體上負責媒介,特別是媒介的政治正確性,廣播電視局負責廣播電視電影的管理,新聞出版局管理報紙、雜志和出版。音像和電子出版物又分屬文化、廣播電視、新聞出版多家管理,互聯網又有國務院和各地新聞辦公室負責。這種政出多門的現實大大降低了我國形成跨行業和跨媒介的媒介集團的可能性。媒介產業重組需要付出很高的制度成本。
其次,產權困境,即媒介集團屬性和產權結構模糊不清。根據現在的界定,媒介集團是事業集團、企業管理。這是混合了公共和商業兩種功能和屬性的機構。這就為媒介集團在進入股市、融通資本、產權交易和治理結構改造上設置了障礙,同時,更為媒介集團處理政治、經濟與公共三者利益之間關系帶來了難度。
再次,壟斷困境。隨著 72 家各種媒介集團的成立,媒介業新的壟斷正在形成,而且這些集團占有了我國最優勢的社會資源,是我國媒介產業的中心,是媒介市場的主流。集團化后國有的弱勢媒介、邊緣媒介,如西部媒介、主流體制外生存的民營的媒介企業日益喪失生存空間和能力。媒介集團與廣告客戶、媒介內容提供商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個地方媒介集團壟斷了當地的廣告價格和媒介內容產品價格,市場喪失了基本的競爭可能。原有體制下已經存在的條塊分割和行業壁壘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新的壟斷又初顯端倪。
第四,發展戰略困境。由于媒介機構是一級政府機構,完全復制政府的科層制結構,導致了媒介治理結構的模糊,并沒有形成委托人 - 代理人( principal-agent )的治理結構;由于是政府行政機構,媒介集團中各級管理者最為關心的是個人職位的最大化,而不是集團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媒介集團缺乏長期的戰略設計,而多為短期的戰術操作;集團化整合過程中有關組織結構、人力資源結構等核心問題并沒有實質的變動。另外,長期以來媒介重復建設,大量同質媒介,在同一市場和層面進行著低水平的競爭。所有國有媒介優不勝、劣不汰造成了生產能力的相對過剩,市場有效性不足,這在我國的電視產業中最為突出。媒介集團普遍缺乏規模經濟效益和范圍經濟效益,核心競爭力不突出,經營分散,管理水平低下,效益下滑。而如今,北美國家的媒介已經從媒介集團化合并走向了日益關注市場占有、成本管理、保障收入流,即從外延擴張走向內涵優化 [22] 。
最近,中央要求,近段時間我國的媒介集團暫停批復,主要是對現有媒介集團進行實驗,總結經驗以后再推進集團化。可以看到,這些問題的解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在后 WTO 時代中經過一個時期的不同力量互動才可能完成。
四、后 WTO 時代我國媒介產業重組的結果:資本化
資本化:多種力量互動的過程
經過幾年的集團化運行,媒介產業重組出現了困難,這種困難是我國現行政治經濟權力結構下容易產生的結果。如前所述,我國媒介產業重組的制約力量是多重的,因此,僅僅依靠一種力量,特別是政治力量完成重組不完整的。應該說,如同任何社會變動一樣,我國媒介產業重組既不完全是自己意愿的結果 , 又不完全是外部力量決定的結果,實際上,它是決定論和自由意志互動而導致的選擇 [23] 。從現實看,制約我國媒介產業重組的制度體系日益受到來自其他力量的沖擊。可以說當前正是我國媒介產業重組力量較量膠著的時期,長遠看,從維護自己既得利益這一根本原則出發,不同利益集團將會協調多種力量的比例,通過現代政治行為的精髓——妥協和折中方式,達到社會主要集團在政治、經濟利益上的平衡,也就是形成一個新的權力結構。
這個妥協和折中過程便是資本化過程,也是一個再制度化( re-institutionalization )過程,即政治力量與資本力量結合,政治力量借助資本力量繼續進行資本化后的政治控制,資本力量漸漸成為媒介重組的主要力量,它借助政治力量的保護獲得更加豐厚的資本回報。
資本化過程中主要有四重互動。首先,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外部力量與國內政府政治力量、媒介經濟力量互動。在我國加入 WTO 后,外部的影響力量,如跨國公司、外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將會日漸強大 [24] 。其次,國內不同政治集團力量互動。 20 多年來,中央政府的政治控制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業保護主義的消解 [25] 。這種地方和行業政治力量需要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因此,最后就是使用政治行為中最為常用的妥協與折中。比如,中央原來只希望中央和省級媒介組建媒介集團,可是在地方政府和媒介的強烈要求下, 2001 年底政府下發的“ 17 號文件”實施細則中對原有政策進行了修改,改為“有相當實力的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在完整轉播中央和省區市廣播電視節目的前提下可以組建集團:‘有相當實力’是指在 2000 年達到以下條件:國民生產總值在 800 億元以上;常住人口在 500 萬人以上;具有較強的廣播電視綜合實力”。地方政治力量終于獲得了中央的妥協,而且雙方政治力量最終還是以經濟指標為妥協標準。第三,國內政治力量與經濟力量互動。無論是國有和民間資本都有進入我國媒介產業的強烈愿望。政府政策中已經向民間資本開放了部分媒介產業領域,雖然目前僅局限在圖書報刊的發行、音像與電子出版物的流通等。與此同時,媒介已經越來越經常地、策略地將經濟驅動放在第一位。第四,非媒介產業資本與媒介資本互動。 2001 年,報紙、雜志、圖書、廣播、電視、電影全年總收入只有 800 億元人民幣 [26] 。我國媒介繼續發展的資本資源非常有限,因此,急迫希望引入日益增長的境內社會資本和境外資本。
(二)資本化過程分析
其實,自 2001 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媒介重組中的主要力量 — 政府、跨國媒介集團、媒介與其他利益集團已經逐步進行著資本化。
1, 中央政府政策推動資本化過程
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在維護和強化政治和意識形態控制的基礎上,通過修訂決策和規制主動適度許可資本化。我們通過分析自 1999 年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相關文件、法規可以看出,一是在對媒介重組的態度越來越積極;二是對媒介的政治控制仍然非常嚴格。雖然控制的范圍在調整,即從原來控制媒介一切傳播行為縮小為控制媒介的新聞、意識形態宣傳等部分領域,但是控制卻越來越嚴格;三是對資本進入媒介產業正在逐步放開。為了兌現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時的有關承諾,政府已經允許外資和國內國有及私人資本進入有關發行、流通等領域 [27] ;四是鑒于我國的政治制度,這種政策和規制的開放將是漸進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確定性。近年來最引人注目的政策就是 2001 年 8 月中央政府下發《關于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干意見》(“ 17 號文件”), 12 月《〈關于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干意見〉的實施細則》。兩個文件要求積極大力推進媒介集團化改革,提出要組建跨地區、跨媒介的大型傳媒集團,適度開放了長期以來一直比較敏感的媒介業融資問題、媒介與外資合作等領域。今后,將有更加實質性的開放政策出臺。
2 ,跨國媒介集團資本漸進式地、策略性地進入我國
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默多克就已經在我國香港開辦 STAR TV ,標志著國外資本期望進入我國媒介市場的開始。跨國媒介集團希望進入我國的直接動因有兩個,一是看到我國媒介市場的規模和潛在的媒介消費能力。二是要為其他跨國公司及其產品與服務進入我國發揮作用,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產品和服務在我國銷售,需要有更強營銷能力的跨國媒介為它們服務,而這些跨國公司都是這些媒介集團的長期客戶。跨國媒介集團進入我國有它相當強的優勢,表現在有雄厚的資本實力;多年積累的內容儲備和創意生產能力;先進的技術,如數字直播衛星、數字有線電視和網絡技術等;發達的市場營銷網絡和豐富的市場營銷經驗;業已形成的品牌效應;強大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益。特別值得關注的就是它們對我國高層政治集團公關的策略和能力。它們深諳我國政治權力結構,因此,進入我國實際上是從政府最高層的公關做起,逐步自上而下地打開其他政治集團的大門,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跨國媒介集團已經開始并將更大地程度發揮建構( frame )我國現行和未來媒介政策的作用。在全球化過程中,這種“電子獸群”( electronic herd )已經在其他國家發揮了這樣的作用 [28] 。
當然,這些跨國媒介集團進入我國還是有不少阻力的,特別是在當前。主要是第一, WTO 并沒有廣泛而直接地涉及媒介,特別是媒介核心產業開放的協議;第二,我國現行的政治制度和政策法律對跨國媒介集團大舉進入我國有明確的制約;第三,我國現有的媒介和其他產業有著自己的既得利益考慮,因此,對跨國媒介集團有著復雜的態度,它們喜歡跨國媒介集團的資本和媒介產品,但是不希望它們進入我國瓜分我們自己的市場。
盡管有這些阻力,有的跨國媒介集團進入我國已經漸有成效,有的還在規劃和觀望階段。總的看來,跨國媒介集團們進入我國采取的均為漸進式戰略,這種戰略既適應我國漸進融入全球化的實際,又便于它們掌控進入與撤出的節奏。它們的漸進式戰略體現在,第一,先從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協議中承諾開放的領域進入,然后逐漸進入其他領域。雖然首先進入的是流通領域,但是媒介流通環節常常是整個大眾媒介產業中不同角色權力分配的決定因素 [29] 。第二,先從我國高收入群體、強經濟實力市場進入,然后再逐漸面向多元化受眾和市場。到目前為止,我國已經允許 3 星級以上飯店接收 30 個境外頻道 [30] 。其實,這種開放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 30 個頻道中的部分頻道已經或早或晚地在我國許多地區的有線電視網中播放,特別是商業化的住宅區中,而居住在這些商業化住宅區中的人均屬于在我國的中高收入階層,而非僅僅局限在 3 星級以上飯店。二是我國頻道相對美國等地的頻道是弱勢,而進入我國的境外頻道相對我國本土的頻道則明顯地具有優勢,這種優勢來自內容、形式、品牌、營銷、我國人的文化勢位差心理等。兩種頻道的消費資本差異巨大,使得這種資本的相互進入出現巨大的不對稱 [31] 。第三,先從我國最高政治集團進行政治公關,然后自上而下地游說各級政府,努力與我國現有的政治利益集團產生親和;與此同時,嘗試與我國媒介聯合雇傭本地媒介人才,制作本地內容,滿足本地市場,分銷媒介產品和服務等,開始了它們在其他國家行之有效的“全球本土化”和“外包”( glocalization and outsourcing )的過程 [32] ,這正是全球化進程中國際勞動分工狀況在我國媒介產業中的體現。
3 ,媒介與其他利益集團極力推進資本化
我國媒介本身都已經是現實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它們從這種制度中獲得了巨大的政治、社會權力,以政府賦予的這些特權再去獲取豐厚的經濟收益。
媒介業者對現有制度具有兩重心理。喜歡的是這種制度具有的用政治權力換取經濟收入的作用,它們不愿意輕易放棄這種體制帶來的壟斷地位,而這正是媒介行業產生尋租現象的制度根源,這種尋租與國家介入并賦予權力直接相關。不喜歡的是這種制度具有的政治剛性以及由此帶來的政治風險性,經常會因政治需要而使它們不得不放棄經濟考慮,這使得它們自身經常處在協調政治與經濟平衡的過程中,更有甚者還會因處理不當而帶來管理者政治生命的終結。在這種時候媒介業就非常急迫地希望實現資本化,一是資本化可能帶來更大的政治空間,二是資本化可以讓資本成為主要標準,帶來更多的獲取經濟利益的機會,三是資本化可以解決地域和行業限制,使強勢媒介可以依靠資本力量形成跨地區、跨行業和跨媒介的媒介集團,迅速在我國尚未成熟的市場上完成媒介財富的集中。 2002 年開始,我國媒介市場已經進入買方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媒介業生存難度越來越大。它們不希望放棄政治賦予它們的特權,但是這種市場生存壓力將迫使它們更愿意親和資本力量,在尋找資本、開拓市場、整合聯盟等方面更加積極和主動。 2003 年特別是今后幾年我國媒介業吸收境外資本方面,將更多集中在類似人民日報、新華社這樣的大型國企報刊、廣電、圖書的強勢傳媒集團和境外強勢傳媒投資資本的合作方面,最大受益者也將是國內擁有行業壟斷資源的這些強勢媒體 [33] 。但是,從跨國媒介集團與我國的主流媒介進行戰略聯盟狀況看,它們可以從我國強媒介和富地區入手,獲得這些主流媒介在我國已經擁有的市場特權和資源特權,從而也成為現實的既得利益者。它們才可能是長期的最大的收益者。
其他利益集團包括地方政府、新興的經濟集團(國有和私有)和知識利益集團等。地方政治力量不希望失去自己手中的對媒介的控制,而且希望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力,從而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媒介為自己創造更大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利益。當前,新興經濟集團是所有力量中最為急迫推進媒介資本化的一支力量。國內外的各種國有企業、私營企業、證券市場、投資公司等關注研究我國媒介,尋找政策機會,希望進入我國的媒介業。 1999–2001 年它們“跑馬圈地”式地在新興媒介市場和市場化程度高的領域迅速擴張,占領市場,先不考慮投資收益 [34] 。現在,雖然收益不明顯,但從長遠看,這種等待不是沒有結果的,“時刻準備著”,待國內進一步改革金融體制,建立完善的公共政策制度,媒介資本市場是可以形成的;再者,我國新政府結構中已經打破對內貿易和對外貿易的區別,統稱為商務部,這意味著我國內部貿易壁壘,如地方和行業保護利益將會有所拆除,這將帶來新一輪的擴張。 2003 年,我國的媒介投資已經開始向將向價值型和戰略性投資為主轉變。
結 論
我國媒介產業重組是一個以資本化為根本特征的重新制度化過程。它是在放松規制思潮盛行、資本全球化以及公司經濟為主體的國際背景中和制度變革、市場驅動、資源和財富重新分配的國內環境中進行的。這個重組過程起始于 20 世紀 80 年代,興盛于 90 年代末期至今,它經歷市場化、集團化和資本化三個主要階段。但是這三個過程不是必然的線性關系,即經濟上的自由市場未必自然而線性地帶來民主政治、市民社會 [35] ,在這個過程中政治、經濟利益集團中的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市場、行政命令與資本要求、媒介與其他利益集團等之間正在進行著權力和利益的博弈,因此,我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是一個仍然處于劇烈變動中的結構。因此,在我國現行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中完成我國媒介產業重組的資本化,可能會產生復雜的后果。媒介資源、資本資源以及權力資源均在我國現行制度的急劇變動過程中日益集中。這種集中將會使我國媒介產業出現明顯的差距,表現在東部與西部媒介、中央與地方媒介、中心與邊緣媒介、主流的體制內媒介與非主流的體制外媒介等,在占有權力資源、媒介資源和資本資源上的分化日益加劇。另外,控制媒介的政治力量和資本力量之間此消彼漲,產生波動,使媒介發展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這在我國 20 多年來的媒介改革中已經可以看到,這對我國未來媒介產業的平穩發展非常不利。還有,從長期看,資本力量裹挾著政治力量形成的雙寡頭 (duopoly) 壟斷將會對媒介的公共利益角色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特別是在政治力量日益缺乏全新的意識形態控制力和吸引力的情況下,資本以及受其支配的價值體系將會日益侵蝕本來就已經非常脆弱的公共利益和價值體系。
如果說早期的媒介產業重組缺乏明確制度化目標的話,那么,到了資本化時期,一個新的制度安排必須在這個博弈的過程中誕生,經過博弈,政治力量逐步擁抱經濟力量,資本在媒介的政治和經濟活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制度既是個體選擇的結果,更是集體決定的過程 [36] ,由于既得利益及其新的意識形態的作用,這一過程是不可逆的 [37] 。
[1] Ferguson, Niall (2001): 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London: Allen Lane
[2] Nolan, Peter (2001):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National Champions,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Big Business Revolution. Basingstoke; New York: Palgrave。Pp.208-10, 214
[3] Friedman, Milton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yek, F.A. (1978):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iedma n, Thomas L. (1999):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4] Schwartz, Herman M. (2000): States versus Markets: 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Economy. Basingstoke: Macmillan, 2nd Ed.
[5] 汪丁丁(2002),《制度分析基礎:一個面向寬帶網時代的講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第53,231-244頁
[6] Wright, E. O. (1994): Interrogating Inequality: Essays on Class Analysis, Socialism, and Marx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7] 邱澤奇(2003),《新興階層與制度變遷》,見《21世紀經濟報道》,2002年12月30日,第49版
[8] Moore, Thomas (2002): China in the World Market: Chines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Reform in the Post-Mao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 江藍生、謝繩武主編 (2003):《2003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179頁。
[10] 劉國光、王洛林、李京文主編 (2002):《2003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1] Moore, Thomas (2002): China in the World Market: Chines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Reform in the Post-Mao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306-7 Nelson, R.R. and Winter, S.G.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16-20
[12] 江藍生、謝繩武主編 (2003):《2003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3] 同上注,第8頁
[14] Doyle, Gillian (2002): Understanding Media Economic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p.170-2
[15] Cohn, Theodore H. (2003):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Pp.395
[16] Moore, Thomas (2002): China in the World Market: Chines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Reform in the Post-Mao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89, 310-1
[17] Nolan, Peter (2001):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National Champions,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Big Business Revolution. Basingstoke; New York: Palgrave. Pp. 306-10
[18] Friedma n, Thomas L. (1999):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 Nolan, Peter (2001):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National Champions,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Big Business Revolution. Basingstoke; New York: Palgrave. Pp. 189
[20] Haberberg, A. and Rieple, A. (2001):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s. Harlow, England;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Pp. 29, 217-8 Nelson, R.R. and Winter, S.G.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1] 劉國光、王洛林、李京文主編 (2002):《2003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汝信、陸學藝、李培林主編(2003):《200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175頁
[22] Damsell, Keith (2003): Broadcasters, Publishers Shift Focus. The Globe and Mail, Toronto, March 26, 2003, Page B12
[23] Bhaskar, Roy (1978):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Bhasker, Roy (1989): Reclaiming Reality. London: Verso; Giddens, Anthony (ed.) (1974): Positivism and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Giddens, Anthony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Basingstoke: Macmillan;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4] Moore, Thomas (2002): China in the World Market: Chines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Reform in the Post-Mao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4-58
[25] 同上注。Pp. 279
[26] 江藍生、謝繩武主編 (2003):《2003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7頁。
[27]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關媒介業的主要具體承諾減讓表》,自《我國入世法律文件參考譯文》,見外經貿部政府網站,www.moftec.gov.cn
[28] Friedma n, Thomas L. (1999):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29] Turow, J. (1997): Media System in Society: Understanding Industries, Strategies, and Power.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ers. 2nd Edition. Pp. 14
[30] 《經批準2003年度可供國內三星級以上涉外賓館等單位申請接收的境外衛星電視頻道名單》, 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網站,http://www.sarft.gov.cn/page/zhglxx/wxpd.htm
[31] 江藍生、謝繩武主編 (2003):《2003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96頁.
[32] Alexander, A., Owen, J. & Carveth, R. (ed.) (1998): Media Economics: Theory and Practice.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2nd edition. Pp.223-247
[33] 北京新華在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2002):《2002年中國傳媒報告摘要》。http://www.xinhuaonline.com
[34] 同上注
[35] Ferguson, Niall (2001): 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London: Allen Lane. Pp. 20
[36] 同上注。Pp. 422
[37] 汪丁丁(2002),《制度分析基礎:一個面向寬帶網時代的講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第2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