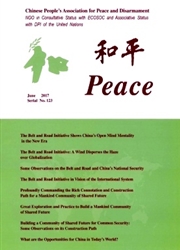制度經濟學角度下的中外合作辦學供求關系
佚名
摘 要:文章從制度經濟學角度入手,通過分析制度對中外合作辦學供求關系的影響,結合中外合作辦學發展過程,分析了制度對于不同時期中外合作辦學發展的影響規律。從而找到中外合作辦學現階段制度建設的漏洞,提出以“本土化”和“引入競爭機制”為目標的制度建設,是解決現階段中外合作辦學供求關系失衡的方向。 關鍵詞:制度制度經濟學 中外合作辦學 供求關系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09)08-049-02 一、中外合作辦學供求的總體情況 從1995年當時的國家教委頒布《中外合作辦學暫行條例》開始至今,中外合作辦學在這14年當中起起伏伏,1995年有71家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到2002年底,中外合作項目達到712個,增加了9倍,至2003年已經上升到800多個。但是經過2005、2006年的復核工作,截至2007年9月,經教育部批準的授予國外學位與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學位的合作辦學在辦項目(本科和碩士)只剩下142個,其中新批項目29個(本科13個,碩士16個),截至2009年1月,通過復核的和新批準的項目發展到了327個,機構22家。其中開辦本科教育的項目有247個,機構19家,批準碩士以上教育的項目有80個,機構5家。可以說表面上中外合作辦學經歷了上世紀90年代末的方興未艾,21世紀初的蓬勃發展,2004年開始的內部淘汰,再到2008年的逐漸恢復。這說明中外合作辦學的市場的供求關系一直處于失衡狀態,市場不穩定,嚴重影響中外合作辦學的健康成長。自1993年6月30日國家教委下發了《關于境外機構的個人來華合作辦學問題的通知》;1995年1月26日國家教委正式頒布實施《中外合作辦學暫行規定》;1996年1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頒布了《關于中外合作辦學活動中學位授予管理的通知》;2003年3月1日,國務院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2004年6月,教育部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實施辦法》。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這些制度的制定并沒有使得中外合作辦學市場趨于穩定,市場的失衡體現在《教育部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外合作辦學秩序的通知》(教外綜【2007】14號)中指出的突出問題,包括招生宣傳不實、不規范;學生不能如期取得國外學歷、學位;收費行為尚需進一步規范;辦學論證不嚴、合作協議不規范、不嚴謹,財務會計管理不符合相關法規;還有的是中方管理不到位,淡化甚至削弱應有的領導權和決策權;個別地方教育管理部門協調和監管職能不到位等。因此十分有必要從供求關系入手,討論如何通過制度建設使其擺脫原來失衡的狀態,回到健康發展的道路上來。 二、制度影響下的中外合作辦學供求關系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一個市場的發展首先必須用制度因素來解釋。奧爾森認為市場的發展不同在于其制度和經濟政策之間的差異。諾思把制度因素內生于經濟體系,認為即使沒有發生技術變化的情況下,通過制度創新亦能提高生產率,實現經濟增長。劉易斯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內生變量進行分析,把制度與資金、技術和勞動等要素等同對待,并認為制度的投入更為重要,因為其它要素的投入規模受制于制度要素。因此本文同樣把中外合作辦學制度作為一種重要市場要素進行分析,對于不同階段制度要素的特點對于中外合作辦學市場的影響進行分析①。 中外合作辦學市場實際上是一個國外資源提供者與國內承辦者結合的市場。在這個市場上,需求曲線指參加者對于國外教育資源的需求量(如圖1)。當在本國市場上獲得外國教育資源的費用高于出國留學時,本國市場上對于外國教育資源就不會有需求,隨著費用的降低,需求量在上升。但是費用下降到一個P0水平時,需求量將不會再隨著價格變化,這時說明費用是和本國提供的教育費用相等。需求量已經和本國教育需求量重合。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做需求量Q是P和P0的函數:記為Qd=f(P,P0) 供給曲線指承辦者根據市場上價格提供的合作機會的量。(如圖2)當市場上的價格低于辦學成本,不能產生收益時,承辦者不會進行中外合作辦學活動。當價格上升,收益上升時,承辦者越來越多,當市場價格達到P0水平時,供應量不會隨著價格變化,供給無限大,這時說明進行中外合作辦學的活動的收益已經高于進行本國教育投資所獲受益,市場上對中外合作辦學的供給和對本國高等教育的供給重合。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做供給量Q是P和P0的函數:記為Qs=f(P,P0) 三、中外合作辦學制度對供求關系的影響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制度是經濟分析的一個內生變量。在需求函數和供給函數Q=f(P,P0)中,P0就是制度這個內生變量的對應變量。從圖1和2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制度對中外合作辦學供求關系的影響。中外合作辦學的制度投入決定了P0的水平。不同時期我國采取了不同的制度,隨之而來的就是直接影響了中外合作辦學供求關系。導致了制度變遷的不同形式和特點。如果一個制度有利于引進國外教育資源,那么P0的水平在需求曲線上就會下降。同理如果中外合作辦學制度限制了中外合作辦學的競爭力,那么需求曲線上的P0水平就會上升。同時當一個國家采用剛性的制度設計時,如果此時鼓勵合作辦學,那么P0水平線就會消失,也就是說需求不再是P和P0的函數了。同理在供給曲線上,如果中外合作辦學的制度有利于國內教育者進行合作辦學,那么P0水平線就會上升,反之下降。在國家采取剛性制度設計時,如果鼓勵合作辦學,那么供給線與P0線重合,說明供給完全和制度相關,與P無關了。 四、市場參與者的策略選擇 在中外合作辦學的發展過程中,概況起來大概有以下幾個狀態: 狀態一(理想狀態)。此狀態是市場最均衡的狀態,也就是說合作雙方各得其所,資源配置最為合理,即最優狀態。因此,這一狀態只能是理想狀態,現實中很難實現,原因在于學習理性的存在,市場的最終結果必然是一個更優狀態而非最優狀態。另一方面中外合作辦學本土化的成功將導致供求曲線向這種狀態變化。 狀態二(有交點)。 情況一:當市場的費用水平在交點以上時(PA水平),市場對國外院校的需求因為費用的原因受到抑制,而國內合作方卻因為有超額利潤而供給充分。這就造成了市場上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眾多,但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很低。這與2003年時市場的狀態吻合。當時由于中方的合作方看到了中外合作辦學市場上的利潤很高,所以全國各個大學申請成立了800多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但是由于市場需求有限,經過一年以后,大多數項目都無疾而終。 情況二:當市場的費用水平在交點之下時(PB水平),市場對國外院校的需求因為費用的原因很旺盛,但是國內合作方卻對于開辦中外合作辦學猶豫不決,認為合作辦學帶來的利益有限,不如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效果的地方。這與早期的中外合作辦學的情況吻合。當時中國教育市場還沒有開放,國內高校對于引進國外教育資源的理解還不太清楚,在加上80年代正是官方大批派出留學生的時代,需要雖然旺盛但是國內大學應之寥寥。只有一些像復旦大學、人民大學和南京大學這些頂尖高校做出了合作辦學的嘗試,而且當時的合作辦學是鮮有盈利的。這也造成了早期的項目在開辦一段時間內,由于資金上的困難而難以為繼。 狀態三(無交點)。 在這種狀態下,對于國外優質資源的需求在一個較高的費用水平上達到滿足,而中方的合作院校在一個較低的費用水平上達到穩定。也就是說國內對于國外教育資源的選擇比較挑剔,一般的教育資源無法達到國內對于教育的總體需求,費用已經不是國內對于國外教育資源選擇的優先條件,更重視品質和教育質量成為了國內對于國外教育資源的選擇觀念。而同時,國內的合作方不再把主要精力投向與國外大學建立合作辦學上,或者說國內合作者對于國外合作辦學的認識使得他們只愿意在較低費用水平上進行合作,除了經濟利益外更看中其他方面。但是這種狀態下,我們必須防范一些情況的出現,例如國外的一些“野雞大學”降低費用水平在國內進行合作,或者一些國內低端的合作伙伴出現,如公司或者以營利為目的的機構開始從事合作辦學,擾亂市場。 五、制度對于供求曲線的影響 制度對于供求曲線的影響主要在于P1到PA的空間和P2至PB的空間大小,或者說決定了PA和PB的水平。如上節所指出的,這個空間的大小是由于市場的非正式約束性因素決定,例如文化、教育觀念等。如果中國的民眾認為只有學習國學才最重要,那么P1到PA的空間就會很大,而P2至PB的空間就會很小,這說明國內市場對國外教育資源興趣不大,而中方合作院校也沒有興趣和國外合作,一心就進行自己的國學研究就行了。這有點像當年的科舉制度盛行之時的狀況。而反過來,如果所有的人都認為國外的知識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不惜代價地讓孩子接受“外國式”教育這就使得P1到PA的空間就會很小,而P2至PB的空間就會很大。此時國內的教育機構就會想方設法地與國外教育資源相結合。 作為調節此空間的唯一有效工具就是制度。這里面存在兩個層面上的制度,一個是國家的制度,另一個是個體的聯合體。國家的制度是一種制度設計,是通過強制力為保證來實施的。而個體的聯合體,例如某種協會、國際大學聯盟都是在自愿的基礎上進行合作,并制定統一的章程和制度。在這方面我國國內的大學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政府的延伸,通過各級政府他們已經被統一在一個制度下了,而國外高校間都是以行業協會或者大學聯盟的形式進行合作,國外政府的制度對于大學非常寬松。因此在進行合作的時候我國教育制度,更準確地說是中外合作辦學制度對于空間的大小起到了直接作用。 六、現行制度的漏洞 其一是現行制度規定了中外合作辦學的公益性原則,這必然導致P2至PB的空間的變小,PB就會向P2方向靠攏。因為這一規定剝奪了中方合作方經濟收益的權利,換句話說,那個大學把中外合作辦學辦成了非公益性的,就是與國家制度精神不符。而大學既是政府的延伸,那么大學的領導們就不會為了這一點經濟利益而冒天下之大不韙。但是,同時現階段國內對于國外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還是較高,也就是說P1到PA的空間也是有限的。這就造成了市場的需求供給曲線變成如下圖: 因此,國內市場對于國外教育資源的需求與國內高校間就存在了一個空間(PA-PB)。這在制度上就造成了需求與供給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兩者間在現階段很難有交集。這就造成了制度的一大漏洞,而這個漏洞就帶來了引進國外教育資源的質量下降,同時,國內的一些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變成了高收費低門檻的高考落榜生的收容所。 其二是中外合作辦學和現行高度教育的雙軌制。由于中外合作辦學制度中沒有規定其與現行高等教育制度的接口,例如招生和就業已經學生在校管理。這使得現有的中外合作辦學缺乏競爭力,國內頂尖高校對于辦中外合作辦學的積極性下降同時,由于畢業生得不到正規計劃內學生的種種制度保障,國內市場對于其需求就在減弱,PA就會向P1方向靠攏,社會表現上就是有錢不如把孩子送出國,也不要上國內的中外合作辦學。因此漏洞就會越來越大,政策希望出現的優質國外教育資源越來越少,市場變得魚龍混雜。 七、現行制度的改進 如果想彌補此漏洞,就必須通過外力使兩者產生交集。一種方式是通過政府補貼,彌補國內合作院校的損失,即(PA-PB)這個水平。在不影響國內需求的情況下,拉升供給。比較典型的案例是北航的中法學院。這個學院是北航與法國工程師大學合作,引進法國教育資源,通過國內高考進行招生,費用及其待遇與國內完全一致的合作辦學項目。開辦至今受到國內市場的高度認可。同時政府為此項目投入了專項資金用來彌補中外之間的費用差距。這個項目是典型的招牌式項目,到現在這種模式也沒有在制度上進行推廣。另一種方式是改變雙軌制,在制度上建立中外合作辦學與現行高度教育制度的接口處,提高中外合作辦學的口碑,對于中外合作辦學的畢業生進行追蹤,與現行高度教育的畢業生進行對比,讓市場主動接受中外合作辦學,改變原有的觀念。總而言之,制度的建設應該立足于如何促進中外合作辦學“本土化”(localization)這個方面,本土化的成功與否是中外合作辦學成功與否的關鍵。 同時,應該把中外合作辦學當作教育改革的一種有益嘗試,在WTO服務貿易總協定的框架下為我國教育市場上引入競爭機制,給予中外合作辦學平等的市場競爭地位。不要再用雙軌制等制度上的設計來制約中外合作辦學發展,人為地制造不平等競爭,使得中外合作辦學先天不足。另外,應充分利用中外合作辦學這個渠道,了解國外先進的教育管理理念,改善我們的教育制度,在教育理念、學校評估機制上進行大膽改革,對我們現行制度進行改進。 注釋: ①宋勝洲.基于知識的演化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23. (作者單位:北京工業大學國際交流合作處 北京 100124) (責編:若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