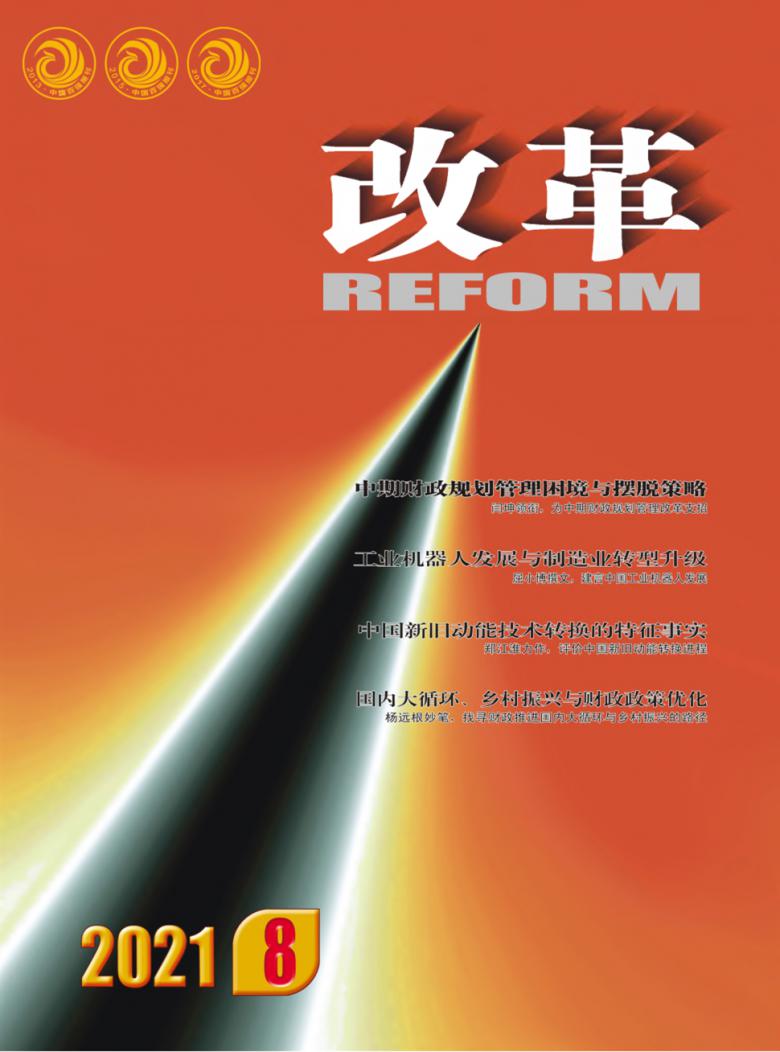論清朝前期外貿政策中的內外商待遇不公平問題
佚名
一、馬克思認為清朝外貿政策具有閉關性和排外性
馬克思在1853年所寫的《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曾有下列意見:
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不列顛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了,開始建立起聯系。[1]
馬克思還認為,清朝實行對外閉關自守政策,不僅有著地理上和文化(人種)上的原因,同時還有著滿清貴族統治全國的原因:
仇視外國人,把他們逐出國境,這在過去僅僅是出于中國地理上、人種上的原因,只是在滿洲韃靼人征服了全國以后才形成一種政治制度。歐洲各國從十七世紀末為了與中國通商而互相競爭,它們之間的劇烈糾紛曾經有力地推動了滿洲人實行這樣的排外政策,這是毫無疑義的。可是,推動這個新的王朝實行這種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國人會支持很多的中國人在中國被韃靼人征服以后大約最初半個世紀里所懷抱的不滿情緒。由于這種原因,外國人才被禁止同中國人有任何來往。[2]
在上述文字中,馬克思對于清朝前期的對外貿易政策做了兩個方面的認定,一是清朝前期對外貿易政策具有閉關性,二是清朝前期對外貿易政策具有排外性。而正是這種對外國人的排斥性決定了清朝前期對外貿易政策的閉關自守性。
馬克思的上述觀點,自五十年代以來,基本上被我國學術界的多數人所接受,并成為人們表述中國清朝對外關系的主流意見,即:清朝在鴉片戰爭以前采取了閉關鎖國政策,而閉關政策造成了中國近代的落后挨打。
--------------------------------------------------------------------------------
[1] 馬克思:《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載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2頁。
[2] 馬克思:《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載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6至7頁。
二、我國學者對于馬克思關于清朝閉關政策觀點的補充或否定
我國學術界對于馬克思的上述觀點雖然接受,但自80年代以來圍繞著清朝前期對外貿易政策的閉關也有很多討論。1979年,戴逸以其敏銳的學術靈感,率先著文并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閉關政策的歷史教訓》一文。他認為,清朝統治者在與西方國家的早期接觸中,曾經采取了閉關政策。“清政府的閉關政策,一方面限制中國人民出海貿易,或在外國僑居,禁止許多種貨物出口;另一方面,對來華的外國人也作了種種苛細而不必要的限制和防范。”[1]在這里,戴逸對清朝外貿政策閉關性的認定,已從馬克思那里單純的對外商的排斥性,到對中國本土商人出海貿易的限制性。
對于馬克思的上述觀點和戴逸的論文,胡思庸在當年則發表文章表示不同意見:“人們把清政府對外國商人的嚴格限制當作閉關政策的主要內容,這是一種誤解。如果是這樣,那就可以說清朝基本上沒有實行閉關政策,因為那些規定有些是合理的,即令有些過苛的規定,也只是一些具文,基本上沒有付諸實現;再退一步說,即令實現了一小部分,那也只是閉關政策的一個側面,而且并非主要的側面。我們應該把西方資產階級所極力宣傳的那種觀念改過來。閉關政策的主要內容,不是對外國商人的‘防范’條例,而應該是它對國內所實行的一些商業的文化的政策”。具體包括:對國產貨物出口的嚴格限制;嚴格限制中國商人制造海船;長時期的“禁海”,海禁解除后又有一段時期禁止華人赴南洋等地貿易,以及種種對出國華商及海外華僑的刁難和迫害政策;絕大多數封建統治者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都采取不加的深閉固拒態度;對西方制造品,也不加分析地一概視為“奇技淫巧”而予以排斥;禁止中國史書流出國外;由行商壟斷對外貿易。“上述那些工商業、文化上的政策,才是閉關政策的主要內容”。[2]由此可見,胡思庸并不贊同馬克思把清朝對于外商的排斥而作為清朝實行閉關政策的依據,而認為主要依據應該考察清朝對于國內工商業和文化上的政策。
不過,從80年代以來我國學者發表的相關論文來看,贊同清朝閉關政策論者多傾向于戴逸的意見,即清朝閉關政策包括有對本國商人和對外國商人的兩方面內容。因此,在提出清朝實行閉關關政策的具體證據方面,不少人都把清朝實行“海禁”政策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限令廣州一口通商作為主要證據。[3]
而在清朝實行閉關政策的原因方面,我國學者對于馬克思的觀點也有不同看法。馬克思認為“推動這個新的王朝實行這種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它害怕外國人會支持很多的中國人在中國被韃靼人征服以后大約最初半個世紀里所懷抱的不滿情緒。由于這種原因,外國人才被禁止同中國人有任何來往。”戴逸先生雖然同意馬克思所認定的清朝實行閉關政策是滿洲貴族以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的政治產物,但卻還指出,“從根本上說,閉關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的產物。”而“清政府頑固地堅持閉關政策,還由于它和廣大人民群眾階級矛盾的尖銳化。”[4]胡思庸認為,清朝實行閉關政策,一是中國封建王朝重農抑商政策的延續,二是來自中國封建統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三是通過隔絕人民與外界的聯系,以利于專制統治。[5]張光燦則是從政治、經濟和思想等三個方面來認識清朝實行閉關政策的原因,具體包括漢族人民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反清斗爭,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天朝上國”的傳統思想觀念。[6]我本人也曾發表論文認為,“閉關政策是中國封建晚期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混合物”。“明清時期封建政治體制的高度壟斷性,決定了它必然要盡可能的阻斷中外之間的民間聯系。而中國領土的幅員遼闊,使控制技術更成為一個中國封建王朝建立有效統治的關鍵。它不象邦國林立的歐洲,生存中充滿著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和競爭。同時,中國經濟的自給自足性和國內市場的廣闊,使中國可以不依賴于海外市場,又為封建統治者的閉關提供了客觀物質基礎;文化傳統上的‘華夷’觀,也限制了他們對于海外世界的視野,妨礙了海權觀念的形成;而北邊邊防的長期威脅,又制約著明清政府對于海防的建設;而這種海防的薄弱,更迫使他們本能的通過閉關政策來進行自我保護。”[7]也就是說,閉關政策并不是清朝因為滿洲貴族以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的政治產物,因為明朝對于外國商人來華貿易的限制以及本國商人出國貿易的禁止更甚于清朝。[8]
關于對清朝在對外貿易活動中實行閉關政策的和作用問題,我國學者多認為它阻礙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窒殺了中國的生機和進取精神,從而造成了近代中國的落后挨打。例如,張光燦認為,“閉關政策的歷史影響是嚴重的,它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惡果。首先,清朝前期的閉關政策直接阻礙、摧殘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從而使中國在社會制度方面落后了一整個”;“其次,閉關政策還扼殺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最后,清代閉關政策造成了近代中國不斷挨打、受辱,這是最集中的惡果”。[9]但高翔卻認為,“閉關政策導致近代中國落后的說法是不準確的”,“18世紀歐洲產業革命爆發,中國在社會制度、科學技術、社會生產等重要領域全面落后于西方,只是歷史長期演變的結果”;而“以產業革命為代表的社會變革未能產生于中國,只是對數百年中國落后歷史的一次罷了,把這個落后完全歸罪于清朝以及由它推行的閉關政策顯然是不公正的。”[10]
不過,我國學術界也有不少學者不同意馬克思所認定的清朝實行閉關政策的觀點。郭蘊靜于80年代初就對清朝實行閉關政策提出了質疑。她在《清代對外貿易政策的變化----兼談清代是否閉關鎖國》一文中指出,清朝統治者入關口,因忙于國內統一戰爭,無暇顧及對外貿易。1655年以后,為了對付鄭成功的反清力量,清朝先后出臺了“海禁”令和“遷海”令,只是權宜之計,并非對外關系的既定國策。她還認為,“一、歷來任何主權國家的統治者,為了維護國家、民族的利益和自身的地位,在對外關系方面(無論政治或經濟)制定的政策、措施,都帶有限制性”;“二、清政府制定的各種規章制度,無疑是嚴厲的,有些條文過于苛刻。然而,其內容和目的卻沒有超出‘限制’與‘防范’的界限,并不是從根本上斷絕對外通商往來”;“三、所謂‘閉關鎖國’,并未見諸清代史籍、。而最早使用這一措詞的卻是西方列強,他們迫切希望擴大中國市場,憤于清政府的種種限制,而將之強加于清政府的”;“四、(清朝)即使關閉一些口岸,但并沒有影響對外貿易的進行”[11]。后來,黃啟臣、夏秀瑞、王永曾等人也通過自己的提出了相似的觀點。[12]
最明確提出馬克思的清朝閉關政策觀點失誤的中國學者是嚴中平先生。他在80年代初給中國近代經濟史專業研究生的授課過程中,曾就學術界主流學者所引以為據的馬克思關于清朝實行閉關自守政策的觀點,進行了專門的評述。他認為,“在明清兩代,中國政府是針對外國海盜冒險家的行徑,限制他們只許在少數港口進行貿易,并加以管束監督的,這是出于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和社會秩序的安寧所采取的國防措施。世界各國無不如此,中國當然也必須提高警惕。只要外國人在中國規章允許的范圍之內,進行貿易,他們就受到保護和優待。”實際上,據英國下議院東方貿易情況調查小組在1830年的調查,“絕大多數在廣州住過的作證人都一致聲稱廣州的生意幾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好做。”所以,他“不承認在歷史上中國封建政府,曾經實行過什么‘閉關自守’政策。更不承認,中國曾經出于地理上、人種上的原因,對外實行過‘野蠻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閉關自守’政策。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提法是一個失誤。”在他看來,馬克思之所以清朝對外政策問題上產生認識上的失誤,是由于深受當時西方殖民主義者有關報道和議論的影響。當時,清朝面對西方人在華的諸多不合活動,“只許英商在廣州一個口岸和政府特許的少數行商進行貿易,并對外國人的行動加以約束,禁止鴉片進口。于是在鴉片販子的帶頭之下,向中國推銷品的產業資本家,經營中英印貿易的商業資本家,從事歐亞航運的商船資本家,在英國內外市場上進行活動的銀行資本家群起鼓噪,一致叫喊中國仇外排外,貿易不自由。”于是,“閉關自守”就成為這些西方殖民者對清朝海外貿易政策進行詆毀和攻擊之詞。而事實上,清朝對外商來華貿易實行的是嚴格管理監督的政策。[13]
--------------------------------------------------------------------------------
[1] 戴逸:《閉關政策的歷史教訓》,載于《人民日報》1979年3月13日。該文又收于寧靖主編:《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91至98頁。
[2] 胡思庸:《清朝的閉關政策和蒙昧主義》,載于《吉林師大學報》1979年第2期。該文又收于寧靖主編:《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99至124頁。
[3] 除戴逸和胡思庸論文外,還可:汪敬虞:《論清朝前期的禁海閉關》,載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4至16頁;張光燦:《論清朝前期的閉關政策》,載于《寧夏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第20至25頁;陳東林、李丹慧:《乾隆限令廣州一口通商政策及英商洪任輝事件述論》,載于《歷史檔案》1987年第1期;朱雍:《洪仁輝事件與乾隆的限關政策》,載于《故宮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4期,第10至16頁;王先明:《論清代的“禁教”與“防夷”----“閉關主義”政策再認識》,載于《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97至106頁;高翔:《康雍乾三帝統治思想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444頁;吳建雍:《清前期對外政策的性質及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載于《北京社會科學》1989年第1期;向玉成:《清代華夷觀念的變化與閉關政策的形成》,載于《四川師大學報》1996年第1期,第131至137頁。
[4] 戴逸:前揭文;又見于戴逸:《乾隆帝及其時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408至409頁。
[5] 胡思庸:前揭文。
[6] 張光燦:前揭文。
[7] 陳尚勝:《也論清前期的海外貿易----與黃啟臣先生商榷》,載于《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96至107頁。
[8] 《明與清前期海外貿易政策比較----從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一書談起》,載于《歷史研究》2003年第6期,第45---57頁。
[9] 張光燦:前揭文。
[10] 高翔:前引書,第455頁、第457頁。
[11] 郭蘊靜:《清代對外貿易政策的變化》,載于《天津社會科學》1982年第3期。
[12] 黃啟臣:《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載于《歷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151至170頁;夏秀瑞:《清代前期的海外貿易政策》,載于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8月版,下冊,第1106至1119頁;王永曾:《清代順康雍時期對外政策論略》,載于《社會科學》(甘肅),1984年第5期,第100至106頁。
[13] 嚴中平:《科學研究十講----中國近代經濟史專業碩士研究生參考講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第192頁、第177至177頁、第172頁、第173頁。作者按:這本著作雖出版于八十年代中期,卻是嚴先生給1982級研究生授課時的講義。
三、“閉關”話語系統的片面性
我個人認為,嚴中平先生的這種觀點,指出了馬克思在看待清朝問題時受了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嚴重,非常值得注意和重視。我個人認為,“閉關”作為作為一種對清朝對外貿易政策的屬性取向,在用來研究清朝前期海外貿易政策時仍有諸多的片面性。
首先,“閉關”和“開放”等詞匯,是西方化國家的話語系統。通過這一話語系統,西方國家不僅非常巧妙地掩蓋了他們對清朝所要索取的貿易利益,也充分地顯示了他們將要建立的商業霸權。我們使用它作為標準來觀察農業文明國家的國際貿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有失公允性。
漢語系統中的“閉關鎖國”等詞匯,最初來自于日本。1801年,日本蘭學家志筑忠雄節譯德國人恩格爾伯特·肯普費(Engelbert Kaempfer)所著的《日本史》時,曾用“閉關鎖國”的概念來表述日本德川幕府初期的對外政策。[1]清朝末年,“閉關鎖國”等詞匯即從日本輸入中國。從德國人肯普費已明確指出日本德川幕府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的情況看,“閉關鎖國”等詞匯起源于西方國家。實際上,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西方部分對華貿易商人,由于清朝只允許他們在廣州一個口岸和政府特許的少數行商進行貿易,他們在對華貿易過程中的諸多要求并未能夠得到全部滿足,于是以“閉關”來病詬清朝的對外貿易政策,甚到叫喊中國人仇外排外。而自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后,英國政府在謀求對華關系的努力失敗后,也開始采用“閉關自守”等用語對清朝海外貿易政策進行詆毀和攻擊。由此可見,所謂“閉關”和“開放”等詞匯,是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奠立機器大工業生產格局后,并在與東方國家貿易表現理想與現實矛盾的情況下所出現的一種話語系統。因為隨著資本主義大工業體系的確立,西方工業資產階級不僅需要為其工業生產準備充足的原料,更需要為其大量的工業產品尋找市場。由此所出現的結果則體現為,他們不僅需要加強對已成為殖民地國家的控制,還需要對一些獨立的仍是農業文明的主權國家進行貿易擴張,甚至進行更大規模的殖民侵略。于是,“閉關自守”和“閉關鎖國”就成為他們指責這些主權國家妨礙其貿易擴張的武器,“開放”也就成為他們企圖打開這些國家市場的“文明”話語。而對于一些“后進的”農業文明國家來說,尤其是地大物博的中國(清朝前期),國民體系的高度自給自足性根本就缺乏這種“開放”政策的內部機制。所以,用這種西方工業化國家的標準,強加于農業文明國家的對外貿易政策,不僅有尊從西方國家商業霸權之味,也有生搬硬套之嫌。
其實,即使在當時算是標準的工業化先進國的英國,對其它國家也沒有采取他們所要求的“開放”。眾所周知,英國在17世紀以后曾連續制訂和實行排他性的《航海條例》,禁止外國商人染指英國本土以及其殖民地的運輸業和商業。而英國在工業革命以后,仍然存在著排他性的對外貿易政策。譬如,1785年英國與愛爾蘭之間所草擬的通商條約,原是為兩國工業品進入對方市場提供互惠特遇而訂,就因為遭到英國制造商公會的反對而被拋棄。[2]由此可見,連當時形成“閉關”或“開放”話語標準的英國也沒有絕對的開放。若用它作為標準來評判清朝前期的海外貿易政策,就極失公允了。
其次,“閉關”和“開放”的研究取向,也難以處理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演變的復雜進程。從1644年到1840年,清朝前期幾乎占有整整二百年的時間。在這期間,清朝統治者鑒于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對海外貿易政策也先后多次予以調整。而簡單的以“閉關”或“開放”來判定清朝前期海外貿易政策的性質,都是將它視為一成不變的行為,因而無法揭示清朝前期海外貿易政策的演進的復雜軌跡。張彬村在考察明清兩代海外貿易政策時就已注意到,明清兩朝關于官方海外貿易的政策,無論是中國官方的出海活動還是外國官方的來華朝貢貿易,都是在走向消極退化的方向;而就民間貿易政策而言,則表現出積極進步的趨勢。因此,單用“閉關自守”來形容明清兩朝的海外貿易政策,即使適用于官方貿易,也決不適用于民間貿易。[3]
再次,“閉關”論也無法從海外貿易層面揭示出清代中國何以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在閉關論的學者看來,清朝采取閉關政策,阻礙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特別妨礙了中國人民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和技術,從而使中國在科學技術、生產等方面完全落后于西方,由此造成了近代中國的挨打局面。我們認為,上述觀點將中國落后挨打的原因過于簡單化。關于這一失誤,高翔在前引著作中已指出,中國落后于西方是長期演變的結果,它有著廣泛的歷史原因,而把落后完全歸罪于清朝所推行的閉關政策是不公正的。同時,上述觀點只是結論,而缺乏具體的事實論證。閉關論者所確認的“閉關”,多是指清朝對外商來華貿易所采取的嚴密防范和嚴格限制的措施。既然外商在清朝普遍受到這種防范和限制,為何清朝海外貿易發展的最后結果卻是:被動貿易(指外商的來華貿易,尤其是西方商人的來華貿易)的日益發展和主動貿易(指中國商人的出海貿易)的不斷萎縮呢?[4]顯然,用這種“閉關”政策無法解釋本國商人海外貿易不斷萎縮和外商來華貿易日益發展的原因。因此,“閉關”論也就不能從海外貿易層面揭示出清代中國何以落后挨打的原因。
從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看,也不乏閉關鎖國并未導致落后挨打而對外開放卻尚未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的實例。例如,與清朝處于同一時段的日本江戶幕府(1603—1867),在1639至1854年間就采取了比清朝更為限制的海外貿易政策,它僅僅允許中國、荷蘭、朝鮮和琉球四國商船前往日本貿易,而禁止日本商人的出海貿易。日本江戶幕府的上述政策,已被學術界認定為“鎖國”政策。但一些學者卻認為,鎖國政策是推動明治朝(1868—1911)日本近代經濟發展的一個正面因素。[5]而依附論學者也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國家雖然采取了對外開放的政策,但其經濟卻一直處于不發達甚至落后的局面。[6]由此可見,簡單地使用“閉關”或者“開放”的研究取向來研究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政策,已難以說明上述國家化的不同結果。
--------------------------------------------------------------------------------
[1] 參見高橋磌一:《高橋磌一著作集》第2卷,日本あゆみ書房1984年版;加藤榮一:《幕藩國家的形成與對外貿易》,日本校倉書房1993年9月版。
[2] (法)保爾·芒圖著、楊人楩等譯:《十八世紀產業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319頁。
[3] 張彬村:《明清兩朝的海外貿易政策:閉關自守?》,載于吳劍雄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四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1年版,第45至59頁。
[4] 陳尚勝:前揭文。
[5] (日)北島正元:《江戶》,東京,波巖書店,1971年版,第34頁;信夫清三郎:《江戶時代·鎖國の構造》,東京,新地書房,1987年版,第171至207頁;Marius B. Jansen, “Tokugawa and Modern Japan”, 載入John W. Hall and Marius B. Jansen, des., Studies in the Intitution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0, pp. 317-330。
[6] (英)安德魯·韋伯斯特著、陳一筠譯:《發展社會學》,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5至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