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qū)域政府合作:區(qū)域經(jīng)濟(jì)一體化的路徑選擇
佚名
五、結(jié)語(yǔ) 綜上所述,區(qū)域政府合作機(jī)制,就是在中央政府良好的政策引導(dǎo)下,依靠區(qū)域內(nèi)地方政府間對(duì)區(qū)域整體利益所達(dá)成的共識(shí),運(yùn)用組織和制度資源去推動(dòng)區(qū)域一體化,從而塑造區(qū)域整體優(yōu)勢(shì)。作為實(shí)現(xiàn)我國(guó)區(qū)域經(jīng)濟(jì)一體化的現(xiàn)實(shí)選擇,這是由我國(guó)改革的初始條件決定的。我國(guó)是一個(gè)政府主導(dǎo)型的、化的后發(fā)型國(guó)家,一方面,計(jì)劃體制下政府對(duì)經(jīng)濟(jì)的深度干預(yù),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的管理和直接運(yùn)行經(jīng)濟(jì)的權(quán)力和能力。另一方面,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發(fā)育還極不成熟、公民的力量也還有待于和壯大,所以,除非政府之間達(dá)成共識(shí),通過(guò)政府間合作,依靠一致性的行政力量、中央政府的政策資源和制度去實(shí)現(xiàn)一體化,否則在政府之外幾乎沒(méi)有足夠的力量和制度渠道來(lái)實(shí)現(xiàn)這一制度變遷。當(dāng)然,以政府合作來(lái)推動(dòng)區(qū)域經(jīng)濟(jì)一體化,并不是強(qiáng)調(diào)政府的力量去替代市場(chǎng),而是試圖通過(guò)區(qū)域內(nèi)地方政府的共同行動(dòng),一起嘗試并進(jìn)行以市場(chǎng)化為導(dǎo)向的制度創(chuàng)新,為區(qū)域內(nèi)社會(huì)經(jīng)濟(jì)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提供一個(gè)一體化的制度平臺(tái)。 同時(shí),我們也必須意識(shí)到,在一個(gè)缺乏普遍的法治規(guī)則、統(tǒng)一的市場(chǎng)秩序和完善的區(qū)域政策的國(guó)度里,要真正建構(gòu)起一個(gè)行之有效的區(qū)域政府合作機(jī)制,實(shí)現(xiàn)區(qū)域經(jīng)濟(jì)一體化,絕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從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經(jīng)驗(yàn)看,甚至連歐洲的一體化也走過(guò)了半個(gè)世紀(jì)的艱難歷程。但區(qū)域經(jīng)濟(jì)一體化的前景是誘人的。而且近年來(lái),以長(zhǎng)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為代表的經(jīng)濟(jì)區(qū)域內(nèi)各級(jí)政府通過(guò)實(shí)質(zhì)性的合作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區(qū)域經(jīng)濟(jì)一體化的績(jī)效,也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建構(gòu)一個(gè)行之有效的區(qū)域政府合作機(jī)制,推動(dòng)和實(shí)現(xiàn)區(qū)域經(jīng)濟(jì)一體化,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全國(guó)統(tǒng)一市場(chǎng)的形成,也決非是一個(gè)遙不可及的烏托邦。
注釋: [①]轉(zhuǎn)引自Bruce Gilley,Provincial Disintegration:Reaching your marker ismore than just a matter of distance ,22/11,2001.載于《遠(yuǎn)東經(jīng)濟(jì)評(píng)論》。 [②]代表性成果有:上海證大研究所主編的《長(zhǎng)江邊的:大上海國(guó)際都市圈建設(shè)與國(guó)家發(fā)展戰(zhàn)略》,學(xué)林出版社2003年3月;洪銀興、劉志彪等著:《長(zhǎng)江三角洲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模式和機(jī)制》,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4月版以及發(fā)表在2003年《浙江社會(huì)》、《浙江經(jīng)濟(jì)》的數(shù)篇文章。 [③]其中以張?jiān)瓶傻摹秴^(qū)域大戰(zhàn)與區(qū)域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民主與建設(shè)出版社2001年5月,最為典型。 [④]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張文范主編的《中國(guó)行政區(qū)劃研究》(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1年)、浦善新等主編的《中國(guó)行政區(qū)域概論》(知識(shí)出版社1995年)、劉德君的《中國(guó)行政區(qū)劃的與實(shí)踐》(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以及近幾年發(fā)表在《中國(guó)行政管理》上的數(shù)篇論文。 [⑤]盧現(xiàn)祥:《西方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中國(guó)發(fā)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頁(yè)。 [⑥]銀溫泉、才婉如:《我國(guó)地方市場(chǎng)分割的成因和治理》,載于《經(jīng)濟(jì)研究》2001年第6期。 [⑦]周黎安于2002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學(xué)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研究中心作的題為“晉升和財(cái)政刺激:中國(guó)地方官員的激勵(lì)研究”的學(xué)術(shù)報(bào)告。 [⑧]數(shù)據(jù)來(lái)源:《中國(guó)統(tǒng)計(jì)年鑒》1993~1997年歷年的相關(guān)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 [⑨]參見[澳]奧德麗·唐尼索恩《中國(guó)的蜂窩狀經(jīng)濟(jì):文化革命以來(lái)的某些經(jīng)濟(jì)趨勢(shì)》,載《走向21世紀(jì):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的現(xiàn)狀、和前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⑩]盛世豪:《長(zhǎng)三角一體化中的政府與定位》,載《浙江經(jīng)濟(jì)》2003年第6期。 [11]盛世豪:《長(zhǎng)三角一體化中的政府與企業(yè)定位》,載《浙江經(jīng)濟(jì)》2003年第6期。 [12]L.E.戴維斯與D.C.諾斯:“制度變遷的理論:概念與原因”,載《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與制度變遷——產(chǎn)權(quán)學(xué)派與新制度學(xué)派譯文集》,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0頁(yè)。 [13]美國(guó)1887年通過(guò)的《洲際商業(yè)法》、1890年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以及后來(lái)的《克賴頓法》都對(duì)美國(guó)統(tǒng)一自由市場(chǎng)的形成起到了極為關(guān)鍵的作用。參閱希爾曼斯:《美國(guó)是如何治理的》,商務(wù)印書館1988年,第499~504頁(yè)。 [14]參閱銀溫泉、才婉如:《我國(guó)地方市場(chǎng)分割的成因和治理》,載于《經(jīng)濟(jì)研究》2001年第6期。 [15]W.W.拉坦:“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載《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與制度變遷——產(chǎn)權(quán)學(xué)派與新制度學(xué)派譯文集》,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9頁(yè)。 [16]Michael Talyor ,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 ,New York:CambridgeU.P.1987.PL. [17]張可云:《區(qū)域大戰(zhàn)與區(qū)域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民主與建設(shè)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506頁(yè)。 [18]V·奧斯特羅姆等:《制度與發(fā)展的反思——問(wèn)題與抉擇》,商務(wù)印書館1996年,第89、98~99頁(yè)。 [19]曼庫(kù)爾·奧爾森:《集體行動(dòng)的邏輯》,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第71頁(yè)。
劃與市場(chǎng).jpg)
院學(xué)報(bào).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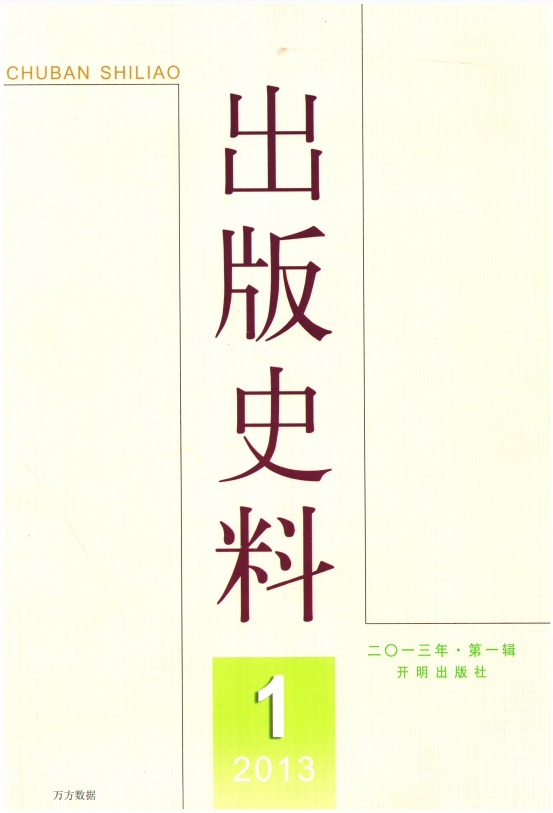
外醫(yī)學(xué)情報(bào).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