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述清代閩人入川與川閩經(jīng)濟文化交流
佚名
福建人口的遷移和流動,在不同的時期具有不同的特點。清初福建人民不畏蜀道之難,扶老攜幼,輾轉(zhuǎn)于溝壑之中,綿延數(shù)千里由閩入川。在這超人的開拓膽識與吃苦耐勞精神的后面,蘊藏有特殊的歷史原因和背景。他們的遷徙動機與目的亦各不相同。嘉道之后直至民初,通過數(shù)代乃至十幾代入川閩人的努力,對推動閩川兩省的文化,均作出突出的貢獻。本文擬就明末清初至道光之前,閩人入川的原因與背景、動機與目的,以及對兩省經(jīng)濟文化的互動效應(yīng)作一初步的探討,希望能對福建與四川人口的有所裨益。
一、福建人民遷徙入川的原因與歷史背景
1.長期戰(zhàn)亂造成川中人口劇減
明朝之前閩人入川可能是零星的,因而未見史書記載。明末,福建遭受嚴重的戰(zhàn)爭禍害,鄭成功抗清斗爭在閩南進行得十分激烈,順治九年(1652年)漳州城被圍五個多月“餓死男女?dāng)?shù)余萬人”,但到順治十八年(1660年)統(tǒng)計福建仍有丁145萬,口469萬;可見總的人口損失不是太大[1]。而四川的情況則大不相同。明末清初張獻忠起義軍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權(quán),起義失敗后,南明政權(quán)與起義軍余部聯(lián)合抗清;之后平西王吳三桂又聯(lián)絡(luò)駐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以四川為前線與清朝分廷抗禮,川中遂成兵家必爭之地。為此清軍曾六進成都。飽受長達37年的兵燹戰(zhàn)亂,川中地區(qū)人口傷亡迨盡;血腥的屠戮之后又是瘟疫流行,號稱數(shù)百萬人口的“天府之國”只剩下區(qū)區(qū)五萬丁稅之口,總計不過三、五十萬人,不抵明中葉興盛時人口之10%。以致許多地方官員均無民可治,賦稅大省也無產(chǎn)可收。順治年間四川巡撫張德地到成都走馬上任時“行數(shù)十里絕無人煙”,只好退駐保寧(今川北閬中縣),直至康熙四年(1665年)將衙署搬入成都,康熙五十七年(1778年)才重修毀于戰(zhàn)火的成都城。
為解決昔日米糧之倉的川中人煙稀少問題,清初順治朝下令“湖廣(今湖南、湖北)填四川”,一些湖廣地方人士“奉旨”入川,實際上這是帶有強制性質(zhì)的性移民。隨之康、雍、乾三朝均以比較優(yōu)惠的移民政策鼓勵各省民眾遷徙入川,如康熙十年(1671年)下詔“定各省貧民攜帶妻、子入蜀并開墾者,準其入籍……應(yīng)準其子弟一體”,康熙五十一年(1772年)“往四川墾地至滿五年起征”,每丁給農(nóng)田30畝或旱田50畝,五年內(nèi)免征稅糧。雍正年間下詔“凡流寓情愿墾荒居住者,將地畝永給為業(yè)”。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戶部批準入川墾戶“每戶給銀十二兩”用作安家費。[2]這樣從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川中統(tǒng)一開始,一直到嘉慶年間(1796—1820年)移民才停息,前后持續(xù)了一百多年,入川移民以湖廣人為主,贛、粵較多,福建較少。據(jù)統(tǒng)計福建入川民眾僅占移民總數(shù)的不及5%。我們從嘉慶年間的《四川通志》“戶口”統(tǒng)計,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至嘉慶元年(1796年)四川人口凈增2516491人,其中約80%是外省移民,即74年中移民總數(shù)為201.3萬,每年以2.7萬人速度移民。加上康熙六年奉詔入川屯墾的12萬福建投誠官兵及其家屬(后詳),福建入川移民總數(shù)約在30萬人左右。但是,不足移民總數(shù)15%的福建入川移民對川閩文化交流卻帶來了相當(dāng)深遠的。
2.地狹人稠與連年災(zāi)荒迫使閩人遠徙入川
明清之際我國開始進入第四個災(zāi)害宇宙期。[3]隨著人口的大幅度增加,災(zāi)害的頻繁發(fā)生,人口流動的規(guī)模也不斷增大。福建自宋元以來人均耕地即十分有限,入明之后更是大幅減少。謝肇浙《五雜俎》就描述了福建人迫于耕地日減而外出謀生,在廣東、廣西一帶的遷移和開發(fā)。他說:閩人“地狹則無田以自食,而人口則射利之途愈廣;什五游食在外”。萬歷年間“江、浙、閩三處,人稠地狹,總之不足以當(dāng)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則口不糊,足不出外則技不售”;在廣東廉州還有被俗稱為“東人”的,“雜處鄉(xiāng)村,解閩語,業(yè)耕種”[4]。這些操閩語、有技術(shù)而雜處之人,就是流寓粵東的閩人后裔。贛南瑞金一帶,明中后期“閩廣及各府之人視為樂土,繩繩相引,僑居此地。土著之人,為士為民;而農(nóng)者、商者、市儈者、衙胥者,皆客籍也”。[5]在江西寧都的6個鄉(xiāng)中,“上三鄉(xiāng)即土著,下三鄉(xiāng)佃耕者悉屬閩人”[6]。即使是在清政府嚴密控制之下的滿洲腹地,也有數(shù)萬福建人在當(dāng)?shù)亟?jīng)營實業(yè),甚至定居。乾隆皇帝聞報后大為驚訝卻也十分無奈,他說:“朕聞奉天一帶沿海地方,竟有閩人在彼搭寮居住,漸成村落,多至萬余房”;“此皆系地方官以閩人在彼貿(mào)易營生,藉此多征商稅,遂爾任其居住,若不亟行查禁,則呼朋引類,日聚日多”;“但閩人在彼居住,已非一日,且戶口較多,亦未便概行驅(qū)逐”;且“錦州、蓋州、牛莊等處,每年俱有福建商船到彼貿(mào)易。即有無業(yè)閩人,在該處居住”。[7]這種頗具規(guī)模的人口流動,體現(xiàn)了明末清初福建人民向外省遷徙的明顯趨勢。甚至早至明朝初年即有閩人不畏蜀道的艱險而進入四川謀生,主要集中在資中、新繁、健為等條件較好的地區(qū):“資(中)無六百年以上土著,明洪武時由楚來居者十之六七,閩、贛、粵籍大都清代遷來。明初來者今謂川省人,余則各以其籍相稱”。[8]川中新繁縣人口主要由湖北、江蘇、福建、廣東和陜西移民所組成。[9]岷江之濱的《健為縣志》專門列出所有由移民按地域建立的會館。湖廣、寶慶、長沙、江西、福建等會館人數(shù)最多。由于移民數(shù)量大大超過本籍人,因而在太平天國時期各籍移民自選人員負責(zé)為官府征派特捐、收集捐款。[10]
福建地處熱帶、亞熱帶地區(qū),氣候炎熱,時常爆發(fā)大規(guī)模的流行性疾病甚至傳染病,亦是瘟疫常發(fā)之地。順治九年(1652年)正月,由于漳州潮水突漲5尺,鄭成功軍隊得入海澄。同年漳州城被鄭軍團團包圍,糧盡彈絕,以致“人相食,斗米值五兩”。至清軍解圍之時,在城內(nèi)收得顱骨73萬;于是“疫大作,死者無數(shù)”。[11]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月汀州永定水災(zāi),漂圯民房無數(shù),沖垮城內(nèi)臥龍橋;秋季永定“大疫,死者千余人”。[12]乾隆十八年(1753)海澄爆發(fā)大規(guī)模瘟疫,“死者無算”。同年泉州府也有瘟疫流行,“至明年秋乃止”。[13]道光元年(1821)七月間福建全省瘟疫流行,患者均因吐瀉暴卒,“朝人夕鬼”,不可勝數(shù)。[14]其實,早在明萬歷時謝肇浙著《五雜俎》就對福建瘟疫心有余悸:“閩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請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禮許賽不已。一切醫(yī)藥付之罔聞。不知此病郁熱所致,投以通圣散開辟門戶,使陽氣發(fā)泄,自不傳染。而謹閉中門,香煙燈燭,煮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即幸而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紙糊船,送之水際。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閉戶避之。余在鄉(xiāng)間夜行,遇之輒徑行不顧。友人醉者至,隨而歌舞之,然亦卒無恙也”[15]。在當(dāng)時條件下,對瘟疫幾乎是束手無策,只好求助于裝神弄鬼。為躲避瘟疫等重大傳染性疾病,閩人只得遠走高飛,包括遙遠的四川等地也成為遷徙的目的地。
二、清代福建移民入川的動機與移民的類型
1.為求生存而移民入川
福建移民就其入川動機論之,多屬生存型的,即由于福建人多地少,一些少地或無地佃戶,兄弟子女多,遇上水旱歉收,生活無著;為求生存而不畏蜀道之難,輾轉(zhuǎn)徒步數(shù)月,歷經(jīng)艱辛而入川的閩人家族,在家譜中留下詳實的記載。如龍巖萬安鄉(xiāng)溪口村徐姓《族譜》記載:“啟祖原系福建省漳州府龍巖州溪口縣萬安里,地名庵子腳下老屋基居住,耕種祖父遺留之業(yè)。不意年寒欠豐,男繁女眾業(yè)乏之苦。常言四川耕種貿(mào)易之隆,是日弟兄同堂議妥:長么兩房仍就福建受業(yè)耕春;二房徐美周(入川啟祖,號永旭,時年40歲)同緣韓氏(28歲)二人,隨帶長子良彪,用籮兜挑著次子良鳳(6歲),女兒(半歲),與三房美昌(號永鎰),于乾隆十七年壬申歲(1752年)九月初四日擇取吉良黃道,起身移居四川。長么兩房二人送至三十里,弟兄分別淚如雨點,大哭而回。永旭、永鎰六人于乾隆十八年癸酉歲三月初二日來川,在大足城西門住座貿(mào)為業(yè)一載五月。因干旱,貿(mào)易不順,弟兄各尋各居。以至八月內(nèi),搬移中敖三板橋,地名劉家溝,佃田耕種三十余年。……嘉慶六年(1801年)男女五人遷移大足茅居子(山鄉(xiāng))屋座幾載。承天地之德,至嘉慶十三年(1808年)落業(yè)成糧(立為糧戶),螽斯千古,永振家邦”[16]。從徐氏家譜中我們發(fā)現(xiàn)二個兄弟從龍巖來到川中大足并以此為中心的遷徙軌跡和發(fā)展經(jīng)歷。
2.閩人為尋求新的商機入川發(fā)展
福建入川民眾中也有些原本生活就較為富裕者,其移民性質(zhì)是屬于發(fā)展型的。他們隨著移民大潮,入川尋求新的商機,發(fā)展事業(yè)。如“康熙十年(1671年)福建汀州商人曾達一來到四川內(nèi)江,見三月菜花開放,內(nèi)江之氣候與福建相近,可種甘蔗,遂藉返鄉(xiāng)迎親之際,帶來蔗種和制糖工具,延聘了制糖食品的工人,在內(nèi)江龍門鎮(zhèn)梁家壩開設(shè)了糖坊。由于種植甘蔗獲利高于種糧食,甘蔗種植由內(nèi)江拓展到資中、資陽和隆昌等地,興起了種蔗熱”[17]。這類發(fā)展型的移民大多農(nóng)商工并舉,對清中葉四川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有相當(dāng)大的促進作用。
3.先求生存而后圖發(fā)展類型
另外一種是始求生存而后圖謀發(fā)展類型,此類典型代表即如郭沫若的先祖,原籍是福建寧化。郭老在1939年寫的《德音錄·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說:“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前(1781年,即乾隆四十六年)由閩遷蜀,世居樂山縣銅河沙灣鎮(zhèn),銅河者大渡河之俗名,古又稱沫水。……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郭沫若祖父),族已昌大”。據(jù)郭沫若族弟郭開宇回憶:“我的曾祖父郭賢惠講,先輩由福建來四川,開始是做苧麻生意。從福建寧化采集野生苧麻,跟著入川的馬幫,到了現(xiàn)在的牛華鎮(zhèn),牛華是鹽井林立,盛產(chǎn)食鹽的地方。苧麻用于鹽業(yè)生產(chǎn)中纏扎鹵水筒。后來也運麻布來賣。賺了錢,自己也辦起了馬幫,沿途開設(shè)了13個驛站”[18]。入川的郭氏家族正是仰賴如此殷實的家業(yè),至其父郭朝沛時才有經(jīng)濟實力在家里辦起了家塾專館—一綏山館,而后又藉此送郭沫若與其長兄郭開源留學(xué)日本成才。
4.入川為宦與軍屯入川類型之閩籍移民
此外,還有些福建籍的官員與軍人以游宦和軍屯的身份入川的,如康熙《四川總志》卷10《貢賦》記述,早在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親政當(dāng)年就招福建鄭成功軍事集團的投誠官兵及其家口入川,當(dāng)時四川巡撫張德地曾奏請朝廷:“福建一省投誠一項,除家口外,尚有二萬三千八百余名之眾,歲支銀米除移駐外,尚有三十六萬余兩、八萬余石之多,入伍者驟難補完,墾田則無地可屯。自宜以福建投誠最多之人而墾西川荒蕪之地,兩利各便,無逾此者……。抵蜀安插之后,一年分田墾地,二年習(xí)成土者,三年起科”[19]。這個條件比其他地方招撫投誠官兵更為優(yōu)惠。如《清實錄》載康熙皇帝于六年八月初七日下詔“令河南、山東、山西、江南、浙江見駐投誠官兵開墾荒地,自康熙七年始,每名給五十畝,預(yù)支本年俸餉以為牛種,次年停給;三年后照例起科。”安撫在川西屯墾的福建籍官兵,如以每戶5口計,則當(dāng)年入川閩人至少有12萬之眾。僅此一項即相當(dāng)可觀。再從今天成都等地的“大福建營巷”、“小福建營巷”等地名看,數(shù)年中入川屯墾的福建官兵加上眷屬的數(shù)目相當(dāng)可觀。移屯入川安家立業(yè),雖帶有一定的強制性質(zhì),但其目的主要是為安置屯戌軍人與開發(fā)川西經(jīng)濟,仍屬經(jīng)濟性移民。
三、清初、中葉福建人民由閩遷徙入川的歷史意義與影響
通過清初的移民入川,在較短時間內(nèi)恢復(fù)了天府之國的元氣,直至嘉慶朝閩人入川仍絡(luò)繹于途,因而也促進了川閩兩地的經(jīng)濟、文化的交流與發(fā)展。其影響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四川省由于人口迅速增加,勞動力資源漸為充裕,經(jīng)濟得以恢復(fù),并且迅速發(fā)展。康熙五十年(1711年)巡撫年羹堯上奏稱:“連年大有,運販米谷出川者不在少數(shù)計,是吳楚歉收資食川米。”雍正初年就有“江浙糧食歷來仰給于湖廣,湖廣又仰給于四川”之說,四川又恢復(fù)了賦貢大省的地位[20]。清代初期,就當(dāng)時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與人口增長情況來看,福建的人口密度已趨飽和狀態(tài),可供開發(fā)利用的自然資源包括可墾荒地已臻枯竭。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省有耕地1362萬畝,到光緒十三年(1887年)減少至1345萬畝,而人口密度卻從乾隆十八年的每平方公里40.38人,增加到咸豐元年(1851年)172.31人[21]。據(jù)葛劍雄主編《移民史》統(tǒng)計,四川在清初移民大潮中共接納移入623萬人,其中福建20萬人(包括這一百多年中入川定居閩人后裔,筆者以為該數(shù)目偏少,如前所述當(dāng)為30萬人),所以清初移民入川從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福建本地的人口壓力。
第二,兩地農(nóng)業(yè)耕作與經(jīng)濟作物栽培、加工技術(shù)的交流,促使兩省經(jīng)濟的共同發(fā)展。早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四川巡撫在奏折中就提倡“須廣招在川之閩、粵農(nóng)民,鑿引泉源,或設(shè)堰分流,庶灌溉有資,旱澇而無患矣”[22]。說明閩、粵兩省農(nóng)民積累了豐富的引渠灌溉、抗旱保苗的生產(chǎn)經(jīng)驗,四川官員十分注意發(fā)揮這些閩粵籍移民的長處。此外,福建移民還引進可收雙季的水稻良種及紅薯、玉米、煙、甘蔗、木棉等多種經(jīng)濟作物。紅薯是在萬歷年間從呂宋傳入福建,藉以抗御災(zāi)荒的;經(jīng)閩粵移民帶入四川后,由于紅薯十分適宜于川中丘陵和山區(qū)種植,又是一種高產(chǎn)耐旱作物,使得四川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面貌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dāng)?shù)厍鹆晟絽^(qū)得到開發(fā)利用,移民也可以在那里蕃衍生息。再比如煙草和甘蔗的種植,民國重修《傅氏宗譜》記述入蜀始祖、福建龍巖銅缽人傅榮沐“由瑞金遷居金堂趙家渡。初猶食力于人,繼乃自為貿(mào)易并佃田,使諸子力農(nóng),及遷易家壩,廣種煙草。時蜀中未諳種煙法,而滿、蒙八旗弁兵尤所必需,故一時傅姓煙重于錦城(成都),其價過倍他種。又熬蔗糖于趙家渡,發(fā)販四方,獲資益厚”[23]。在閩籍移民的影響下,當(dāng)時沱江、涪江沿岸移民大縣遍種煙草、甘蔗。總之,花生、甘蔗、煙草、水稻、柑桔等經(jīng)濟作物的栽培都與當(dāng)時各地入川移民有關(guān),這在地方志書和族譜中多有記載。從而使四川物產(chǎn)大為豐富,迅速成為糧食輸出的省份。明清時期福建長期缺糧,這種糧食與經(jīng)濟作物栽培的交流,可以使兩省共同受益。而四川茶葉種植和加工的歷史相當(dāng)悠久,茶文化比較發(fā)達,釀酒經(jīng)驗豐富,還有極為豐富的水力資源和資源,閩籍移民作為多元文化交流的橋梁作用應(yīng)當(dāng)重新評估。
第三,促進閩川兩省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福建移民把自己的風(fēng)俗、習(xí)慣、方言和民間信仰帶進了四川,促進四川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多元一體文化。比如閩人的二次葬俗,敬祖重教的傳統(tǒng)在四川得到川人的認同和發(fā)揚。在俗神信仰中,福建沿海人民尤重于興建天后宮(天上宮),廣泛信仰媽祖(天后圣母)。遍布四川各地的天后宮一般是由福建籍商人捐建或同鄉(xiāng)集資所建,而富順縣城天后宮則是乾隆二十五年(1751年)由該縣知縣主持修建。這一方面說明官方對福建人的重視,著意團結(jié)福建人;另一方面也說明福建商人的數(shù)量已十分可觀,在當(dāng)?shù)卦斐闪艘欢ǖ挠绊憽?jù)四川各縣志及有關(guān)材料統(tǒng)計,全川建有天后宮約220座[24]。天后宮主要是入川福建人士聚會議事祭祀酬神之地,并兼有交流工商、農(nóng)、學(xué)各界事務(wù),聯(lián)絡(luò)感情,商議互濟互助的諸多功能,也祈禱天后媽祖關(guān)懷和保佑在川閩人子孫繁衍昌盛。
綜上所述,由于閩籍移民入川而建立起閩川兩省特有的密切關(guān)系。清初福建移民由于本地兵燹災(zāi)荒而由閩輾轉(zhuǎn)入川,可分為生存型、發(fā)展型、先求生存而后發(fā)展型及入川為宦與軍屯型等4類。他們均為四川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文化繁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促進了兩省人民之間文化的交流和溝通。典型者如福建的媽祖天后信仰遍及四川大地,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
自20世紀80年代始,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強勁東風(fēng),廣東、福建等沿海省份率領(lǐng)開始經(jīng)濟騰飛。四川、湖北、江西等大量民工開始輸入閩、廣等地。截至2002年底的統(tǒng)計,在閩務(wù)工的內(nèi)地各省民工有220萬人,其中四川籍(含重慶市地區(qū))民工至少有100萬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次西南內(nèi)地人口向東南沿海地區(qū)的大遷徙。龐大的民工隊伍成為福建經(jīng)濟建設(shè)的生力軍,并作出了驕人的業(yè)績。四川民工入閩的同時,也帶來了濃郁的巴蜀文化,“四川麻辣燙”、“水煮活魚”、“重慶火鍋”等川中飲食文化在福、廈、漳、泉等地舉目可見。今天,福建人民也應(yīng)當(dāng)發(fā)揚當(dāng)年先輩的奮發(fā)開拓精神,積極入川,把人才、資金、技術(shù)等帶進中國的西南腹地,為我國西部大開發(fā)作出應(yīng)有的貢獻,讓兩地文化交流再創(chuàng)輝煌。:
[1]詳見陳壽祺《重纂福建通志》卷五“人口”。正誼書院同治二年刻本。
[2]《清圣祖實錄》康熙十年、五十一年;《清仁宗實錄》雍正六年。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
[3]這個時期是我國工作者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的三個重大災(zāi)害群發(fā)期之一。即夏禹宇宙期(約4000年前)、兩漢宇宙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20年)、明清宇宙期(公元1500年至1700年)和兩個較小的災(zāi)害群發(fā)期,即清末宇宙期和20世紀60年代末迄今正在進行中的災(zāi)害相對頻繁期。參見高建國:《災(zāi)害學(xué)概論》,《農(nóng)業(yè)考古》1986年第2期;徐道一:《嚴重自然災(zāi)害群發(fā)期與》,載馬宗晉等編:《災(zāi)害與社會》,地震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297頁;任振球著:《全球變化---地球四大圈異常變化及其天文成因》,科學(xué)出版社1990年版。
[4]王士性:《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80頁、103頁。
[5]同治《瑞金縣志》卷十六“兵寇”,引楊兆年“上督府四賦始末”。
[6]魏禮:《魏季子文集》卷八,“與李邑侯書”。
[7]《清高宗實錄》卷一三七六,乾隆五十六年四月庚戌,第26冊,第549頁。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
[8]民國《續(xù)修資中志》卷八“方言”。第68頁。
[9]光緒《新繁縣志》卷五“戶口”。第2頁下。
[10]民國《健為縣志》“種族表”,第6頁,第51頁。
[11][12][13][14]道光《福建通志》卷二七一、二七二“祥異”,同治二年正誼書院刻本。
[15]謝肇浙《五雜俎》卷五“人部”二。第259頁。國學(xué)珍本文庫第一集第三十種,中央書店1935年印本。
[16][23]崔榮昌:《四川方言與巴蜀文化》,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頁
[17][24]孫曉芬:《四川的客家人與客家文化》,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頁
[18]詳見四川大學(xué)《郭沫若集刊》,四川大學(xué)學(xué)報編輯部編輯出版,1983年。
[19][20]正剛:《清前期閩粵移民四川數(shù)量之我見》,《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1]梁方仲:《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tǒng)計》有關(guān)統(tǒng)計表格,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2]轉(zhuǎn)引自陳世松:《中國西部大開發(fā)與客家文化》

文獻.jpg)
報.jpg)
絡(luò)安全技術(shù)與應(yīng)用.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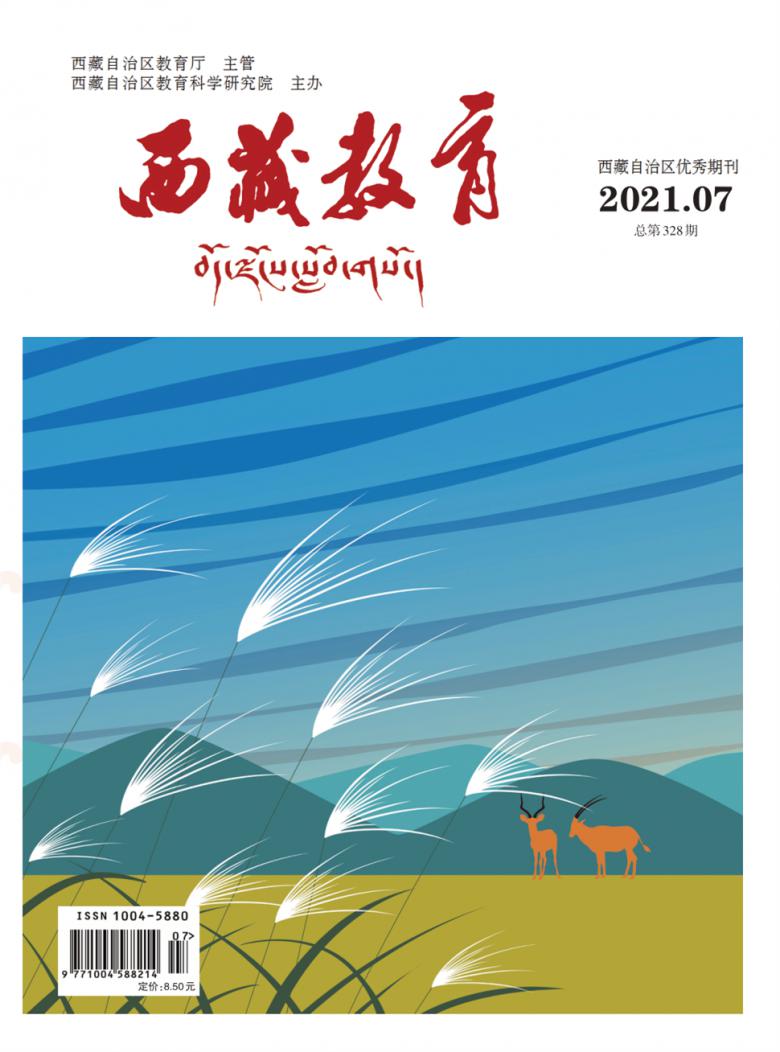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