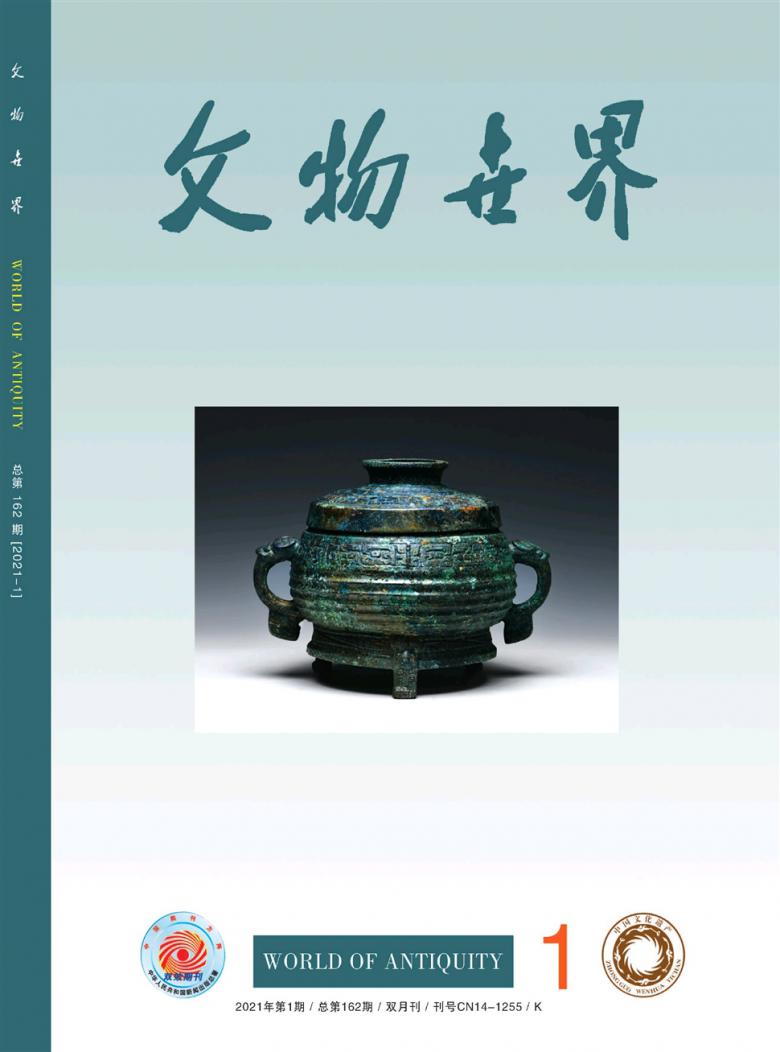亞洲的終結,還是亞洲的挑戰?——東亞文化與經濟現代化相關性理
佚名
東亞經濟增長是如世界銀行所說的“奇跡”,還是如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 R. Krugman)所說的“虛幻”?東亞現代化模式是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的“正在走向終結”,還是如小R.霍夫亨茲和K.E.柯德爾(Roy Hofheinz , Jr. and Kent E Calder)所說的“正在挑戰西方”?東亞文化與現代化模式是相關聯,如金耀基認為的“沒有沒有傳統的現代化”,甚至如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言“是關鍵變量”,還是如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新古典綜合派)認為的“現代化模式與文化無關”?帶著這些極其富有挑戰性的問題,考察東亞文化與經濟現代化相關性理論就十分有必要了。 一、東亞文化與經濟現代化相關性的現有理論述評 研究東亞經濟現代化的西方學者對于東亞文化與經濟現代化的相關性大體持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東亞經濟的發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場化的結果,東亞經濟發展沒有模式價值,只有政策價值,即沒有現代化的多種模式和多元現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家認為只有經濟增長模式的不同),現代化是單線發展的。基于工業主義的邏輯,所有走上工業化之路的社會,無論起點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現政治、經濟、文化全套性的越來越相似。從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到塔爾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爾根?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學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現代化與現代性具有政治、經濟、文化的一整套關聯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現代化和現代性實質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價值,要想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必須也只有“華山一條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經典現代化理論或現代化理論的“去文化論”就持這種觀點,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會變遷理論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現代化的“匯流論”(theory of convergence)是為代表。發展理論中的經典發展學派,如增長和發展經濟學派,解釋東亞經濟發展的經濟學派,如新古典學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學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綜合派和親市場學派(如世界銀行關于東亞奇跡的發展報告),東亞整體增長機制論(如雁形模式論或產業周期理論,噴泉模式論或多發經濟增長源理論,齒輪模式論或經濟整體咬合聯動理論,環形模式論或美國主導環太發展論,航母模式論或中國主導環太發展論等)等基本上持這種非文化因素的東亞經濟發展論。第一種觀點在西方學者中往往有一種這樣的學術系譜,在西方中心論的大系譜下,依次為亞洲千年停滯論(亞洲早熟論)——亞洲命定殖民地論——亞洲發展幻象論(亞洲崩潰論)——亞洲模式不存在或終結論——歷史終結論(全盤西方論)。這種學術系譜似乎有一種內在的關聯,承繼著東方學的傳統,對亞洲的發展不是積極地鼓勵和引導,而是有著某種幸災樂禍的陰暗心理,對自身則有一種說不出的優越感和命定感。這種系譜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極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價值和普世意義的經濟理論與經濟對策。 第二種觀點認為研究東亞經濟增長的動因除了對經濟自變量考察,也不應忽視對東亞地區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東亞經濟與東亞文化之間有一種明顯的互動關系。他們追問“為什么恰恰是東亞繼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驕人的成績”。東亞文化對東亞經濟發展有一種精神動力的巨大支持。東亞的社會、經濟、市場、制度、甚至政策,都彌漫和滲透著東亞文化的無孔不入的影響。尤其是作為東亞經濟或市場的行為體的東亞人,在市場的游戲規則和運行環境方面,主要體現為制度規范性和文化規范性兩方面,深刻地受到東亞地區文化因素的制約。作為傳統的文化已經成為東亞人民深層的精神構造(李澤厚認為儒學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深層精神構造),自發和無意地或有意而自覺地對經濟增長發揮直接或間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與經濟或市場的親和力是明顯不同的,任何經濟或市場都有其內在的人文氣象。發展倫理學之所以追問“什么是真正發展”,就緣于對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論并非文化決定論,也非因果鏈條的單因素論,他們并不否認經濟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認為也不應該否認經濟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與生產力密切相關的生產關系就與文化傳統有關聯,經濟學家的目光應該看得更遠。現代化理論中的修正學派或新現代化學派或現代化理論的“文化論”或現代性的多元論者,發展理論中的新發展理論(又稱真正發展理論或全面發展理論)學派,如發展哲學和發展倫理學派,經濟學中的制度學派、文化學派、歷史學派、倫理學派和心理學派等,經濟學中的重視非理性因素的學派,西方所謂的現代化的“懷疑論者”和“反現代化論者”,經濟哲學中的新發展哲學,歷史學中的現代化學派、社會學中新發展社會學派和未來學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這種觀點。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國社會學家Robert Bellah,《亞洲大趨勢》(1996)的作者、美國未來學家John Naisbitt,《日本資本主義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譽為“把日本經濟學提高到國際水平的最大貢獻者”、《透視日本》(1982/1999)一書的作者森島通夫,《新加坡的挑戰》(1989)和《現代精神和儒家傳統》(1996)的作者杜維明,提出亞洲資本主義理論的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教授John Gray,《亞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書的作者Jim Rohwer,《東亞之鋒》(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東亞發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繆爾?亨廷頓、艾森斯塔德、赫爾曼?卡恩、麥克法夸爾、克利福德?紀爾茲、哈羅德?卡恩、哥爾德夏米德、羅納德?多爾、拉爾夫?林頓、丹尼斯?古萊特、本迪克斯、麥克萊蘭、哈根、摩爾、英克爾斯、巴洛齊齊、金日坤等。第二種觀點在西方學者中也有一種學術系譜,即在西方危機論(虛構的亞洲中心論)的大系譜下,依次為黃禍論——亞洲崛起論——亞洲挑戰論——亞洲威脅論——西方危機論(西方衰弱論)。這種系譜緣于西方對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對自身衰弱的憂慮,對亞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學者居安思危的危機感的集中體現,當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層次上也回應和反映了亞洲的發展和實際,熱情地鼓勵和樂觀地前瞻了亞洲的未來發展,但對亞洲的高度恐懼心理溢于言表。“文明沖突論”也好,“歷史終結論”也好,最擔心的就是亞洲文明,尤其是東亞文明在經濟高速發展(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下的自我申張。“和平崛起”和“負責任的大國”戰略是中國政府對這種深刻憂慮的積極回應。 當代中國學者包括港臺學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體認和支持后一種觀點,這與我們身處東亞,對東亞文化有切身體會,以及我國政府倡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任務有關。中國學者如經濟學的厲以寧(《資本主義的起源》2003)、林毅夫(《經濟發展與中國文化》,見《戰略與管理》2003.1)、陳峰君(《當代亞太政治與經濟析論》1999和《東亞與印度——亞洲兩種現代化模式》2002)、張蘊嶺(《亞洲現代化透視》2000、《探求變化中的世界》2002)、陳巖(《東亞再崛起》1999)等,歷史學的羅榮渠(《現代化新論》1993和《現代化新論續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論》1988、《東亞:走向近代的精神歷程》1995、《新亞洲文明與現代化》2003)、章開沅(《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系試析》1988、《國情、民性與近代化——以日中文化問題為中心》1988)、、馮天瑜(《中華元典精神》1994)、孫福生(《20世紀東南亞國家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含義與影響》,見《北大亞太研究》1998.4)等,社會學的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1966和《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1985)、蕭新煌(《東亞的發展模式:經驗性的探討》1988)、陸曉光(《中國特殊論》,見《戰略與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認同文化因素對東亞經濟增長的貢獻。美國《知識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與經濟發展”專號,香港中文大學1985年編輯的《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論文匯編》,1989年臺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編的《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1994年在國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歷史系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持召開了“東亞現代化歷史經驗國際學術討論會”,會后由羅榮渠、董正華編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東亞現代化:新模式與新經驗》,以上學術文集或研討會專門就文化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