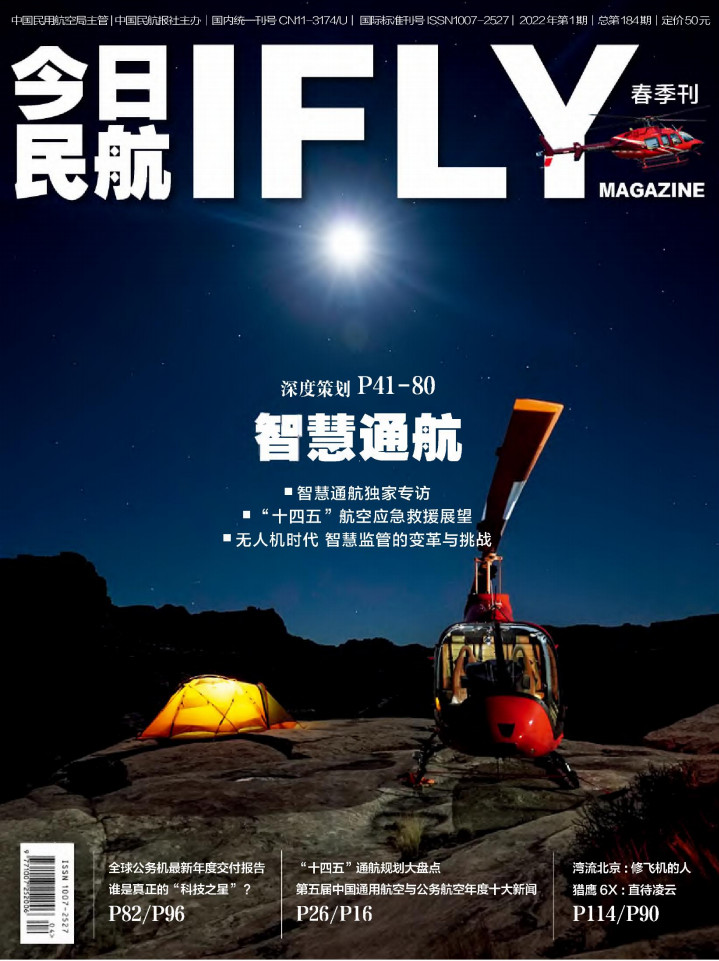中國女性文化:從傳統到現代化
林丹婭
摘要:中國女性新文化有著兩次重要的歷史性進程:一是她們在男性同盟者的幫助下,嘗試改變傳統文化中既定的女性角色身份與位置;二是她們嘗試更深入地認識并擺脫自我形成與自我生存過程中無所不在的男權狀態。后者使她們在目前陷進了一種類似孤軍奮戰的困境。
關鍵詞女性文化女性主義中國傳統
現代化一傳統文化中的中國女性中國女性文化伴隨著中國漫長的父權封建制社會形態與文化形態的形成,形成了一種可謂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內涵,在這個內涵中,“性別/位置/角色/屬性”是一串重要的文化識別符號。它們之間的關系密不可分,它們中間任何一個符號的出現,同時也意味著其余符號意義的同在。在實際運用上,它們成了可相互取代的指稱。假設一個人生下來就是個“女性”的,那么,她就被社會意識“意識”了自己這一生所處的“陰”的位置。而陰位,即“坤位”,早在中國上古時代的卜筑之書《易經》里,這種位置的屬性便已被規定好了:“坤,順也。”①順,即順從。之所以要“順從”,是因為這個位置的“卑”,陽為天處上而尊,陰為地處下而卑,“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②這是中國數千年以來至今仍盤踞在廣大國民意識深處之“男尊女卑”觀念的顯在。同時,她的角色分配業已注定:主內,做一個媳婦、妻子與母親。在這之前,她必須在娘家(女兒期)接受一整套的婦德教育,為著將來扮演好這些角色而精心準備。因此,在中國封建社會,做為女性,她們最高的人生價值、美德規范是做一個孝婦、賢妻與良母。她們會因之受到男權社會的極大稱頌,會被記載在男人專權的典籍中,盡管她們大多數仍舊無名,只以某氏、某妻或某女的模糊名目出現。如被記載在《明史》中韓太初妻劉氏的孝行:她以自己的血肉為藥引子,多次治好了婆婆的病,挽救了婆婆的生命,推延了婆婆的死亡。②這是一個媳婦用肉體最痛苦的“凌遲”之刑來完成的道義上最美滿的孝行,它表示了一個女人必須對其公婆履行的一系列孝順義務的限度,同時也表明一個女人修持圓滿婦德所必具有的血腥方式與實質。在有關清末慈禧太后專權過程的多種故事版本里,人們最津津樂道的是西太后慈禧雖因子母貴,但對懦弱的東太后慈安原還是有所忌憚的,因為傳聞慈安手中持有咸豐遺沼。于是慈禧效孝婦之行,則肉做藥引子,慈安因此對慈禧大為感動與放心,終于當面燒毀了咸豐帝暗遺的那條專轄慈穆保護正宮安全的密沼。④可見當時社會,人們對孝婦褒揚與崇尚的程度,慈禧利用了這一點,為自己專權參政掃清了來自宮內的阻力。賢妻,在今天的中國,仍然是丈夫對娶妻的最普遍心理期待,也是社會對妻子角色是否稱職的評價。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因為夫妻關系的主從性質,妻子的本份與職責就是為滿足丈夫的需要而存在的。漢時的女教圣人班昭形象地說:“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⑥事夫便當如事天。如何“事”呢?其一,是需對丈夫的事業及生命有助,謂之賢內助也。元關漢卿的著名雜劇《望江亭》中的潭記兒很能代表這種內助的作用:身為潭州理官的白士中,面對待皇帝尚方寶劍與金牌前來取他首級的楊衙內束手無策,妻子譚記兒挺身而出,扮做一美麗漁婦,以酒色迷之,賺取楊的皇帝寶劍、金牌,從而保住丈夫的官職與性命。⑥其二,是對丈夫的忠貞守節,從一而終,不管丈夫在世不在世。中國大地上雖經文革破壞而今猶存的貞烈石頭牌坊,就是用節婦們的青春與生命換來的。也許可以用曹禹的名作《雷雨》(1934)中男性家長周樸園對妻子繁漪的態度來說明:周令其妻吃藥,莫妻表示不想吃,周說:“就是自己不保重身體,也應當替孩子做個服從的榜樣。“服從的榜樣”,這就是傳統文化對良母品質最重要也是最具體的要求與認定。二接受現代化洗禮的中國女性中國女性“孝婦賢妻良母”的角色文化模式,在本世紀初中國劇烈的社會變革與思想變革中受到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重大沖擊。當時的有識之士,面對中國腐敗沒落之現實,無不痛感封建體制的腐敗沒落,人心不古,人心思變,反封建主義思潮遂成為主流。而西方現代文化挾物質文明、學術思潮,還有軍事侵略,長驅直人國力衰弱、國門洞開的中國,在引起國人極大的震驚外,同時也引起國人對自身文化的反省與批判,尤其是對可稱為慘無人道的女性文化。在關注國家與民族前途的視野中,在關注“人道”狀況的視野中。女性所身受的非人待遇才被人們前所未有地關注并被力倡改善。在此情況下.中國的“男人接過女權主義反對封建主義”。⑦女性在這場推翻封建固有秩序的斗爭中,可以說是不“自覺”地就成為一個“婦女解放”的天然同謀者、參與者與受益者。另外,在中國女性文化傳統主流之外,也一直存在著一種反女性文化傳統的聲音。她們并不安于既成命定,她們通過改變服裝的方式來改變文化性別,從而改變了自己命定的身份與位置;從而臍身于男性角色的行列中得于一展毫不遜色于男性的才華;從而打破了一種有關于男女能力與智力有別的神話界限。如從著名的六朝樂府《木蘭詩》中的花木蘭女扮男裝替父從軍,一直到胰炙人口的清長篇彈詞《再生緣》里的盂麗君女扮男裝中狀元。而在清末出現的反封建戰士,女革命先行者秋瑾(1875一1907)就是這一隱形傳統的承繼者與顯在看。中國女性的傳統文化使她不得不成為這樣的一個女人:當她定上革命道路之日,便就是她不能不背棄做“孝婦賢妻良母”之時棗她不得不拋夫棄子離家而去。她常常把自己妝飾在一襲男裝之下參與社會活動,這種反傳統規范的行為是否反過來也可以這樣證明:即便是做為革命者的秋瑾,在她文化女性的意識深處,仍隱藏著她對是女性棗以文化本質的服裝為性別鑒別棗就該天經地義地成為孝婦賢妻良母的潛在認同?但對其家庭來說,她事實上就是一個十足的不孝之婦、不賢之妻、不良之母。這也許便是秋瑾每每慨嘆身不得男兒列的隱情隱痛吧”。在秋瑾同時或稍后,一批生長在較為開明的中國貴族家庭或知識家庭的女性,得西洋現代風氣尤其是女權思想之先,也不約而同鄙視并拒絕自己本該扮演的傳統角色。如楊絳的姑母們,一定深受當時西洋女權思想的影響,否則她們恐怕很難做出:雖由父母之命而嫁,然而“出嫁后都和夫家斷絕丁關系”。尤其是三姑母楊蔭榆,其夫為獨子,她不僅抓破丈夫的臉皮,后索性就不回夫家,更莫談為夫家生兒育女。她拋棄了做“孝婦賢妻良母”的角色后,苦學勤工,先后留學日本、美國,從事女子教育,直至任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校長。⑩她們是五四運動前后一大批從家門中跑出來,從夫門中跑出來,從封建婚姻中跑出來的女性代表。她們厭棄傳統文化,她們企圖從西洋現代文化知識的汲取中,來改變自己的傳統屬定命運,做與自己的祖輩女性不一樣的人,過不一樣的人生,與此同時,在中國廣大的地區與眾多家庭中,“孝婦賢妻良母”仍在源源不斷被制造產生。如巴金小說《家》中的人物瑞壓。巴金用傳統經典的女性形象,一個典型的“孝婦賢妻良母”的形象塑造與其死亡,不再重彈“善有善報”老調,而是以其悲劇的毀滅,涉及了傳統女性角色事實上毫無生路的揭秘。這無疑從另一個角度促動了人們反省:中國女性也只有接受現代化。把目己從傳統角色中解放出來,才有出路與生機。傳統與現代化狹縫中的中國女性艱巨的、復雜的中國婦女解放,卻意想不到地被挾在中國民族革命、階級斗爭的過程中,隨著無產階級政黨的勝利與無產階級政權的建立而順利完成。此后,女性問題,不再因反封建任務的需要與迫切而被重視與提出。這就造成了‘種奇怪的現象:在婦女解放了的表象之下,四婦女參加社會工作,同工同酬;在制造了女性對自己性別意識的漠然之下,如婦女半邊天,男文都一樣,性別壓迫與性別歧視依然強大地存在于革命陣營、社會關系、人際關系、家庭關系、天妻關系以及個人意識之中棗反幾千年封建文化意識的任務實際上遠遠還未完成,也不能就此完成。中國女性陷進了一個對性別問題既十分敏感又認識模糊、既言不由衷又無法言說的境地。從說個體(女性)話語蛻變成說大眾(革命)話語的女作家丁玲,在四五十年代書寫了大量的革命作品間寫了一點對女性問題的觀察與思考的作品,便被革命視為異己分子,直至遠遠發配到北大荒不再寫作發言為止,可見當時意識形態對女性問題(當然還有別的問題)忌言的程度,中國重提女性問題是在被稱為本世紀第二次思想解放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包括女性主義在內的西方現代思潮,再次藉世界性文化交流之氣候與中國加速現代化之契機,堂而皇之地涌進國門,給思想文化界帶來了革故鼎新的助燃劑。中國文化女性在較為寬松而活躍的人文環境中,開始嘗試直面男性談論男權狀態下存在的性別歧視與性別壓迫問題。女作家開始在自己的文學本文中呈現這個問題和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孝婦賢妻良母”的角色內涵在兩性關系的歷史層面上,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與剖析。在大陸,受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啟蒙”與女性主義話語滲透現象是顯而易見的。在職業女性身上,她們從并不意識到自己是女性性別始,或是忌諱或是模糊,到意識并強調自己的性別,并把自己的性別意識帶進自己的工作或作品中去。人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涌現的一批女作家從努力創作與男性作家同步話語的作品,到終于有意識、且不恥講述出自己有關于性別問題的種種體驗與故事。張辛欣《在同一地平線上》率先尖銳地把一個長期以來人們避而不談,或無法說清的問題揭示出來:即在中國目前的性別意識狀態下,即使是一個接受過高等教育,有良好文化素養的知識女性,也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追求事業、堅持獨立與做一個賢妻良母的角色之間兼得;同時她還揭示了當代中國知識女性所特有的兩難境地,即要愛就必須犧牲,犧牲自我、個性。
注釋: ①元陽真人著,倪泰一編:《易經說勢傳》,《同易》,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頁。②班昭:《女誡·卑弱第一》,《后漢書》眷八十四《列女傳·曹世叔妻》,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787頁。②《明史》卷一八九,《列女傳一》,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691頁。④蔡東藩:《慈搐太后演義》,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⑥班昭:《女誡·專心第五》,第2790頁。⑧減晉叔編:《元曲選》,中華書局1958年版。⑦[清]李漁短篇小說集《十二樓》之《奉先樓》,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⑧李小江等主編:《性別與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68頁。⑨曹禹:《雷雨》,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⑩李小江等主編:《性別與中國》,李小江認為這是女權主義進入中國的一個特點。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5頁。⑩鄭云山著:《鑒湖女俠秋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⑩楊絳:《回憶我的姑母》,《將飲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87?/FONT>116頁。⑩張辛欣:《在同一地平線上》,《收獲》1981年第6期。⑩張潔:《方舟》,《收獲》1982年第2期。⑩方方:《行云流水》,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88一150頁。⑩拖莉:《你是一條河》,《小說家》1991年第3期。⑩埃萊娜·西蘇:《美杜莎的笑聲》,張京援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頁。⑩林白:《致命的飛翔》,《花城肥995年第l期。⑩這里借用臺灣子宛玉主編的《風起云涌的女性主義批評》一語,以概臺灣女權運動與女性主義思潮流行的現象。谷風出版社1988年版。⑩這里借用女性主義作家林白的小說之名《一個人的戰爭》,以概括中國女性在當下文化進程中的精神狀態。小說見《花城》1994年第2期。⑩《傷逝》中的新文化女性子君置社會家庭的非議于不顧,勇敢爭取婚姻自由,成功地與愛人渭生同居,但渭生不久后就發現成為妻子的子君全然與先前不一樣了,平庸、怯弱、依賴,在渭生的冷淡與厭棄下,子君只有回到娘家,并寂寞地死去。魯迅《訪捏》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l14一1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