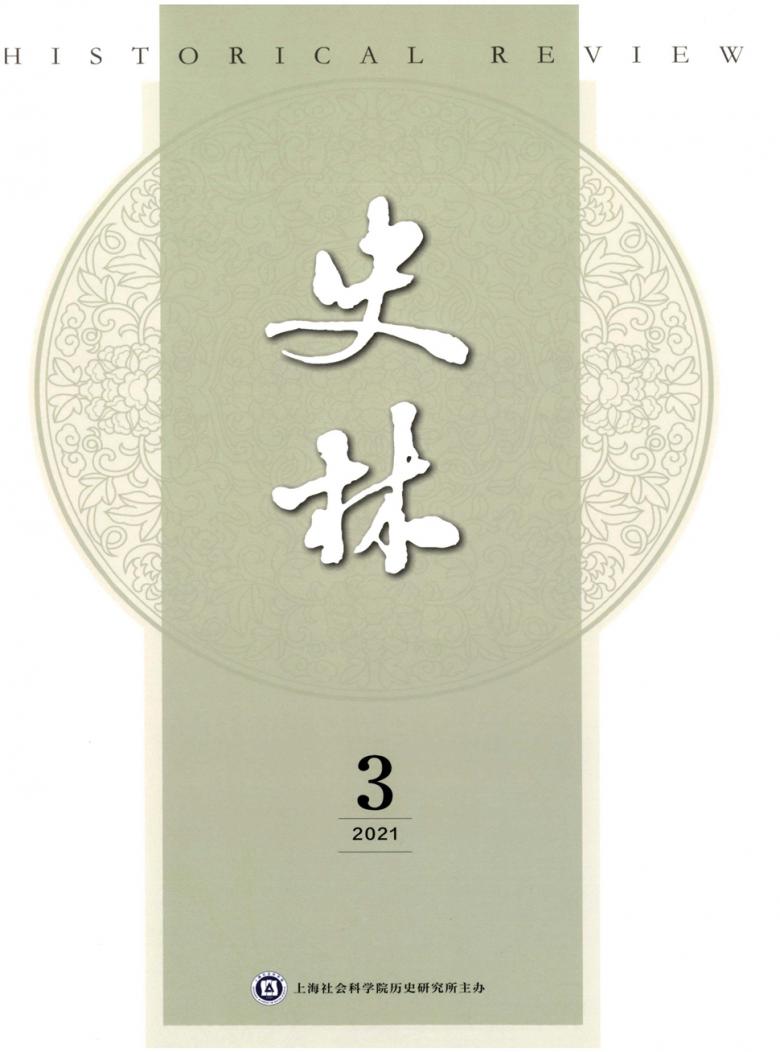關于中國現代文學、文化中的頹廢和城市——評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
練暑生
: 現代性正在成為一個巨大的學術話題。這個話題深刻地影響到文學史研究,特別是現代文學的形成及其內在構造。李歐梵的《現代性的追求》是一部相當重要的著作。關注印刷文化對于現代性的意義,關注“新感覺”派小說以及城市文化的意義,考察“頹廢”的美學風格,這一切無不為現代文學研究提供了異于傳統的坐標。如果說,“國民性”、鄉土中國、左翼文學、《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均是我們熟悉的范疇,那么,《現代性的追求》提到的諸多問題顯示了新的視域。盡管這些問題已經在現代性研究中得到程度不同的論述,但是,這些問題進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仍然意義非凡。當然,如同人們時常發現的那樣,洞見與盲區往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新的視域可能產生新的遮蔽。從這一意義上說,《現代性的追求》也存在某些疑問,至少存在一些值得進一步討論的空間。這肯定將引起一系列后續的對話——這篇書評不妨視為對話之一。
自夏志清1961年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開創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以來,海外漢學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不僅“蔚為風潮”,而且能人輩出。王德威曾指出:“在中堅一輩的學者中,李歐梵教授的成就,堪稱最受矚目。” ①李歐梵的現代文學研究,一方面和王德威一樣,重視晚清文學的現代性意義,力圖把中國現代文學的起源推向晚清;另一方面,他從美國學者卡林內斯庫在《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提出的“美學現代性”和“資產階級文明現代性”的對立這一基本問題出發,在反思現代性的問題視野中考察了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現代性”追求的文化和美學特征,特別是“城市-頹廢”文學、文化問題的提出,突破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以“五四”啟蒙為分水嶺、建立在“線性進化論”基礎上的新/舊、傳統/現代等二元對立的常識框架,為重寫現代文學史提供了一條新的理論線索。《現代性的追求》(三聯書店2000年版)比較全面地反映出李歐梵近年來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成果。全書共分三輯,第一輯“真的惡聲”兩篇文章,分別討論了印刷業和中國的現代性以及魯迅思想的內在矛盾問題;第二輯“浪漫的與頹廢的”共六篇文章,主要討論了所謂“五四浪漫個人主義”和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城市-頹廢”;第三輯則收入了兩篇寫作于70年代初的文章,這是他應《劍橋中國史》之邀而作的兩篇關于中國現代文學歷程的長文。第二輯是全書的核心,用王德威的話來說是“最見其個人情性的發揮” ②。其中,《中國現代小說的先驅者——施蟄存、穆時英、劉吶鷗》和《漫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頹廢”》兩篇文章,是其反思中國現代文學之現代性內部諸矛盾的集中體現。
一
在《漫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頹廢”》(以下簡稱《漫談》)一文中,李歐梵首先指出:“從一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角度來談頹廢,當然是一件極為困難——甚至不可能的事。即使從新文化運動所用的詞匯來看,一切都是一個‘新’字,氣象一新,許多常用的意象指涉的是青春、萌芽、希望。” ③而“頹廢”(decadence)卻是一個有關于時間和歷史逐漸走向衰落的概念。卡林內斯庫指出,頹廢概念是一個古老的神話-宗教主題——“時間的破壞性和沒落的宿命” ④。在基督教文化傳統里,關于時間、歷史的頹廢和進步的意識其實構成了一種辯證對立的復雜關系,因為基督教的“末日審判”信仰,使“千年至福的信念”和“末日的陰沉期望”共存于中世紀基督徒的內心意識中。而自文藝復興以來,隨著科學、理性和人道主義信念的確立,人們逐漸發展出了一套關于歷史是無限發展的樂觀主義信念——即所謂的“進步神話”,但在這種樂觀主義背后同樣伴生出一種新的“頹廢”觀念。“高度技術的發展同一種深刻的頹廢感顯得極為融洽。進步的事實沒有被否認,但越來越多的人懷著一種痛苦的失落和異化感覺來經驗進步的后果。” ⑤這種“頹廢”感從19世紀中后期法國象征派詩歌中逐步發展起來,并最終形成了一種“現代性”自身的對立面——“美學現代性”。“這種美學現代性盡管有著種種含混之處,卻從根本上對立于另一種本質上屬資產階級的現代性,以及它關于無限進步、民主、普遍享有‘文明的舒適’等等的許諾” ⑥。在這一觀念下考察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頹廢”問題,李歐梵認為,雖然“五四”傳統致力于求“新”,但是作為與始發于西方的現代性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中國現代文學,“頹廢”卻成為其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概念。“它是和現代文學和歷史中關鍵問題——所謂‘現代性’(modernity)和因之而生的現代文學和藝術——密不可分的。” ⑦
那么,“頹廢”究竟在中國現代文學進程中具體扮演什么角色?在所謂的“頹廢現代性”和“進步現代性”相對照的問題框架下觀照中國現代文學進程,中國現代文學將呈現出怎樣的美學和文化形態?在《漫談》一文中,李歐梵從時間觀念入手,指出“五四”時期《新青年》對“理性主義、人本主義、進步的觀念”等啟蒙精神的呼喚,對中國最大的沖擊是時間觀念的沖擊,即“從古代的循環變成近代西方式的時間直接前進——從過去經由現在而走向未來,所以,著眼點不在過去而在未來,從而對未來產生烏托邦式的憧憬”。這種線性前進的時間想象導致了一種新的歷史意識形態:“歷史不再是往事之鑒,而是前進的歷程,具有極度的發展(development)和進步(progress)意義。” ⑧因此,“五四”所繼承的“現代性”其實是卡氏意義上的所謂的“資產階級的現代性”,即所謂的“進步現代性”。“經過五四改頭換面之后(加上了人道主義、改良或革命思想和民族主義),變成了一種統治性的價值觀,文藝必須服膺這種價值觀。” ⑨由于“頹廢”從未作為“現代性”的另一面進入中國現代作家的追求視野,因此,在一切都求新的“五四”時代,“頹廢”作為一個關于墮落或衰敗的概念成為了一個“不道德的名詞”。
李歐梵獨重“頹廢”的現代美學和文化意義,因為“頹廢”作為一種反資產階級庸俗現代性的美學立場,“它更注重藝術本身的現實距離,并進一步探究藝術世界的內在真諦” ⑩。因此,和當年夏志清立足于“純文學”框架勾畫出一條所謂非政治化的現代文學譜系一樣,李歐梵則基于“頹廢美學”立場,在中國現代文學版圖中構建出一條“頹廢”文學史線索。在《追求》第二輯的后三篇文章里,李歐梵追尋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的歷史譜系,它上接中國晚明文學、《紅樓夢》,下接新感覺派、葉靈鳳、張愛玲,在某種意義上還包括魯迅和郁達夫。雖然中國的“頹廢文學”特別是“新感覺派”的作品與西方的“頹廢文學”有著相當密切的聯系,然而李歐梵卻進一步指出,這些城市頹廢作家“在模仿英法頹廢之余,并沒有完全體會到其背后的文化意蘊……其資源仍來自‘五四’新文學商業化以后的時髦和摩登”。在這張頹廢系列圖中,他認為只有張愛玲是一個例外,因為這位女作家作品中的“荒涼感”,包含著對“時間和歷史的反思”,是對于“現代歷史洪流的倉猝和破壞的反應”。(李歐梵認為魯迅的某些作品已經“跨入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門檻”,但是魯迅的“那種彷徨的心靈并沒有完全迷失在虛無主義之中”,最終還是“退回”到中國現實中,加入了“他的同時代人的那種‘現代化進程’”。)
二
李歐梵引入“頹廢”現代性的問題框架,并不僅僅只是提供了一條重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新線索,他還力圖據此反思“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性追求”的整個文化進程。作者認為,“五四”知識分子在“進步現代性”的新歷史觀的影響下,“有人開始去疑古,有人開始對歷史分期和中國社會本質展開辯論,而最終的趨勢是知識分子的偏激化(radicalization)和全盤革命化。”為此,他在反思現代性內在矛盾的視野下,指出所謂“五四浪漫個人主義”、30年代的現實主義和最終全面革命化這些似乎具有各自獨立性的文學問題背后,存在著相同的現代性態度或者說現代性信仰。第二輯的《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浪漫個人主義》等前三篇文章分別討論了“五四”的“個人主義”、“孤獨的自我”和“情感”等所謂的“浪漫個人主義”問題。作者認為“五四”對“個人主義”的標榜,形成了一種關注“本我”的主觀主義的創作潮流。主人公與他所處的“客觀環境”之間的那種陌生和疏離的關系,“成了早期‘五四’小說的一種典型的安排”。這不僅“對于整個中國文化來說,是相當獨特的”,而且對于文藝創作而言是一種“有意義的關系”。但是,“五四”的個人主義是在反傳統的特定背景下提出的,是一種更傾向于追求進步、創造新世界的歷史姿態,而不是一種有可能趨于“頹廢”的美學態度。因此,中國現代文學的“這個內向性的旅程并沒有能在最終將這群作家帶領到存在主義式的絕望或藝術上的超越現實……對中國現代作家而言,他們最終的依據依舊是他們那個時代的歷史現實。”在第三輯的《追求現代性(1895-1927)》這篇總體把握中國現代文學發端期的長文的最后部分,李歐梵總結性地指出:無論是20年代前期的主觀抒情的泛濫,還是從20年代末開始的日益政治化的文學,中國現代作家從未“否棄現實”,并“一直在憧憬著光明的未來”。由于反“進步”的“頹廢”態度的缺失,隨著20年代后期中國社會現實日趨緊張,在“孤獨的自我”中游蕩了十年的中國現代作家,逐漸放棄了“個人主義”,“由對作者本身狹窄的個人經驗轉移到另一個更寬廣的社會現實上去”,“把現實主義作為改革社會的工具,把個人與集體逐漸合而為一,而最后終于把人民籠統地視為革命的動力和圖騰。” 在頹廢現代性與資產階級物質現代性的矛盾框架下反思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進程,無疑在“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等建立在“線性進化論”基礎上的問題框架之外,為我們思考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進程(包括當代問題)開辟了一個新的問題視閾。不過,李歐梵在現代文學、文化史研究中引入“頹廢”現代性的參照框架并不是企圖拒絕“現代性”這一歷史、文化平臺,也沒有表現出用全球經驗及其相關的問題性“化約”中國地方經驗的“海歸”常態(他對中國現代性進程的設想,其實非常重視中國文化-經驗特別是日常生活經驗的復雜性,詳見下文)。在文學史領域,作者獨重“頹廢”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與他對所謂“純文學”的追求這一美學和藝術傾向密切相關;而在文化史問題上,以“頹廢”作為參照批判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對“進步現代性”的片面追求,則是出于對中國現代性進程的獨特認識。在李歐梵看來“‘現代性’既是概念也是想象,既是核心也是表面”。他聲稱他對概念不感興趣,而是關注工業文明條件下形成的聲、光、化、電等處于日常生活層面的物質表象,作為“集體感性之輪廓和文化產品”,它們“并不一定進入深層思維,但它們必然召喚出一種集體‘想象’”。在這一前提下,李歐梵認為,中國的現代性進程是在西方的知識體系,特別是工業文明條件下的物質構造、日常生活表象和復雜的傳統文化、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經驗等錯綜復雜的糾葛過程中形成的,是一種接近于“自發狀態”的中國現代性工程,而不是由某種理論體系設計出來的結果。“中國的現代性不可能只從一個精英的觀點來看待,精英只能登高一呼,至于社群共同的想象,其風貌和內容不可能是一兩個人建立起來的,需要無數人的努力”。而在其中,大眾出版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談到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時,作者指出:“作為‘想象性社區’民族之所以成為可能,不光是因為像梁啟超這樣的精英知識分子倡言了新概念和新價值,更重要的還在于大眾出版業的影響。”
因此,李歐梵以現代性中的“頹廢”為參照,批判“五四”知識分子所片面追求的“進步現代性”,其矛頭其實是指向建立在“線性進步”史觀基礎上的、企圖憑借某種所謂科學的概念體系設計歷史和未來的啟蒙精英主義或者說先知主義(左翼思想就是其中的代表,事實上無論在美學還是在文化意義上,李歐梵的“頹廢”都包含著對左派文藝的反撥)。對存在于城市日常生活中“自發式現代性進程”的信任,是作者對一百多年來中國人追求現代性進程中飽經戰爭與革命之苦進行自覺反思后的結果(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國現代作家“把現實主義作為改革社會的工具,把個人與集體逐漸合而為一,而最后終于把‘人民’籠統地視為革命的動力和圖騰”。)第一輯中的《批評空間的開創》一文從《申報》副刊《自由談》切入,特別強調了晚清和民初的“游戲”文章在“造就新國民”和“開創新的社會的空間”方面的價值。第三輯中的《現代性的追求》一文中,作者更為系統、明確地闡述了晚清刊物和通俗小說實踐的現代性意義,“在‘文學革命’前至少二十年,都市文學刊物……已經為日后從事新文學運動的人們建立起市場和讀者群”;同時,編輯和作者們的作品“所獲得的商業上的成功證明文學能夠成為一種獨立的、能夠賺錢謀生的職業”;此外,也許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印刷出版業的推動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文學精英的共同努力,“嶄新的知識生命和政治意義”藉此得以廣泛傳播。晚清帶有嚴肅的政治目標的“新小說”理論及其創作實踐,到了民初逐漸被“迎合中產階級和下層民眾趣味”的鴛蝴式都市通俗小說所取代。作者認為以鴛蝴派為代表的文學“遁世主義”的盛行,除了因為人們對民初的國家現實普遍感到失望以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新的都市生活”的形成,它“反映出都市居民在經歷‘環境現代化’——這種急速變化過程中那種心理上的焦慮不安”。但是嚴肅的啟蒙意義的缺失并沒有損傷這些小說的現代性意義,恰恰相反,在李歐梵看來,正是在《文明小史》、《玉梨魂》之類的小說所展示的華洋雜處的生活情境和東西混交的敘述形式中,一種塑造中國人的新型文化想象的“大敘述”被創造出來——上海這個由所謂“新的公共構造”和“新的日常物質生活表象”所共同構造出來的現代性文化形態,就是這種自發現代性進程中的典范文本。
為此,他繞過了“五四”啟蒙主義,構建了始發于通商口岸的、從民族國家想象到城市-日常生活現代性想象的所謂中國“自發現代性”進程。“中國的現代性我認為是從20世紀初期開始的,是一種知識性的理論附加于在其影響之下產生的對于民族國家的想象然后變成都市文化和對于現代生活的想象”。并在此基礎上,以城市-鄉村二元框架重構了中國現代文化尤其是文學的基本格局:“中國現代文學中如果有城鄉對比的話,鄉村所代表的是整個的‘鄉土中國’——一個傳統的、樸實的、卻又落后的世界,而現代化的大城市卻只有一個上海”(在這張新型城鄉文化地圖中,即使是北京也是屬于“鄉村”)。不過,中國“現代性”進程中的諸多問題是一個知識問題,同時更重要的它還是一個經驗問題。在卡林內斯庫那里,“頹廢”本身就是經驗到充分發展的現代性所帶來的異化現實并抗議這種現實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在積弊重重、內憂外患的20世紀早期,“五四”知識分子選擇了“進步現代性”的知識信仰是否有自己的歷史-現實經驗合理性?中國的現代性追求并不是簡單被動地接受西方“現代性”知識系統,而是一個立足于自身的經驗現實和知識傳統對外來知識不斷進行取舍和改造的過程,因此,究竟是從“進步”知識角度還是從中國歷史-經驗的復雜性出發來解釋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從個人主義走向全面革命化的歷史過程,是一個值得深入考量的問題。
三
由于對“自發現代性”的信任,李歐梵因此特別重視由工業文明條件下的日常物質表象所召喚出來的城市——“上海”,以及在這一城市文化條件下形成的現代性另一面——“頹廢”文藝。但是在近現代中國復雜的歷史-經驗背景下,這種以上海——城市為典范的或許是成功的中國現代性經驗是否能作為整個中國的現代性方案來設想?因為,如果上海是所謂中國集“自發現代性”之大成者,那么需要考慮的是這種“自發性進程”是在什么歷史和現實條件下形成的?這些條件又包含著怎樣的上海內部差異和上海與中國廣大內地的差異關系?如果上海的內部階級分化問題可以視作現代性進程中的不可回避的結果,因而可以避而不談,而且在中國特殊的文化、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所謂上海“世界主義”可以兼容華洋,從而消解殖民問題,那么上海與中國內地之間的外部差異關系卻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
稍具中國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上海從開埠以來所經歷的所有歷史沉浮是中國近現代史進程的直接結果,它的繁榮與近現代中國復雜的政治進程和上海獨特的地理位置密切相關,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它與殖民特權的關系。有論者通過資本主義生產與全球空間構造之間的關系對此曾作過不失精辟的論述:為了維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剝削關系,“資本主義不僅在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同時也在殖民地內部重組了‘中心’和‘邊緣’的空間關系”。這種在殖民地內部的空間重組不僅導致了上海、孟買等城市的繁榮,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復制了類似于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空間關系,為自己的發展制造出依附于‘中心’的廣闊‘邊緣’,以‘邊緣’地區的資金、原料、勞動力和市場來滋養殖民都會的繁榮”。在這個意義上,以上海為代表的所謂“自發現代性”只是一種在殖民特權保障下的“理想形態”,“上海”和中國廣大內地之間構成的所謂“城鄉對照”,也因此并不是單純的在現代性條件下的 新型城鄉文化地理劃分,更重要的它還是一種復雜的政治、經濟等方面利益相互沖突的產物。有論者甚至還認為,“‘上海’與中國是此消彼長的‘蹺蹺板關系’,中國的內地越凋敝,‘上海’的城市越浮華,最極端的,是上海‘淪陷’時期,國家主權完全喪失,‘上海’社會醉生夢死,畸形地最后地瘋狂。”《春蠶》中老通寶一家因豐收而破產的故事,顯然可以視作這種近乎不可調和的城鄉矛盾關系的經典寓言。因此,如果對以上海-內地關系為代表的、現代性條件下的城鄉政治經濟學缺乏必要的討論,所謂的“自發現代性”即使充分照顧到華洋兩方面文化和日常經驗相互糾葛的復雜性,也只不過是用市民化的“日常生活烏托邦”代替了精英主義的“理論烏托邦”。當然,單就“上海”自身而言,它在所謂的“自發現代性”進程中無疑創造了不失為輝煌的現代性大觀。正如李歐梵所提到的那樣,這不僅表現在其自身的聲、光、化、電以及由此召喚出了城市——頹廢文學,而且“上海”在中國現代文學中還占據著特別重要的地位,如與中國現代文學相關的一系列文學文化活動如印刷出版業、作家群體活動大多集中在城市(在李歐梵看來即使是輕視城市文學的左翼作家也是“城市的產物”)。由于“城市”在中國的現代性追求中的特殊地位,在李歐梵建構出來的新型“城鄉”文學、文化二元框架下,作者還特別指出了中國現代作家在內心對待城市的一種特殊態度。在《中國現代小說的先驅者》一文中,李歐梵指出“‘五四’以降中國現代文學的基調是鄉村,鄉村的世界體現了作家內心的感時憂國的精神”,但是“中國現代作家的想象世界雖以鄉村為主,他們的生活世界卻不免受到城市的影響;作家心目中的矛盾也就奠基在這個無法調節的城鄉對比上”。中國現代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與上海——城市之間既依賴又疏離的矛盾關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也正是這種中國現代作家與城市空間的特殊關系還隱含著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因為,中國現代作家身上對“上海——城市”的這種類似精神分裂式的態度,并不只是城-鄉文化沖突的結果,這里面折射出更深層次的中國現代性問題,那些來自五湖四海的作家,是身背著巨大的身份差異(包括地域、語言甚至種族)而聚集于通商口岸。一方面,他們來到上海充分享受著這座城市在思想、創作甚至生活上提供的便利;另一方面,他們充滿差異的身世背景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切身經驗使他們都很清楚地意識到:這座殖民都會的現代化只不過是殖民特權保障下的中國特殊地域的產物。因此,在這種特殊的身份與空間的意識條件下,他們的中國身份意識和他們“在上海”的身份意識無疑會經常發生激烈的沖突。這種沖突不僅僅折射出上海/內地之間文化的、政治經濟方面的差異關系,同時更重要的是它還應是中國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特殊性的反映。中國是從一個前現代的帝國轉換為現代主權國家,因此現代中國民族國家想象的形成,與那種以方言為單位,以單一民族為主要形式的民族國家想象的創制過程應該存在著很大的不同。關于這一點,汪暉曾指出:“既不是方言,也不是地方性……這個‘想象的共同體’及其認同,與其說是全新的現代創制,毋寧是民族形成的漫長歷史中不斷衍生的話語、制度、信仰、神話和生活方式的產物,是民族戰爭和現代政黨政治在民族運動中將地方性文化綜合在民族主義的訴求之中的方式和能力。”李歐梵所設想的由印刷資本主義所推動、存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的“民族國家-城市-現代性日常生活想象”的“自發性進程”也許更適合于單一民族國家。很難想象一個內部存在著族群、地域、語言甚至是人種等方面巨大差異的帝國,沒有一種類似儒家文教禮儀的抽象理念的支持,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全局性的政治動員和觀念重組,前清帝國留下的人口、版圖和多民族體制可以通過始發于上海等通商口岸的“自發現代性”進程,在不導致分裂的情況下整合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如果把這些復雜的中國現代歷史-經驗問題考慮進去,這種所謂的“自發性進程”至多只能形成區域認同,如今天人們所熟悉的上海認同或香港認同。
在這個意義上,“一種能夠將個人從家族、地方性和其他集體認同機制中抽離出來并直接組織到國家認同的”、在某種意義上是精英化的新概念,在中國現代性進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否應具有中國歷史和現實經驗的合理性?中國現代作家在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最終走向“全面的革命化”,以及1949年以后所謂“城市‘精神狀態’的消失”,或許是中國完成由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化時必須付出的代價?正如劉小楓在論述中國現代國家形態為何最終采用了政黨國家的形式時所指出的那樣:“中國之革命黨的出現,正因為它們承擔了為民族共同體爭取現代國家形態的歷史使命。”
①②王德威:《現代性的追求·編后記》:載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340頁。
③⑦⑧⑨⑩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第145頁、第142頁、第146頁、第149頁、第149頁、第166頁、第166頁、第233頁、第238頁、第146頁、第59頁、第47頁、第65頁、第240頁、第66頁、第146頁、第181頁、第191頁、第111頁、第112頁。
④⑤⑥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61頁、第167頁、第173頁。
李歐梵:《上海摩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頁、第71頁、第56頁。
李歐梵:《晚清文化、文學與現代性》,上傳日期:2003-4-20,http://www.liyangwz.com。
李歐梵:《當代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和后現代性》,載《文學評論》1999年第5期。
羅崗:《再生與毀滅之地——上海的殖民經驗與空間生產》,載當代文化研究網www.cul-studies.com。
倪文尖:《再敘述:“上海”及其歷史》,載新青年北大在線之文學大講堂。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一部),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78頁、第79頁。
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