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書降神”新議——北宋與契丹的文化競(jìng)爭(zhēng)(一)
胡小偉
“澶淵之盟”是北宋武力收復(fù)五代以來北方失地的最後一次認(rèn)真努力。這次戰(zhàn)役雖然以小勝結(jié)束,但最終訂立的盟約,卻是宋廷每年向遼輸納白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名副其實(shí)地“化干戈為玉帛”。[i]古云:“天子之事,唯祀與戎。”既然戎事不行,精力自然轉(zhuǎn)向“祀”來。據(jù)說和議成立後,“上(宋真宗)既罷兵,垂意典禮”,[ii]也是“偃武修文”的意思。這種反復(fù)倒也和太祖太宗的政策相距不遠(yuǎn)。但對(duì)于宋真宗趙恒而言,“澶淵之盟”的輸款結(jié)好,無論如何喚不起踵武漢唐的感覺來。既欲彰顯盛世,則無論遠(yuǎn)述秦皇漢武,近譬唐代玄宗,致力祀事都是標(biāo)明盛世,點(diǎn)綴太平之一大景觀。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無平等結(jié)盟的先例可循,宋與契丹的澶淵之約是用賭咒發(fā)誓的方式訂盟的。據(jù)載宋人的盟書寫明:
“質(zhì)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jiān),共當(dāng)殛之!”
契丹文書亦有“孤雖不才,敢尊誓約。有渝此盟,神明殛之”等語。[iii]可知盟誓雙方都具有共同的,至少是相當(dāng)?shù)奶斓厣耢笮叛鱿到y(tǒng)。后來宋徽宗約金滅遼,違背了這個(gè)誓言,不久金兵入汴,徽欽二宗“北狩”,“斧聲燭影”以后當(dāng)政的趙光義一系宗室親貴,幾乎都被擄往漠北,受盡凌辱,異鄉(xiāng)為鬼。趙構(gòu)只身南渡,卻終因無後,傳位給趙匡胤之後裔。南宋與金亦曾有類似的詛神盟誓,只是輩份矮了一節(jié),屈身為“侄”,但後來約蒙伐金,如出一轍,結(jié)局也差似。故宋遺民曾感慨系之,曰:
“國家與遼結(jié)歡。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宣和伐燕之謀,用其降人馬植之言,由登、萊航海,以使于女真,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土地歸本朝。時(shí)主其事者王黼也。時(shí)論多以為不可。宇文虛中在西掖,昌言開邊之非策,論事亶亶數(shù)千言。設(shè)喻以為猶富人有萬金之產(chǎn),與寒士為鄰,欲肆吞并以廣其居,乃引暴客而與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得其全。”暴客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為切鄰強(qiáng)暴所窺。欲一日高枕安臥,其可得乎?種師道亦言今日之舉,如寇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分其室也。兩喻最為切當(dāng)。當(dāng)事者既失之于女真,復(fù)用之于蒙古,而社稷隨之矣。”[iv]
這種“瀆神背盟,該遭報(bào)應(yīng)”的宿命,就像一個(gè)壓在中華民族心底的夢(mèng)魘,即使在今天看來,仍然不脫某種荒誕的巫術(shù)味道。如果我們明白“恢復(fù)情結(jié)”和“神道設(shè)教”這兩個(gè)主題詞,實(shí)際上與有宋一代,特別是崇道的真宗、徽宗兩帝共相始終的話,那么會(huì)更容易理解這節(jié)文字論述的重心所在。
有關(guān)宋代國君崇道傳統(tǒng),以及“天書封禪”、“蚩尤作亂”與關(guān)羽崇拜的關(guān)系,筆者已有論述。[v]此節(jié)所論,是“天書降神”究竟只是一場(chǎng)短暫的鬧劇,還是一個(gè)影響深遠(yuǎn)的政治文化設(shè)計(jì)之開始。這對(duì)于我們理解關(guān)公崇拜所以大興于元、明、清三代,是很有必要的。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景德四年(1007年)十一月條記載說,殿中侍御史趙湘曾上言請(qǐng)封禪,真宗不答。王旦等奏:“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圣朝承平,豈能振舉?”真宗也表示“朕之不德,安敢輕議?”[vi]但他的內(nèi)心里,恐怕總是有一點(diǎn)不甘。既不能收復(fù)燕云失地,建立祖宗夢(mèng)寐以求的功業(yè),又想當(dāng)盛世的明君圣主,趙恒的這種兩難情意結(jié),被聰明透頂?shù)耐鯕J若敏銳地捕捉到了:
“契丹既受盟,寇準(zhǔn)以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zhǔn),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為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zhèn)服四海,夸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dāng)?shù)锰烊鹣J澜^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圣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旦黽勉而從。帝猶尤豫,莫與籌之者。會(huì)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cè)其旨,漫應(yīng)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設(shè)教爾。’帝由此意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fā)之,皆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fù)異議。’”[vii]
這是一般引述的看法。但司馬光《涑水紀(jì)聞》記述王欽若的回答,側(cè)重卻略有不同:
“今國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敬鬼神,今不若盛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viii]
無論成書年代還是史官地位,司馬光的這條記載都更應(yīng)該成為本文論述的基礎(chǔ)。下文再談。
“以神道設(shè)教爾!”可謂一語道破了天機(jī)。緊接著宋真宗期待的奇跡就相繼出現(xiàn)了,而降神、天書、封禪、祥瑞等事也次第展開。關(guān)于“天書降神”的整個(gè)過程,《宋史·禮七(吉禮七)》中有比較詳細(xì)的記述,可以參看。大致而言,這一次精心設(shè)計(jì),而且持續(xù)了十?dāng)?shù)年之久的“國家造神活動(dòng)”,主要經(jīng)歷了三個(gè)階段:
第一階段謂之“造勢(shì)”。趙恒說“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ix],告曰:‘來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黃箓道場(chǎng)一月,將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接著就是連降“天書”,總計(jì)三次,第一次是“左承天門屋南角有黃帛曳鴟尾上,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道,封處有字隱隱,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內(nèi)容則是“趙受命,興于宋,付于恒。[x]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書·洪范》、老子《道德經(jīng)》,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凈簡(jiǎn)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然後“天書”又不厭其煩,在四月、六月分別再降于宮禁及皇帝即將“封禪”的泰山。其間自然伴隨著異香紛呈,祥云繚繞,先把道具的功夫做足了。
第二階段則是“發(fā)揮”。這就是以“東封泰山”、“西祀汾陰”和“朝謁老子”為主要標(biāo)志的大規(guī)模全國性“巡游表演”,以及朝野上下經(jīng)久不息的朝奉祭拜的“廣場(chǎng)表演”。此外的典禮儀制諸如上尊號(hào),修儀注,建宮觀,祀岳瀆,也都不惜花費(fèi),務(wù)求崇大。各地官員亦不憚勞煩,爭(zhēng)相報(bào)符瑞,呈禨祥。趙恒也典從理順,亦步亦趨,不惜以皇帝之至尊,敬禱備至。可以說主要演職員和參與的群眾,都把自己的戲份演到了十足十。
第三階段照例是“曲終人散”。隨著趙恒駕崩,他的兒子宋仁宗趙禎為尊者諱,“一抔黃土掩風(fēng)流”,將“天書”隨葬永定陵。這出戲的其它主要演職人員,也相繼以不太光彩的方式謝了幕。曾任會(huì)靈觀使、景靈宮使的王欽若雖經(jīng)道士譙文易案牽連,但都得到優(yōu)容,黜而復(fù)相,只是史家定評(píng),可謂“誅心”之論。玉清昭應(yīng)副使的丁謂最終被貶崖州。景靈宮副使林特落職知許州。亳州太清宮經(jīng)度制置副使、天書同刻玉副使陳彭年早逝。他們和真宗權(quán)閹劉承珪一起,榮幸地入選“五鬼”之列。而趙恒本人晚年也頻頻發(fā)作“心疾”之癥,形同瘋癲。不提。[xi]
這樁“天書降神”的奇事,其實(shí)在北宋就頗有詬病爭(zhēng)議,主要理由是“侈靡費(fèi)財(cái)”,其次是“危亂之跡”。更深層的原因還有儒家的理性反抗,這就是孫奭著名的駁論“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明史·海瑞傳》稱為“兩語括盡欺詐”。批判諸賢已經(jīng)列舉了足夠理由,故不贅。
但是從道教立場(chǎng)又生發(fā)出另一層意思。他們?cè)O(shè)問,如果是僅僅為了雪澶淵納幣之恥而降神、封禪,為什么會(huì)相隔三年之久?他們以為,宋真宗需要提攜本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借以鎮(zhèn)懾契丹貴族,崇奉道教乃是其中關(guān)鏈的一環(huán)。據(jù)宋僧志磬的《佛祖統(tǒng)紀(jì)》一書所載,景德四年(1007年)臣僚言:“愚民無知,佞佛過度,謂舍財(cái)可以邀福,修供可以滅罪,蠹害國政,宜加禁止。”真宗對(duì)宰臣說:“佛教使人遷善,誠有其益,安可禁之?且佛法所至甚廣,雖荒服諸國皆知信奉。唯道教中原有之,然不甚盛。”王旦答對(duì)說:“頃歲虜使登開寶塔,瞻禮甚虔,當(dāng)戒殺,及至上清宮,不復(fù)屈膝。是知四夷唯重佛而不敬道也。”[xii]這是發(fā)生在與“降神”同年的對(duì)話。同年三月,真宗游幸龍門,睹巖崖石佛甚多,經(jīng)會(huì)昌法難毀廢,皆已摧壞。左右進(jìn)言:“非官為葺治,不能成此勝跡。”真宗答道:“軍國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勞費(fèi)滋甚。”[xiii]十一月,真宗又對(duì)王欽若說:“君臣事跡,崇釋教門,有布發(fā)于地令僧踐之,及自剃頭以徼福門。此乃失道惑溺之甚,可并刊之。”[xiv]關(guān)鍵在視佛教為“外教”,足見真宗崇道,乃是被宋遼和戰(zhàn)刺激起來的民族主義意識(shí)的表現(xiàn)。[xv]問題涉及到了宗教,寓有“文化抗衡”的意味,或者更接近事實(shí)。但是否真宗只是單純以“崇道”對(duì)抗遼主“佞佛”,似仍不足以服人。
倒是元朝修撰《宋史》時(shí),理學(xué)編撰者對(duì)趙恒表示了相當(dāng)?shù)睦斫猓⒃凇墩孀诒炯o(jì)》後附評(píng)贊曰:
“贊曰:真宗英晤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屢言其聰明,必多作為,數(shù)奏災(zāi)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雜,天書屢降,導(dǎo)引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dāng)。瑦貉员印F醯て渲鞣Q天,其後稱地,應(yīng)歲祭天,不知凡幾。獵而手接飛鴈,鴇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xí),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jìn)‘神道設(shè)教’之言,欲假是以動(dòng)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jì)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按元丞相脫脫當(dāng)初率人分別撰修宋、遼、金三史,各自獨(dú)立,因而後人未能在《遼史》中見到相關(guān)或相應(yīng)的記述,趙翼《廿二史札記》反而批評(píng)元修《遼史》“太簡(jiǎn)略。蓋契丹之俗,記載太少。”且遼國歷代修史早有舊稿。[xvi]亦可推斷上述議論也是有據(jù)而發(fā)的。這道出元儒這樣一個(gè)認(rèn)識(shí):宋遼之對(duì)抗,除了戰(zhàn)場(chǎng)中的武力爭(zhēng)勝之外,尚有文化上的“分庭抗禮”。由于處境相似,所述或者更近于歷史真實(shí)。
[i] 《劍橋中國遼金西夏元史》特意指出“澶淵之盟”中受到信任的遼國使臣王繼忠不但是被俘的宋朝官員,而且是宋真宗密友,可能私下溝通雙方意愿。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8年出版,121頁。
[ii]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六三。
[iii] 司馬光《涑水紀(jì)聞》卷第十一。又言“周革曰:景德中,中國自為誓書以授虜,虜繼之以四言曰:‘孤雖不才,敢遵誓約;有渝此盟,神明殛之。’慶歷中,增歲給二十萬,更作誓書亦如之。嘉祐初,樞密院求誓書不獲,又求寧化軍疆境文字,亦不獲。於是韓稚圭曰:‘樞密院國家戎事之要,今文書散落如此,不可。’乃命大理寺丞周革編輯之,數(shù)年而畢,成千余卷。得杜衍祁公手錄誓書一本於廢書,其正本不復(fù)見。”(205頁)
[iv]《宋稗類鈔·鑒識(shí)》,上冊(cè)218頁。詳情可參岳珂《桯史》卷第九“燕山先見”條記載宣和約金滅遼時(shí)宇文虛中之長篇諫言(101-104頁)。
[v] 參拙文《“關(guān)帝斬蚩尤”考――道教與宋代關(guān)羽崇拜》第三、四節(jié)。載香港《嶺南學(xué)報(bào)》新三期(2001年12月出版)。
[vi] 參《長編》卷六七。
[vii] 《宋史·王旦傳》。
[viii] 《涑水紀(jì)聞》卷第六,120頁。
[ix] 《景德傳燈錄》卷二七《天臺(tái)智顗》曾述助其修建天臺(tái)國清寺者,即為“皂幘絳衣”之三神人。《大宋宣和遺事》元集敘關(guān)羽神像現(xiàn)身,亦言“絳衣金甲”。可知“神著絳衣”之說貫穿于宋。
[x] 清人畢沅《續(xù)資治通鑒》中“恒”作“昚”。按趙昚為宋孝宗(公元1127-1194年)之名。他為宋太祖七世孫,秦王德芳之後。初名伯琮,後改名瑋,賜名無,字元永。受高宗趙構(gòu)內(nèi)禪而繼位,在位27年。由太宗後改為太祖後承統(tǒng),為兩宋宮闈“斧聲燭影”以來之大事件。可知後世記述已將“天書”之說改為讖言。所謂“世(傳)七百(年),九九(八十一代)定”的預(yù)言,無非極言宋之“世祚延永”,亦道家夸誕之慣技。
[xi] 《涑水紀(jì)聞》卷第七已言“欽若為人陰險(xiǎn)多詐,善以巧詘中人,人莫之悟。”(134頁)真宗瘋癲事參卷五“嘉祐違豫”條。(95—98頁)《宋史·王曾傳》言,宋仁宗曾說“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奸邪也!”王曾答稱:“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shí)謂之‘五鬼’。奸邪險(xiǎn)偽,誠如圣諭。”
[xii] 《佛祖統(tǒng)紀(jì)》卷四五。
[xiii] 《長編》卷六五。《佛祖統(tǒng)記》卷五一“圣君護(hù)法”條又言:“真宗侍讀孫奭請(qǐng)損修寺度僧。上曰:釋道二門有助世教。安可即廢?”如果屬實(shí),趙恒雖然心向道教,但也不愿作出極端排佛的事情來。孫奭則兼反二教,倒是儒生本色。
[xiv] 《長編》卷六六。
[xv] 此節(jié)轉(zhuǎn)引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二卷第七節(jié),558-559頁。
[xvi] 《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七,583頁。趙翼曾歷數(shù)遼、金兩代纂續(xù)遼史的經(jīng)過。又近年在云南施甸縣木瓜榔村村民蔣文良家中,發(fā)現(xiàn)了明代契丹後裔繪制的《施甸長官司族譜》,開篇“青牛白馬傳說圖”後附有歌謠說:“遼之先祖始炎帝,審吉契丹大遼皇。白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駕女來。一先先祖木葉山,八部後代徙潢河。南征欽授位金馬,北戰(zhàn)皇封六朝臣“云云。(葉啟曉、干志耿《滇西契丹遺人與耶律倍之裔》,《北方文物》1995年第4期)與遼史記載符合,已和西南少數(shù)民族一樣自稱炎帝之後,但仍然保持著契丹始祖?zhèn)髡f的面目。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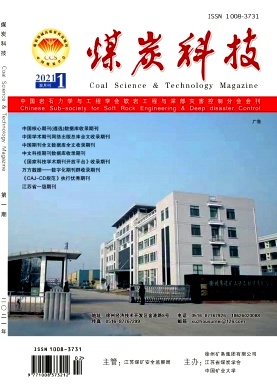
業(yè)工程技術(shù).jpg)
代法學(xué).jpg)
.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