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芬蘭IHME藝術(shù)節(jié)當(dāng)代藝術(shù)的樂與路
殷紫
赫爾辛基港口,波羅的海的氣息撲面而來。這里是整個城市最熱鬧的地盤,聚集了為北歐風(fēng)光慕名而來的游客和步履匆匆的當(dāng)?shù)厝恕K麄儺?dāng)中稍有閑情的,會停下腳步看一眼港口旁不知何時架起來的大銀幕。銀幕上放的,正是背后的斯道拉恩索(Stora Enso)大樓的影像,好像一模一樣,又好像不太一樣。倘若是天天路過的上班族,可能會在某天下班時,突然發(fā)現(xiàn)銀幕上的大樓開裂了,玻璃都碎了。震驚之余趕快再看那真的樓,便松一口氣,這不好好的嘛!
顯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搞清楚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兒,他們不知道這大銀幕上放的是赫爾辛基,應(yīng)該也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長的一部電影《永恒的現(xiàn)代時光》,它歷時整10天,由丹麥藝術(shù)組合Superflex制作。它也為一年一度的IHME當(dāng)代藝術(shù)節(jié)也拉開了序幕。
赫爾辛基的KIASMA當(dāng)代美術(shù)館是北歐地區(qū)頗有影響的機構(gòu),展覽向來具有國際水準(zhǔn)。古根海姆美術(shù)館也有了進駐赫爾辛基的計劃,芬蘭各界反應(yīng)都算良好,認(rèn)為這有利于提升民眾對當(dāng)代藝術(shù)的關(guān)注程度。事實上,作為一個北歐小國,芬蘭當(dāng)代藝術(shù)相當(dāng)活躍,除了民間資金,政府和官方都在不同程度上給予公開的支持和鼓勵。比如最近在KIASMA舉辦的非洲當(dāng)代藝術(shù)大展就獲得了芬蘭總統(tǒng)哈羅能的鼎力相助,她不僅作為贊助人出現(xiàn)在展覽圖冊上,更在開幕當(dāng)天親自捧場,和一大堆藝術(shù)愛好者們擠來擠去,樂此不疲。
但在芬蘭當(dāng)代藝術(shù)界的有識之士看來,芬蘭民眾對當(dāng)代藝術(shù)的認(rèn)知度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有相當(dāng)一部分民眾在對當(dāng)代藝術(shù)并不了解的基礎(chǔ)上心存偏見,也不愿意花心思搞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兒。在《永恒的現(xiàn)代時光》放映現(xiàn)場,雖然也有一些人會向IHME藝術(shù)節(jié)工作人員詢問詳情,但畢竟是少數(shù)。
自2007年創(chuàng)辦的IHME藝術(shù)節(jié)由Pro Arte基金會組辦,這是一個由芬蘭藝術(shù)界的精英智囊團們組織的基金會,資金全部來源于民間私人捐助,用于在公共場合舉辦當(dāng)代藝術(shù)活動,讓更多普通民眾參與、討論當(dāng)代藝術(shù),起到藝術(shù)教育之目的。“IHME”,在芬蘭語中原意為“奇跡”,在口語中也有“好奇”、“奇怪”的意思。藝術(shù)節(jié)以此為名,就是想吊起人們的好奇心,跑過來看看這到底是啥玩意兒。
公共空間(Public Space)、社區(qū)(Community)和國際化(Internationalism)是IHME藝術(shù)節(jié)的三個關(guān)鍵詞,所以無論是活動主題,還是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的作品,都以此為參照。英國著名雕塑家安東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就曾在2009年應(yīng)邀參與IHME藝術(shù)節(jié),和赫爾辛基當(dāng)?shù)厝嗽诠珗@里大玩了一把陶土游戲,氣氛相當(dāng)火熱。同時,圍繞藝術(shù)家項目和藝術(shù)界專家、學(xué)者的講座,舉辦一系列放映和討論活動,是藝術(shù)節(jié)的傳統(tǒng)模式。 2010年,著名美國獨立策展人瑪麗·簡·雅各布(Mary Jane Jacob)擔(dān)任IHME講座主講人,和芬蘭當(dāng)代藝術(shù)家共同探討如何參與公共藝術(shù)。
為期3天的IHME日總是放在周末,向公眾免費開放。市中心的舊學(xué)生大樓被充分利用了起來,講座、影像放映、工作坊之類的多種活動,在里面被從早到晚安排得滿滿的。今年的主題城市建筑與規(guī)劃相關(guān),開場大戲就邀請了英國西英格蘭大學(xué)的學(xué)者克萊爾·朵提(Claire Doherty)和Superflex一起討論《永恒的現(xiàn)代時光》。
斯道拉恩索大樓由著名的建筑大師阿爾瓦·阿爾多(Alvar Aalto)于1950年代設(shè)計。這座被戲稱為“方糖”的現(xiàn)代建筑一直頗受爭議,反對者們對其恨之入骨。由于當(dāng)時的政治經(jīng)濟狀況,斯道拉恩索公司能有錢買下海邊黃金地段,無人競爭,所以這座樓也成為了權(quán)力的象征。Superflex選其為載體,當(dāng)然是看中了其背景之隱喻。影片描述了大樓在今后幾千年中的經(jīng)歷,所以Superflex戲稱能在10天里放完幾千年進程,這部電影節(jié)奏算很快了。結(jié)尾不難猜測,但仍具有視覺沖擊力——大樓變成了廢墟,銀幕上永恒的,只有藍(lán)天白云。對于這樣一部肯定不會有人從頭看到尾的“大片”,講座現(xiàn)場的觀眾發(fā)言相當(dāng)活躍。一個女孩略微激動地說自己有天起晚了,路過碼頭時發(fā)現(xiàn)大樓只剩了小半,突然意識到人生之短暫;另一位曾參與大樓內(nèi)部改建工程的建筑師則直言:“為什么電影里除了大樓和藍(lán)天白云,甚至連鳥都沒有?”對此,Superflex強調(diào),他們要的就是這樣的效果,突出時間的作用,而非其他外來因素,比如戰(zhàn)爭或自然災(zāi)害等。盡管大樓廢墟不由令人想到戰(zhàn)爭中的建筑,甚至有不少路人面對這大海前的銀幕不可避免地聯(lián)想到剛剛在日本發(fā)生的海嘯和地震。
如果說在碼頭偶爾駐足看電影的過客并非都了解這是一部當(dāng)代藝術(shù)作品,那么一不小心參與Superflex作品《免費商店》的顧客,就更不知所以然了。《免費商店》是Superflex這幾年來在各國實踐的一個作品,通過事先和商店店主協(xié)商并提供資金,不收取顧客的任何費用,直到資金用盡。顧客只有在收銀臺拿到總數(shù)為零的收據(jù)時,才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被免費”了,而根據(jù)Superflex的規(guī)定,收銀員不允許作出任何解釋,更不能道出其中蹊蹺。大多數(shù)顧客的反應(yīng)自然交織著驚喜和疑惑,幾乎沒人會想到自己已然成為當(dāng)代藝術(shù)品的一部分。面對追問,風(fēng)趣的店員會反問:“難道你對此不高興嗎?你還不乘我沒改變主意之前就快點走?”Superflex的作品總是質(zhì)疑并挑戰(zhàn)既定規(guī)則,《免費商店》正是顛覆了人類社會經(jīng)濟體系的基礎(chǔ)——貨幣交易,寄望顧客由突如其來的“被免費”進而引發(fā)思考:消費者是想獲得更多免費的商品?還是對免費的商家做點什么補償?還是感到被侮辱了而有些憤怒?
更有趣的是當(dāng)IHME實施作品時,一些店主以各種有趣的理由拒絕,比如:藝術(shù)家不是芬蘭人;甚至一聽是當(dāng)代藝術(shù)就搖頭;當(dāng)然也有比較傳統(tǒng)的生意人理由:“我們尊重顧客,可不想把他們給搞糊涂了”。這些都算是《免費商店》收獲的意外效應(yīng)。
“消失的城市”和“漂浮的城市”是更具娛樂性的老少咸宜的藝術(shù)活動。“消失的城市”是用餅干和糖果搭建房子,然后吃掉,類似于藝術(shù)家宋冬作品《吃城市》的大眾參與版;“漂浮的城市”則用氫氣球放飛由紙板搭建的城市。兩個活動都讓參與的大人小孩玩得不亦樂乎。吸引觀眾廣泛參與的趣味性正是IHME藝術(shù)節(jié)消解普通民眾對當(dāng)代藝術(shù)的陌生、疑慮,甚至是抗拒態(tài)度的重要途徑,藝術(shù)節(jié)主辦方對當(dāng)代藝術(shù)的執(zhí)著推廣可謂煞費苦心。
除了為藝術(shù)本身,藝術(shù)節(jié)的主辦方和支持者們都認(rèn)為當(dāng)代藝術(shù)是啟發(fā)民智、挑戰(zhàn)既定觀念的有力載體,是民主社會的一部分。有趣的是,一個名叫“真芬蘭人”(True Finns)的黨在今年國會選舉中從一個幾年前沒人關(guān)注的小黨派一躍排名至全國支持率第三,而這個黨正是以其反當(dāng)代藝術(shù)的言論受到各界關(guān)注。他們曾大言不慚地宣稱,政府“應(yīng)該把錢花在芬蘭傳統(tǒng)藝術(shù),而非當(dāng)代藝術(shù)上”。
事實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對此言論感到荒謬,而“真芬蘭人”黨和歐洲各國民粹主義黨派一樣,也是個反移民、反全球化的黨派。可以說像IHME這一類當(dāng)代藝術(shù)推廣機構(gòu)的宗旨,恰恰是和“真芬蘭人”們唱對臺戲。都說藝術(shù)不要泛政治化,但把當(dāng)代藝術(shù)抽離政治語境,也恰恰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北歐國家。相信明年的IHME,因為政治氛圍的微妙變化以及全球經(jīng)濟局勢的莫測,或會變得更有看頭。
學(xué).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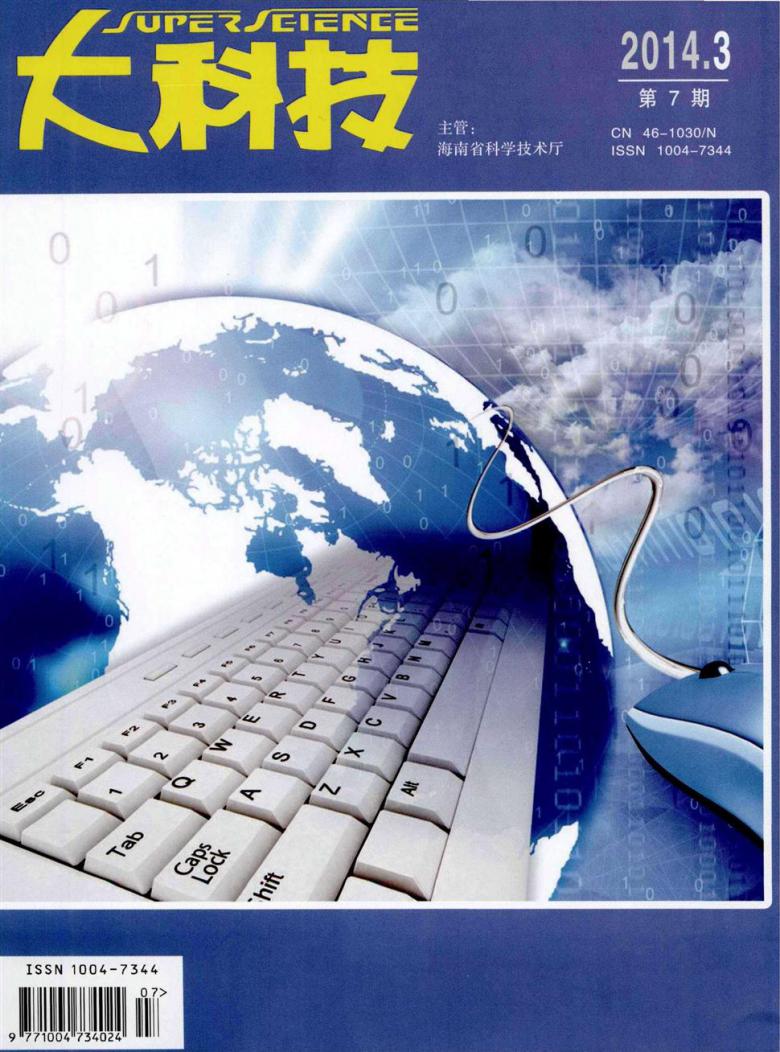
疾病.jpg)
與健康.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