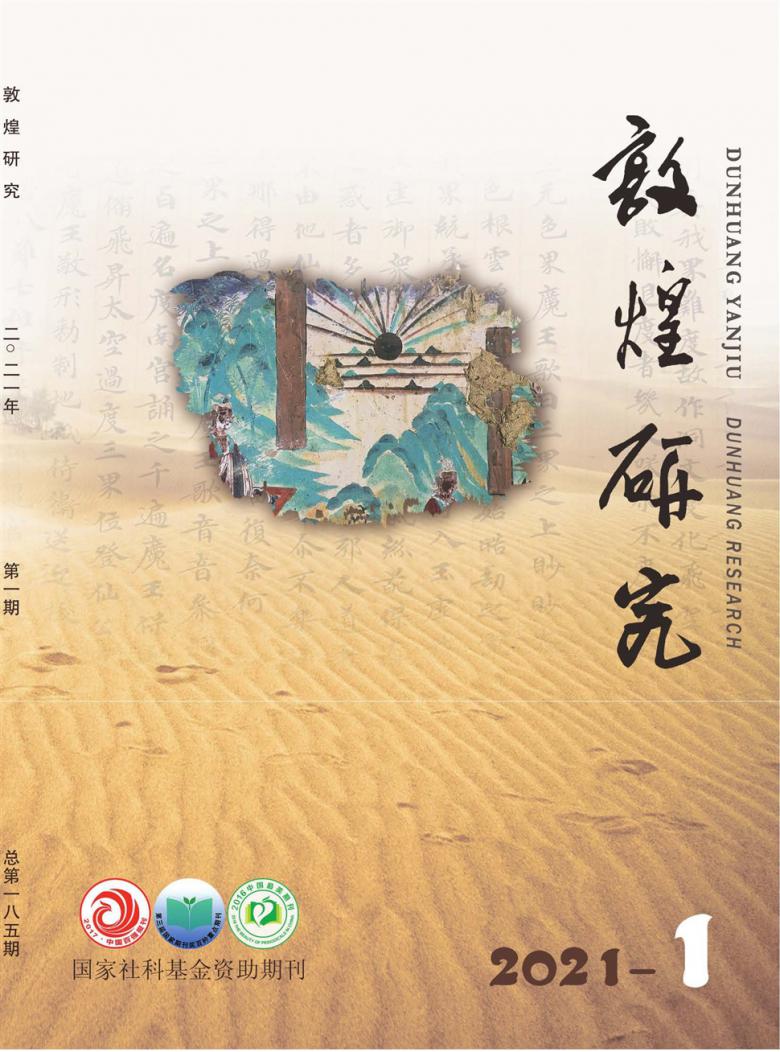正統觀與《三國演義》
劉孝嚴
歷來在對《三國演義》的討論中,“正統觀”問題總是研究者頗感興趣的問題。討論這一問題,不僅要涉及政治和歷史范疇,而且也要涉及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范疇,對考察《三國演義》的思想傾向和藝術創作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
中國的封建社會有二千余年的歷史,朝代興替更迭頻繁,占統治地位的封建集團為了保護本集團的利益并排斥其他封建集團和派別的爭奪,都力圖使自己的統治地位合法化,便制造了種種借口和“理論”,把自己封建集團的政權說成是“天命”特權,依托于上帝天神的意志,使本集團的封建政權的“神圣”與“合法”得以維護。同時,封建統治階級又確定宗法制度的嫡派子孫的繼承權,遞相傳授封建王朝的統治權,不許他人篡奪,以之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防止統治階級內部其他成員對皇位的爭奪,維護一朝一姓嫡派子孫的一統天下。因此,便產生了所謂“正統”之說。梁啟超在《論正統》中說:“言正統者,以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于是乎有統。又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統。統之云者,殆為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謂一為真而余為偽也。”把統治階級所謂“正統”之論的本質說得可謂透徹明白。所謂“統”,是指體系;所謂“正”,是相對于“偽”,即是合法。“統一天下,一系相承謂之正統”,在中國封建時代,“正統”是特指中國古代封建政權延續的合法的政治體系。
《三國演義》以漢末三國晉初的歷史為基礎內容,從題材內容處理和創作藝術構思兩方面看,都需恰當處理漢、蜀、魏、吳、晉幾個封建政權的沿革及相互關系,并對這幾個封建政權加以適當評價,這就必然表現出作者的統系觀和正統觀。
在總體統系格局不違史實的基礎上,在對待各個封建政權的態度上,在情節的具體描寫中,《三國演義》卻表現出不同的傾向。
對漢王朝的封建統治,作者的心態是復雜的。他一方面對漢末政治的腐敗不滿,對桓、靈二帝的昏暗加以暴露,指出漢分三國的“致亂之由”是在于桓、靈二帝。另一方面又對漢室氣運的衰敗流露出由衷的嘆惋。作品描繪了漢末政治腐敗、社會動蕩的圖景:“桓帝禁錮善類,寵信宦官”,“靈帝即位”,“中涓自此愈橫”(1回),而“十常侍”受龐專權,終于導致“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正是奸臣宦官得勢,內閹外戚矛盾激化,忠直之士受到排擠,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終于造成漢室的傾危。這種分析和描寫,應當說是客觀的,對朝政腐敗及奸佞肆虐的暴露也是明顯的。但當漢室政權受到威脅,董卓“懷廢立之意”時,作者便表現出對傾覆漢室的董卓的強烈不滿,斥責董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6回),而對楊尚書等人怒斥董卓則極加稱揚。當漢獻帝回至東都洛陽,時經戰亂,東都已是“宮室燒盡,街市荒蕪。”作者有感于此,哀嘆“漢末氣運之衰,無甚于此。”又引后人之詩嘆曰:“天子懦弱奸邪起,氣色凋零盜賊狂。看到兩京遭難處,鐵人無淚也凄惶。”(14回)這種極具感情色彩的描寫,表現了作者對漢王朝政權衰敗的哀傷嘆惋。
《三國演義》也描寫了漢末的黃巾起義。揭示了起義的原因是“朝政日非”所致。書中還反映了起義迅速發展的形勢。但書中將農民起義者稱為“賊”,而把鎮壓黃巾起義的封建階級人物劉備、關羽、張飛等人物稱揚為“救國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這與作者對漢王室的態度恰成比照,說明作者的立場和感情傾向是維護漢王朝的正統地位的。
《三國演義》的重點是寫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形成及演變過程,寫漢末政治的腐敗、漢室的衰微和黃巾起義的發生,而這些都不過是為曹操、劉備、孫權等封建階級英雄人物的登場做好鋪墊,為寫三國鼎立的形成布置背景。因此,對曹操、劉備、孫權等三國代表人物的描寫及對魏、蜀、吳三國關系的處理,則更可見《三國演義》的統系觀和正統觀。
陳壽在《三國志·武帝紀》中曾對歷史上的曹操的功業才德作了評論,認為:“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鑒申、商之法術,談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囂,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國演義》描寫曹操在討董卓、剿黃巾、除袁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平定統一北方的斗爭中,南征北戰,戎馬生涯幾十年,斗志頑強,氣度恢闊,知人善任,表現了軍事家的才能。官渡之戰,以少勝多,更顯示了他軍事家的膽略。作者曾借郭嘉之口將他與袁紹相比,贊他有“道”、“義”、“治”、“度”、“謀”、“德”、“仁”、“明”、“文”、“武”等“十勝”,分析了他可以戰勝袁紹的條件,對其功業戰績及識士用人等領袖人物素質加以贊美,可以說大體與史評略同,與歷史上曹操大體相符。但對赤壁戰后,當曹操位高權重,挾天子令諸侯,謀魏公魏王,僭越專權時,作者則態度有變,明顯表現出抨擊貶斥的意向,不僅稱之為“國賊”、“反賊”,而且利用情節描寫貶斥他“托名漢相,實為漢賊”,為忠直之士所切齒痛恨。綜觀全書,作者立意是要將曹操描繪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故在描寫他的功業將略之時,斥其僭越專權之為,而對其品德心胸尤多貶黜意向。書中穿插了大量的具體描寫,如殺呂伯奢、夢中殺近侍、割發代首、血洗徐州、許攸問糧、枉殺糧官王辱、哭祭袁紹借刀殺彌衡、妒殺楊修、赤壁賦詩、大宴銅雀臺等,用以突出表現曹操性格的奸詐、偽善、詭譎、狠毒、殘暴的特點,表現他的“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極端自私陰暗的心理,這就使歷史上曹操性格中的“酷虐變詐”(《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傅子》)得以渲染發揮,而成為一個“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78回引《鄴中歌》)的藝術形象的曹操。很明顯,《三國演義》對曹操形象的描寫,與《三國志》對曹操的評價,是同中有異的,在基本史事上相同者多,而具體情節描寫和虛構方面則相異者多,并且明顯地表現出對曹操貶抑憎惡的傾向。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對劉備的評價是:“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托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于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三國演義》描寫劉備是以史評的美贊為基調更為渲染美化。極寫劉備忠于漢室,重于義氣,寬厚愛民,是圣主仁君的代表。全書以蜀漢為描寫的重點,用將近全書三分之二的篇幅描寫劉備集團的霸業。強調劉備乃是“皇叔”、“帝胄”,以“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為己任,為統一大業奮斗不止;贊揚劉備集團的英雄人物間所表現的忠、義、仁、智、信等道德品質。對劉備以帝室之胄的名義發展勢力、奪取政權加以肯定。把劉備集團寫成正統與仁政合一的體現者,作為全書的正面肯定的封建集團,與書中貶抑的曹魏集團相對立。書中第60回寫劉備與龐統對語,說:“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劉備所言不僅是與曹操在道德品質上的不同,更是政治態度與策略上的對立。但是,盡管《三國演義》對劉備及蜀漢倍加偏愛,極力贊美,為之爭取正統地位,而在實際的描寫中卻仍然遵循著史事的約束,三國之中,蜀國始終處境艱難,蜀國劉備、諸葛亮、關羽、張飛等人物也時有失誤;劉備雖口稱忠于漢室,卻自己終于也在漢中稱王,最終又未能擺脫被魏所滅的命運。《三國演義》體現了嚴肅的創作態度,對劉蜀集團的褒美并未改變歷史的基本狀貌。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評論孫權云:“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于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史評對孫權德行政績有褒有貶,《三國演義》對孫權也有褒有貶,但褒貶之中褒多貶少,主要展示了他的英雄性格。在作品描寫的三國關系中,吳國基本上處于陪襯地位,與曹操、劉備相比較,孫權的性格未能充分展開,正面描寫也較少。但他承繼兄業,自擅江表,知人善任,也堪稱三國時“人之杰矣”。孫權在決策聯蜀拒魏時,既審慎又果斷,對取得赤壁之戰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東吳使者趙咨使魏,對魏帝曹丕稱說孫權乃是“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并言:“吳侯納魯肅于凡品,是其聰也;拔品蒙于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江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趙咨所美之詞似有過之,但所敘事跡確為真實。《三國演義》對東吳聯蜀抗魏予以肯定,赤壁之戰尤為明顯;而對制造磨擦、為小利而失大局、破壞與蜀漢聯盟的作法則加以批評。對孫權的游說動搖、目光短淺也有所描寫。
總觀《三國演義》對魏、蜀、吳三個封建集團,對曹操、劉備、孫權三個封建集團的代表人物的描寫,可以看出,在史事基本格局方面是依據歷史、尊重史實的;而在形象刻畫、細節描寫中,則表現出擁劉貶曹的傾向,表現出斥奸頌仁、譽忠責篡的政治態度,這種藝術描寫的傾向是內含著以蜀漢為漢后正統的觀點的。
《三國演義》盡管傾向于蜀漢為漢后的正統,但客觀上還是描寫了魏代漢,晉代魏的政權更迭,而且對漢、魏、晉幾個封建政權的正統論加以描寫,從而使人們得以從更寬闊的視角來考察當時的歷史發展情況。《三國演義》一方面傾向于漢與蜀漢為正統,另一方面也客觀反映了由漢而魏、由魏而晉的政權更替統系,可見作者是重史甚于重統的。
在傾向蜀漢正統時,《三國演義》還注意從不同角度透視其正統論的實質。揭示劉備集團打著維護漢室正統的旗號,實際上不過是借此發展本集團的勢力,以爭取稱雄爭霸的主動。劉備集團的主要謀士諸葛亮深知這一斗爭策略的重要。他一方面更三強調“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為奪取政權,代漢自立制造輿論;另一方面,又經常標榜劉備乃帝胄皇叔,蜀漢當為正統,借以與群雄抗衡,爭取統一天下的合法地位。73回,諸葛亮引法正等人勸說劉備乘時即皇帝位,說:“今曹操專權,百姓無主;主公仁義著于天下,今已撫有兩川之地,可以應天順人,即皇帝位,名正言順,以討國賊。”劉備則答曰:“劉備雖然漢之宗室,乃臣子也;若為此事,是反漢矣。”諸葛亮于是深入談開內情說:“方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舍死忘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龍附鳳,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義,恐失眾人之望。”劉備仍表示不肯“僭居尊位”,遂暫定為“漢中王”。劉備的不敢稱帝,本質上并非是“忠”于名存實亡的漢王朝,而是感到此時即皇帝位的時機還不成熟;他所謂“僭居尊位”之忌一則為“避嫌”,二則也是心虛。至于諸葛亮所說“應天順人”也是借口,而乘時割據爭雄是真,他從形勢發展角度考慮,力勸劉備即帝位,根本動機是為了在與吳、魏的角逐中爭取主動。果然,當形勢進一步發展,曹丕自立為大魏皇帝,劉備有了即帝位的借口,這時諸葛亮再勸他“繼統以延漢祀”,他便不再拒絕。雖然也作了痛哭終日的表演,但還是借口“畏天明命,又懼高、光之業,將墜于地”等,即皇帝位。(80回)在羅貫中的筆下,蜀漢集團的政治家雖然標榜正統,口稱忠漢,但其實并不是一批忠于有名無實的漢王朝的迂腐的忠臣,而是一批乘時割據的梟雄。他們打著正統的旗號其實不過是斗爭的策略而已,這與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策略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在爭奪政權的斗爭中爭取主動。
二
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的基本方法是“據正史,采小說”(明·高儒《百川書志》),把史家史著的素材與民間傳說野史等素材捏合在一起,而以史實為基礎依據。全書基本史事過程和總體歷史變化格局,均“據實指陳,非屬臆造”。但在題材處理和具體情節、人物描寫中,羅貫中不僅汲取了傳說野史中相關的素材,而且,進行了大膽的藝術虛構,使《三國演義》虛實結合。清代史家章學誠評論《三國演義》的虛實結構,曾有“七分實事,三分虛構”的論斷(《丙辰劄記》),點明了《三國演義》藝術方法的基本特征。這種“七實三虛”的藝術方法,是羅貫中“據正史,采小說”創作《三國演義》最基本的藝術經驗。
與“七實三虛”的藝術方法相聯系,《三國演義》表現的擁劉貶曹的傾向和蜀漢正統的藝術處理,也體現了羅貫中的藝術經驗。
在《三國演義》中,擁劉貶曹的創作傾向與強調漢和蜀漢為正統,兩者是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正統觀主要反映了史家史著的歷史正統觀對《三國演義》的影響,體現《三國演義》創作中羅貫中對三國政權真偽主次的歷史觀點。“擁劉貶曹”的創作傾向,主要受來自民間的傳說和野言稗史的影響,主要反映歷代人民的思想愿望和審美意識,是羅貫中“采小說”的結果。把蜀漢正統與擁劉貶曹結合起來,體現了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的藝術構思的重要特點。
作為創作傾向的“擁劉貶曹”與作為史系評斷的蜀漢正統論在《三國演義》中表現著不同的形態。涉及歷史發展及政權更替、政權相爭,則有正統之爭;展示政治仁暴、人物善惡,則多有“擁劉貶曹”描寫。根本上說,“正統論”主要體現在《三國演義》中政治歷史內容的范圍內;“擁劉貶曹”主要體現在作品的藝術虛構的部分內。“擁劉”,一方面包含著稱揚劉備乃是“帝室之胄”,合當繼漢統的蜀漢正統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稱揚劉備具有雄才大略,重義氣,行仁政,寬厚愛民,具有圣主仁君的品德。蜀漢集團主要人物信義友愛,體現了理想化的封建道德。作品把“擁劉”與正蜀相結合,對蜀劉集團所行仁政加以肯定。而“貶曹”,一方面是斥曹魏挾天子令諸侯,“托名漢相,實為漢賊”,不當繼統: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暴露曹操的狡詐殘忍、虛偽自私,具有奸雄的特征,是酷虐和暴政的代表。作品把“貶曹”與夷其非統相結合,對曹魏所行暴虐僭越加以否定。“擁劉貶曹”不僅是《三國演義》統系觀念的反映,還是對政權性質、政治狀況的一種評價傾向,是對人物功過品德的情感態度。因此,不能把“擁劉貶曹”的創作傾向與蜀漢的正統觀分割開來,但也不能將兩者混同或等同起來。
《三國演義》的創作是將史家史著的寫實筆法與文學家的藝術虛構筆法結合起來,這與史家史著的撰著手法明顯不同,本質上屬于文學創作。因此,《三國演義》中表現的蜀漢正統觀與朱熹《通鑒綱目》等史家史著的蜀漢正統觀也相區別。史著的蜀漢正統觀雖也含有褒貶之意,但主要是史家認定封建蜀漢政權的合法地位,主要依據的是史實。而《三國演義》的蜀漢正統觀,則是與藝術虛構、與擁劉貶曹的創作傾向聯系在一起的,所包含的內容除了政權合法性之外,還有政治狀況的良差、政治道德品質的完善等內容。《三國演義》的正統觀,實際上是羅貫中將元明時期史家史著的蜀漢正統觀念與民間傳說野史中表現的擁劉貶曹的創作傾向相結合,并融入自己的歷史觀點和情感傾向而形成的藝術創作的重要構思,是羅貫中進行《三國演義》創作時處理創作素材,安排蜀、魏、吳三方政治勢力主次格局地位的觀點和方法。因之,《三國演義》中的蜀漢正統論雖與史家史著的蜀漢正統論有密切聯系,但又有明顯的區別,是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