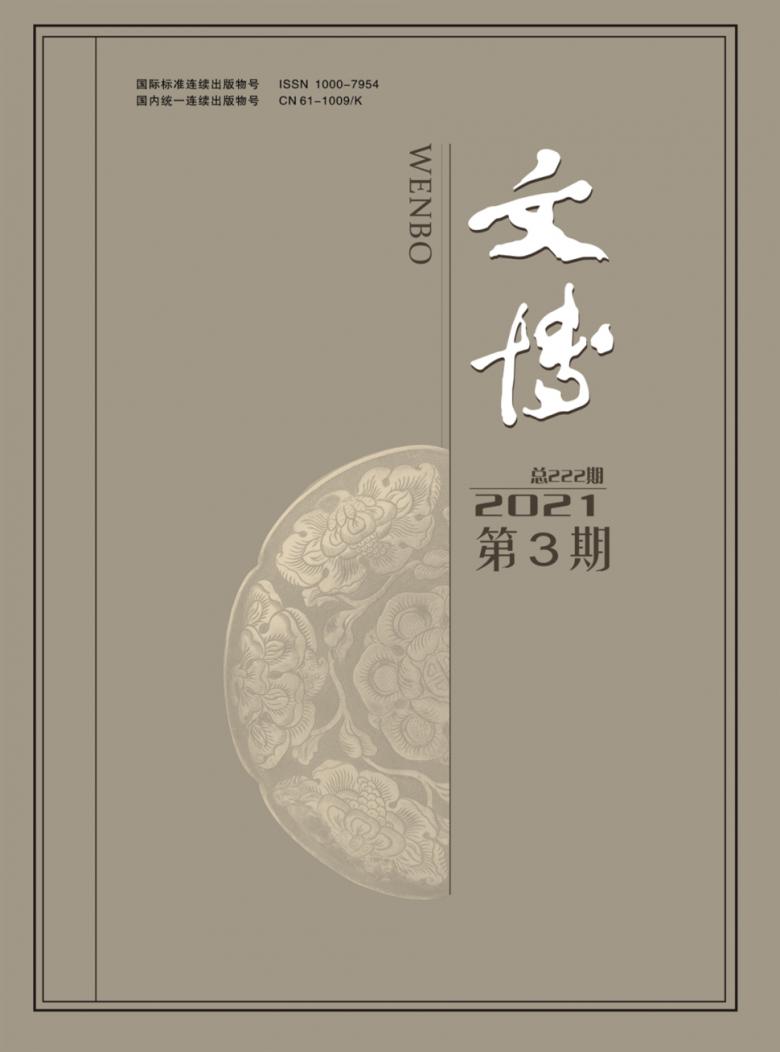明代以來江南農業(yè)的生態(tài)適應性
洪 璞
傳統(tǒng)時代,農業(yè)為其經濟核心,經濟結構的轉變以農業(yè)生產結構的轉變?yōu)榍疤幔晦r業(yè)生產結構的轉變又是農業(yè)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的結果。明代以來,吳江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正是在農業(yè)種植結構由糧食獨重轉變?yōu)榧Z桑并重的前提下發(fā)生的;種植結構的轉變也是由包括氣候、土壤、生物等因素在內的農業(yè)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轉變引起的。 明代以來,江南成為全國的經濟重心的格局愈加不可動搖。江南經濟的發(fā)展是包含了商業(yè)、手工業(yè)和農業(yè)在內的綜合發(fā)展,其中農業(yè)又是整個經濟的基礎,因此探討江南農業(yè)發(fā)展水平,有助于我們深刻地理解這一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的內在機制和局限性。以往相關的研究,較多地集中在對反映農業(yè)生產率的一系列指標的分析,以及農業(yè)生產技術的考察。本書試圖從農業(yè)生態(tài)學的角度對這一問題作一個案研究,從而使我們深切地領會歷史時期農業(yè)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核心地位。 一、江南著名的米、絲、綢三市 吳江地處太湖東南,蘇州之南,屬蘇州府所領六縣之一。自明代以來,這一地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包括農業(yè)、手工業(yè)和商業(yè)均有顯著的提高,集中表現(xiàn)為這里出現(xiàn)了為數(shù)不少的江南名鎮(zhèn),并以此為核心形成了自成體系的經濟格局。區(qū)域內的米、絲、綢“三市”名聞江南,聲貫全國。 平望米市形成于明前期,此處“宋元問,兩岸邸肆間列以便行旅;明初居民千百家,百貨貿易如小邑;然自弘治迄今,居民時增,貨物益?zhèn)涠准岸果溣榷啵胰f舸遠近畢集,俗以小楓橋稱之”[1],“蓋蘇州之楓橋為米船聚集之處,而平望亦不相亞”[2]。同里米市,自宋代始漸形成,至清嘉慶十六年(1811)鎮(zhèn)上“米市在沖字、洪字、東*[禾+會]*[禾+即]、*[禾+囗+文]*[禾+廉]四圩,官牙七十二家,商賈四集”[3];民國時期,同里米市與無錫北塘、江都仙女廟、上海南市并稱“江蘇四大米市”。 震澤絲市形成于明代,明成化年問(1464—1487)震澤已有居民三四百家,至明末達二三千家,清初“食貨交易……貿絲糶粟為多”[4]。乾隆年間,震澤絲市“棟宇鱗次,百貨俱集。以貿易為事者,往來無虛日”[5]。鴉片戰(zhàn)爭以后,大量輯里絲及輯里干經由震澤經上海轉口輸出,震澤成為我國近代著名的絲市之一。 盛澤綢市興起于明代中期,此地“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間倍之。以綾綢為業(yè),始稱為市”[6]。至清乾隆年間,“居民百倍于昔,綾綢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賈輦金至者無虛日,每日中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蓋其繁阜誼盛實為邑中諸鎮(zhèn)之第一”[7]。清末,盛澤與蘇州、杭州、湖州并稱為我國四大綢市。 江南著名的米、絲、綢同時出現(xiàn)在吳江,并不是單純的商業(yè)現(xiàn)象,而是這一地區(qū)整體經濟實力的體現(xiàn)。在以農業(yè)為經濟核心的傳統(tǒng)時代,吳江三市的繁盛,更多地反映了這一地區(qū)農業(yè)生產格局的變動。只要我們對三市流通的貨物稍加分析,便不難認識到這一點:平望、同里米市中流通的主要貨物自然是農產品,震澤和盛澤流通的絲和綢雖不屬農業(yè)產品,但是作為絲綢生產原料的蠶繭卻是農產品,因此,繅絲和織綢是以栽桑和養(yǎng)蠶這一農業(yè)生產為前提的。需要指出的是,三市流通的貨物或原料相當一部分來自本地區(qū),這在下文將有具體論述。 因此,可以認為,種植糧食和栽桑養(yǎng)蠶這兩類農業(yè)生產是整個吳江經濟的基礎。由糧食獨重轉而糧食與桑蠶等經濟作物并重,這種農業(yè)生產結構的變化在明代以來的江南地區(qū)是較為普遍的,這對江南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明代以來就江南地區(qū)而言,吳江的經濟發(fā)展是較為突出的,它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也是較為獨特的,因此,從生態(tài)學的角度考察這一區(qū)域內農業(yè)生產結構的轉變,對于我們理解明代以來江南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具有典型的意義。 二、農業(yè)生產的種類和地域分布特征 考察一個地區(qū)農業(yè)的生態(tài)適應性,必須從該地區(qū)農業(yè)生產種類、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及兩者間的相互關系等方面進行。我們先來看一下,明代以來吳江農業(yè)生產的種類和地域分布特征。 明代以來,吳江逐漸形成了以谷物種植和桑蠶植養(yǎng)兩大部類為主體的農業(yè)生產格局。吳江素稱“魚米之鄉(xiāng)”,宋室南渡前,以一年一熟中秈稻為主;南渡后,為了滿足東南地區(qū)不斷增加的人口需要,逐漸增加小麥種植面積,形成了稻麥(或油菜)兩熟的耕作制度;直至民國時期,兩熟制面積雖然逐漸增加,但仍以一熟水稻為主。民國年間的統(tǒng)計,“全縣稻田13000余頃,豐稔之年產米200萬石,除縣內48萬丁口之民食外,實綽有余裕。每年外銷白米在100萬石以上”。由同里運出的白粳,在上海米市特標以“蘇同白”,其銷售量約占當時上海全年食米供應量的十二分之一[8]。 吳江的桑樹種植興盛于明初,“洪武二年詔課民種桑,吳江境內凡18033株,宣德七年至44746株。近代(清乾隆時)絲綿日貴,治蠶利厚,植桑者益多,鄉(xiāng)村問殆無曠土。春夏之交,綠陰彌望,通計一邑無慮數(shù)十萬株云”[9]。植桑和養(yǎng)蠶往往是相互聯(lián)系的兩項農業(yè)生產活動,農家飼蠶極為普遍,全縣桑樹的產葉量“自給不足,每年向吳縣之洞庭山及浙省之烏鎮(zhèn)等處購人桑葉”[10]。 種植糧食和植桑養(yǎng)蠶成為人們從事的兩項主要的生產活動,就連農家娶婦也必須試以育蠶和拔秧,如《盛湖竹枝詞》中唱道:“荊布苗條新嫁娘,花蠶看罷又分秧。落田羞被旁人笑,不敢回頭偷覬郎。”沈云解釋為“農家娶婦必大育蠶,謂之看花蠶,拔秧多婦女,為之名日落田。”[11]農家年成的好壞也是由谷物的豐歉和桑蠶的好壞決定,正如明代莊元臣哀嘆道:“三春谷斷誰遺種,二月桑枯那有絲。”[12]栽桑育蠶和種植谷物在人們心目中是同等重要的生產活動。 吳江農業(yè)生產的部類結構,由單純的糧食獨重向二元的糧食與蠶桑并重轉變的同時,其地域分布結構也在逐漸形成。全縣范圍內,糧食種植與桑蠶檀養(yǎng)有著明顯的地域特征。大體上,沿太湖東南岸的西南境以蠶桑為務。明嘉靖年間“每歲暮春邑人多治蠶,惟塘西為盛。”[13]即太湖以東、運河吳江段塘路以西地區(qū)的蠶事盛于它處。清乾隆年問“桑所在有之,西南境壤接烏程,視蠶事綦重,故植桑尤多,鄉(xiāng)村間殆無曠土。春夏之交,綠陰彌望,別具名品,蓋不下二三十種。”[14]根據(jù)民國二十三年(1934)的調查,該縣“桑地面積以五七二區(qū)為最多”[15]。五七二區(qū)正處縣之西南境。1950年該縣的桑田依然“大部分布于該縣的南岸四個區(qū)——震澤、嚴墓、大廟和壇丘,約占全縣桑田總數(shù)的90%左右。……而這四個區(qū)的養(yǎng)蠶戶,即占總數(shù)的90%左右。”[16]吳江塘路以東的縣之東北境,則種田為多而栽桑育蠶為少。如《平望志》稱“吾鄉(xiāng)伺蠶者少,服田者多。”[17]位于縣境東北角,分屬吳江、昆山二縣的周莊鎮(zhèn)也是“婦女則皆以木棉為紡織,間作刺繡,未有嫻蠶桑者矣”[18]。東部地區(qū)本少有蠶桑的情形,隨著西南地區(qū)蠶桑事業(yè)的興盛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如地處東境的黃溪“溪民在明時多不習蠶桑,國朝乾隆初,凋字圩、梧字圩一帶頗有養(yǎng)蠶者”[19]。盡管如此,植桑育蠶的地域特征還是十分明顯的,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全縣“除震澤一隅外,統(tǒng)計植桑養(yǎng)蠶之戶十無二”[20]。
三、氣溫變遷的影響 吳江農業(yè)種植結構及其地域分布特征是由該地區(qū)的農業(yè)生態(tài)環(huán)境決定的。農業(yè)生產的基本原則是因地制宜,其核心是土地資源的利用和保護,土地資源包括氣候、土壤和生物等環(huán)境因素。 吳江縣位于江蘇省東南隅,東接上海市青浦縣,南鄰浙江省嘉善縣、嘉興市和桐鄉(xiāng)縣,西南靠湖州市郊區(qū),北與本省昆山縣、吳縣交界,西濱太湖,是太湖水網平原的一部分。地理座標是:北緯30°45′736″~31°13′41″,東經120°21′04″~120°53′09″。東西最大距離52.67公里,南北最大距離52.07公里,全縣總面積為1176.68平方公里,另有東太湖水面約85平方公里。全境地勢低平,河道稠密,湖蕩棋布。四季氣候溫和濕潤,雨水充沛,日照充足,無霜期長,壤土質的水稻土分布全境。 吳江氣候,據(jù)縣氣象站觀測資料,1959—1985年,年平均氣溫15.7℃,年平均日照時數(shù)為2086.4小時,全年無霜期為226天,年降水量為1045.7毫米。春夏兩季盛行東南風,秋冬季節(jié)多偏北風,7—9月常受臺風影響。冬季多出現(xiàn)寒潮天氣。 吳江地貌特征為:全縣地勢低平,白東北向西南緩慢傾斜,南北高差2.0米左右,河道稠密,湖蕩星羅棋布,水面積(不包括太湖水面)占全縣總面積的22.70%,屬湖蕩水網平原,又可分為湖蕩平原和濱湖圩田平原兩種類型。縣境絕大部分地區(qū)屬于湖蕩平原,占全縣總面積的83.1%。區(qū)內田面高程(吳淞基面,下同)3.2~4.0米,最高處5.5米,最低處2.2米。湖蕩大多呈圓形或長圓形,一般水深2.0~3.0米,湖岸平齊,岸線圓滑,湖底平坦硬實,風浪、水流對湖岸形態(tài)及漲坍有明顯的作用。全縣水面,千畝以上的湖蕩絕大多數(shù)分布于此。江南運河、頔塘、爛溪等主要河道集中在本區(qū)。區(qū)內土壤,北部黃泥為主,中部以黃泥土、灰底黃泥居多數(shù),雜以白土、小粉土,南岸以青紫泥為主。屬濱湖圩田平原的地區(qū)占全縣總面積的16.9%,主要分布在鄰近太湖的松陵、菀平、橫扇、廟港、七都等鄉(xiāng)鎮(zhèn)。區(qū)內田面高程2.2—3.5米。河道密且向太湖呈網格狀分布。區(qū)內土壤以小粉土為主,粉沙含量高。 首先,從氣溫環(huán)境分析,由于地理緯度跨度不大,全縣南北兩端溫差不會很大。但是歷史上的氣候變遷,可能是形成桑樹種植縣域分布特征的一個因素。 自唐代起,太湖地區(qū)就盛行柑橘類果樹的栽培,并一直延續(xù)到明初。明初“湖中諸山大概皆以橘柚為產,多或至千樹,貧家亦無不種。”[21]弘治元年(1488)“三十年來,吳江盛植之(柑橘),不減洞庭。”[22]柑橘為喜溫類樹木,然而,自14世紀開始中國氣候逐漸轉冷。元天歷二年(1329)“冬大雨雪,太湖冰厚數(shù)尺,人履冰如平地,洞庭柑橘悉凍死。”[23]15世紀以后,氣候加劇轉寒。據(jù)國外有關研究表明,1500—1900年是世界性氣候寒冷期,即所謂小冰期。就中國而言,也是5000年來四個低溫時期中持續(xù)時間最長、氣溫最低的時期[24]。據(jù)清代杭州、蘇州、南京等地晴雨降雪記錄和物候資料,長江下游在18世紀20—70年代,冬季平均溫度比現(xiàn)代低1℃—1.5℃,冬季降雪日數(shù)比現(xiàn)代多10%—15%[25]。整個明清時期,包括吳江在內的太湖地區(qū),不斷遭受凍害,平均二十年左右就要遭受一次較為嚴重的凍害(詳見表1—1)。柑橘類果樹畏霜雪,氣候轉寒使其無法適應而大量凍死,“景泰四年冬大雪積五尺余,明年正月太湖冰厚二尺,諸山橘十稿七八;弘治十四年至十六年(1501—1503),連歲大雪,山之橘盡斃,惟橙獨存,難成易壞,物之珍者固然邪。于是山人多不肯復種橘,而衢州江西之橘盛行于吳下矣。其亦氣數(shù)之一變乎!”[26]可見,氣候的轉變使得太湖地區(qū)已不適合于大量地栽種柑橘類經濟果樹了。然而,柑橘經濟價值極高,“凡栽橘,可一樹者直千錢,或二三千,甚至萬錢”[27]。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在不得已放棄柑橘類樹木種植的情況下,農戶很自然地會去尋找其它能適應變化了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樹木,于是,他們選擇了桑樹。桑樹對低溫具有較強的抵抗能力,因此,相對而言,栽桑較之種橘,無凍害之虞。
低溫對桑樹的為害主要有霜害和凍害兩種:
冬季的第一次霜稱早霜,春天的最后一次霜稱晚霜。在晚秋桑樹尚處于生長時期,如遇早霜,枝條梢端的葉片會受霜凍而焦枯。在一般情況下,早霜為害不明顯。春季桑芽萌發(fā)后,如遇晚霜,新的芽葉會因霜凍而受害,輕則局部變色,重則幼嫩芽葉全部枯死。晚霜為害較重,往往造成春葉減產,打亂春蠶生產計劃。根據(jù)吳江縣現(xiàn)在的氣候狀況,我們可以推測,該地桑樹一般不會遭受晚霜之害。我們知道,寒冬過后,當土溫和氣溫上升到5℃以上時,根的吸水作用開始;到達10℃并持續(xù)幾天后,樹體內開始變化,貯藏物質開始溶解,可用作生命活動的能源,冬芽開始萌發(fā)。根據(jù)1959—1985年吳江氣象站記錄,氣溫為10℃的初日為4月1日;4月份氣溫回升較快,多數(shù)年份到清明可斷霜,即4月4日左右可斷霜。前文說過,本書考察的歷史時期,該地的氣溫較現(xiàn)代低1—1.5℃,即10℃初日要比現(xiàn)在遲幾天。因此,桑樹冬芽萌發(fā)之際正值晚霜之后。
桑樹受凍害的氣溫為0℃以下。桑葉組織細胞的結冰點為-2—-5.9℃,相當于百葉箱氣溫4— -3℃,尤以0—1℃最易結冰。當氣溫低于-5.9℃時,幼嫩芽葉立即凍死。但是,桑樹凍害并不是由于細胞內部的結冰,而是由于細胞內部的水分被引至細胞壁外側而結冰,結果細胞高度失水而收縮,細胞間隙變大,原生質由于自體脫水的影響,產生不均勻的細胞收縮,使細胞失去膨壓,細胞膜失去了半透性,原生質凝固,葉片變褐枯死。因此,凍害不單純由氣溫決定,其它的一些因素也制約著凍害的發(fā)生與否。首先,桑樹品種的遺傳性與它抗凍性的強弱有關,北方的桑樹品種有較強的抗凍性,例如山東的魯桑。明代以來,吳江地區(qū)栽種的桑樹品種多為“湖桑”。湖桑是在南宋時期,由北方的魯桑隨著桑樹嫁接技術的南移,在江浙地區(qū)經多年的異地培育而逐漸形成的[28]。宋代以前,江浙地區(qū)多植“荊桑”。“荊桑”即長江中下游荊楚之地固有的桑,一說“荊桑”是以江蘇宜興的“荊溪、荊南山”而得名,還有認為“荊桑”源自湖北省。因此,無論采用“荊桑”來源中的哪一說,由“魯桑”轉接而成的“湖桑”比當?shù)卦械摹扒G桑”均具有更強的抗凍遺傳性。其次,低溫的程度和持續(xù)時間與凍害有關,如果冰凍時間不長,細胞內滲出的水不多,一般不致引起凍害;凍害從梢端開始,隨著嚴寒的持續(xù)延長,自上向下,加長枝條的干枯凍死。再次,桑樹本身的營養(yǎng)發(fā)育狀況,即枝條的成熟程度也與凍害有關,枝條在秋季貪青徒長未充分成熟時,易受凍害;充分成熟的枝條,組織充實,木質化程度強,水分含量高,貯藏養(yǎng)分多,細胞液濃度較高,冰點降低,故抗凍能力強。從樹型高低看,低干桑易受凍害,而高干桑則受害較輕。“扳桑附葉”,即去掉桑樹上的附枝,是夏季桑樹管理上的一項重要工作。這項工作有很多作用,其中一條就是為了疏去枝芽,使養(yǎng)分集中于主要枝條,使其健康發(fā)育并充分成熟,從而增強桑樹的抗凍性。吳江桑園是“下無寸草,上無附枝”[29],桑農甚至在采桑時就考慮到今后的剪枝工作了,“蠶之時其摘也必凈,既凈乃剪焉”[30]。冬季不可避免地有少量的桑枝遭受凍害,則開春后也立即將它們剪去,“初春而修也,去其枝之枯者,干之低小者”[31],不至于影響整個桑樹的生長發(fā)育。因此夏春二季的整枝,都有助于增加桑樹的抗凍性。吳江桑型,也以抗凍性較強的高干桑為主,“其大者長七八尺……,株二三厘,所謂大種桑也”[32]。此外,桑樹的栽培條件也與凍害有關,靠近江河湖泊的桑園,由于水面的夜間溫度比地面高,水面上的暖空氣上升以后,地面上的冷空氣向水面流動,使冷空氣不能積聚。特別在濱水地帶經常有霧籠罩,不易散熱,溫度下降較慢,所以不易受凍害。最初,吳江桑樹絕大部分集中在沿太湖東南岸的濱湖地區(qū),可能也是受到了當時氣溫較低這一因素的影響而形成的。
四、土壤變遷的影響 其次,從土壤環(huán)境分析。氣候條件,在全縣范圍內無甚差異,因此它不可能是造成地區(qū)間農業(yè)結構差異的主要因素。吳江境內,土壤的地區(qū)性特征卻是較為明顯的,這可能是導致其農業(yè)生態(tài)環(huán)境差異性的主要原因。明代以來吳江的地貌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太湖水面西北高于東南,以吳江八坼為最低,因此西水東趨,現(xiàn)在吳江所屬的太湖西岸至平望一帶與太湖同為一體,天水一色,渺無人煙。相傳隋唐時平望一帶“淼然一波,居民鮮少,自南而北,止有塘路鼎分于葭葦之間,天光水色,一望皆平,此平望之所以名也”[33]。宋代,現(xiàn)在吳江縣治所在地還是太湖中的一個沙渚。元末至正六年(1346)“至正石塘”的建成,使情形為之一變,“自塘阻其水勢,塘西遂積土為平陸矣”[34]。其實,淤淀在泥沙沉積和風暴作用交替的影響下,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停止,不過它始終在坍漲不定的過程中累積著并向外延伸著,在初期漲露不明顯,而且坍多漲少,所以成陸較緩。日久湖水終究日淺,于是淤沙漸現(xiàn),而成陸的現(xiàn)象加速,這種情況在明代以后才日益顯著[35]。嘉靖時,吳江已是西距太湖三里許;震澤鎮(zhèn)附近北距太湖十里;吳江南和稍東的南湖和東湖(均在岸西),已淤漲成陸;離吳江三十里的太湖中,也漲出周圍三十里的平沙灘,盛產蒲葦之屬[36]。這些新漲湖灘的墾植,必須由多方面的因素決定,其土壤特征是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認為,新漲灘地以沙土為主,現(xiàn)在對日益墾熟的吳江土壤的調查反證了這一點。 現(xiàn)在的調查結果顯示,吳江土壤以水稻土為主(見表1—2)。但是其土屬的地區(qū)性差異卻是十分明顯的,全縣水稻土的大體分布為北壤、南粘、西粉和中雜四個不同類型區(qū)。東北部黃泥土,主要分布在大運河以東、平望一線以北的同里、北厙、屯村、金家壩、蘆墟、莘塔鄉(xiāng)鎮(zhèn),以及松陵和八坼的東北部。南岸青紫泥土,主要分布于盛澤、震澤一線以南各地,集中在麻溪和爛溪兩岸。西部小粉土,主要分布在松陵、八坼、橫扇、廟港、七都等鄉(xiāng)鎮(zhèn)沿太湖一帶。中部以黃泥土、灰底黃泥土居多,白土、小粉土也有一定的比例,主要分布在八坼以南、運河以西和盛澤、震澤一線以北地區(qū)。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包括小粉土、白土在內的輕壤土約占全縣土壤的25%,它們主要分布在太湖沿岸、運河以西地區(qū)。 不同土屬的土壤對于桑樹生長發(fā)育的影響是不同的,對此我們僅從桑樹與水分關系這一角度略作探討。
水分是桑葉發(fā)育中的極重要的因素,桑樹在一定程度上對土壤中水分的過多或不足,會直接影響桑葉產量的高低。
首先,桑樹需要水,其一生中,葉片含水率約70—80%,枝條58—61%,根54—60%。樹體各部分的水分主要依靠根部從土壤中吸收而來,如果土壤供水不足,便將影響桑樹健康地生長發(fā)育直至干枯死亡。當土壤對桑樹的供水不足時,首先是礦物質的供應受到限制,葉片內進行的光合作用削弱甚至停止,原生質由溶液態(tài)變?yōu)槟虘B(tài),粘性增大,生命活動顯著削弱,失去對高溫的調節(jié)能力,最后導致死亡。從圖1—1中可以看出,正常發(fā)育的桑葉,其含水量對干物重的比約為230—350%,此間光合成速度的下降對于含水量的下降呈迅速遞增的態(tài)勢,當含水率從原來的290%降低到280%時,光合成速度就下降了一半,降至220%時,光合作用就完全停止了,如再降至120—150%,葉片就將因干燥而死。可見在葉片干燥死亡很久以前,水分已成為抑制光合作用的主要因素,光合作用早已停止。
桑葉中的水分是由根部從土壤中吸收而來的,但不是土壤中所有的水分都能被根部吸收利用,可供桑樹利用的水分,僅限于一定的范圍,這一范圍內的含水量,即是桑根分布最多的耕作層保持的有效水。在有效水范圍以上,即土壤可以暫時容蓄的水量,叫做“田問容水量”(也叫土壤持水量),也可為植株所利用,但它很快就流失,所以又叫“過剩水”,它為桑樹生長發(fā)育所能利用的時間不長。在有效水范圍以下,指土壤中還有一部分水量與土壤粒子密切吸著在一起的叫做“吸著水”,桑根對它不能吸收利用,所以又叫“無效水”。如果土壤中的含水量降低到有效與無效水之交,則葉片出現(xiàn)凋萎,如能及時補給水分,生理機能尚可恢復,這叫“暫時萎蔫”,如土壤進一步失水,就會“永久萎蔫”,這時根部就不能吸收水分,葉片脫落,桑樹干枯。
土壤對桑根的供水能力因其土屬的不同而各異。一般來說,桑樹的適當含水量為田問容水量的60—80%,其中砂土為60—70%,壤土為70—80%,粘土為80%。(見圖1—2)因此,就桑根吸水能力而言,與壤土和粘土相比較,砂土的田問容水量要求較低,即桑根更容易從砂土中吸收水分。也就是說,從桑樹對水分的需求來看,土質接近于沙土的小粉土,比屬于重壤質地的黃泥土和粘重質地的青紫泥能更大范圍地適合于栽桑。小粉土較易滿足桑根對土壤的吸水要求,這也是吳江桑樹集中于太湖沿岸地區(qū)的原因之一。
除了土壤的供水能力外,土壤本身的持水量對于滿足桑樹的吸水要求也有著一定的影響。一般情況下,當土壤有效水尚有以上數(shù)值的1/2時,桑根還可以從中吸收到所需的水分,低于1/2時,則即使是沙土也無法滿足桑根的吸水要求;此外,在有效水范圍內,如果經常地保持水量增加,便能大大地提高桑根對土壤中礦物質的吸收而增加光合作用,相反,當有效水處于低限時,光合成量顯著下降。吳江全縣自東北向西南緩慢傾斜,南北高差2.0米左右,這造成了整個西南地區(qū)地勢較為卑濕,即含水量較高。當時人們甚至把地勢卑濕視為栽桑養(yǎng)蠶的惟一原因,“邑中田多窐下,不堪藝麥,凡折色地丁之課及夏秋日用皆惟蠶絲是賴,故視蠶事綦重”[38]。此外,濱臨太湖一帶水源充足,且河道稠密,有所謂“震澤七十二溇港”所構成的水網系統(tǒng),十分有利于灌溉。因此,總體上看,西南地區(qū)土壤的含水量要高于東部地區(qū),即使在土壤有效水低于下限值的情形下,西南地區(qū)也可以方便地通過灌溉來緩解桑根吸水不足的問題。可見,吳江的地勢特征和水資源分布決定了西南地區(qū)比其它地區(qū)更能滿足桑樹對水分的需求。
但是,水分既能對桑樹為利,也能對它為害,通過土壤水分引起樹體受害便是桑樹的澇害。當土壤積水過多時,土壤缺氧,好氣性細菌的活動受阻,桑根的生長和吸收機能受到抑制,影響有機物的分解,使桑樹得不到養(yǎng)分的供應,從而也影響到葉片內光合作用的進行,枝條上的葉片自下而上發(fā)生缺水萎蔫,接著枯黃脫落。水澇持續(xù)為害,桑根死亡,植株枯死。太湖地區(qū)的水澇災害是較為頻繁的,對于桑樹而言,除了通過一些種植制度對它加以克服外(這在下文將談到),土壤對澇害程度的影響也是不同的。與壤質較重的黃泥土和青紫泥相比較,西部小粉土,由于其粉砂粒含量高,在土壤積水過多時,其田問持水量會相對較低;澇害過后,其田間持水量也能較快地得到蒸發(fā),而恢復到正常的狀態(tài)。因此種植于小粉土之上的桑樹,受澇害的程度和害后的恢復,相對來說要輕而快。
五、生物環(huán)境的影響
最后,從生物環(huán)境分析。吳江位于太湖之濱,湖蕩星羅棋布,水面遼闊,尤其是瀕臨太湖的西南地區(qū)湖蕩密布,西部和南岸分別以長漾和麻漾兩大湖蕩為中心分布有眾多的大小湖蕩,頔塘、麻溪和爛溪等主要河道也集中于此。并且,自唐中葉吳江塘岸筑成,其岸西便隨著淤灘的逐漸漲出而發(fā)展成許多溇港。至明代,自北往南在太湖與吳江運河北段和頔塘之間分布有許多縱向的小渠,稱為“溇”或“港”,南岸的溇港尤其密集,其相距僅一二里,北起大浦港,西南至胡溇有72條直通太湖的河道,即所謂“震澤七十二溇港”。西南地區(qū)遼闊的水域面積,為湖蕩和水道養(yǎng)魚提供了十分良好的環(huán)境。唐代內塘養(yǎng)魚興起,主要養(yǎng)殖品種有青、草、鰱、鳙、鯉。明代對青、草、鰱、鳙四大家魚已有較完整的飼養(yǎng)方法,而種桑和養(yǎng)魚卻構成了一個十分良好的生物生態(tài)結構,現(xiàn)代稱之為桑基魚塘系統(tǒng)。食物鏈是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基本結構,通過初級生產、次級生產、加工、分解等完成代謝過程,完成物質在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循環(huán)。桑基魚塘構成了比較典型的水陸交換生產系統(tǒng)(見圖1—3),明代以來吳江西南地區(qū)桑樹的廣泛種植,基本形成了這種多目標的生產體系。
在這個體系中,桑樹通過光合作用生成有機物質(桑葉)。桑葉喂蠶,生產蠶繭和蠶絲(生物工藝的物質轉化)。桑樹的凋落物、桑椹和蠶沙,或者直接返回桑基為桑樹提供養(yǎng)分;或者施撒到魚塘中,能使塘中有機質增加,有利于各種浮游生物、節(jié)肢動物繁殖、生長,為魚類提供了豐富的飼料,經過魚塘內這一食物鏈過程轉化為魚。魚的排泄物及其他未被利用的有機物和底泥,經過底棲生物的消化、分解,取出后可作為混合肥料返回桑基,培養(yǎng)桑樹。這一生產體系無論從經濟上或農業(yè)環(huán)境上都是十分合理的,而明代以來吳江桑樹種植地區(qū)的經濟大體具備了這一內容。他們以蠶沙和河泥為肥料培養(yǎng)桑基,“桑之下……以蠶沙……以溝池之泥田之肥土”[39]。蠶沙是養(yǎng)蠶的副產品,是蠶糞殘桑和干燥材料等的混合物。飼養(yǎng)一張蠶種一般可得新鮮蠶沙五百至六百斤。蠶沙中含有豐富的有機質和氮、磷、鉀等營養(yǎng)元素。一般蠶沙中含氮1.45%,磷0.25%,鉀0.11%。因此,無論是直接將蠶沙返回桑基,還是撒入魚塘都是十分經濟的。河泥為河網地區(qū)桑基常用的泥土肥,歷來受到重視,古人有“桑不興,少河泥”的說法。河泥一般于秋冬季節(jié)鋪施地面,以后結合耕地翻入土中;夏秋季節(jié)施用水河泥,則能起到保墑防旱,提高秋葉產量和質量的作用。1920年“江蘇省立育蠶試驗所關于吳江縣栽桑調查報告”就明確指出:“施肥:河泥,……大都春秋行二回施肥。”[40]河泥不僅能給桑基增加養(yǎng)分以供桑樹吸收,而且還給桑地填回新土,補益一年來雨淋土剝的損失,以及使土壤疏松以抵抗旱澇。因此,同屬太湖南岸的湖州地區(qū)特別強調“罱泥”對桑樹的作用[41],吳江地區(qū)的情形應大體相同。
關于明代以來江南經濟的發(fā)展,中外學者都熱衷于從社會或經濟的角度加以探討,尤其強調人口壓力這一外在的因素,這無疑具有啟發(fā)性。但是,通過本文的探討,我們發(fā)現(xiàn)明代以來吳江農業(yè)結構的轉變,是適應當?shù)剞r業(yè)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變化的結果,而整個經濟結構的變化,正是在農業(yè)結構轉變的基礎上發(fā)生的。從明代盛澤綢市的脫穎而出,到今天盛澤東方絲綢市場的獨領風騷,絲織業(yè)的生產和貿易長達五個世紀的繁榮局面,完全是以明代以來其農業(yè)生產結構的轉變?yōu)橐劳卸纬傻摹_@一點對于我們今天的經濟建設不無啟發(fā),即建立一種適應于當?shù)厣鷳B(tài)環(huán)境的產業(yè)結構,是該地區(qū)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必要保障。
[1] 乾隆《吳江縣志》卷四《鎮(zhèn)市村》。
[2] 范煙橋:《吳江鄉(xiāng)土志》民國六年。
[3] 光緒《同里志》卷八《物產》。
[4] 康熙《吳江縣志》續(xù)編卷一《市鎮(zhèn)》。
[5] 乾隆《震澤縣志》卷一《疆土》。
[6] 乾隆《盛湖志·序》。
[7] 乾隆《吳江縣志》卷四《鎮(zhèn)市村》。
[8] 范煙橋:《吳江鄉(xiāng)土志》民國六年。
[9] 乾隆《吳江縣志》卷五《物產》。
[10] 《吳江縣蠶桑改良區(qū)二十三年工作報告》,江蘇省建設廳:《江蘇建設月刊》第二卷,第三期(蠶業(yè)專號),中華民國二十四年(1935)出版。
[11] 沈云:《盛湖竹枝詞》卷下。
[12] [明]莊元臣:《閔農》,道光《震澤鎮(zhèn)志》卷十三《集詩》。
[13] 嘉靖《吳江縣志》卷十三《風俗》。
[14] 乾隆《震澤縣志》卷四《物產》。
[15] 《吳江縣蠶桑改良區(qū)二十三年工作報告》,江蘇省建設廳:《江蘇建設月刊》第二卷,第三期(蠶業(yè)專號),中華民國二十四年(1935)出版。
[16] 吳江縣農民協(xié)會:《吳江縣蠶桑情況調查》(1950年3月),《江蘇農村調查》,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編,1952年。
[17] 光緒《平望續(xù)志》卷一《風俗》。
[18] 光緒《周莊鎮(zhèn)志》卷四《風俗》。
[19] 道光《黃溪志》卷一《土產》。
[20] 吳江縣檔案,案卷號乙2—2·57。
[21] [明]王鏊:《震澤編》卷三《風俗》。
[22] 弘治元年《吳江縣志》卷六《風俗》。
[23] [康熙]翁澍:《具區(qū)志》卷十四《災異》。
[24] 鄒逸麟:《中國歷史地理概述》第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5] 龔高法等:《18世紀我國長江下游等地區(qū)的氣候》,《地理研究》1983年第2期。
[26] [明]王鏊:《震澤編》卷三《土產·風俗》。
[27] [明]王鏊:《震澤編》卷三《土產·風俗》。
[28] 陳恒力校釋,王達參校、增訂:《補農書校釋》(增訂本)第193頁,農業(yè)出版社1983年版。
[29] [清]《儒林六都志》上卷《土田》。
[30] 乾隆《震澤縣志》卷二十五《生業(yè)》。
[31] 乾隆《震澤縣志》卷二十五《生業(yè)》。
[32] 乾隆《震澤縣志》卷二十五《生業(yè)》。
[33] 道光《平望志》卷首《凡例》。
[34] 乾隆《吳江縣志》卷一《疆土》。
[35] 繆啟愉:《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農業(yè)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頁。
[36] [明]沈*[啓去口加山]:《吳江水考·水道考》。
[37] 1994年《吳江縣志》第133頁。
[38] 乾隆《震澤縣志》卷二十五《生業(yè)》。
[39] 乾隆《震澤縣志》卷二十五《生業(yè)》。
[40] 《江蘇實業(yè)月志》第15期,第57頁,1920年。
[41] 詳見《沈氏農書》之《運田地法》,[清]張履祥輯補,陳恒力校釋,王達參校、增訂:《補農書校釋》上卷,農業(yè)出版社1983年版。




境科技.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