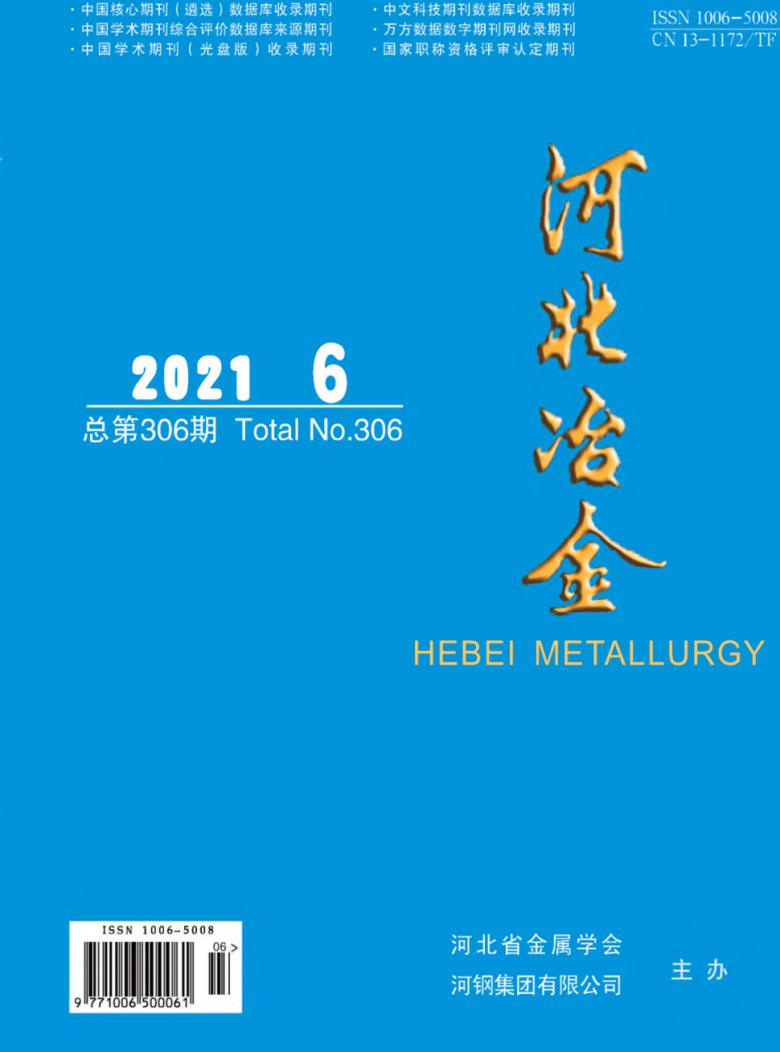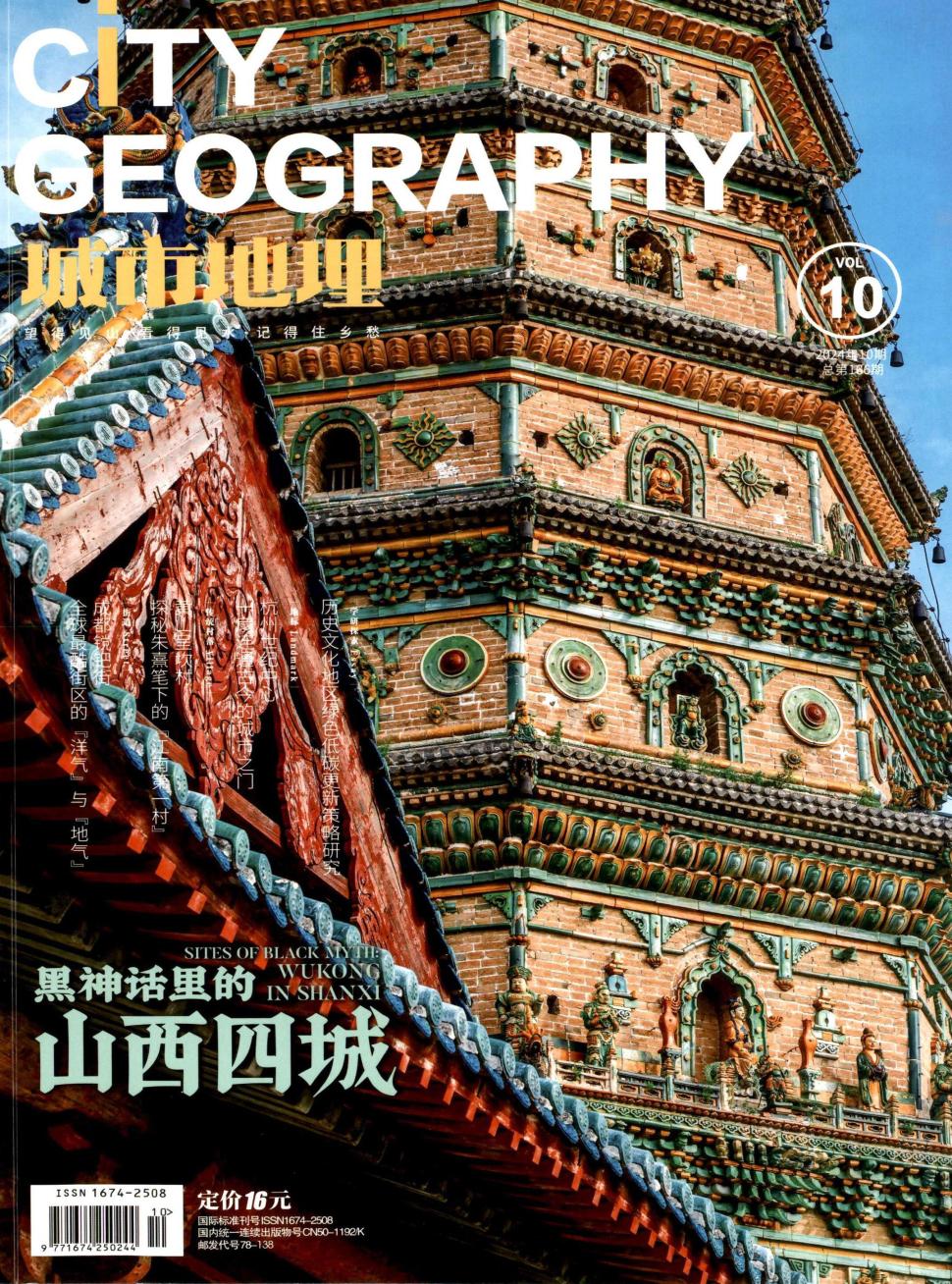明代四川州縣田賦征收考察
李蓁 李映發
本文立足于四川州縣研究,運用省內外地方志史料,采取橫向與縱向比較方法,探討明代農業的發展和田賦征收,從而揭示明代前、中、后三個時期中,四川的平均每畝征糧額僅次于蘇、松二府而位居全國前列。
四川的田賦征收以中央政策為指導原則,且兼具自己特色:平均每畝征糧額高;由于州縣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平原與丘陵、漢區與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不同的田賦征收政策;民田多,官田數較少,因此明中期受土地兼并風潮影響較小,田土和征糧數下降幅度低于全國平均下降幅度;明中期全國出現一系列簡化賦役征收的改革措施,四川也出現“一把連”等征收之法。諸項新變革皆是萬歷年間張居正“一條鞭法”改革的先聲,也是其推行的基礎;四川征收的財賦,起運多為邊倉,有力地鞏固了西南邊疆的穩定,促進了與藏區的茶馬貿易,對發展民族地區經濟具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明代 四川州縣 田賦 考察
中國封建王朝以農立國,其經濟命脈是田賦,故歷朝的賦役征收是學界關注的重要領域之一,多有著述行世。今所見有關著述,多從宏觀表述朝廷的賦役政策,也有微觀者偶及府州縣,但例舉之地也較少涉及四川。四川地方史研究中涉及賦役者均為通史性表述,迄今尚無關于明代四川賦役征收方面的專論。本文試辟蹊徑,從明代四川田賦征收,揭示有明一代的中央與地方的有關政策和比較出四川農業在全國的重要地位。
一、明代四川地方政權與征收田賦
明代府州縣地方政權,知府、知州、知縣總管一府、一州、一縣之政,包括田賦征收。此外,各級政府部門中還有專門負責田賦事務的機構及人員:省下有督糧道,督察財賦征收與轉運,府中由同知、州中由判官、縣中由縣丞和主簿主管田糧、治農及督糧諸事,具體操作諸項事務者,由縣衙中的戶房負責。縣以下實行里甲制,以110戶編為1里,推丁糧多者10戶為里長,其余100戶編為十甲,每甲推一甲首。一里中各戶,由甲首催征錢糧,再由里長匯總,解運官府。從中央到地方,通過這種層層管轄的方式來確保田賦的征收。明初,朱元璋為削弱地方官的經濟大權,還曾在一些地區設糧長制,糧長“專督其鄉賦稅”[1] 。有明一代,四川未曾設過糧長,所謂“蜀中舊不設糧長”[2] ,田賦征收由地方政府、里甲完成。有的縣由鄉社中的約正、約副行使里甲職能,如營山縣:
“國初洪武置邑必有鄉,鄉必有社,……此法一立,則凡賦稅、徭役與夫軍國之務,種種皆備。鄉社耗乏,冊籍無存。至嘉靖己未,奉分守川北道王公喬齡舉行保甲編鄉,義鄉直勇以次統攝。嘉靖丙寅,又奉提學道胡公直舉行鄉約,定約正、約副等名,公之法皆所以推廣。”[3]
此外,四川還設有許多倉,這些倉對田賦征收后的貯存、起運、存留有很大作用,由大使、副大使管理倉中田糧事務。如:
“洪武九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左右布政使:……建昌倉,會川倉,冕山橋倉、鎮西倉、禮州倉、德昌倉、建鹽二打沖河倉、松潘倉、立來化倉、鎮平倉、三舍倉、小河倉、廣備倉、長寧倉、壩底堡倉、大印堡倉、安遠倉、疊溪倉、瀘州倉、永豐倉;成都府:廣豐倉(大使一,副大使一)、廣寧倉(大使一,副大使一);廣安州:豐濟倉(大使);雅州:廣盈倉(大使、副大使);……。”[4]
另外,“州縣則設預備倉……以振兇荒”,[5] 如眉州[6] 、邛州[7] 等地。軍民府、宣慰使司中亦有倉,如烏撒軍民府有烏撒倉。[8] 個別的縣,如江油縣,還設有“驗糧廳”。[9]
明朝的賦役征收,主要以田土和人丁為依據,洪武元年曾推行“均工夫”政策,洪武三年曾推行“戶帖制度”,洪武五年明軍平定四川,洪武十四年在戶帖制度基礎上推行《賦役黃冊》和《魚鱗圖冊》政策。
《賦役黃冊》使十甲編定次序,輪流應役;田賦征收的依據是《魚鱗圖冊》,征收的對象是土地。明初的土地,按所有權性質,可分作國有的官田、屯田和私有民田兩大類。
“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時入官田地。厥后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皇莊,牧馬草場,城土需 苜宿地,牲地,園陵墳地,公占隙地,諸王、公主、勛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莊田,百官職田,邊臣養廉田,軍、民、商屯田,通謂之官田。其余為民田。”[①]① 其籍沒田(抄沒田)和還官田,明朝建立過程中籍沒張士誠、陳友諒等敵對集團中權貴之家的土地和抄沒明初獲罪官民之家的土地,為籍沒田或稱抄沒田;明初大量功臣獲罪,原封賞之田土還官稱為還官田。
民田則是屬于地主和自耕農的私有土地,有祖傳的、有購買的,也有自耕農墾荒所得,“州郡人民,困兵亂逃避他方,田產已歸于有力之家,其耕墾成熟者,聽為己業”。[②]②
不同類別的土地,田賦征額不同。《大明會典》卷十七《戶部四·田土》載,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各州縣田土,必須開豁各戶若干及條段四至,系官田者照依官田則例起科,系民田者照依民田則例征斂”。明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③]③另《大明會典》卷十七《戶部四·田土》增寫:“蘆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畝三合一勺”。但對于蘇、松、嘉、湖地區,明太祖怒其原為張士誠效力,于是將豪族及富民田抄沒為官田,而且皆依被抄沒之前的私租起科。這一作法,造成江南田賦數量激增,形成有名的“江南重賦”現象。
四川的土地種類與其它地區別無二致,但四川的土地由于歷史原因而呈現出自己的特點,即民田居多,官田數量少。“川省田額,以民賦田為最多,屯田地及土司地,均處邊遠,為數極微”。[10] 正德七年(1512年),四川民田88517.83頃,官田1926.89頃,官田只占2.1%;民地1449.46頃,官地196.10頃,官地也僅占1.3%。到正德十三年,四川田土共107869.62頃,官田2134.16頃,占1.98%。[11]
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特點,筆者據《續文獻通考》卷三《田賦考》的記載,列出弘治十五年(1502年)各地官田占田地總數的百分比,如下表:
表一:各行省及蘇、松二府官田占田土總量的百分比
——|官田(頃)|民田(頃)|官田所占比例(%)
全國|598456.92|3629601.97|14.2
浙江|54781.94|417560.78|11.6
四川|2134.12|105735.50|1.98
山東|2892.90|540036.47|0.5
河南|3804.46|402295.22|0.9
山西|11957.91|378851.42|3.1
陜西|6862.95|253799.86|2.6
江西|26870.42|375482.03|6.7
湖廣|185896.23|50232.23|78.7
福建|11290.85|123875.32|8.4
廣東|17961.96|54362.49|24.8
廣西|2841.54|10506.47|21.3
云南|205.56|3425.78|5.7
蘇州府|97786.35|57463.62|63.0
松江府|39856.33|7300.28|84.5
表中顯示,除山東、河南外,四川官田占田土總數的百分比大大低于其它地區。四川官田特點有二:一為數量少;二為官田多集中于成都平原,其它州縣較少。史載成都附近土地“為王府者十七,軍屯十二,民田僅十一而已”。[12] 天啟年間,“成都雖名沃野,而他道之仰給者頗奢……天潢派衍而腴田膏土盡是王莊,貧民或為彼佃戶,收償租庸,此亦無府中之最可閔者。”[13] 這應該與明初朱元璋封其第十一子朱椿為蜀王,建王府于成都,其諸子封郡王,從而造成官田集中于成都平原有關。終有明一代,四川官田一直為數甚微。萬歷六年(1578年),官田2922.35頃,民田131905.32頃,[14] 官田占總數的2.2%,比例雖有增長,但仍然偏低。由于官田少,民田多,因此田賦征收情況能體現出四川農田數與農業生產狀況。
二、明初四川田賦征收及其比較
明朝田賦分夏、秋兩季征收。夏季所征稱夏稅,限當年七月納完;秋季所征稱秋糧,限當年十一月交清。夏稅、秋糧分別以麥、米為主,稱“本色”;麥米之外,農桑絲、綿花絨、絹、絲、苧布、麻布等物隨各地情形征收,稱“折色”。明初也曾以錢、鈔、金、銀等折納田賦,但明前期貨幣田賦所占比重甚少。四川實征米麥的情況,以部分州縣為例。
表二:洪武、永樂時期瀘州地區米麥征收一覽表
州縣|洪武時夏秋米麥(石)|永樂時夏秋米麥(石)|資料來源
瀘州|24433|47992.6|永樂《瀘州志》卷2
江安|3332.8|9458.3|
納溪|405.9|1762.9|
合江|1418|5387.3|
由表二可以看出,瀘州地區永樂時比洪武時的田賦征收總額高得多,這主要歸于明初招民墾荒的政策。如瀘州洪武時有田土2918.63頃,永樂時達到6472.77頃,增加一倍有余,下屬三縣增加的倍率更高。列表如下:
表三:明初瀘州地區田土變化
州縣|洪武時田土(頃)|永樂時田土(頃)|增加率|
瀘州|2918.63|6472.77|122%|
江安|431.41|1321.93|206%|
納溪|49.07|249.05|408%|
合江|170|710.18|318%|
資料來源:永樂《瀘州志》卷2
隨著荒地的不斷開墾,加之有利于民的賦稅征收政策,不僅使地方農業經濟得到恢復與發展,而且保證了國家的賦稅收入,并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其次,考察明初四川部分州縣田賦征收中實征米麥的畝均征額。仍以營山縣、瀘州地區為例:
表四:明初四川部分州縣畝均征糧額一覽表
州縣|年代|夏秋米麥(石)|田地(頃)|畝均征糧(升)|資料來源
營山|洪武24年|1554.1|213.17|7.29|萬歷《營山縣志》卷3
瀘州|洪武時|24433|2918.63|8.37|永樂《瀘州志》卷2
江安|洪武時|3332.8|431.41|7.73|永樂《瀘州志》卷2
納溪|洪武時|405.9|49.07|8.27|永樂《瀘州志》卷2
合江|洪武時|1418|170|8.34|永樂《瀘州志》卷2
營山|永樂中|1570.9|214.44|7.39|萬歷《營山縣志》卷3
瀘州|永樂中|47992.6|6472.77|7.41|永樂《瀘州志》卷2
江安|永樂中|9458.3|1321.93|7.15|永樂《瀘州志》卷2
納溪|永樂中|1762.9|249.05|7.08|永樂《瀘州志》卷2
合江|永樂中|5387.3|710.08|7.59|永樂《瀘州志》卷2
由表四可看出,營山縣永樂時比洪武時畝均征糧數略高一點,而瀘州地區略微降低;瀘州地區田土數、米麥數都有大幅增長,但畝均稅糧基本保持在7—8.4升/畝。
再看蓬州。據正德《蓬州志》卷二《田賦》載,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蓬州官民田地共223頃56畝,其中田(即水田)為179頃35畝,地(即旱地)43頃21畝;夏稅分別為:麥折米126.5石,絲折米358.7石,桑絲折米121.4石;秋糧米969.7石。由此可算出蓬州田的科則為5.4升/畝,地的科則為14升/畝,田地平均科則9.7升/畝,高于營山縣及瀘州地區。
為了說明四川賦額高低,這里選取浙江溫州府樂清縣,山西太原縣,湖北應山縣及河南郾城縣,作一比較。
表五:樂清、太原、應山、郾城田賦征收情況
州縣|時間|田土(頃)|夏稅秋糧(石)|畝均征糧(升)|資料來源
樂清|洪武24年|5475.86|15606.2|2.85|永樂《溫州府樂清縣志》卷3
樂清|永樂10年|6196.08|27510.6|4.44|同上
應山|洪武24年|599.86|5481.6|9.14|嘉靖《應山縣志》卷上
應山|永樂元年|661.53|5521.9|8.35|同上
太原|洪武24年|4830.67|32233.1|6.67|嘉靖《太原縣志》卷1
太原|永樂10年|4787.86|32271|6.74|同上
郾城|洪武24年|1618.14|13167.2|8.14|嘉靖《郾城縣志》卷4
郾城|永樂10年|1618.14|13167.2|8.14|同上
上述數字與表四中四川一州四縣的畝均征糧數相比,浙江樂清,山西太原明顯低于四川;湖北應山,河南郾城與四川持平或略高。總的看來,四川居中偏高。再將四川行省的畝均征糧數與其它行省作一比較,列表如下:
表六:明初全國及各行省、直隸府州平均畝征糧數一覽
十二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田土(頃)|夏稅米麥(石)|秋 糧 米(石)|畝均征糧(升)
全國|8496523.00|4712900|24730450|3.47
浙江|517051.51|85520|2667207|5.32
北平|582499.51|353280|817240|2.01
福建|146259.69|665|977420|6.69
江西|431186.01|79050|2585256|6.18
湖廣|2202175.75|138766|2323670|1.12
廣東|237340.56|5320|1044078|4.42
河南|1449469.82|556059|1642850|1.51
山東|724035 .62|773297|1805620|3.56
廣西|102403.90|1869|492355|4.83
山西|418642.48|707367|2093570|6.69
陜西|315251.75|676986|1236178|6.07
四川|112032.56|325550|741278|9.52
云南|/|18730|58349|/
直隸應天府|72701.25|11260|320616|4.56
松江府|51322.90|107496|1112400|23.77
蘇州府|98506.71|63500|2746990|28.53
資料來源:《續文獻通考》卷三《田賦考》
從各地畝均征糧數的比較可以知道,除蘇、松二府最高,分別達到28.53升/畝,23.77升/畝外,位于第三的便是四川:9.52升/畝,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數(3.47升/畝)。
四川營山縣、瀘州、蓬州的畝均征糧數均高于全國平均數,但營山、瀘州低于四川平均數,蓬州與之持平。這幾地均為川中丘陵地區,其農業狀況位居四川中游,土地不腴不瘠,尚且能達此數,成都平原的情況便不言自明,必定高于9.52升/畝。
浙江、湖北等地均為中國歷代產糧區,其勞動生產率也較高,而四川的畝均征糧數能高于此二處,其原因不外有三:第一,四川自然條件好,土地肥沃,水利發展,尤其成都平原;第二,四川有深厚的農業文明歷史基礎;第三,四川認真貫徹執行了明太祖輕徭薄賦,恢復生產的政策。在明初短短的一段時間里,人丁興旺,洪武以后,四川人口持續穩步增長。經過185年,到萬歷六年(1578年),四川人口增長了114.89%。[15] 人口的迅速增長,使大量土地得以復墾,因之農業經濟迅速發展。
雖然明中央政府所定科則為官田5.3升/畝,民田3.3升/畝,但其制定不是以農業發達地區為依據,而是以絕大多數地區能夠達到的水平為依據,所以科則是可以在“薄賦”原則下有所變動的。對于農業經濟較發達的地區,由于其耕作技術及勞動生產率較高,糧食畝產量可以達到較高水平,因此可在“薄賦”的原則下制定一個高于5.3升/畝、3.3升/畝的科則,四川便是如此,畝均征糧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對國家的貢獻相對其土地額則為較大。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為例,列表如下:
表七:明初四川田土、人口、實征米麥占全國的百分比
——|四 川|全 國|四川占全國的百分比(%)
田土(頃)|112032.56|8507623.68|1.32
人 口|1466778|60545812|2.42
實征米麥(石)|1066828|29442350|3.62
資料來源:《大明會典》卷17、19、24
四川以占全國1.32%的土地,2.42%的人口,交納了3.62%的米麥,正是得力于每畝科則較高,從而對國家的賦稅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三、明中期賦役征收的變化
明初政府恢復小農經濟的努力收到了顯著效果,經濟出現興盛景象。但自英宗始,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劇,導致田賦收入日益減少,國家陷入財政危機之中。《續文獻通考》卷三《田賦》載,世宗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霍韜奉命修《大明會典》,上疏云:
“洪武初年天下田土8496000頃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額4228000頃有奇,失額4268000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賦稅何從出,國計何從足?……若湖廣額田220萬,今存額23萬,失額196萬;河南額田144萬,今存額41萬,失額103萬,失額極多。”
明中期全國土地失額幾近一半,湖廣、河南等行省失額大大超過存額,這種狀況最終導致了“賦入則日損,支費則日加”。[16] 據《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從洪武至隆慶歷朝的夏秋兩稅米麥額呈下降趨勢:洪武時32278983石,永樂時31824023石,正統時26871152石,成化時26469200石,嘉靖時22850535石,隆慶時24074189石,可見降幅較大。
在全國土地兼并風潮影響下,四川亦不能幸免,但四川的土地兼并,就其程度而言,緩和得多,田土數下降幅度低于全國平均下降幅度。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四川田土112032頃,[17] 弘治十五年,田土107869頃,[18] 比洪武時下降約4%;正德七年(1512年)為105131頃,[19] ,比洪武時下降6%。四川土地額下降幅度比之其它行省小得多,筆者以為這主要與四川官田數目極微,豪強地主為數不多有關。四川土地兼并不劇烈,因此田賦收入減少幅度亦低于全國平均減少幅度。如表:
表八:明前期、中期實征米麥數對比(單位:石)
——|洪武26年|弘治15年|萬歷6年|弘治、萬歷時分別減少|
全國|29442350|26792259|26638414|9.0%; 9.5%|
四川|1066828|1026672|1028545|3.8%; 3.6%|
資料來源:《大明會典》卷24《戶部十一·稅糧一》
面對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各地先后試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山東“一串鈴”;嘉、隆間海瑞在浙江、南京應天府;隆、萬間龐尚鵬在浙江、福建等地試行的“一條鞭法”等,四川州縣亦進行了賦役改革。
宣德以來,各地普遍實行永充制,由殷實之家長期擔任。他們在稅糧的征收、儲存、運輸等環節上極盡貪污舞弊之能事。四川雖“舊不設糧長,但歲推殷實戶為總部,倉各一人,催督納取通關號紙,各戶糧數既少,往往派與總部附納,始則索價甚高,終多侵欺不納。有司迫其期會,未免重追或有先行截納,不容小戶附搭,歸而追息,于是總部之名交為上下所惡”。[20] “總部”既不能解決問題,“乃革總部,令里甲自往上倉,則又散無統紀。奸民攬納,糧價虛出,石朱 串通關,官民俱累,害為尤甚。”[21]
為解決奸民攬納的問題,“成化初,巡撫都御史汪公浩將稅糧灑派遠近倉,分令各戶自行上納,革去攢運人夫,如米一石,存留本處若干,廣豐若干,松疊若干,壩底若干,威茂若干,建昌若干,貴州折納銀布若干。以上戶派納遠糧,下戶止于近糧”。[22] 這樣的做法有利亦有弊,利在于“細民稍甦而豪右不便胥動”[23] ,弊在于“以一戶而遍走各倉實為細碎”;[24] 弘治十四年(1501年),革去督糧;正德八年(1513年),“馬公昊乃令松疊糧每一石折色2斗,小民輸銀;本色8斗,坐于大戶輸米。折色解布政司,差官類解,兵備道給散本色。該州縣與兵備道各為半,印字號票紙以驗真偽”。[25] 在此基礎上,嘉靖十二年(1533年),巡撫都御史范嵩會同巡撫貴州都御史劉士元,對部分州縣邊倉糧的征收作了改革,“將重、敘二府原派貴州永寧倉糧每石折布2匹,共銀3錢5分,解貴州布政司支給,畢節、烏撒、赤水、永寧、普定等衛所,官民著為例”。[26]
另外,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巡撫都御史潘鑑允行糧儲事宜,命“各府、州、縣今后起征夏秋稅糧,不必僉點殷實以滋弊端;亦不必令小民自運原倉以啟繁瑣。……如一甲人戶見年正辦里甲,則用六甲人戶收解錢糧;如二甲則用七甲,周而復始,就于本甲下揀選。上戶分解邊倉,中上戶分解起運腹里并祿糧,中次戶坐分本州縣存留。不許冒名頂替包攬”。[27]
而明中期,四川賦役征收改革最著名者,當推“一把連”征派之法。
“嘉靖十四年,按察使劉璋建議一把連征派之法。……將各項事宜通行議擬,成之為目:一曰稅糧,二曰歲支、均徭、里甲、課程、驛傳、年例、雜役、雜用。”[28]
“一把連”征法有許多好處,“既分析詳明輸運,又慮置機密可以杜勢豪趨避之計,亦足以彌里書飛詭之奸,簡而易行,一而易守,真能補舊議之偏,捄全蜀之弊也。”[29] 可以說,此法是總結了前人改革利弊后的一個突破。“一把連”征法施行后,在四川很快普及。據萬歷《營山縣志》卷三《田賦》載:
“十四年按察使劉璋建議一把連征之法,呈允都御史潘鑑行各府、州、縣遵行。本府知府朱良申明條約,云照本府所屬夏稅秋糧,其田地之起科原無輕糧、重糧之分。至官府之征解,方有腹倉、邊倉之異,但以邊糧價重、腹糧價輕,故人戶利于便己,愿納腹糧而不愿納邊糧。里書巧于舞文,腹糧多上戶而邊糧多下戶,輕重失均,苦樂不一。民間買契先已認定輕糧,作弊以欺人者習以為俗,田去而糧存者積而愈多矣。遵照巡撫衙門所行一把連征收之法,誠足以均賦裕民,革除積弊。為此曉諭,仰各遵照后開則例,通融一把連征收,則不論上戶、下戶,俱有腹糧、邊糧,而下民無不均之弊矣”。
此段記載清楚地表明田賦征收中的積弊及改革的目的——均賦裕民。
營山縣“一把連”征收的具體操作辦法是:“每石征存留4斗,起運6斗。起運者邊糧也。并折色荒絲一總,征銀1兩4錢4分3厘3毫8絲5忽。存留者永豐、文林二倉本色米也。起運松潘倉800石,內400石買本色米解倉,400石折色銀880兩,解布政司;起運安化倉200石,內100石買本色米解倉,100石折色銀224兩,解布政司。”[30]
又如洪雅縣。改革前該縣按起運、存留不同項目,分為九倉,納戶也分為九處上繳,不僅往返費時,而且每處都要索取“秤頭耗米”,極不利民。改為“一把連”后,合并項目,糧戶只需在一地一倉即可繳納完畢。嘉靖《洪雅縣志》卷三載:“嘉靖癸巳以前,戶雖糧一、二石者,亦分為九數,甚零星而索秤頭耗米者則數人矣,民安得不病耶!甲午歲巡撫潘公鑑始立一把連法,每糧一斗征銀6分4厘,米2升6合,即糧數逾百,米、銀各輸一倉耳,一倉足更開一倉。至今稱便,蓋不易之法也。”
“一把連”征收法杜絕了里甲制的積弊,嘉靖《洪雅縣志》中議道:“各倉收頭謂之殷實,舊令里長排年呈報,富民遂緣以為奸,賣富差貧,歲開一騙局矣!乃若猾徒則營充焉,侵盜靡所不至,蓋官民俱受其弊也。近以十甲糧戶輪當其害始息云”。[31] “一把連”征法在總結前人經驗教訓中產生,對賦役征收、解運進行了較完善的改革。明中期四川賦役制度改革與江南相呼應,成為萬歷年間“一條鞭法”推行的先聲和基礎。
明代不同時期由于田賦征收政策與作法的不同,加之土地狀況、生產力的變化不同,因而各個時期、各個地區的畝均征糧數經常處于變動中,如表:
表九:明代不同時期全國平均每畝征糧數
時 間|田土(頃)|夏麥秋米(石)|畝均征糧(升)|資料來源
洪武26年|8496523.00|29443350|3.47|《續文獻通考》卷3
弘治15年|6228058.81|26792260|4.30|《大明會典》卷17、24
正德7年|4697233.00|26794024|5.70|《明武宗實錄》卷95
嘉靖21年|4289284.00|22850599|5.33|《明世宗實錄》卷269
萬歷6年|7013976.28|26638414|3.80|《大明會典》卷17、24
表九顯示出,從明初洪武年間到中期嘉靖時,田土數大幅降低,直到萬歷6年才恢復到接近明初的水平;實征米麥數下降幅度不大。一方面田土數大幅減少,一方面實征米麥數減少幅度不大,所以畝均征糧數從明初到中期呈上升趨勢也是可以理解的。而萬歷年間隨著田土總數的回升,則畝均征糧數隨之下降,接近洪武時的指數。明中期盡管實征米麥數的絕對值有所減少,但畝均征糧數上升,勞動人民的負擔比明初更為沉重。
表十:四川明初、中期平均每畝征糧數的變化
時 間|田土(頃)|夏麥秋米(石)|畝均征糧(升)|資料來源
洪武26年|112032.56|1066828|9.52|《續文獻通考》卷3
弘治15年|107869.63|1026672|9.52|《大明會典》卷17、24
正德7年|107869.62|1028124|9.53|正德《四川志》卷8
嘉靖21年|109907.00|720079|6.55|《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第33頁
萬歷6年|134827.67|1028545|7.63|《大明會典》卷17、24
四川在正德七年(1512年)以前都維持著很高的畝均征糧數,嘉靖時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同期全國平均數(5.33升/畝)。在所列的幾個時期中,全國平均每畝征糧數以正德七年為最高,四川亦如是。這里以該年為例,說明四川的農業情況。
該年全國田土有4697233頃,四川有107869.62頃,四川田土占全國的2.3%;全國實征米麥26794024石,四川實征米麥1028124石,四川米麥占全國的3.8%。四川以占2.3%的土地,交納了3.8%的米麥,其百分比數比明初均有增長,由此可得出結論:四川對封建國家的賦稅貢獻是相對大的,其農業生產技術及勞動生產率相對較高。
四川境內不同地區,由于其不同的自然地理條件,因而經濟發展、生產力水平亦不同。反映在田賦征收中,一方面,同一時期,各地畝均征糧數有的高于全國及四川平均數;有的高于全國平均數,低于四川平均數;有的比全國及四川平均數均低。另一方面,同一州、縣在不同時期亦有不同,在某些時期高些,在某些時期低些。以四川部分州縣為例。據萬歷《合州志》載,弘治十五年,合州田池塘2748.36頃,夏秋米麥27927.4石,可算出畝均征糧數為10.2升/畝。大大高于同期全國平均數(4.30升/畝),亦高于四川平均數(9.52升/畝)。萬歷初合州所轄銅梁、定遠二縣田賦征收情況見表:
表十一:萬歷初定遠、銅梁兩縣米麥征收情況
州縣|田土(頃)|夏秋稅糧(石)|畝均征糧(升)
定遠|881.50|8137.6|9.23
銅梁|2427.86|22281.6|9.18
資料來源:萬歷《合州志》卷6《田賦》
萬歷初畝均征糧數雖比弘治時略低,但仍屬偏高。又如營山縣,見下表:
表十二:明中期營山縣米麥征收情況
時 間|田土(頃)|夏秋米麥(石)|畝均征糧(升)|資料來源
成化8年|213.17|1754.7|8.23|萬歷《營山縣志》卷3《田賦》
正德7年|239.23|1754.7|7.33|正德《蓬州志》卷2《田賦》
嘉靖14年|213.17|3055|14.33|萬歷《營山縣志》卷3《田賦》
營山縣在正德七年(1512年)的畝均征糧數高于全國同期平均數(5.70),但低于四川平均數(9.53);到嘉靖十四年(1535年),則大大高于全國及四川平均數。
又如夔州府。夔州位于四川東部地區,土地貧瘠,山高水急,溝壑縱橫,交通不便,屬四川農業經濟較落后地區。據正德《夔州府志》卷四《田賦》列表如下∶
表十三:正德七年夔州府米麥征收情況
州縣|田地(畝)|夏稅(石)|秋糧(石)|合計(石)|畝均征糧(升)
奉節|14394|224.6|1033|1257.6|8.74
云陽|26086|108|1413.7|1527.7|5.86
萬縣|28463|1.9|1806.3|1808.2|6.35
梁山|67867|/|4687.8|4687.8|6.91
開縣|501537|66|2921.8|2987.8|0.60
新寧|41857|20.8|1736.2|1757|4.20
東鄉|20205|13.8|1137.3|1151.1|5.70
達州|42032|122.7|888.8|1011.5|2.41
大昌|6678|18.6|365.1|383.7|5.75
大寧|18914|50.5|1024.1|1074.6|5.68
建始|26440|89.3|1279.6|1368.9|5.18
注:表中缺巫山縣。
表九、十中已分別算出正德七年畝均征糧數全國平均5.70升,四川平均9.53升。以此對照可知,正德七年夔州府各州、縣畝均征糧數未有高于四川平均數者;有低于四川但高于全國平均數者,如奉節、云陽、萬縣、梁山等縣;有與全國平均數不相上下者,如:東鄉、大昌、大寧等縣;有低于全國平均數者,如:開縣、新寧、達州、建始等縣。另外,夔州府之云陽縣在正德七年(1512年)時畝均征糧數為5.86升,到嘉靖十一年(1532年)則上升為9.39升。其它一些邊遠貧困之地在嘉靖時指數亦不低。列表如下:
表十四:嘉靖時云陽、洪雅、馬湖府米麥征收情況
府縣|時 間|田地(畝)|夏秋米麥(石)|畝均征糧(升)|資料來源
云陽|嘉靖11年|22193|2082.9|9.39|嘉靖《云陽縣志》卷上
洪雅|嘉靖中|52613|4829|9.18|嘉靖《洪雅縣志》卷3
馬湖府|嘉靖33年|27508|2809.8|10.21|嘉靖《馬湖府志》卷4
四、 “一條鞭法”的推行與明末“三餉”加派
萬歷初年,張居正當國時,內部民窮財盡,外部邊患不已。張居正針對現實問題,提出了經濟、政治改革的方針。經濟上,清丈土地,調整賦稅,并制定了影響深遠的“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并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于官,故謂之一條鞭。”[32]
其內容主要為:將各項差徭及雜稅的折色部分攤入土地,統一折成銀兩,按糧(田)丁的不同比例攤派,四六開或三七開;田賦大部分亦征收折色銀。“一條鞭法”的精神實質在于化繁為簡,從而減輕農民負擔。
“一條鞭法”推廣之前,四川部分州縣已實行過田糧、徭役折銀。正德七年(1512年),共征秋糧米588891.6石,內折銀米50000石,每石征銀3錢,共銀15000兩;[33] 正德八年,松疊糧每石折色2斗,小民輸銀;[34] 嘉靖十二年(1533年),重慶府、敘州府將原派貴州永寧倉糧每石折布二匹,共銀3錢5分;[35] 嘉靖十四年試行的“一把連”征收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簡化了賦役征收,如營山縣:
“正德間機兵40名,快手80名。嘉靖以來至隆慶五年,有銀、力二差,四里花戶以丁糧多者編為力差,以丁糧少者編為銀差。隆慶六年,內奉都御史嚴公明文將力差亦并征銀召募,每年銀差銀446兩1錢,遇有閏加銀7兩;力差召募工食銀681兩6錢,有閏加工食銀50兩9錢6分,每人丁一丁,錢糧一石,各派銀9錢8分,足夠三年之數。”[36]
從營山縣在嘉、隆時已實行了徭役征銀可知,四川在萬歷時實行“一條鞭法”是有其基礎的,從“一把連”征收法到“一條鞭法”的過渡也是自然的,二者基本精神一致——化繁為簡,減輕人民負擔。
“一條鞭法”原創于嘉靖初年,江浙、福建等地區已有試行,而后推廣向全國。史載,“萬歷十年,新都縣知縣劉文征條陳里甲之害,一條鞭之利,已蒙撫院司道議行矣,尋于十年奉明例通行條鞭之法。輪年里甲悉放歸農,永著為令”。[37] 由此可知,四川遍行“一條鞭法”是在萬歷十年。以部分州縣為例說明“一條鞭法”在四川實行情況。
據萬歷《合州志》卷六《田賦》載:“今夏秋米27929.3石,每年每石征本色米2斗6升,共7315.1石;折色銀5錢8分,共征銀16107兩8錢”。
又如嘉定州,據萬歷《嘉定州志》卷四《賦役》載:
“原額稅糧7745石,原額綿花2627斤。每花1斤征銀7分,共征銀186兩;原額男婦12225口,該征銀220兩零五分;大糧撒數:工部料米470石,每石折色銀5錢,共銀235兩;普安倉:夏秋米1000石,每石折色銀1兩9錢5分,共該銀1950兩;壩州倉:米1400石,每石折色銀1兩2錢,共該銀1697兩6錢;成都廣豐倉:折色米1993石4斗5升,每石折色銀6錢,共該銀1196兩7分;廣濟庫:夏米68石,折荒絲68斤,每斤價銀5錢,共該銀34兩。”
嘉定州在實行一條鞭法之前,已開始折銀,綿花、絲、米、丁口折銀,俱有比價。推行“一條鞭法”之后:
“原額人丁6078丁,內除逃絕單寡朋丁111丁4斗7升,實編5967丁5斗3升。內灶丁877丁,每丁折糧6斗,民丁5090丁5斗3升,每丁折糧5斗。公費銀:795兩;力夫:80名,每名工食銀7兩2錢,共銀576兩,有閏加銀48兩;州馬:40匹,每匹工價銀21兩6錢,共銀864兩,有閏加銀24兩;老灶課銀:685兩6錢,奉文議將600兩于本州秤盤鹽茶二贖抵補外,余85兩6錢,仍于條鞭銀內起征;外小井課銀:580兩2錢9分,……不入條鞭丁糧內起征”。[38] 另有均徭、力差,此處略。可見,嘉定州實行一條鞭法后,簡化了賦役征收。
一方面,每畝實征米麥數減少,勞動人民負擔大為減輕;另一方面,由于清丈土地增加了田畝數,因而盡管畝均征糧數減少,但全省的田賦征收額卻未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增加封建國家的財政收入,此法于國于民皆有利。弘治十五年(1502年)四川田土107869.63頃,夏秋米麥1026672石;[39] 萬歷后期四川田土134827.67頃,夏秋米麥1028545石。[40] 萬歷后期田土、稅糧數比弘治時均有所增加,但畝均征糧數下降。如成都縣,據天啟《成都府志》卷三《田賦》載,成都縣田地113786畝,科糧9920.5石,可算出天啟時成都縣畝均征收8.72升,低于明初、中期的四川平均數,亦可推知低于該縣在明初、中期的畝均征收額更甚。勞動人民的負擔確有所減輕。
自明末至清初,基本遵循“一條鞭法”實行后的田賦征收政策,因此清初的征收也可反映出明末的一些情況。如華陽縣,“自康熙六年奉文清查起至雍正七年征輸止,上田每畝載糧1升3勺4抄,中田每畝載糧8合,下田每畝載糧6合3勺3抄,上地每畝載糧6合,中地每畝載糧4合,下地每畝載糧2合5勺。每糧一石征糧銀1兩1毫,征條銀5錢1分9厘”。[41]
又據嘉慶《直隸綿州志》卷八《田賦》載,綿州“稻田每畝載糧8合3勺3抄,陸地每畝載糧2合5勺。每糧一石征糧銀1兩7錢,征條銀9錢2分”,可知當時田地每畝載糧數大大低于一條鞭法實施前。
明代的田賦,正課之外,常有加派。加派始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即為建造乾清宮,加賦一百萬兩。[42] 明末加征的三種軍費——“三餉”,即遼餉、剿餉、練餉,數額巨大,不僅將“一條鞭法”的改革成果否定,而且給人民帶來沉重負擔,而且驅趕大批勞動力投入戰爭,致使土地荒蕪,經濟衰退,階級矛盾激化,最終導致了農民大起義的爆發。四川亦深受加派的侵擾。崇禎初年,彭縣知縣“以民間未納鞭銀為衙役工食,令自往索之。歲除,索甚急。民皆怨”[43] 。明末四川的階級矛盾也十分尖銳。
五、余 論
四川在宋代便是重要的稻米產區,“南宋時四川負擔川陜駐軍軍糧即達一百五十萬余斛之多,占全國軍糧總數的三分之一”。[44] 經過宋元之際的戰亂,四川社會經濟受到極大破壞,元時“四川省每年收入稅糧為116574石”[45] ,到洪武二十六年,稅糧征收額達到1066828石,為元時的近十倍,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從此,明代四川農業始終穩中有進,其畝均征糧額一直位列全國前茅。通過以上對明代前、中、后三個時期中四川部分州縣田賦征收情況的考察中,可獲得如下幾點認識:
(一)明初,四川貫徹執行中央“輕徭薄賦”政策方面是得力的,取得了良好效果,田野開辟,人口增殖,四川農業開始迅速恢復,農業經濟達到較高水平。
(二)由于農業發展水平較高,尤其是成都平原地區,因此四川的畝均征糧額可以達到較高水平。在整個明代,四川的畝均征糧額均僅低于蘇、松二府而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如表:
表十五:全國、蘇松府及四川行省在不同時期內的畝均征糧額(升)
——|明前期(洪武26年)|明中期(弘治15年)|明后期(萬歷6年)
全 國|3.46|4.30|3.80
蘇 松|26.15|17.68|23.4
四 川|9.52|9.52|7.63
資料來源:《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第346-347頁
(三)四川不同地區的自然地理條件及經濟發展水平迥異,因此對不同地區實行不同的田賦征收政策。川西成都平原畝均征糧額很高,而其它邊遠貧困地區則很低,有的縣甚至低于全國平均數,如夔州府內開縣、達州在正德七年時的畝均征糧數分別為0.6升/畝、2.41升/畝,對于這些地區,統治者征收糧食雖少,但征收的土貢方物就相對多些。
(四)明初較好的賦役制度,至明中期遭到了破壞,國家財政亦因之陷入危機之中。有識之士為確保賦役征收,安定社會,在嘉靖、隆慶和萬歷初試行了一些賦役征收的整頓與變革,如“一串鈴”、“綱銀”、“一條鞭”之類。嘉靖年間,四川也出現“一把連”等征收法。這些措施,均在于簡化征收項目與手續,便利于民。正是這些改良,為萬歷年間張居正“一條鞭法”改革在全國的推行長鳴先聲,鋪墊基礎。“一條鞭法”推行后,四川州縣的田賦征收確有所減輕,折色、征銀都大便于民,便于征收與解運。四川州縣征解實例說明“一條鞭”確為一代良法。清朝恢復此征收,四川亦如此,如華陽縣“每糧一石征糧銀1兩1毫,征條銀5錢1分9厘。原載稅糧1450石,原載人丁2009丁8分4厘,原載丁條糧銀3246兩6錢”[46] 。
(五)明末“三餉”加派,破壞了萬歷初年改革施行的“一條鞭法”,給人民帶來了災難,四川也難于幸免,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終于爆發了明末農民大起義。四川也成為李自成、張獻忠起義的戰場和明朝政府鎮壓人民起義的重災區。
(六)四川作為全國農業發達地區之一,對封建國家的貢獻是相對大的。洪武二十六年,四川以占總數2.42%的人口及1.32%的田土,交納了3.62%的米麥;正德七年,以占2.3%的田土,交納了3.8%的米麥。
明代四川征收的夏稅秋糧乃至布帛絲絹、隨征物品,大多充實邊庫。這就有力地保證了西南邊疆的穩定,對促進與藏區的茶馬貿易也有積極意義。由于在少數民族地區施行了因地制宜的經濟政策和田賦征收政策,有利于這些地區生產力提高和社會進步。
(七)從明朝前、中、后三個時期四川田賦征收政策、方式以及數額的具體情況及其變化中,可以窺見有明一代經濟發展和賦役制度變化的一斑,一斑可窺全豹,明代四川州縣田賦征收是有明一代田賦征收的一個縮影。
四川是一個大省。平原、丘陵、山地,地形復雜,土質有別,水利灌溉條件相異甚大,農業發展水平不一;漢、藏、彝、回、羌民族眾多,內地與邊藏、府州縣與安撫司、宣慰司、招討司所轄地面大有區別,政府的賦役征收也就因之而異,有的差別極大,問題復雜,本文僅以部分州縣為例,難免有不足和缺漏之處。只得容后繼續努力了。
注釋
[1] 《明會要》卷51《民政二》
[2] 萬歷《四川總志》卷21《經略志一·財賦》(二十七卷本)
[3] 萬歷《營山縣志》卷2《鄉社》
[4] 正德《四川志》卷3
[5] 《明史》卷79《食貨三》
[6] 萬歷《四川總志》卷15《郡縣志·公署》(三十四卷本)
[7] 萬歷《四川總志》卷16《郡縣志·公署》(三十四卷本)
[8] 萬歷《四川總志》卷17《郡縣志·公署》(三十四卷本)
[9] 萬歷《四川總志》卷14《郡縣志·公署》(三十四卷本)
[①]① 《明史》卷77《食貨一》
[②]② 《明太祖實錄》卷34
[③]③ 《明史》卷78《食貨二》
[10] 《四川財政匯編》第175頁,第一集上《田賦》
[11] 正德《四川志》卷8《財賦·諸司職掌》
[12] 《明神宗實錄》卷421
[13] 天啟《成都府志》卷4
[14] 萬歷《四川總志》卷21《經略志一·財賦》(二十七卷本)
[15] 《中國人口·四川分冊》第52頁
[16] 《明史》卷78《食貨二》
[17] 《大明會典》卷17《戶部四·田土》
[18] 《大明會典》卷17《戶部四·田土》
[19] 正德《四川志》卷8《財賦》
[20] 萬歷《四川總志》卷21《經略志一·財賦》(二十七卷本)
[21] 萬歷《四川總志》卷19《經略志一·財賦》(三十四卷本)
[22] 萬歷《四川總志》卷21《經略志一·財賦》(二十七卷本)
[23] 萬歷《四川總志》卷21《經略志一·財賦》(二十七卷本)
[24] 萬歷《四川總志》卷21《經略志一·財賦》(二十七卷本)
[25] 萬歷《四川總志》卷21《經略志一·財賦》(二十七卷本)
[26] 萬歷《四川總志》卷19《經略志一·財賦》(三十四卷本)
[27] 萬歷《四川總志》卷19《經略志一·財賦》(三十四卷本)
[28] 萬歷《四川總志》卷21《經略志一·財賦》(二十七卷本)
[29] 萬歷《四川總志》卷19《經略志一·財賦》(三十四卷本)
[30] 萬歷《營山縣志》卷3《田賦》
[31] 嘉靖《洪雅縣志》卷3《食貨志》
[32] 《明史》卷78《食貨二》
[33] 正德《四川志》卷8《財賦》
[34] 萬歷《四川總志》卷21《經略志一·財賦》(二十七卷本)
[35] 萬歷《四川總志》卷21《經略志一·財賦》(二十七卷本)
[36] 萬歷《營山縣志》卷3《編徭》
[37] 萬歷《四川總志》卷21《經略志一·財賦》(二十七卷本)
[38] 萬歷《嘉定州志》卷4《賦役》
[39] 《大明會典》卷24《戶部十一·稅糧》
[40] 雍正《四川通志》卷5《田賦》
[41] 嘉慶《華陽縣志》卷8《田賦》
[42] 《續文獻通考》卷2《田賦考二》
[43] 《四川古代史稿》第五冊,第350頁
[44] 《四川古代史稿》第272頁
[45] 《四川古代史稿》第296頁
[46] 嘉慶《華陽縣志》卷8《田賦》
A study of land tax imposition in local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of Ming dynasty Sichuan
The land tax imposing of Sichuan had its own characters: the average tax of per MU was high; Since the economic imbalance of different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the government took different land tax levy policies; Because there were much more private lands than official lands, Sichuan was not influenced seriously by the land-annex stream of mid-Ming and its fall percentage of the amount of lands and tax was lower than the average fall percentage of the whole country; Reform measures of taxation predigesting taken by Sichuan were forerunners and bases of Single-whip taxation system; Most of the levied fortunes sent out from Sichuan were transited to frontier depots. This strengthened the stabilization of southwest frontier and promoted the exchange of tea and horse between mainland and Tibetan areas.
In this essay, we paid most attention to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of Sichuan, extensively researched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land taxation of Ming dynasty, and the taxation system change of Ming dynasty was revealed clear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