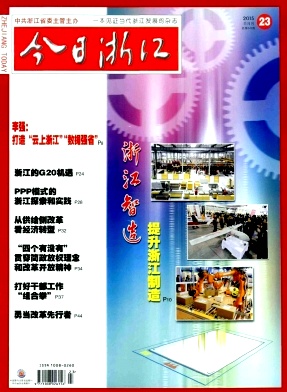明代小說讀者與通俗小說刊刻之關系闡析
程國賦
【內容提要】 小說讀者是通俗小說刊刻與傳播過程中的重要環節,讀者的心理需求與閱讀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小說刊刻的類型、風格、形態等等,這在城市化、商業化、市場化日益顯著的明代小說刊刻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本文主要探討明代不同時期小說讀者主體構成的演變及其對小說通俗化趨勢的影響,闡述明代讀者階層的閱讀行為與通俗小說分欄刊刻、合刊等刊刻形態、讀者心理與通俗小說刊刻之間的內在聯系,由此探尋明代通俗小說刊刻的內在動力與發展規律。
【關鍵詞】 明代 通俗小說 讀者階層 刊刻形態 讀者心理 作為古代小說傳播鏈條上重要的一環,讀者階層與通俗小說創作與刊刻之間的關系相當密切,這在明代書坊所刊小說之中體現得尤為突出,對于以市場、讀者為出版導向的書坊與書坊主而言,讀者階層的喜好、需求直接影響到小說的編撰及刊刻。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在分析小說盛行的原因時指出:“古今著述,小說家特盛;而古今書籍,小說家獨傳,何以故哉?……夫好者彌多,傳者彌眾,傳者日眾則作者日繁。”①由此可見,讀者階層的喜好以及參與傳播推動了小說創作的發展,影響著小說作品數量與藝術水平的提高。明代萬歷時期謝友可介紹《國色天香》在南京刊刻的緣由時也強調讀者的因素:“具劂氏揭其本,懸諸五都之市,日不給應,用是作者鮮臻云集,雕本可屈指計哉!養純吳子惡其雜且亂,乃大搜詞苑得當意,次列如左者,僅僅若干篇,蓋其寡也……是以付之剞劂,名曰《國色天香》,蓋珍之也。”②因為受到讀者與市場的熱烈歡迎,所以金陵書坊萬卷樓聘請江西文人吳敬所在舊本基礎上重新編輯之后刊刻出版,以饗讀者。 關于明代通俗小說讀者階層的文獻資料數量較少,散見于小說序跋、識語、凡例以及相關文集、筆記之中。就明代通俗小說研究的整體來看,學術界關注較多的是小說作家、作品研究,對于小說傳播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讀者階層的研究卻往往忽略。本文試圖討論明代讀者與通俗小說刊刻之間的內在關聯,分析明代不同時期小說讀者主體構成的演變及其對通俗小說創作與刊刻的意義,讀者階層的閱讀行為與小說審美趣味、刊刻形態的關系,讀者心理對小說刊刻的影響。 一、明代不同時期小說讀者主體構成的變化 在論述明代通俗小說興盛原因時,學界一般認為,明代通俗小說多應市民需要而刊,這種說法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是不能一概而論,明代不同時期小說讀者階層的構成主體不盡相同,所以,關于明代小說的讀者階層及其對通俗小說創作與刊刻的影響,我們應針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 美國漢學家何谷理以敘述唐朝李密故事的幾部白話文學為例,闡述明清時期白話文學的讀者階層,他認為,明代圍繞這一題材而創作的雜劇《魏徵改詔》、《四馬投唐》是為準文盲讀者閱讀服務的,明朝中期的長篇歷史敘事作品《隋唐兩朝志傳》(成書于1550年)、《大唐秦王詞話》(成書于1550年左右)等是為中等文化程度讀者閱讀服務的,17世紀出現的兩部文人小說《隋史遺文》、《隋唐演義》是為文化程度很高的社會精英階層閱讀服務的③。換言之,有明一代,小說、戲曲讀者階層的文化層次由低而高,文人群體到明代中后期才加入到小說讀者隊伍之中。何谷理對相關文本的分析比較細致,這一分析對于解讀李密故事的讀者隊伍演變也許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就整個明代小說的讀者狀況而言,筆者認為,他得出的結論頗有值得商榷之處。 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物質材料的豐富,印刷技術的改進,印刷成本的降低,一方面,社會民眾的購買力普遍增強,另一方面,明刊書籍的價格呈下降趨勢,再加上自萬歷中期開始,文人的小說觀念得以改觀,所以,從總體上看,明代通俗小說的讀者階層在不斷擴大,然而不同時期小說讀者階層的構成與差異并非如何谷理所劃分的那樣清楚。我們大約以萬歷中期為界,將明代分為前后兩期,筆者認為,明代前后期通俗小說讀者階層的整體構成并沒有發生很大的改變,上至帝王、貴族、官員,下至普通士子、下層百姓,共同構成小說的讀者階層,不同時期讀者階層的演變主要體現在:其一,與前期相比,后期讀者人數增加,閱讀范圍擴大,讀者階層的主體產生變化,也就是說,不同身份、階層的讀者在明代不同時期小說讀者整體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不同;其二,前后期小說讀者的閱讀形式不太一致。下面,筆者試就明代通俗小說前后兩期讀者主體構成的變化及其特點加以闡述。 第一,在明代前期通俗小說讀者群體中,“農工商販”之類的下層讀者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正如明代葉盛(1420—1474)《水東日記》所云:“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偽為小說雜書……農工商販,鈔寫繪畫,家蓄而人有之。”④嘉靖三十一年清白堂所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的《凡例》聲稱:“大節題目俱依《通鑒綱目》牽過,內諸人文辭理淵難明者,愚則互以野說連之,庶便俗庸易識……句法粗俗,言辭俚野,本以便愚庸觀覽,非敢望于賢君子也耶!”⑤這里說得很清楚,《大宋中興通俗演義》是為“俗庸”而不是為“賢君子”所編的,“以便愚庸觀覽”,因而句法粗俗,言辭俚野。不過,前期的小說價格較高,關于這方面的現存資料很少,明代錢希言《桐薪》卷三記載,武宗正德時期《金統殘唐記》“肆中一部售五十金”⑥,此說恐不可信,然而,我們從明代前期其他書籍的價格可以加以推斷,例如嘉靖時刊本《李商隱詩集》六卷值四兩銀⑦,如此看來,小說刊本也是價格不菲,下層讀者當無力購買,所以他們參與小說傳播的形式主要是以聽說書或以抄寫、租賃等為主,真正購買小說刊本的應該不會很多。 筆者認為,從小說刊本讀者的角度來看,明代前期主要由中上層商人、士子構成讀者主體。先說士人讀者,受小說觀念等多種因素影響,士人階層應該是從萬歷中后期才大量參與到通俗小說的編撰、評點、序跋、刊刻等活動之中,不過,在此之前,輕視通俗小說的觀念并沒有影響他們對小說的閱讀興趣和閱讀行為。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今世人耽嗜《水滸傳》,至縉紳文士亦間有好之者……嘉、隆間一巨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南華經》,右置《水滸傳》各一部。”⑧萬歷十五年金陵萬卷樓所刊《國色天香》卷四《規范執中》篇標題下注釋云:“此系士人立身之要。”卷五《名儒遺范》篇標題下注釋云:“士大夫一日不可無此味。”可見,《國色天香》、《繡谷春容》、《萬錦情林》等雜志型小說選本是書坊為滿足士人群體的閱讀需要而編刊的。書商周曰校在萬歷十九年所刊《三國志通俗演義》的識語中也指出:“此編此傳,士君子撫養心目俱融,自無留難,誠與諸刻大不侔也。”⑨這些都表明,在17世紀之前,士人群體是小說的重要讀者。 再看商人階層。陳大康認為,嘉靖、萬歷朝通俗小說的主要讀者群應該是既有錢、同時文化程度又很不高的商人⑩,筆者基本同意此說,不過值得提出的是,明代前期通俗小說的讀者應以中上層的商人為主,對于小商人而言,一、二兩銀子甚至更高的小說價格也遠遠超出他們的購買能力。 第二,在明代后期的讀者隊伍中,隨著下層讀者的大量介入,市民群體、商人、士子共同構成通俗小說讀者群體,其中,以下層百姓的數量最多,最為引人矚目,當為后期讀者階層的主體。崇禎間王黌《開辟衍繹敘》交代此書編刊原因時認為,對于“開天辟地、三皇五帝、夏、商、周諸代事跡”,“民附相訛傳,寥寥無實,惟看鑒士子,亦只識其大略”,所以編刊此書,“使民不至于互相訛傳矣,故名曰《開辟衍繹》云。”(11)在這里就提到,“士”與“民”均為小說的讀者。 我們根據小說序跋考察明代通俗小說讀者階層的微妙變化。嘉靖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首所附庸愚子序稱:“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12)到萬歷十九年,周曰校在所刊《三國志通俗演義》的識語中,還囑目于“士君子”之類的讀者階層,但是后期的《三國》刊本,如崇禎時夢藏道人《三國志演義序》則兩次提及“愚夫愚婦”、“愚夫婦”:“正欲愚夫愚婦,共曉共暢人與是非之公。”(13)“愚夫婦與是非之公矣。”從小說序跋來看,在萬歷中期以前,雖然也有提及“愚夫愚婦”,如《大宋武穆王演義序》(14),不過,萬歷中期以后的序跋中則頻繁出現這種對下層讀者的稱謂,如,萬歷末林瀚《隋唐志傳序》云:“(編撰《隋唐志傳》)使愚夫愚婦一覽可概見耳。”(15)明末大滌余人《刻忠義水滸傳緣起》云:“以此寫愚夫愚婦之情者。”(16)樂舜日崇禎時撰《皇明中興圣烈傳小言》稱:“使庸夫凡民亦能披閱而識其事。”(17)這些都顯示出明代后期大量下層讀者參與到通俗小說的閱讀與傳播領域。 二、讀者階層與明代小說的通俗化趨勢 作為明代小說讀者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下層讀者的參與對小說創作與刊刻帶來深刻的影響,小說通俗化甚至俚俗化的趨勢就是其中一個重要體現,尤其是明代后期,下層市民群體逐漸成為小說讀者的主體構成,加速了小說通俗化的進程。綠天館主人《古今小說敘》稱:“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說甚富。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畀為一刻。”(18)從其編刊目的來看,注重下層讀者需要,以求“嘉惠里耳”,這種創作目的推動了明代小說創作與刊刻的通俗化趨勢。 從小說刊本的文體形式來看,在某種意義上,按鑒創作、語言通俗的演義體小說就是適應這種需求而產生的。《五雜俎》云:“《三國演義》與《錢唐記》、《宣和遺事》、《楊六郎》等書,俚而無味矣。何者?事太實則近腐,可以悅里巷小兒而不足為士君子道也。”(19)這條資料說明小說擁有不同的讀者階層,同時,也反映了不同階層的讀者具備不同的審美趣味。隨著越來越多下層讀者的加入,他們的閱讀需求和審美趣味必然在通俗小說刊刻中有所體現,這對演義體小說的大量刊印帶來一定的推動作用,正如萬歷時余邵魚《題全像列國志傳引》所言:“抱樸子性敏強學,故繼諸史而作《列國傳》……且又懼齊民不能悉達經傳微辭奧旨,復又改為演義,以便人觀覽。”(20) 從通俗小說刊本的描寫重心來看,也呈現出通俗化的趨勢。以明末“三言”、“二拍”等小說為例,在這些作品中,小商人、不得意的書生等市民群體占據突出的比例,蔣興哥、賣油郎秦重、程宰等,都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小商人形象,小說描摹他們的婚姻、家庭與生活經歷,反映他們的喜怒哀樂。“三言”、“二拍”中也有大量作品描寫讀書人的生活尤其是社會地位、文學修養不高的下層文人的生活。明末所刊話本小說中出現包括小商人、下層文人在內的諸多市民形象并非偶然,小說讀者主體構成由前期的中上層商人、士子而變為下層市民,作者、書坊主應對這種變化,在編刊小說過程中,注重貼近市井生活,適應市民需要,因而帶來小說刊本描寫重心的變化。 從小說刊本的注釋(包括釋義、音注等)來看,也體現出通俗化的趨勢,筆者以歷史小說與公案小說的刊刻為例試加說明。先談歷史小說的刊刻。在明代歷史小說流派興起階段,建陽書坊主熊大木是較早參與創作與刊刻的作家與出版家,嘉靖后期至萬歷年間,他一人創作《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唐書志傳》、《全漢志傳》、《南北宋志傳》等四部小說,分別由清白堂、清江堂、克勤齋與三臺館等書坊刻印。熊氏在小說中,普遍運用注釋的方式,穿插于正文之間,有人名注、地名注、官職名稱注、風俗典故注、音注、詞語注等等,如《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卷一《李綱措置御金人》一節:“遣太宰張邦昌隨御弟康王為質于金營。”原注:“康王者,名構,乃徽宗第九子,韋賢妃所生;為質者,做當頭也。”(21)這是人名注、詞語注。在熊氏注釋中,有些并非疑難字,也加了注釋,比如,《唐書志傳》卷四第三十四節《世民計襲柏壁關唐主竟誅劉文靜》:“爾兄日前飲醉至酣。”原注:“半醉也。”(22)從這里對“飲酒至酣”的注釋可以看出,編刊者顯然是為識字不多的下層讀者閱讀服務的。在其他的歷史小說中,也存在類似的注釋,比如《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卷一《鄭畋大戰朱全忠》:“鄭畋復來搦戰。”原注:“搦音諾。”卷二《安景思牧羊打虎》:“其人趕上,用手撾住虎項。”原注:“撾音查。”(23) 再以明代公案小說的刊刻為例,我們從其音注、釋義等也可以判斷讀者階層,如建陽劉太華明德堂萬歷刻《詳刑公案》為“辜”、“盟”等一些不太難讀的字也加上音注,卷三《趙代巡斷奸殺貞婦》:“事系無辜不究。”原注:“辜音孤。”卷四《蘇縣尹斷指腹負盟》:“(葉)榮帝悔盟。”原注:“音明。”與耕堂萬歷二十二年刊《包龍圖判百家公案》第四回《止狄青家之花妖》有注:“歸寧即謂回家也。”此類注釋顯然也是為識字不多的讀者閱讀服務的,而不是為士子所做的注釋。 由于下層讀者的存在,讀者人數的增加,無論是小說編撰者,還是刊刻者,都自覺考慮到他們的身份特點與文化程度,在小說的題材選擇、文體形式、敘事藝術諸方面,注重適應下層讀者的精神需求和閱讀水平,從而加快了明代坊刊小說通俗化的進程。 三、讀者階層的閱讀行為與通俗小說刊刻形態 作為明代商品經濟發展與城市化的產物,通俗小說刊刻的興盛取決于市場與讀者,小說的刊刻形態也受到讀者階層閱讀行為的影響,對此,筆者從以下兩個方面加以論述: 第一,分欄刊刻。早在元刊平話之中,已經出現分欄刊刻的形式,如建安虞氏所刊平話即為上圖下文。明代書坊刊刻小說,分欄刊刻的形式比較常見,一般分為上、下兩欄。不過,上、下兩欄的內容各不相同,明代中后期金陵、建陽等地刊刻的《國色天香》、《繡谷春容》、《萬錦情林》、《燕居筆記》等雜志體小說,上下欄俱為文字,或收中篇文言小說,或收詩文雜類,正文中間,偶有較小的插圖;約刊于萬歷年間的《小說傳奇合刊》上欄選話本小說《李亞仙》等,下欄為傳奇。這種分兩欄刊刻的形式在明代小說選本中比較普遍。 就刊刻的地區而言,建陽版圖書多為上下兩欄,上圖下文,圖文結合。從通俗小說的刊刻來看,明代采取分兩欄刊刻的形式比較早的當屬金陵周曰校萬卷樓萬歷十五年所刊《國色天香》,此書原有舊本,雖然“雜且亂”,但是深受讀者歡迎:“懸諸五都之市,日不給應。”(24)《國色天香》等雜志體小說之所以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一方面正是因為其內容之“雜”,無所不包,另一方面,《國色天香》的分欄刊刻的形式也是此書受到讀者歡迎的原因之一,這對后來的雜志體小說以及其他通俗小說分欄刊刻帶來一定的影響。 建陽書坊主余象斗在此基礎上創建上、中、下三欄的形式,上評、中圖、下文,如雙峰堂萬歷二十年刻羅貫中編次、余象烏批評《三國志傳》,萬歷二十二年刻題羅貫中編輯《忠義水滸志傳評林》,三臺館萬歷三十四年重刊余邵魚撰《列國志傳評林》,萬歷刻羅貫中《三國志傳評林》,都采取三欄形式。 在分欄刊刻過程中,正文之外所增設的一欄或兩欄多為插圖與評點,顯示出書坊主對插圖與評點的重視。“曲爭尚像,聊以寫場上之色笑,亦坊中射利巧術也”(25),戲曲無圖,便難以得到市場與讀者的歡迎,所以在刊刻中出現“曲爭尚像”的現象。同為敘事文學的小說也是如此,明末所刊《玉茗堂摘評王弇州艷異編》卷首所附無瑕道人識語聲稱:“古今傳奇行于世者,靡不有圖。”評點也是為便于讀者閱讀而出現的,正如余象斗在刊刻其族叔余邵魚的《列國志傳》的識語中所言:“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斷,以便海內君子一覽。”(26)署名李贄的《忠義水滸全書發凡》云:“書尚評點,以能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也。”(27)評點是溝通作者與讀者的橋梁,而搭橋者往往是書坊及書坊主。 第二,合刊。約刊于萬歷之際的《小說傳奇合刊》就是小說、傳奇的合刊本,據《小說傳奇合刊》書末所題“三集下”可知至少還有一、二集。崇禎時期,建陽熊飛雄飛館合刻《三國》、《水滸》,雄飛館主人在《英雄譜》卷首的識語中聲稱: 語有之:“四美具,二難并。”言璧之貴合也。《三國》、《水滸》一傳,智勇忠義,迭出不窮,而兩刻不合,購者恨之。本館上下其駟,判合其圭。回各為圖,括畫家之妙染;圖各為論,搜翰苑之大乘。較讎精工,楮墨致潔。誠耳目之奇玩,軍國之秘寶也。識者珍之!雄飛館主人識。 由此觀之,《英雄譜》合《三國》、《水滸》而為一書,也是考慮到讀者的閱讀行為,“兩刻不合,購者恨之”,于是“本館上下其駟,判合其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