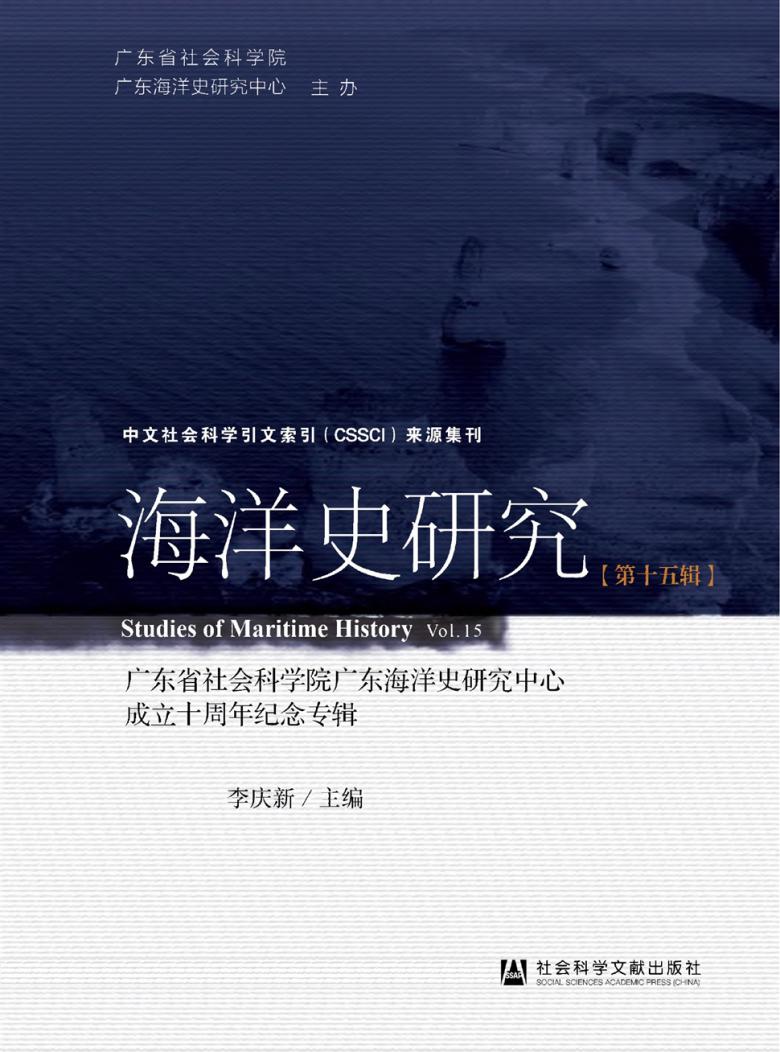陶淵明在宋代被空前接受原因之探究
周遠斌
【內容提要】 陶淵明在宋代被空前接受并非憑空而起,而是由作為享樂性文化氣候之“反動”的淡泊精神、復古革新運動中產生的平民心態及高風絕塵之詩風追求、思想感情上的禪定和老大心態、詩歌審美上推尊蕭散簡遠之趣四個主導因素促成的。
【關鍵詞】 陶淵明;淡泊;平民心態;高風絕塵;禪定;“老大”;瀟散簡遠
宋代前的幾百年中,陶淵明是寂寞的。南北朝時期,劉勰的《文心雕龍》、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論》和蕭子顯的《南齊書·文學傳論》,皆論及以前及當代的重要作家,但都沒有提到陶淵明。鐘嶸在《詩品》中稱他為“隱逸詩人之宗”,但只把他的詩列為中品。北齊陽休之匯錄陶詩,并在《陶集序錄》中稱“頗賞陶文”,但卻認為陶文辭采未優。盡管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以“余素愛其文,恨不同時”、“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跋宕昭彰,獨超眾類”等高評陶淵明,但他卻在《文選》中只錄陶詩八首,而陸機的錄了四十九首,謝靈運的錄了三十九首,張協、左思的也比陶淵明的多錄三首,可見蕭統對陶淵明的“素愛”是打折扣的。到了唐代,王績、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韋應物、柳宗元等都追慕陶之為人及其詩作,但對陶并非全無芥蒂地接受。王維早年時責難陶淵明守小而忘大,杜甫認為“陶潛避俗翁,未必能大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1](P35)白居易認為陶詩“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2](P107)陶在唐的情況正如《蔡寬夫詩話》中所言:“淵明詩,絕無知其奧者。”南北朝、唐朝言及陶者雖有幾十位之多,但這幾十位中可以說無陶之知音可言,可真真寂寞了這一大家。 宋代與南北朝、唐朝對陶的冷淡相反,而空前地喜愛起來,并貫穿宋朝始末。文字上論及陶者僅《陶淵明研究資料匯編》所錄就有八十五家,他們尊陶、贊陶、學陶詩、和陶詩,并多以陶為知音,陶的接受史因此而熱鬧起來。歷史對一過客有時旁置冷落,有時親近非常,乍看是歷史的鬧劇,其實里面有不可更替的歷史原因在左右。
一、文化氣候
一個朝代的政治、經濟和生活原則往往形成一個獨異的文化氣候,而這一文化氣候又會影響置身其中的文人士子的心態。 宋王朝建立不久,宋太祖趙匡胤對軍事重臣說道:“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身。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3](P50)這是趙匡胤為加強中央集權所玩的“杯酒釋兵權”把戲,殊不知這一“金口玉言”為趙氏王朝在文化上定下了享樂性品位,宋代因此對享樂性生活的認可和推崇尤為顯著,從吳曾《能改齋漫錄》所載宋太宗說的“寇準年少,正是戴花吃酒時”可窺一斑。在權本位的政治體系下,中國人的享樂實用心態是隨歷史發展的。即使沒有特別的環境、特別的氛圍,有著上千年發展史的世俗享樂本身就已經是積重難返了,何況宋太祖、宋太宗等又威逼利誘別有用心地倡導之,這自然使大宋王朝的享樂之風變本加厲。趙匡胤及宋代的其他帝王又都缺少唐代明君所具有的豪邁與放達,大唐帝國的崩潰,五代十國的風起煙滅,使他們憂心忡忡于國內之禍患。內患意識使得宋代帝王在帷幄運籌中采取了“守內虛外”的政治軍事策略,加強了中央集權。“陳橋兵變”式的歷史鬧劇雖然因此避免了,但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再加上朝內劇烈的黨派之爭,使為官者莫不人人自危。大批的為官為政之人,深感報國無門,只好入朝則得過且過,出朝則自尋逍遙,享樂人生。奢侈浮靡的享樂自上而下,就連三任宰相的呂蒙正、主張節用愛民的歐陽修也是樂此不疲。 宋代迅速發展的城市經濟也為有宋一朝的享樂性生活提供了物質基礎。中國城市發展到宋代出現了大的突破。北宋以前,住宅區(坊)與商業區(市)是嚴格分開的,而且大多實行宵禁。進入宋代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城市人口的增加,市坊界限打破,宵禁取消,金銀銅鐵貨幣及“交子”開始通行,于是,商業、手工業、娛樂業、服務業等大量興起,瓦舍、勾欄等娛樂場所遍及各地。《東京夢華錄》載:“夜市直至三更,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處去,通宵不絕。”城市生活熱鬧到這種程度,難有耐得住寂寞者,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庶民百姓,無不傾心相樂。由于以上主、客觀原因,宋代柔軟性、享樂性的文化大氣候便形成了。 宋代平民氣、世俗氣的享樂不同于晚明思潮下的縱欲享樂。晚明的文人士子已亂了“方寸”,宋代的文人士子不但沒有亂“方寸”,而且保持并深化著傳統儒家的人格精神與品德操守(宋代的理學精神可以為證)。宋代文人士子在這享樂性的文化大氣候下,該何去何從?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隨波逐流者自甘沉溺,昂首矯俗者有自己的思考。宋代的有識之士認識到,歷朝歷代的官場腐敗主要是入仕之人不恪守德性、惟利惟欲是圖所致,陸九淵曾論道:“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4](P493)“終日從事者,雖曰圣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又唯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4](P276)為了社會之治,宋代從趙匡胤就開始自上而下地注重德性上的教化,以至于后來出現了理學,所以,宋代不乏以“孔顏樂處”為高標和趨向淡泊者。梅堯臣以淡泊為人生正味,奉行“淡泊全精神,老氏吾將師”的準則,范仲俺、韓維等也都有推崇淡泊自守的言論。王昭素講《易》在宋初也甚有影響,趙匡胤把王昭素對其言的“治世莫若愛民,養生莫若寡欲”朝思夕誦,作為治世養生之術,這對他所誘導的享樂性生活也起了扶正糾偏的作用。 佛教在宋代有很大的影響,不少君臣喜佛好佛而身體力行之,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駁了享樂之風。趙匡胤曾詔西川轉運使沈義倫于成都寫金銀字《金剛經》,可見他事佛的虔誠。趙匡胤為了江山社稷的安穩,別有用心地誘導大臣們享樂,而對自己的孩子卻是本于佛家思想,告誡他們要惜福,不要為傷生的惡業之端。永慶公主有次衣著華麗地入宮,趙匡胤不悅,批評道:“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效仿。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3](P286)“利欲如摽鋒”、“積善來百祥”等佛家說教在宋代的一些官吏身上也有所體現。護國節度使陳思讓在任期間“無敗政,然酷信釋氏,所至禁屠宰,俸祿悉以飯僧,眾號為陳佛子。身沒之后,家無余財”。[3](P329) 宋代在儒道佛相應思想的作用下,追求恬靜寡欲的淡泊人生也成一潮流,與享樂人生相反相成,享樂氣愈濃,淡泊之追求也就愈強。在如此的世風下,陶淵明“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斯濫豈攸志,困窮夙所歸”的人品就成了一面旗幟,因此而得到同道相契者異口同聲的推尊。朱熹贊論道:“晉宋人物,雖曰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所以高于晉宋人物。”[5](P187)宋代還注意到了陶淵明“恥事二姓”重名節的人格,這一人格在南北宋黨派之爭民族之爭不斷的政治環境中,頗受從一而終的仁人志士的推崇。林甫在《省心錄》中言:“陶淵明無功德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文天祥《海上》詩云:“王濟非癡漢,陶潛豈醉人。得官需報國,可隱即逃秦。”以上是在大文化環境下宋代對陶淵明人格人品的接受。
二、復古革新
宋初,佛老思想顯得空前活躍,儒家的正統地位受到嚴重挑戰,致使石介驚呼,舉中國而皆從佛、老。以孫復、胡瑗、石介為代表的一些學者,為了維護儒家的正統地位,打著復古旗號,標榜王權,鼓吹道統,反對佛道,復興儒學,同時也從理論上批評當時的浮靡文風。這些舉措打破了當時思想文化界的沉悶,中唐的復古中求變革的學術運行機制在宋代又開始運轉起來。 宋代的經學復古與唐代的依古注治經的復古做法不同,而是對以“五經”為代表的漢代經學體系大膽懷疑,欲求在考證和重新闡釋中恢復“五經”在先秦的“樣子”。據《能改齋漫錄》記載:“慶歷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甫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荊公修《經義》蓋本于原甫。”劉原甫撰《七經小傳》,多出己意,與漢儒舊說不同;王安石“視漢儒之學若土梗”,二人已有另起爐灶之勢。歐陽修、蘇軾、蘇轍對儒學中的漢學體系也有懷疑和非議,此不細舉。 宋人經學研究中突破最多的是《詩經》研究。宋以前,說《詩》者皆宗毛、鄭之說,視之為金科玉律。而宋代說《詩》者對漢儒在《詩經》的序、傳、箋中做的穿鑿附會和曲解原文進行了大膽的懷疑和指正。北宋時期,歐陽修、蘇軾等在總體上向漢儒《詩經》學體系發難,并在部分問題上打開了突破口。南宋時,《詩經》研究者重新對《詩經》進行全面的梳理、考證、研究和闡釋,而且多有新見。鄭樵認為《詩序》不是圣賢之作,而是村野妄人所作。王質對漢儒《詩》學也是持否定態度,但他并沒有采取直接批評的方法,而是對《詩經》重新詮釋,用了30年的時間,撰寫了《詩總聞》三十卷。朱熹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對《詩經》進行了更為深細的探討。所撰《詩集傳》,棄舊序,寫新序,對《詩經》作品逐一解釋,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詩》的真實目。朱子強調要“平心看詩人之意”,他在《詩集傳》中說:“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還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相與歌詠,各言其情者也。”朱熹的闡釋和觀點在一定范圍內恢復了“詩”人和《詩》的原貌,但《詩經》在漢儒的闡釋中所產生的規約性、神圣性卻都隨之遠離了。 宋代儒學上的復古,目的是為恢復儒學的正宗地位,鼓吹道統,可是對漢學體系的推翻卻也抹去了經學的神圣性及其所具有的積極入世的鼓動性,使經學平民化了。以平民化的“經”為指導思想的士子也就以“平民”的心態入世,所以,宋代儒學上的復古,復出的是平心靜氣的心理,這與魏晉南北朝儒學萎靡狀態下的士子心理相近。心態上的契合使宋代不像唐代(唐代士子們大都急功近利,有貴族化心態)那樣冷淡陶淵明,而是以愿與之為伍的心態親近之。 文學上,宋代在反對浮靡文風中也在走復古道路,其目光投向晉宋,甚至再前的“古詩”時代,認同其高古樸素、自由無為的藝術境界。與唐人的“好詩婉轉如走丸”之追求不同,宋人重古詩的意象簡樸。呂本中言:“大概學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為主,方見古人好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6](P572)張栻說:“古詩皆是道當時之時事,今人做詩都愛裝點語言,只要斗好,卻不思一語不實便是欺。”[7](P532)呂本中不喜齊梁綺靡氣,但并沒有以唐詩為學習樣本,可見他也不喜唐詩之“婉轉走丸”氣;張喜歡像古詩那樣直道其事。從宋人詩論和詩作上看,宋人對風華正茂之詩是卑視的,而這正是宋人有意識地對詩歌燦爛之唐代的超越。所以,蘇軾等看重古詩的高風絕塵,欣賞陶詩的超然。陶詩的超然自然是迎合了宋代詩歌在復古中欲求超越唐代的意旨。總之,宋代的復古革新運動把文人墨客帶到了陶淵明的近旁。
漢魏以來,佛道思想廣泛傳播,對儒家思想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本土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碰撞融合,推動了中國思想的演變。性命之理是中國古代思想界的老問題,佛道之學深入人心并蔓延,自然會使老問題生出新觀點。雖然宋代學術界不時有排斥佛老的口號,但這并沒有影響儒、釋、道三教在宋代的交融。佛學的空寂、冥悟,道家的虛靜、逍遙,與儒家的溫柔敦厚、治心是極相親近之說,正是基于這相近相通的層面,宋代出現了儒為主佛道次之的三教合一之學——理學。理學家出入佛道最后所要完成的就是營造一個與“天國”、“彼岸”相媲美的“入圣”境界,從而使儒學面目一新,并達到其“修己安人”的社會目的。理學的理想是欲求在安身立命中實現治世安人,這就重新樹立了士子的價值觀,這一價值觀務求理義的智慧化自覺、內斂的修身實踐與為人師以匡世的統一。所以,宋代思想家特別強調“靜”,主張“以靜為本”,主張在“靜”中體識萬事萬物之理,以求知道達機。在這種思想氛圍下,文人士子的思考雖然多無意禪定,卻在不自覺中進入了禪定式的思悟狀態。陶淵明詩中有不少類似禪定狀態的詩境,故頗得宋人的嘉許。施德操在《北窗炙四則》中有言:“陶淵明詩云:‘山色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時達摩未西來,淵明早會禪。”其他人還多以“此老悟道”、“知道之言”等語贊陶。蘇軾還曾反駁杜甫“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之言,于《書淵明飲酒詩后》中說道:“《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陶淵明“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辛勤無此比,常有好容言”的言行,堪稱大徹大悟者之言舉,故深得宋代坎坷之士的追慕。辛棄疾以陶淵明為自己歸隱閑居之精神上的慰藉者,這在他的詞作中多有表白,其《水調歌頭》(賦傅巖叟悠然閣)下闋寫道:“回首處,云正出,鳥倦飛。重來樓上,一句端的與君期。都把軒窗寫遍,更使兒童誦得,歸去來兮辭。萬卷有時用,植杖且耘耔。”思想境界的相慕相投,使他們跨越半個世紀的歷史距離走到了一起。 宋朝人之感情相對于唐人的,有進入“老”境之感。“夕陽西下幾時回”的感嘆、美人遲暮的悲傷是宋代文人士子的感情基調,偶爾的金戈鐵馬之聲只是已經興不起風浪的“老”之心態所產生的幾個浪花而已。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偉大詩人雖早年豪健清雄,但后期多蕭散簡易。這種感情基調是與宋代用人尤其看重“老成持重”相一致的,據《國老談苑》載,寇準“年三十,太宗欲大用,尚難其少,遂服地黃兼餌蘆菔以反之,未幾髭發皓白”,于是不久為相。這看起來簡直是笑話,但卻真實地反映了宋代當朝者的心理年齡狀態。所以宋人對人之老境多有論說,周必大于《跋王民瞻詩》中言:“人年八、九十,語必諄諄。”《容齋隨筆》卷十四言:“士之處世……見紛華繁麗,當如老人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游,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于胸中也。”兩處引語流露的都是對“老”境的鐘情和有意的倡導,由此可以看出宋人對“老”境的留戀和欣賞。“老”境的平淡素樸與陶淵明的平淡素樸是相同性質的感情狀態,處于“老”境的宋人也就不難理解和接受陶淵明,也就不難識破陶詩真味了。黃庭堅跋陶淵明詩卷云,“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8](P99)便能窺見其境,而這恰是唐人做不到的。 一個朝代對前人的接受是以該朝代思想感情上的特點為決定因素的,宋代思想上的禪定狀態和感情上的進入“老”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對陶的喜愛。
四、詩歌審美
宋代特喜歡陶詩是與其詩歌審美理想分不開的。中國古典詩歌的平淡美作為審美理想是自宋代開始的,并確立于成熟的理論自覺中。宋人的平淡詩觀是與梅堯臣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梅堯臣《讀邵不疑學士詩卷……》中的“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詩句是宋人平淡詩觀的經典表述。詩以“古淡”為高是梅的主張,也是其他人標舉的境界。歐陽修在《讀張李二先生文贈石先生》中言:“辭嚴意正質非俚,古味雖淡醇不薄。”蘇舜欽《贈釋秘演》中有言:“不肯低心事雕鑿,再欲淡泊趨杳冥。”王安石《沖卿席上得作字》也言:“古聲無淫,真味存淡泊。”“古淡”在宋初成了復古主義思潮中的一種審美趨向。當時真正“古”而能“淡”的當是梅堯臣了,梅詩筆尚樸拙,意象清雅,立意平實,又多用五言,長于五古,相對于西昆體之七律的麗密致,相對于石延年等詩的慷慨任氣和蘇舜欽七言古詩的宏壯豪獷,都顯出十足的平淡氣質。宋人對梅評價道:“去浮靡之習,超然于昆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諸大家未起之先。”[9](P244)他的實踐和主張使原來寬泛朦朧的美學主張有了一個真實有力的范本,平淡理論的探索因此有了明確的方向。 繼梅、歐等宋初詩人后,蘇軾、黃庭堅把平淡詩美的探索推進到高度自覺的階段。他們的理論和實踐代表了平淡詩美追求上的最高成就,但兩個人的視野是有所分別的。蘇側重于從審美情感上把握平淡的韻味和風神,特別強調平淡中的“至味”、“奇趣”,因此,他高度評價司空圖關于“韻外之致”的觀念和實踐。黃庭堅則側重于從藝術的角度把握造于平淡的艱難歷程,把平淡視作含納大巧而又純熟無跡的藝術境地。 在宋代,平淡不是少數人的詩美理想,而是較普遍的審美傾向。宋初流行“白體”,該體以淺近的語言抒寫閑適的情趣,李、李至等文人士子多操筆于此。宋真宗為改當朝“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為勝”的風氣,下令禁止屬辭侈靡浮艷,并親自“選其平淡者”八聯為標準。真宗朝后期,盛度、晏殊等倡學韋應物,追求平淡之風。再后來還出現了以閑適為宗旨的“邵康節體”,可以看出,平淡是大宋王朝詩歌審美的主調,宋代文人士子多喜陶詩、論陶詩、學陶詩、和陶詩,也就成了自然之事。 ^在宋代首先打開陶淵明接受新局面的是梅堯臣。他是第一個倡導并學習陶詩的宋代詩人,而且第一次對陶詩平淡而深邃的美學價值有了明確的理性認識,并奉之為美的極致,從而開拓出超越唐人的陶淵明接受史。梅44歲前把陶詩作為師法的對象之一,只有一次用平淡論詩;44歲后大力學習陶詩,屢次以平淡論詩,而且將平淡與陶詩并論;50歲左右的梅堯臣提出“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的藝術主張,已超越了對陶詩的學習層面,而是身體力行之。梅44歲后力學陶詩,既與其禍不單行有關,也與知心朋友間的唱和有關。與梅堯臣有交往的晏殊、韓維等人也都推尊陶詩,他們之間以陶詩之風格相互欣賞推許。宋初對陶之接受新局面的打開,為蘇軾全面而深入地接受陶詩奠定了基礎。 蘇軾所謂平淡中之“至味”、“奇趣”,主要是蕭散野逸之趣,因此蘇軾的平淡詩觀較之梅堯臣就更為直接地與陶淵明聯系在一起。蘇軾大量贊陶、和陶詩是寫在戴罪出貶黃州之后,他曾在《與李公擇書》中評自己貶竄之際的生活言:“仆行年五十,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輩為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蘇軾面對人生困境冷靜樂觀,任真自適,與陶淵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辛勤無此比,常有好容言”是同樣的風格,所以他在《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后》中自稱:“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蘇轍還在為蘇軾所寫《和陶詩引》中轉述蘇軾之語曰“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因此,蘇軾追和陶詩109首,而且推淵明為千載獨步之首位詩人。考諸宋代,甚至宋以后諸朝,與陶淵明風調相續者唯有蘇軾。 黃庭堅追求“蕭然于繩墨之外”,無意為文而意已至的妙境,他論陶也取向于此。他在《題意可詩后》中說“至于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于《論詩》中說“淵明直寄焉耳”,于《贈高子勉》中言“彭澤意在無弦”。因為陶之作品的渾然無法,黃庭堅所以尊陶學陶。這好像與宋代平淡的審美追求相偏離,其實,宋代在平淡上的審美,不只在意象上,還包括在詩法上。蘇、黃后,還有為數不少的人喜陶詩、和陶詩、論陶詩。大理學家朱熹也深愛陶詩,他曾論道:“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淡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10](P113)朱熹說出了宋人喜陶詩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蕭散沖淡”的審美趣味使得宋人把陶詩奉之為圭臬。 以上四個方面不可截然分開,而是交融在一起的,它們的合力促成了有宋一朝對陶淵明的空前喜愛、空前接受。這四個方面也是就大處言其原因,細枝末節之因沒有論及。最后須補充的是,宋代對陶淵明的空前接受是以陶之詩文、陶之傳記在唐代、宋代的廣為傳播為前提的,尤其是離不開宋代廣泛流行的陶集抄本、刻本對陶的傳播。 參考文獻: [1]杜甫杜甫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 [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9 [4]陸九淵陸九淵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0 [5]陶淵明研究資料匯編[M]北京:中華書局,1962 [6]何溪汶竹莊詩話·集部詩文評類·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子部雜家類·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葛立方韻語陽秋·集部詩文評類·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宛陵先生集·四部叢刊[M]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 [10]羅大經鶴林玉露[M]北京:中華書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