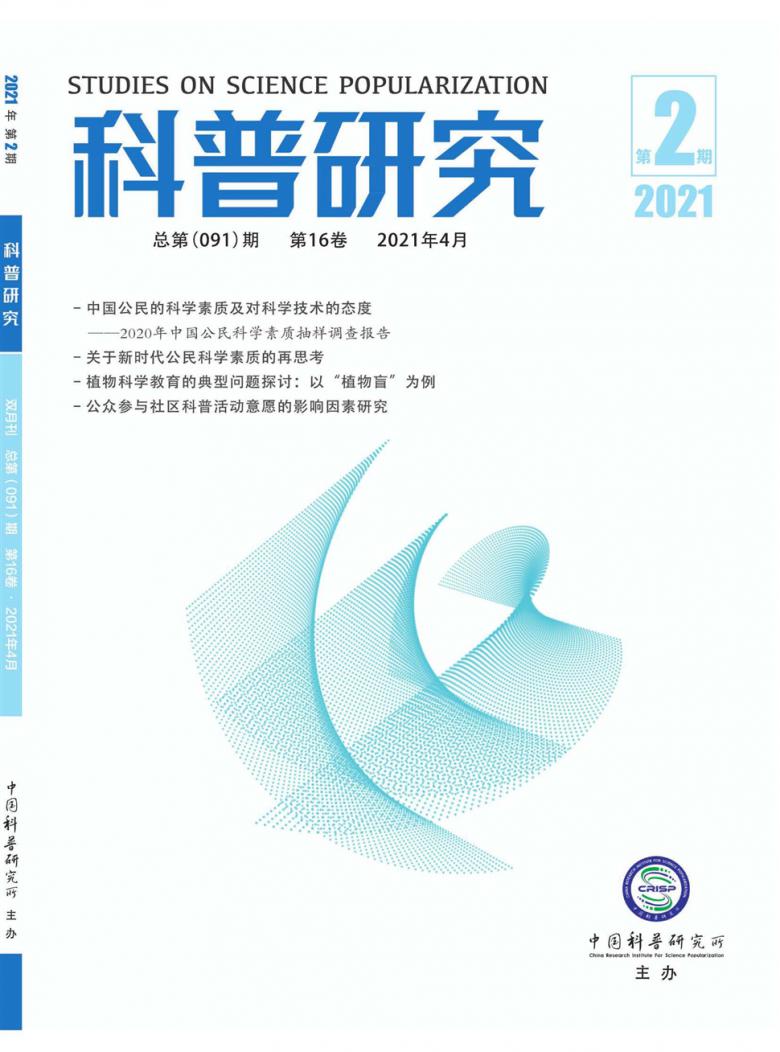儒家傳統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景——從“中庸”的視角出發
張寶明
一 思想界的“自由”動向
當20世紀的人們已經習慣將中庸之道說成是如同貓的溫和、以折中冒充“公允”之后,隨之而來的寬容即是“溫情主義”。更為可怕的是,溫情乃是怯弱和自私的代名詞。[1]尤其是1949年以后,隨著五四精神的論定以及魯迅方向的確認,仿佛五四精神就是不妥協、完全、徹底的代名詞;五四的偏激與固執就是我們民族文化的方向。五四曾經出現過的與改良有點近親的溫和、中庸、折中思想被挖了祖墳,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庸之道更是被被揭批得體無完膚。當世紀的喪鐘和新世紀的晨鐘同時敲響的時候,我們不由得開始了對中庸的懺悔。這樣的懺悔和反思首先來自于海外思想界:如果我們的民族要創新,要追求現代性,就必須在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性的轉化。[2]換句話說就是不能再重復“不破不立”的故事,一定要在注重“傳統的延續性”。[3]環顧當今思想界,無論是自由主義者還是“新左派“,抑或不自由、不新也不左的學者,在對傳統與現代自由的銜接上已經達成大致的“通約”:通向現代自由之路決不是在“過河拆橋”的前提條件下進行的,但究竟怎樣在“老橋”與“新橋”之間找到接口卻是當今學者需要以坐冷板凳的勇氣去正視的。通讀西方自由主義當時哈耶克、薩托利等大師的經典,也都在不同的視角下同時強調自由主義必需與傳統銜接的必要性。在大師們看來,自由主義無法移花接木、從頭再來。與此同時,筆者也看到,無論是海外還是海內的思想界,他們都陷入了一個新的緊張中——對必須打破傳統而又必須在傳統的基礎上創造上嚴重地吊著各自的“詭”。于是,我想,放下抽象的“該怎樣的”論述,從具體的文化資源入手來個傳統和現代的“究竟怎樣”對接也許是一個不無意義的嘗試。
二 儒家思想與自由主義對接的可能性
關于自由主義的淵源,我們可以長篇大論;關于自由主義的定義,可以說是仁者見人、智者見智。這里我們關注的東西都已經不是這些方面,我們首先要認同自由主義的內核,并以此作為我們談話的基線和平臺。筆者認為,無論怎樣扯皮,對自由主義的開放性這一點,也是關鍵的一點或許是無人懷疑的。開放是自由主義內在的質的規定性,拋開這一點談自由主義可能就沒有什么可討論的了。撇開法治的(政治上的立憲秩序)、經濟(私人財產的神圣性)的因素,文化上的導向則是一種地地道道的具有“容器”之“容”的自由觀念。正如世界著名的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先生在點明了“不同類型的自由主義在要求個人自由”時“隱藏著某種重大的分歧”后著重強調的那樣:自由主義的全盛期,“首先意味著自由的個人不服從任意的強制。”[4]沿著這條路走下去,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時刻要有“妥協的準備”。[5]妥協,在20世紀革命的話語里是最丟臉、最掉價甚至是最無恥的事,然而在自由主義的畛域里妥協是一種寬容、兼容、包容的又一表達。
也許,寬容并不是“自由之路”的充要條件,但卻可以說是“必要條件”。可以這樣說,一個社會有沒有寬容將是判斷其是否自由、開明的重要價值尺度。必須注解的是,“寬容也不以相對主義為前提。當然,如果我們持相對主義的觀點,我們會對所有的觀點一視同仁。而寬容之為寬容,是因為我們持有我們自視為正確的信仰,同時又主張別人有權堅持錯誤的信仰。[6]《大英百科全書》里這樣解惑說:“寬容(來源于拉丁字tolerare):容許別人有行動和判斷的自由,對不同于自己或傳統觀點的見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7]
在自由主義的思想境界里,寬容是金。而寬容又是與激進、徹底、“不斷”、不妥協、全盤、“根本”等革命“偏方”相距甚遠的。在西方思想家的文字世界里,洛克的《論宗教寬容》和伏爾泰的《論寬容》以及晚近的房龍《寬容》已經把走向文明歷程的關鍵詞給標識了出來。中庸之道可以不與西方的自由傳統之寬容同祖同宗,但卻可以有同氣相求的精神意念和氣質。在“中庸”的思想境界里,至少可以避免絕對之反“容外態度”(xenoacceptance)招致的偏激禍端。
如果說歷史已經證明了激進主義的革命理論與真正自由主義的格格不入,那么在認識“儒家革命精神的源流”之后再來批講中庸之道與自由主義寬容精神的會通也是頗有一番滋味的。[8]這乃是我們從中庸視角求證儒家傳統與自由精神對接的前提。
三 打撈“中庸”:傳統資源里的一枚人文古幣
在講求以法治國的今天,走向憲政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自由是憲政的理念基礎。沒有自由精神的國度很難形成憲政的社會。而自由理念的產生又不是完全靠移植、舶來或是憑空捏造的,它需要在自我傳統的主體上創造性地轉化。這樣以來,恕吾直言,中國傳統里可供挖潛從自由資源實在是門可羅雀。除卻“矯枉過正”、“深刻的片面”、“不破不立”的“非自由”邏輯外,多元、憲政、獨立、權力都是紙上談兵,幾乎與傳統無緣。一元代替著多元、人治威脅著法治、關系制約著獨立、義務侵占了權力。即使是千年的亮點“以民為本”也充滿了寒夜的風霜,自由的船票難以登上這傳統的客船。
不錯,我們有“吾意懷不忿,汝豈得自由?”[9]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苦熱詩》也有言曰:“始慚當此日,得作自由身。”文學家柳宗元的失意也曾有這樣的“神來之筆”:“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凡此種種,詩歌的愜意還是充滿了“妾意”,無法與正宗的“獨立”之道相提并論。說到這,不是很讓我們對這個已經選定的命題失望嗎?的確如此,不過“車到山前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古典境界還是給了我們一點黎明前的微光:中庸之道至少是我目前所能在傳統文化資源里打撈到的最接近或說最具有“自由主義”精神氣質的思想資源。
必須說明的是,關于中庸的解釋,自古至今莫衷一是。不過,這里筆者注重的是其寬恕之道、懷柔之心。因此本文論述的重點也就不是引文索句式的求證、對應,而是“中庸”涵蓋的自由精神氣質。《四書》里的《中庸》讀本有孔子的語錄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10]從《中庸》字面上看,倒也沒有什么“自由”的直接意義。按照王淄塵先生的注釋是這樣一回事情:
君子能用中和之道,所以說:“君子中庸。”小人不能用中和之道,事事和君子的行為相反,所以說“小人反中庸。”時中,就是喜怒哀樂時時中節的意思。所以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無忌憚,就是無所顧忌,人而到了無所顧忌的地步,還有什么壞事不可做呢?
也許,就這段話本身我們還是對“中庸之道”不甚明了,不過我們還可以借助上溯的辦法來貫通:“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再按王淄塵這位四書老先生的注解即是:
人人都有喜怒哀樂,但人人不免喜怒哀樂之過甚,或不及。只有未發的時候,才能無過甚與不及的弊病,這就叫做“中”。等到發了出來,也能無過甚,無不及,這就叫做“中節”;也就是“和”之一字。所以“中”,是天下事事物物最大的本源。“人”而能“和”,則天下都可通行了,所以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人能夠做到這個地步,就能合于天地的運行。天地運行而能“中節”,而能“和”,就是萬物所以化生所以長養的道理,也就是由宇宙觀以決定人生觀的來由。他所說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就是這個意思。
從上下文的“意思”以及在后面的論述中,我們能讀到的“中庸”精神無非就是一個“凡事有度”的表達。在孔子的思想言論中,諸如“發乎情止乎禮義”,“過猶不及”[11],“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都是在這個意義上運用的。孔老夫子把道德的境界與中庸之道相提并論,足見其價值趨向:“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12]其實,文本的“時中”、“中節”、“中庸”、“中和”無論怎樣演繹,在思想底蘊上都不越“適中”的意思。說穿了這也就是事物的“度”的問題。這個“度”就是哲學上的辯證法。做事不過分,凡事不過頭,遇事不過激,這些都是孔老夫子著意倡導的“君子”氣質。
不過分的背后還有不夠分的缺憾。所以孔老夫子另一方面也將“不及”作為非君子作風來批評。歷史上關于孔子“悟道”的過程是這樣記載的:一次,孔子去魯桓公宗廟觀禮,看到一只傾斜的瓦罐。孔子問守廟人為何不把那只瓦罐扶正?守廟人回答說:這是“佑座之器”。無水之時傾斜,裝滿水時傾倒,只有裝上一半水時才是正的。于是,孔子在觀察一件小事中悟到了一個大道理。公元前522年,鄭國公孫僑在病危中告誡后人他的一生治理之道是“寬猛相濟”。孔子聞道則喜,稱贊說:“寬猛相濟,政是以和。”[13]過分嚴厲和過分放任都不是君子之道、治國之術。看來,一味放縱的、無法無天的、無所畏懼的無政府主義放縱邏輯是孔子不喜歡的,而極端專制主義的“苛政”也是不為孔子所歡迎的。
自由主義的精神氣質講求權利與義務。即在責任和享受的義理中把握一個活絡的“度”。這和中庸之道有一定的親和性。對中庸之道的理解,有的學者解釋為“折中”、“調和”,有的將它與激進(其實就是偏激)相對理解為“保守”,還有人根據其不走極端的非革命性質詮釋為“好人主義”的平庸“改良”。這些,都是從中庸之道的一個側面解釋了其基本的意念,應該說并不離題。說它講求“適度”、“適意”也好,論它主張“中和”、“平庸”、“保守”也好,反正“中庸之道”走的是漸進的路徑,與偏于一極的激進套路有一定的距離。與此同時,還必須看到,中庸之道的遠離激進、革命也不是為保守、退縮、僵化找借口,因為老夫子還有更貼近我們論點的說法在這里:“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14]“狂”乃急進、莽撞;“狷”乃退葸茍安,這兩個極端都是孔子所不茍同的,而他最為欣賞的境界還是“中庸”之道。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對劉小楓先生新近出版的《儒家革命源流考》中的“革命”源頭的孤注一擲還是持保留意見的。
當然,孔子雖然不止一次地述說“懷柔遠人”的方略,但他老人家對“中庸之道”作為一種境界的難度還是有一定的心理準備的。所以他說“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15]如同自由主義作為西方憲政的理論基礎也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演繹一樣,中庸之道的演繹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學者去耐心地栽培、養育的。 四 “中庸之道”的現代詮釋
講儒家傳統和自由主義的對接,在這方面有過先賢的嘗試,哈佛大學的狄百瑞以及新儒家徐復觀先生都作過有意的工作。從他們的論述來看,要貫通東方儒家和西方自由主義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傳統并非易事。即使像狄百瑞這樣的漢學家在長篇論著《中國的自由傳統》里也很難有個準確的思想“接榫”關節。[16]如此模糊的痕跡也是本人動筆的原因之一。我非常同意一位學者的觀點,儒學和自由主義作為東西方的顯學,各自的思想內涵極其龐大,因此后生在“注解”時很容易在“注我”的過程中向各自熟悉的苗頭衍發。即使是在一本薄薄的《中庸》里也存在著多元演繹的勢頭。
鑒于本文是要在傳統里尋求“轉換”的依據,所以這里不好“中庸”,只能“不及其余”地將中庸所能呈現的自由氣質完全給抖落出來。
同樣是我上面提到過的那位被同意的學者在一篇文章這樣論述道:
自由主義,盡管有其特定的價值傾向,但卻是一切“主義”中最為開放的主義、最能寬容其他主義的主義,是唯一允許甚至提倡反對自己的主義。所以,“寬容”也罷,“兼容并包”也罷,在性質上都是自由主義的。當然,“寬容”并不等于“贊同”。蔡先生把各種思潮都引入北大,完全不意味著他對各種主張都實行“等距離外交”,但他還是能夠尊重不同主張的權利。這使我想起了自由主義的一句口頭禪:一個自由主義者可能反對你的觀點,但堅決維護你持反對意見的權利。[17]
不難發現,寬容的精神氣質乃是自由主義的緊要之處。沒有寬容的自由主義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或說是冒牌的、虛假的自由主義。寬容是一種開放的觀念,大氣的思想,還是一種敢于正視真理的勇氣。
同樣是出于對這位著名學者的尊重,也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在我對他的觀點兩次認同之后,也有對其表述自由主義的異見。他這樣批評一些有“中庸”傾向的學者說:“許多人聲稱,他們既不反對集體主義,也不反對個人主義,他們反對的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和極端的集體主義,他們愿意接受的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的折衷。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都有所‘偏頗’,‘正確的’立場是站在兩者的中間。·……然而,個人主義于集體主義是相互對立的立場,兩者中間沒有平衡點。”[18]在筆者這里,我以為有三點需要考求:一是主張這類“折衷”的人不乏抱有漸進、迂緩、調和的自由主義信仰者,他們是在幾千年前的傳統面前無奈的情況下走向反對“極端”的,值得同情;二是持這種觀點的人本身就具有寬容的自由主義精神氣質,他們的“中庸”思想至少不會使用以一方壓倒另一方的手段,或用一方抹殺另一方的方法而“偏于一極”,符合自由主義的捍衛對方發言權的“自由原則”。換句話說,假如我們不能恰當的剝離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合理內核,又怎能在既反對徹底打倒傳統又主張對外包容的同時來進行創造性地接榫、轉化、貫通呢?三是要從自由主義的思想底蘊談起。眾所周知,自由主義講究的是權利和義務的有機統一。誠然,其他主義也這樣聲稱過,但真正能夠落到實處的只有自由主義這樣一個“主義”。按照這個“統一”,集體主義是是過分強調了“義務”,忽視了做人的權利,而個人主義則是過度地看重了“權利”,由此造成了雙方的誤解。這恰恰應了英國思想家雷蒙德·威廉斯的話:“人類的微機往往是理解上的危機。”[19]在人類發展史上,任何只講個人權利,不講個人義務和責任的“主義”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是“度量”的適宜不適宜而已。
為此,站在中庸立場上看問題,只有超越了兩個極端的“主義”也才是真正的“自由”世界。《中庸》里反對的“無忌憚”就是防止過度放縱的“極端”產生。無忌憚是一種“傻大膽”行為。一般來說,這類人又是以無知作為大膽的“理論”前提的。一貫反對愚昧和偏執的美國人德里克·房龍就在他的代表作《寬容》之第一章里就專門描述了“無知的暴虐”。[20]無知不可能折衷,只會產生偏見。偏見則是走極端的羅盤針。
“中庸之道”符合漸進的路數,在一定程度上為寬容提供了可能性。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經驗的點滴積累史。中庸不鼓勵急進,反對貿然行事,為各種思想、主張的并存提供了可能性縫隙和空間。如果我們不以告別自己的傳統為走向現代的依據,也不以全盤西化作為明天的方案,那么充分挖掘中庸以及類似中庸之道的傳統自由精神資源,乃是一條較為切實的途徑。
五 “自由”追求者的精神銜接
在以往關于傳統儒家資源與自由主義銜接的研究中,大陸尤其是海外的學者都注重對新儒家的求證,而對具有激烈反傳統傾向的西方價值傾斜者往往不置一詞。其實,這些西方價值的追求者,往往是最能反映“傳統”與“現代”互動、涵納的典型。尤其是通過這些個案的解析,我們能清楚地感覺到“不破不立”的不可能性,以及在傳統的基礎上重建現代性的必要。
這里,我們遴選了中國自由主義鼎盛時期的蔡元培、李大釗兩位具有新潮傾向的思想文化先驅作為本文的立論個案。
如同已已經引述的觀點,蔡元培雖然是“兼容并包”的集大成者,但他在對新舊派人物都能容納的做法并不意味著“半斤八兩”的“等距離外交”。其實蔡元培是一個外圓內方的傳統型文人。他在內心深處是一個充滿激情的西方價值論者,而在外表則是一個忠厚、溫和的“中庸之道”保持者。作為清末的一名翰林,蔡元培在加入同盟會之前,就已經是光復會的會長,力主暴動、暗殺。在上海與楊篤生、陳獨秀相約研制炸藥,成為“暗殺團”的主要成員后,他儼然是一位在血雨腥風中持槍弄棍的武者。[21]
蔡元培的革命情懷與其他革命者不同之處在于,他又是一位書生意氣的寬容論者。入主北京大學是蔡先生一生文化教育事業中最為燦爛的時段。他的辦學方針至今家喻戶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919年,就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漸至高潮而引起林琴南等守舊派的不滿后,蔡先生寫信公開回答自己的教育思想說:
至于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如下:(一)對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二)對于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于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22]
而這一看似完全從西方舶來的自由、兼容精神,其實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積淀。1918年11月10,翰林校長在《北京大學發刊詞》中這樣袒露自己施行教育宗旨的原委說:
大學者,“包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體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剛柔也,若相反而實相成。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論與厭世論,常樊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23]
按照傳統的中庸之道來論學,盡管也是相反價值觀念的引進,但還是不乏調和、折衷、涵容成分。蔡先生這樣自述在北大辦學的動機時說:“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余地。”[24]這也正是當時北大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庶民主義、國家主義保守主義等各種學說“五花八門”、“無奇不有”的根本原因。正如一位當事人這樣描述的那樣:“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長短。背后拖著長辮,心理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并坐討論,同席笑謔。·……這情形很像中國先秦時代,或者古希臘蘇格拉和亞里斯多德時代的重演。”[25]在這樣一個并立競進、包容并舉的環境里,不但北京大學自身生機勃勃地強盛起來,而且它作為龍頭帶動了全國輿論、思想的活躍。
即使是留學西洋、思想新潮的學者也不忘記從自己的傳統中尋求依托資源,這充分說明:傳統作為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已經深深烙在了我們的遺傳密碼里。對此,我們只有正視、延傳、衍發、升華,而不是一股腦兒連根拔除。
如果說蔡元培在中庸之道的表述上只是稍露崢嶸,那么被其聘任為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則是將傳統與現代自由精神的轉換、對接提到了一個非常的日程。
在李大釗“五四”的思想資源中,一個突出的特征是“調和”。在以往的歷史研究中,對其“調和”思想往往避而不談,只對著重挖潛其直線發展式的急進思想。現在看來,對李大釗“調和”思想的有意忽略不但違反了歷史原則,而且歪曲了李大釗思想的本來面目。自1916年至1918年,李大釗反復思索著文化的走向與出路,“調和”一詞一度成為他筆下使用率最為頻繁的詞匯。其實這一思考正乃政治模式在文化中的折射。無論是文化上的“調和”還是政治上的“調和”,思路都萬變不離其宗:“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為世界進步之二大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須時時調和、時時融會,以創造新生命,而演進于無疆。”[26]這是李氏不“挾種族之見,以自高而卑人”的“平情論之”,帶有很強的理性成分。在《調和之美》的“審美”、《辟偽調和》的“駁論”、《調和之法則》的“設計”、《調和謄言》的“主張”里,先生的立論都不曾離開“并立”、“競存”的意念。如果用我們日常使用的“調和”之意來附會都是無法解讀的。綜合先生的“調和”理路,它的意義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1)“肇于兩讓,保于兩存”;(2)“新舊之質性本非絕異”;(3)唯有雙方,而無“第三者”;(4)涵納有容的并舉精神。在李氏那里,太激進了,就會出現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慘劇;太保守了,又會因為傳統勢力太重而“淪于腐敗”。為此,找到一種維持“競立”格局的文化資源乃是當務之急。他反復述說“競立對抗為并駕齊驅”之勢的優長,目的只有一個——避免兩種勢力的復合為“一”。“舊”、“緩進”、“古”、“保守”代表的是“秩序”;“新”、“急進”、“今”、“進步”則意味著發展。怎樣處理穩定與發展的關系是李大釗議論的中心,這也是每一位立足于現實的仁人志士所不能不關注的焦點時代課題。即使是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的文化比較里也沒有忘記這一“能量守恒”定律。進化規則是競爭的規則,沒有競爭也就失去了前進的動力,缺少了動力只能是社會活力的式微。他說:“人類社會,繁矣頤矣。挈其綱領,亦有二種傾向,相反而實相成,以為演進之原。譬如馬之兩韁,部勒人群,使軌于進化之途。以年齡言,則有青年與老人;以精神言,則有進步與保守。他如思想也,主義也,有社會主義則有個人主義,有傳襲主義則有實驗主義,有惰性則有強力。”[27]這是在西方思想刺激下的對“周易”、“中庸”思想的沸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它呈現出開放、多元的思維方式。
在李大釗筆下,“涵納”、“有容”、“調和”、“平衡”等與“中庸之道”氣質同聲共契的詞匯頻繁出現。盡管其中多有西洋詞匯點綴,但文氣里潛存著厚重的傳統自由精神底蘊卻是歷史的真實。《青春》一文看似全為一個“新潮”著意,但在文中卻不乏這樣的“易經”之道:“一成一毀者,天之道也。一陰一陽者,易之道也。”[28]這種“易經之道”就是中庸之道的前奏、寬容之理所在。唯有這樣的“中和”,才有避免偏激、極端的可能;唯有這樣的共存、并立,才會有寬容之下的多元、開放、民主、自由。在兩者的平衡、相持、緊張中漸進,這就是李大釗富有傳統氣息的自由演進、發揮潛能的“青春”思想。也許,沒有什么能比下文更能印證本論。《青春》有言曰:
周易非以昭代立名,宋儒羅泌嘗論之于《路史》,而金氏圣嘆序《離騷經》,釋之尤近精微,謂“周其體也,易其用也。約法而論,周以常住為義,易以變易為義。雙約人法,則周乃圣人之能事,易乃大千之變易。大千本無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謂也。圣人獨能以憂患之心周之,塵塵剎剎,無不普遍,又復塵塵周于剎剎,剎剎周于塵塵,然后世界自見其易,圣人時得其常,故云周易。”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此同異之辨也。東坡曰:“自 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此變不變之殊也。其變者青春之進程,其不變者無盡之青春也。其異者青春之進程,其同者無盡之青春也。其易者青春之進程,其周者無盡之青春也。其有者青春之進程,其無者無盡之青春也。其相對者青春之進程,其絕對者無盡之青春也。
其色差別者青春之進程,其平者平等者無盡之青春也。推而言之,推而言之,乃至生死、盛衰、陰陽、否泰、剝復、屈信、消長、盈虛、吉兇、禍福、青春白首、健壯頹老之輪回反復,連續流轉,無非青春之進程。[29]
這段描述帶有鮮明的傳統文化色彩,含有“易經”“一陰一陽之謂道”的相錯互補觀念,有著濃厚的(“進退”)自如、平和、從容之中庸觀念。以往學者的解釋多注意其“新”字,而筆者這里恰恰看到的是李大釗在強調“進”之過程的“守成”色彩。譬如上文中將“生死”這一演進過程的放大,“青春白首”有一個演繹時段的拉長等等相持、對立的“齊物論”,無不飽含著厚重的保守主義或說消極自由主義的“積極”成分。[30]可能,以這樣的視角談蔡元培容易接受,其實那是由于我們沒有走近李大釗。應該說,如果不是篇幅有限和主題的限制,進駐李大釗原本自由主義的思想大本營還是頗為值得回味的。
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推出一個同步結論:表面激進的思想先驅不一定就是“不可救藥”的偏執主義者。蔡元培、李大釗的“中和”質地就為我們的進一步研究埋下了伏筆。
綜上,儒家傳統資源與自由主義的接榫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學術命題。本文的嘗試只是一個初步的工作,深入細致全面的拓展還寄希望于來者。但,筆者可以預言:對這樣一個命題的探討既是一個從現實出發的真問題,也是一個真學術。對這樣一個關系到民族文化復興和現代命運的話題,希望有更多的言說衍生。 注 釋:
1、中國人似乎總是不習慣折衷,魯迅批評過“費厄潑賴”的寬容,著名評論家舒蕪也在其《回歸五四》中對這樣一個價值取向格外反感。他們似乎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乃至的心理積淀。參見魯迅《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舒蕪《論中庸》,《回歸五四》,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 劉軍寧在《自由主義與儒教社會》里這樣說:“中國作為世界上有著悠久連續文化傳統的泱泱大國,與傳統根基較淺的新興國家,或無很深文化傳統部落國家不同,既不可能徹底告別自己的文化傳統,更不可能把自己的文化傳統重新封閉起來,與外界隔絕。”參見《共和·民主·憲政——自由主義思想研究》第332頁,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陶東風說:“中國具有自由思想因子的知識分子卻偏偏對于激進主義情有獨鐘,他們急于要與保守主義劃清界限,采取了與傳統勢不兩立的敵對立場;但事實最終卻表明,在像中國這樣一個傳統深厚的國家,傳統的權威徹底瓦解之后,秩序的重建幾乎是不可能的。”《社會轉型與當代知識分子》第105頁,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
4、〔奧〕哈耶克:《自由主義》,《公共論叢:自由主義與當代世界》第12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
5、〔英〕波普:《自由主義的原則》,《公共論叢:自由主義與當代世界》第147頁。
6、〔美〕薩托利:《民主:多元與寬容》,《公共論叢: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第62頁,三聯書店1998年版。
7、 轉引自房龍《寬容》第13頁,三聯書店1985年版。
8、 劉小楓:《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
9、古代樂府詩歌:《孔雀東南飛》。
10、 王淄塵:《四書讀本上·中庸》第3頁,中國書店1986年版。
11、 《論語·先進》。
12、 《論語·雍也》。
13、 《左傳·昭公二十年》。
14、 《論語·子路》。
15、 王淄塵:《論語讀本上·中庸》第4頁。
16、狄百瑞:《中國的自由傳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版。
17、 劉軍寧:《共和·憲政·民主》第338頁,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
18、劉軍寧:《回歸個人:重申個人主義》,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年版。
19、〔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與社會》第41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20、房龍:《寬容》,三聯書店1985年版。
21、俞子夷:《回憶蔡元培先生和草創時的光復會》,《文史資料選輯》第77期,文史資料出版社,第13頁。
22、 《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71頁。
23、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11頁。
24、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351頁。
25、 蔣夢麟:《西潮》,臺灣業強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123頁,轉引自崔志海:《蔡元培》,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57頁。
26、 《李大釗文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0頁。
27、 《李大釗文集》上冊,第555頁。
28、《李大釗文集》上冊,第197頁。
29、 《李大釗文集》上冊,第196頁。
30、 根據鄧正來先生的翻譯與理解,這兩種自由概念在中文世界應該表述為“肯定性自由”與“否定性自由”。見《自由秩序原理》上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12月版,第14頁。細讀“中庸之道”,不難發現它與消極(低調、保守)自由主義精神氣質的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