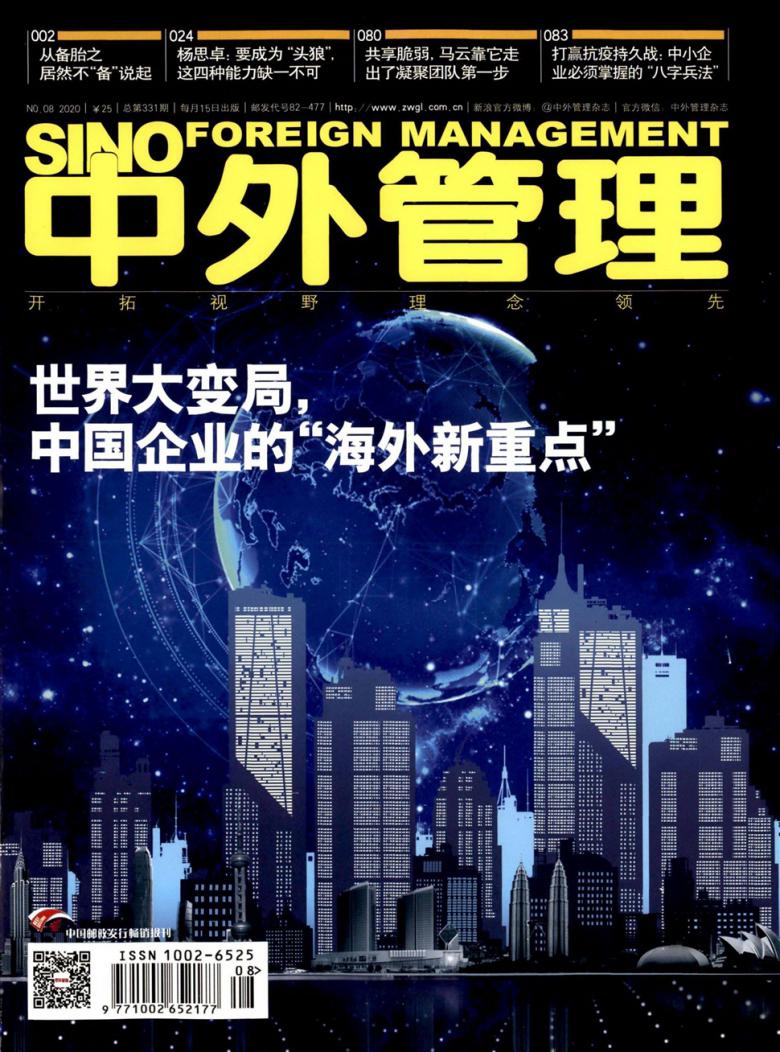中國古代和近代小說創作理論特征論
涂昊
關鍵詞:小說 創作理論 邊緣性 混雜性 摘 要:邊緣性的古典形態小說創作理論和混雜性的近代形態小說創作理論推動中國小說創作理論向現代轉化,都是中國小說創作理論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環。 中國古代小說創作的發展源遠流長,小說創作理論同樣也歷史漫長,內涵豐富,特征鮮明。從先秦至1840年的古典形態小說創作理論基本上在中國自身文化體系中獨立發展,1840年至1919年近代形態小說創作理論具有明顯的過渡性質,意味著古典形態小說創作理論的終結和現代形態小說創作理論的萌芽,是整個中國小說創作理論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環。 一 中國古代小說處于邊緣地位,邊緣的地位導致邊緣的心態,這種心態不僅對于小說作家,而且也對于從事小說創作理論的學者們,在中國古代強大的文化體系中,他們著力于提高小說地位,致力于小說創作理論研究,小說創作理論具有明顯的邊緣性特征。 1.與小說發展軌跡一樣,小說創作理論也在曲折與復雜的經歷中不斷發展。 古代小說長期受歧視,但還是有一部分有識之士認識到小說這一文體的價值和生命力,發表了一些對小說觀念轉變和進化有意義的理論見解,由此也萌生了中國最初的小說創作理論。 先秦兩漢期間小說題材不外是一些“叢殘小說”、“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之類,寫作意圖無過是“干縣令”和“小家珍聞”,這個時期的小說創作理論還處于醞釀階段。隨著“志怪”小說和“志人”小說的大量出現,魏晉南北朝時期強調真實性,以記敘歷史為小說的宗旨,力求使小說處于獨立的地位,這也客觀地推動了小說創作實踐的發展。到了唐代,像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論述:“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于搜奇匯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有意為小說。”{1}伴隨小說創作上創新之勢,小說創作理論雖文字不多,但最有意義的最大的突破莫過于淡化小說記史的忠實特性,強調了創作的主體情感因素,開始注意到了小說語言、人物塑造等屬于小說自身的問題。宋元時期,話本的出現,預示著中國小說即將成熟,小說藝術手法的論述也開始有較大發展,如可能編于宋末元初的羅燁《醉翁談錄·舌耕敘引》中“講論處不帶搭,不絮煩,敷演處有規模,有收拾。冷淡處提綴得有家數,熱鬧處敷演得越久長。曰得詞、念得詩、詩得話、使得砌”{2},這些藝術手法幾乎為后來的長篇小說完全吸收,成為中國民族特色的小說藝術。明代嘉靖萬歷以后,在具有啟蒙色彩的文藝新思潮的影響下,小說創作理論迎來了一個發展高潮,涉及到了小說創作理論許多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提出了小說的真實性、生動性、形象性以及由此產生的強烈的藝術魅力,對小說的審美特征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論述了小說和歷史在創作上的不同,研究了虛構和真實的關系;提出了小說人物塑造的理論;總結了“因文運事”“三境說”“個性化”“澄懷格物”“因緣生法”“間架”等一些經典的規律性話語。這些創作理論成就的取得,建立在對小說文體特性的充分把握的基礎上。 文體意識的發展源于小說創作理論發展的內在要求,但因古代小說長期受歧視,外在因素的牽引,決定了小說理論的重心首先落在提高小說的地位上,而非小說創作上。而且提高小說地位的最主要的途徑是將小說比附于史傳,這同時也導致了對小說創作非常不利的傾向——排斥虛構,這也就不可能正確認識和解釋小說創作,更不可能建立全面系統的創作理論。 2.理論形式的局限 晚明以前中國小說理論史,找不出一部專門的小說論著,甚至找不出專門的小說論文,小說創作理論遺產,除了少數散見于詩、文、筆記及小說作品中外,基本上是以序跋形式出現的,而序跋篇幅短小,無法深入到系統而繁復的小說創造工程中去,更何況小說序跋的目的也不在詳盡的理論探討上,要么在稱頌作者,要么說明該小說的社會價值,要么記載小說的成書和流傳情況,甚至是出于敷衍應酬而已。還有一種就是適當地從文論、詩論、畫論中提取現成的理論角度和思維方法評析小說。小說畢竟是小說,文論、詩論和畫論的方法只能停留在表層對小說藝術作模糊的描述,同樣也無法具有理論深度的探尋和歸納。這種方式發展到明清,出現了成熟的評點。評點中才情飛揚,知識靈動,展現了小說創作一個個鮮活的存在,而且評點和作者心心相通,激情對話,魅力無窮,但這也是從具體實踐出發的感悟式認識,重直觀重個別重感受而輕概括輕宏觀輕抽象,始終缺少強大的思辨力量和深入本質的抽象工夫,也無法推動小說擺脫邊緣的地位。 3.小說創作理論的核心觀念是“文”與“道”。 儒家的“人道”精神作為中國文學的哲學基礎之一,其主要影響在于對文學濟世化人等方面價值和功能的實現;道家的宇宙意識作為中國文學的哲學基礎之一,其主要作用于對文學審美體驗的深化和文學審美境界的開拓。中國的詩歌創作與詩學理論始終于兩者之間作綜合性的審美選擇,儒道合成的哲學基礎始終在共同發揮潛在而強有力的影響。而中國古代小說不像詩歌一直在文學秩序中處主導地位,處于邊緣地位的小說則主要受儒家精神的影響,急功近利觀念強烈,它對主流的文學觀念雖不是簡單的認同和延續,但小說創作理論的觀念還是根源于傳統的“小說關乎世道人心”的功利觀念和文學教化的倫理中心主義,“文”“道”依然是共同的核心范疇。所以無論對小說本身的認識走得多遠,都只可能是一種表面形態的更新而不能產生質的變革。這也導致小說創作理論忽略審美價值判斷而重倫理價值判斷。創作理論不從對象自身出發,也不回到對象自身,以對對象的倫理價值判斷取消了對象本體,創作理論很難回歸文學。 二 近代形態小說創作理論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70余年時間。作為古典形態創作理論的終結和現代形態創作理論的萌芽,過渡性質的近代小說創作理論,受時代特征的影響,開放的心態和襟懷不夠,游移于古典小說理論和西方小說觀念之間,小說創作理論具有明顯的混雜性特征。
尤其是甲午戰爭之后,向西方學習的熱潮加劇,西方的小說創作理論對中國小說創作理論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也有益于現代中國小說的創作實踐。但無論是于生活中寄托理想的現實主義創作理論,還是離經叛道、借幻想映射生活的浪漫主義創作理論,也無論是主張形式至上,作家寫給作家看的唯美主義創作理論,還是注重教化走向大眾的革命的創作理論,都一味地效法域外,追隨他者,考慮融合于中國自己的創作理論不多,因此,在中國小說創作理論不斷的發展中,很難給人的審美觀念帶來很大的差異,也很難完全滲透到具體的創作實踐中去。由此,現實主義的創作理論借助時代潮流逐漸成為普遍認同的準則,在世界小說創作理論豐富駁雜之時,中國小說創作理論在近代就逐漸走了單調之路。 3.就近代小說創作理論的整體走向而言,既指向未來,又暗合過去。 近代小說創作理論是對古典小說創作理論的否定為起點的,它認為小說使文學在內容上從過去的充滿高雅的詩意的天上落到充滿俗氣的人間,這將是文學未來發展的主流,這是新的社會時代及其代表階級的審美趣味。由此可見,近代小說創作理論實質是在政治化的背景,以政治目標為歸依,依靠政治力量而進行的。它們即使認識到小說所具有的本體意義上的審美屬性,其旨歸依然是提高小說的價值和地位,重新構建新的文學秩序。 由此,以嚴復、梁啟超為代表的張揚小說社會功利為核心的“小說革命”式的創作理論并沒有真正深入到小說內部世界中去建立現代意義的創作理論體系。作為反撥的以徐念慈、黃摩西、王國維為代表的要求回歸文學自身,強調小說本體的創作理論一則缺乏新的創作實踐的強有力的支持,二則時勢不宜,影響也極其有限。倒是鼓吹趣味、消閑、金錢的創作理論與傳統視小說為“小道”“閑書”的觀念有暗合相通之處,在社會影響頗大。這種從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呈現出一種曲折反復的復雜性。雖然,近代小說創作理論提出了許多反叛傳統的富于革新意義與現代氣息的新的理論命題,但諸如理論家梁啟超對古代小說的否定是基于中國的小說不外是誨盜如《水滸》誨淫如《紅樓》兩端,跟封建正統完全一致。可見,對傳統觀念的叛逆,又是非常不徹底,其未來走向依舊混沌。 總之,近代小說創作理論的意義主要不在其理論方面,而在于推動促進了中國古典小說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化過渡。歷史表明,“中國近代小說理論具有先導性的特點,小說理論倡導在前,而后有小說創作的繁榮”{3}。中國近代社會前60年,即從1841年到1900年,只出版了133部小說,而且大都是公案、俠義、狹邪小說。近代小說的繁榮,是在庚子之后。從1901至1911年,創作出版了529部小說。{4}雖然其中有印刷術的發達,稿酬制度的建立,西方文化的影響,社會的腐敗諸種原因,但近代小說創作理論是其中最直接的推動力量。 中國小說創作理論發展到近代,古典形態小說創作理論的概念和范疇已經不能滿足闡釋近代小說創作實踐活動的需要,對異域理論的吸收也處于移植階段,現代小說創作理論的概念和范疇只是處于萌芽階段,但如何面對中與西、古與今的矛盾在近代就開始擺在中國學者面前,一些優秀的中國學者開始意識到在世界化的進程中如何亮出自己的民族品牌,在小說創作理論和實踐之間找到較好的結合,始終保持理論開放的活力和創造的潛能,促進小說創作的繁榮。可以說,中國小說創作理論始終是本土的,我們沒有理由要求中國小說創作理論要循西方模式演進,也沒道理說要固守傳統才是正道,中國小說創作理論從近代開始就在一種矛盾的情態中散發著闡釋中國自己的小說創作實踐的能力和創造熱情,這個意義不僅是對近代的,也是對現代的,對當代的。 ① 魯迅:《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② 羅燁:《醉翁談錄》,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③ 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1—3),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1993年版,第1147頁。 ④ 所引數字據《中國通俗小說總目錄提要》,江蘇省社科院清小說研究中心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