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崛起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近代轉(zhuǎn)型——以昆曲的文化角色為背景
傅謹
【內(nèi)容提要】 19世紀中葉誕生的京劇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重要表征之一。它是“地方戲時代”出現(xiàn)的最重要的劇種,是雅文化在中國文化整體中漸趨衰落的時代變革的產(chǎn)物。相對于超越了特定地域?qū)徝廊の兜睦デ裕嗟厥翘囟ǖ赜蛭幕漠a(chǎn)物;相對于昆曲所代表的文人士大夫趣味,它更接近于底層和民間的趣味,京劇的劇目系統(tǒng)更充分體現(xiàn)出其歷史敘述的民間性或曰草根特性。 【關(guān)鍵詞】 京劇 昆曲 地方戲時代 花雅之爭
京劇是戲曲三百多個劇種里最重要的劇種之一,在中國戲劇領(lǐng)域有著特殊地位。從19世紀中葉以來,京劇就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重要表征之一。京劇的誕生與發(fā)展過程是近代以來中國戲劇發(fā)展的范本,京劇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關(guān)系體現(xiàn)了中國文化傳統(tǒng)明清以降發(fā)展演變的關(guān)鍵脈絡。解讀京劇的歷史文化內(nèi)涵,對于解讀中國表演藝術(shù)的發(fā)展及其傳播,對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內(nèi)在構(gòu)成和近代轉(zhuǎn)型,都具有重要和典型的意義。 一 京劇誕生于清中葉的北京,承接宋元以來業(yè)已歷經(jīng)數(shù)百年的中國戲曲文化之流,是在中國戲曲發(fā)展史的所謂“地方戲時代”出現(xiàn)的許多劇種之一。和這一時代出現(xiàn)的大量地方劇種一樣,它的出現(xiàn)并不是從宋元以來以戲文與雜劇為主體的戲曲歷史的簡單延伸,或者說,它并不僅僅是宋元南戲、元雜劇以及明清傳奇的地方化身或變種。在戲曲史上,京劇的出現(xiàn)意味著戲曲文化領(lǐng)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這一重要變化的內(nèi)涵和背景十分復雜,這種復雜性,主要源于它所處的特殊的政治文化與社會背景。 日本學者波多野乾一著《京劇二百年之歷史》指“三慶、四喜、春臺、和春四班,以乾隆二十五年入于北京,余竊以此為‘皮黃紀元’之年”①。姑且不論其中“乾隆二十五年”為“乾隆五十五年”(1790)之誤,今人將“紀念徽班進京二百周年”視同為紀念京劇誕生二百周年,實與該書有直接關(guān)系,即以乾隆五十五年徽班進京為京劇誕生的標志。徽班進京是京劇發(fā)展進程中的重大事件,但徽班進京不等于京劇誕生,而且離京劇誕生還有相當一段距離,這已經(jīng)是學術(shù)界的共識。但是,徽班進京這一事件本身仍值得特別注意,它的藝術(shù)學含義,更準確地說,多個徽班相繼進京并且在北京這座作為國家政治中心的城市里立足發(fā)展的藝術(shù)學含義,仍值得發(fā)掘。 中國戲劇進入“地方戲時代”的背景,是中國文化整體大變革時代的來臨,徽班之所以能夠進入京城演出并且在北京站穩(wěn)腳跟,贏得市場與觀眾的認可,進而催生出京劇,就是這一時代變革的突出呈現(xiàn)。這個大變革時代的實質(zhì),是漢代以來大一統(tǒng)的文化格局逐漸讓位于更加錯綜復雜的新的多元文化格局。秦漢以來迄至明清,中央集權(quán)的政治格局雖然少有變動,但是中國的文化格局,因南宋覆亡發(fā)生了深刻變化,宋元之交是其重要拐點。其重大變化之一,就是隨著文人社會身份的日益邊緣化,千百年來充分體現(xiàn)中國文化成就、并且成為文化傳統(tǒng)之主干的雅文化,在文化領(lǐng)域內(nèi),尤其是在中國廣闊的政治管制區(qū)域內(nèi)的文化影響力逐漸下降,甚至喪失了文化領(lǐng)域的主導能力,構(gòu)成俗文化主干的地方文化因此獲得了廣泛滋生并且迅速發(fā)育的機會。 中國文化傳統(tǒng)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的單一體,它包含了不同的社會與文化階層,不僅可以區(qū)隔為所謂的“大傳統(tǒng)”與“小傳統(tǒng)”,還可以更細化地分割為三個組成部分,那就是文人士大夫文化、宮廷文化和民間文化。這樣的三分法之所以成立,是由于歷代朝廷所代表的社會上層以及文人士大夫所倡導與堅守的文化價值和美學趣味,與民間倫理道德以及審美取向大異其趣,而宮廷的皇家貴胄所代表的文化取向,包括其美學趣味,與文人士大夫的價值取向也并不是始終且完全重合的。 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這三大組成部分,在不同時代的地位與影響力并不相同。中華民族的以文人為主要承載者的雅文化傳統(tǒng)從漢代以來一直未曾中斷,雅文化傳統(tǒng)本身在社會上的地位以及雅文化在中國廣大地區(qū)的影響力卻并非亙古不變。從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以來,文人士大夫就已經(jīng)形成了他們相對獨立于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而且在幾乎所有時代,文人士大夫都自認為是中華文明與文化傳承的主要載體。然而在不同時代,他們的社會地位并非都與其文化地位相稱,或者說,他們與統(tǒng)治階層之間的關(guān)系,時而密切時而疏離。如同秦始皇時代的“焚書坑儒”,官方主導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與文人士大夫主導的文化價值觀之間的沖突經(jīng)常出現(xiàn)。像兩宋年間那樣文人擁有極高的社會地位,因而文人士大夫的文化理念成為社會的核心價值,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現(xiàn)象,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盡管不是特例,但也并不多見。南宋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文人掌握社會主流話語權(quán)的最后一個時代。如果說兩宋的文化格局在金代政權(quán)統(tǒng)治的區(qū)域內(nèi)仍然勉強地延續(xù)著,那么,蒙元時代來臨后,文化人的地位就迅速跌落到了秦始皇時代以來的又一個低谷。兩宋時代文人文化地位與社會地位相互映襯的景象,從元代開始崩潰。即使蒙元的統(tǒng)治很快結(jié)束,流寇出身的朱元璋所建立的明代政權(quán),對于文人的態(tài)度依然曖昧,顯然無意于重建文人在社會中的主體地位。清朝是滿族入主中華,清初的統(tǒng)治者對于他們是否應該接受漢文化的傳統(tǒng)價值觀念并以之統(tǒng)治國家,持有強烈的保留態(tài)度。盡管在他們的統(tǒng)治地位確立之后,也給予以漢族的文人士大夫為主要載體的中華文明傳統(tǒng)一定程度的尊重,漢族文人的地位卻始終受到民族身份的明確限制。因此,宋元之交之后,文人士大夫階層在文化上的獨立性、尤其是他們與宮廷文化的分離漸漸開始明朗化。 就戲劇而言,文人的推舉、民眾的喜愛、官府的倡導,三者之間一直是既有關(guān)聯(lián),又有疏離。如同王芷章所說:“歷來樂官所典,為廟堂之樂,良輔所制,為雅士之樂,而元人弦索與清代亂彈,斯乃民間之樂也。”②這段話最清晰地闡明了藝術(shù)——戲劇是其中的核心組成部分——領(lǐng)域內(nèi)分別對應于中國文化三個組成部分的不同取向。然而,至少在明中葉前后,這三者之間若即若離的關(guān)系,對兩漢以來以文人為中心的文化秩序形成的挑戰(zhàn)仍相對有限。昆曲一經(jīng)出現(xiàn)就傳播到各地,被作為一個整體的文人階層所廣泛接受,并且獲得了無可比擬的文化地位,而文人的肯定以及廣泛的參與,對于整個明代的社會風尚的深刻影響,都說明雖然文人的社會地位已經(jīng)不如往常,至少在戲劇領(lǐng)域內(nèi),以文人趣味為中心的文化秩序,依然存在并且能夠找到它特有的表現(xiàn)方式。 京劇誕生的意義卻與此不同。京劇非但不是這種已有秩序的產(chǎn)物,更意味著對這一秩序的顛覆。昆曲一經(jīng)出現(xiàn),就迅速傳播到各地并且在戲劇藝術(shù)領(lǐng)域普遍獲得了至高無上的美學地位,昆曲所代表的美學趣味雖然明顯是南方的,尤其是江南地區(qū)的,但是其文化身份卻并不屬于一時一地,它凝聚了中國廣大地區(qū)文人的美學追求以及藝術(shù)創(chuàng)造。正是由于它是文人雅趣的典范,才具有極強的覆蓋能力,有得到廣泛傳播的可能,并且在傳播過程中,基本保持著它在美學上的內(nèi)在的一致性。更重要的一點在于,昆曲并不是吳中地區(qū)的“地方戲”,至少它從未被視為吳中地區(qū)的“地方戲”,它雖與昆山地區(qū)的方言和聲腔昆山腔有承繼關(guān)系,昆曲——無論就其文學性而言,還是就其音樂性而言——之所以成為雅文化的象征,就是因為它不是基于昆山一地民眾的美學趣味生成的。相比之下,各地的地方戲就不是如此。嚴格地說,除了昆曲以外,其他所有劇種——包括京劇在內(nèi)——都只能稱為“地方戲”,因為除昆曲之外的所有劇種,都是基于某種地方趣味發(fā)展而來的。更局限地說,京劇幾乎在所有方面都與昆曲構(gòu)成鮮明的對峙——就其藝術(shù)上的地域特色而言,京劇無疑更接近于北方而不是江南,它在音樂聲腔體系上,是梆子亂彈系統(tǒng)在其流變過程中不斷與各地的方言土語相結(jié)合而衍生出的地方聲腔中的一種,由源于湖廣、安徽加上北京本地的諸多地方聲腔發(fā)展演變而來,既為特定地域的民眾所喜愛,同時也充分體現(xiàn)著這一特定地區(qū)的美學趣味。京劇是地方的,它的出現(xiàn)與繁榮,是地方戲相對于昆曲而言不斷發(fā)展壯大的最重要的表征之一,同時也正是在戲劇上由文人的美學趣味一統(tǒng)天下的文化秩序趨于解體的最重要的表征之一。出現(xiàn)在明清之際戲劇領(lǐng)域的“諸腔雜陳”現(xiàn)象,與文人的社會地位下降以及雅文化統(tǒng)治地位的動搖不無關(guān)系,這一點正需要我們?nèi)ダ迩濉U怯捎诖硌盼幕奈娜耸看蠓虻纳鐣匚怀粮〔欢ǎ晌娜苏紦?jù)主導地位的大一統(tǒng)的美學趣味開始讓位于更平民化也更多元化的情感表達。我們在明清兩代看到的現(xiàn)象就是,至少在藝術(shù)上,尤其是在最集中地表現(xiàn)了中華民族在音樂和表演藝術(shù)方面的美學追求的戲劇領(lǐng)域,因為文人趣味長期的壟斷地位的動搖,地方性藝術(shù)的生長空間得到了更多拓展的機會。在某種意義上,包括京劇在內(nèi)的諸多地方劇種,是在中國文人的審美趣味從主流漸漸趨于邊緣的特殊時代背景下出現(xiàn)的,而這些被視為“地方戲”的劇種不僅在演出市場上輕而易舉地獲得了成功,更因受到權(quán)貴階層的支持推動而逐漸改變著曾經(jīng)低微的文化身份。 這一趨勢在20世紀進一步加劇,恰恰是由于文人崇尚的雅文化傳統(tǒng)在20世紀遭遇滅頂之災,京劇達到了它的全盛時期,而且,有相當多比京劇更具草根性的地方劇種,在20世紀堂而皇之地進入主流社會,繼京劇之后書寫它們的輝煌。凡此種種,文化的解釋比起任何其他的解釋,都更能說明問題。 二 近代中國文化本身的內(nèi)在秩序所發(fā)生的深刻變化與轉(zhuǎn)型,更清晰地體現(xiàn)在以京劇為代表的大量地方戲劇種相對于昆曲而言的蓬勃生長的命運上。 有著悠久歷史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之所以選擇了具有明顯江南風格的昆曲作為她的文化象征,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南宋以來,江南成為中國的文化中心,尤其成為雅文化的中心。此后,這一中心從未偏移,這是以吳文化為基本特征的昆曲在明代勃興的根本原因;而昆曲音樂細膩到可以稱之為“水磨調(diào)”,文辭以風雅綺麗為要義,文學與音樂之間的珠聯(lián)璧合更是其顯著特點。它是中華文明長期以來對文人雅韻的特殊理解與定義的結(jié)晶。 一種文化對文明雅致的追求和定義,需要漫長的時間積累,并且需要通過無數(shù)具有較高文化和藝術(shù)水平的經(jīng)典作品,得以具象的表現(xiàn)。它需要基于日常語言之上的文學的創(chuàng)造與嫻熟運用,以及包括音樂、美術(shù)、舞蹈等在內(nèi)的不同情感表現(xiàn)模式的建構(gòu)乃至于成熟,當文明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時更可能出現(xiàn)以多門類藝術(shù)綜合協(xié)調(diào)而孕育產(chǎn)生的戲劇。只有藝術(shù)發(fā)展到相當?shù)某潭龋瑢徝廊の恫艜呌诰⒑图毮仯把胖隆辈庞锌赡艹蔀檫@一文明的美學取向。各種不同民族對于“雅致”的內(nèi)涵理解殊異,但“雅致”之成為一個文化圈內(nèi)占據(jù)主導位置的文化與美學追求,多少可以視為這一文明已經(jīng)成熟的標志。因此,文明的差異既有相對性,也有可比性。其中,文化經(jīng)典的累積程度和成熟戲劇的出現(xiàn),就是可以相比并且可用來判斷不同民族之文明發(fā)育程度差異的重要指標。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如同南宋末年以其強大的軍事實力摧枯拉朽般地打敗了南宋的蒙元一樣,我們恐怕很難說明來自東北的滿清占領(lǐng)者,在文明的發(fā)展程度上已經(jīng)足以和漢族相比擬。我們至少可以肯定,無論是蒙元還是滿清,在其文明發(fā)育的歷史上,都未曾擁有可與漢族相比擬的豐富的文學和藝術(shù)積累,更沒有做好在其文化圈內(nèi)孕育和發(fā)展出成熟戲劇的文化準備。而相對于滿清,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文明圈內(nèi),已經(jīng)擁有在宋戲文和元雜劇基礎(chǔ)上發(fā)展了數(shù)百年之久的、可以最典型地用于定義“雅致”的絲竹悠揚的昆曲。 因此,昆曲對于明代的文人,不僅是一個劇種、一種表演樣式,更是文化靈魂所在,是用以標舉文化理想和整合文化秩序的最重要的藝術(shù)。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看京劇的興盛和昆曲相對而言的衰落,就不難理解,這不僅僅是重大的戲劇事件,也是重大的文化事件。 京劇誕生的時代,昆曲已經(jīng)處于不無尷尬的地位。明代中葉以來,充分代表文人趣味的昆曲臻于高度成熟,除了音樂上和表演上達到了中國表演藝術(shù)的高峰之外,在文學上,也由于大量杰出的文人參與劇本創(chuàng)作而取得了極高的成就。但是,昆曲在獲得它的崇高地位的同時,作為一門表演藝術(shù)卻并沒有在市場上得到充分認可,那正是由于昆曲所代表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情趣,它是千百年來雅文化傳統(tǒng)在表演藝術(shù)領(lǐng)域里最集中、最典型的結(jié)晶,而在演出市場上,民眾比起文人士大夫群體來,卻是更具有發(fā)言權(quán)或話語權(quán)的群體。因此,就在昆曲在藝術(shù)上臻于極盛的同時,“花雅之爭”隨之而起。作為文人雅事的戲劇與作為市民娛樂的戲劇之間的分野,決定了昆曲在濃縮了文人趣味的同時,卻與民眾趣味漸行漸遠,越來越成為文人以及少數(shù)追逐風雅的富豪人家廳堂里玩味的“小眾”藝術(shù),雖然高雅,卻被鄉(xiāng)野民眾乃至于都市里的普通市民敬而遠之。即使在昆曲的誕生地、明清之際最重要的商業(yè)中心揚州一帶,各種所謂的“俗謳”,即各種地方戲,卻成為更受歡迎的戲劇樣式。因此,昆曲雖然名滿天下,在京城卻立足艱難,出現(xiàn)這樣的現(xiàn)象并不奇怪。 無論如何,京劇劇本的唱詞以七言或十言、上下句齊言對偶的詩贊體為主,戲劇化表達方式接續(xù)的是從唐代的說書講史到明清彈詞等等民間敘事文學的文體,它與運用格調(diào)錯落有致的長短句、接續(xù)唐詩宋詞的文學化情感表達方式的昆曲,其雅俗之間的區(qū)隔涇渭分明。戲曲的音樂與文辭之間具有高度的相關(guān)性。適宜于演唱京劇文辭的是西皮二黃為主體的板腔體音樂,它與昆曲從劇本創(chuàng)作階段就將每個字的音韻化入曲調(diào)的曲牌體唱腔之間的雅俗之分,同樣也無可懷疑。用板腔體演唱的京劇的伴奏樂器,更擅長于營造豪放而熱烈的氣氛,文場剛烈,武場喧鬧,當然不似昆曲以笛子、小鑼為文武場領(lǐng)銜的樂隊那樣文質(zhì)彬彬。京劇能夠在演出市場上吸引比昆曲更多的受眾并不值得大驚小怪,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中葉之后,尤其是在近現(xiàn)代歷史上,事實上京劇漸漸取代昆曲而扮演中國戲劇代言人的角色,甚至成為中國戲劇的藝術(shù)成就的象征,它的文化與藝術(shù)地位,已經(jīng)遠遠不能用花部或民間俗文化的流傳風行加以描述。 眾所周知,京劇的繁榮與發(fā)展,與清朝歷代帝后的偏愛與鼓勵息息相關(guān)。有清一代,除偶爾的幾個時段外,宮廷內(nèi)的戲劇演出一直極為興盛。清廷演劇對于京城戲劇的影響,乃至于對中國戲劇整體上的影響,相當復雜且耐人尋味。 在京劇誕生的時代,滿清王朝在中國的統(tǒng)治已經(jīng)基本穩(wěn)定。八旗貴族在北京的顯赫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左右著北京的獨特城市風格。北京作為國家的政治中心,固然集中了大量文人出身的官吏,但是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nèi),漢族官員的社會地位與出身滿清八旗的貴族的社會地位,完全無法相提并論。然而,我們還需要看到另一點,滿清貴族雖然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在文化與美學上的成就卻根本無法與文人相比。一方面,那些出身于仕林熟讀詩書的漢族文官,仍然保持著他們作為精神貴族的矜持與驕傲,這樣的矜持與驕傲在清初曾經(jīng)表現(xiàn)為強大的民族主義情緒,終其滿清一代從未完全消退,但是無可回避的事實是,在另一方面,這批精神上的貴族在現(xiàn)實生活中已喪失了社會支配地位,他們曾經(jīng)擁有的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也漸漸演變成為一種表象或曰假象。相反,正由于滿清貴族的社會地位與影響力無可比擬地高于同時居住于北京城的其他社會階層與群體,他們的文化需求與審美趣味,當然會得到更多充分表達的機會,這種表達,與京劇的誕生發(fā)展之間的關(guān)系,尤為密切。
展.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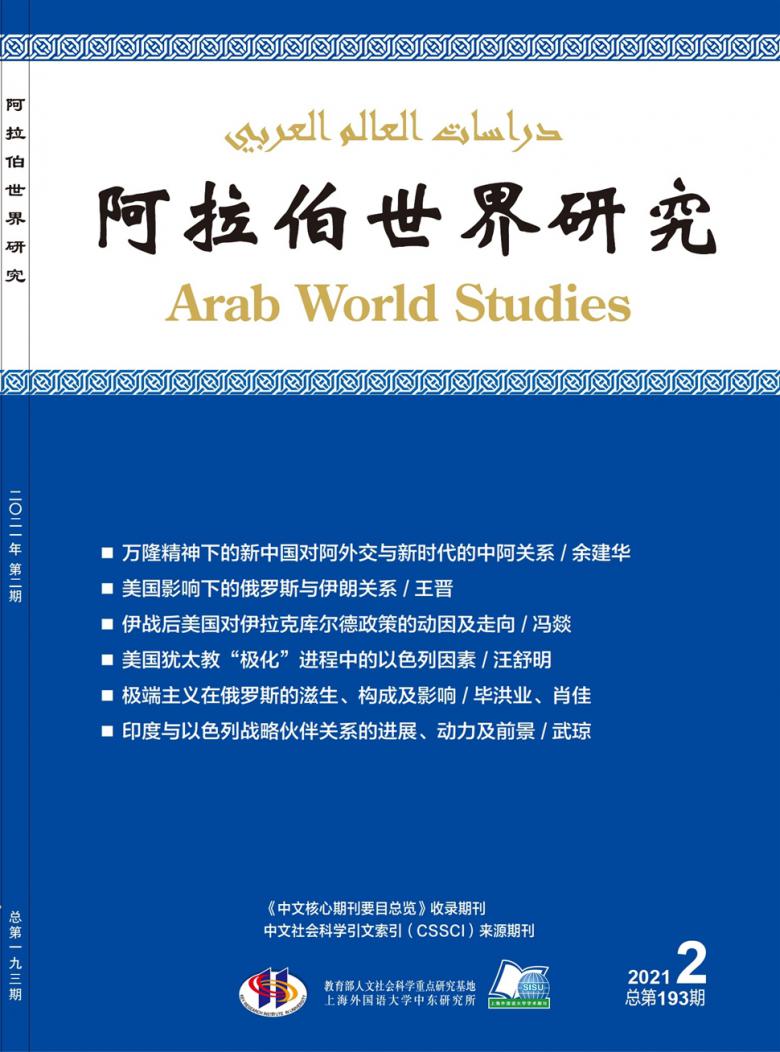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