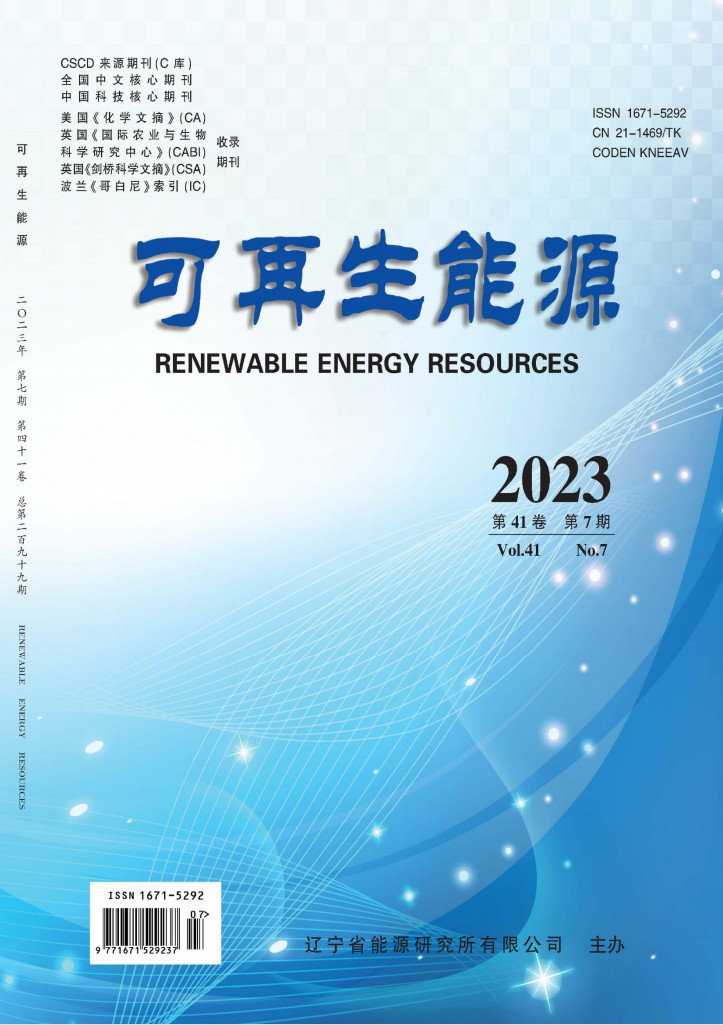關于水粉畫《金訓華》創作秘聞
佚名
1969年冬,我與陳逸飛以“逸中”筆名,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志12期上首次發表了水粉畫《金訓華》。40年來,我們沒有向媒體談過此畫創作的過程。不少媒體有關此事的報道,與實際情況出入較大,就連一些中外美術史的研究專著和地方志也有不少錯訛。今借《上海灘》一角,將當年的事實真相表述如下,以正視聽。 1968年12月起,我被《解放日報》美術編輯洪廣文從崇明縣前進農場借調到報社,起先是為報社的兩幢大樓畫毛主席像,接著又畫了禮堂、走廊和各樓梯口的領袖像,后來就讓我負責每日報紙版面的插圖和配畫。晚上與陸炳麟等一起值夜班,一旦有新的最高指示發表,就要在—兩個小時之內配上一幅主題圖,往往要趕畫到早上四五點鐘。馬上制版見報。 我參加了《金訓華》組畫創作組 1969年9月,《解放日報》記者龔心瀚從黑龍江遜克縣兵團采訪了金訓華事跡回來,寫了重點報道。報社領導趙元三極為重視,批示要求各部門配合重點報道。洪廣文決定出整版的美術畫刊,并與我商量成立創作組,我推薦陳逸飛,因為他是我在少年宮的同學。老洪當即發函邀請陳逸飛、蔣昌一、張嵩祖、秦大虎、丁榮魁與我六人組成創作小組,在報社集中創作。同時,還請工人詩人王森、張鴻喜配寫《金訓華道路金燦燦》的詩。 龔心瀚幾次認真地向大家介紹了金訓華的背景資料,講解金訓華奮不顧身搶救國家財產的感人故事。他提供的形象資料,只有一張金訓華的正面報名照。老洪要求我們根據這張照片去想象,然后畫出六幅畫。老洪和我們討論了幾次如何選擇畫面情節和構思,安排了各人的分工。 最后決定由我畫《解放畫刊》領頭的主題畫——《搶救財產》,陳逸飛畫《深夜寫日記》,蔣昌一畫《半夜扣門》,張嵩祖畫版畫《勞動》,秦大虎畫《巡山防火》,丁榮魁畫《學習毛選》。各人雖分工明確,但還是要求群策群力,搞好創作。 當年還沒有彩印的報紙,所以我們就用黑白兩種廣告色畫黑白水粉畫。畫都不大,只有25×40厘米左右,使用的是白卡紙。 我與陳逸飛從小就認識了。當年他23歲,我22歲,都是浙江鎮海人。我們都覺得,能為黨報創作發表作品,機會很難得,所以大家都很謹慎。6個人在漢口路274號二樓一間不到十五平方的房間里畫畫,雖然擁擠,但有說有笑,非常融洽。 我吸取大家的意見三易畫稿 老洪很重視領頭主題頤的效果,一直在我邊上觀察。第二天,我畫完了第一稿后,就進行集體討論。張嵩祖認為我畫的金訓華抱著木頭,給人感覺像落水逃生,而且戴了帽子也不好。于是,我畫了第二稿。大家認為這一稿中的金訓華在游泳時人太直,看起來洪水顯得很淺。后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著名宣傳畫畫家哈瓊文見到這兩幅草稿,認為第二稿與后來發表的第三稿已非常接近。 兩天后,我畫出了第三稿,畫中的金訓華脫了帽子,姿勢改成左臂向上,高呼同伴:“跟我來!”集體討論中,大家對每人的畫都提了意見。老洪再三強調:一切為了出效果,分工不分家,領頭畫是畫刊的“報眼”,很重要,要大家都出力,提高畫的質量。當時沒人在意名利,登報也不登作者名字,更沒有稿費,互相改畫是常事。老洪希望加強領頭主題畫的效果,請蔣昌一來幫助我提高。蔣昌一推給陳逸飛來協助,蔣則坐在一邊觀察,提出不少修改意見。 陳逸飛是我們六個人中畫得最好的。此前不久,我還在淮海路上見他畫整堵墻的毛主席像。現由他來協助,我非常高興。逸飛為人謙和,在拿筆修改前,一再問我:“這樣改,行不行?”他提出讓金訓華眉頭鎖得更緊,嘴張得更大些,伸出的五指改為后三指合并。蔣昌一也提出把濕衣服加深,右邊的浪花減弱些,木頭減小,推遠。就這樣,我們互相商量,輪替改著、畫著,直到大家滿意。討論陳逸飛畫的《寫日記》畫時,大家認為油燈太亮,會影響同伴睡覺,他就在油燈上加了張穿孔的紙,遮一遮。秦大虎也幫丁榮魁改了畫中人的大衣。大家合作得很愉快,沒有任何功利心。 四天后,各人的畫稿都完成了,由老洪拿去排版、送審。完成了畫稿,大家都很高興。騎自行車回家時,我與逸飛特意到山東路攤頭上吃了碗餛飩,還到浙江電影院看了場電影。第二天,畫刊見報,我與夜班實習編輯許根榮,一起到評報欄前,看見上面已寫了不少對領頭主題畫的好評,同時見到我的畫中多了三條白色水紋線,猜想那一定是老洪連夜加上去的。 “旗手”看中了《金訓華》主題畫 傍晚,老洪急匆匆找我,說中央首長看了《金訓華》主題畫,很重視,現在報社領導要與你和陳逸飛談話。我和逸飛來到總編輯辦公室。趙元三總編輯問了畫的創作過程,還看了三張變體圖,說了句“三易其稿啊”。第二天,市革委會徐景賢、王少庸等找我們談話。市寫作組的朱永嘉還在報社制版房對我與陳逸飛說:你們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這幅畫受到江青同志(當年被稱為“旗手”)的肯定,要在《紅旗》雜志上發表。今天姚文元已三次來過電話、電報,要3H的彩色反轉片送中央的《紅旗》雜志發表。但沒想到原畫只是黑白的。你們不要離開,估計上面還要你們進一步畫出彩色稿。 果然,很快上邊來了通知,要我們趕畫彩色稿。我與陳逸飛一起到上海中華印刷廠,和工廠領導開會討論,如何把25×40厘米的黑白原稿改成彩色宣傳畫。此時已是下午兩點。 我和逸飛坐著,靜靜地聽大家提的各種方案。因為要放大原黑白畫成為彩色畫而不走樣,兩人同時上板畫色彩稿又不可能,很有難度。大家一時都很為難。哈瓊文很有經驗,也極聰明,他提出了當時的最佳方案。他說:先把原畫拍照制成版,放大在瑞典進口的水彩畫紙上,手工打印成多張有各種層次的淡棕色的畫稿,再分別由徐純中、陳逸飛按原畫輪廓上水粉顏色。畫完后將這兩張彩色稿送到北京,請領導選擇、決定發表哪張畫稿。哈瓊文還說:“不要畫太大,對開足夠,印刷時可略為放大些。” 傍晚時,才確定下方案。大家都集中在中華印刷廠,連夜趕畫稿。很快就請專業師傅手工制版,打印了二十多張不同深淺的棕色畫稿,掛在車間的墻上,由我們去選擇自己喜歡的棕色稿。然后我和陳逸飛到各自的房間去畫,用水粉上色。哈瓊文認為這樣分別畫,可以互不干擾,更好地表現主題和自己的想法。 哈瓊文等人足足陪了我們一夜,他不時在我和逸飛的房間里來回地走動,指導我們如何達到出版印刷上的要求。我們整整地畫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四點,才完成了上色稿。最后,又請美術編輯陸壘根手寫了美術字紅色標題:“毛主席的紅衛兵——金訓華”,附在畫后。隨即有車將畫稿送到市里,再由飛機直送北京。陳逸飛畫的上色稿很像油畫,色彩豐富。我 上色稿比較忠于原畫,只是把畫幅拉長了些,人物的頭部放到了畫面的中央。我對陳逸飛說:“你畫得好,上頭肯定是要選你的畫了。” 誰知第二天,北京送回彩色原稿,并傳達了江青的指示:發表徐純中的上色稿,陳逸飛的畫不用。我很驚奇,不知他們是用什么標準來選畫的。逸飛不滿地輕輕對我說:“這些人到底懂不懂畫?”哈瓊文輕輕拍了拍陳逸飛的肩表示安慰。接著還傳達了上面的指示說,為了宣傳好金訓華,畫作發表時作者不用真名,在我們兩人名字中各取一個字作筆名。我們討論過用“純逸”或“純飛”。后來徐景賢向姚文元電話匯報時,姚傳達了江青的話:“我看用‘逸中’吧!”于是《紅旗》雜志在刊發這幅畫時,署的就是“逸中”筆名。 《紅旗》發表了水粉畫《金訓華》 水粉畫《金訓華》是發表在當年第12期《紅旗》雜志的封底上的。這是《紅旗》雜志創辦以來首次發表繪畫作品。該期雜志上,還發表了評論員文章,說:“作者在三大革命斗爭與火熱的生活中,努力感受與鍛煉,才畫出了歌頌英雄的好作品。”文章號召全國藝術工作者向我們學習。不久,全國所有的報紙、雜志都轉載了此畫。《金訓華》宣傳畫迅速貼滿了全國,前后印制了四千多萬張。許多城市還在街口畫了大幅《金訓華》的宣傳畫。 《金訓華》發表后,對我的畫友們很有影響。當時,我的那位在江西插隊的師弟陳丹青對我說:他在農村翻了好幾座大山,走了幾十里路,見山凹凹里的一戶農家門上貼了一張金訓華的畫,就像門神似的。他馬上想到我這個大師兄,感到只有堅持畫下去,才有出路。 《金訓華》一畫,被捧為繼《毛主席去安源》之后的“樣板畫”,被印成特種郵票和各種書的封面,也被做成瓷瓶、屏風、刺繡、木刻、玉雕等工藝品,甚至還排了畫中造型的朗誦劇。國外不少報刊也轉載了這幅畫。法國共產黨和阿爾巴尼亞的美術團體還寄來獎狀。逸飛與我都被“一夜成名”的浪潮包圍了。我們前后參加了多次宣講團,兩人共同作過幾十次報告,反復講述我們受感動和合作的故事。我們都難以理解這突如其來的巨大變化,只覺得戰戰兢兢。陳逸飛的爸爸是厚道人,拉著我的手鄭重地對我們說:“夠了,人爬得越高,跌得越重。” 我拒絕了江青為我改名字 不久,陳逸飛入了黨,擔任了油雕室負責人和文藝界領導,還被評為標兵。我倆常一起接待外賓,接待過法國共產黨書記儒爾蓋、印尼領導人等。 我參加了宴會后,還是回崇明農場種地。過了好多年后,逸飛在香港對張正、梁家輝、劉德華等人說:“《金訓華》一畫對我的一生影響是巨大的。”不久,我被調到國務院文化組。但在討論我是否當選“四屆人大”代表時,很多人對我說過的一句話很有意見。我曾說:“江青看過全國很多畫,怎么像‘唐伯虎點秋香’似的,居然點中了《金訓華》這幅畫。”我當時率真幼稚,大概也是從小聽了太多蘇州評彈,不知深淺吧。 江青曾認為我名字起得不好,要為我改名。我說:我爸起我這名字,意思是“純粹的中國人”。江青聽了不語,過后說:“就這樣吧,不改了。” 我調北京一年多,跟國畫大師關山月、方增先、楊之光、周思聰、盧沉等人學畫國畫,也參加“批黑畫展”工作。我把要處理掉的大畫家作品,一張一張地送還到吳作人、李可染、李苦禪等家中,還拜他們為師。后來給江青、王曼恬知道了,說我與“老朽混在一起”,就把我送回了上海。 由此,逸飛與我有了更多的交往,常常在油雕室(現“新錦江”的地址上)他的小閣樓里聽古典音樂,天南地北地暢談到深夜。他有深厚的藝術修養,精通古典音樂。他說只有哼得出旋律的人,才算懂音樂。他給我解釋什么是“賦格”,什么是“卡農”。 我們并沒有認為《金訓華》一畫在藝術上有什么太大的成就,只是時代把畫和我們推到了前沿。我們前后畫過六張金訓華畫(三張黑白水粉,兩張彩色水粉畫,一張油畫),沒拿過一分錢的稿費。我們覺得從小下功夫學畫畫,今日能得到社會肯定,就是自己最大的滿足了。 不久,中國歷史博物館通知我們畫一張大幅油畫《金訓華》,作為博物館收藏品。陳逸飛認為這是糾正以前畫的不夠好的機會來了,要“扳”回藝術上的“印象分”。他鼓勵我說,一定要畫出真正的水平。我們從圖書館、美協借了不少俄國畫家艾瓦爾素夫斯基的海浪畫來做參考,并以我作姿勢參考拍照。陳逸飛信心很足,說這次要完成“為內行人都稱贊”的作品。 在油雕室畫這幅油畫的過程中,俞云階、王大進、張隆基、魏景山、邱瑞敏、夏葆元、秦大虎都給我們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見。畫好后,送北京歷史博物館收藏至今。 “貧下中農”始于何時 “貧下中農”一詞,在20世紀60至70年代可謂家喻戶曉,它表明一個人的“階級成分”,該詞最早始于何時呢? 1957年7月31日,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中指出:“這里談一個社員成分問題。我以為在目前一兩年內,在一切合作社還在開始推廣或者推廣不久的地區,即日前的大多數地區,應當是:(1)貧農,(2)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3)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這幾部分人中間的積極分子,讓他們首先組織起來。”這是在黨的重要文獻中首次出現“下中農”這個“階級成分”。1955年9月7日,《農業合作化必須依靠黨員團員和貧農下中農》文件發布后,“貧下中農”一詞在各新聞媒體頻繁出現,“文革”時期達到了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