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藝美術保護與發(fā)展中的文化矛盾
邱春林
本著基本的生存需要,直立行走的人利用雙手來造物。由簡單造物發(fā)展到工藝美術,既反映社會文化的形成過程,也顯示社會文化對人的行為的反作用。文化包括族群或社會團體共同享有的和習得的行為模式、信念及感情。生活中常見的工藝美術品,既是技術的產物,也是觀念、習俗、制度等文化的“凝結”物。而不同族群所創(chuàng)造的工藝美術因選材、設計、加工、使用方式的不同而表現(xiàn)出鮮明的文化差異。 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工藝美術行業(yè)承載著深厚的中華文化,其生產和組織形式有多種,可分為民俗性質的工藝美術、官辦作坊的工藝美術、民辦作坊的工藝美術和現(xiàn)代產業(yè)化的工藝美術。民間工藝美術作為民俗、民間信仰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特點,市場化程度較低。封建時代官辦作坊的工藝美術服務于宮廷和上層貴族,用料昂貴,工藝精細,適用人群小。民辦工藝美術作坊屬于傳統(tǒng)手工業(yè)或農業(yè)中的副業(yè)生產形式,一般以前店后坊的形式面向商品市場生產普通人群所需的日用品,它的適用面最廣。鴉片戰(zhàn)爭以后,官辦工藝美術逐漸式微。新中國成立后,私營工藝美術作坊經過公私合營等方式的改造,形成了有一定規(guī)模的國營或集體工藝美術企業(yè)。改革開放后,絕大多數(shù)國營和集體工藝美術企業(yè)重被改制,化整為零,個體和私營的手工作坊形式再度興盛。與此同時,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涌現(xiàn)出了具有現(xiàn)代企業(yè)性質的工藝美術企業(yè)。 在過去的百余年里,工藝美術從生產經營方式到產品,它所發(fā)生的轉變是深刻的。一些誕生于農耕文明時代的民間工藝美術紛紛走出鄉(xiāng)村,積極融入現(xiàn)代文化元素;一些有悠久歷史的家族式工藝美術作坊大膽融合現(xiàn)代技術和現(xiàn)代經營管理思想,在數(shù)年間擴張為大工業(yè)企業(yè);而東南沿海城市則興起著現(xiàn)代首飾和現(xiàn)代禮品的產業(yè)群,許多洋味十足的禮品和裝飾物占領著普通百姓的消費市場,塑造著新的民風民俗。工藝美術行業(yè)內部的變化更新著我們日常生活的面貌,只要環(huán)視左右,就會發(fā)出“時代變了”的感嘆!年輕一代的衣、食、住、行與上一輩相比變化明顯。如今,即使在最偏遠的鄉(xiāng)村,現(xiàn)代文明新風也在沖擊著人們原本習以為常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態(tài)度。 經濟和技術的一體化以及文化的全球化既給中國傳統(tǒng)工藝美術的產業(yè)化創(chuàng)造了機遇,也給傳統(tǒng)物質和非物質文化的保護工作帶來了難題。許多有久遠傳承史的工藝美術種類遭遇市場淘汰而面臨消亡。在近百年里,技藝失傳或瀕臨失傳的傳統(tǒng)工藝美術品類難計其數(shù),有人因此發(fā)出傳統(tǒng)工藝美術是“夕陽”藝術的感嘆!技術、資本和文化的力量似無形的巨手推動著中國社會的文化變遷,為應對這種變遷造成的傳統(tǒng)文化特質的丟失,1997年國務院頒布了《傳統(tǒng)工藝美術保護條例》,此后,全國多數(shù)省市結合當?shù)貙嶋H情況也紛紛制定了保護條例和具體實施細則。2006年7月,經過實地調研南方四省一市(粵、閩、浙、寧、滬)工藝美術的保護和發(fā)展狀況以及分析其他省市的上報材料,筆者認為,這些年全國各省市對工藝美術的保護和發(fā)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對工藝美術在全球化時代遇到的文化矛盾認識不足,以至出現(xiàn)保護與發(fā)展上的失衡現(xiàn)象。 一、手工制作與機器生產的矛盾 傳統(tǒng)的工藝美術重視手工技能,手工藝人掌握著設計和加工秘訣,他們全神貫注于一個事物,在一個事物身上花費大量的勞動時間,產品或作品的價值不僅體現(xiàn)在它凝聚著手工藝人的精湛技藝,還體現(xiàn)在它凝聚著手工藝人的驚人毅力。但工藝美術是否必須是純手工制作?半機器生產的、依然保留了傳統(tǒng)工藝美術文化特質的產品是否算工藝美術?技術和工具是否是決定工藝美術本質的東西? 從中國工藝美術發(fā)展史來看,工具的改進始終在發(fā)生,新舊技術的更替也都在盡可能地進行,利用機械輔助人手加工制作工藝美術品古已有之。舊時碾玉用腳踏轉輪,也屬于半機械化,現(xiàn)在使用電動鉆頭更加降低了碾玉工人的勞作強度,縮短了勞動時間。舊時純手工的抽紗刺繡,在上世紀50年代后在剪裁、打樣及洗熨等后處理工序方面整體上實現(xiàn)了機械化;牙雕行業(yè)在機械時代有條件改進雕刻工具,用電動蛇皮鉆代替了手工粗雕部分。當下,走上產業(yè)化之路的工藝美術企業(yè)表現(xiàn)出對人造智能的依賴,大量控制性工具如自動雕刻機、自動化系統(tǒng)和電腦——支持技術被運用到工藝美術產品的設計和生產流程中。 工藝美術重手工技藝,并不排斥以機械之力輔助之。工藝美術在各個發(fā)展階段中,都是那個時代高新科技與先進工藝的集合,無論是瓷器燒造工藝,還是歷史更久遠的玉雕和鑄劍工藝,無不折射出科技和設計水平的發(fā)展進步歷程。許多傳統(tǒng)工藝美術品類之所以能夠綿延數(shù)百年,乃至數(shù)千年,其核心就是與時俱進,不斷進行技術創(chuàng)新。以半自動機械、全自動機械甚至智能化機械取代手工,這是工藝美術歷史發(fā)展的總體趨勢。 盡管在“機械復制時代”工藝美術品被大批量生產后,在藝術韻味上較之純手工制作品有所削弱,卻并沒有改變工藝美術的本質特征。工藝美術本質上依然是“在制作造物品時,將美觀的要求和實用的要求融合為一體,以實現(xiàn)美與用的雙重功用”①。當工藝美術師的雙手部分地被機器解放了出來,與此相關的文化記憶并沒有完全在機器面前消失,他們的設計創(chuàng)新思維反倒成了一種特殊的技藝。福建仙游的木雕工藝師在試制完小樣之后,借助自動控制的雕刻機,可以僅用數(shù)人之力完成高達幾十米的佛像。南京云錦因工序復雜、技術繁難,一度瀕臨失傳,如今借助電腦編程技術,初步實現(xiàn)了圖樣設計的智能化。廣州的骨雕廠設計流水線用以批量生產骨雕作品,卻基本保留了傳統(tǒng)象牙雕的工藝特色。 華美的織錦起源于最簡單的手工編織,精細的制瓷工藝源自粗陋的泥條盤筑,由手工技藝發(fā)展過渡到機械化、智能化,其間既有跳躍性,也有技術發(fā)展的連續(xù)性。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技術體系。純手工時代,所有的技術都是經驗性的,以百工技能的形式體現(xiàn),工序的程式化和手工藝人的感性動作中都貫穿著復雜的技術體系;半機械化時代,許多高新技術已然與手工技藝結合到一起,成為手工與機械相輔相成的技術系統(tǒng)。當代的技術體系與傳統(tǒng)的技術體系之間并非完全斷裂,而是存在文化上的關聯(lián),或者說存在人類經驗的連續(xù)性。 恩伯說:“發(fā)現(xiàn)和發(fā)明是一切文化變遷的根本源泉,它們可以在一個社會的內部產生也可以在外部產生。”②雖然有不少文化人類學學者對L.A.懷特所持的技術決定論抱著質疑態(tài)度③,事實上在信息化時代,誰也不能阻擋高技術向低技術文明區(qū)域的傳播。如今造成導致社會變遷的技術力量以信息控制技術為代表,技術的引進還伴隨著更為復雜的市場經濟體制,日益民主化的社會結構也在促使傳統(tǒng)的社會機制發(fā)生變化。 在全球化時代,要發(fā)展工藝美術行業(yè)不可能完全拒絕現(xiàn)代技術工具;要保護好傳統(tǒng)工藝美術,同樣也不能一味地拒絕現(xiàn)代技術工具。巧妙地讓雙手與機器工具結合起來,讓人腦與電腦結合起來,才能降低成本,才能在市場經濟環(huán)境中生存下去。否則,那種“救濟”式、“輸血”式的保護只是一種保守的文化保護措施,根本無法讓一種瀕臨滅絕的工藝美術煥發(fā)生機。只有那些依然能服務于民眾生活的工藝美術才是有生命力的,也才是參與了當代文化建設的好的工藝美術。 我們應該樂觀地看到,機器生產不可能徹底取代手工制作。在以往任何時代,高尖端的技術發(fā)明都無法覆蓋所有的生產和生活領域。社會文化有分層,技術體系也有分層。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手工藝人的技能所反映出來的藝術品位和個性價值不會在工藝美術行業(yè)中徹底失去位置。 當今一些文化保護工作者過于強調手工技藝的重要性,把它視為“詩意”的存在。其實,手工藝仍然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是現(xiàn)代機器工業(yè)的有益補充,我們不必過度強調它的重要性,甚至用它來抗拒被“妖魔化”了的機器巨子。雖然手工制作與機器生產之間存在著文化沖突,但不能以保護傳統(tǒng)文化之名,拒絕現(xiàn)代技術對傳統(tǒng)產業(yè)的改造,尤其是不能阻止傳統(tǒng)工藝美術產業(yè)化的進程。畢竟社會進步、文化變遷隨時都在發(fā)生,對于促使這一變遷的技術邏輯應該有足夠的尊重。 二、用與美的矛盾 美不僅僅存在于純藝術中,也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經驗中,也就是文化中。杜威的這一思想啟示我們:文化意義上的人造物,都有一種指向美的形式的傾向④。由于藝術與傳統(tǒng)手工技藝以及現(xiàn)代工業(yè)的關系都十分密切,讓人難以從實用技術中劃分出藝術的邊界。威廉姆斯曾用“好的藝術”(fine arts)與“有用的藝術”(useful arts)⑤來區(qū)分日益復雜的藝術現(xiàn)象。這種區(qū)分方法并不是十分有效,因為易給人產生這樣的錯覺:有用的藝術與好品質是天然對立的;好的藝術也必定是徹底擺脫了功利性質。事實上,人類古往今來的絕大多數(shù)藝術行為都不純然是非功利的,今天堂而皇之占據著博物館神圣展示位置的藝術杰作,通常都誕生于普通人的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之中。今天被視為傳世杰作的工藝美術品曾經都是人們的日用器物。 有用之物可細分為生活必需物和特殊裝飾物,工藝美術可大致分為日用工藝美術和欣賞用工藝美術,但不管是哪種性質的工藝美術都兼具“用”與“美”兩種功能。作為收藏品、室內陳設品以及一般裝飾物的工藝美術以審美欣賞為第一功能,同時它可以起到美化環(huán)境、改善人的氣質的作用。日用工藝美術之用主要是滿足人們日常生活所需,其審美的功用是次要的、連屬的。 日用工藝美術和欣賞用工藝美術并不是截然分別的,隨著社會結構和文化的變遷,許多原本是日用的工藝美術逐漸失去了它的實用價值,卻被人們賦予了新的審美價值,演變成以裝飾審美功能為主的欣賞用藝術。如傳統(tǒng)建筑構件上的木雕逐步與建筑物分離,走上人們的案桌,成為獨立的擺件;原本用于插花盛水的瓷瓶,發(fā)展成獨立的陳設瓶;原本用于沏茶的紫砂壺成為櫥窗里的珍玩。工藝美術發(fā)展還潛藏著另一條規(guī)律:當一種工藝美術與其他藝術形式結合達到一定高度之后,原本的實用功能可能被藝術表象掩蓋了,從而造成工藝美術向非功利的轉化。如刺繡與書畫結合、竹編與書畫結合、瓷雕與雕塑結合等等都使得這類工藝美術有“邊緣”藝術的特點。當然,這條看似工藝美術自我發(fā)展的規(guī)律其實依然受社會文化環(huán)境變遷這根本原因的制約。 作為當下消費者而言,最佳的工藝美術恐怕是既經濟、實用,又美觀的人造物。“用”與“美”的矛盾其實是一對文化矛盾,不同世界觀的人們對此有不同偏向。過去,官辦手工作坊直接服務于宮廷和上層貴族,生產者的個人意志基本上以消費對象的群體意志為轉移(魯迅曾把藝術區(qū)分為“生產者的藝術”和“消費者的藝術”)。他們生產的工藝美術品不論是日用之物,還是欣賞用之物都表現(xiàn)出價值失衡的現(xiàn)象。這類工藝美術品無明確的實用目的,過多地追求華美繁復的裝飾效果,以“淫巧奇技”取勝,只能滿足極少數(shù)權貴對財富和權力的占有欲。如故宮博物院藏的清代和田玉雕“大禹治水圖”,既不經濟、實用,也不具有健康的審美趣味。中國現(xiàn)當代的工藝美術品在一定程度上還沿襲著宮廷工藝美術的特點,殘留著重雕鏤裝潢、輕實用和藝術的傾向,如不少牙雕、木雕、瓷雕、微雕作品乍一看令人驚異,嘆服于作品的工巧和毅力,但看過之后,沒有留下多少回味的東西。此類材料貴重、造型陳舊、工藝繁復的作品顯然已落后于時代,這些難以喚起當代人審美感情的人造物既無實用價值,也無審美價值。 對比宮廷工藝美術的做法,民間工藝美術和文人工藝美術在處理用與美的文化矛盾上有較合理的做法。民間工藝美術主實用,同時又適度地進行裝飾美化,達到“用”與“美”的高度統(tǒng)一。盡管可能裝飾手法上略顯粗陋,卻因為真誠而顯示出質樸的美感。文人工藝美術盡管不一定是文人創(chuàng)造的,卻是他們直接或間接參與指導的結果,具有精雅的文化氣息,達到了“用”與“美”的高度平衡。誕生于明嘉靖、萬歷年間的上海露香園顧繡,積極地從書畫藝術中汲取營養(yǎng),在題材、繡法和格調上改造了傳統(tǒng)刺繡的面目,使其具有了高雅的文化品位。嘉定竹刻自明代始就聲譽鵲起,一個主要原因是歷代的竹刻藝人都自覺地提高這門技藝的文化內涵。以徐素白為例,他廣泛與文人雅士交往,并與當時的書畫名家如江寒汀、錢瘦鐵、唐云、沈尹默、程十發(fā)等合作,創(chuàng)造了令世人矚目的藝術品。 歷史上優(yōu)秀的工藝美術品的問世,幾乎都離不開作者真誠面對生活的心態(tài)和自覺地接受文化的滋潤。工藝美術的“用”指的是適用于當下的生活,工藝美術的“美”指的是能喚醒當代人的審美情感。只有貫徹這一思想,工藝美術才具有打動消費者的魅力,才具有“移風易俗”的社會作用。20世紀80年代初倡導的“工藝品實用化,日用品工藝化”的方針依然是解決“用”與“美”矛盾的有效方針。 三、經濟事業(yè)與文化事業(yè)的矛盾 筆者在南方四省一市的調研中,聽當?shù)毓に嚸佬g行業(yè)協(xié)會負責人陳述較多的一個困惑是:工藝美術究竟是經濟事業(yè),還是文化事業(yè)?現(xiàn)實的狀況是政府把它劃歸經濟部門管理,完全按工業(yè)企業(yè)的性質向工藝美術企業(yè)征收稅賦,即實行17%的增值稅,一些省、市、自治區(qū)還根據自己的情況征收程度不等的消費稅,少則5%,多則10%。稅賦偏重導致傳統(tǒng)工藝美術的發(fā)展受到一定的阻礙。如果把工藝美術視為需要保護的文化事業(yè),或把它歸入文化部門管理,這樣做又難以令其走上產業(yè)化道路。可見,圍繞工藝美術的保護與發(fā)展問題,還須妥善解決經濟事業(yè)與文化事業(yè)的矛盾。 本質上講,工藝美術有兩重屬性:一是商品屬性;一是文化屬性。所以它既不可能是單純的文化事業(yè),也不可能是單純的經濟事業(yè)。弗格森說:“沒有一種藝術不是源于人類生活,而且在人類生存的某些環(huán)境中,沒有一種藝術不意味著實現(xiàn)某種有意目標的手段。由于愛財產生了手工藝術(mechanical arts)和商業(yè)藝術(commercial arts),并且由于可能不冒風險,有利可圖而得到了促進。”⑥應該看到,經濟動機只是手工藝術發(fā)生、發(fā)展的動機之一,表達信仰、情感和愿望等也是手工藝術發(fā)生、發(fā)展的重要動機。不管是出于哪種動機而產生的工藝美術品,都凝結和沉淀了社會文化因素,人們的衣食住行最直截了當?shù)胤从骋粋€國家或民族的社會文化狀況。 比較而言,工藝美術的文化屬性是隱含的,商品屬性卻是最外在的、直接的。在現(xiàn)實生活中,常常遇到一些工藝美術師受眼前利潤的誘惑,專注于經濟利益,忽視了文化效應。如歷代都曾出現(xiàn)過這樣的工藝美術現(xiàn)象:有的人一味追求作品的巨大,或追求作品的微小,力爭獨一無二。有些人則一味地炫技,使作品煩瑣臃腫,毫無美感。鴉片戰(zhàn)爭以后還曾生產過迎合洋人獵奇心態(tài)的“洋莊貨”,像官服的補子、女人的小腳鞋等。不排除此類作品有時亦能贏得一些人的好奇心和收藏者的青睞,但在文化上是不可取的。 中國近二十幾年的經濟生活正發(fā)生著深刻變化,當前工藝美術由生計經濟基礎向商業(yè)經濟基礎轉變。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各種文化失衡的現(xiàn)象屢屢發(fā)生。如因急功近利,不計其數(shù)的質量低劣的工藝美術品充斥旅游點和地攤。在南方某城市出現(xiàn)玉雕作品泛濫、以堆估價的怪現(xiàn)象。有些品類的工藝美術走假古董、偽文化的路線,制造和銷售像“發(fā)財貓”、“財神爺”這類畸形觀念的產品。近幾年北京以及周邊地區(qū)小作坊粗制濫造嚴重,把景泰藍多達十幾道的復雜工藝縮減到幾道,鍍鎳代替了鍍金,機器壓制代替了手工掐絲,因此看似差不多的兩件中等個頭的花瓶,正規(guī)企業(yè)要賣到1000-2000元,小作坊200-300元就可以出手。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張同祿指出,為蠅頭小利損害了景泰藍的名聲,景泰藍因此背上了“景太濫”的惡名⑦。片面地追求商業(yè)利潤,忽視了文化傳承,可能使一些歷史積淀深厚的工藝美術,在當代人面前消散了它原有的文化品位和藝術韻味。 深圳市這些年采取舉辦大型“文博會”的形式,力圖使工藝美術產品擺脫地攤貨的形象,提升整個行業(yè)的文化層次⑧。這種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形式也是東南沿海地區(qū)的流行做法。筆者認為,讓工藝美術回歸文化產業(yè),不能僅關注流通領域,而要把文化保護意識滲透到工藝美術設計、生產、流通的全過程。 揚州市保護和發(fā)展工藝美術的做法值得重視。原本就有較高聲譽的揚州玉器廠和漆器廠至今仍屬集體制企業(yè),近年來通過內部改革,充分重視玉雕和漆器工藝的文化意義,走出了一條對傳統(tǒng)工藝美術文化進行整體保護之路。如揚州玉器廠堅持辦玉校和研究所,按保護文化遺產的標準整修了廠房,拆除了圍墻,建設了藏品室和展覽館,花巨資維護了古藤走廊。現(xiàn)在的廠區(qū)是開放型的,與揚州護城河連成一體,極具園林文化特色,成為揚州市的文化窗口單位,也是集生產、銷售、教育和傳播傳統(tǒng)文化多功能于一體的生態(tài)社區(qū)。李硯祖在十余年前就提出,工藝美術的歷史結構中存在兩種文化因素:一是具體的工藝美術作品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二是工藝美術的生產和使用形式同樣體現(xiàn)出文化意味⑨。揚州經驗恰好是一種整體文化保護意識,它成功地處理了發(fā)展經濟與保護文化之間的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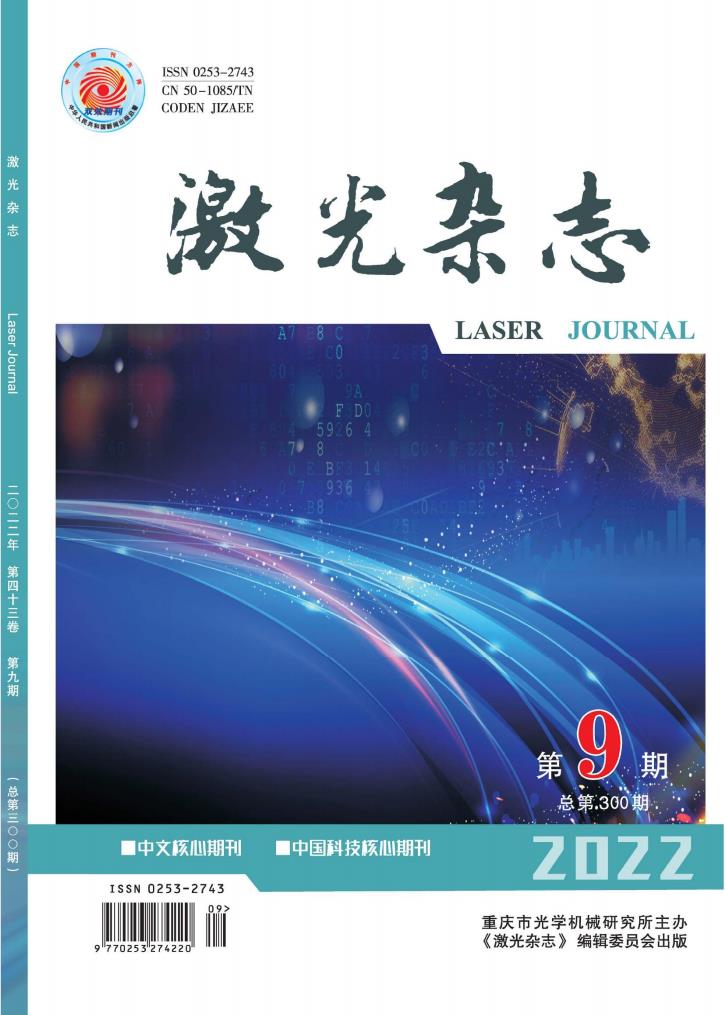
化.jpg)
學.jpg)
災害研究.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