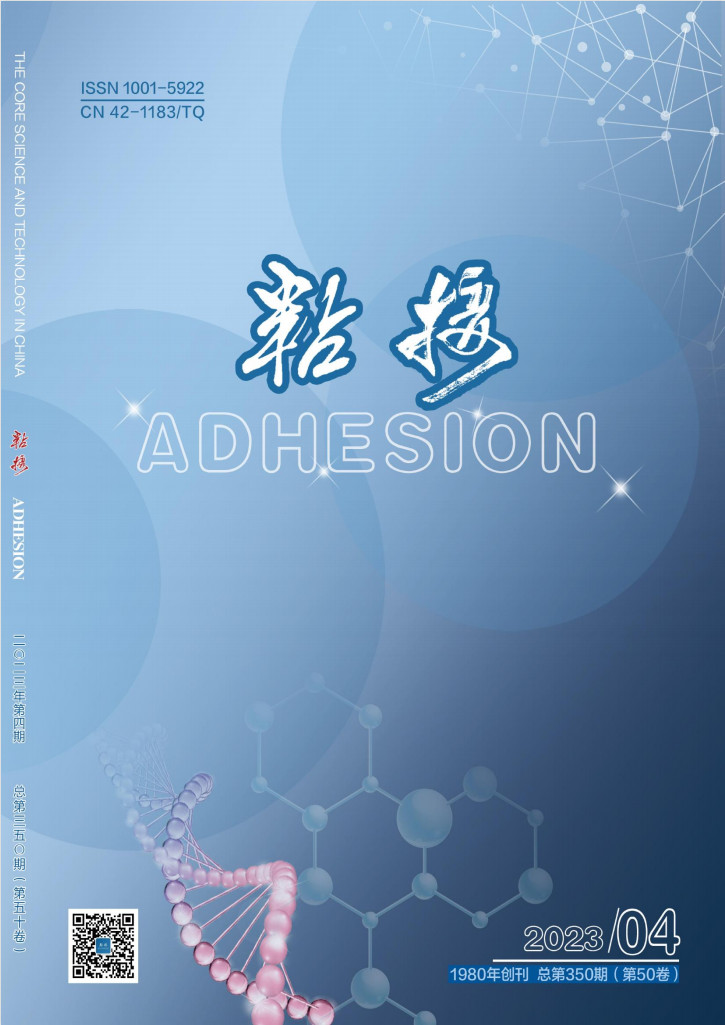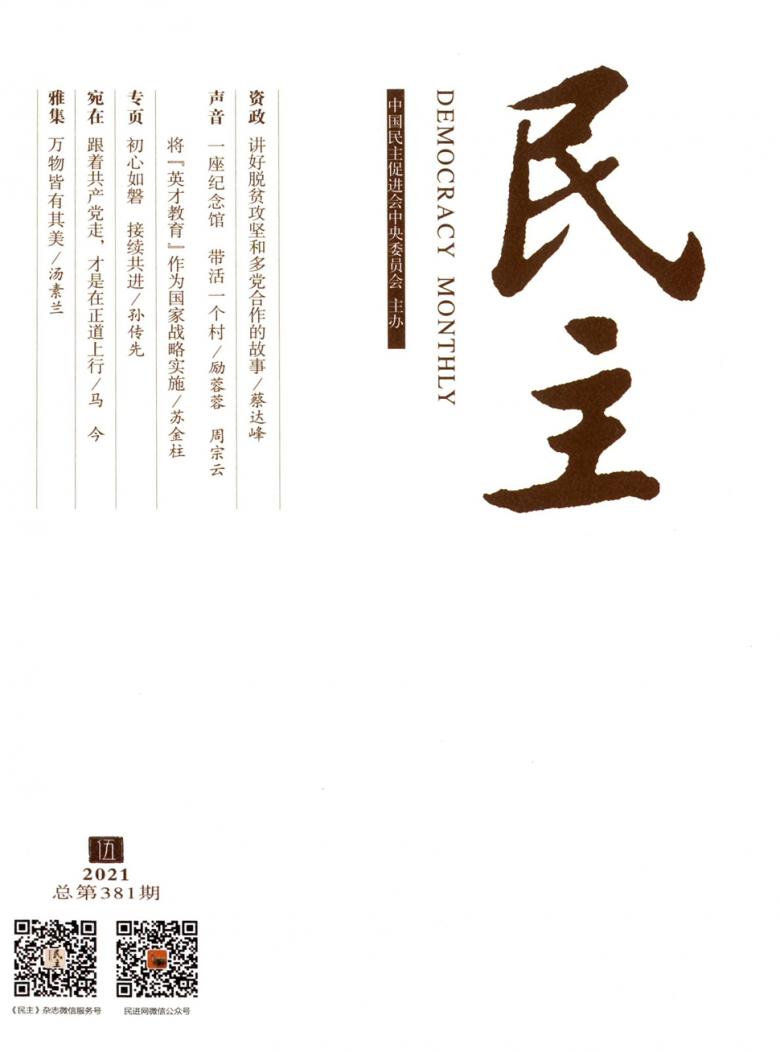散文天空中的絢麗星光
陳劍暉
也許,當批評家們和大眾傳媒在上世紀90年代興奮地宣布一個散文時代正在向我們走來時,散文已開始顯露出一些疲態,出現了“繁華掩蔽下的貧困”。的確,當散文置身于一個巨大的、混亂和喧嘩的消費現場,當車載斗量的散文隨筆夾著后現代商業社會的聲色光影散落于人們的閱讀視域中,人們對其批評責難,甚至認為是“世紀末的狂歡”也就毫不奇怪了。但不要忘了:在世紀末的散文潮中誠然有大量世俗化、商業化的粗制濫造之作,同時也有一批作家堅守散文的精神邊界,創作出了同樣數量可觀的堪稱優秀的思想隨筆。他們的存在不僅是當代散文的光榮,也是一個平庸的物質時代仍孜孜執著于精神維度的作家的一種文化選擇。而迄今為止,對這類思想散文的研究不能說沒有,但應當說數量相當少,而且基本上都是印象式、隨感式的,缺乏實證的考量、客觀的辨析和學理上的梳理。因此,本文擬從具體的創作入手,對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思想散文作多層面的梳理和探討,并以此作為觀察點展望新世紀散文的發展方向。 一、 從抒情散文到思想散文 熟悉中國散文史的人都知道,中國的現代散文主要有三條流脈:一是以魯迅為代表的側重于精神探索的散文;二是以周作人為領袖的閑話聊天式散文;三是以朱自清為典范的抒情散文。由于魯迅的散文充滿象征和隱喻,在結構和精神上過于復雜多義;而周作人的閑話聊天式散文又因不適宜于時代和社會現實的需要而長期遭到漠視,這樣一來,從上世紀3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先是及時反映當時社會現實和斗爭生活的報告文學或特寫大受青睞,而后(特別是60年代前后)是抒情散文的一統天下,并成為一個時期散文創作的主導性品種。由于抒情散文在內容上有一個明確的政治化、世俗化的教育目標,在藝術上通常采用“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表現手法,加之這類散文篇幅短小,結構精致,注重意境的營造,在語言上又體現出圓熟簡約的文體特色,因而在特定的時代里,以楊朔、劉白羽和秦牧為代表的“當代散文三大家”的散文的確頗受讀者的歡迎和批評家的認同,甚至即便“四人幫”打倒后到上世紀80年代初,楊朔式的抒情散文的影子仍如影隨形,“以小見大”、“托物言志”的寫作法則仍束縛著不少散文作家的手腳。其時雖有一些老作家如巴金、孫犁、楊絳等的反思回憶性散文頗具影響,但總體而言,從1976年至整個80年代,相對于小說、詩歌、戲劇乃至報告文學的火爆繁榮,散文創作的狀況可謂波瀾不驚、冷落蕭條。這就難怪有人斷言:“散文,正從中興走向末路”,并由此預言散文是“多余的文體,必然滅亡”。 但散文的發展卻與散文的預言家們開了一個玩笑。進入90年代以后,散文在沒有任何征兆,沒有任何預言的情況下,突然熱鬧和繁榮起來,真可謂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而在這股散文熱潮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思想散文的崛起了。思想散文的崛起并形成一股散文創作潮流大概有兩個契機:一是這一時期,一些有識之士編輯出版了一批“思想隨筆”叢書。比如“思想者文庫”、“草原部落名報名刊精品書集”、“草原部落黑馬文叢”、“九十年代思想散文精品叢書”、“思想者文叢”、“曼陀羅文叢”、“野草文叢”等等。二是隨著大量“思想文叢”的推出,這一時期涌現了一批傾向于思想探索的散文寫作者。在這其中,較為優秀的有史鐵生、韓少功、張承志、張煒、王小波、周濤、林非、王充閭、李銳、邵燕祥、林賢治、孫紹振、雷達、筱敏、南帆、周國平、王開林、劉燁園,以及錢理群、朱學勤、劉小楓 、謝有順、徐友漁、金岱、秦暉,等等。他們的寫作,可以說是對以往的抒情散文的一種偏離,更是一種沖擊和挑戰。這類思想散文,一方面展現了在社會轉型期敢于獨立思考的可貴精神品質;另一方面也是對當代散文進行必要的補鈣和換血。是的,正是有了這樣一批熱心于思想探索的散文家和他們的思想散文,90年代以來的散文創作才呈現出“思想散文凸現,抒情散文淡出”的特色。它們是日漸明麗的散文天空中的點點星光,是庸常時代的精神堅守和心靈吶喊。 那么,產生于上世紀90年代的思想散文有什么樣的外在特征和內在規定性呢?它與以往文學作品的“思想性”又有什么樣的區別?這一切都需要我們進一步追問。 讓我們先對思想散文中的“思想”作一簡要的歸納與梳理。 思想,按《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客觀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識中經過思維活動而產生的結果。《牛津詞典》的解釋則是:“思想就是人類運用心靈與智慧觀察外部的客觀對象,并在這一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看法、意見與決定”。從上述兩部權威詞典的解釋可知,“思想”不同于“學術”。“學術”的“術”在《說文解字》中是“從行,求聲”,“邑中道也”,且這“道”并非終極意義上的“道”,而是“路徑”的“道”。這樣“學術”便帶有“技術”的意味,它的目的是“求證”,重在爬梳整理。而“思想”則不同。它既為客觀的社會存在所決定,也是心靈與智慧的產物,所以笛卡兒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其所強調的便不僅僅是人作為物質和生理的身體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由“心”指向“思”和“靈”的存在。因此在我看來,能稱之為“思想”的,一般應有這樣的一些特征:1.個人性。思想是最具私人性、個人性的東西。而這種個人性又與個體的生活經驗和生命力密切相關。沒有個體的經驗和生命的原動力就沒有思想的創造力。2.獨創性。思想富有的人,往往也是獨立的人,自由的人,有個性的人,也是對事物有獨到的認識和見解的人。思想最忌千篇一律,所以雷同就意味著思想的消亡。3.質疑性與批判性。思想不懼怕權威,不滿足于現成的結論,也不安于保守平庸。思想心懷憂患,目光四射,堅定從容。它既是現存秩序的挑戰者,也是紛紜世界的提問者。當然,思想也是新的價值觀、新的秩序的建構者和維護者。4.重大性與根本性。思想應是“心事浩茫連廣宇”。它不是一般性地提出問題與回答問題,而是以深廣的包容性,原創的穿透性,洞見的前瞻性對一些重大的、帶根本性的歷史和現實問題提出自己的卓見,比如馬克思、達爾文、愛恩斯坦、海德格爾、維特根思坦等的思想就是如此。正因思想有如此的特征,所以它才彌足珍貴,甚至有人將思想比喻為泥沙中淘出的金子,海水里凈濾出來的鹽。 思想是主觀的東西,是無形的、看不見的;但它又是有形的、可以感知的。就散文來說,思想首先必須具備心靈性。散文作為一種人類精神的實現方式,它比任何一種文類都更傾向于情感的傾訴、靈魂的呢喃。因此,思想散文的特點是用“心”去思考、質疑和批判。這就要求散文作家在創作時要以人為中心、為主體,突出創作者的主體作用和潛能,而且必須具有內心世界的通透和豐盈,這樣散文才能在個人心靈的建筑,在對人類內在精神的探測上有所突進。其次,散文的思想還需要有智慧的中和。因為散文既是哲人的近鄰,也是智慧的文體,所以散文家需要用慧眼慧心去體人悟事。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散文的精神一般寓于個體的生命 ,但精神的盔甲有時難免過于沉重,生命的熱烈有時也會過于絢爛刺目,這時如果加進一些智慧和幽默,那么散文的冷峻尖銳中就有了溫潤和柔韌,厚實沉重中也會有從容、閑適和機趣相伴,這于散文無疑是不可或缺的元素。第三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由于散文本質上的自由隨意;或者說,由于人類的精神是自由和獨立而散文對自由精神的依賴又超過了所有的文類,所以,自由的精神應是思想散文旗幟上最為耀眼的標志。在這方面,洪堡特有過十分精彩的描述:“詩歌只能夠在生活的個別時刻和精神的個別狀態之下萌生,散文則時時處處陪伴著人,在人的精神活動的所有表現形式中出現。散文與每個思想,每一感覺相維系。在一種語言里,散文利用自身的準確性、明晰性、靈活性、生動性以及和諧悅耳的語言,一方面能夠從每一個角度出發充分自由地發展起來,另一方面則獲得了一種精微的感覺,從而能夠在每一個別場合決定自由發展的適當程度。有了這樣一種散文,精神就能夠得到同樣自由、從容和健康的發展”。 從上述可見,我在這里所指的“思想”,與以往我們分析文學作品時所歸結出來的“主題”、“中心思想”或“思想內容”有著極大的區別。在過去,我們研究文學作品特別是評價建國后“十七年”的文學時,我們所謂的“主題”、“中心思想”的提出,一般都是與意識形態密切聯系,都是服從于文學作品的教育功能或某個世俗目標,而且這“中心思想”無一例外都是積極的、正面的,利他同時沒有任何個性色彩和靈魂掙扎的痕跡。臣服于意識形態之后產生出來的失去了生活的血水和生命體溫的“思想”,它與真正的思想有著無法遙測的距離。誠如上述,真正的思想是個體的,也是獨到的;是單純的,也是豐厚的;是樸素自然的,也是神圣崇高的。它既帶著生活的血水,烙上苦難的印記,又是超越現實,超越作品的題材、主題、外在結構,甚至超越語言的一種精神性的存在。這正如曼·英伽登所說:在文本之上,還存在著一個懸浮在上的“精神層面”,它是作品的“形而上本質”,是文學的“變幻無定的天空”,也是一些洞然大開而又捉摸不定的東西。不消說,我在這里所指出的散文中的思想,正是英伽登所認為的文學的“形而上的品質”,而這種“形而上”散文品質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今天這個價值多元的時代。 的確,我們無法繞開這樣的提問:其一,為什么思想散文偏偏在上世紀90年代而不是在別的時代崛起?其二,難道別的時代——比如“五四”時期就沒有思想散文嗎?為什么你對20世紀90年代的思想散文情有獨鐘?關于第一個問題,我在《論20世紀90年代中國散文的文體變革》一文中談到:“文學生態環境的相對自由寬松,是90年代的思想隨筆濫觴的根本原因。” 由于中國社會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原先統一的規范已被多元的價值取向所取代。這樣,作家在寫作時心態比較放松,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觀念,可以無拘無束地敘述自己感興趣的事情,這一點對于思想散文的興起至為重要。其次,20世紀90年代是一個眾聲喧嘩、日益多元的時代。這一時期,舊有的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而物質欲望的膨脹、理想的失落又加重了人們的精神危機。與此同時,當現實生活中“精神”、“感情”和“心靈”的因素越來越稀缺的時候,往往正是優秀的文學奮起抗擊的時候。換言之,“精神危機的情狀廣泛而深重,正是文學實現其精神價值的歷史性契機”(韓少功語)。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一些作家選擇了思想散文,實際上就是選擇一種精神維度,選擇了一種生存的方式和態度。這樣我們就能夠解釋為什么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思想散文能夠超越過去的任何時代,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第三,思想散文的興起,還有其散文自身的原因。如眾所知,90年代以來的散文出現了空前的繁榮,但在這散文熱的背后又存在著貧困和蒼白的一面。也就是說,這一時期,以娛樂媚俗、迎合大眾的消費性為特征的散文大量產生。由于它們的存在,人們對這一時期的散文產生了極大的誤解,甚至有人認為散文已進入了“侏羅紀末期”。 在文學出現如此 嚴重的分化的時刻,一些散文家執著于文學的精神價值追問,拒絕將散文創作看做簡單的一次性的文化消費,這不僅保持了文學應有的尊嚴,同時他們還以宿命般的精神皈依,和他們的富于思想力度的散文創作,回擊了“侏羅紀末期”、“笑柄”之類的指控。還應看到,他們對于散文的思想深度的建構還深化了人們對于散文的認知:散文,不應只是軟性的文化消費,不應只是媚俗的商品吆喝和文化弄姿。作為一個自由且富于個性體驗色彩的文學品種,散文應揭示出這個時代中的人性的多面性,為現代人提供精神的多種可能性空間。 在我看來,上述幾個方面,便是90年代思想散文興起的“特殊歷史語境”,這樣的歷史語境,在整個現代散文史中,只有“五四”時期的散文創作可以與之相比。但“五四”時期除了魯迅的散文有較高的思想含量外,其他散文家的創作從總體看思想的元素是較為稀缺的,所以“五四”時期大行其道的是朱自清式的抒情散文,以及周作人式的閑談聊天式散文,而思想散文卻從未形成一股創作趨向。至于“五四”之后至90年代這段時間,由于文學生態環境的惡劣以及散文家創作主體的萎縮,思想散文根本就沒有獲得生長的空間,更沒有形成一個堅守人文與啟蒙立場的散文“思想群落”。當然,由于散文的思想源于個體精神的豐富性,因此在這一時期思想散文的創作中,每個作家的思想風貌都是卓爾不群的;但作為一個思想群落而言,他們又具有某些近似的思想表征。惟其如此,他們的散文創作才顯得厚實多樣、異彩紛呈。 二、 傾聽思想者的聲音 如果從人類精神發展的大框架來考察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散文思想,我們會發現這一時期的思想散文與過往時期散文中的思想是十分不同的。概括來說就是立足于人文主義的立場,堅守知識者的心靈和道德理想,關注現實、歷史以及人類的生存與命運的大命題,保持自由、獨立的思考與質疑批判的姿態——這一切都使這一時期的思想散文達到了一種較高的精神維度。下面,我打算對這一時期較有代表性的傾向于精神思考的散文家作了一抽樣分析,通過對他們散文中的思想表征的描述,藉以探測世紀之交當代散文的思想流向。 (一)獨立的思考:質疑與批判 帕斯卡爾說,“人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雖然它十分脆弱,甚至一滴水就能將他折斷。但因其會思想,會追問我為什么活著,我為什么存在,所以脆弱如蘆葦的人才獲得了做人的價值和尊嚴,才得以超越瑣屑與平庸,翱翔于壯闊的精神天宇之中,并使生命變得強健有力,發出人性的迷人光澤。的確,如果從事文學的人失去了思想的動機和思想的能力,那么從某種意義上也就沒有了文學,當然也就沒有散文。不過,我們也必須看到這樣一個事實:由于中國文學歷來十分強調“載道”的功能,后來又發展到“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而“五四”時期的所謂“言志”,在很多時候也未能真正擺脫“載道”的束縛。所以,在建國后“十七年”乃至上世紀80年代,散文其實并未真正獲得獨立思考的思想品格。唯有到了20世紀90年代之后,散文才逐漸擁有了獨立思考的權利和質疑批評的能力。 考察這一時期的散文創作,可以看到較早堅持獨立思考、致力于思想質疑和批判的散文家當屬邵燕祥、牧惠、舒展、嚴秀,以及錢理群、林賢治等人。他們的思想隨筆秉承魯迅雜文的精神和筆法,而反對現代迷信和造神運動,呼吁恢復“五四”的啟蒙精神,抨擊法西斯的獨裁專制,反省人性的脆弱和缺失,等等,則是他們散文隨筆的主要思想指向。在這些作家中,要特別提及的是林賢治。他不僅和邵燕祥合作主編了《散文與人》等思想性散文刊物和一批思想散文叢書,而且還在理論上力倡散文的批判和自由精神。此外,林賢治還創作了《平民的信使》、《守夜者札記》等思想隨筆集。這些思想隨筆都帶著強烈的懷疑、批判和探索精神,體現出了強健、獨立和追求自由的思想者的風采。總體來看,林賢治的思想隨筆堅硬、直白和犀利,文體較為自由松散,相對來說在詩性方面則稍有欠缺。這一時期既顯示出思想者獨立思考的人格色彩,其創作又貼近散文文體,體現出散文的詩性特征的代表性作家當屬張承志、王小波和韓少功。面對著消費時代人類精神的節節潰敗,張承志挺身而出,決心“以筆為旗”,為“清潔”現實生活中已被污染的“精神”而奮起反擊。在《天道立秋》、《致先生書》、《清潔的精神》、《無援的思想》、《以筆為旗》等作品中,他猛烈抨擊文化知識界的道德墮落,批判媚洋媚俗的時代風氣,同時對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則采取拒絕乃至敵對的態度。張承志的特立獨行的姿態是異端的,同時也是偏執和激憤的,而他的行文則優美且富于穿透力,因此比起那些媚俗矯情的風花雪月、家長里短、阿貓阿狗之類的寫作要有意義得多,所以當代中國的散文版圖中應保留張承志這一脈。王小波思想隨筆的批判鋒芒,大多指向專制主義所帶來的思想壓迫,同時對中國文化的道德取向則深表懷疑。他還有不少思想隨筆對中國知識分子自我人格的萎縮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與自省,對單一刻板和愚昧的思維方式進行嘲笑反諷,并由此提倡一種智慧的思維方式,一種健全的現代理性精神,這些思想對于處于轉型期的世道人心都是清新而急需的及時雨。而韓少功的思想隨筆,更多地保持著對當下社會現實的關注與警惕。比如對世道人心、時代弊病、人性弱點,尤其是時下流行文化新潮的質疑與批判,是韓少功思想隨筆最為著力之處。在《人之四種》、《個狗主義》等作品中,他對在金錢和權勢面前各種人的不同態度的分析可謂入木三分,而他對時下流行文化的批判,更體現出他作為一個思想型散文家的開闊、智慧與深邃。在《夜行者夢語》中,他一開始就這樣寫道: 人類常常把一些事情做壞。比如把愛情做成貞節牌坊,把自由做成暴民四起。一談起社會均富就出現專吃大鍋飯的懶漢,一談起市場競爭就有財迷心竅唯利是圖的銅臭,思想的龍種總是在黑壓壓的人群中一次次收獲現實的跳蚤。或者說,我們的現實中本來就有太多的跳蚤,卻被思想家們一次次吹成龍種,讓大家聽得悅耳和體面。 這篇散文全面質疑了后現代主義的價值觀,批判了“圣徒和流氓,怎樣都行”的后現代行為方式,同時維護了人性的高貴、神圣和責任。由于韓少功是一個既入世又出世,既看透又寬容,既有獨立個性又不張狂的散文家,加之他的智慧和哲學思辨無處不在,這樣,《夜行者夢語》對于后現代的批判便超越了同類的作品,不但視野開闊,深刻獨到,而且富于思辨的色彩和智慧的調侃反諷。而意象的豐滿奇警,語言的節制、簡潔和老辣,更顯示了這位散文家深厚的學養和不凡的才情。需要指出的是,在韓少功的創作中,類似《夜行者夢語》這樣優秀的思想散文,還可舉出《性而上的迷失》、《心想》、《世界》、《佛魔一念間》等一大批,它們當之無愧地代表了當代思想散文的創作高度,有效地拓展了當代散文的精神空間。 在20世紀90年代的思想散文作家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幾位外,史鐵生、張煒、李銳、周濤、筱敏、王開林、劉燁園、劉小楓、朱學勤、摩羅等人也以思想探索著稱。他們的散文隨筆面影不同,情態各異,但在獨立思考、質疑和批判這一思想指向上卻高度地一致。惜乎篇幅所限,此處不可能對他們的思想散文一一加以描述和呈現。 (二)人文主義的堅守: 重建人類的心靈和道德理想 誠如上述,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多元化時代。由于現實社會的相對自由,拜金思想、享樂至上、消費主義的盛行,從而導致了價值觀念的混亂和理想主義、道德水準的大面積淪陷。而隨著大眾精神生活的日益空洞和閱讀口味的轉變,文學也變得越來越商品化、功利化和世俗化。在這樣的情況下,作家普遍感到了一種生存危機和精神危機:是臣服于世俗還是反抗世俗?是放棄理想還是堅守理想?是任由精神混沌還是重建人文主義的精神家園?這一切都要求作家做出屬于自己的明確答復,這其實也是消費時代作家無法逃避的兩難抉擇。 我們高興地看到,當文學越來越成為消費時代里人類精神潰敗的表征,當現實生活中“精神”的含量越來越少,人們的感情越來越沙化,心靈日漸枯萎的危險時刻,有一批秉持著知識分子良知的優秀散文家挺身而出,他們以圣徒般的決絕和赤子之心“一次次奔赴精神的地平線”(韓少功語),義無反顧地反抗世俗,拒絕平庸,同時堅守著人文主義的精神世界。在這方面,張承志是特別令人尊敬和值得推崇的一位作家。他的散文的思想內核,不僅包含著高貴、血性、激情、理想、浪漫等元素,而且,他還是一位為民族而活的散文家。在他那里,民族性已經成了一種誘惑,一種揮之不去的宿命。所以,他寫回民的黃土高原,寫西海固,寫北莊的雪景,寫旱海里的魚。他以一種心靈獨白的抒寫方式,忘情于大西北貧瘠凄厲的風景,或借助下層勞動人民貧困然而堅韌的生存方式,贊美了他心目中的 “清潔的精神”,體現出一種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的生命激情。特別在《漢家寨》這篇富于詩性的散文中,這種理想主義和生命激情更是凝固為一種“堅守”的精神:“我從天山大阪上下來,心被四野的寧寂——那充斥天宇六合的恐怖一樣的死寂包圍著,聽著馬蹄聲單調地試探著和這靜默敲擊,不由得屏住呼吸”。作品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漢家寨”是空曠寧寂、四顧無援的。它坐落于“三百里空山絕谷”之中,周圍是“鐵色戈壁”、“酥碎紅石”、“淡紅色的焦土”,以及“獰惡的尖石棱一浪浪堆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走進了“漢家寨”。“我”看到的“僅僅有一柱煙在悵悵升起”,有“幾間破泥屋”,“我”還看到一個老漢和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老漢自始自終都是“無言”,而小女孩則是“一動不動”地“凝視著我”。她身上穿著的一件破紅花棉襖特別惹眼,她黑亮的眼睛卻深深嵌進我的靈魂里……的確,在張承志筆下,“漢家寨”就如“一顆被人丟棄的棋子,如一顆生銹的彈丸,孤零零地存在于這巨大得恐怖的大自然中”。但是,畫面中的這一老一少卻頑強地在這“絕地”里生存了下來,而且“從宋至今,漢家寨至少已經堅守著生存了一千多年了”,他們靠什么生存下來?這對“我”和讀者來說永遠是一個謎。但這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從“漢家寨”這一象征性的隱喻中,“我只是隱隱感覺到了人的堅守,感到那堅守如這風景一般蒼涼廣闊”。而且日后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在不知不覺之間,堅守著什么”。很顯然,張承志在這里“堅守”的是一種理想主義,一種人文主義的精神。這種堅守自然十分苦澀、孤獨,也相當地艱難,但這種堅守并非毫無價值可言。尤其在當今的時代,當許多人眼中只有金錢利益,只有物質享受,而理想主義失落,沒有生活的方向和目標。這時候,的確需要一種在物欲橫流中堅守清貧,在庸俗泛濫中堅守高潔,在寂寞孤獨中堅守理想,在“全盤西化”中堅守民族自尊的人文主義精神。在我看來,張承志的《漢家寨》,包括《離別西海固》、《英雄荒蕪路》、《禁錮的火焰色》等作品的價值正在這里:他以特有的嚴峻、決絕和深邃筆致,把讀者帶進一個雄大磅礴、空寂遼闊的生活空間、自然空間和精神空間,讓讀者在靜靜的文字里感受著精神的硬度和心靈的力量。 類似張承志堅守理想主義立場的散文作家,還可以舉出張煒、周濤、韓少功等人。在張煒的散文名篇《融入野地》中,他告別了城市的喧囂和虛偽,告別了物欲和世俗,執意到“野地”中去“尋找一個原來,一個真實”。而當他真正“融入野地”,用心去諦聽,去感受大地上的一切活躍的生命時,他便成為了“野地”的一部分,他的靈魂因此獲得了超越。周濤的《鞏乃斯的馬》,表面上在寫馬,寫馬的力與美,實際上卻是在彰顯一種理想的人格,一種進取的精神和對于崇高與壯闊的向往。在這里還要特別談及韓少功新近出版的長篇筆記體散文《山南水北》,在我看來,韓少功的這部新作與張煒的《融入野地》,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這是一部記錄山野自然與民間底層生活的真實摹本。作者遵從生活和心靈的召喚,順勢而為,不浮躁,不矯飾,也不故意逃離現代文明和人群。于是,他在鄉村當了7年“業余農民”,在“春夏種豆南山,秋冬奔走紅塵”的半隱居生活中,感受到了一種最自由最干凈的空氣。韓少功的寫作與返鄉,其實也是一種人文主義的堅守:他將知識分子對現代城市生活的焦慮與思考,延展到大自然和民間,他希望以一種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相結合的健康生活方式,使自己的創作重獲活力,重獲一種健全的精神維度。也正因此,“第五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的主持人在2006年度杰出作家的“授獎辭”中,認為韓少功的《山南水北》是“用一種簡單的勞動美學,與重大的精神難題較量,為自我求證新的意義。……在這個精神日益掛空的時代,韓少功的努力,為人生、思想的落實探索了新的路徑”。韓少功、張煒、周濤、張承志的散文創作實踐表明:散文堅守人文的陣地,要重建人類的理想和道德秩序,關鍵是作家要有一種健全的人格和精神的維度,尤其是散文家要以一種高遠的、自由和純凈的心靈,即“天道人心”去建筑人類的心靈世界。如果散文中有一顆健康、自然、和諧與澄明的心靈,那么散文就有能力建構起一個完整的自我的世界——一個既有心靈的豐盈饒富,又有日常生活的現場感并與重大的命題、宏闊的歷史空間息息相關的獨特的精神世界。
假如世界上沒有了苦難,世界還能夠存在么?要是沒有愚鈍,機智還有什么光榮呢?要是沒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維系自己的幸運?要是沒有了惡劣卑下,善良與崇高又將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為美徳呢?要是沒有了殘疾,健全會否因其司空見慣而變得膩煩和乏味呢?…… 看來差別永遠是要有的。看來就只好接受苦難——人類的全部劇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來上帝又一次對了。 史鐵生以對人性的洞察和至囿至慈的寬容,對苦難做出了一種迥異于世俗的理解:他發現了苦難也是財富,虛空即是實在,而生存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選擇,需要承擔責任與義務。他由個人的嚴酷命運上升到對整個人類的生存困境的思考,于是,他的散文便超越了一己的悲歡,具有一種闊大的精神境界和人性內涵。 雷達的散文《還鄉》,雖在思想境界上不及《我與地壇》那樣闊大深邃,但他對于人的存在狀態的思考,卻更多地帶著鄉土的況味和世俗的原生態。作者相當具體、細致和生動地描寫了“我”還鄉途中擠火車的難堪尷尬的景況,正由于有這樣的切身感受,“我”才“有一種跌落到真實生存中的感受”。并意識到“平時對人生的了解,太片面,太虛浮了,生活的圈子愈縮愈小,感性的體驗愈來愈單調,雖然也大發感慨,大談社會,實際多是書本知識和原先經驗的重復”。不僅如此,作品還進一步從與親友的交談和喝酒的場景中,思考我的“存在”和“不存在”,這種角色的經常倒置和錯位,不正是現代人類存在的真實景況嗎?正是通過非常寫實、非常具體的底層日常生活的敘寫,《還鄉》探測到了人的生存狀態,從另一個方面體現了散文的思想指向。 90年代以來散文創作的思想表征還可以梳理出許多方面。比如,在劉小楓、筱敏、一平等的散文中,他們不約而同地涉及了“苦難記憶”和“拒絕遺忘”的問題;而王小波的思想隨筆,則集中關注人的尊嚴、平等,特別是智慧和健全以及理性的問題;至于錢理群、朱學勤、葛兆光、葛劍雄、秦暉、金岱、徐友漁等學院派思想者的散文,則以反省拷問國民性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弱點,以及以歷史反照現實,以現代性與偽現代性的文化沖突剖析文化轉型期中國人的精神走向而受到讀者的歡迎。他們的思想隨筆雖為學術研究之余的副產品,卻以其獨特的人格色彩和文化智慧為世紀末的中國散文創作守魂和導航。 三、散文的骨骼與靈魂 思想之所以值得我們如此重視,蓋因思想是散文的骨骼和靈魂,對于散文而言,它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價值。然而,必須承認,我們過去對于思想之于散文的意義是重視不夠的;或者說,我們只是從“文學為政治服務”、“抒時代之情和人民之情”的“政治高度”去重視散文中的思想,這自然是狹隘和膚淺的理解,是帶著鮮明意識形態烙印的“思想”,這樣的思想與直面靈魂、直指人心的散文精神在本質上是南轅北轍的。因此,在我看來,思想之于散文的作用和價值,主要應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由散文的文體本質和特征所決定。我們知道,散文是一種最富個性化、最自由和寬容的文體。它不是文學的高山峽谷,卻是文學的廣闊平原。也就是說,它有著平原的遼闊、從容、沉穩與綿延不絕的地平線。散文的這種“平原”狀態,既能最大限度地接納其他文類在藝術上的長處,同時也是一切思想或精神的理想棲息地。如果打個比方,我們可以說詩歌是人類感情和精神的極致,它是文學中的舞蹈,它不僅尖銳優雅,而且十分看重才情;小說是文學中的跑步,它體現了人類生存的危機、沖突與和解,因此它更重視閱歷、敘述和結構的技巧;而散文則是文學中的散步,由于沒有規范,沒有太多約束,因此它更接近人的本性和生存的日常狀態。正因這個特點,與其他文類相比,散文更是心靈、智慧和哲學的近鄰,它的長處不在于描狀一片樹葉的枯萎,而在于用哲人的慧眼慧心去深究這片樹葉與樹枝、樹干、大地乃至季節的內在聯系,這一點是小說和詩歌所不及的。再從文體表現生活的特點來看,散文不似小說那樣有人物、情節和敘述可以依傍,也不像詩歌那樣以高度凝練的語言、跳躍的韻律節奏和奇特的意象組合來吸引讀者。散文是以“自然”的形態呈現生活的片斷,以“零散”的方式對抗現實生活的完整性和集中性,以“邊緣”的姿態表達對現實和歷史的臧否,所以散文不僅呼喚思想,它更適合思想的生長,它更渴求有個性、原創和深刻獨特的思想的支撐。可以這樣說:任何文學都需要思想,但散文對思想的渴望超過任何文學。的確,倘若沒有思想的支撐,散文充其量只是一具徒有其表的空殼,只是一堆沒有靈魂的文字的瓦礫。這樣的散文文字再美麗,結構再嚴謹,意境再動人也是徒然。正是因此,“散文,我們時代的散文,沒有理由逃避或淡化思想”。這是從散文文體本質和特征與思想的內在一致性,以及散文需要思想的支持這一角度來考察。 其二,如果說散文隨筆是一種屬于思想者的文體,沒有思想的散文隨筆是紙做的花朵的話,那么,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思想的大規模介入,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散文的文體空間和心智空間。如前所述,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當代的散文只有抒情散文一統天下,散文的品類、題材和表現手法都十分刻板單一。而現在,隨著思想散文的崛起,散文的文體形式也有了較大的演進與突破。比如說,過去的抒情散文一般篇幅都較短小,而現在的一些思想散文動不動就是兩、三萬字;過去的散文一般都遵循散文的邊界,而現在“破體”已成為一種較普遍的現象;過去散文的敘述一般都是按照“景——事——理”的模式展開,現在卻是真正地無拘無束,當行則行,當止則止,有的甚至采用多種人稱互換和“意識流”的敘事手法。這是從文體模式方面而言。從思維層面和心理層面來看,以往的散文極少涉及精神體驗和心靈體驗,而現在的思想散文卻有大量的有關精神體驗和心靈體驗的敘寫。舉例說,在王充閭的《用破一生心》這篇散文中,王充閭一方面從政治的角度寫了曾國藩的才干和野心,另一方面又從人性、人生哲學,從心理方面對他進行解讀與批判,準確而細致地寫出了曾國藩心理上的壓力、靈魂上的折磨,這就抵達了人性的深處,拓展了散文的心智空間。可見,思想散文對于“重建散文的體裁,重建散文的深度,重建散文的個體經驗和母語經驗,同時開拓散文全新的文化語境和更有創意的審美境界”,都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和價值。 若我們將視野放開一些,我們還可以看到,但凡古今中外那些優秀的散文,都有著深厚的思想的底子。莊子的散文就是如此。從思想的角度看,他的《逍遙游》既是生命的存在形式,又是追求自由精神和人格獨立的體現。而正是這種生命體驗和藝術精神,使兩千年前的莊子成為一個比現代派更為現代的思想家。蘇軾的《前赤壁賦》同樣是建立在龐大的精神心理結構上的經典之作。這篇作品之所以成為中國散文史上的名篇,固然得益于“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傾之茫然”這樣的精妙寫景和奇詞麗句,但更重要的是,文中還有諸如“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叟,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于悲風”這樣的哲理思考:我們雖然生存于天地之間,但其生命就如蜉蝣一樣短暫。我們的存在,其實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那么渺小。于是,我們一邊悲嘆生命的短暫,一邊羨慕著長江的不盡東流。正是因此,我想挽著神仙結伴而遨游,也想與明月相守而長存。但我知道這樣的愿望不可能實現,于是只好借著簫聲將這無邊的遺恨寄托于悲涼的風中。在這里,蘇軾借助赤壁的月夜與江水,透過無限的宇宙時空來體驗人生和觀照自然,同時融進一種灑脫曠達的生死觀。這樣,《前赤壁賦》也就因其闊大豐富的思想內涵而超越同類的散文并流傳千古。可以設想:倘若沒有超越個體的思想追問,即便是再絢麗多彩的句子,也只是一件華美的外衣而已,不可能有現在這樣的思想境界和藝術穿透力。 中國古代的優秀散文包括現代魯迅的《野草》,都有著極為豐富深邃的思想內涵,那么,外國散文的情形又如何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外國稱得上一流的散文家和散文作品,同樣以追問生命的價值,個體的存在狀態,以及自由、平等,人的尊嚴等理性見長。比如蒙田、培根、羅素等人的散文就是如此。在這方面,南美大作家聶魯達的散文堪稱典范。他有一篇散文寫他穿行于南美的叢林中,當他看到一個被洪水連根拔起的大樹頭,他這樣寫道:“櫟樹倒下時發出天崩地陷般的聲音,有如一只大手在敲擊大地的門,要敲開一個墓穴。它聽憑風吹雨打和隆冬的肆虐已達上百年,它傷痕累累的織體,銀灰色的色調,形成一種粗硬的、令人心醉的莊嚴美。它現在來到我的生活里,也許是要把它的沉默傳染給我,并揭示出大地再次給予我的美學教育”。從表層看,這只是一段寫景的文字,但若從精神生命的角度看,這段文字無疑包含著極為豐富廣闊的精神與歷史空間:它由大樹根那種“粗硬的、令人心醉的莊嚴美”,延伸到南美這片大地上的“百年孤獨”,呈現出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紛紜復雜的精神心理結構,并且給予人類以生存的信息和無限的“美學教育”。這樣的描寫的確具有一種直逼事物本質的思想硬度。當然,這樣的描寫絕不僅僅是文字經營的結果。只有具備了大胸臆,并將這種大胸臆投放到無限廣闊的精神歷史空間的作家,才有可能寫出如此冷峻而又壯美的形而上的文字。 由此,我們便接觸到這樣一個問題:思想散文中的“思想”是否豐富、獨立和深刻,與創作主體精神和心靈的強健純正有著密切的關系。一般來說,個性獨立而富于自由精神、胸臆博大且心靈充盈的作家,他筆下的思想必然富厚活潑并充滿著啟迪人心的力量,反之則平庸蒼白了無生氣。由此可見,任何一種文體的本質都取決于進入這種文體寫作的人的精神高度和心靈的純度。因此,要提高當代散文的思想質地,關鍵是散文寫作者首先要成為真誠的人,獨立的人,自由的人,有個性和有智慧的人。其次,他要敢于面對現實生活,敢于接觸重大的社會命題并發表自己的意見。此外,他還要敢于直面下層人民的生存狀態,使其作品有一種生存感。第三,他既要擁有哲學家的心智又必須具有自己獨到的眼光,還必須有對全人類的愛和擁有一顆悲憫之心。倘若中國當代的散文家擁有了這樣的主體性和心靈性,那么,他的精神和心靈的質量必定是高的,他的散文中的思想自然也就富有價值且一定不同凡響。 四、思想散文的局限及提升 作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散文創作的主流品種,思想散文所取得的成就,其對于當代散文在散文題材、散文深度和散文文體的拓展等方面有目共睹。但肯定成績并不意味著忽視缺點。從21世紀散文發展的高度來要求,我認為思想散文還存在著如下的一些不足。 不足之一:是一些熱衷于思想探索的散文寫作者精神維度上還有所欠缺;或者說,他們的精神維度還不夠闊大與寬容,還缺乏一種更加健康、更加民主的現代理性精神。在這方面,張承志表現得特別突出。他一方面堅守著人文主義精神的邊界,一方面又執著于他的哲合忍耶圣徒的立場和“紅衛兵情結”。如果說,他抨擊時下知識界和文人圈的墮落,抵抗西方的新殖民主義文化還有其合理性和積極意義的話,那么他狂熱地贊頌荊軻一類的潔凈精神,甚至倡揚一種暴力主義,就值得今天的人們警惕了。在這個問題上,散文理論家王兆勝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張承志被荊軻精神的光圈罩住了,缺乏了自己心靈的光芒。就是說,在對荊軻個人精神的陶醉中,張承志失去了自我反省的能力,而這正是現代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品質”。不獨張承志欠缺現代理性精神,在張煒、林賢治以及祝勇等人的創作和批評文字中,我們也或多或少感到了這種缺失。比如張煒的《融入野地》等贊美鄉野的散文固然寫得很美很具個性,但他將“野地”和現代都市對立起來,揚鄉村生活而抑商業文明,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的確值得商榷。再如林賢治的文章中的評人衡文,只要是“五四”或外國的,便一定是自由的、民主的、強健的,值得今天的人們脫帽致敬和大力提倡,反之便不值一提不屑一顧。而祝勇對“體制散文”和傳統散文的批判,同樣流露出思維的狹窄、片面和簡單化的創作傾向。顯然,這些都與包容、明澈與自省的現代理性精神格格不入。 為什么張承志等人的創作會如此偏執?在我看來這主要由兩方面造成:一是他們過于執著于個體的經驗,且在做出價值判斷時往往過于粗暴和簡單化。歷史在變化,時代在發展,社會生活更是錯綜復雜,因此作家在對社會現象做出價值評判時,應具有如康德說的從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綜合思考能力。此外,思想者還應心存信念,極目神游,心涵太虛。他的思想既具有快刀砍竹般的犀利,同時還應具備深廣的包容性和“萬物與我一體”的和諧澄明。倘若一個散文家只是偏執于一己的經驗和感受,而缺乏一種博愛和大度、仁慈和寬容、悲憫與人道的心懷,那么他的散文創作就很容易走進片面、偏激、孤憤甚至走火入魔的誤區,從而遮蔽了他本應獨特深刻的思想。這是其一。其二,是傳統文化的影響。我們知道,植根于農業文明的中國傳統文化在本質上其實有著根深蒂固的封閉自足性和反現代性的文化特征。這樣的一種文化特性自然會潛移默化地滲透到每一個中國人包括中國作家的血液中。張承志、張煒等人自然也不能例外。雖然他們常常以反傳統和抗爭世俗的姿態出現,但一落實到具體的寫作中,他們的作品中在行文立意、價值取向和意蘊情調等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了某種小農式的思維。由此可見,對于當代的散文作家來說,建構一種全新的文化品格,以現代的理性精神來指導自己的散文創作,便顯得尤為重要。這一點,其實在散文創作和理論研究上均作出過重要貢獻的林非先生早就倡導過,可惜他的呼吁沒有引起散文作家普遍的重視。 不足之二:是某些“思想散文”中的思想缺乏深度和獨創性,有的甚至只是表達了某個生活的常識。我們在前面談過,思想的特征是個人性、原性、穿透性和根本性,然而縱觀90年代以來的思想散文,有不少實際上并沒有達到這樣的思想高度。比如,有一些散文家的思想隨筆,充斥于其中的無外乎經典名著或宗教故事以及神話傳說的改寫或闡釋,不但理念陳舊,缺少新意,有的還存在著生吞活剝,乃至曲解和誤讀的成分。這種現炒現賣、隨意衍生、勾兌思想的做法,在我看來并非寫作思想散文的正途。還有一類思想散文,以格言體或語錄體的方式談論理想、人生、信仰、愛情和藝術等問題,表面看來頗具文采和哲思意味,但從“思想”的精義來衡量,其實只是一些適合白領口味、裝潢精致的“心靈的雞湯”。甚至即便是以思想獨立著稱的王小波的思想隨筆,有不少也只是在闡釋自由、民主、理性等常識而已,并沒有包含多么深刻、獨創的思想。凡此種種,都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思想,并非是裸露于地表的隨處可以撿到的礦石;思想,是深藏于地底的黑金,唯有長久的尋找,艱難的探測與挖掘,才有可能觸摸到思想的礦脈。 不足之三:是文學性不足,理論性有余。如上所述,我們倡揚散文中的思想,尤其是深刻獨到且富于個人性的思想,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當我們全面考察90年代以來的思想散文,我們不難發現有相當一部分思想散文存在著理勝于文、思想的盔甲過于沉重的弊端。舉例說,有的思想散文流于知識的介紹、學問的考證、邏輯的推演;有的思想散文過于仰仗對于大師思想的援引,滿紙都是“自我”、“經驗”、“超驗”、“此岸”、“彼岸”之類的哲學術語,幾乎是哲學大師的思維和話語的翻版;還有的思想散文語言過于糾葛纏繞,表述又過于玄虛,而結構上又過于呆板單一。總而言之,沒有生動可感的形象,只有一些所謂的“思想”;沒有優美蘊藉的文字,只有一些大白話的堆砌;沒有引人入勝的意境,只有千篇一律、冷冰冰的邏輯演繹,這是當前某些思想散文的主要病象。關于思想散文存在的這些病象,王兆勝在《超越與局限——論80年代以來中國的女性散文》、《困惑與迷失——論當前中國散文的文化選擇》等文中已有過相當精彩的分析和中肯的評價,故此處不再展開論述。 通過上面的考察可以看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的思想散文并非盡善盡美,甚至可以說還存在著較大的問題。為了思想散文在新的世紀能夠更好地發展,或者說,為了借助對思想散文的研究,克服、改變長期以來困惑當代散文創作和理論研究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我認為,未來的散文包括思想散文應在幾個方面加以改進和提升。 第一,個體與整體。散文固然十分強調自我、個性、個人的生活經驗和生命感受,但個體并不是遠離大地、與世隔絕的絕緣體,更不是一些私人化的生活碎片的聚合。散文中的個體,應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方面,散文中的個體是對自我世界的體驗,它忠實于自己對生活的認知和心靈的感受,是自我的感情、生命和人格的自由自在的釋放;另一方面,散文中的個體又聯系著時代、社會、歷史乃至整個人類,也就是說,散文的個體離不開整體,或者說,個體只是整體的一種濃縮。可以設想一下:如果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只是沉溺于一己的苦難,如果他沒有用一顆富于同情且健全的身心去感受園子中不同的人物對于生命過程的追求,如果他沒有將個體的苦難與全人類共有的苦難融會于同一個調色板里,在靜靜的生命荒涼里感受著生與死、差別的意義、欲望的動力,以及宗教與信仰對于個體的啟迪,那么可以肯定,《我與地壇》充其量也只是一篇藝術上較為圓熟,而思想則十分平庸落套的作品。而一旦史鐵生將個體與整體聯系起來,由個人嚴酷的命運上升到對全人類命運的思考,于是,《我與地壇》便超越了一己的悲歡,有一種闊大的思想境界和人性內涵。與此形成比照的是:一些被譽為“新散文”的作品,其創作所體現出來的個性應當說是十分鮮明突出的,可惜它們是為了突出個性而個性,是完全疏離于時代、社會與全人類的正常的價值觀,疏離于整體的個性。因此,“新散文”中的個體化、私人化描敘受到一些批評家的批評也是理所當然的。可見,思想散文包括新世紀的其他散文要獲得大的境界和思想深度,就應當跳出“惡劣的個體化”的泥潭,而讓社會的氛圍、時代的精神、大眾的情感和人類的命運融進散文的創作中。當然,要做到這一點,散文家首先必須具備一種精神的高度,有廣闊的生活視野,還應有一顆寧靜而從容、淳樸而廣大、敏銳而深刻的散文心。 第二,物質與思想。我們提倡散文中應有思想的元素,不過我們要十分清楚:散文中的思想,決不是來自于書齋,來自于書面知識或大師語錄的摘抄。散文的思想,應來自于現實,來自于生活細節,來自于作家對這些生活細節的心靈和生命的感受。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談道:當代的散文一方面要有一種對抗流俗的精神性存在;一方面又要更加貼近日常的、瑣碎的現實生活,而且,在“題材上要‘雜’一些,‘野’一些”。謝有順則說得更肯定和明確。他將日常生活細節看做散文的物質部分,并認為:“今天的 散文似乎并不缺少精神性的抒寫,缺的正是有價值的物質元素。散文的物質性就是大量經過了內心發現和精神省察的事實、經驗和細節,它們在散文中的全面建立,使心靈的抖動變得更真實,也使那些徒有抒情、喻理之外表的散文在它面前變得輕佻而空虛”。謝有順的這一見解,深得我心。為什么有一些思想散文中的“思想”缺乏血肉,顯得那樣蒼白、生澀、呆板和難以捉摸,蓋因這些作品中的思想是懸空的、不及物的。因此它們徒有思想的外衣,而沒有思想的靈魂。所以說,思想散文中的思想應建立在具體的、真實可感的、毛茸茸的生活細節之上,惟其如此,思想散文中的思想才能真正落實到實處,才有可能既有一種精神的大境界、大氣象,又具有建立在心靈發現和細節經驗之上的存在感。 第三,思想與詩性。海德格爾有言:思想即是詩,詩即是思想。如果以此為標尺來檢驗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思想散文,應當說有不少散文尚不能達標。因此在新的世紀,思想散文要獲得更多讀者的接受與認同,就必須在思想與詩性的融合上多下力氣。在思想的探索和詩性的融合方面,史鐵生、韓少功、張承志、張煒等人的創作都是較為理想的范本,而稍晚出現的筱敏的思想隨筆,同樣值得我們重視。筱敏的思想散文,有對法國大革命的遙想,有對俄羅斯精神的禮贊,有對德國法西斯暗影的省察,還有對“紅衛兵”運動的反思,以及對“家”和“路”的追問,等等。總之,她的散文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個宏闊的歷史空間和思想空間,但她的散文又是富于詩性的。她的詩性首先來自于以神圣與高貴為底色的情思與理想浪漫的想象;其次來自于大量新奇與獨特的意象;第三來自于優美典雅、清晰準確、精致結實的詩一般的語言。正是上述三方面,使筱敏的思想散文成為名符其實的思想的詩和詩的思想,并因此而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和批評家的好評。筱敏散文創作的成功,給了我們這樣的啟示:在思想散文的創作中,思想與詩性的高度融合,可以使散文思想的地平線更加堅實、明朗和遼闊,同時也使散文的思想因詩性的融入而更加柔韌、綿長和令人沉醉。因此,在我看來,這是新世紀的散文走向闊大和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散文之路。 五、結語 正如柯漢琳先生所說:“散文的世界宛如那廣袤無際的星空,而這星空是仰望她的眼睛而存在的”(15)在這篇文章獎要結束時,我想接著柯先生的話往下說:散文的天空是困思想而絢麗,因其鑲嵌了人類美麗的心靈而存在,因其注入了責任承擔而高貴的。這正如作家鐵凝所說:“文學可能并不承擔審判人類的義務,也不具備指點江山的威力,它卻始終承擔理解世界和人類的責任,對人類精神的深層關懷。它的魅力在于我們必須有能力不斷重新表達對世界的看法和對生命新的追問,必須有勇氣反省內心以獲得靈魂的提升”。的確,從個體的創作來說,一個散文作家如果擁有正義、良知、責任、承擔、博愛、同情心以及反省批判等高貴品質,加之有真誠的態度,有生命的投入,有心靈的發現和文體方面的自覺,他就有可能寫出無愧于自己和時代的散文。而就一個民族而言,“一個真正充滿了希望的民族總是善于思考的,反過來說,一個渾渾噩噩的民族和遠離思想的民族,就不可能走向光輝燦爛的明天”。 我期待著新世紀的散文在思想的天空中無限地延展,也期待著散文思想的光芒隨著時代的前進而更加絢爛。我相信,當散文的思想和時代的精神真正獲得共振的時候,一個屬于散文的時代也就到來了。 注釋: (1) 黃浩:《中國當代散文:從中興走向末路》,《文藝評論》1988年第1期。 (2) 轉引自林賢治:《五十年:散文與自由的一種觀察》,《書屋》,2000年第3期。 (3)轉引自魯樞元:《超越語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頁。 (4) 李敬澤:《“散文”的侏羅紀末期》,《南方周末》,2002年8月1日。 (5)見《南方都市報》2,007年4月8日。 (6)(15)柯漢琳:《仰望思想的星空——關于90年代以來思想散文的思考》,《文學評論》,2002年笫3期。 (7)王岳川:《關于王充閭散文的學術點評》,《中國散文論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頁。 (8) (10)王兆勝:《文學的命脈》,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頁,第149頁,第178頁。 (9)林非:《現代觀念與散文寫作》,《文學報》,1986年3月13日。 (11)見《詩性散文的可能性與闡釋空間》,《福建論壇》,2005年第11期。 (12)謝有順:《從俗世中來,到靈魂里去》,鄭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頁。 (13)鐵凝:《無法逃避的好運》,見《散文研究》,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頁。 (14)林非:《當代散文精品序言》,見《散文研究》,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