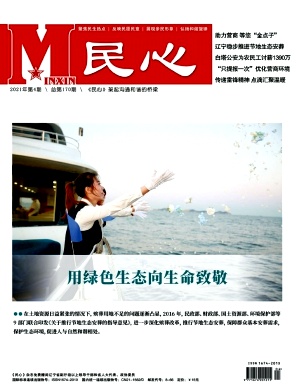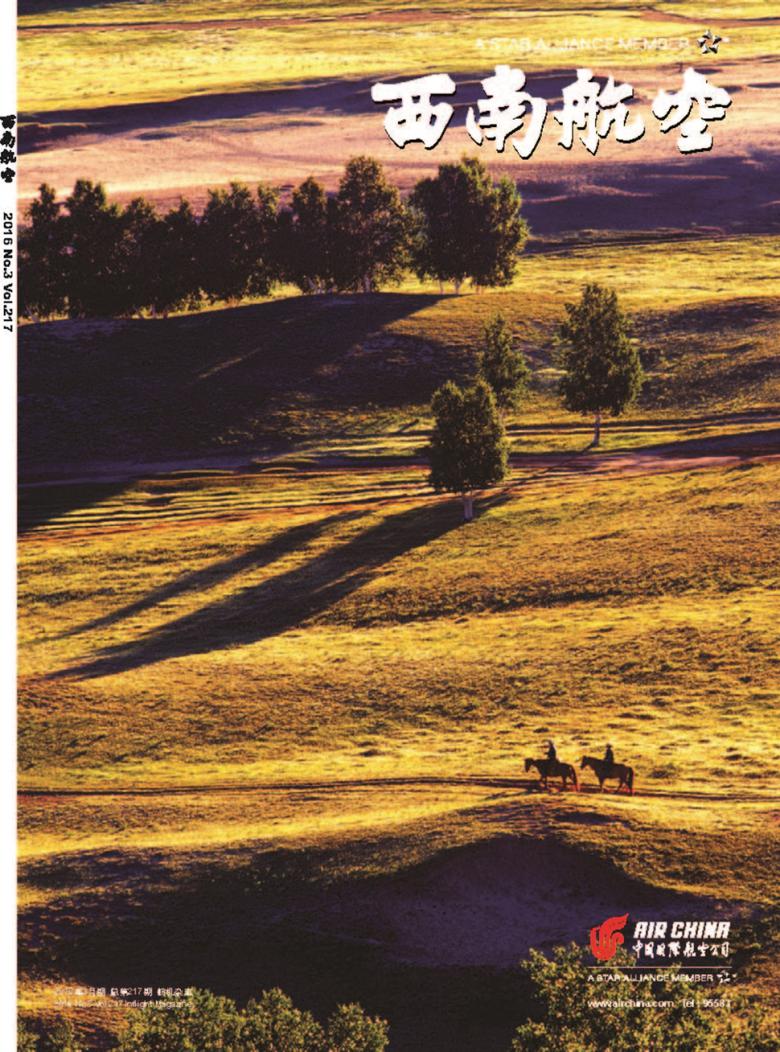當代散文理論建設的回顧與反思
未知
一、“形散神不散”散文觀的形成及其影響
“形散神不散”散文理論出現于被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者稱為“散文年”的1961年,它是“十七年時期”的社會與文學思潮、散文寫作等綜合因素所整合的結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成立之初,散文寫作上,表現為建國初期大量熱情洋溢地歌頌新生活、新制度、新建設等方面成就的特寫類散文的興盛。這種特寫類散文雖然有著可以及時、迅速、生動地報告社會生活的新人、新事、新景觀,但是在藝術形式上有粗糙之氣,摒棄了寫作者個人的抒情空間,降低了散文的美學品格。這樣,如何在一元的抒情機制里使散文“既好看又好吃”,成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誘人“菜肴”,這成為文藝界所思考的問題。1950年代中期的“復興散文”運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復興散文”運動中所出現被稱為“佳作”的散文,如楊朔的《香山紅葉》、秦牧的《社稷壇抒情》、魏巍的《我的老師》、何為的《第二次考試》、老舍的《養花》等,形式靈活,文筆優美,所表現出的是與工農兵具有“同質同構”的情感關系。經過1957年的“反右運動”,1958年的“大躍進”,知識分子自由言語的空間徹底喪失,整個國家處于一種虛幻抒情狀態,表現為對“共產主義”一相情愿式的幻想與渴望,對社會生活賦予詩意的浪漫情調。形式靈活、文筆優美的抒情類散文,成為熱愛國家、頌揚人民的有效文本,走到當代文學寫作的前臺位置。
1961年之所以成為“散文年”,它有這樣幾方面原因:一是抒情散文寫作獲得豐收,大量意境雋永、文體優美的“抒情散文”涌現出來;二是許多全國性的報紙展開對散文創作理論的討論,形成了相當的氣候,出現了為多方所激賞的“形散神不散”散文理論。換言之,“散文年”是散文寫作實踐與散文理論探索“水到渠成”的結果。總體而言,1950年代的散文研究,基本上集中到對作家作品的評論上,雖說出現了一些鳳毛麟角的探討散文特質的文章,但沒有形成大的沖擊波。抒情散文的寫作雖說隊伍擴大、作品大面積豐收,但同樣也出現寫作題材狹窄、風格單一等狀況,這樣勢必要求散文研究者對散文的概念、范疇、特征、傳統等方面內容做出相對明確的探討,以指導散文寫作實踐。應該說,到了1960年代之初,探討散文基本內涵、特征理論準備的時機相對成熟。《人民日報》專門在1961年1月28日至6月5日,在第八版開辟了“筆談散文”的專欄,發表了二十來篇文章,專門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散文的詩意、意境、結構、范疇等藝術問題。此外,《文藝報》、《文匯報》、《光明日報》、《羊城晚報》等多種報刊,也刊發了提倡、議論散文寫作的文章。這次“散文筆談” 的重點,不是討論散文生存的土壤問題,而是把精力集中到散文文體等一些技術性問題上,估計也有像一些學者所猜度的原因:“這次‘散文筆談’的策劃者盡量避開敏感的政治話題,將討論的重點放在散文的本體建設和藝術表現方面,從而避開來自政治的干預,這是頗具策略的明智做法。”
對散文“形散神不散”特征的概括和論爭,首先成為當時討論較多的話題。有人認為“散文忌散”——李健吾提倡散文的“竹簡精神”,作家師陀也提出了“散文忌散”的觀點。也有人提出“散文貴散”的觀點,把散文形容為“文學的輕騎兵,是從戰斗的風沙中跋涉過來的”、“散文是一切文學樣式中最自由活潑,最沒有拘束的”。與此同時,王爾齡在《光明日報》發表《散文的“散”》文章,也贊同散文的特點在于“散”。蕭云儒的千字短文《形散神不散》,綜合“散文忌‘散’”與“散文貴散”觀點,提出自己關于散文“形散神不散”的觀點:“神不‘散’,中心明確,緊湊集中,不贅述。形‘散’是什么意思呢?我以為是指散文的運筆如風、不拘成法,尤貴清淡自然、平易近人而言。‘像煞有介事’的散文不是好散文。會寫散文的人總是在平素的生活和日常的見聞中有所觸動,于是隨手拈來,生發開去,把深刻的道理寓于信筆所至的敘述上,筆尖飽蘸感情,時而勾勒描繪,時而倒敘聯想,時而感情激發,時而侃侃議論”。蕭云儒不光認為散文的“散”與“不散”相互統一、相映成趣,更具體地發揮了這種“神不散”的觀點,即“中心明確,緊湊集中”、“字字珠璣,環扣主題”、“形似‘散’,而神不散”。
“形散神不散”觀點是對當時文藝主潮的一種闡釋:作品的主題必須明確與集中,完全符合當時盛行的反個性主義的大一統文藝思想。《形散神不散》的短文一出現,立刻引起評論家們的重視,經過宣傳、推廣,終于構筑成當代散文的理論框架。與其說這些文章從理論上推動了當時散文寫作的發展,毋寧說是對當時散文狀態的理論總結與進一步規范,給散文的發展戴上更為沉重的“緊箍咒”,由此,所謂的“散文年”真正形成了屬于“十七年時期散文”的理論與創作模式。
在擁有具體的“形散神不散”理論指導下的散文環境中,散文“詩化”這種散文寫作的技術方法,成為散文作家們自覺的追求。當然,這種影響是全方位的、普遍的,既表現社會大眾對于“三大家”散文創作的“詩化”方式的模仿上,也表現在當代的文學教育上的一種全力引導與灌輸。就拿“十七年時期”散文對中學語文教育的影響來說,到了“撥亂反正”后的“新時期”,“十七年時期”所涌現的散文佳作,如楊朔的《香山紅葉》、《荔枝蜜》、《茶花賦》、《海市》、《泰山極頂》,劉白羽的《長江三日》、《日出》,秦牧的《花城》、《土地》、《社稷壇抒情》,冰心的《櫻花贊》,吳伯簫的《記一輛紡車》、《菜園小記》、《歌聲》、《獵戶》,何為的《第二次考試》,袁鷹的《井岡翠竹》等大量散文作品全面進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著的全國統編語文教材,成為全國中小學生所誦讀的名篇佳作。就是蕭云儒的《形散神不散》也一度進入中學語文教材,其關于散文特征的論述“形散神不散”,成為中學生必須牢記的散文特征“定律”。這種影響所造成的社會意義不言而喻。
二、對于“真情實感”的討論
1980年前后,著名作家巴金先生連續發表了《說真話》、《寫真話》、《三論說真話》、《說真話之四》、《未來(說真話之五)》隨筆文章,并在1982年把“講真話”的一組隨筆輯成《真話集》出版。巴金先生反復說“我所謂‘講真話’不過是‘把心交給讀者’,講自己心里的話,講自己相信的話,講自己思考過的話”,表現出了一位具有“五四”文化精神的老作家的社會良知。現在有人看“說真話”這個命題似乎很幼稚,其實在沒有明確的社會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說真話”并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以“新時期”之初的特定社會語境來分析,“說真話”應該成為散文寫作的最基本條件。因為能否忠實而冷靜地記述“文革”乃至“極左路線”時期的歷史現象,能否客觀地追述那些已經在“文革”中逝去的人們的歷史功過,能否真實地表達作者自己對社會生活的真實理解,這些均不是易事。
其實,“講真話”曾是當代許多作家的共同心聲。早在1962年,作家周立波主編的《散文特寫選》(1962年)序言中這樣強調:“描寫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散文特寫絕對不能仰仗虛構。它和小說、戲劇的主要區別就在這里。”秦牧說:“文學作品應當宣傳真善美,反對假丑惡”,他認為的“真”,就是“要本著現實主義的態度寫作,反對弄虛作假,反對粉飾太平,反對掩蓋矛盾,反對誆誆騙騙”。可以看出,長期以來散文的“真實性”問題,一直被視為散文不可動搖的基石和不容偏離的創作原則。眾多作家對于散文“真實性”原則的強調,主要是捍衛最基本的寫作權利。這里既有對當代散文創作中長期出現的“假大空”、“假嗓子”的不滿,也有對于散文生存語境的反思。
80年代后期,林非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提出散文的“真情實感”問題,他指出:“散文創作是一種側重于表達內心體驗和抒發內心情感的文學樣式,它對于客觀的社會生活或自然圖景的再現,也往往反射或融合于對主觀情感的表現中間,它主要是以內心深處迸發出來的真情實感打動讀者。”林非這里反復強調“真情實感”對于散文創作的重要性,認為它是散文審美價值觀的核心問題。
林非引出的對散文“真情實感”探討的話題,成為新時期以來散文研究界長期糾纏不清的問題。樓肇明認為:“‘真情實感’是一切文學藝術創作的基礎,它在掃蕩‘瞞和騙’的文藝中是立了功勞的”;“其二,‘真情實感’論因過于普泛,不可避免地非文學、非藝術的因素也一古腦地全包含了進來”;“其三,真情實感,本身包含著若干層次,又人和人不盡相同,這樣就為相對主義留有藏身的洞穴”。陳劍暉也認為:“‘真情實感’是可以作為散文的本體范疇和對散文的文體進行規范的,它的功勞也是別的散文概念所不能代替的”“問題在于,我們充分肯定這一散文范疇的同時也應看到:首先,散文雖是‘表現自我’的‘主情性’藝術,但它的情感抒發和小說、詩歌的情感抒發有著較大的區別……”;“其次,感情有文學的因素,也有非文學的因素;有具備很高審美價值的真,也有毫無藝術意義的真”;“再次,還應注意到,感情還有‘大’、‘小’和‘高’、‘低’之分,這是就散文的情感質量而言。事實上談論散文的情感,必然涉及作家的主體人格結構、思想涵養、文化心理等因素”。那么,“真情實感”是不是散文的內核,是不是散文創作的靈魂?我以為應該這樣回答:“真情實感”仍是文學進入審美需求的最基本的層次,它是一種外在現象,“真情實感”的內核應當是“個性”精神,正如郁達夫所言:“散文的解放,第一要寫‘散文的心’”,“散文的心”就是散文創作者所釋放的“個性精神”,而這種充分與自由的個性精神的釋放,必須有足夠的社會條件來保障。
探討散文在技術上可否進行“虛構”的問題,也是對于散文“真情實感”的討論邏輯必然。90年代初,秦晉堅持認為:“從接受美學的角度,散文如果描寫不是關于實際發生的事情,而是關于可能發生的事情,讀者就會出現閱讀障礙……如果越來越多的人在散文中像小說一樣虛構事實情節,那無疑是‘自毀長城’,失去疆界的散文也就失去了散文自身。”秦晉對于散文“真實性”的討論,已經不是簡單層面的情感訴求了,而是上升對于散文特質的探討了。可是,陳劍暉卻認為:“從散文的創作規律和散文發展趨勢來看,要使散文所描寫的內容與作者的‘個人經歷’完全吻合幾乎是不可能的”;“在我看來,只要我們把握好‘真實與虛構’的‘度’,既不要太‘實’又不要過‘虛’,則散文的‘真實性’這一古老的命題便有可能在新世紀再現它的原有活力。”
其實,我們完全不必在“真實性”問題上糾纏不休,“真實性”就是現代散文不容動搖的特質之一。現代散文具有“現代性”、“真實性”、“自由性”三大特質。所謂“現代性”就是一種表現為科學、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權利、法制等普遍原則的現代意識精神;“自由性”,既是散文寫作者心靈的最大自由,也是散文文體的自由,呈現一種開放的態勢;而“真實性”就是寫真相、表真情、訴真心,散文中所涉及到的人和事都必須是真實的,不能虛構和杜撰。也就是說,散文的“真實性”所符合的原則是真人、真事與真實的時空場景,但是作者在真實時空中包括想象、幻覺等心理體驗,則不能以簡單的“真實性”來加以限制了,因為人的思維具有“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功能。如果否定散文中的合理想象,某種意味上也就是否定散文的“文學性”特征。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講真話”是對散文生存環境的強烈質疑,是對散文作者自我權利的捍衛;而“真情實感”論,已經上升到對于散文本體特點的探討上;對于散文“虛構”的討論,雖說停留在散文寫作的技術層面的討論,但因為涉及到散文的本質性內涵方面,仍能吸引人們的關注。
三、對于“形散神不散”的質疑
和對于“三大家”的重新審視
1980年,松木在《語文戰線》1980年第8期發表《“形散神不散”質疑》。此論文主要從散文文體的角度來深入探討散文的特點,對“形散神不散”理論進行大膽的質疑,開啟了新時期對于“形散神不散”理論的重新認識之門。到了1980年代中期,散文研究界對于“形散神不散”批判之風日盛。這些研究文章對“形散神不散”的批評角度不一,對“形”與“神”的解釋亦各有出入,但如同樓肇明所指出的那樣,“基本上都認為‘形散神不散’說對散文寫作主導造成境界狹窄,主題單一之弊,促使散文寫作單一化、格式化,束縛了散文藝術追求,是一種封閉的體系規范”。需要指出的是林非的《散文創作的昨日與明日》,不僅僅從文體角度加以探討,更重要的是他注意到“形散神不散”與特定社會政治文化的契合性,抓住了其實質問題進行批判。“(形散神不散)這個主張自覺不自覺地表達了我們當時一種相當盛行的文藝思想:作品的主題必須集中和明確(這其實是古典主義式的藝術趣味)。短論《形散神不散》具體地發揮了這種‘神不散’的主張,即‘中心明確,緊湊集中’,‘字字璣珠,環扣主題’,完全符合于當時盛行的這種文藝思想,所以它得到廣泛的流傳是可以理解的”、“追求單一化和模式化,必然會使散文創作陷于僵化和停滯的境地;只有沖破單調和模式的多樣化的趨勢,才有可能使散文創作得到充分發展和繁榮”,這種分析令人信服。
由于“形散神不散”觀點出現于1960年代,當代散文研究界要質疑這個散文理論,就勢必要對形成此理論的經典作品進行重新審視。因此,對于楊朔、劉白羽、秦牧“三大家”的重新審視,也成為“新時期”散文研究的一道風景。
1、對于楊朔散文創作的再評價。對楊朔散文寫作的“再評價”問題,當代散文研究界在1980年代之初就開始了,也已經觸及到楊朔散文的弊病了。1984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吳周文《楊朔散文的藝術》,是較早出版的楊朔散文研究的學術專著。吳周文認為,楊朔詩化散文的理論所指導下的創作實踐,使其作品在意境創造、藝術構思、人物描寫、結構藝術、文學語言和個性風格等方面,形成了與眾不同的藝術個性,比較完整地構成了他的散文美學,形成了“楊朔體散文”。吳在論及楊朔散文缺點時也認為,在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楊朔散文仍沉浸于光明的歌唱,他沒有能夠很清晰地觀察、體驗、研究、分析現實社會的許多矛盾,更深一步地去發現與研究當時的方針、政策和路線存在的“左”的問題。這使他的散文存在思想方面有偏離現實主義的傾向;而在藝術方面,由于刻意追求“巧”的構思,也使他的不少散文結構雷同。
1980年代后期,佘樹森從宏觀角度論述了楊朔現象出現的社會原因。認為1950年代中的散文“復興運動”及60年代初的“詩化”,是對40年代散文通訊化的反撥。由于政治功利觀念的主導與制約,楊朔散文形成了“強化群體意識而淡化個體意識的‘載道’精神,托物言志(包括借景抒情)的表現方法,以及‘三大塊’的結構形式”,導致了“散文創作上題材的狹窄,真實品格的貶值、藝術形式與風格的單調”,并由此走上了“模式化”的路子而束縛了散文的發展。
1990年代初,溪清、渝嘉認為“楊朔散文致命的弱點恰在于‘自我’的弱化,‘主體意識’ 的隱蔽”。我的理解,類似這樣的評價似乎“有站著說話不腰痛”的感覺。試想,整個社會尚對于“個性”封殺的特定年代,楊朔作為一介文人,他有何力量與整個社會對抗?他只能順應形勢,并在順應形勢中進行力所能及的及時調整,追求在形式上“詩化”的突破;再之,單就楊朔的出身和成長經歷而言,他已經經過革命之風的熏陶,成長為一名革命戰士,又怎可能走“個性化”之路?
而吳周文在其著作《散文十二家》的自序《“楊朔模式”及其悖失態勢》中進一步分析“楊朔散文現象”的成因與影響,并指出:“如果說,十七年散文因說真話抒真情美學原則的弱化以致喪失而形成了散文創作一統化的審美思維方式,是‘楊朔模式’的第一層含義;那么楊朔和眾多散文作家在藝術表現的詩意傾向與追求,則是‘楊朔模式’的又一層含義”。應該說,吳周文的觀點擺脫了就事論事的簡單分析,而是通過“楊朔現象”來把握整個當代散文的走向問題,其觀點更有深度與新意。
2、對于劉白羽散文創作的再評價。早在1960年代,井巖盾認為,劉白羽散文的優點是包含的感情比較豐富,他能以熱烈的感情、生動的形象賦予戰斗的思想以感人的力量;同時,他的散文又兼含意境的清新和文辭的優美。不過,他認為劉白羽散文的缺點在于有些概念化,同時在文字上功夫也不夠。這可以說是較早注意到劉白羽散文缺點的論文了。
到了1980年代,對劉白羽散文創作研究逐漸深入,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論著。當然,這些研究性論著主要是研究劉白羽散文的特點為主。也有研究性論文在指出劉白羽散文優點的同時,進一步分析其散文創作的缺失。如鄭鍬稱贊劉白羽散文“如飛瀑,如奔馬,感情豪放,境界壯闊,氣勢沉雄,給人昂然向上的力量和一種奇偉、剛健的美的享受”。不過,他也批評了劉白羽散文議論過多的缺點。認為,劉白羽力求在幾千年散文傳統和五四以來散文傳統的基礎上,創作“我們時代的新散文”,主要表現在他要把先進的革命思想引進作品中來。這是造成劉白羽散文過分強調思想性與政治標準,而忽視散文藝術美的原因。溪清、渝嘉也認為劉白羽散文,“看起來,表現的是‘個性’,但實際上‘共性’的成分很濃;抒發的是‘個性’感情,但實際上‘階級’的感情比重更大”。應該說,這些分析還是切中肯綮的。
3、對于秦牧散文創作的再評價。秦牧散文融說理、敘事、抒情為一爐,使知識性、思想性、藝術性相結合,借談天說地、辨析名物之方式,來寄寓對人生的褒貶。同樣,早在1960年代,研究者對于秦牧散文的評論主要集中在作家觀察生活與選取題材、藝術手法、語言應用等方面的獨特性上認為秦牧散文的特點在于其“思想性、知識性、趣味性”。到了1980年代,隨著對秦牧散文創作研究的深入,出版了不少有著真知灼見的研究論著。研究者的主要著眼點開始轉向對于秦牧散文創作的總體得失反思上。溪清、渝嘉認為:“他的散文接近于周作人、林語堂、豐子愷的一路,但‘知識性’被推到了極致,語言的‘趣味’實已不足,‘感情’的調和則尤欠功夫,這就大大影響了他的藝術成就”。循著這個思路,劉錫慶在1990年代后期為中進一步指出,秦牧散文是《講話》所孕育的“新散文”表現形態之一——以“談天說地”的軟性題材,以富于知識趣味的健康情調和明快、暢達的輕松文筆所寫出的一種新型的、大眾化的隨筆。其根本缺點在于用“知識”替代了“自我”,也喪失了抒情的自性,從而使得他的作品未能超越“知識小品”的藩籬而進入“藝術散文”的殿堂。有意味的是,劉錫慶先生始終是以“藝術散文”的鋼圈來套當代散文作品,這種方法的確有些捉襟見肘的尷尬。事實上,散文的現象具有豐富性,一味地要求其表現“個性”,那豈不是一相情愿的事?
還有1990年代中期,林賢治在中更是給秦牧下了危言聳聽的判詞:“對個性的遺棄:秦牧的教師和保姆角色”。他決然認為,秦牧并非文學史所稱譽的“散文大家”,而是“一個思想貧乏而語言平庸的作家”。他之所以獲得了與其實際水準不相符的地位,是因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寫作有兩個死結:一是降低了標準,一是放大了成就”、“一個統一有序的社會,必然要成批生產與之相適應的作家……而且,必然要從中推舉出某位代表人物,極力樹作優秀的典型,以期群體仿效,免得標新立異。制造優秀,是政治手段在文學方面的運用,是政治入侵文學的眾多現象之一”。批評不是作秀,任何脫離作家生活的社會現象而強作家所難的批評方法應該為我們摒棄。事實上,在一個整個民族整體“失語”的社會機制里,即使有個性的作家又將如何?文學批評的目的也不是嘩眾取寵,而是認真地總結文學的經驗與教訓,更好地啟迪未來。
四、1990年代消費環境中的幾種散文觀念
早在1980年代,一些研究者對長期背負著“形散神不散”精神枷鎖前行的當代散文產生深深的失望。有人認為“散文已趨于解體”,當代散文“以廣泛的蕭條來慢待這個對文學充滿厚愛的時代”,“走的是一條下坡路”;在“舊有‘散文’概念的內涵已經分化完畢”的今天,“‘散文’作為一個文學概念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和價值”;還有人認為“一直被誤作文學的散文”,“已完成了它的歷史文化使命,它應當壽終正寢了”,“當代文學不再需要散文”。
可是,散文沮喪地告別1980年代,來到1990年代后,卻出現了人們事先所沒有料到的“散文熱”現象。1990年代,我國進入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快速轉型的社會時期,人們的生存狀態日趨復雜。生活的多樣性和多變性給人們帶來了更多表現情感與思想的訴求,散文這種最善于直接表現人們真情實感的文學樣式,正好就承擔了這一使命。各種隨筆類圖書的銷量一路看好,刊載承載百姓情感的都市平民報紙一時走紅,眾多作家紛紛轉型,專門報紙、刊物的隨筆寫作。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要求散文求新、求變的“大散文觀”的聲音。
在1990年代較早提出“大散文”概念的是賈平凹。1992年《美文》雜志創刊時,賈平凹作為主編旗幟鮮明地提出“大散文”概念。他說:“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隨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為何提出這樣一個概念呢?賈平凹當時是有現實考慮的,“我們確實是不滿意目前的散文狀態,那種流行的,幾乎滲透到許多人的顯意識和潛意識中的對于散文的概念,范圍是越來越狹小了,涵義是越來越蒼白了……”因此,“我們的雜志擠進來,企圖在于一種鼓與呼的聲音:鼓呼大散文的概念,鼓呼掃除浮艷之風,鼓呼棄除陳言舊套,鼓呼散文的現實感,史詩感,真實感,鼓呼更多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屬于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的散文”。“大散文”概念的提出,是針對流行于當時社會上的那些僅限于花花草草、借景抒情的抒情散文的。也就是說“大散文”的概念盡管籠而統之,但作家更注重一種風氣,一種關注社會的境界。因此,作為散文期刊的宣言的“發刊詞”,對于“大散文”的鼓與呼,無疑是當代散文創作求新求變的催生劑。
“大散文”概念提出后不久,就遭到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錫慶先生的反對。他先是在《當代散文:更新觀念,凈化文體》中提出了“凈化文體”的觀點,認為散文的文體特點是“自我性”、“內向性”、“表現性”,提出“創作‘主體’以第一人稱寫法和真實、自由筆墨,用來抒發感情、表現個性、裸露心靈的藝術性散體短文,即謂之散文。”他用更為隨意性的解釋進行翻譯:“散文就是更本色、更自由地表現自己”;“散文即個性和心靈的赤裸”;“散文是作者性靈(獨特個性)的自然流露和自由展現”;“散文即自我心靈美、人格美的本質‘對象化’”等。他還對散文的審美“特征”加以規范,提出四個特點:“篇篇有‘我’,個性鮮明”;“外物內化,以小見大”;“真實、自然,筆墨自由”;“紙短韻長,風格各異” 。后來,劉錫慶在進一步展開對中國現當代散文流變史的把握的論述中,強化其“散文凈化”觀。
劉錫慶文章資料豐厚翔實、論述嚴密自恰,其征引考辯、爬剔、梳理的實證功夫和務實風格,實為諸多散文研究者所不及。然而,他的“凈化文體”觀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散文本身就是“文類”的問題,而不是“文體”的問題。二是散文的基本特點是“有神無形”,其“形”之豐富,非其他文體所能比。散文過于“凈化”,導致了所謂的“藝術散文”才是“散文”,其他散文不是散文。他連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散文熱”都視而不見,認為“從藝術散文的觀點來看,散文并不‘熱’;不僅不熱,還有些‘冷’呢”。這樣嚴格的“門戶清理”,只能造成散文品種的單一。因此,正如陳劍暉所指出的那樣:“無視90年代散文的繁榮主要是思想隨筆繁榮這一基本的文學事實,而偏執于‘藝術散文’這一隅,一味追求散文的凈化,這無論如何是難以令人茍同的,也無益于當代散文的健康發展。也許正是這個緣故,劉錫慶的‘凈化’ 理論發表后便一直遭到世人的詬病”。也有學者指出:“搞‘文體凈化’充其量也不過是在技巧修辭層面做些調整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散文理論家的樓肇明先生在對20世紀中國散文進行歷史評判的基礎上,與人合作編輯“當代散文潮流回顧·寫作藝術借鑒叢書”,對當代散文寫作潮流進行扎實而細致的案例研究。他提出散文最基本的三個本質規定是:“散文的文化本體性”、“與史與哲學相綰結的思維性”、“審美變革中的前驅地位”。在對散文本體研究的基礎上,他還提出“復調散文”的概念,即:“一是維度的改變,不再是一件事,一種情感、一個道理;二是一個主題包括二個母題、一個意象包含二個縮影,在兩個層次、兩個側面展開;三是宏觀時空和微觀時空碰撞,兩個敘事人,雙重視角;四是七嘴八舌,敘事人非常隱蔽”。他還認為“復調實際上是對完整的要求。藝術的根本原則是經濟原則,復調散文就是要求在一定的篇幅內表達比較多的內容,它要求作者改變以往那種唯我獨尊的寫作態度,召喚讀者參與作品的完成”、“要打破這種近乎宿命的循環,就必須提倡思想者、學者和詩人的三位一體,提倡復調散文”。樓肇明將散文寫作的主體——作家定位在思想者、學者和詩人,集三位于一體,視散文文本為思、史、詩的三維于一身。在這三者中,思是靈魂,史是骨架,詩是主觀形態或承載方式。他心目中的最高境界的散文是文化、歷史、哲學與詩性完美結合的散文。他認為“散文的文化本體性的核心部分,即在于重鑄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性格,或者說是旨在創造性地轉化民族文化性格”。應該說樓肇明先生“復調散文”觀的提出,就是對于我國消費文化環境中文化缺失現象的回應,要求散文必須負擔起“重鑄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性格”的使命,而不是一味地成為大眾情感的消費“甜點”。然而,他將散文寫作主體的定位于“思想者、學者和詩人”,雖然是出于一種美好的愿望,但似乎也有些不切合實際。其一,散文本身就是社會情感與思考的載體,它的門檻很低,只要有情感有思考,誰都可以涂抹幾筆,不是說只有思想者、學者、詩人能夠寫作,而一般的普通大眾就不能表達自己的心聲;其二,在人心浮躁的市場經濟年代,人們以追逐利益的最大化為目的,許多“思想者”熱衷于制造“噱頭”而沽名釣譽、許多“學者”熱衷于制造“泡沫學術”、許多“詩人”熱衷于進行“下半身寫作”之時,他的這種“空谷清音”又有幾人能夠善于傾心聆聽呢?
正如美國學者杰姆遜所指出的那樣:“文化已經大眾化了,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純文學與文學的距離正在消失。商品進入文化意味著藝術作品已經成為商品,甚至理論也成了商品……總之,后現代主義的文化已經從過去那種特定的‘文化圈層’中擴張出來,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成為消費品。”文學的生產同樣受制于文學的消費,受制于為文學消費所服務關聯的如市場、讀者、出版、發行相關環節,而批評者的引導只能占到很小的比重。也就是說,廣大的作者更愿意投市場、投讀者所好,也不愿意讓批評家的頤氣指使。對于1990年代的散文寫作者來說,他可以不考慮何為“大散文”、何為“藝術散文”、何為“文體凈化”這些理論家們所設定的問題,可是絕對不會忽視社會的需求。也就是說,面對消費市場,散文理論家、批評家越來越處于一種“無能為力”的尷尬境地。散文一方面朝著“形而上”學識與思想的高度挺進,涌現出諸多標識“思想散文”、“思想隨筆”、“文化散文”、“文化隨筆”、“學者散文”、“學者隨筆”、“學術隨筆”等散文的風行于市;另一方面也可能朝著如“小女人散文”、“生活散文”、“媒體散文”、“城市散文”、“經濟散文”、“網絡散文”等更能從容不迫地表現平民百姓閑適情感與希冀的散文內容靠近;當然,這種散文的探索,還可能出現類似“新潮散文”、“女性散文”、“新生代散文”等在形式和內容上具有探索精神的散文形式。可以這樣說,1990年代各種眼花繚亂的散文概念的背后,是不同檔次、不同規格的文學、文化期刊上各類鋪天蓋地的散文作品,是書店里琳瑯滿目的充斥著人們視野的散文隨筆類圖書。
注釋:
(1)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53頁。
(2)秦牧:《散文領域——海闊天空》(《文藝報》1959年第14期);吳調公:《什么是散文》(內蒙古《語言文學》1960年第2期)。
(3)(38)陳劍暉:斷裂中的痛苦與困惑——20世紀散文理論批評評述[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第55頁,第52頁。
(4)李健吾《竹簡精神——一封公開信》,《人民日報》,1961年1月30日。
(5)師陀:《散文忌散》,《人民日報》,1961年2月27日。
(6)柯靈:《散文——文學的輕騎兵》,《人民日報》,1961年2月28日。
(7)王爾齡:《散文的“散”》,《光明日報》,1961年4月23日。
(8) 蕭云儒:《形散神不散》,《人民日報》,1961年5月12日。
(9)巴金:《隨想錄》,新知·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87年第506頁。
(10)秦牧:《三十年代的筆跡和腳印》《秦牧全集》(2),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327頁。
(11)(19)林非:《散文創作的昨日和明日》《文學評論》,1987年第3期,第37頁,第39—41頁。
(12)(18)樓肇明等:《繁華遮蔽下的貧困——九十年代散文之路》,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5頁,第144頁。
(13)(16)陳劍暉:《中國散文理論存在的問題及其跨越》《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第145頁,144頁。
(14)郁達夫:《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圖書出版公司,1936年,第4頁。
(15)秦晉:《新散文現象和散文新觀念》《文學評論》,1993第1期,第133—134頁。
(17)喻大翔:《散文觀念更新談》(《散文世界》1986、7)、《歷史與現實:形散神不散》(《河北學刊》1988、1),王堯《散文藝術的嬗變》(《當代文壇》1986、5)、葉公覺《新時期散文發展淺說》(《當代文藝探索》1987、1)、郭風《關于“形散神不散”》(《解放日報》1988、2、25)、楊振道《散文藝術形象的形神統一》(《河北學刊》1988、2),以及林非《散文創作的昨日與明日》(《文學評論》1987、3)。
(20)張明吉《談楊朔散文的不足之處》(《光明日報》1982、8、19)、創淮《成就與局限》(《光明日報》1982、9、10)。
(21)佘樹森:《當代散文之藝術嬗變》,北京大學學報,1989第5期,第6頁。
(22)(27)(30)(37)溪清、渝嘉:《當代散文縱橫談》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42頁,第84頁。
(23)吳周文:《楊朔模式”及其悖失態勢》,《散文十二家》,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8頁。
(24)井巖盾:《評〈冬日草〉和〈平明小札〉》,《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
(25)如胡樹琨、譚舉宜著《劉白羽作品賞析》(廣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孟廣來、牛運清編選《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劉白羽研究專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牛運清著《劉白羽評傳》(重慶出版社1995年版);朱兵《劉白羽評傳》(百花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26)鄭鍬:《他歌唱紅日和大江——漫談劉白羽的散文創作》《福建師范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
(28)杜埃《論秦牧的散文——〈花城〉讀后》,《文藝報》1962年第12期,收入《筆談散文》1980年版;易征、張綽、關振東《十里花街——談秦牧的散文》,《上海文學》1962年第4期)。
(29)林湮選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秦牧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陳其光、陳碧秋《秦牧散文欣賞》(廣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張振金《秦牧的散文藝術》(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等。
(31)張炯等人主編:《中華文學通史》第10卷“當代文學編”,華藝出版社,1999年版。
(32)林賢治:《對個性的遺棄:秦牧的教師和保姆角色》文藝爭鳴,1995年第3期。
(33)王干、費振鐘:《對散文命運的思考》《文論報》(石家莊),1986-7-21。
(34)黃浩:《當代中國散文:從中興走向末路》《文藝評論》,1988年,第1期。
(35)(39)王聚敏:《散文文體凈化說質疑》,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
(36)如《世紀之交:對“散文”發展的回顧與思考》(《文學評論》1997、2);《當代散文創作發展的幾個問題》(《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1、1)。
(40)樓肇明、老愚主編:《當代散文潮流回顧·寫作藝術借鑒叢書》共六種,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41)(43)樓肇明:《文化接軌的航程》,樓肇明、老愚主編“當代散文潮流回顧·寫作藝術借鑒叢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頁,第5頁。
(42)樓肇明、老愚:《散文從單調走向復調》,中華讀書報,1996-7-31第5期,第5頁。
(44)[美]弗·杰姆遜著,唐小兵譯:《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48頁。